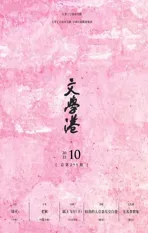手艺里的生活
2023-10-07陈纸
陈 纸
我想象着,在南瓜花的时间里,开出一朵朵黄色的喇叭。喇叭被时间浸泡着,慢慢地,长成果实。记忆将果实切开,从里面蹦出形形色色的人来。南瓜伏在村口的墙根,与我一起数着他们,一个个走进村子里,有做衣物的裁缝,有造家具的木匠,有建房子的泥水匠,还有篾匠、铁匠、剃头匠,当然还有油漆匠、补锅匠和弹棉花的……他们一律被当时的人们称为 “手艺人”。当时的“手艺”,甚至就是“饭碗”的代名词。而如今的人们,则时髦地称他们为 “工匠”,工匠精神也被时人炙手可热地捧为最富时代感的褒义词。
时光如书页般翻动,泛着微黄的底色,在秋日里浮现。每一个身影,每一个动作,在我的记忆中烙上了一圈光晕。光晕下的图像,总是那么生动地存活着。关于手艺人,以及在手艺人影响下的生活,互为映照,互为烘托,一幕幕,一桩桩,串联出生活的质感,令人久久地回味。
“为自己寻找一名可靠的女友,/那并非依仗数量称奇的女友。/我知道,维纳斯是双手的事业,/我是手艺人,我懂得手艺。”——茨维塔耶娃说她是手艺人,她用诗歌创造了复杂的人性之美。我庆幸,我也是写作者,而且,至今仍然用笔在纸上写。笔迹的外观直接表达了我的本质与品性。从这个特征上说,我不但是手艺人,而且是 “传统”的手艺人——这是我的幸福,也是我的骄傲。
俗话说:天旱三年饿不死手艺人。记得小时候,农村人对手艺人保持着足够而持久的羡慕与敬畏。手艺人在人群中是最体面的一个。村里人如果要为自己的孩子找个光明的前景,就送他去学一门手艺。父母为自己的女儿找个好男人也是说:对方有一门手艺呢!我作为男孩,曾经躲在被窝里私自暗想:像我这等手无缚鸡之力、身无所长之人,如果能找到一个女手艺人做老婆那就再好不过啦。但车水马龙,人来人往,手艺人中女的真是凤毛麟角呢。当然,有的手艺以女的居多呢。
裁缝
小时候,在老家,裁缝师都是女的。在我看来,她们都是世界上最干净、最高雅、最手巧的女子。在我心里,也是最圣洁的。我甚至羞怯得不敢靠近。就连被母亲推到她们面前量体裁衣,也是半推半就挪着碎步,连正眼都不敢看她们。
最兴奋的声音啊,母亲在历经了两三个年头,终于在某一个年底说出了那句:请裁缝来做几件衣裳吧。日子一下就崭新了起来,太阳格外灿烂。母亲似乎从来不问我要什么款式、什么颜色,也不问我想做几件、想做几套。那时候,还有得选择吗? 关于布料,我更加一无所知。大人口中得意相传的 “的确良”,我也是在上了初中后,在偶尔读到的课外书中见识了这三个字。它也成了那个年代披在我身上最尊贵的字眼。那的确良的确凉啊,像某种动物的皮肤摩擦着我的皮肤。初穿时,身上像要起鸡皮疙瘩,适应起来花了几个礼拜。而且,的确良不好擦汗,似乎不怎么吸水,于是,就怀念之前的粗布褂子。母亲从我不自在扭动的身子上看出了我的心情,她问:做小了? 她拎拎双肩,扯扯下摆,说:不小哇,大小长短合适。我也连忙摇头,生怕亵渎了裁缝的手艺。母亲嗔了我一眼,又说:鸡婆坐不得轿,坐在轿上会赖尿。意思是:我不习惯穿这种高级布料——的确如此啊!
记忆中,母亲请一位裁缝到家来做衣服是一件很庄重、很慎重、很重要的事情。谁的手艺好,请哪位来,什么时候请……她提前三四个月念叨,都还没做好决定。其实,方圆几个村庄,会量体裁衣的也就四五个,母亲郑重其事的结果是无所选择,只得在来村里做的裁缝身后排队等候。当缝纫机前一晚搬到我家来后,当夜,母亲就用两条长凳架起了两块木板,放在最靠近大门的地方,标榜着她家正发生大事、好事、喜事。
第二天早上,她迎来裁缝师,从卧室的衣柜里捧出一手新布来。裁缝将皮尺搭在肩上,一边翻着一叠叠新布,一边认真地听母亲说哪块布做谁的衣服,哪块布做谁的裤子。听完有底了,量好每个人的身材,便是一笔一划地画线,一刀一剪地裁剪。然后,就踩着缝纫机“嗡嗡”响起来。
熨斗在淡淡的汽雾中游走,日子也在艰难中前行。吃饭穿衣是多么重要啊。所以,这乡村的裁缝自然是手艺人中最重要的匠人之一。她衣着讲究、知书达礼,用赤橙黄绿青蓝紫的布料,为他人装点门面,自然也最能赢得尊重。这门手艺甚至可以说是尊贵呢。传说明朝嘉靖年间,京城有位裁缝,官员们都爱找她设计和缝制衣服。因为她深谙官场与人性。对升迁的官员,因为意气风发、谈笑风生,身体略往后仰,衣服就做得前面长一点后面短一点;对贬谪的官员,因为垂头丧气,弓着腰身,衣服就做得前面短一点,后面长一点;对连任的官员,因为心态平和,身体保持自然姿势,衣服就做得前后长短一致……她这一精妙的 “算计”,官员对她佩服得五体投地,生意自然也就应接不暇。
木匠
现在,不管隔多久回一次老家,一旦踏入门槛,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大厅中央的那张灰黑的饭桌。奔波在外十几年,最想坐在老屋里,彻彻底底地放下繁杂,寻味最初的人生感受,于是,本能地拉过一张小板凳,放在饭桌边,妥帖地将屁股放上去,头枕臂,舒服地扑在饭桌上。
侧起耳朵,仿佛有木头跑出来,各种各样的,长长短短、大大小小、方方圆圆,松树的杉树的樟木的……无一例外,都 “沦落”到工匠的手中。刀劈斧削,凿子深掘,刨子飞奔,利锯穿梭……最熟悉的,最难忘的,还是师父训徒弟的声音,仿佛还在耳畔。
如今,那些声音淡淡稀疏。只是,村里的陈梅根老了,跟了他几年的学徒陈检根仍在村支书的位置上操劳;只是,我表哥邓友根早已丢下了那一手精湛的手艺,而全部交由 “隆隆”的切割机和拼接机处理胶合板了。就在我写下这篇文章的前一个星期,执了一辈子斧头的我的姑父杨明亮也去世了。我与他、以及他曾经的徒弟儿子杨永安已经有近十五年没有见面。
木匠这门手艺里,斧头是把比墨斗与墨线还严格的 “标尺”。如果是徒弟,斧柄不能完全卯进斧眼里,要预留一寸。记忆中,来我家做木匠的,一般都是两人,一位师父、一位徒弟。徒弟刨子推不平、拉锯跑了线、砍斧过了头,便常常招来师父的提醒。我还听见不留情面的谩骂,甚至看见父亲扬起斧头要砍儿子、哥哥抡起尺子打弟弟的头,想着自已将来可能会做人家徒弟的遭遇,吓得在旁心惊肉跳。
据说木匠学徒三年,学会了使用各种工具,学会了家常木头的制作,便可出师。只可惜,陈检根、杨永安跟了师父几年后均没有坚持下去。表哥邓友根出师后倒是炙手可热,被到处请去做工。母亲很得意,说自己家里出了一位远近闻名、心灵手巧的工匠。从此,我家里大大小小的家具都叫她侄子来做。有时,母亲暗自嘀咕:想不到他没读几年书,小学没毕业,做木匠手艺那么好!停了两三秒钟,她接着补充:他摸的那几样东西实在好,有样子,又结实……
记得有一年冬天,表哥邓友根在我家做木匠,屋外大雪纷飞,我拎着两根刚踩断的高跷回到家。母亲接过那两根棍子正要往灶火里丢,表哥见了,马上说:不要烧了,可以做两个小凳子的腿呢!表哥接过断了的那两根棍子,量了量,削了削,刨了刨,不到十分钟就装在了小凳子的下方,成了两条支撑有力的腿啦。
据说,耶稣的父亲是木匠。我想,他是在怎样的条件下掌握了这门手艺的呢? 哲学家斯宾诺莎被教会和家庭驱逐后,坐在一栋封闭狭窄的阁楼里一边苦思冥想,一边磨制着镜片。现在想来,究竟是磨制镜头时成就了他的思想,还是思想造就了他的手艺呢?
铁匠
一般在冬季农闲的时候,还没走进村里的祠堂,便能听到榔头在铁板上急促而有节奏的敲打声——它们夹着热气及火星汇入冬天的寒风,借此表明那些昔日握在农人手里或压在农人肩上的铁的农具趁着休息的当儿又要厉兵秣马、锤炼自己,以便在开春之时再开赴战场。
在来村里的所有手艺人中,也许数铁匠最辛苦,也是最讲火候的。风箱拉起,炭火燃得呼呼生风,火炉上,铁匠师傅将烧得红彤彤的铁夹到铁架上锤打,再冷的天气,也是满头大汗,再洁净的环境,也是全身屑灰。一件农具,吃到土地里很简单,但用得是否得心应手,农人们最清楚、最有体会,这其中的原因又与铁匠师傅的手艺休戚相关。
打造一件农具,包括选料、烧火、锤打、成型、淬火、打磨、制作等十几道工序,我们这些毛孩子在旁看着热闹,却看不出其中的奥秘。长大了才知:比如烧火,火太大,会把铁板烧穿;火太小了,铁片又打不开。比如淬火,也是打铁中的精华部分,只有经过特殊的淬火工艺,菜刀、锄头才会锋利,而且经用。但这些似乎还不够,我时常听到父母埋怨锄头或镰刀不好用,说:偷工减料,钢放少了。
打铁需在开阔的地方,断不能在哪家哪户,以免火星四溅殃及四周;又不能在户外,怕风吹雨淋影响炭火燃烧。所以,村里的祠堂是理想之所。祠堂不但开阔,可容纳七八百人,屋顶也高,任由火星四溅,自由驰骋。而且有天井,天井直接对接着天空与雨水,天井四角均有水缸伺候接水,如恰逢雨季,还不用去井里打水,水缸蓄水即可做淬火之用。
打铁光有师徒两人太孤独,光有 “叮当”之声太寂寥。得有穿梭之人,拿各种铁具进来,生意方能兴隆,还有来取打好的农具之人,财源才能滚滚而来。偏偏不管来送的还是来取的,都不肯轻易走。于是,人越围越多,闲话也越扯越多。来的人都是男人,扯的话题都是男人经常聊的。无非是农具如何如何好用,田里收成如何如何。如果聊到哪把菜刀如何如何,那就要借他老婆的嘴说如何如何。再如果聊着聊着脸上泛起了似笑非笑的表情,那一定是聊到男女之事,打铁的人锤子落下去也似乎更快更重更猛。
我们这些小屁孩也爱凑打铁的热闹,因为那里有炭火啊,熊熊燃烧啊,散着热啊。屋外冷,这里多暖和啊。虽然大人的话不能全听懂,但打铁人的 “表演”能吸引我们的目光。有的调皮鬼还会趁着风箱没人拉时,上去乱扯两下,让打铁人抡着铁锤追了两步吓唬吓唬他。
现在,已二三十年没见打铁的啦。如果这会儿眼前有位铁匠,我不再会像少儿时那般激动,我一定只盯着铁墩上的那块铁,只看它如何被敲打、被翻面、又被敲打。我安静地悟着,像戏里入定的老僧……
篾匠
和大家一样,时间再久,总还记得一些人。比如来我们村做事的篾匠:陈贵生和邓师傅。其实,来我们村的篾匠都是固定的那一拨人。可能有五六个人,但就只记得他俩。原因呢? 有点说不清楚,又有点说得清楚。主要是因为这两位篾匠师傅有故事。
陈贵生先是有性格,讲话有意思,每讲一句话都好笑,都有意思。后来,我才晓得,这是有幽默感。有幽默感的人大多长得慈祥,陈贵生也不例外。印象中,他不高,一米五几的个头,身材胖乎乎的,头圆圆的,有点像年画上捧着桃子的老头。他从不恼,脸上总是笑吟吟的。哪怕再冷的天,手上拿着再冷的篾片或竹子,好像拿的都是奖状,脸上都是笑。有时我们恶作剧,去抽他手上的篾片或竹子,他也是笑着扬起手中的篾刀,夸张地跺了两下脚,吓吓我们。村里人不管有没有看见他,不管他在不在我们村做事,我们一提到陈贵生,就想起温暖的笑。
话说某一年,陈贵生带几个篾匠来我们村做事。还是生产队时,篾匠来做事,村里人轮流管饭。篾匠们手下忙活之余,议论哪家的饭菜味道好,自然是口口相传的内容之一了。于是,霉鱼的故事便成了经典。有一次,轮到村里陈福根家里请饭,陈贵生见桌上一盘方块状、涂满鲜红辣椒粉的菜,大喜过望,连忙招呼其他同伴说:来来来,大家吃一块霉鱼。说完,他带头抢先夹了一大块,迫不及待地放在嘴里咬了一大口,感觉是豆腐乳。他用舌头摩擦了两下——没错,是豆腐乳。他见其他同伴尴尬的样子,自己也苦笑了一下。从此,舍陂村陈福根家装一盘豆腐乳招待客人的传说,便在方圆四五个村庄家喻户晓了。陈贵生也背上了一个爱吃豆腐乳的 “美名”。为了纠正他的 “美名”,陈贵生一边忙着手上的活,一边对在旁观看的其他村人半开玩笑半认真说:哪天你家轮饭千万不要将豆腐乳端上席啊,我们虽然是县郊人,没见过什么大世面,但豆腐乳与霉鱼总归还是分得清的。听得旁人哈哈大笑。
邓师傅徒弟时是跟陈贵生一起学的。本来我不晓得他姓邓,只见他从学徒到出师,每天都跟着陈贵生。他长得比陈贵生高大得多,陈贵生支不起的竹子,在邓师傅的手里像拾一根晒衣服的竹竿。邓师傅手里的篾刀也走得比陈贵生流畅、彻底。所以,剖竹之类的大活、力气活一般是邓师傅做。陈贵生一般是做些编织类的精细活,也最能体现他娴熟的技术。
后来,生产队成了承包经营户,篾匠是各家请各家的。我家没等请一次篾匠,父亲便去世了。我也到了城里工作。有一年,一位来自家乡叫邓爱明的医药代表请我在工作的城市南宁吃饭,为了表示我们之间之前有过 “联系”,他抬出他父亲来,说:我父亲是篾匠,他年轻的时候年年去你们村做篾,他还说认得你父亲,说你父亲当时是生产队副大队长,我父亲至今还叫得出你父亲的名字,说与你父亲结为老庚呢。我说:你父亲是哪个? 邓爱明说:最高的那个。我眼前马上浮现那位拎根竹子快速爽利 “开肠破肚”的大高个。我这才知晓他姓邓,高个子的邓,抢大活揽重活的邓篾匠,印象深刻的邓师傅。

泥水匠
我与泥水匠最亲密、也最持久的接触是在1990 年。那一年,我被老师请出了高考考场外。我的人生灰色沉闷。有过一两个礼拜,我像被贬谪放逐到荒凉之地的弃儿,迷惘而无所事事。是堂姐夫宋枧苟收留了我。宋枧苟是位泥水匠,当时,他承建了乡政府的一座粮站仓库。他手下需要小工;当时他手下已有四五个小工,但都是女子。他需要一个干重活的男子。他心目中关于男子的固有印象是一定孔武有力。
于是,我被他召到乡镇圩上的建筑工地上,对宋枧苟一对一服务。其中,有一项工作是在脚手架下往上抛砖。他一手持一把水泥刀,一手接我从脚手架下抛上去的砖,然后往墙上砌。宋枧苟对我说:别看我接得很轻松,好像也很简单,你上来试试。的确,一只手接,不但要求看得准,还要求手要有劲,能抓得住砖。宁枧苟又说:现在是青砖倒没什么,以前我学徒时接的是土坯,一块土坯比一块青砖要厚一倍不止。那时又没手套,经常抓得手指出血。说着,他伸出粗大的手掌给我看:现在都是一层茧包着,没感觉啦。
小时候,有人编顺口溜说 “淤泥糊十指,日晒风雨淋,房无半片瓦,夜无御寒墙”——这是对泥水匠户外做工的真实写照。我家房子是村里最后一批旧式的,地基打在一片废弃的池塘里,全是用一块块百多斤的石头砌起来的。记得打地基时是冬天,泥水匠打着赤脚,在齐腰深的淤泥里将规格不一的青石磨合、敲打,糊上砂浆一块块垒出地面,之后又砌了一米高的砖。
砖是从老屋里拆下来的旧砖,上面还沾着顽固的砂浆,要消除、刮平。砌了旧砖,往上一直到房顶,都是土坯。一块土坯七八斤,上面覆盖着薄薄的一层霜。宋枧苟说:学徒的时候,在你家建那幢土坯房吃的苦最有代表性,想必你都忘了吧? 我站在脚手架下狠狠地往他手掌方向抛上一块青砖,说:那时我读小学三四年级,不记得了。
在粮站仓库工地上干了三四个月,吃了三四个月的苦。后来,父亲生病,我回家照料他。离开建筑工地时,粮站仓库才长一半高,宋枧苟他们继续干了近半年才算完工。
后来我离开家乡,来到城里。宋枧苟继续做他的泥水匠,而且,听说他越来越吃香了。因为周边村里学泥水匠的人越来越少,以前那一代老了,做不动了,年轻的又吃不了那个苦,纷纷离开农村去了城里。宋枧苟为了适应新形势需求,跟一些小工程队在县城做工,学习建小楼房和商品房。回来后,能建时兴的钢筋水泥小楼房。我堂弟家那幢三层小楼房就是请他建的。现在的泥水匠与装修工人是分开的,泥水匠负责外部结构,搭起毛坯房。里面贴瓷、装修是另一拨人。其实,从广义上讲,装修工也属于泥水匠的范畴吧?
现在,乡村的泥水匠真的不多了。而且,既能建房造屋,又能翻盖房瓦、砌灶安炉的泥水匠更是凤毛麟角。以一把砌砖刀、一个吊线陀、一把卷尺、一把抹灰刀和一个盛灰板行走江湖的传统泥水匠逐渐绝迹啦。突然有一日,村里老了一个人,入了土,堆了土,想起要立一块碑,却想不到哪里有会干这活儿的泥水匠呀。
的确,烟火气的生活渐渐稀释,日子撒野似的任性前行。曾经,从我眼前掠过的,那还有补鞋的、补锅的、修伞的、炸爆米花的、剃头的……记忆随便翻动,人物个个鲜活。我想:裁缝、木匠、铁匠也好,篾匠、泥水匠也罢,他们的手艺都是有灵魂的。要做好一门手艺,得有丰富的情感、生活的趣味,以及日常的温度。
父亲生前经常说:家有良田万顷,不如薄艺在身。父亲对我这么说,与其说是对手艺人的看重,还不如说是对我这位学习成绩差得不可救药者的无奈期许。我连父亲唯一的期许都没能实现,父亲没等看到我将来的道路便郁郁而逝。后来,我背叛了土地,来到了城里,从事的是写字营生。侧着身子从时代的缝隙中走过,不管是手艺人,还是我手下的笔,都是在记录生活里的所爱、所依和所托。明里是生计,但要长期坚持,或是终其一生,暗地里没有一份宗教般的认真及执着,是难以寻找到其中的充实及幸福的。
“……固定在那里:一个祭坛,/在那里他把自己消耗在形状的音乐中。/有时候,围着皮革巾,鼻子里满是茸毛,/他斜着身子靠到窗框外,想起双蹄/在风驰电掣的来往车辆中碰击;/然后咕哝着走进去,轻一下重一下/要打出真铁,要煅出吼叫声”——希尼对铁匠铺的诗意表达,其实也是对所有手艺人最强烈的仰望。
现在,我以手中的这支笔为手艺,重拾这份生活的仰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