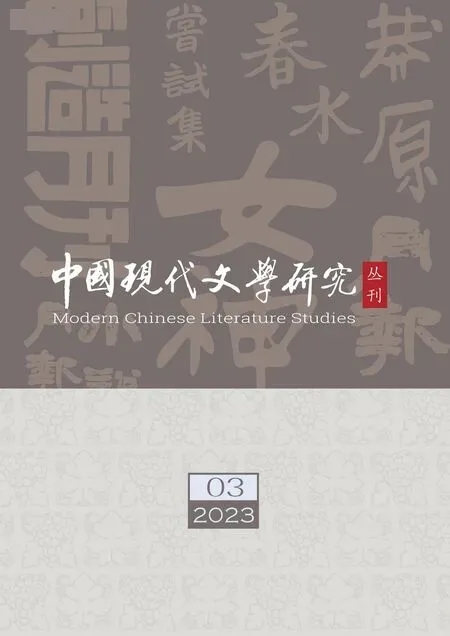从《荷花淀》到“荷花淀派”
2023-10-06刘卫东
刘卫东
内容提要:《荷花淀》的写作和成功,是时代、文学、个人性情融合发酵的产物,可遇不可求。1950年代到1960年代,孙犁的风格被研究者凸显,主要体现于对“美”的书写。认为“孙犁的风格是写‘美’”的观点没有问题,但忽略了这种风格的“极致”性。“荷花淀派”在1950年代中期已经形成。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荷花淀派”概念正式被提出。孙犁不支持“荷花淀派”提法,采取了“疑信参半”的态度。孙犁在世期间,无论是他本人还是研究者,都因为“疑信参半”的说法,把“荷花淀派”问题悬置起来了。目前的研究,正倒逼文学史对“荷花淀派”做出“重写”。
孙犁文学的风格独特,在文学史上拥有一席之地,这是确定的,但如何叙述和定位孙犁,不同文学史却有一些差异。一种呼吁是,对孙犁的评价不够,应予以“重评”。程光炜描述说,孙犁去世后,“‘孙犁现象’对当代文坛产生的冲击波一刻也没有停息过。很多作家、学者都抱怨文学史没给他应有的评价,这对文学史研究提出了很大的挑战”1程光炜:《孙犁“复活”所牵涉的文学史问题——在吉林大学文学院的讲演》,《文艺争鸣》2008年第7期。。本文赞同重评孙犁。笔者认为,此前对孙犁的评价中,忽视了文学流派的参照系,对其创建的“荷花淀派”采取了“疑信参半”的态度,而这其实可以作为重评的入口之一。因此,本文拟以文学流派的生成、演变为线索,梳理“荷花淀派”的风格及成型过程,并与相左观点商榷,从而厘定其文学史地位,达到重评的目的。
一 《荷花淀》的发表及其风格的“极致”
“荷花淀派”能够确立,源于《荷花淀》等作品形成的风格及其得到的认可,而其中的因缘际会,却常被忽略。《荷花淀》的写作和成功,是时代、文学、个人性情融合发酵的产物,可遇不可求。抗战时期孙犁做了很多短平快的工作,比如参与《冀中一日》的征集和编辑,撰写写作教材等,找到了独特的“家国启蒙”切入点,形成了独特的抗战文艺观。孙犁认为,“善良的东西、美好的东西,能达到一种极致”,“我经历了美好的极致,那就是抗日战争。我看到农民,他们的爱国热情,参战的英勇,深深地感动了我”。1孙犁:《文学和生活的路——同〈文艺报〉记者谈话》,《孙犁文集》5,百花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565页。普通农民发生了划时代转变,从田间走向战场,舍弃小家,投入民族解放斗争,来自人性深处的美好和时代需求相互照亮,虽很短暂,却迸发出无与伦比的强光。因此,民族大义(参加党领导的抗日工作)、知识分子心态(贴近群众生活)的特殊性,是《荷花淀》得以问世的两个重要背景。
明朗素朴,“现实性、政治性、政策性”是解放区对作品的要求。2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54页。孙犁符合潮流,但其中又有调子的差别。孙犁从不讳言,自己性格中,有偏“抑郁”的成分。他从小有“神经方面的症状”,“敏感、联想比较丰富”。3孙犁:《和郭志刚的一次谈话》,《孙犁文集》8,百花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285页。由此,他笔下的抗战带有自己的风格。他作品的主题是表现战斗中的军民,却并不追求慷慨豪迈的风格,而是婉约曲折,充满抒情色彩。1942年,孙犁写了《爹娘留下的琴和箫》,1943年发表于《晋察冀日报》。小说以“我”的视角,写了抗战中的一家人。父亲牺牲,母亲离家参加革命,两个女儿大菱、二菱擅长乐器,用演奏来纪念牺牲的父亲,她们后来也死于敌手。作品发表后,受到批评,认为有些“感伤”,这恰从反向说明,小说的风格与众不同。4见孙犁《文学和生活的路——同〈文艺报〉记者谈话》,《孙犁文集》5,第570页。受到批评后,孙犁有意识地对作品色调做了调整,使之更为适合要求。5孙犁没有把《爹娘留下的琴和箫》收入1957年的《白洋淀纪事》,但一直没有忘记这部作品,1980年,重新以《琴和箫》为题在《新港》发表,考虑的显然是作品风格与时代要求的匹配度。李展:《文学“感伤”:时代主流话语中的艰难表达——孙犁的〈琴和箫〉和一段沉痛的“肃托”史》,《兰州学刊》2008年第5期。
正是时代和个人性格的因缘际会,促成了《荷花淀》的发表并迅速以特异的风格受到关注。《荷花淀》写于延安,发表于1945年5月15日《解放日报》副刊,副标题为“白洋淀纪事之一”。8月31日又发表了“白洋淀纪事之二”《芦花荡》。孙犁作品迅速受到关注,重庆的《新华日报》及解放区的报纸多次转载。《荷花淀》被收入1946年周扬编的《解放区短篇创作选》,成为孙犁的代表作。关于《荷花淀》的风格,孙犁在1978年说,“这篇小说引起延安的注意”,是因为西北高原上“刮来的是带有荷花香味的风,于是情不自禁地感到新鲜”,以及看到“群众的抗日决心日益坚决,而妇女们的抗日情绪也如此令人鼓舞”。1孙犁:《关于〈荷花淀〉的写作》,《孙犁文集》6,百花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347页。在孙犁看来,“荷花香味的风”、人民的“抗日决心”和“情绪”,符合时代需要,是作品受到欢迎的原因。在当时的延安,孙犁作品的美学风格无疑是对“整风”后凝重氛围的一种缓和、调节。
1950年代到1960年代,孙犁的风格被研究者凸显出来,主要体现于对其独特“美”的指认:一、自然地域之美。孙犁作品的题材基本是冀中抗战生活,白洋淀水乡的风光、民俗与故事融合,形成独特的氛围。王林指出“孙犁同志是个有浓厚地方色彩,有自己独特风格的作家”2王林:《介绍〈白洋淀纪事〉》,收入刘金墉、房福贤编《孙犁研究专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55页。。二、情感、人性之美。孙犁在激扬时代的抒情诗味道,具有很强的辨识度。当时有观点认为孙犁过于抒情,这更印证了这种风格不容忽视。新文学史家王瑶1953年《中国新文学史稿》中对孙犁的看法,就是一例。王瑶极为看重孙犁,认为孙犁的作品“有着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抒情的风格”,但“也有一些爱情男女的细致情绪,有时,这种细致的感情写得太多,太生动了,就和整个作品中那种战争的气氛很不相称”。3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下),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版,第319、320页。三、女性之美。孙犁视角独特,关注抗战中妇女的出色行为,且将其打造成人物画廊,绝无仅有。孙犁不掩饰他对女性的赞美,“她们并没有多少学问,但她们都能直觉地认识到斗争的实质,她们总是那么奋发、乐观、勇敢,为了解放斗争,情愿献出自己最心爱的人”4吕剑:《孙犁会见记》,收入刘金墉、房福贤编《孙犁研究专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页。,“我以为女人比男人更乐观,而人生的悲欢离合,总是与她们有关,所以常常以崇拜的心情写她们”5孙犁:《孙犁文集自序》,《孙犁文集》1,百花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4页。。四、语言之美。冯健男从文体的角度,认为孙犁写出了“诗体小说”,“他的语言赢得了不少读者和作家的喜爱”,“《白洋淀纪事》里的故事是诗的小说,小说的诗”。1冯健男:《孙犁的艺术——〈白洋淀纪事〉》,《河北文学》1962年第1期。
上述对孙犁风格的界定比较恰切,也一直沿用至今,但须做进一步辨析。孙犁的《荷花淀》只写“美”,摒弃战争中的鲜血和死亡,高度写意,克服了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中的问题,受到欢迎。现在来看,孙犁风格是比较特殊的,是时代精神、个人性格、美学倾向的一次“高度匹配”的结晶。抗战即将胜利时,冀中普通农民(女性)身上焕发出来的“美”给忧郁的孙犁带来的感动、回忆,不可复制。变量稍有不同,味道就改变了。即便孙犁本人,也无法始终保持《荷花淀》的味道。1945年的《荷花淀》是“荷花淀”风格发展的极致,长篇《风云初记》反响一般,到1956年《铁木前传》,难以为继。孙犁晚年并不以《荷花淀》为荣,这一点研究者往往不大论及。他在1980年的一篇访谈中,说自己“不大愿意回顾我年轻时代写的作品”,为之“常常感到害羞”,“在年轻时代,我说了多少过分热情的,过分坦率的,不易为人了解的,有些近于痴想梦呓的话语啊”。2孙犁:《答吴泰昌问》,《孙犁文集》5,第583页。何出此言?孙犁其实意识到了自己风格的“特殊点”,但表述比较隐晦。其一,孙犁风格的产生是一种机缘巧合。他写的是抗日年代赋予的极为“极致”的状况,“是时代、个人的完美真实的结合”3孙犁:《孙犁文集自序》,《孙犁文集》1,第4页。,不可重复。其二,正是在此“机缘”下,孙犁早期写了“美”,讴歌伟大感情的纯洁,不必触碰“美”的倒影和反面。时代变迁后,他说自己对“邪恶的极致”体验很深,但“不愿意去写这些东西”,“也不愿意回忆它”。4孙犁:《文学和生活的路——同〈文艺报〉记者谈话》,《孙犁文集》5,第566页。因此,晚期孙犁风格大变,与《荷花淀》写作时期迥异。5阎庆生认为“孙犁作为文学大师的实绩,主要在于他的晚年”的观点,也值得商榷。孙犁抗战时期的《白洋淀纪事》,更加风格化和不可替代,是孙犁的“标志”。阎庆生:《晚年孙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实际是,孙犁的“痴想梦呓”需要“过分热情”“过分坦率”的自己来匹配,而自己却不可能永远保持那种状态。
因此,认为“孙犁的风格是写‘美’”的观点没有问题,但忽略了这种风格的“极致”性。《荷花淀》抓住的是美的瞬间。只有辨清“荷花淀派”代表人物孙犁艺术风格的特殊性,才能解释此后流派发展过程中的诸种问题。《荷花淀》风格如荷花绽开的瞬间,自然纯粹,但这种风格极难“保鲜”,更无法被固定。出现这种“美”,需要诸多条件匹配,人工集齐几无可能,这是“荷花淀派”风格的内在难度。1949年后,怀有“文学梦”的作者,可以很容易地在革命性的氛围中,发现美得“异质”的孙犁。1铁凝回忆说,自己小时候读一本没有封面的“破书”,被里面的人物吸引,受到“‘鬼祟’的美的诱惑”,后来才知道是孙犁《村歌》中的双眉。铁凝:《怀念孙犁先生》,《人民文学》2002年第11期。到了后来,无论孙犁还是学习者都无法复制“天人合一”的“极致”境界。
二 “荷花淀派”流派的形成
1949—1956年,“荷花淀派”逐渐成形。通常的文学理论认为,文学流派“指一定时期里有着相近艺术追求和思想倾向的作家汇聚而成的文学群体”,形成原因是“相近的文学观念和主张”“相近的题材”“相近的艺术方法和技巧”等。2《文学理论》,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62页。就此而言,“荷花淀派”完全符合流派的要件,因此可以被视为一个文学流派。
首先,孙犁个人的风格得到确认后,借助《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以下简称《文艺周刊》),影响到其他作家。一份刊物是文学流派形成的重要条件。1949年,孙犁进津,负责《文艺周刊》的编辑工作,并以此为媒介,影响了一批年轻作家,吸引他们与自己创作风格靠近。《文艺周刊》在当时影响很大,作品的风格,带有很多孙犁的印记。1951年,孙犁在一次指导写作的发言中,不断举出的例子,就来自《文艺周刊》,还批评“有的人参考着副刊上发表的文章的样式写作”3孙犁:《作品的生活性和真实性——在〈天津日报〉副刊写作小组的发言》,《孙犁文集》5,第500页。。孙犁晚年回忆,办刊时没想过“形成一个什么流派,结成一个什么集团”,但主张“办出一种风格来,用这种风格去影响作者,影响文坛,招徕作品”。4孙犁:《我与〈文学周刊〉》,《孙犁文集》8,第267页。这话实际上肯定了《文艺周刊》的风格化倾向。
孙犁发现与自己风格类似的投稿,帮助发表,是尽编辑的责任,客观上,促进了“荷花淀派”人员的“向心力”。他与韩映山之间,就既是编辑与作者关系,又是师友关系。孙犁1952年认识了韩映山,“那时他是一个农村青年,在保定一中读书。后来,他经常在《天津日报》的《文艺周刊》上投稿。一直到现在,我们之间的文字交往并没有断绝”1孙犁:《韩映山〈紫苇集〉小引》,《孙犁文集》6,第149页。。查《孙犁文集》书信卷,孙犁与韩映山联系密切,从文学到个人生活,无话不谈。关于二人的师承关系,孙犁说“你的创作不能说是学我”,又说“你的生活和气质,有些和我相似”,引为知己。2孙犁:《致韩映山》,《孙犁文集》9,百花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212页。从维熙与孙犁见面不多,也是因为给《文艺周刊》投稿,得以结识。3孙犁:《〈从维熙小说选〉序》,《孙犁文集》6,第169页。孙犁并非有意组建某个流派,反而主张“文人宜散不宜聚”4孙犁:《答吴泰昌》,《孙犁文集》5,第580页。。他出自编辑的职责,明知道“作用并不能像你们所称许的那样大”5孙犁:《写作漫谈——在暑期讲座上对同学们讲的话》,《孙犁文集》5,第533页。,还是不厌其烦指导后进,持续一生。《孙犁文集》书信卷显示,很多业余作者得到过孙犁的指点。可以说,孙犁以写作为中心,与师友、晚辈一起,潜移默化,形成了一个“队伍”。孙犁1979年在给工人作家阿凤散文集写的序言中,用“队伍”打比方:“他是我们当时苦心经营组织起来的,那一支并不很小的作者队伍,兵折将损后,荷戟彷徨的一员‘福将’。”6孙犁:《阿凤散文集序》,《孙犁文集》6,第157页。初学者受到孙犁影响,模仿他的风格,走上创作道路,再正常不过。
其次,被认为属于“荷花淀派”的作家,也承认自己受到孙犁影响。1950年代初期,一批作家得到孙犁帮助,在《文艺周刊》发表作品,小有影响,形成了事实上的流派,这一点得到学界指认。7布莉莉:《〈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与荷花淀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2期。狭义上说,“荷花淀派”包括《荷花淀派小说选》中的作者孙犁、韩映山、刘绍棠、房树民、从维熙。韩映山还开过一个广义的名单。8收入苗雨时、许振东主编《荷花淀派研究资料汇编》(上),花山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韩映山:《关于“荷花淀”文学流派》,《韩映山文集》3,河北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331页。上述作家对孙犁十分尊敬,将其视为文学上的导师,执弟子礼。1957年,孙犁在北京住院,刘绍棠、从维熙和房树民买了鲜花,一起到医院看望他,可惜被拦在门外。9参见孙犁《〈从维熙小说选〉序》,《孙犁文集》6,第167页。1978年,孙犁到京开会,与刘绍棠、从维熙重逢,“嘱咐三点:一、不要再骄傲;二、不要赶浪头;三、要保持自己的风格”10段华编著:《孙犁年谱》,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57页。,可谓谆谆教诲。“荷花淀派”作家在很多场合,谈过与孙犁的师承关系。韩映山在1981年出版的《绿荷集》后记中说:“五十年代初,开始写作时,由于受作家孙犁同志的影响和指导,知道文学是要写生活、写人的。那时自己所写的作品,虽然天真幼稚,但有一股浓郁的泥土气息,也渗透着作者的真情实感。”1韩映山:《绿荷集·后记》,河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5页。刘绍棠说,“孙犁同志把《文艺周刊》比喻为苗圃,我正是从这片苗圃中成长起来的一株树木”2刘绍棠:《忆旧与远望》,《天津日报》1983年5月5日。。1950年代初期,《文艺周刊》上的作品或多或少有孙犁影响的成分,是不争的事实。3参见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9年出版的《天津日报文艺周刊70年精品选》。
再次,出现了艺术旨趣相似的作品。刘绍棠、韩映山、从维熙、房树民等,纷纷把笔触伸向乡土,用抒情笔法,写出追求“进步”的女性,尤其是女孩子。在他们的作品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孙犁风格的影响。1953年,刘绍棠等发表在《文艺周刊》上的九篇小说结集为《运河滩上》,是对“荷花淀派”风格作品的一次大规模推介。4刘绍棠等:《运河滩上》,华北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其中包括《运河滩上》(刘绍棠)、《红旗》(从维熙)、《瓜园》(韩映山)、《年底》(房树民)等。时隔30年,1983年,冯健男主编了《荷花淀派小说选》,对“荷花淀派”作品做了集中展示。从风格来看,很容易辨认其他作品中的“荷花淀”气息。刘绍棠的《鸡鸭委员》写村里的姑娘翠枝儿精心管理社里的鸡鸭,为给鸭子治病,在风雨之夜不顾危险去找畜医,终于解决了问题,得到社员肯定。《大青骡子》(刘绍棠)、《摆渡口》(刘绍棠)、《夜过枣园》(从维熙)等作品,都以剪影的方式,塑造活泼、进步的女主人公。“荷花淀派”后继者大多写合作化时期的农村新人,仍然一味歌颂其中的“美”,坚持把摒弃“丑”作为风格的一部分。虽然对孙犁的学习惟妙惟肖,但在“美的极致”方面,没能达到时代和文学、个人个性的完美匹配。不过,这是“荷花淀派”风格本身的问题,并不影响本文的立论。
需要辨析的是,“荷花淀派”作家的交集是阶段的、流动的、发展的,并非一成不变。其一,孙犁不希望别人总是学自己。孙犁按照“荷花淀派”风格培养了作家后,希望他们不要故步自封,走向更为广阔的舞台。孙犁1979年给刘绍棠的序中说:“我不希望你们(指从维熙和其他同志),老是在这个地方刊物(指《天津日报》的《文艺周刊》)上发表作品。它只是一个苗圃。当它见到你们成为成材的参天大树,在全国各地矗立出现时,它应该是高兴的。我的心情,也是如此。”1孙犁:《〈刘绍棠小说选〉序》,《孙犁文集》6,第165页。他对从维熙说,“我是低栏,我高兴地告诉你:我清楚地看到,你从我这里跳过去了”2孙犁:《〈从维熙小说选〉序》,《孙犁文集》6,第169页。。孙犁殷殷期盼“荷花淀派”承传、光大的心情,跃然纸上。其二,作家要想取得更大成绩,不能总是写孙犁风格的作品。“荷花淀派”风格易于学习,但容易流于“单纯”,很多作家起步后,风格逐渐变淡,这很正常。孙犁主张写真善美的力量,因此对从维熙作品中的“悲剧”有不同看法,认为“完全可以叫善与美的力量,当场击败那邪恶的力量”3孙犁:《关于〈大墙下的红玉兰〉的通信》,《孙犁文集》6,第87页。。有的作家开始受到孙犁影响,后来风格发生转变。孙犁认为,有的小说写情爱还“嫌不应时”,“开始描写乱伦的情节”,“把这种小说,也算作荷花淀流派,不大妥当吧?”4孙犁:《和郭志刚的一次谈话》,《孙犁文集》8,第288页。一些作家后来自我调整,淡化了风格,不能视为“荷花淀派”不曾存在的理由。
作为文学流派的“荷花淀派”在1950年代中期确然形成。如果一定拿“文研会”“创造社”的标准界定文学流派,要求具有社团章程、集会活动等,就有些苛刻了。在“十七年”的语境内,文学流派由于涉及“宗派”而成为讳莫如深的词汇。孙犁作为革命作家,不可能有建立“组织”的想法;而被认为是“非法组织”的胡风、丁玲集团,并无章程。确定流派,应该本着事实第一、程序第二的原则。刘绍棠1988年谈及“荷花淀派”时说得清楚:“不是哪个人的独家经营,也不是一些人的有限股份公司;而是由艺术旨趣上相近的作家的共同劳作,艺术追求上可以引为同调的作家的日积月累,自然而形成。虽未申请注册,领取执照,但早已为广大读者有目共睹,人所共知,事实胜于雄辩,无须谁的钦定和恩准。”5刘绍棠:《我说“荷花淀流派”——〈荷花淀〉创刊述旨》,《刘绍棠文集》10,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255页。“荷花淀派”之所以没有形成确定的流派概念,是因为外部环境发生巨变。孙犁1956年生病,淡出文坛。刘绍棠、从维熙风头正劲之时,因“反右”问题,失去了写作资格,韩映山、房树民趋于谨慎。“荷花淀派”戛然而止,没有继续发展。但是,“荷花淀派”风格,仍然是写农村生活时必要的参照,浩然开始写小说时,也是“喜欢孙犁的优美”1胡世宗:《日记中的浩然》,《苍生文学》2009年第1期。。
三 “荷花淀派”概念及孙犁的“疑信参半”
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荷花淀派”概念正式被提出。当时大背景是,研究者开始注意曾经被压抑的“文学流派”,不仅对现代文学史上的“九叶派”“新感觉派”等重新定位,还特别强调发展新的流派。《文汇报》发表《发展社会主义文学流派》,大张旗鼓,予以鼓励。2曾文渊:《发展社会主义文学流派》,《文汇报》1979年10月23日。赵树理、马烽、西戎、束为、胡正等在题材、风格、地域等方面都有相似性的“山药蛋派”也得到讨论。3《有关“山药蛋派”的探讨》,《文汇报》1980年7月21日。由此,“荷花淀派”的命名,获得了一个契机。
事实上,在1960年代津京保一带就有了“荷花淀派”的提法。冉淮舟在回忆中述及,当时“有人提出荷花淀地域文学,成立荷花淀地域文学研究会,编辑荷花淀地域文学丛书”,而且都落到了实处,完成了《荷花淀地域文学作品选》《荷花淀地域文学图志》《荷花淀地域文学简说》。4冉淮舟:《欣慰的回顾》,天津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09页。上述材料并未公开发表,但可以作为“荷花淀派”命名的前史。较早将其作为流派论述的,是理论家,以“荷花淀派”研讨会的召开为标志。1980年9月,“作协分会、河北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河北文学》编辑部、《长城》文学丛刊编辑部,最近联合举办文艺理论写作班,就文学流派——‘荷花淀派’的问题,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进行了热烈的讨论”5白海珍:《关于“荷花淀派”的讨论》,收入刘金墉、房福贤编《孙犁研究专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1页。。很多研究者将其作为“荷花淀派”得名的确定时间。《人民日报》以《河北开展关于“荷花淀派”的讨论》为题,报道了此次会议,扩大了“荷花淀派”概念的传播。6《河北开展关于“荷花淀派”的讨论》,《人民日报》1980年11月1日。会议上,批评家站在流派标准、发展角度,“对是否形成了一个以孙犁为代表的‘荷花淀派’,提出了两种不同的意见”7白海珍:《关于“荷花淀派”的讨论》,收入刘金墉、房福贤编《孙犁研究专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1页。。一种意见认为,“荷花淀派”形成了文学流派。对“并没有真正形成一个文学流派”的意见,会议综述概括为三点原因:一是推崇“阳刚之美”时期,孙犁的“阴柔之美”被“排斥和冷落”;二是1950年代初期一批文学青年学习孙犁,但没有形成“成熟的风格”;三是没有形成作家集群,“充其量也只有那么一个雏型、一个胚胎,没有形成一个文学流派——‘荷花淀派’”。1白海珍:《关于“荷花淀派”的讨论》,收入刘金墉、房福贤编《孙犁研究专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2、293页。现在看来,用这三个原因均无法论证“荷花淀派”不存在。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在这次座谈会上,有的批评家的态度似乎不明朗,模棱两可。初看起来,似乎如此。阎纲在发言中说:“有没有一个‘荷花淀’派呢?看来似有若无。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艺术流派,‘荷花淀’派若即若离,忽隐忽现,宛在堤柳烟波之间。”2阎纲:《孙犁的艺术——在〈河北文学〉关于“荷花淀”流派座谈会上的发言》,收入《孙犁研究专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7页。鲍昌说:“荷花淀派似乎又没有正式形成。用句古诗来形容,是一种‘草色遥看近却无’的状况。”3鲍昌:《中国文坛上需要这个流派——在〈河北文学〉关于“荷花淀”流派座谈会上的发言》,收入《孙犁研究专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8页。但是,是否可以说,有些批评家不同意“荷花淀派”的说法呢?并非如此。1980年,百废待兴,文学园地亦然,此刻学术机构联合召开关于“荷花淀派”的座谈会,批评家来参加会议,本身就是一种行动肯定。在当时语境下,说“荷花淀派”若有若无,给予“有限肯定”,这种表达策略,达到了确定“荷花淀派”的目的,也为自己和孙犁减少了文化政治的压力。
把“荷花淀派”在文学史上“固定”下来的,是评论家冯健男编的同名文集。1983年,冯健男编选了《荷花淀派小说选》,收入孙犁、刘绍棠、从维熙、韩映山、房树民五位作家的三十篇小说,并在该书序言中勾勒了“荷花淀派”的大致轮廓,“‘荷派’缘起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冀中和延安,形成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津、京、保三角地带,而人们对它予以回顾,认为它是我国现代文学中的一个流派”,则是“近几年”的事。4冯健男:《荷花淀派小说选·自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页。由此,确定了“荷花淀派”的渊源、地点和主要人物。就1980年代的讨论看,作为文学流派的“荷花淀派”已经被明确定位。5艾斐:《论“荷花淀派”的艺术变迁》,《当代文坛》1984年第11期。
关于“荷花淀派”的讨论,孙犁密切关注。孙犁因病未参加1980年的会议,《文艺周刊》的编辑宋曙光等会后向他做了详尽汇报。1宋曙光:《忆前辈孙犁》,天津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4页。孙犁当时严肃思考了这个问题,发表了多篇文章表达看法,也在访谈中多次提及。但孙犁的态度,被研究者简化了,认为他不同意“荷花淀派”的提法,并以此否认该流派存在。其实,孙犁虽然不支持“荷花淀派”提法,但并未否定,采取了“疑信参半”的态度。孙犁观点辨析如下:一、理论上,孙犁认为不必树立一个名词作为“标榜”。在1981年的《关于“乡土文学”》中,不赞成刘绍棠在刊物搞“乡土文学”的特辑,认为其中有“客观方面的激励”因素。2孙犁:《关于“乡土文学”》,《孙犁文集》5,第500页。孙犁对“乡土文学”这样五四时期确定的概念都不以为然,何况对于以自己为中心的“荷花淀派”?对于大力提倡“荷花淀派”的,孙犁甚至认为其中有私心。二、人员上,孙犁认为不必形成一个团体。他认同鲁迅的话,认为“文学团体非豆荚”。孙犁接着发挥,“即使为豆荚,能总体一时,豆熟则荚裂,命运亦各不同。本身充实,得天独厚者,坠入土壤,则生发无穷,另生新荚,其不得水土者,或至腐朽湮灭。况于荚内之时,即志趣不同,有所变异,甚或萁豆相煎者乎”3孙犁:《再论流派——给冯健男的信》,《孙犁文集》6,第254页。。孙犁对团体不信任,甚至对其中的关系问题抱有警惕。对所谓流派的前途,孙犁并不看好,态度很潇洒,来去自由,“有为之士,所关心者,为本身之利益及创作之前程,非必关心流派之前途也。于己有利时,则同派而同流,于己无利时,则异派而自流矣”4孙犁:《再论流派——给冯健男的信》,《孙犁文集》6,第254页。。就此来看,孙犁不会同意存在“荷花淀派”团体的观点。三、个人性格上,孙犁没有首领欲望。孙犁个人低调谦虚,在给冯健男的信中表示:“关于流派之说,弟去岁曾有专题论及。荷派云云,社会虽有此议论,弟实愧不敢当。自顾不暇,何言领带?回顾则成就甚微,瞻前则补救无力。名不副实,必增罪行。每念及此,未尝不惭怍交加,徒叹奈何也。”5孙犁:《再论流派——给冯健男的信》,《孙犁文集》6,第254页。孙犁当然有其骄傲,但这时的谦虚也并非故作姿态,而是他本人性格如此。孙犁对做“头领”一事,并不热衷,数次坚辞各种行政、学术职务。四、在影响问题上,孙犁认为建立“荷花淀派”容易束缚自我,窄化创作道路。他评价刘绍棠时,就是这个理念——“我以为绍棠深入乡土,努力反映那一带人民的生活和斗争、风俗和习惯,这种创作道路,是完全可以自信的,是无可非议的。自己认真去做就可以了,何必因为别人另有选择,就画地为牢,限制自己?”1孙犁:《关于“乡土文学”》,《孙犁文集》5,第501页。综上所述,孙犁对“荷花淀派”命名非常关心,但热情不高。不过,这不等于孙犁否定“荷花淀派”。对“荷花淀派”的命名,孙犁主张悬置。他对冯健男表示感谢:“弟亦俗人,未敢多违众议。故于兄之编选劳作,虽疑信参半,然于兄之文章及好心,仍感激而击节称善也。”2孙犁:《再论流派——给冯健男的信》,《孙犁文集》6,第255页。以孙犁对语言运用的讲究,这里的“疑信参半”值得玩味。其中既对“荷花淀派”的存在表示怀疑,但也有一半“信”的成分。不妨做个假设,当时无论出于何种考虑,孙犁都不会表态承认“荷花淀派”的存在的。
如果说1950年代的刘绍棠、韩映山等人是第一代“荷花淀派”作家的话,1980年代初期孙犁仍然按照自己的方式,以《文学周刊》为纽带,关心、帮助了一批崭露头角的新人。他用自己的影响力,推介、帮助了一批与自己风格近似的作家,其中不乏初出茅庐、此后成名的铁凝、贾平凹等。3张莉:《作为文学批评家的孙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6期。比如,1982年他评论铁凝的《哦,香雪》时,认为“这是一首纯净的诗,即是清泉”4孙犁:《谈铁凝的〈哦,香雪〉》,《孙犁文集》6,第136页。。铁凝著文《怀念孙犁先生》表示,孙犁曾给予自己很大影响。5铁凝:《怀念孙犁先生》,《人民文学》2002年第11期。孙犁在1983年致贾平凹的信中,赞扬对方“散文写得很自然”6孙犁:《致贾平凹》,《孙犁文集》10,百花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7页。。贾平凹在《孙犁的意义》中说,对自己产生过“极大影响”的两个人是孙犁和沈从文。7贾平凹:《孙犁的意义》,收入刘宗武等编《孙犁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71页。如同当年对刘绍棠、韩映山等一样,孙犁对与自己风格契合的青年作家的认同和帮助,是无私和一以贯之的。当然不能说这是“荷花淀派”的承传,但孙犁风格的影响,是显而易见且得到对方承认的。“荷花淀派”后继者的作品中显然有孙犁风格的影子,但随着创作发展也逐渐走出了不一样的道路,这正是孙犁希望和欣慰的。8莫言初登文坛时,也曾受孙犁影响,后来淡化了“荷花淀派”风格。李宗刚:《孙犁与莫言:从认同走向疏离》,《文学评论》2019年第2期。他们无法复制孙犁自己也无法复制的《荷花淀》的“极致”,转而去寻找属于自己的“极致”了。
可以说,孙犁在世期间,无论是他本人还是研究者,都悬置了“荷花淀派”问题。自从1980年代初期“荷花淀派”被命名,文学史在处理孙犁及“荷花淀派”问题上,有三种情况。一是提及孙犁,但没有把“荷花淀派”作为文学流派。二是文学史提及“荷花淀派”,但并不肯定其存在。如金汉就认为:“荷花淀派更多地看作一个作家群体。作家群体与流派而言,多了松散性和各自主体性。遗憾的是,这个文学群体由于社会历史的种种原因未能成长起来。”1金汉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20~121页。为何会出现上述状况?究其原因,是对“荷花淀派”的“美”及其影响力认识不够,没有将其视为复杂语境中的乡土叙事传统,而这,是孙犁特殊性的更重要表现。当前文学史叙述框架基本是“重写文学史”后确立的。1980年代末,“重写文学史”潮流中,更为注重曾被压抑的张爱玲、沈从文等;另外,1980年代文学思潮重视现代主义作家,曾因不够革命而“多余”2杨联芬:《孙犁:革命文学中的“多余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8年第4期。、受到冷遇的孙犁,又因属于革命作家,仍然位居边缘。敏感的派别站队,也是关于孙犁的评价始终不够“得力”的原因之一。三是在研究文学流派的专著和论文中,“荷花淀派”得到确认。正是在更为特殊的参照系中,“荷花淀派”被推到了聚光灯下。严家炎在《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中,把“山药蛋派”和“荷花淀派”并举,认为这是解放区的两个文学流派:“孙犁、康濯等作家,他们的作品清新朴素,抒情味浓,富有新的生活情趣,有内在的美。到五十年代经过发展,加进新的成员,就成了人们所说的‘荷花淀派’。”3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页。丁帆在《中国乡土小说史》中认为,“荷花淀派”“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初具规模于50年代初期,活跃于50年代中期,其后在日益酷烈的政治文化语境中渐趋凋零”4丁帆主编:《中国乡土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7页。。看得出来,到了“流派史”“乡土小说史”的框架中,“荷花淀派”就成为不能被忽视的存在了。可以说,目前的研究,正倒逼文学史对“荷花淀派”做出“重写”。
小 结
本着“回到文学现场”的研究方法和客观公正的理念,文学史应当给予“荷花淀派”更高地位。这样做的意义是:一、将孙犁与“荷花淀派”并举,有助于进一步厘定孙犁的意义,廓清乡土叙事的潮流与支脉。孙犁在传统、现代交汇的关头,开始自己的艺术创造,形成鲜明风格,且对其他作家产生了影响。孙犁的风格不是个人的,而是一个流派在处理乡土问题时的集体努力。二、彰显文学史的公正性。文学史要发挥“后见之明”,纠正“现场”批评,让被遮蔽者现身,为蒙冤者辩白,将名不副实者撤下神坛。其实,无论研究者还是孙犁本人,已经把“荷花淀派”作为流派,但出于当时思维框架及人事纠葛,仅在部分范围内加以确认。孙犁是“文学现场”自甘边缘、崇尚“人淡如菊”的作家,但文学史不应“顺势”而为。三、对当下文学场域的价值观产生示范作用。1980年的“荷花淀派”会议总结说,“没有成为‘工具’”、与提倡的题材“格格不入”、“恪守现实主义之法”,是“荷花淀派”的特点。1白海珍:《关于“荷花淀派”的讨论》,《河北文学》1980年第12期。收入《孙犁研究专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5页。肯定“荷花淀派”,意味着重申、铭记这些“历史经验”,是文学史的责任,也是对文学价值观和学术良心的守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