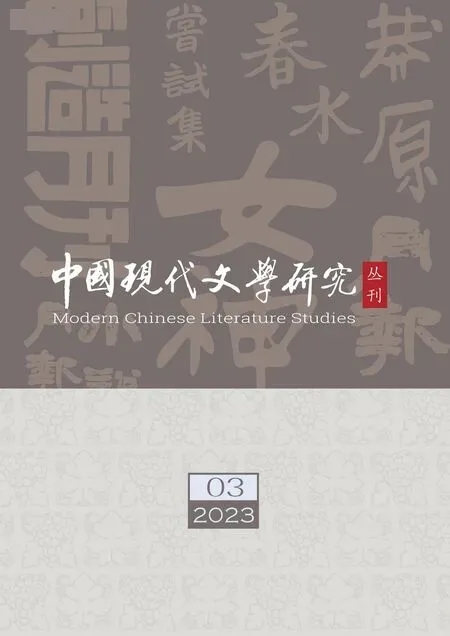摩登最美是“风情”?※
——《长恨歌》的怀旧书写评议
2023-10-06程小强
程小强
内容提要:著名作家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见证了作为文化和文明形态的上海摩登并未随1940年代摩登时代的终结与革命时代的到来而离场,其关于摩登时代魔力的抒叙影响深远。然而,如王安忆者将颓靡情调演绎成摩登时代最重要的精神遗产并将之普泛化与赋予超时空魅力,无疑是对作为现代性典范的上海摩登的曲解。《长恨歌》抽空历史丰富性而陷溺于虚无绝望的怀旧态度与探寻历史的路径在当代中国是不可取的。
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上海接连遭遇“一·二八”事变、淞沪会战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全面沦陷。与沉重的历史叙事相比,1927年以来全面发育的上海摩登引领着时代风潮,并成为1930—1945年间中国都市文化与文明走向现代的典范。李欧梵的学术畅销书《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从时尚建筑、摩登生活、电影杂志、文学期刊、商业出版等方面溯源了上海摩登的存在形态及相应文化文明与文学的互动场景。该著选择1945年作为考察上海摩登的下限并非李欧梵的随意裁断,而是基于1946年新的中国革命与政治进程影响下的社会文化思潮转向,最终在1949年上海进入人民政权时期,上海摩登连同民国叙事从表面上消匿。应该说,作为文化和文明形态的上海摩登并未随摩登时代的终结与革命时代的到来而瞬间离场,《长恨歌》关于“真实的实用人生态度”与“充满怀旧气息的生活知趣”1朱栋霖、朱晓进、吴义勤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5—2018(第四版)》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年版,第132页。的抒叙重构了摩登时代的魔力,但将颓靡情调演绎成摩登时代最重要的精神遗产并将之普泛化与赋予超时空魅力,无疑是对作为现代性典范的上海摩登的肤浅理解,至如《长恨歌》抽空历史丰富性而陷溺于虚无绝望的怀旧态度与路径则不甚可取。
一 如何进阶?如何转型?
《长恨歌》如是叙描上海弄堂日常生活:
王琦瑶家的前客堂里,大都有着一套半套红木家具。堂屋里的光线有点暗沉沉,太阳在窗台上画圈圈,就是进不来。三扇镜的梳妆桌上,粉缸里粉总像是受了潮,有点黏湿的,生发膏却已经干了底。樟木箱上的铜锁锃亮的,常开常关的样子。收音机是供听评弹、越剧,还有股票行情的,波段都有些难调,丝丝拉拉地响。王琦瑶家的老妈子,有时是睡在楼梯下三角间里,只够放一张床。老妈子是连东家洗脚水都要倒,东家使唤她好像要把工钱的利息用足的……2王安忆:《长恨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页。
上海弄堂里极富质感的生活景象自成体系,将每日饮食起居演化出有声有色的情调,小市民们花费大量闲余时间来游戏娱乐。可除此之外,依然浸透着与上海摩登隔绝的一般中国人琐屑庸常的生活气息与沉沦的精神气质,屋宇阁楼亭子间的陈旧破败、每日生活的简单无聊与精打细算等窘迫成为日常感性。弄堂的狭窄逼仄不仅指向一份生存空间,更是代际间生命同质化背后的终极无出路,多有论者所欣喜的生命韧性着实不缺,而生命气度早已凋零,都市民间性质的弄堂生活绝对不是精神后花园和人间乐园,后来者不负责任的浪漫想象不能也不应代替现实生存的艰辛。相较而言,同期的“沪上淑媛”生活是这样的:
上海的夜晚是以晚会为生命的,就是上海人叫作“派推”的东西。霓虹灯、歌舞厅是不夜城的皮囊,心是晚会。晚会是在城市的深处,宁静的林荫道后面,洋房里的客厅,那种包在心里的欢喜。晚会上的灯是有些暗的,投下的影就是心里话,欧洲风的心里话,古典浪漫派的。上海的晚会又是以淑媛为生命,淑媛是晚会的心,万种风情都在无言之中,骨子里的艳。这风情和艳是四十年后想也想不起,猜也猜不透的。这风情和艳是一代王朝,光荣赫赫,那是天上王朝……1王安忆:《长恨歌》,第48页。
风情是摩登生活的催化剂,背后是金钱富足之后的纵情狂欢,是有闲阶级的今朝醉,王琦瑶居于“民间”而心向“都市”,久已濡染摩登生活显然不满意于寒碜的弄堂生活。稍事考究即知,1929年王琦瑶生于沪上弄堂,其成长适逢上海摩登的蓬勃兴起,摩登时尚与弄堂生活的参差对照触目惊心,物质主义的诱惑真实又贴切。在这种情形下,王琦瑶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高度同化,均注重培育弄堂女子的摩登气质与习得摩登生活方式。相比一般平民家庭教育的严肃活泼、学校教育的积极上进、社会教育的择善而从,王琦瑶的三重教育多有错失:家庭教育的缺位使王琦瑶获得自由选择的可能但也放逐了培育正确价值观的可能2有论者言:“上海弄堂闺阁的‘不严密’,自然形成闺阁女孩思想的开放,她们不仅感知着上海这个洋场社会的人生百态,而且接受着它的各种新潮思想和时尚观念。”见崔志远《寻找上海——解读王安忆的〈长恨歌〉》,《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家庭教育的缺位仍源于王琦瑶日常生活的弄堂处所及闺阁的非封闭性,弄堂及闺阁生活与上海摩登生活质地大不同,但接受摩登影响与接受摩登风习能力却一点不差:“贞女传与好莱坞情话并存,阴丹士林蓝旗袍下是高跟鞋,又古又摩登。‘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也念,‘当我们年轻的时候’也唱。它也讲男女大防,也讲女性解放。出走的娜拉是她们的精神领袖,心里要的却是《西厢记》里的莺莺……”见王安忆《长恨歌》,第14页。,学校教育全面受摩登社会风潮影响而导向不负责任的摩登主义,社会教育如大染缸般邀约王琦瑶们加盟摩登。这些都诱导王琦瑶拼命突破出身制约、努力跳出单调局限的弄堂去奋力“追逐潮流”了。
“片厂”的故事、“开麦拉”的经历、“照片”的见刊对王琦瑶的转型至关重要,现代传媒技术提供了王琦瑶融入上海摩登空间的契机,王琦瑶深谙其理并加以充分利用。至于“沪上名媛”与“上海小姐”就不是简单的名号问题,而是弄堂小儿女进阶摩登的刚需,背后是近现代以来中国社会阶层与阶级松动,是商业主导下的重物质重实利追求对都市资源的再发掘与集中。因此,相比于闺蜜吴佩珍和蒋丽莉,王琦瑶的“闭月羞花”之美成为进阶的必要条件,她能将上海弄堂滋育的“小女儿情态”、“小情小调”与“小心眼”等“过日子的情态”加以摩登改造,使小家碧玉气质为上海摩登所接纳与喜爱。王琦瑶接受现代摩登改造后的“美”是其由民间通向摩登的入场券,使现代摩登与都市民间的媾和及流动变得可能,同步提升了王琦瑶之于上海摩登场的“生命等级”:“隐含作者、叙述者对美女的这种特权没有任何质疑,终归默认了这样的世俗观念,即漂亮与否决定了女人尤其是未嫁女人的生命等级。”1李玲:《以女性风情阉割女性主体性——对王安忆〈长恨歌〉叙事立场的反思》,《扬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凡胎之美提供并顺利铺就了王琦瑶的进阶之途,此诚所谓“摩登最美是风情!”
二 摩登时代的刹那主义
上海摩登有一个很重要的面向就是有钱有闲阶级对颓靡生活的热望与肯定,王琦瑶的“上海小姐”身份获得意味着其对摩登颓靡生活的高度认同,《长恨歌》全面简化了王琦瑶的心理转变过程,由叙述者直陈王琦瑶入选“上海小姐”后同步获得上海摩登场的“交际花”身份,并夸赞“交际花”们心性与摩登颓靡气息多么契合:
这样的公寓还有一个别称,就叫作“交际花公寓”。“交际花”是唯有这城市才有的生涯,它在良娼之间,也在妻妾之间,它其实是最不拘形式,不重名只重实。它也是最大的自由,是城市里逐水草而生的游牧生涯,公寓是像营帐一样的避风雨,求饱暖。她们将它绣成了织锦帐。她们个个都是美,还是高贵,那美和高贵也是别具一格,另有标准。她们是彻底的女人,不为妻不为母,她们是美了还要美,说她们是花一点不为过。她们的花容月貌是这城市财富一样的东西,是我们的骄傲。感谢栽培她们的人,他们真是为人类的美色着想。她们的漫长一生都只为了一个短促的花季,百年一次的盛开。这盛开真美啊!她们是美的使者,这美真是光荣,这光荣再是浮云,也是五彩的云霞,笼罩了天地。那天地不是她们的,她们宁愿做浮云,虽然一转眼,也是腾起在高处,有过一时的俯瞰。虚浮就是虚浮,短暂就是短暂,哪怕过后做他百年的爬墙虎。2王安忆:《长恨歌》,第101页。
在这段心理写实中,王安忆为弄堂女子走向摩登进行全面道德松绑:人应该紧握眼前实惠,花容月貌是财富,美色是第一位的,短促的花季应该尽情盛开,人生即使如浮云也应在高处。此番启示并无推陈出新之论,实质上就是中外文学关于刹那主义、一般中国现实人生的今朝有酒今朝醉的认知、及时行乐的现世生存观等的集聚。王安忆将这些滥俗的人生启示给予一个刚刚进阶成功的弄堂女子,以使其心安理得地陷溺于摩登颓靡的浮华生活。上海摩登对弄堂女子的欲望化与物化改造获得成功,身为女子应该及时行乐,结果是宁做有钱有权者的外室而不做老实人的良妻,一般情商不高且经济困窘者被摩登时代所嘲讽与轻侮。
极具吊诡意味的是,1946年再度开始的国共两党争战引起上海摩登危机的可能被置之不顾,革命话语被上海摩登嘲讽:“他支吾了些男女平等,女性独立的老生常谈,听起来像是电影里的台词,文艺腔的;他还说了些青年的希望和理想,应当以国家兴亡为己任,当今的中国还是前途莫测,受美国人欺侮,内战又将起来,也是文艺腔的,是左派电影的台词。”1王安忆:《长恨歌》,第 59、60页。“导演是负了历史使命来说服王琦瑶退出复选圈,给竞选‘上海小姐’以批判和打击。电影圈是一九四六年的上海的一个进步圈,革命的力量已有纵深的趋势。关于妇女解放青年进步消灭腐朽的说教是导演书上读来的理论,后一番话则来自他的亲闻历见,含有人生的体验,这体验是至痛至爱的代价,可说是正直的肺腑之言。”2王安忆:《长恨歌》,第 59、60页。此类嘲讽写来漫不经心又触目惊心,包括女性解放在内的现代中国以来的启蒙成果与已日趋明了的革命力量对比变化均为上海摩登所无视,叙述者口吻举重若轻又极尽轻侮,在率性的声调下丑化革命到了一个新高度。要多说一点的是,王安忆用摩登颓靡对抗同为时代主流的革命话语,早已被证明只是一场幻梦,因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要流血牺牲的,革命与非革命之间并不存在对等对抗的可能,何况上海摩登本来就是一个呈开放性的意识形态体系,用不着在和革命的对抗中彰显魔力。
三 自我洗白与人生再出发
1949年之后,王琦瑶曾经的摩登颓靡生涯及与国民政府要员的情史成为革命语境下的历史垃圾,而王琦瑶为了不再困溺于底层甚至遭遇牢狱之灾,就必然采取一系列自我洗白行动,叠加其所受情伤亟须疗养,王琦瑶的邬桥行意义重大。
邬桥行为王琦瑶提供了人生由刹那走向永恒的启示。王琦瑶的摩登颓靡与及时行乐生活化为泡影后,其人生还须做长远计,王琦瑶幸运地回到了(外婆家的)邬桥:“邬桥这种地方,是专门供作避乱的……这种小镇在江南不计其数,也是供怀旧用的。动乱过去,旧事也缅怀尽了,整顿整顿,再出发去开天辟地。”外婆家历来就是“后花园”与精神寻梦之所,在此番参悟中,邬桥由历史走来的亘古性寓言了生命的恒常性,千年来世道变换在邬桥留下“空和静”,而支撑千年空静邬桥的还是与都市民间日常生活样态无异的“柴米油盐,吃饭穿衣”与人生的“繁琐”底子,“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成为“良辰美景”,邬桥力透纸背的是“通透”“俗”“苟且”等人生与人性之基,“活着”1王安忆:《长恨歌》,第127~129、129页。成为人生取舍的唯一标准。可以说,由历史走来的邬桥在现实生活中的有滋有味行进及时启发了王琦瑶放下那些不切实际的摩登颓靡浮华生活,而复归民间日常生活。至于外婆反复启示的人生得失只是一时,而地老天荒的苍凉当为人生常态就积极地救治了王琦瑶的情伤,又叠加愣头青阿二的朴素感情对既往情伤的稀释,王琦瑶经由摩登颓靡生活所酿成的伤痛在时间的推移中全面得到疗救。王琦瑶由此获得了人生再出发的勇气与心态:“有反有正的,以反作正,或者以正作反。这是一个奇迹,专为了抑制这世界的虚荣,也为了减轻这世界的绝望。它是中介一样的,维系世界的平衡。这奇迹在我们的人生中,会定期或不定期地出现一两回,为了调整我们。”2王安忆:《长恨歌》,第127~129、129页。正反的尖锐对立与决绝的是非判断已不复存在,邬桥以上海后花园的地理空间变成纾解摩登颓靡丧失之痛与风花雪月场失意后的救赎地,王琦瑶也轻易地化解了革命与摩登的尖锐对立。这是《长恨歌》的又一叙事创获。
当然,中国人长久以来就相信此一时彼一时,无论是周易之辩,还是老庄之学都讲求变通,王琦瑶在时代之乱与变的大势中谋求通变本无可厚非,然而王琦瑶于摩登时代里拒绝接受任何关于健康人生的指导,全面放弃人之为人的底线,一旦进入革命时代,其如变色龙般再次吞食自己先前所执迷的摩登信仰,此次邬桥行又通过与人民政权时期的上海拉开距离,既全面抛弃了那些不实用的摩登颓靡热情,又有效地避免了革命时代清理历史垃圾的可能,成功地洗白了身份,自我道德解绑轻易地促就了革命时代的人生转型。乍看人生转型似乎完成了,而人性堡垒则很难被攻破,转身容易而“翻心”实难,摩登生活必然为王琦瑶所执迷。
四 不绝如缕的摩登主义
1949年后,中国大陆进入人民政权时代,革命是此后30年间的主流话语,王琦瑶经过自我洗白后重返原生地——上海弄堂,重新发现并欣喜于都市民间的日常生活样态:“平安里的一日生计,是在喧嚣之中拉开帷幕;粪车的轱辘声,刷马桶声,几十个煤球炉子在弄堂里升烟,隔夜洗的衣衫也晾出来了,竹竿交错,好像在烟幕中升旗。”1王安忆:《长恨歌》,第148、150页。虽然是一场无可奈何的回归,但上海市民真切的日常生活很快治愈了王琦瑶的伤痛:“令人目不暇接的细节化叙述,带出的是日常生活素朴的美和鲜活的生命质感。”2刘艳:《上穷碧落下黄泉,续上海繁华旧梦——王安忆〈长恨歌〉重释》,《长江文艺评论》2019年第3期。王琦瑶适应了人民政权时代的弄堂生活,其平民化的护士职业是新时代按劳分配制度的产物。同时王琦瑶之所以是王琦瑶,仍在于她不会单纯地满足此类日常生活,其摩登底子作为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就轻易地苏醒了:“王琦瑶总是穿一件素色的旗袍,在五十年代的上海街头,这样的旗袍正日渐少去,所剩无多的几件,难免带有缅怀的表情,是上个时代的遗迹,陈旧和摩登集一身的。”“周璇的《马路天使》,白杨的《十字街头》,这也是旧相识,最不相关的故事也是肺腑之言。”3王安忆:《长恨歌》,第148、150页。怀旧的乌托邦性质并不能遏止人类的怀旧冲动,在时代更替之际尤其近乎本能,而每每通过历史记忆与残存碎片重建当下与过去的联系通道,将当下生活与历史记忆进行勾连,在历史缅怀中不断体味与咀嚼一种伤感主义成为文学叙事的迷宫。摩登主义于1946—1949年之际的王琦瑶而言就是危机重重中的繁华梦:“当她们以牺牲自己全部的代价来走向自己一生中最为光彩夺目的顶峰时,正好遇到这个社会整体开始滑向低谷和最后幻灭。这种在个人命运与时代风云之间出现的奇谲莫测的错位,恰恰以一种残酷荒谬的玩笑,讽刺了市民阶层怀旧梦的虚假,为所谓的‘上海寻梦’奏起了一曲挽歌。”4陈思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01页。1949年之后,作为历史惯性与心理真实的摩登主义以记忆碎片形式再次进入民国遗民的视野中,王琦瑶是这个怀旧群体的代言人。这也是王琦瑶与《长恨歌》能够担当起王安忆“怀旧”叙事执念的魔力所在。
摩登主义作为历史盛景全面走向革命时代的日常生活。王琦瑶在与同为民国遗民的严家师母的争强斗勇中以不凡的化妆技巧获胜,除了年龄优势外,当源于其对上海摩登风尚习得之深。及至在艰难的生活中保障精致的每日饮食,外界处处风声鹤唳而其仍迷恋玩牌等娱乐活动,均源于上海摩登作为一种记忆回落至日常生活的新常态:“随波逐流,随遇而安,不求大富大贵(能得到也好),只求太太平平过得去,心理上始终保持一种满足感。”1王铁仙等:《新时期文学二十年》,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38页。程先生再次邂逅王琦瑶并与其旧情复燃,王琦瑶对之有意低徊与暧昧丛生即如王安忆所言是“与往事干杯”。“文革”结束后,王琦瑶的女儿薇薇步入青春期,在新一轮的争奇斗艳中,王琦瑶与薇薇关于摩登认知上的高下之别立显,结局当然不是江山代有才人出的年轻一代走上摩登舞台,而是王琦瑶借助1940年代的摩登体验,在1978年以来上海怀旧热潮萌生伊始即占得先机,那些深藏已久的前朝服饰与器物本身并不具备一丝光晕,而是拥有它们的主人王琦瑶关于摩登时尚的体验位于二十世纪摩登风潮的制高点,上海摩登的韵味深厚已具备超越革命话语的力量。进而言之,无论是1940年代的李主任,1960年代的康明逊,还是1980年代以来的老克腊,三个时代翻来覆去,而王琦瑶幼时以来习得的摩登颓靡气息却具备了永恒性。不管是李主任将其作为“人生娱乐”,还是康明逊将其看作“是上个时代的一件遗物”,抑或是老克腊的怀旧寄托,概因王琦瑶承载着三代男性迷恋上海摩登的物化想象:“摆设”“造物”“娱乐”。诸如此类叙写都是创作者为了凸显上海摩登的永恒性、超越性的叙事设计,也就是革命话语即使全面主宰当代中国社会也不会从根本上动摇上海摩登的文化与文明根性。“王琦瑶与其说和这几个男人发生情感和肉体的纠葛,不如说始终在和旧上海发生关系,这样的纠葛让旧上海一点点复活,历史在变,但都有旧上海的男人在场,革命的强大的历史反倒是背景,旧上海情爱与生活反倒始终在场”2陈晓明:《在历史的“阴面”写作——试论〈长恨歌〉隐含的时代意识》,《文学评论》2013年第6期。,“在王琦瑶身上容纳了几代的上海市民阶层对上海四十年来都市日常生活的追忆和难以言明的梦想”3陈思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第二版)》,第299页。需要说明的是,对王琦瑶迷恋与心向往之的三代上海男性并不全是“上海市民阶层”,而应为三代上海有钱有闲者。,“王琦瑶一生其实都是坚忍和坚韧的海派文化中女性生存方式和生命形态”。可以说,上海摩登成为王安忆上海叙事的最高价值典范,进而走向迷信。
王安忆有个叙事冲动,即在召唤性结构中,有将旧上海的摩登颓靡普泛化进而作为一种风华来写,其实是混淆了二者的区别。颓靡是人生放纵心性基础上的伤感迷恋至陷溺的状态,而一个时代的风华则是格局、心态与风流的生命启示,二者不能同日而语。因此,不能借民国风华经历风吹雨打摧折后的屹立不倒及超越性的文化与文明力量呈现复活一种低级趣味。具体而言,民国风华复兴尚有一丝文化基础,而颓靡情调的反刍近乎痴人说梦,虽然本质都是一种乌托邦寓言。饶有意味的是,创作《长恨歌》稍后的王安忆对追怀民国颓靡往事和风华的不可完成性有清晰的判断,如《富萍》的上海叙事就已经离开摩登颓靡而转向抒叙异乡人的现代都市求存体验。只是王安忆一直以来太过于相信“怀旧热”与上海摩登的魔力,其对上海摩登颓靡有种近乎一往情深的耽溺,所以《长恨歌》面世二十多年后,《考工记》仍力图在残破的器物中寄托并想象民国盛景,一座庭院熬过了革命岁月的风蚀雨蛀仍屹立不倒,但终究不可遏抑地走向残破,陈书玉的坚守与王安忆的追怀再次变成幻梦,即使上海摩登和一座座民国沪上花园依旧存在,民国也回不来了。《一把刀,千个字》在追念精致与丰腴的淮扬菜系筑建起的日常弄堂生活后指向历史的灾变,上海摩登气息渡过革命时代的大劫后早已烟消云散,只留人间沧桑坚硬地存在,也只有日常美食具备跨越历史时空的力量,但其兴盛早不复当初。可以说,即使上海摩登作为上海百年文化史与文明史上最具创造性的形态,也无论叙述者如何讲述与无限缅怀摩登时代,其作为历史仍渐行渐远。民国作为一个时代已然终结,后来者可以将之当作审美对象,但大可不必过于哀伤地想象着寄寓其中,至于陷溺在此类历史盛景,那就是糊涂人的一厢情愿了。
五 一份文学与文化行进的启示录
1980年代以来,上海摩登作为上海历史文化的典型形态之一同步复苏,《长恨歌》及文学形象王琦瑶便是这一召唤结构的产物:“《长恨歌》在王安忆的所有创作中很特别,不只是她讲的故事,而是她讲述故事的态度,她讲述的故事的面向——她并不反思历史,她愿意欣赏做旧的历史。”只是无论上海学者和作家们如何努力,“后革命时代”的大环境也确乎在经济复苏的强力支撑下走向新的摩登与现代,1990年代以来的上海还是不会全面重返1930年代的摩登颓靡,民国情调最多存在于点点斑斑的历史文化街景和世纪之交的各种怀旧读物中,迈向国际化大都市的上海越过了摩登时代的颓靡情调而全面高扬消费主义与世俗精神。于是,王琦瑶1980年代的最后风华就来自作家王安忆和王琦瑶们的自我错位期待与错误定位,随着人文精神大讨论的落幕,上海摩登作为文化与文明复兴的召唤性结构就是一场当代文化梦幻,《长恨歌》寓言了上海摩登主宰人性的欲望化结构、传统才子佳人结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对女性的物化结构、现代时期以来女性堕落原型等的回光返照。从文学的现代性视野来看,美国学者马歇尔·伯曼关于现代性症候“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论述从根本上道明了现代性文学对人类历史命运的终极观察。在历史长河中,王安忆用以对抗革命政治的摩登颓靡本来就是一个刹那存在,更何况1930年代以来高度发育的上海摩登在精神旨趣上日趋走向畸形,金钱主宰人性成为文学内外的真实。当革命力量抽空了上海摩登的畸形资本力量,并以制度形式予以根除后,1930年至1945年上海摩登的当代复活也只剩理论可能和想象的重构了。
上海摩登本来就不是一个摩登颓靡的情调、概念及相应的心理结构所能涵盖的,1930年代以来的上海摩登给彼时的中国社会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和思维空间,其中包括现代公寓、消费购物、建筑美学、林荫大道、公园街景、无轨电车、科学医疗、卫生防疫、现代出版、大众传媒、文化沙龙等公共服务与新的人文-科学空间。这在最大限度上改变了中国文明的历史进程,世界主义、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在中国全面落地生根,人生与人性启蒙以全新的技术手段介入时代中国。这些都应该被持续发掘并做出符合历史与现实的评判,后来者更应批判性地借鉴与继承这一文化与文明遗产,而不应将颓靡欲望完全等同于上海摩登并将其普泛化、绝对化与本质化,尤其在1990年代以来意识形态松动的语境下,就不应将民国时代上海摩登的颓废面以偏概全地上升为彼时的时代盛景,《长恨歌》对摩登上海的颓废欲望与颓靡情调之重构,说到底不过是一厢情愿的想象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