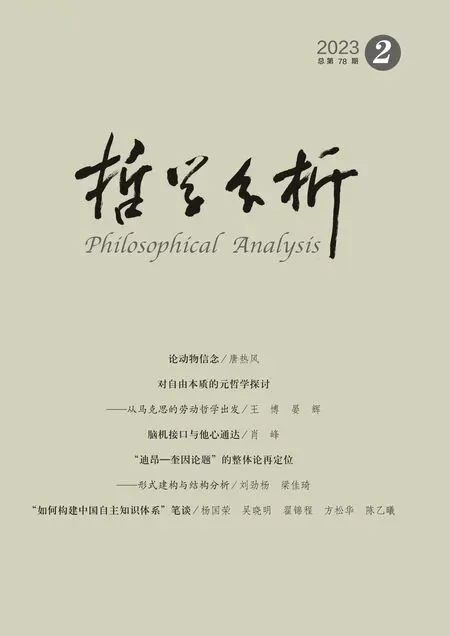海德格尔和阿伦特对奥古斯丁《忏悔录》第十卷的解读
2023-10-03王寅丽
王寅丽
阿伦特在雅斯贝尔斯的指导下完成的博士论文《奥古斯丁的爱的概念》 (Der Liebesbegriff bei Augustin),1929 年在柏林出版,这是她1951 年发表《极权主义的起源》之前出版的唯一著作。1996 年出版的英译本《爱与圣奥古斯丁》 (Love and St.Augustine),是在此书的英译稿和阿伦特1960—1961 年对英译稿的部分修订的基础上编辑而成的。在1920—1930 年的德国学界,奥古斯丁是一个持续的热点,被视为存在主义的先驱,引起了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天主教哲学家瓜尔蒂尼(Romano Guardini)、新教神学家布尔特曼(Rudolf Bultmann)的研究兴趣,阿伦特那一代青年学子也沉浸在此学术氛围中,纷纷以奥古斯丁为论文选题。①海德格尔1921 年夏季弗莱堡讲座以“奥古斯丁与新柏拉图主义”为题,该讲座已收入海德格尔全集第60 卷,即《宗教生活现象学》 (Phänomenologie des Religiösen Lebens);雅斯贝尔斯为他的未完成的《大哲学家》写了《柏拉图与奥古斯丁》两章;瓜尔蒂尼1935 年发表了《奥古斯丁的皈依》 (The Conversion of Augustine);汉斯·约纳斯的首部著作(1930 年)是《奥古斯丁与保罗主义的自由问题》 (Augustin und das paulinische Freiheitsproblem)。在围绕着奥古斯丁展开的思想激荡中,阿伦特与海德格尔的关联无疑十分重 要。
海德格尔对奥古斯丁的全面解读开始于1921 年夏季学期在弗莱堡大学开设的讲座。在以“奥古斯丁与新柏拉图主义”为题的初步考察中,他首先批判了19 世纪德国思想界对奥古斯丁的种种历史主义阐释进路,表明他真正关切的是宗教的“事实生命经验”(faktische Lebenserfahrung)。海德格尔对奥古斯丁《忏悔录》第十卷的解读,是他的“实事诠释学”(hermeneutics of facticity)形成中的重要环节①James K. A. Smith, “‘Confessions’ of an Existentialist: Reading Augustine After Heidegger: Part I”, New Blackfriars,Vol. 82, No. 964, 2001, p. 273.,并引向了《存在与时间》中对于此在的生存论分析。海德格尔的《奥古斯丁与新柏拉图主义》和阿伦特的《爱与圣奥古斯丁》都以对奥古斯丁《忏悔录》第十卷的解读为重点,他们都从“事实生命经验”的角度来解读奥古斯丁,都坚持他们的解释是现象学的而非神学的。②Hannah Arendt, Love and Saint Augustine,Joanna Vecchiarelli Scott& Judith Chelius Stark (eds.),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p. 4; 中译本参见阿伦特:《爱与圣奥古斯丁》,王寅丽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9 年版,第39 页;Martin Heidegger, Phänomenologie des religiösen Lebens, Frankfurt am Main:Vittorio Klostermann, 1995, S. 210; 中译本参见海德格尔:《宗教生活现象学》,欧东明、张振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年版,第234 页,译文略有改动,下同。海德格尔对奥古斯丁的阐释已得到较多研究③例如:Frederik Van Fleteren (ed.), Martin Heidegger’s Interpretations of Saint Augustine: Sein und Zeit und Ewigkeit,Lewiston: The Edwin Mellen, 2005; Daniel Dahlstrom, “Truth and Temptation: Confessions and Existential Analysis”, in S. J. McGrath & Andrzej Wierciński (ed.), A Companion to Heidegger’s Phenomenology of Religious Life, New York: Rodopi B. V., 2010;中文研究主要有李成龙:《从幸福生活到实际生活:论海德格尔对奥古斯丁〈忏悔录〉卷十的阐释及其得失》,载《道风:基督教文化评论》,第54 期,2021 年,第462—501 页;邵铁峰:《海德格尔与奥古斯丁的恐惧诠释》,载《哲学与文化》2020 年第9 期;王坚:《奥古斯丁的自我生命——海德格尔对〈忏悔录〉第十卷的现象学阐释》,载《科学·经济·社会》2013 年第1 期。,阿伦特的奥古斯丁解读也随着她的博士论文英文版的问世而受到重视,但是阿伦特与海德格尔这两部论奥古斯丁作品之间的关联却鲜有讨论。阿伦特的研究者多数认为她在政治上对“现象学存在主义”的发展是对海德格尔的批判和超越,却鲜少关注他们之间的分歧更早产生的这一起源。④例如Villa, Dana, Arendt and Heidegger: The Fate of the Political,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Martin Jay, “The Political Existentialism of Hannah Arendt”,in Permanent Exiles: Essays on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from Germany to America,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237—256; Lewis P.Hinchman and Sandra K. Hinchman, “In Heidegger’s Shadow: Hannah Arendt’s Phenomenological Humanism”,The Review of Politics, Vol. 46,No. 2,1984, pp. 183—211。本文大致依照海德格尔对《忏悔录》第十卷所作的章节划分,将第十卷主要内容分为四部分:第1—7 章的引言部分,第8—19 章对“遗忘”和“记忆”的分析,第20 —39 章对“欲望”和“实际生活”的分析,第40 —43 章为结语。我们首先讨论海德格尔和阿伦特在解读引言部分时提出的不同解读路向,然后比较他们对记忆和欲望部分阐释的要点;最后基于以上指出的内在联系,说明阿伦特在揭示人们组成的“共同世界”方面与海德格尔的“共在世界”的分 歧。
一、《忏悔录》第十卷第1—7 章引出的解读路向
奥古斯丁出生于公元354 年,《忏悔录》写于公元397 年至401 年间,讲述了他从出生直到33 岁皈依上帝为止的生活历程,被誉为西方思想史上第一部精神自传。“忏悔”(confession)在书中有认罪、皈依和见证三层含义:对背弃上帝的前半生所犯下的罪过表示悔恨,请求上帝的宽恕;“忏悔”同时也是作者对自己的反省,以回忆的方式从现在之“我”的角度观看过去之“我”:“但现在我站在你面前,通过这本书向人们既忏悔现在之我,也忏悔过去之我。”(X,3:4)①Augustine,Confessions, Albert Cook Outler (trans.), Peabody: Hendrickson Publishers, 2004.中译本参见奥古斯丁:《忏悔录》,周士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年版,以下此书引文仅在括号中用罗马数字标出卷次,用阿拉伯数字标出章和节。这个不同于“过去之我”的“现在之我”在忏悔中呈现出来;另外,“忏悔”(Confessor)在拉丁文中也有“见证”的意思,奥古斯丁在第十卷开篇表示要以文字的形式在众人面前承认自己的过错,见证上帝在自己身上的作为:“因此我愿意透过我的忏悔,在你面前在我心中,同时在许多见证人面前这样做。”(X, 1:1)“忏悔”的言说首先是“在上帝面前”,其次是“在众人面前”的言说,向着上帝的忏悔唤醒了被遗忘的“内在之我”,对众人见证的目的则是“履行真理”(veritatem facere),揭示真理,希望读者从中获得益处。以《忏悔录》的自传性质来说,本书到第九卷已经结束,第十一、十二、十三卷是从神学上对圣经《创世记》开篇的解释。但第十卷却是全书最有哲学性的一卷,是从前九卷的忏悔文学向神学主题的转折。在这卷中奥古斯丁提出著名的“自我之问”(“quaestio mihi factus sum” [I have become a question to myself]),并将自我理解为存在于永恒上帝中的“记忆之我”,使得个人生命通过记忆的中介与永恒生命汇合。前九卷的自我叙事汇入后三卷更为宏大的圣经创造叙事之中,自我的故事在创造故事中获得意 义。
正如J. K.史密斯指出的,奥古斯丁主题对存在主义传统最深刻的影响之一是自我对于理解存在或生存的优先性。②James K. A. Smith, “‘Confessions’ of an Existentialist: Reading Augustine After Heidegger: Part I”, p. 275.在第十卷开篇讲述了“忏悔”的含义和目的之后,奥古斯丁自问作为忏悔者的“我”是谁,既然我在上帝面前是完全袒露的,为何还要向他忏悔?别人听我谈论自己,只能认识过去的我,却不认识现在的我,“而这方寸之心才是真正的我”(X. 3:4)。在奥古斯丁看来,人并不知道自己真正是“谁”,真正的我既不是我的人生故事,也不是别人眼中的我,而是这个“内在之人”(ipse intus)。就像莎士比亚创造了哈姆雷特,从而了解他的全部一样,“我是谁”的问题,即我的存在和意义的问题,要从他存在的源头、创造主那里得到回答。阿伦特评论说,奥古斯丁这种转向自身存在的源头,从“造物主—受造物”(creatorcreature)的语境下来理解人之存在的方式,隐含着一种根本的人类依赖性(human dependence):“人非自造,乃是被造,这个事实意味着人存在的意义感既在他自身之外,又先于他自身。”①Hannah Arendt,Love and Saint Augustine, p. 49, p. 50;阿伦特:《爱与圣奥古斯丁》,第98 页、第100 页。
在《忏悔录》第十卷第6 章,奥古斯丁从对自我的发问转向对上帝的发问:我爱上帝,究竟爱的是什么?(X. 6:8)海德格尔认为奥古斯丁在忏悔态度中所传达的所有现象都处在“寻求和拥有上帝这一任务之中”,“重要的是指出经验上帝得以付诸行动的真正条件”。②Martin Heidegger,Phänomenologie des religiösen Lebens, S. 283;海德格尔:《宗教生活现象学》,第335 页。如同《存在与时间》中对此在的发问从属于存在是什么的根本问题一样,在这里他指出“我”通过爱的经验行为获得对“上帝”(存在)的领会。海德格尔以现象学方法解读“神之爱”:“当他活在神之爱(the love of God)中时,有什么向‘充实性直观’(fulfilling intuition)呈现,什么东西满足和充实他在对神之爱中所意指的东西”③Ibid., S. 178—179;同上书,第192 页。。奥古斯丁把人分成“外在之人”和“内在之人”(homo interior),外在之人从物质对象的经验(形貌的秀丽、暂时的声势、肉眼所好的光明灿烂等)中不能把握上帝,上帝也不在大地海洋、飞禽走兽、日月星辰当中(“我问这一切事物,它们皆回答‘我们不是你所寻求的上帝’”)。但我经验到我内在拥有另一种“内心的光明、音乐、馨香、饮食、拥抱”。这类经验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在上帝那里永存。在海德格尔看来,这个“内在之人”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之灵魂,也不能以希腊—罗马哲学中的理性灵魂来理解,因为内在经验到的上帝是“我的上帝”,这个内在者“被经验为在人之中渗透身体、驱动和为之贯入生机的东西”④Ibid., S. 180;同上书,第194 页。,从而上帝被经验为“越—出”(ek-static)我的灵魂者,表明灵魂本身有待被超越。海德格尔因此区分了奥古斯丁寻求上帝的两种路向,一种是把上帝视为经验的最高“对象”,存在者的最高秩序来寻求,一种是进入此在的具体历史—生存分析。“通向秩序关涉和对象关涉的生存上的突破之进路(Ansatz)——心理学,或者对于以具体的历史的—生存的方式来自实际生活的问题之解释和领会。”⑤Martin Heidegger,Phänomenologie des religiösen Lebens,S. 181;《 宗教生活现象学》,第196 页。接下来他将《忏悔录》第十卷第8—19章阐释为第一种寻求上帝的路向,第20 —39 章阐释为第二种寻求上帝的路向。⑥参见Ryan Coyne,Heideggers Confessions: The Remains of Saint Augustine in“ Being and Time” and beyond,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5, pp. 63—64。
阿伦特在《爱与圣奥古斯丁》中对奥古斯丁的解读,着重于分析“上帝之爱”与世俗社会生活的“邻人之爱”(neighborly love/Nächstenliebe)之间的张力。⑦阿伦特在博士论文德文版中轮流使用“邻人”(der Nachbar/der Nächste)和“他人”(der Anderer),第二章第3 节标题为“近人之爱”(Dilectio proximi)。既然“爱邻如己”的要求包括在基督教“爱上帝”的命令中,她追问这两种爱在奥古斯丁关于爱的概念中是否内在一致。“自爱”(amor sui)是将“上帝之爱”与“邻人之爱”联系起来的枢纽,但她发现奥古斯丁的“自爱”实际上有两个并不一致的意涵:一种是在“爱作为欲求”的概念语境中以希腊哲学的自足、无依赖性来定义的,在那里,真正的自爱是从无欲求的“绝对未来性”(absolute futurity)角度否定现实自我,并从“爱的秩序”出发合宜地、冷漠地爱每个人。对奥古斯丁而言,“这种自忘(selfforgetfulness)和对人之存在的彻底否定的最大困境是,它使基督教爱邻如己的核心命令变得不可能了”①Hannah Arendt,Love and Saint Augustine, p. 27, p. 28;阿伦特:《爱与圣奥古斯丁》,第69、71 页。。另一种是在“造物主—被造物”的概念语境中来定义自爱,“自爱”始于人的自我追问(quaestio mihi factus sum)。“正是这种对自我的寻求,让他最终转向上帝。”②Ibid, p. 25; 同上书,第66 页。在人转向上帝的同时,上帝之爱(amor Dei)将人的生命“唤入存在”,让人的生命不再是无。后一种“自爱”概念肯定人的依赖性,因为人从无中被造,人的存在从无到有,介于存在与不存在之间,这种变易、不确定的存在方式需要和绝对存有相连,即人的存在过程始终依靠上帝之爱的扶持。她认为这个自我就是奥古斯丁在《忏悔录》第十卷揭示的“内在之人”,造物主内在于我的居所。这个“内在永恒”(internum aeternum)是我所缺乏、所不是者,但它却是上帝之爱和邻人之爱的深奥核心,“人本质的‘居所’,这个肉眼不可见的‘内在之人’正是不可见的上帝工作的领域”③Ibid, p. 26; 同上书,第68 页。。在她看来,正是自我和上帝之间的爱的关系——我爱“我的上帝”和上帝的觅人之爱,体现出人与上帝的相似性,人所具有的独特“上帝形象”(imago Dei)本质上是一种建立爱的关系的能力。这个我在爱中把握的“我的上帝”,我的渴求和爱的正确对象,是奥古斯丁内在自我的核心,其“心灵的本质”。人心随着时间变换,心灵的本质却超越了时间,“我可以凭借爱而归属于这一本质存有,因为爱赋予其归属”,超越于我的永恒本质在我自身之内,“因为你就是你所爱”。④Hannah Arendt,Love and Saint Augustine, p. 26;阿伦特:《爱与圣奥古斯丁》,第67—68 页。可见,阿伦特与海德格尔都尝试对奥古斯丁的上帝观作出区别于古希腊式的,特别是新柏拉图主义上帝观的“宗教生活经验”阐释,海德格尔将寻求上帝引向此在(自我)的生存分析,阿伦特则引向对爱作为人之存在的构成性活动的分 析。
二、《忏悔录》第十卷第8 章的“遗忘难题”
《忏悔录》的作者在自我见证中对“我是谁”的发问,也是对“我的上帝”为何的发问。站在基督教立场上,奥古斯丁认为上帝是人的创造者和生命本源,人对自身的探索必须在上帝之内进行,而人要洞见本源性的上帝,就需要灵魂的内在转向。在他那里,灵魂向内的探索同时是一个灵魂上升的过程:“我要超越我本性的力量,层级上升趋向我的创造主。我进入记忆的领地,那里是储藏感官对一切事物所感受而进献的无数影像的府库。”(X, 8:12)正如吴飞指出的,记忆有“连接自我与上帝之存在的功能”①吴飞:《奥古斯丁与精神性存在》,载《哲学动态》2018 年第11 期,第51 页。。在《忏悔录》第十卷第8 至19 章,奥古斯丁对上帝的寻觅从自身以外转回到心灵记忆中“自外而内”的找寻。记忆里包含着无数事物的图像,以及我们关于它们同时想到和感受到的一切,经过思想的收集、加工、增损都储备在里面,随时听从我们的召唤,构成“一种广阔而无限的内在”(penetrale amplum et infinitum)②Martin Heidegger,Phänomenologie des religiösen Lebens, S. 182; 海德格尔:《宗教生活现象学》,第196 页。。奥古斯丁依次考察了五种记忆类型:第一种是感性对象的影像,包括颜色、声音、气味、味道等;第二种是非感性的知识,如文学、论辩学以及各种知识问题;第三种是数理对象,包括数学和逻辑;第四种是内心的情感,如对快乐、希望、忧愁、恐惧的记忆,以至于人能喜悦地回想曾经的悲伤,或忧伤地回想往昔的快乐;第五种是“对遗忘的记忆”。在论及最后一种类型时,他阐述了著名的“遗忘”疑难(aporie)——遗忘是记忆的缺失,既然遗忘,便无从记忆,但我们又怎么会记得我们忘记了什么呢?比如我们常常忘记了什么东西,但当别人问是不是这个或那个时,我们又能说是这个或不是这个,可见并非全然忘记。③对“遗忘疑难”的分析,参见保罗·利科:《记忆,历史,遗忘》,李彦岑、陈颖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年版,第125—126 页。“遗忘疑难”表明记忆的“内在”空间有着自身不可触及的深层性,自我与永恒上帝之间存在着深不可测的距离。奥古斯丁一边感叹记忆的广大深邃令人敬畏,一面继续向上帝发问:你在哪里,我到哪里去找你?——“我将超越记忆而寻找你。但在哪里寻见你,……如果在记忆之外寻找你,那么我已不记得你。如果根本不记得你,那么我怎能找寻你呢?”(X, 17:26)可见心灵更根本的遗忘是对上帝的遗忘。奥古斯丁遍历记忆的角角落落找寻上帝:“我进入了心灵的最内室,这是记忆专为心灵而设的——因为心灵也回忆自身——你也不在那里,因为你既不是身体影像,也不是活人的情感(如我们欢乐或悲伤时感受到的,或我们愿望、恐惧、回忆、遗忘,诸如此类时感受到的),又不是我的心灵本身;你是心灵和所有这一切的主宰,而你永不变易地居于这一切之上”(X, 25:36)。人的心灵中所有关于物质、情感、思想的记忆,都不是对上帝的记忆,后者居于人的心灵之中,却超越人的心灵之上。对奥古斯丁来说,上帝正是透过心灵的内在空间向他显露:“到哪里能找到你以便认识你?只能在你之内,在我之上”(X, 26:37)。
奥古斯丁用“遗忘难题”揭示出心灵的内在广阔空间,也引出人有着对“幸福生活”(Beata Vita)的回忆,以及幸福求而不得、人生无法免于被试探诱惑的困境。他在早期作品《论幸福生活》中就表述了幸福在于拥有上帝、享受上帝的观点,不仅因为在他继承的古典的至善幸福论中上帝是最高善,以及在新柏拉图主义的存在序列中上帝是至高完满存在,还因为奥古斯丁从基督教立场指出人有一种根本的存在性缺乏——如《忏悔录》开篇所叹:“我们的心如不安息在你怀中,便不会安宁”。在第十卷第20 章,他说:“我寻求你,就是在寻求幸福生活。”他指出,人人都意愿幸福,却并不拥有幸福。可是没有幸福,人们又是从哪里知道幸福呢?也许它存在于我们的记忆中,我们总有过一些幸福生活的模糊影像,对幸福生活的记忆最终让我们渴望幸福本身,即归向作为完满存在的上帝。“幸福生活就是朝向你、在你之内、为了你而欢乐,这就是幸福,此外无他。”(X, 22:32)在考察幸福生活时,奥古斯丁不得不正视人的欲望享乐的问题。在尘世生活中,自我本有被世间欲望所吸引而“消散在万物中”(X,29:40)、灵魂又总是受“习惯”的牵引而下坠;他在第30 —39 章依此分析了“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三种贪欲,并深深认识到人靠自身能力无法抵挡心灵的混乱失序状况,“我对我自身成了一个谜”(X,33:49),而上帝则是自我之谜的真正答案。第十卷卷末(第43 章)指出只有上帝之爱才能拯救人脱离罪恶重压下的生活,呼应了后三卷关于圣经的创世主 题。
三、“诱惑”和“爱”的现象学阐明
奥古斯丁关于灵魂在记忆的内在空间上升的观念,受到新柏拉图主义的普罗提诺的影响。普罗提诺主张灵魂的自我转向和逐级上升运动,灵魂转向之所以能够发生是因为至善、绝对或上帝的理念已经存在于灵魂记忆之中。不过与普罗提诺不同的是,奥古斯丁的记忆回转之路始终受一个“觅人的上帝”的引导。①参见章雪富:《救赎:一种记忆的降临——奥古斯丁〈忏悔录〉第十卷至第十三卷研究》,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 年版,第35 页。海德格尔在这里批评奥古斯丁的记忆概念仍受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不是关注历史性此在赢得“幸福”的生存运动,而是受永恒不变的“持存”的规整:“记忆(memoria)没有彻底地、生存地付诸实现,毋宁说,按希腊的讲法,它在内容上是下坠的,不是它如何‘曾是’与他同在以及在‘曾是’中如何‘是’。”②Martin Heidegger,Phänomenologie des religiösen Lebens, S. 247;海德格尔:《宗教生活现象学》,第286 页。相比于记忆,他更为重视奥古斯丁的“遗忘”在生存运动中的地位。“遗忘”是记忆的不在场,作为当前未进入掌握之中的东西,但这里的遗忘不是记忆的彻底缺失,而是“遗忘的记忆”(即我记得遗忘本身)。在他看来,奥古斯丁的遗忘让所关涉意义的“不在场”得到了把捉,“先把握”(Vorgriff)得到了非当下的呈现。海德格尔指出了它在现象学上的两层含义。第一,它与当下呈现之物的意向性关涉意义——原本的拥有和可能会失去的拥有,来到隐而未现的把握之中:“遗忘不是回忆的彻底缺失,它有着意向性关涉意义。从关涉上理解就是我们在失落某物时,我们仍然‘拥有’它”①Martin Heidegger,Phänomenologie des religiösen Lebens, S.191; 海德格尔:《宗教生活现象学》,第208—209 页。。第二,“遗忘”唤起更深层次上的存在论遗忘:在寻找的时候,还有什么是可供我资用的?我在为着什么寻找?什么东西在逃离我而去?在奥古斯丁那里寻找发生在对上帝之为真实生命的失落和找寻中,在海德格尔看来,奥古斯丁意义上的上帝经验并不是孤立的具体行为或理论构型,而是“存在于本己生活的历史实相(der historischen Faktizität des eigenen Lebens)的经验关涉中”②Ibid., S. 294; 同上书,第360 页。,故而,“在我对上帝的寻找中,在我之中的某物不仅得到了‘表达’,而且构建着我的事实生命和我对它的关切”③Ibid., S. 192; 同上书,第209 页。。
近代以来,笛卡尔的“我思”通常被视为“奥古斯丁式自我”的继承,但海德格尔在《奥古斯丁与新柏拉图主义》中明确批评说,笛卡尔的主体理论把自我研究带到了错误的方向,他主张:“奥古斯丁意义上的自身确定(self-certainty)和自身拥有(self-possession)完全不同于笛卡尔的‘我思’(cogito)的明证性。”④Ibid., S. 298; 同上书,第356 页。自我不是具有明证性的“我思”,而是始终处在不确定、不安、对自身的“不拥有”的开放性生存过程中。海德格尔对此的分析集中于后半部分的“诱惑现象学”。他指出,在奥古斯丁那里,自我流散于万物,在自身之外寻求意义。当上帝的召唤临到它,它被命令对抗流散,对抗生命的分崩离析来“集聚”自身。“将你所命赐予我,并依你所愿来命令我。”(X, 29:40)但这个对抗流散的反向运动在自身中并不能一劳永逸的赢获,生命不断地将自身向反方向拉扯,从而奥古斯丁式的自我始终具有一种“越—出”(ek-static)的特征。“我永远不能诉诸一个静止的时刻,在其时我貌似看透了我自己;总是有下一个时刻能让我跌倒,并暴露出我是全然不同的另一个我。出于这个原因,只要拥有—自身毕竟是可以实现的,它就总是处在朝向和远离生命的拉扯之中,一种来来回回。”⑤Ibid., S. 217; 同上书,第244—245 页。在海德格尔看来,试探、诱惑(tentatio)是据以理解宗教经验生活的本质,他以奥古斯丁引用的《约伯记》名言——“整个人生是一场试探”——来概括“此世生活”的特征。接着也依照“肉体的贪欲、眼目的情欲、世俗的骄傲”⑥奥古斯丁关于世间欲望的三种划分来自《新约·约翰一书》2 章16 节。的顺序分析了诱惑的三种形式,对他来说,这不是自我与世界、肉体与灵魂、“爱世界”与“爱上帝”之间的搏斗,而是作为生命实际生活基本特质的“关切”(curare/care)的三种形式。诱惑的前两种形式分别来自周围世界(感觉和认知)引起的愉悦、好奇,感觉是与某物打交道(Umgehen)的欲求,认知是在各种不同的范围和领域里的寻视(Umsehen),前两者指向“周围世界”(Umweltlich)。第三种形式“世俗的骄傲”(ambitio saeculi)则来自与他人共在的世界,因为我们从那里获得对自身价值和自我意蕴的关切,正是与“周围世界”和“共在世界”(Mitweltlich)的无休止对抗,让信仰生活成为真实的生命。如李成龙所指出的,对诱惑的存在论分析是《存在与时间》中分析“沉沦”概念的基础。①李成龙:《从幸福生活到实际生活:论海德格尔对奥古斯丁〈忏悔录〉卷十的阐释及其得失》,第488 页。另参见《存在与时间》中的论述:“此在为它自己准备了要去沉沦的不断的引诱,在世就其本身而言是充满诱惑的。”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年版,第250 页。
阿伦特仍然通过分析爱的概念来说明奥古斯丁对古典幸福论的超越,爱者的最终目标是他自身的幸福,但他并不拥有幸福,而是在其所有活动中被非他自身的某种东西所引导,被驱向自身之外。她认为让奥古斯丁摆脱斯多葛学派和普罗提诺影响的,正是他对人之为人的“依赖性”(dependency),非自足性的体验,也是促使他归向上帝的经验,即人必须与自身之外的他人、世界或上帝建立联结。阿伦特以爱的两种“概念语境”(conceptual context)——希腊哲学和新柏拉图主义的“爱作为欲求”语境和基督教的“创造主—被造物”语境,来分别阐释奥古斯丁在《忏悔录》第十卷所描绘的“欲望”和“记忆”的寻求模式。在“爱作为欲求”的定义中,欲求规定了爱者和爱的对象:“欲望介于主客体之间,通过把主体转化为爱者,把客体转化为爱的对象,消除了它们之间的距离。……既然人非自足,总是要渴求在他自身之外的某物,那么他是谁的问题就只能通过他欲望的对象来回答,而不是像斯多葛学派认为的,通过对欲望本身的压抑、消除来回答:‘因为你就是你所爱’。”②Hannah Arendt,Love and Saint Augustine, p. 18;阿伦特:《爱与圣奥古斯丁》,第57 页。贪爱(cupiditas)和圣爱(caritas)在此的区别在于爱的对象不同,前者是对属世对象的爱,渴求尘世中能带给人的满足之物,却总是伴随着对丧失的恐惧(fear of losing),并最终落在对死亡的最大恐惧中。这种根本的恐惧只有当我们所欲求的对象是永无丧失之虞的“永恒”时才会消除。在此语境下,“圣爱”寻求永恒的“绝对未来”或“无未来的现在”,“这个无未来的现在——不再关注具体的善,因为它本身就是至善(summum bonum)——就是永恒”③Ibid,p. 13;同上书,第50 页。。“圣爱”的永恒视角建立的秩序,规定了任何人或任何物都不能“因其本身的缘故”而被爱或被渴求,而应当“为着上帝的缘故”被爱,只有上帝才能“因其自身”被爱,简言之,人对世界的恰当态度是“使用”(usi)而不是“享受”(frui),只有上帝才是享受的对象。由此,人自身的生命被设定为一种欲望相关物时所必然呈现的死亡恐惧,通过圣爱概念得到了解决,但阿伦特认为,使用和享受的区分再次让“邻人之爱”的概念陷入矛盾:“一个生活在绝对未来之期盼中,并且把世界及其上的一切当成使用物(包括他自己和邻人在内)的人,为何应当重视和建立这种在所有爱中都隐含的关系,并且明确地听从基督教命令:‘汝当爱邻如己’?”①Hannah Arendt,Love and Saint Augustine, p. 39;阿伦特:《爱与圣奥古斯丁》,第85 页。
在“爱作为回忆”的语境中,对幸福生活的寻求从“期待的未来”(anticipated future)转向“记忆的过去”(remembered past),这里,爱不是以“指向”(aiming at)未来的方式,而是以“回转”(referring back to)到过去的方式关涉对象:“奥古斯丁将唤回那些逃离我记忆之物的方式,等同于我认识的方式,以及我爱或渴求的方式。”②Ibid, p. 94.我们对所欲之善的看法,依据自身对幸福生活的知识,因而我们总是多少知道一点幸福生活,才会寻求和渴望它。对幸福生活可能存在的知识,是在先于一切经验的纯粹意识中被给定的,它保证了我们一旦在未来跟它相遇,就能认出它来。在自我从“消散”中聚拢,收敛心神的回想(recollection)中,过去被回忆带入当下,他也同自身的整个生存联合。记忆的性质超越当下经验返回过去,正如欲望的性质是超越当下和指向未来:“鉴于记忆提交的知识必定在每个特定过去之前先以存在,它实际上就指向一个超越的、超出尘世的过去,即人类存在本身的源头。”③Ibid, p. 48;同上书,第97 页。记忆的回返最终指向一个先于所有尘世经验可能性的过去,人们回转到他们的源头,即作为造物主的上帝。作为回忆的爱同样区分为“欲爱”和“圣爱”,“欲爱”返回到我们一出生就进入的、我们所属的世界中,把这个世界当成自己的源头,“反认他乡是故乡”,随从习惯(consuetudo)的力量而屈服于世界;“圣爱”返回到世界“之前”的亘古源头——它真正的“所来自”,认识到世界也是被造而有的。阿伦特认为在“爱作为回忆”的语境中,奥古斯丁最终超出了希腊式的存有概念,转向基督教的“造物主—受造物”的存有概 念。
四、“对世界的惧”和“爱世界”
阿伦特在1946 年的《什么是存在哲学》一文中批判了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1958 年的《人的境况》更以人们在世的“协同行动”(act in concert),来回应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孤独此在的本真决断。人们以往认为,阿伦特对海德格尔的批判主要是她在纳粹上台后积极介入政治的思想产物,但通过前面的分析就发现,其博士论文(1929 年)在主题和方法上已受到海德格尔的奥古斯丁讲题的影响,同时她已通过奥古斯丁开启了与海德格尔的批判对话,从强调人离开世界的“有死”转向人在世界中的“诞生”,从对这个世界的“惧”转向对这个世界的“爱”。
在这两部作品中,他们都把奥古斯丁寻求上帝的核心解释为对自我存在的寻求,并通过奥古斯丁论幸福生活的阐释,引向“诱惑”和“爱”的实际生活定向问题。海德格尔所谓的“诱惑”也是出于爱,出于欲求的爱。他说:“爱的倾向是对自身的关切。真正的amor sui是对自己的爱,正是这一点导向了诱惑,也因此产生了严重的愁烦(Molestia)。”①Martin Heidegger,Phänomenologie des religiösen Lebens,S. 294;海德格尔:《宗教生活现象学》,第350 页。海德格尔将沉迷于世界诱惑而消散自身、遗忘自身的“自爱”,解释为“对世界的畏惧”,并以奥古斯丁“奴性之畏”来阐释,真正的自爱或畏惧则是“圣洁之畏”。“第一种畏惧(奴性之畏)即‘对世界的畏惧’(出自周围世界和共同世界的畏惧),是攫住和压倒一个人的不安。相比之下,timor castus(圣洁之畏)是由真正的希望,由它自己所激发的信任所驱动的’自我畏惧’。”②Ibid., S. 297;同上书,第355 页。如邵铁峰分析指出的,奥古斯丁的“奴性之畏”对应着海德格尔作为“现身情态”(Befindlichkeit)的“焦虑”,此在消散于常人和共同世界的非本真存在方式,奥古斯丁的“圣洁之畏”对应着召唤此在回到最本己的存在方式的本源畏惧经验。③参见邵铁峰:《海德格尔论奥古斯丁的畏》,载《哲学与文化》第47 卷第9 期,第138 页。这里的“惧”和“爱”既是道德和心理上的情感,也是人经验世界的实际指引。不过在阿伦特那里,爱有着更积极的内涵,借助对爱作为记忆而非欲求的定义,她将真正的“自爱”定义为对“记忆之过去”的回返,并在论文最后找到了“邻人之爱”的真实基础——邻人是与我拥有共同命运和共享历史“事实”的共同体伙伴。阿伦特在英文修订版中还特地增补了一句对《存在与时间》的批评:“是记忆而非期待(例如,在海德格尔的进路中对死亡的期待)赋予人的存在以统一性和整体性。”④Hannah Arendt,Love and Saint Augustine,p. 56;阿伦特:《爱与圣奥古斯丁》,第108 页。
阿伦特晚年将其政治思想概括为“爱世界”(Amor mundi /love for the world),实际上,“爱世界”的表达最早出现在她的博士论文中。⑤Ibid.在那里,她指出奥古斯丁所用“世界”一词的双重含义:既指作为受造物的世界,也指居住在其中的爱世界者(die dilectores mundi)。对于奥古斯丁“世界”含义的同样说明也出现在海德格尔1929 年《论根据的本质》一文中。⑥“我们也用世界来称呼那些由于爱世界而居住在世界中的人”——参见海德格尔:《论根据的本质》,载《路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年版,第170 页。阿伦特在博士论文的注释中引用了此文,并指出了她与海德格尔在世界阐释上的共同点和分 歧:
在海德格尔对世界概念的历史概述中,奥古斯丁式的世界概念是被提及的其中之一。海德格尔也区分了奥古斯丁的mundus[世界]一词的两种含义:世界一方面是ens creatum[受造物] (对应我们这里的神圣作品,天和地),另一方面世界被设想为爱世界者。海德格尔只在后一种意义上阐释:“世界,因而意味着在整体中的存在,是作为决定性的如何,据此,人的生存关联到存在(ens),向存在行动。”他的解释因此仅限于把世界阐明为“本质上与世界的共在”,而他提到的另一个世界概念却仍未得到阐释,我们的阐释目标正是使这两方面得到理解。①Hannah Arendt,Love and Saint Augustine, p. 66, note 80;相同注释段落参见Hannah Arendt, Der Liebesbegriff bei Augustin, Berlin: Julius Springer Verlag, 1929, S. 42。
奥古斯丁批评那些“爱世界者”,即逗留、沉溺于世界之人,被世界的“习惯”牵引。对于海德格尔来说,世界是施加意义的“存在论构造”,也造成了“此在”与世界的共在,“沉沦”从生存论上规定着在世。但如同奥古斯丁贬低“俗世”一样,海德格尔也用“非本真存在”“闲言”“好奇”“两可”来标识这种“沉沦”、跌落于世的存在方式。阿伦特认为海德格尔“提到的另一个世界概念却仍未得到阐释”,即作为受造物的世界概念未得到阐释,暗示海德格尔受奥古斯丁影响而对世界采取了消极评价。借助“圣爱—贪爱”的框架,阿伦特实际上区分了两种对世界的爱,两种“爱世界者”:一种是沉溺于世界,被欲望和丧失的惧怕所支配的“爱世界者”,一种是响应上帝的创造之爱的“爱世界者”。“圣爱”在她后来的思想中转化为对持久共同的人造世界的照料维护,对人们之间“共同世界”的关爱。②参见王寅丽:《探索阿伦特“爱世界”的奥古斯丁起源》,载《道风:基督教文化评论》第52 期,2020 年,第63—83 页。
五、结语
奥古斯丁的“自我问题”开启了西方思想史上对自我存在的重要探索,海德格尔和阿伦特都将其在神学语境下展开的自我追问解读为对人与世界、与他人关系的“生存处境”现象学分析。对他们来说,奥古斯丁的存在主义神学和他继承下来的与新柏拉图主义的张力,以潜伏的形式体现了现代主体经验与传统形而上学的对抗。海德格尔对“诱惑”的现象学阐明强调欲望在自我真实生命经验中的地位,他对诱惑的存在论分析演变成了他在《存在与时间》中对“沉沦”概念的分析。阿伦特的“爱”则重视记忆带来的反思和自我构建,通过对奥古斯丁的爱的概念的批判阐释,她在博士论文中初步探讨了确立“邻人之爱”可能性的新原则,即以“记忆之过去”形成的共享命运和共同历史事实基础上的共同体伙伴关系。本文对海德格尔的奥古斯丁解读与阿伦特的博士论文的比较,既显示出他们思想共有的奥古斯丁式存在主义的背景,以及他们对奥古斯丁论题所作的世俗化转换,也显示出他们在“世界”概念上的进一步分歧。与海德格尔提出的“对世界的畏惧”不同,阿伦特在她的奥古斯丁论文中为 “爱世界”的思想作了准 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