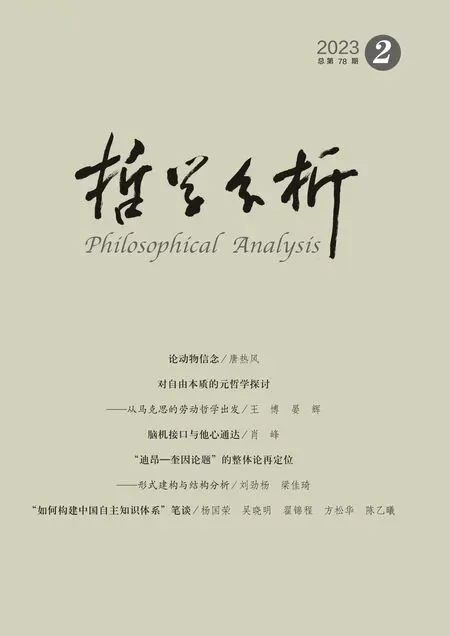认知与主宰:以庄子“真知之路”摹状“人类增强”的应然倾向
2023-10-03易显飞王克宁
易显飞 王克宁
“增强自身”是人类孜孜不倦地追求,纳米—生物—信息—认知协同组合形成的“NBIC 汇聚技术”,使人类增强自身的能力得到本质性提升,出现了所谓的新兴人类“增强技术”(Human Enhancement Technology 简称“HET”)。关于“人类增强”的理论纷争,主要聚焦其产生的一系列现实影响,无论是对增强持“激进主义”还是“保守主义”学派,本质上都希望人类在增强技术的使用之中得以保全与发展,其观点仅在对增强具体效用的态度上存在差异。人类增强固然存在产生负面效用的可能,相关的担忧也是人文反思的合理展开,但本质上是对人类增强可能产生效用后的反思担忧,并未关注人类增强在产生实际效用之前的“应然”倾向。不同于对增强后果的预测与反思,人类增强的应然倾向更加本质也更加抽象,高度的抽象意味着难以从具体现象、问题等角度把握人类增强,但并未阻断认识其应然倾向的可能。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资源中,常用“摹状”的方式,即通过对客体外围表象的描摹与解析把握高度抽象的客体本质,并将其本质复归现象,寻求其中共性的展现。如《庄子·养生主》中“庖丁解牛”一章,通过展现具体的“解牛”行为,摹状“技”之至,并细致描述庖丁解牛后的状态,摹状“道”之得,最终析出“道进乎技”这一技术哲学思想。人类增强作为人类向外拓展实践领域的产物,其根本倾向指向了人类在实践活动中的终极形态,面向外部实践的“极点”,最终必然指向内在的根本之知,可以从向内反思至极致的“真知之路”摹状人类增强的应然倾向。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下,“知”同时具备认知与主宰双重含义,“知”的上升过程便是由认知向主宰不断深化的过程,也是内在的“知”向外发挥效用的过程。在《应帝王》中,“知”的终极形态便表现出“胜物而不伤”的主宰性,但并非所有的“知”都能够合理地发挥正向的作用。在《庄子》中,“知”被划分为三个层次,即与个体自身存有直接相关的“可不可之知”,“此”自身之“此”而“彼”他者之“此”的“是非之知”,以及藏于自知根基处的“不知之知”,“真知之路”呈露出“非彼无我”中不与“此”相对的根源性的“彼”,确立了不断怀疑、不断深入探索根本真知的思考过程。①杨立华:《庄子哲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 年版,第305—307 页。探索“真知”的过程是由“认知”向“主宰”义上升的过程,其展开逻辑与人类增强追求人类终极形态的进路相近,向外实践的终极形态如果不能体认根本的“真知”便不足以作为增强的终点,以“真知之路”摹状人类增强的处境,不断探寻难以把握、无法言说的“不知之知”,将其与人类增强所暗含的、难以预知的终极形态结合起来,足以阐明人类增强的应然倾向。本文以《庄子》内七篇文本为主要依据,沿袭庄子“真知之路”的三个关键环节探索人类增强在人类实践活动中承担的职能与发挥的作用,回避人类增强在结果层面引发的诸多理论纷争,关注并解析人类增强根本的应然倾 向。
一、“可”与“不可”:人类增强的个体“齐同”困境
《齐物论》中庄子提出“可乎可,不可乎不可”的疑问,认为判断具体事物的标准本身并不具备普遍性的权威,但这种含糊的判断反而普遍存在于现实活动中,他在啮缺问于王倪一章中,以大量例证引出“孰知正处”“孰知正味”“孰知天下之正色”来回应“物无知”的问题,再次强调“可不可之知”存在的普遍性。“可”与“不可”的区分是将“是非之知”还原至最原初状态的表征,也是与万物生存发展直接关联的根本需求,其分别的依据在于个体在特定时间对特定事物作出的特定判断,因而不具普遍性的“可不可之知”是普遍存在的。因个体普遍性差异形成的“分别”对于现实生活而言并无过多影响,具体的差异往往会在具体实践活动中达到个体间的动态平衡,而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可不可之知”始终内含着将差异的实质普遍化并上升为“是非之知”的倾向。人类增强的理念同样接续了这种普遍化的趋势,但并未指向“是非之知”的纷争,而是希望在不损害个体多样性的基础上,以排除约束条件的方式展现出由个体强化向普遍增强的倾向,在增强的过程中实现个体的“齐同”,消解“可不可之知”赖以形成与发展的个体差异。对差异的“齐同”并不代表完全同质化,人类增强并不以消除差异为增强的终极目标,因此差异性与多样性仍然有所保留,但也导致人类增强齐同个体差异的过程中,始终受到多方面“可不可”的干预,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可不可之知”的存在,也无法抑制其上升为普遍性认知的倾向,形成了人类增强的个体齐同困 境。
首先,人类增强因个体间差异势能而发展,在增强的过程中又显露出消弭差异的可能,人类增强内在的“可不可之知”集中表现为普遍化倾向的盲目性。人类增强不能等同于消除个体间差异的手段,差异的存在本身仅在推动人类增强的发展与应用中发挥作用,并未成为人类增强作用的主要对象,即使将弥合差异的辅助性治疗手段与增强区分开,由治疗、修复跨越向增强时个体之间的差异性便被剔除人类增强的预期了,因此,人类增强与个体间差异的弥合之间并不具备直接的线性关系,不能以增强的结果来反思人类增强内在的“可不可之知”。虽然关于人类增强的设想中全方位能力增强的需求来源于个体能力上多元化的差异,而实际的增强进路没有也不可能完全覆盖所有的需求,其应用目标主要围绕人类共有的缺陷展开,至于部分人对弥补自身不足的期望则并不具备普遍性,前者是人类发展的整体需求,诸如寿命延长、不治之症的消除等,而后者便不可避免地陷入“可”与“不可”的纷争之中。人类增强希望打造统一的“超人”,使个体普遍地、公正地享受人类增强带来的积极效用,并以普遍的增强防范其自身的“风险”①陈迎年:《人类增强的界线及其可能》,载《探索与争鸣》2022 年第6 期。。然而即使回避了相关的伦理规制,统一的、普遍的增强也不可能完美迎合所有人的实践需求。在该意义上,人类增强预期打造的“超人”并不能完全满足人的需求,这侧面反映出人类增强具有将个体或部分人的需求上升为人类普遍需求的趋势,对于绝大多数在增强过程中不占主导地位的个体而言,增强最终便成为“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齐物论》)①方勇译注:《庄子》,北京:中华书局2015 年版,第26 页。本文所引《庄子》原文皆据此本,后文凡引《庄子》只标注所出篇章,不再作注。的默认存在了,个体差异并未得到齐同,只是通过统一的标准掩盖了差异的本质,将人类引向“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齐物论》)的状态。人类增强预设了人应然的、统一的终极形态,在实现终极形态的过程中逐渐与技术融合,但具体的技术手段是有限度的,即使人类增强不将消除差异作为终极目标,人为预设的增强目标也始终包含着人类对能力近乎无限的盲目期望,因而在人与技术之间始终存在“可”与“不可”的分别,连同人与人之间的“可不可”共同构成了人类增强在微观层面对差异的“齐同”所面临的人文困 境。
在个体层面,对差异任何程度的弥合或扩张都将引发剧烈变化。对人类增强而言,“齐同”只是增强的阶段性产物,人类增强的根本目标指向高于“可不可之知”所在的层面,因而增强并不关注差异,也不关注“齐同”标准的明确。人类增强因其根本目标源于人的主观预设而非现实层面高阶的同一,导致人类增强对具体的“可不可之知”总体上表现出回避的态度,无法以高阶的根源性统御低阶的、繁杂的认知,但对“可不可”问题的回避并未消除“可不可之知”对人类增强过多的顾虑与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人类增强发展的掣肘,使之不得不由对增强目标的追求转向对“可不可”问题的回应。“或于我为利,于彼为害;或于彼为是,则于我为非。”②郭象注,成玄英疏:《庄子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11 年版,第51 页。要回应“可不可”层面的全体需求是不可能的,《庄子》文本中以“可不可”一条来实现对常人“一可一不可”以及惠施“方可方不可”的超越。③冯春晖:《〈齐物论〉“啮缺问乎王倪”寓言发微》,载《东南学术》2021 年第2 期。人类增强对“可不可”问题的回应沿袭了工程主义技术哲学传统,将“可不可”的纷争视作现有技术手段的局限,但在悬置“可不可”问题的同时,人类增强反而借助“可不可之知”内在的普遍化倾向局部消解了“可”与“不可”之间较为平缓的矛盾,优先发展人类基本公认的需求来提高其在“可不可”问题中的权重,逐步引导人与技术间的“可不可”走向普遍的“可”,进而弱化人类增强语境下人与人之间“可不可”问题的重要性,以此稳固其预设的终极目标的现实基础,为人类增强的发展提供合理性前提,同时在没有以外力手段强行抑制“可不可之知”普遍化倾向的前提下消解了其可能产生的负面影 响。
其次,人类增强没有也无法完全消解个体的差异性,而个体的多样性需求与人类增强的“齐同”目标之间存在着外在的“可不可之知”,突出表现在增强层面的单调性。《德充符》中以惠子之口提出常人关于留存个体独特性与多样性的观点:“人而无情,何以谓之人?”庄子对此问题的回应从消除“可不可之知”的普遍化倾向出发,否定多样性的“情”,从“齐万物以为一”的理念引申出“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的观点。人类增强对差异的“齐同”单调地指向能力上高阶的统一,而人类增强同样追求“不以好恶内伤其身”,但其实现方式却并非齐同“可”与“不可”的模式,而是以外力排除精神层面上种种好恶带来的干扰,以此打造个体内心境界的平和,在这个过程中始终蕴含着将个体意识融入群体意识的普遍化倾向,而其最终的目标则落入“益生”的有为之境中。“不益生”不等同于对性命的损伤,而是描绘出“不以生为益”的自然境界,以“因循自然”的要求引导“以生为益”的人类增强,为人类增强展现个体复归生命本真、群体复归普遍幸福、万物复归和谐共生的价值取向。①赛子豪:《“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对人类增强技术的辩护、引导与约束》,载《自然辩证法研究》2021年第8 期。“以生为益”中仍然涵盖着大量的“可不可之知”,对人类增强发挥引导作用的只是其中较为统一的部分,这种程度的“共识”可以保证人类增强总体上有益于人的发展,但本质上并未改变人对实质性增强的根源性需求,至多将人类增强的指向由极致的盲目增强柔化为对美好现实生活的追求。而“因自然而不益生”消除了“生”对人类增强的限制,反而为人类增强的粗放发展与盲目作用提供了合理性基础,彻底消解了人类增强中人类的主体性因素,虽然在理论层面无法为人类增强提供价值引导与伦理规约,但“不益生”的理念实现了对人类增强及相关伦理反思中“益生”因素的解蔽,呈露出价值引导与伦理规约所难以触及的人类增强纯粹的、根本的倾向,同时显现出“齐同”因人类增强的单调性而陷入困境的本质:人类增强悬置了无法从根源上消除的“可不可之知”的问题,进而得出单调性增强或“齐同”的可行性,却忽视了“可”与“不可”的分别在现实发展方面对人类增强的影 响。
外在于人类增强的“可不可之知”并不足以从根源意义上否定人类增强,如果直接面向人类增强的手段与效用,回避其中服务于人类实践的人文关怀,可以发现“益生”对于人类增强而言不过是一种阶段性的人文限制,源于人类对非自然手段的恐惧,“益生”标准的提出至少可以确保人类增强在一定范围内有益于人,不伤害人。而以非“益生”的角度观之,可以更深刻地呈露人类增强的本质,也可以从根源角度发掘人类增强与外在的“可不可之知”之间的关系。人类增强推动人与技术的结合,本质上仍作为外在于人的手段或方式发挥作用,虽为“爱人”而生,却不赖“爱人”而存有,“利泽施乎万世,不为爱人”(《大宗师》)的境界并非一种需要以恐惧或审慎的态度应对的存在,对人类增强而言,无“爱人”之根本也就不存在“益生”的分别,其实际效用有益于人类便是“益生”,无益于“人类”、不“益生”也不会改变其人类增强的本质与应然倾向,故人类增强范畴之外的“可不可之知”并不会影响其根本,其回应也只是对特定问题的“特设性”回应。因此增强的“单调性”不会因为“可不可”的纷争而逆转,反而会在“可不可”的普遍化倾向中进一步深 化。
再次,人类增强“齐同”的动力源于“可不可之知”普遍化倾向,而通往“齐同”终极目标的路径本身存在着根源的“可不可之知”,具体表现为“齐同”模式的复杂性。人类增强通往“齐同”的路径可粗略地视为具体的技术手段,而一旦将技术手段细化到具体的增强过程便可以发现人类多样性的“可不可”间接导致了人类增强问题的复杂性,其中既包括普遍增强的应然性问题,又包含“齐同”的根源动力问题。对于普遍增强的可行性问题除个体好恶产生的纷争外,还存在个体生理基础上的差异,生理上的差异不仅干扰人类增强普遍性的发挥效用,也可能受人类增强的影响而陷入失调和失稳状态。①参见唐跃洺,王前:《从机体哲学视角看人类增强技术的社会风险》,载《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20 年第5 期。《大宗师》中女偊可以引导卜梁倚成为至德者,而受自身局限其仍停留在闻道者的境界,人类个体的差异除具体表现出来,可以观测的性状外,还存在众多难以认知与把握的差异,这就意味着人类要实现普遍的增强就不得不面对高度个性化的现实处境。对于“齐同”的根源动力问题,个体间的差异固然在“齐同”过程中发挥了主要的推动力量,但并不足以作为根源性的动力推动人类增强。人类追求增强的根本倾向不是人类由好恶产生的,而是人源自万物“无毁无成”的根源性动机,“杀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大宗师》),这种根源性动机虽然是人为赋予在增强之中的,但这种动机本身蕴含着漠视生命价值的因素,并引发诸多源于人文的思考,实际上人文反思也同样源于万物本根的根源性动机,人类增强的理念与人文反思本质上可以看作“同出而异名”的关系,故人文反思并不能在人类增强的根源处发挥引导作用,而是在人类增强的应用过程中发挥约束与拦截的作用。不同于增强的单调性,“齐同”的复杂性在人类增强的实践过程中产生了大量内生的干扰性因素,这便是人类增强在“可不可之知”层面困境的根源所在,其复杂性的表征也暴露出人类增强不得不面临的突出问题,即人类增强始终是技术手段发挥作用的过程,在该过程中增强对象的多样性以及个人、社会等层面的众多因素共同构成了人类增强根底的“可不可之 知”。
正是因为人类增强产生的改变是一个过程性变化,针对增强的人文反思与伦理规约才有用武之地,也是因为人类增强的过程性,才使得在“可不可”层面呈露其基础的应然倾向成为可能。“齐同”模式的复杂性暴露了人类增强高阶的同一理想与现实状况的多样性之间的矛盾,尽管多样的“可不可之知”使人类增强在具体层面难以“面面俱到”,但也意味着人类增强的本质倾向是高于个体或部分群体好恶的,对个体差异的消弭只是增强可能产生的影响之一,人类增强始终未将消解“可不可之知”作为增强的现实目的,这就意味着围绕个体或部分群体展开的伦理反思是不适用于人类增强的,同样,以源于社会生活的“善恶”伦理观念来审视人类增强,可以对人类增强可能产生的具体后果进行规约与疏导,但无法触及人类增强更深层次的内涵。人类面对人类增强“可不可”的忧虑本质上源于人类自身能力的不足,人类增强在“可不可”层面面临的“齐同”困境虽然可以在现实增强的过程中产生复杂多变的要求与影响,但并未动摇人类增强的本质倾向,即使是约束、限制了人类增强的发展与应用,也不会消除人类增强这种同出于人类生存根源性因素的根本欲求,人类增强的现实效用,超越了个体具体需求,以人类发展乃至更高阶需求为目标而发挥效用,不会因个体的“可不可”而改变。虽然人类增强并不关注具体的“可不可之知”,但通过“可不可”的分别可以打破人类增强的“外壳”,初步显露其高于个体价值判断的倾向,然而从“可不可之知”的视角解构人类增强的表象将人类增强本质的应然倾向推向了普遍意义的价值判断,因而需要沿袭“可不可之知”的上升路径,从“是非之知”的层面进一步探析人类增强的本 质。
二、“是”与“非”:人类增强的“彼此”对待局限
“是非之知”是“可不可之知”上升的必然结果,也是建立在普遍经验上的、总体性的价值判断。“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齐物论》)从直接成因看,“是非之知”是“随其成心而师之”的产物;从根本来源观之,“是非之知”则来源于“成心”对“彼”与“此”之间对主观分别。“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齐物论》),人的分别与成见使人陷入认知的迷途中,庄子认为关于事物好坏的理性判断会使人陷入主观的是非之争中,不利于对道的体认。①参见余开亮:《庄子、荀子“虚静”范畴比论》,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主客“彼此”对待是人类在实践过程中“是非之知”局限的前提,关于人类增强的理论论争也大多源于此。人类增强因人类“彼此”对待的存在而受到三个层面的局限:一是人类以自身为“此”,将出于自身而用于自身的增强手段视作异己的“彼”;二是将人与技术的融合视作不同于自身的“彼”,是人与人自身的“彼此”对待;向着更本原的层次去追溯可以发现,第三个层面的局限,或者说人类增强“彼此”对待局限的本质不是人对外物、对自身的对待,而是对自身存在基础的异化,是以“成心”对待根源性的、无对待的“彼”的结果。在“是非之知”的层面上,人类增强在其存在意义上的普遍化倾向已经得以实现,“彼此”分别产生的局限集中表现在人类增强的实践环节上,虽然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人类对“彼此”的分别,但从人类增强应对并逐步解构是非实局限的过程中,可以进一步实现对人类增强所追求的、超越对待的终极目标与应然倾向的摹 状。
首先,人类对增强的“是非”对待是“可不可之知”普遍化的必然结果,也是人类在增强的技术性手段下不自觉的状态,呈露出人类增强的本质倾向中暗含的异己因素。“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齐物论》)强调对对象是非利害判断的对待是人类“自取”所必需的前提条件,既表明了人类自身的发展必然取自对所依凭事物的对待,也表明这种对待并非纯粹相反的对立,并且在并行发展中对“分别”的凸显。因此,人类对待增强所产生的“是非之知”不仅关注人类增强具体效用对人的是非利害,还关注人与增强本质上的关联与区别。这种“对待”范式是人类长期实践过程中形成的,通过对彼此的分别形成“是非之知”,再凭借人在“是非之知”中主体性的彰显而证得人类在实践活动中“有真君存焉”的主宰性,是人类在未认识到更本质因素存在前对自身能动性的极致发展。但人类增强不能与以往的实践客体等同,现有的增强手段较以往的技术手段在广度与深度上均有加深,新兴的科技手段不再满足于对人类肢体的拓展,与人类身体及精神的高度融合导致人在适应增强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对增强的抵抗①参见葛玉海:《现代增强技术的身体抵抗问题及哲学反思——从机器到NBIC 会聚技术》,载《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22 年第4 期。。这种“对待”本质上来源于人类对未知或较低程度认知的增强手段的担忧,暴露出人类增强概念之中的确内含着异于人类自身的因素与倾向。其中人类因认知程度上的不足而产生的担忧较易解决,而人类增强中异己倾向的来源则需要进一步发掘。人类增强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在涉及社会生活之前所呈现出的异己倾向必然以其现实产生的社会效用作为判定标准,回归增强本身可以发现这种“倾向”的本质是人类自发地对增强的异化,人类对增强的“对待”根本上是人的有限能力与无限欲求之间的“对待”,明确人对增强“对待”的本质,重新审视人类增强的“是非之知”,便能在实现增强普遍性后重新呈露人类增强的应然倾向,即人类增强的“是”与“非”是人类对自身过度“自审”的结果,因而对其是非利害的判断始终是人类中心的,无法回避人类在否定、异化自身本质欲求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对待”的局 限。
人类增强在“可不可之知”层面所面临的困境至多对人类增强的发展进程产生一定的牵制与阻碍,而在“是非之知”层面对人类增强的局限则会切实地干扰人类增强的应用与发展方向,且“是非利害”的判断本质上仍然来源于人的主观感受,因而“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齐物论》)“是非之知”相较于“可不可之知”已具备相当的普遍性,但仍不可能形成确定的、统一的“知”,故人类增强无法简单地按照“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的模式发展与应用,甚至陷入“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的处境中。这些多样的“是非之知”作为与人类增强相关的种种伦理规约的来源,其价值体现在人类增强与人自身的交互中,其局限性则指向了人类增强中所蕴含的人自身的原始动机,反映出人类在增强欲求与现实需要之间的矛盾,其本质是人类增强欲求的强现实倾向与现实生活需求模糊复杂性之间的矛盾。因此人类增强在“是非之知”层面的局限本质上是人对自身的限制,对是非利害的判定结果虽然会影响人类增强的未来发展方向,但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人类增强的基础,而人类对自身的局限也不会仅止步于自身现实需求与思维上的矛盾,将人与增强之间“是非之知”的本质具象化,可以将人类增强盲目发展人类自身欲求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异己因素凸显出来,这就意味着在人类增强本质的应然倾向中的确存在源于人自身而超越人现有认知能力的因素存在,这种“未知因素”是人类在“彼此”对待中期望认知并主宰的根源性的因素,也是人类将增强视作“彼”所意指的“自取”目标,然而一旦这种“知”超出“对待”,便不为“是非之知”的判断方式所能确证,对人类增强的“对待”反而成为人类进一步探知人类增强应然倾向的限 制。
其次,未增强者对受增强者的对待是“是非之知”的主要表现,是人对自身无意识的分别,体现出人类增强在发挥具体效用的过程中所蕴含的异于人自身的因素。不同于对人类增强概念本身的对待,对受增强者的分别本质上是人对自身对待的增幅,且不同于“可不可之知”层面因个体需求差异产生的分别,在“是非之知”层面对人自身的对待是相较于个体需求更普遍的忧虑,也是人面对实际增强时对自身的限制。“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齐物论》)在“此”“彼”以及根源性的“彼”之间,无论是否感受到增强带来的益处,人对根源之“彼”的体认在自身认知能力局限的前提下被增强所带来的“小成”所遮蔽,这便是人对自身局限的本质,为消解“小成”对根源之知的遮蔽,直接面向的便是人类增强产生的实际效用,而其实际效用只有在作为客体的“人”身上才得以呈现,人又只能认识并掌握由“彼”投射到“此”之中的部分内涵,且在“此”中仍有对自身的“不知”,因而受增强者对于未增强者而言,是难以认知且具备更强能力的“彼”,故陷入“我与若与人俱不能相知”的处境之中。对于“俱不能相知”的处境,人类无意识地激化了“彼此”之间的分别,并“欲以明之彼”,但由于人在“是非之知”中认知“彼”的失能,最终反而“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坚白之昧终”(《齐物论》)。人自身因受增强而产生的对待是由于自身“知”的局限性而施加于自身的局限,难以以人自身能力的提高而打破。反观在此境遇之中的人类增强仍未因“是非之知”而动摇其根基,但在“对待”之中,人类增强始终扮演了推动“是非之争”发展的角色,即使增强对个体差异的“齐同”趋向完全意义上的同一仍然会催生并放大“是非利害”的分别。在人自身“彼此”对待的处境下,人类增强的概念并未被视作自然或偶然的对立面,而人因自然局限或自身偶然性产生的对自身的对待也无法依赖外在的技术手段克服①Yuk Hui,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in China: An Essay in Cosmotechnics,Falmouth: Urbanomic Media Ltd., 2016, p. 70.。因此要打破这种局限,既要进一步消解“是非之知”,摆脱对人类增强或人自身的单纯依赖,同时也需要关注人类增强在人对自身对待的过程中显露出实践层面异己因素的根 源。
人类增强作为人对自身“对待”的过程中起转换作用的中介,在改造人的过程中绝非中立性因素,而是扮演了助推人对自身“对待”的角色,人与人之间的对待因“可不可之知”的存在而存在,同时因人类增强的普遍化倾向上升到“是非之知”的层面,这种倾向是人类增强本质中蕴含的,但仅凭其中异己的因素并不足以形成人对自身的对待。对这种“对待”的形成进行溯源,只能停留在人类增强发挥具体效用的环节,即人类增强只有在作用于人类自身时才得以具备“对待”形成的前提,而人类增强在实际作用于人的过程中所受支配力量的来源则是这种“对待”的根源所在。“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道之所以亏,爱之所以成。”(《齐物论》)即使“是非之知”相较于“可不可之知”已具备普遍性,但仍然受到人自身的“爱”而呈现出相对性,也正是因为这种相对性使人类增强从外在于人的手段向“人—技”结合体转变的过程中成为异己的因素。人成为人类增强的实践客体,也就意味着人将自身视作自我主体的客体,进而在“彼此”对待的背景下试图重新认识并主宰人类增强与增强后的自身,而根源于人类在实践层面模糊形成的关于人类增强的终极追求是超出人类群体现有认知水平的,也不可能具备将这种片面认知转化为“主宰”的可能性。因此试图通过对待自身的方式来定夺人类增强实际效用的“是非”不仅不足以把握人类增强的根本所在,反而成为人类对自身的局限。虽然面向具体受增强者的对待因人类认知的有限性而成为无效对待,面对人类增强具体效用的“是非之知”也无法从具体现象层面来解决,需要求诸对人类增强应然倾向的呈露并进一步解构现象层面的“是非之知”,对人自身在“是非之知”层面的局限本身也是摹状人类增强应然倾向的必要环 节。
再次,对人类增强的“是非之知”进一步解构,可以追溯到人对根源之“彼”的对待,这既是人类增强无法消除的“是非”,也是人类增强必然存在的自我局限。庄子在《齐物论》尝试提出解决“是非”分别的可能方法,“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人类在最终的分别对待面前不得不面对“辩也者,有不见也”的“辩无胜”难题,因此“是非”的分别无法从根源上得以解决,只能转向对“是非之争”的消解。人类增强的直接效用指向人类能力的提升,但无论是实践能力的提升还是人类认知思维能力的提高均不会改变人类内源性的对外界一切事物的对待,人类生存在充满差别对待之物的世界中,始终无法逃脱差别与对待的处境。①张立文,高晓锋:《庄子道物关系的一种诠释进路——以“物物而不物于物”为例》,载《中州学刊》2021年第4 期。人类试图对世界本原问题的探索也并未超出“对待”的范畴,这种“对待”甚至会因能力的提升而进一步强化,作为人类展开认识活动的前提之一,区分“彼此”并形成“彼此”间的对待是必需的。人类增强在“是非”层面所受的局限因人自身的局限性而无可回避,但在解构人类增强的“是非”过程中也显露出人类增强自身的局限性。在实际产生效用之前,人类增强虽可被视作中立性的概念,但悬置对人类增强的价值判断不会改变其所受局限的本质,人类对增强的欲求来源于人类根源意义上存在的缺陷,只要将人类增强视作实践活动的客体,就意味着人类将自身外化为异己的因素,并将关涉人自身根源性不足与面向人类增强的双重对待之间的矛盾凸显出来,人类增强正是矛盾双方对立统一的现实表征。人类将自身根本上的缺陷外化为具体的手段来遮蔽对自身有限能力的忧虑,同时将因自身无法认知自我应然的最终状态而产生的忧虑也外化至人类增强的概念之中,因而导致通过外在技术手段的增强在其价值构成上与人对自身对待的负面情感高度关联。对于人类而言,人类增强同样具备着异化人的能力,并在与现实政治、科学等因素结合的过程中形成人与技术异己的关系。②陈迎年:《人类增强的界线及其可能》。而无论将人类增强置于何种现实处境下,人与增强相互异化及其本身内含的矛盾均使其无法脱离由主体对待产生的“是非”局 限。
但在“是非之知”的层面,人类增强仍然具备消解“是非之争”的倾向,这种异于其内部矛盾存在的根源性倾向也可以回溯到人类本身。人类增强无法消解自身的内部矛盾,同时承担了将人外化出的矛盾以极致的、具体的技术方案消解的职能,从而在“是非”的局限之中尝试实现人类对根源之“知”或终极形态的追求。正如《齐物论》中对人籁、地籁、天籁的描述中,充分呈现出人类对自然、完满存在的“天籁”的向往,而认知能力则局限在“地籁则众窍是已,人籁则比竹是已”层面。在“是非”的局限下,人类增强的本质究竟于人自身形成何种关系也受到人自身认知能力的限制与“是非之知”的主观影响。如果将人类增强视作人类创造过程产生的“比竹”,则人类增强与以往的技术手段别无二致,仅在具体的效用上存在量的差别,这种处理范式虽然悬置了人类增强的普遍性问题,但也弱化了人类增强在应用对象等层面与以往技术手段现实存在的差异。如果将人类增强视作人在实践活动中认识到的“众窍”,虽然承认了人类增强相较于人创造“比竹”的超越性,但人类对于外在于自身的“地籁”始终需要面对人自身认知能力的局限,因而距离人类增强或人自身完全意义上的认知并主宰万物而言还有相当的差距。至于“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的“天籁”在自然观上可以将其视作人类认知能力暂未触及的“自在自然”,体现出庄子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意识和人对精神自由的无限向往。①马治军:《中国古代生态理论资源的核心蕴含与后现代价值论析》,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3 期。而在认识论上,“天籁”则是超出人类现有具体之“知”的范畴,指向根本的“不知之知”。人类增强显然不是完全出自非人自然的自然存在,因而其根源性与人自身同出于更高阶的“不知之知”中,在“是非”层面具体的表现及其与人的关系无论是自在的、盲目的,还是自觉的,均无法超越“是非”的局限,且“是非”的分别无法凭借现有的手段消除,只能依赖对人类增强的进一步溯源在“是非”对待必然存在的前提下回避“是非之争”对人类增强与人自身产生的局 限。
三、“知”与“不知”:人类增强的本质处境约束
《庄子》中并未对“知”与“不知”进行区分对待,而是将“不知”视作“知”的一种状态,且将“不知之知”视作根本的、至德的“知”,但并没有为“不知之知”提供确切的描述,对于这种常人无法体认的根本之知的摹状是通过个别至德者在他人对话的故事中展开的,文本中涉及的至德者存在一个共同特点,即无法言说,在言说之外,通过闻道者与知道者对王骀、哀骀它等至德者的描述,尤其是对卜梁倚达到“见独”之境过程的展开,将“杀生者”与“生生者”的独体完整呈现出来,最终将掌握“不知之知”的至德者对“万化”的主宰作用具象化至现实生活中。②杨立华:《道体、性命、独体:当代中国思想展开中的相为与相与》,载《哲学动态》2020 年第12 期。至德者通过“用心若镜”的方式鼓动万物生息,以无法言说的“不知之知”构建主宰万物的体系,其可行性的前提在于:普通人与根本之知的关系并非体认的失能,而是对真知无法回溯的历史性遗忘。人类现实生活以及人文关怀面向的核心问题是人在自身命运中的处境,而人类增强则是人类试图改造自身处境的现实表现,意味着人类对增强的预期是人类对根本之知彻底遗忘之前主宰自身的尝试,因而人类增强的本质处境是人类遗忘根源性的“不知之知”的最终环节,试图沿袭遗忘的路径回溯“真知”,但这种回溯又受到人类自身的局限而难以实现。虽然无法实现对“不知之知”的回溯,但在回忆“不知之知”的过程中,人类增强的应然倾向也将被彻底呈露出来,并使摹状人类增强与“不知之知”的关系成为可 能。
首先,人类增强作为人类回溯真知的尝试,本身面临着在现实应用层面的种种问题,其约束的根源在于人类增强不可回避现实处境的“不得已”。人类增强自始至终是围绕人类具体实践活动展开的,脱离实践的增强是无效且不必需的,而人类增强中对天地万物的“主宰性”是超越实践活动的,但这种超越性又不得已被现实的实践活动所掣肘,回归被“主宰”的处境。庄子在《人间世》中以“颜回请行”“叶公子高将使于齐”“颜阖将傅卫灵公太子”三个例子表达出超脱人生境遇的人在人生历程中的“不得已”,无论主动还是被动,无论能否自我选择,均无法逃离现实处境的约束,从而引出“无用之用”的概念,以“无用之用”观照人类增强可以更具体地呈露出人类增强本质之中的“不得已”,凸显人类增强“有用”的约束与“无用”的解脱之间的矛盾。“不得已”除了人在世的无可奈何之外还蕴含着人之于世界、之于世间万物感应的不得已①陈徽:《庄子的“不得已”之说及其思想的入世性》,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3 期。。这种感应自然的“不得已”构成了人类增强应然倾向的第一个约束环节,承认人类增强与人自身的有限性可以弱化现实处境的约束,但这种方式不会改变“不得已”的本质,通过悬置“不得已”而获得的人类增强发展空间也是有限的,且这种“让步”回避了人类增强追求根本之知的原始动机,使增强成为完全外化于人、附属于人的技术需求,并永远局限在“是非之知”的应用层面。“且未乘万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人间世》),直面自身的“不得已”虽然无法消解现实层面的约束但可以使人类追求根本之知的倾向在增强过程中得以留存,人与技术的融合共生以及增强的现实效用在“不得已”中“养中”,这意味着人类增强应然倾向的转向,即从人类沿自然生成的路径回溯范式转向人类体认并尝试实现对自身的保全。从人类探索自在自然的角度看,人类增强并非纯粹依据人的生成路径回溯而发展的,其本质是人类主观能动性的现实表现;但从人类实践的根源性目的入手,这种对外界能动的实践本身便是对人生成路径的回溯,因而无法以“对待”之外的方式体认根源的“不知之 知”。
人类增强的现实面向既是实践过程中的“不得已”,也是其自身内存的根本性倾向,且在现实面向之外,人类增强还面对着其自身作为实践工具的“不得已”。对人类增强过程中人类主体性的担忧虽然较大程度上源于“人—技”融合造成的主体性模糊,但其实质在于人自身的主体性模糊后人类增强并不具备独立的主体性来补足并支撑人类实践活动对主体性的需求进而丧失对外物的“主宰”能力,人类增强在该处境下的“不得已”便是作为人类实践活动产物的被动性本质与“人—技”融合过程中的主动性需求之间的矛盾,这种“不得已”在人类增强的现实面向过程中影响并构建了其应然倾向,即人类增强涵盖人对根本之知探索欲的同时还必须存有人类自身的主体性并与之融合。从人自身的角度来看,为了维护自身“主宰”万物的合理性,将自身主体性外化至人类增强之中,从而使增强具备较强的实践性,但人类因此又恐惧增强之中人为赋予而又外在于自身的主体性。虽然无法影响人类增强的应用方向与实践过程中由人延伸出来的“主宰倾向”,更不会干扰到人类增强在技术意义上产生的实际效用,但底层逻辑上的约束导致向外探索的实践活动并不指向根本的“不知之知”,对人类增强“不得已”的分析仅能明晰人类增强的现实处境,并初步呈露出其应然倾向的根源所 在。
其次,人类增强的应然倾向中对“不知之知”的追求还受到“不知之知”不可言说的处境约束,集中表现在人与增强的交互过程中人类被迫对源于自身增强的“不知”。庄子将超越现实存在“不得已”的方法寄托于至德之人对现实生活中律令式的必然与不可控的偶然之间分歧的弥合,而至德者在该过程中既作为真理性生存的具体体现而存在,也作为“不言之教”对现实生活产生影响。①杨立华:《庄子哲学研究》,第179—180 页。人类增强能否对人类实践活动产生“不言之教”不能仅从其“不可言说”的处境展开,但人类增强的沉默与“不知之知”的不可言说产生的关联是超出人类增强在器质性上不具备言说能力的深层体现,即人类增强的沉默不仅因其作为外在于人的技术范畴而无法使用语言,或受自身技术“黑箱”的影响无法让使用者明晰增强的流程,还在于增强对人类自身产生的效用式反馈无法以被改造客体的形式存在并被主体认知,人类增强的效用与作为主体的人深度结合,导致了人类增强在效用反馈上彻底的不可言说。然而虽然庄子认为根本性的“不知之知”是不可言说的,但并不意味着沉默的人类增强以“不知之知”的形式存在并发挥效用,增强的本质仍然是不具备绝对普遍必然性的经验之知。“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大宗师》)在庄子看来,知“天人分界”便已经是经验之知的极致了,但仍然需要面对“庸讵知吾所谓天之非人乎?所谓人之非天乎?”的问题,无法触及根本的“不知之知”。在经验的深层次中存在着根本的不知,其现实表现就是对现实生活及其自然本质的敬畏与审慎,与人类增强所指向的对外物掌控式的“主宰”是相悖的,因此人类增强既不能作为根本之知而存在,也无法作为人类体认“不知之知”引导手段发挥作用,同时又因人类探求“不知之知”的指向而使人类增强作用于人并因此受到不可言说处境的约束。对于人类增强而言,这种约束不会改变其自身的应然倾向,但在人与增强交互的过程中,却切实地影响到人对增强的预期与实践反思,无法对增强效用进行量化评判就无法客观认知人类增强,也就无法在人类增强的前提下触及体认“不知之知”的可 能。
尽管人类增强在认知根本之知上的不足并不会对其现实效用产生直接影响,但意味着能力的极致提升与“至德之才”之间仍然存在着不可弥合的鸿沟。《大宗师》南伯子葵问乎女偊一章中对“圣人之才”与“圣人之道”作出分别,且将“圣人之才”视作成为至德者所必需的前提,“圣人之道”可学,而“圣人之才”却是可遇不可求的,庄子从“圣人之才”的特殊性推出人人成圣的不可能,而人类增强的现实效用恰好指向对“才”的塑造。以外在手段的增强来塑造普遍的“圣人之才”首先面对的就是增强过程的“黑箱”。不同于自身修行体系中“坐忘”“朝彻”等具体修行范式,人类增强的作用进程难以直观把握与描述,因而仅能从现象反馈中把握其走向的可能性。在《庄子》中有多处对至德者境界的表述,如《德充符》中王骀的“审乎无假而不与物迁,命物之化而守其宗”;哀骀它“未言而信,无功而亲,使人授己国,唯恐其不受也”;《大宗师》中卜梁倚“其为物无不将也,无不迎也,无不毁也,无不成也”。从对至德者的描述中可以发现人类增强的直接现实指向与至德之才的生成路径并不同一,这种分歧源自人类增强本身的应用逻辑,即使不以“全才而德不形”的要求来引导人类增强,能力的无限增强也不意味着人类向“不知之知”的靠近。而从人与自然弥合的角度看,增强也无法保证人的实践活动与万物自然的流转并行不悖,甚至会放大人与自在自然间的分歧。因此,由普通人通往至德者的进程中,人类增强追求根本之知的倾向受到自身约束而无法完全发挥,以至于人类增强在终极追求层面存在着不彻底性,故而,人类增强只能展开人类的能力层面上的提升,也就无从关注人生中最本质的需要与自身存在最高形态的追求,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现有的境 遇。
再次,人类增强自身蕴藏着引导无法言说的“不知之知”进入现实生活的应然倾向,但即使人类增强可以在实际应用中发挥积极效用,也终究无法企及根本意义上的真知。关于至德者对现实生活的复归在《应帝王》中有所提及,“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至人以自身不动鼓动天地万物的生机变化,于至德者而言便达到了万物齐同为一的境界,是“不知之知”的现实展开,但具体生活中的差异、是非对待没有也不可能被彻底消除,只能在至人的影响下实现对纷争的消解。在庄子“真知之路”中由终点向起点的复归是依赖至德者自身以“用心若镜”的形式照映现实产生影响的,而人类增强对至德之知的引导没有也无法依赖至德者的存在而延伸,在这个前提下,人类增强从未深入“知”的本质,仅停留在实践的表层。人类增强本身的实践倾向是对世间万物进行认知、改造并最终主宰万物,对于无法改变的事物则将其视作实践能力上的不足,并进一步依赖外在的技术手段增强自身,而“用心若镜”则是以极致的精神境界来反馈现实生活,尤其在面对人力无法改变的事物时,事情的纷扰与命运的流变均不会动摇至德者的主观精神境界,始终如镜一般澄明,呈现出“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状态。①孙明君:《庄子的全德境界》,载《中国哲学史》2021 年第6 期。对于个体而言,人类增强拒斥所谓不可改造的“命”,是对先定于自身的约束的解构,是人类主观能动性的积极发挥,但对于人类群体而言,得到增强的实践活动仍然面临着依赖自身主观能动性无法消解的“不得已”,是人类增强追求至德之知的极限,虽然最大程度地模拟了至德者的存在,但终究无法体认根本意义上的“不知”,也就无法等同于精神境界上的“至德”,导致了人类增强自身逻辑上的局限。虽然人类增强在具体效用上表现为对人类能力纵深的提高与多方面能力的综合,但增强的实质是人类自身实践展开范围的扩张,至于人类自身境界的提升则超出了人类增强在实现逻辑上所能达到的极限。人类增强打造的扩张式实践不同于“用心若镜”的反馈式实践,其差异约束了人类增强应然倾向的展开,实践能力在增强意义上的有限性与增强在实践领域内的无限扩张共同约束了人类自身的积极发 展。
增强后的人类必然要回归实践,故人类增强的实践倾向对于人的实践活动而言是正向的,但扩张性的实践无法抵达“以自身不动鼓动万物不息”的境界,反而因人类增强使实践过程中非人的客体,尤其是与人相近的生物体在能力上被动地削弱了,这种最终试图指向全知的“增强之知”是对“不知之知”的背离,使人与人、人与其他生物乃至整个自然界的差别具有了无限扩张的可能,并伴随产生一系列的“是非之知”与“可不可之知”。这是人类增强与人类认识世界的实践需求相结合的必然结果,于人类基本的实践活动而言并无负面影响,但通过实践成果遮蔽了人类增强最本质也最难以表现出来的根本需求,即人类对“不知之知”历史性遗忘的抗拒。《应帝王》最后一章中这样摹状这种历史性遗忘的过程:“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浑沌之死展现出人与根本之知在认知上的对立,倏、忽与浑沌的关系代表了人的原始形态与现实欲望之间的关系,人浑朴的自然本性在“七窍”产生的现实欲求面前堕入不可挽救之地,而“以为未始有物”的“浑沌”便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被遗忘①颜世安:《老庄对人自身问题的认识》,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8 年第2 期。。这种历史性的遗忘是单向的,不会因人类增强追求“不知之知”的倾向而得到回溯,也不会因对“不知之知”的最后回忆而有所留存。人类凭借增强扩展自身的实践范围,这种实践倾向本身就是对遗忘的延伸,而非回忆,是对“不知之知”的背离;因而可以说,人类增强在人类追求“不知之知”的过程中仅是一次回忆的尝试,“不知之知”并非蕴含在外在于人的自然中,而是由人自我对外物的不断“忘却”而回归的最原初的状态,无法由向外的实践探索实现;但增强自身能力,扩展实践探索范围及对身外万物的实践的主宰,或许可以为人类重新正视自身,回望“不知”的根源状态提供新契 机。
四、结语
人类增强在上述三个“知”的层面分别面临着不同的认知问题,这些问题的本质便是人类试图通过增强“主宰”万物的同时不被增强所主宰,形成了人与包含自身在内的万物的“对待”并产生一系列的纷争与欲求。而人类增强本身始终存在着消解纷争,引导人类“知”的不断深化的应然倾向,但受限于主体认知能力与人类增强的技术属性,对真知的回溯始终无法回归终极的“不知之知”。然而无论人类增强自身的应然倾向最终以何种方式呈现,这个过程本身便已经是人类对体认真知、实践地解决对自身根源本真之知的历史性遗忘的人文尝试,因而在警惕、审慎人类增强负面影响的同时,需要把握并接受人类增强的应然倾向,引导人类增强在人类探索真知的进程中发挥积极作 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