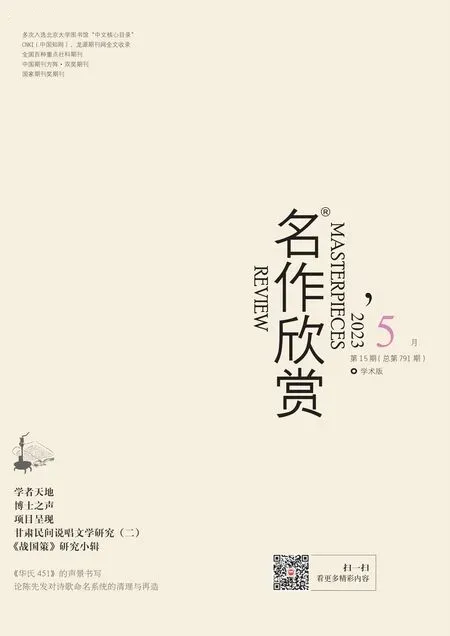《献给艾米莉的玫瑰》的哥特主义叙事艺术
2023-09-28王子君中国海洋大学山东青岛266100
⊙王子君[中国海洋大学,山东 青岛 266100]
《献给艾米莉的玫瑰》是美国现代作家威廉·福克纳的一部非常经典的哥特主义小说,而小说中哥特元素的成功运用离不开福克纳本人高超的叙事艺术。小说在线性的叙事顺序中打破了原来故事自然发生的顺序,以艾米莉的死亡为开头,而艾米莉的未婚夫霍默·巴伦被毒杀并藏尸的真相最后才得以揭露。小说采用了外聚焦的叙述视角,丝毫没有对主人公的心理描写,受述者只能不断地去猜谜。在猜谜的过程中,小说的恐怖与悬疑气氛得到了极大的烘托。通过对叙述时间和语式的特殊处理,福克纳使得哥特元素自然地融入这部小说中,形成了这部小说独特的艺术魅力。
一、叙述时间
(一)“时间倒错”下不断营造的神秘
“时间倒错”是由法国叙事学家热奈特提出的概念,热奈特认为叙述时间具有双重性,即文本时间和故事时间。其中,文本时间是指事件或时间段在叙述话语中的排列顺序,故事时间则是指事件或时间段在故事中的接续顺序。文本时间和故事时间完全重合的状态一般是不存在的,只有大体上的相符。叙述者在叙述中故意破坏原来的故事发生的顺序而造成的故事时间与文本时间之间各种不协调的形式,称之为“时间倒错”。
按照热奈特关于时间倒错的理论,这部小说的倒叙为外倒叙,小说中所有的倒叙部分都在第一叙事即艾米莉的葬礼的时间起点之前,倒叙中收税事件、臭味事件等所有事件的幅度都在第一叙事的幅度之外,不干扰第一叙事。但这部小说中的倒叙却占据了小说文本的主体部分,如热奈特所说的“与从中间开始的手法有关,旨在恢复叙述的全部前事,它一般构成了叙事的重要部分,有时甚至是主要部分”。
在《献给艾米莉的玫瑰》这部小说中,倒叙是构成叙事的重要部分,甚至可以说是小说叙事的灵魂。在小说中,臭味事件和艾米莉买毒药这两件事对于小说的情节发展十分重要,与霍默·巴伦被凶杀的真相密切相关,是霍默·巴伦被杀事件的两条故事线索。可是叙述者通过时间倒错的手法偏偏把两条故事线索在倒叙中进行提前叙述,分割开来叙述,故意阻断两条故事线索与霍默·巴伦失踪事件之间的联系,而霍默·巴伦失踪的事件在倒叙中却被滞后叙述了,只能让受述者在分裂开的故事线索和不确定的信息中去猜测霍默·巴伦失踪的真相,在不确定的信息和读者不断的猜测中,这部哥特小说中的神秘感和恐怖感便增加了。阿蒙德指出:“神秘”这个词自然而然地同哥特题材联系在一起。这部小说的神秘感与恐怖感被叙述者以独特的时间倒错的叙述方式进一步扩大和加强了。
如果按照故事时间的顺序来展开叙述,如事情自然发生的那样,先叙述艾米莉与霍默·巴伦的恋爱,接着叙述镇民干预艾米莉恋爱、艾米莉购买男性盥洗用具、买毒药,然后叙述霍默·巴伦失踪以及艾米莉房子的气味事件,故事的神秘感便会大大降低,受述者便可以很轻易地将买老鼠药事件和臭味事件与霍默·巴伦的失踪联系在一起,进而很快地推断出事情的真相。显而易见,小说的恐怖感和神秘感的营造离不开福克纳运用时间倒错的叙述艺术。
另外,小说以艾米莉的死亡开始,以倒叙的方式回顾艾米莉的父亲,并通过巧妙安排叙述的顺序最终揭示霍默·巴伦死亡的真相,在短短7000多字的小说中叙述了三个人的死亡,把哥特式小说的一大主题元素——死亡表现得淋漓尽致。
(二)省略与停顿的巧妙结合
在热奈特看来,叙事是有速度的,并由此提出了时距这一概念。叙事的时距将由以秒、分、时、日、月、年计量的故事时间和以行、页计量的文本长度之间的关系来确定,叙事可以没有时间倒错,但是叙事却不可能没有节奏效果,并且热奈特据此把叙述运动由快到慢分成了四个基本形式,即省略、概要、场景、停顿。结合这一理论来分析《献给艾米莉的玫瑰》,可以发现这一小说将省略和停顿这两种叙述时距的基本形式进行了巧妙的运用,从而给这部小说带来了惊人的阅读效果,并且突出了小说的哥特元素。
叙事是有节奏的,有节奏的叙事才能让故事更加详略得当,跌宕起伏。小说中的省略主要是暗含省略,体现在对父亲的死、艾米莉与霍默·巴伦的恋爱过程以及艾米莉最后一次与霍默·巴伦相见并毒杀他的几个重大事件的省略上。在热奈特关于省略的概念中,叙事时间=0,故事时间=n,此时,叙事时间无限小于故事时间。对于凶杀小说来说,最重要的情节是凶杀的具体过程,可是在《献给艾米莉的玫瑰》中,艾米莉毒杀霍默·巴伦的事件经过以及与凶杀情节密切相关的艾米莉与霍默·巴伦的恋爱过程却被叙事省略了,在叙事时间中不占据任何位置,故事最重要的部分被有意隐藏了。而关于凶杀真相的另外两条故事线索臭味事件和艾米莉买老鼠药的事件却在小说的前半部分被分开详细地叙述了。
故事线索被叙述者详细地叙述,但被叙述者有意以时间倒错的方式掩盖了它们与凶杀真相之间的联系,最重要的凶杀情节更被省略了,只能让受述者在小说的阅读过程中去猜测,直至最后才明白霍默·巴伦被杀害并藏尸的恐怖真相,进而小说的恐怖气氛达到了顶端。小说没有对凶杀情节的正面叙述,却在推理的过程中更令人毛骨悚然。
小说省略的叙述方式还有比较明显的另一处,即直接省略了父亲死亡的具体细节,只简单叙述了艾米莉在受到巨大打击后不愿面对现实的精神状态。对于艾米莉父亲的死亡这一事件,小说中直接进行了省略,转而去叙述艾米莉父亲死后镇上人们的心理和艾米莉父亲的葬礼。对于小说受述者来说,非主人公父亲的死亡可能并不重要,对于这一情节的省略情有可原,父亲的死给主人公艾米莉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才是更重要的,但是在小说中连艾米莉在受到父亲去世这样巨大的打击后不愿面对现实的精神状态的叙述,也只有简单的几句:“艾米莉小姐在家门口接待她们,衣着和平日一样,脸上没有一丝哀愁,她告诉她们,她的父亲并未死,一连三天她都是这样。”
从小说中我们得知,父亲是家族的掌权者,更是这一家族的支撑,父亲的死对于从小丧母的艾米莉意味着失去了人生唯一的依靠,这种依靠不仅是物质上的依赖,还是精神上的依赖。父亲在世时,将艾米莉与外界隔绝起来,将她封闭起来,按照贵族精神中淑女的标准来培养她,赶走一切追求她的男人,艾米莉的精神世界除了贵族淑女典范外,只剩下对父亲的依恋了。所以父亲去世的打击对于艾米莉来说一定是致命的,这种时刻应该是艾米莉感情激烈爆发的时刻,小说的叙述却将此刻艾米莉的感情省略了。同样被省略的凶杀事件里同样是艾米莉感情最为激烈和复杂的时刻,艾米莉与霍默·巴伦最后一次见面具体发生了什么,他们进行了怎么样的对话,艾米莉以怎么样的心情亲手毒死了自己的恋人,统统都被省略了。故事的叙述时间被大大加快了,在加快的叙述时间中,艾米莉的感情却被忽视了,叙述者和受述者无法得知她真正的心理世界,艾米莉被神秘化了。神秘未知的主人公在省略的叙述中又为这部小说增添了冷酷神秘的黑暗基调。
热奈特还提出了停顿的概念,在叙事的停顿中,叙事时间=n,故事时间=0,此时故事时间无限小于叙事时间,并且热奈特进一步指出了关于停顿的狭义定义,即停顿的使用一般留给情节停顿、故事中止、由叙述者承担的描写。在叙述者对一个事物进行客观的描写时,故事情节一般总体停顿下来,叙述速度大大减慢,停留在对客观事物的细致描绘中,而场景描写恰恰是哥特式小说的经典手法之一。
《献给艾米莉的玫瑰》便有着大段的对艾米莉住所的细致描绘:“他们被那个黑人老仆让进了一间阴暗的大厅,大厅里有座楼梯升入更浓重的暗影中。屋里发出灰尘和那种经年不用的房屋的气味——一种窒人的、潮湿的气味”,“在一栋尘埃遍地、鬼影憧憧的屋子里”,“她死在楼下一间屋子里,笨重的胡桃木床上还挂着床帷,她那长满铁灰头发的头枕着的枕头由于用了多年而又不见阳光,已经变黄发霉”,“一层薄薄的、气息辛辣的尘埃,像坟里的幕布,覆罩着这间陈设得又像新房的屋子各处”,等等。叙述者不遗余力地对艾米莉的住所进行了细致的描绘,生动地描绘出了这栋旧宅的破败阴森。生活在这栋像坟墓一样的住宅里的主人公同样在细节中透露着阴暗恐怖:“她看上去虚浮臃肿,活像在死水里浸久了的尸体,白生生的。她的一双眼睛深藏在脸上肥厚的皱褶里,就像嵌在一团发面里的小煤炭。”这段细致的描述将艾米莉浑身散发着死亡气息的形象表现了出来,她的肤色如同肿胀发白的死尸,她的眼睛像煤球一样呆滞而无神,夸张而生动地刻画出了一个长期与世隔绝的如同行尸走肉般的恐怖形象。在停顿中,虽然故事时间大大减速了,但是阴暗恐怖的气氛并没有随之减少,反而在细节的描绘中更加浓厚了。“描写的重点在于细节,细节作用在于诱发受述者的想象,而想象的空间是无穷的,随着想象,恐怖感也被无限扩张了。”
可以说小说将时距范畴中的省略和停顿巧妙地结合了起来,使得一个再平常不过的凶杀故事变得跌宕起伏起来。省略的凶杀情节在细节描绘的停顿中留给了人们无穷的想象空间,在无穷的想象中恐怖与悬疑的哥特元素也被无限放大了。
二、外聚焦语式下的悬疑与隔膜
(一)悬疑与“我们”信息的缺失和虚假
热拉尔·热奈特在1969年的《辞格Ⅱ》一书中首次提到“叙述聚焦”这一概念,并在1972年出版的《辞格Ⅲ》一书中详细阐述了这一理论。聚焦是热奈特所提出的语式范畴里的概念,热奈特将叙述聚焦分为零聚焦、内聚焦和外聚焦三种类型。零聚焦也被称为“全知视角”,即叙述者>人物,文本中的叙述者所知道的比小说中的任何人物都多,在这种叙述方式下,叙述者的视角是不被限制的。但是叙述者的无所不能很难让受述者再有二度创作和想象的空间,叙述的真实性更容易遭到质疑。正如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存在上帝一样,现实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事无巨细地知道所有的信息。在内聚焦中,叙述者=人物(叙述者是作品中的一个人物),其叙述视角是从文本内的某个人物出发,也就是说用作品中一个人物的眼睛去看。受述者所能了解的也只能局限于该人物的所知所想,无疑内聚焦下的人物所提供的信息具有很大的片面性,但同时也为受述者提供了更多思考的空间。
外聚焦与零聚焦相比则刚好相反,为叙述者<人物,叙述者从外部观察所发生的一切,作品中的主人公就在我们眼前活动,被我们观察,但我们永远无法知道主人公的思想感情,叙述者提供给我们的信息十分有限,其所叙述的内容极具客观性,信息有限导致小说所散发的无知感容易营造一种悬疑的氛围,出现“因存在一个谜而饶有趣味”的情况。《献给艾米莉的玫瑰》主要采取的便是这种聚焦方式。
在热奈特看来,聚焦的本质是限制,在《献给艾米莉的玫瑰》这篇文章中,叙述者是由故事中的人物——镇上的居民“我们”所承担的,“我们”在叙述艾米莉以及其他小说中的人物时,仿佛只是一个旁观者。虽然“我们”与艾米莉生活在同一个时空中、居住在同一个城市里,“我们”了解艾米莉整个家族的来龙去脉,“我们”更是在不停地窥视、监督着艾米莉的一举一动,但是“我们”的所感所知却被紧紧地限制在小镇居民外部纯客观的观察视角中,“我们”无法得知艾米莉的心理状态,只能限于故事的时空中去感知,去猜测关于艾米莉的一切事情,“我们”的叙述缺失了太多的重要信息。“我们”的叙述中提供了“四个小镇居民在艾米莉的地窖口洒下白石灰以后,臭味便消失了”的详细信息,却缺失了更为重要的信息,即“引起臭味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我们”得知霍默·巴伦失踪,却无法看到他被谋杀。
总之,这部小说能够轻易编造悬念,并把悬念设置到小说结尾,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采用了“我们”这个外聚焦叙述模式,避免了零聚焦语式下对小说神秘感和悬念的破坏。“我们”是城镇上很普通的居民,是所有事件的“非参与者”和“旁观者”,没有上帝视角,所以无法讲清楚所有事情的来龙去脉以及猜想与实情有出入都是情有可原的,所以叙述中造成信息缺失和假象也是合情合理的。叙述者的有限视角使作者得以成功地设置悬念,将与艾米莉相关的信息和事件进行灵活加工,最后布成了一个悬念林立的疑阵,并成功在情节展开中加入了许多不确定的因素,设置了悬念,营造了悬疑的氛围。
(二)“我们”与艾米莉之间的隔膜
在外聚焦语式的叙述下,“我们”从外部观察着艾米莉,“我们”也只能从外部观察着艾米莉。因为全镇没有任何居民可以随意进入她的住宅,没有任何人可以随意与她交流,她更不会主动和“我们”交流,“我们”与艾米莉有着身份和精神上的巨大鸿沟,所以“我们”只能去猜测她,观察她,而无法理解她。“只知艾米莉的活动,从不知艾米莉的心理”的叙述,实际上反映的是“我们”与艾米莉之间无法穿透的隔膜,我们无法理解艾米莉在贵族道德与解放自己之间的挣扎,以及反抗失败后走向扭曲的过程。
艾米莉从小就被父亲封闭隔绝在了古老遥远的南方意识形态世界里,按照贵族道德中的淑女规范来约束自己。当父亲离她而去时,艾米莉被独自抛弃在凄凉的现实中。此时她眷恋着过去,却也意识到了自己所受的贵族精神的毒害,她想要在现实世界中生存,她勇敢地与霍默·巴伦恋爱,在星期日下午与恋人坐马车兜风,可是“我们”对此的反应却是认为她有失身份,不停地说“可怜的艾米莉”,却不理解此时艾米莉对传统贵族道德的反抗,不理解她此时追求自由和解放的快乐。当艾米莉因为父亲将求婚者不断拒之门外而在三十岁依然孑然一身时,“我们”不但不能体会到艾米莉深受南方清教传统和淑女规范毒害的命运悲剧,还认为终于出了一口气:“高高在上”的艾米莉也会面对找不到配偶的烦恼。甚至当艾米莉死后,在她的葬礼上,在她与命运抗争失败后,“我们”依然没有理解她,男人们把她当成一座倒塌的纪念碑来眷恋,却不知正是这座看似光荣却沉重无比的纪念碑压死了她。连同时代一样遭受过清教思想毒害的女人们,也只有可怜的好奇心,好奇一直封闭在自己的世界里的艾米莉是什么样子。城镇里没有一个人思考过艾米莉的一生和她的悲剧。
在外聚焦下的“我们”是那个时空南方的所有普通民众,“我们”有着时代的局限性,正如那个时代对艾米莉的态度,面对滚滚而来的工业时代,艾米莉不知所措。迎面而来的是霍默·巴伦代表的强大而无情的工业力量,当艾米莉试图打破束缚,勇敢去追求自由和爱情,去拥抱时代时,同时代落后的封建力量却依然禁锢着她,“我们”从远处冷眼观察着她,站在“我们”自己的立场上去随意评价她。新旧力量的不可调和下,她的反抗只能以失败告终,连带着她的爱情。最终随着她的葬礼,她和她的爱情、她的时代彻底走向了毁灭。
三、结语
福克纳高超的叙事艺术塑造了这部经典的哥特小说,而这部小说之所以经典,更是因为做到了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加入哥特元素不是福克纳写作的目的,福克纳更不会单纯地用感官的刺激来取悦读者。在这部短篇小说中,无论是独特的时间叙述,还是外聚焦的叙述语式,都是福克纳为了唤醒美国南方的沉睡心灵的大声疾呼。正如奥康纳所说的:“对于那些听觉不灵的人,你得大声叫喊;而对于那些快失明者,你只能把图画得大大的。”只有借助哥特元素和独特的叙事艺术才能产生冲击心灵的力量,才能让美国南方的人们认识到罪恶和危险,看到历史前进的不可阻挡和传统南方文化中的糟粕和精华,不沉迷留恋过去,不盲目接受未来。不管人类世界如何改变,人的猎奇心理是亘古不变的,创新的叙述技巧和哥特元素满足了人的心理需求,从而更容易刺激人的心灵,但一部文学作品如果只流于酷炫式的展示叙事技巧,营造恐怖氛围,那便丧失了文学价值,无法成为经典。只有与直击人心的主题和对时代的思考相结合,才能将叙述技巧和哥特元素发挥更大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