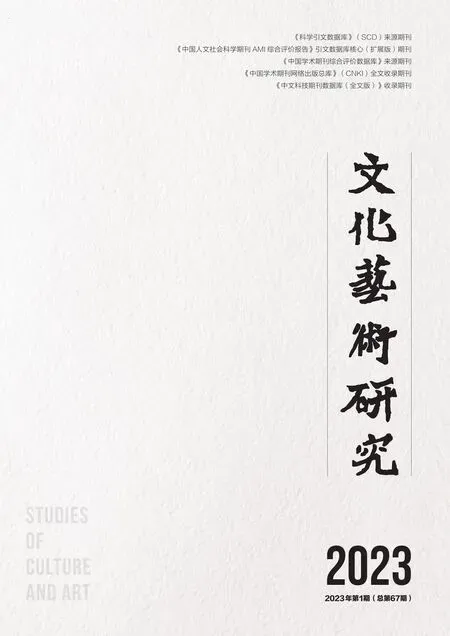交融互渗与共生发展:大运河流域文化景观特征及其实践路径*
2023-09-21毛巧晖
毛巧晖
(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面对全球化及其对地方性知识、区域文化共同体的冲击,沟通南北、贯通不同地域和民族文化的京杭大运河引起了广泛关注。流域视角下的运河研究超越了村落、行政区划、族群或民族的边界,所凸显的不再是地域、民族特性,而是不同文明、文化的交融和交流。虽然当下京杭大运河大部分河段已经失去实用功能,但自其修筑以来所形成的文化意义与价值随着历史不断发展。在京杭大运河流经的北京、河北、河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等省份,这一文化意义上的“流域”通道依然留存于各区域文化之中,也持续影响着区域内的民众生活;当然它不再是“显性”存在,更多的是“隐性”呈现。大运河文化的研究,须立足于流域,对运河沿岸不同地域、族群文化的差异与互动的复杂性进行整体关照。本文以文化景观为视点,在总结运河流域文化景观类型的基础上,阐述与分析景观如何通过视觉、听觉、触觉等,表达运河在流动与交融中所形成的共享的文化意识与文化认同机制及其当下价值。
一、创造性转化与消耗性转化:大运河流域的文化景观
“文化景观是由文化因素与自然景观共同作用的结果。文化是动因,自然区域是媒介,文化景观则是结果。”[1]1文化景观引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之后①1992 年12 月,在美国圣菲召开的第16 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文化景观(cultural landscape)被正式写入《实施〈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Operational Guidelin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成为世界遗产中的一个新类别。,人们对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中的人地关系有了新的认知。2014 年,大运河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运河流域“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景观中有形和无形文化价值的存在”[1]2日益引起各领域学者的关注和重视。研究者关注大运河在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后,文化景观内涵与外延所衍生的变化,同时在景观概念的象征价值中融入了人造景观的概念。
从文字记载到图绘记录,再到照片、纪录片等影像档案及博物馆、广场、公园等文化空间,除了有形遗产之外,节日、仪典、民俗、传说、信仰、歌谣、曲艺等非物质文化部分经由不断“物化”,大多通过景观得以“在场”或呈现。在大运河流域文化遗产②关于文化景观与文化遗产的概念,有论者提出文化景观比文化遗产广泛得多,文化景观一词包含着人类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多种表现形式。世界遗产文化景观被归入文化遗产之列的操作方式,相较于人们对人地关系理解上的前进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停滞或倒退。参见邓可、宋峰:《文化景观引发的世界遗产分类问题》,《中国园林》2018 年第5 期。本文的相关讨论亦立足于此。的保护中,景观更是进一步发展与丰富,但并非同质化存在,在实现“创造性转化”的同时,也有“消耗性转化”,因此在景观保护及其建构中就表现出对文化遗产本身意义的“超越”“守恒”“消减”。基于此,运河流域的文化景观大致可分为三类。
第一,由实用性向功能性转变的文化景观。“实在性是一切可供主体从感觉上感知到的事物的本质属性和物质基础,它是事物成为客体、独立于主体而存在的前提。”③参见路璐:《大运河文化遗产与民族国家记忆建构》,《浙江学刊》2021 年第5 期。笔者认为使用“实用性”一词更易理解,也与全文表达更为一致。如河道、湖泊、驳岸等运河河道景观遗存、码头聚落等商业景观,古村落、古建筑群等建筑景观,等等。它们的“实用性”寄寓在其物质性印记之中,同时又超越了其自身意义,物与人、物与空间、物与材料之间的复杂关系构成了运河流域文化景观的丰富意蕴。如杭州富义仓作为大运河流域保存较完整的古代城市公共仓储建筑群,初建时中心位置为仓储式厂房80 间,可储存稻谷4 万—5 万石,还有砻场、碓房、司事者居室等。运粮舟停靠处筑有一亭,以供搬运者休息。现存三排仓储式长房、门廊、偏厢,仓库遗址及河埠,其基本格局尚存。[2]杭州富义仓见证了历史上米市、仓储码头装卸业等经济业态曾经的发展、繁荣,如今已然成为文化、创意与旅游的复合体——“富义仓创意园”。
第二,集功能性与象征性为一体的文化景观。此类景观多与民众生活实践息息相关,并在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化交流、交融与共生中成为维系“流域”文化认同的一种方式。[3]如集中展现运河工程建设与漕运管理技术的水闸建设,元至元三十年(1293)秋开凿成功的通惠河河道上,自上游至河口依次设有广源、西城(会川)、朝宗、海子(澄清)、文明、魏村(惠和)、籍东(庆丰)、郊亭(平津)、杨尹(溥济)、通州(通流)与河门(广利)等24 座水闸。[4]水闸不仅解决了运河流域城镇用水、农业灌溉和漕运问题,对周边城市的供水格局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坐落于北京市朝阳区通惠河北岸的明清时期的漕运闸坝遗迹“庆丰闸遗址”,初名“籍东”,后易名“庆丰”,俗称“二闸”,始建于元代,因漕运而建,亦因漕运而兴。[5]清代运河漕运衰落之后,庆丰闸一带碧波荡漾,桃柳映岸,景色清雅秀丽,成为都城居民的消闲胜地。这一历史文化传统在当下的城市建设中得以留存,如2009 年“庆丰公园”建设落成,它作为“通惠河滨水文化景观带”的一部分,内部设有京畿秦淮、大通帆涌、惠水春意、文槐忆故、新城绮望、庆丰古闸、叠水花溪、银枫幽谷游览地。此外,北运河通州段的甘棠闸至杨洼闸也将打造“绿道花谷”“延芳画廊”两大景区,不仅要建设集防洪、水质净化、生态景观功能为一体的湿地公园,还要带动周边发展,形成自然涵养的天然景观带。[6]
第三类是叠加实用性、功能性及象征性三重意蕴的文化景观。包括民俗信仰、仪式、节庆活动等民俗景观,记录河务、漕运、水利等资料的文献景观,漆器制作、花丝镶嵌、建筑营造等手工技艺景观,浦江剪纸、杨柳青年画、通州杨氏风筝、柳琴戏、茂腔等涉及民间音乐、民间舞蹈、传统戏曲、民间美术、曲艺、杂技等的艺术景观。
此外,运河流域还有复合型文化景观,如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曹雪芹墓石、曹家当铺、曹家坟等真实地理景观以及萧太后河一带建造的曹雪芹塑像、归梦亭、红学文化绿色走廊等空间景观;作为感知地方与空间的关键路径的声音景观①“声音景观”(soundscape)这一理论是由加拿大作曲家及生态学家穆雷·谢弗(R. Murray Schafer)于20 世纪60 年代末70 年代初在声音生态学(acoustic ecologe)的范畴下提出的,这个观念可以帮助我们用来定义和理解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的一切声音的综合。,也是运河流域文化景观研究中重要但却容易被忽视的一类。丰富驳杂的文化景观,是运河流域不同区域、族群文化互动交融的结果,我们对其分析亦应着眼于此,关注运河流域文化景观的整体性,同时也注重文化景观间的交融共生。
二、交融互渗:大运河流域文化景观的基本特征
大运河作为漕运命脉满足了南北之间的政治联结与经济畅通,同时也带动了运河流域不同区域、族群间的文化交流。随运河裹挟而来的曾经流行于中亚的火神俗信、南方的妈祖文化、北方的河神祭祀及河道、湖泊、驳岸等河道景观,样态丰富、内容驳杂,但彼此之间并非孤立存在。它们之间可以说是“兼和相济”“互补共生”,在“存有交互性”(mutuality of being)②参见纳日碧力戈和凯沙尔·夏木西发表于《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4 期的《试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交互性》一文中的表述。这一术语来源于萨林斯对亲属关系的描述。中融合为一个整体。这也如前文所言,对于这些分属不同区域的文化景观,我们不能局限于传统的区域或族群研究,而要从“流域”对其进行整体分析。“存有交互性”来源于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对亲属关系的阐述,他认为亲属成员结成了“存有的内在互渗” (participate intrinsically in each other's existence)的关系[7],“一个群体的成员通过这些要素和活动,互相关联,交融一体”[8]。笔者借用“存有交互性”这一话语,旨在阐述运河流域文化景观交融互渗的特性。
运河流域共享着以“运河”为中心的“历史文本、文学文本、数据文本和艺术文本”[9],在对“文学文本”的挖掘中,《红楼梦》因其充盈着真实生活感受与艺术构思的运河叙事,点缀于运河沿线,建构起纵贯南京、镇江、苏州、扬州、北京等地的景观空间。如各地兴建的大观园、“红楼梦”主题景观、“曹雪芹纪念馆”、“曹雪芹文化园”及在喜马拉雅、蜻蜓FM、哔哩哔哩③一个搭载弹幕系统的视频播放网站,主打UGC(user-generated content)的视频生产分享模式。等视频音频网站上线的各类“红楼梦”有声景观,形成了独特的红学文化聚落和“一脉同气”的流变格局。
运河流域的“红楼梦”文化景观呈现出一种“结构性的相似”,如上海、北京、河北正定等地所修建的“大观园”多依照《红楼梦》对大观园内部景观的描写,其各处景观以园内馆舍命名,且按照地方气候种植水杉、紫柏、紫藤、檀竹、斑竹等植物。以河北正定荣国府为例,它很好地诠释了书中所说的“金门玉户神仙府,桂殿兰宫妃子家”,是一座具有明清风格的仿古建筑群。整个府邸分为中、东、西三路,各路均为五进四合院:中路为贾政公务院,采用了宫廷式彩绘,东西两路为内宅院,采用了明快的苏式彩绘,室内落地花罩典雅气派,再现了“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的富丽。河北正定荣国府这类的复合型景观并不鲜见,它们“分形同气”,描绘了曹氏家族的生活轨迹及运河流域的真实生活图景。以张家湾博物馆①以保护、研究、传播和展示人类及环境发展见证的博物馆,其运作中也在有意或无意地受到文化景观理念的影响,不管是博物馆的社会文化性还是博物馆诉诸视觉性,都决定了博物馆作为文化景观存在及呈现的可能性及合理性。参见田军:《博物馆:文化与景观属性兼在的文化景观》,《中国博物馆》2016 年第3 期。为例,馆内除了播放冯其庸讲述张家湾发现“曹雪芹墓石”及红学的视频,展柜中还陈列了曹家当铺遗址、古籍、奏折等历史资料,大量展板呈现了“曹家井”“三家坟”等传说,并设计了“红楼情牵张家湾”“曹雪芹如是说”“红楼画境”等主题景观。仅北京一地,就存在一条连缀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与大运河文化带的“红学文化区”,以“蒜市口十七间半”曹雪芹故居纪念馆为中心,将黄叶村曹雪芹纪念馆、张家湾曹雪芹墓石、曹家当铺、曹家坟及萧太后河畔的曹雪芹塑像、张家湾公园内“曹石印记”、通州文旅胜地“运河文化广场”的“曹雪芹像”等串联起来,加之西城的大观园、恭王府景区,清晰地勾勒出运河流域的红学文化的发展脉络。而南京乌龙潭公园的红楼梦景区、江宁织造博物馆、苏州织造署旧址②今苏州市第十中学西南部。、辽阳曹雪芹纪念馆及唐山曹雪芹文化园等文化景观,虽然在外在形态、展陈形式、景观类型等方面略有差异,但在文化本质、价值内涵、文化功能等方面却有着内在的暗合。此类文化景观正是以水脉贯通文脉,在运河流域流播与衍生,它们有着不同地域的文化特质,同时又共享着“运河”的共性。
运河流域漕运的兴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带动了文化的兴盛,依赖于运河便捷的交通和大量人口的流动,逐渐滋生出具有“集体同一性”③“集体同一性不仅指涉事件与事件连缀而成的历史,也指涉诸多事件所经历的时间……”参见刘龙心:《知识生产与传播:近代中国史学的转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 年版,第5 页。的信仰意识,同时也逐渐建构出具有地域特征的文化景观。以敕建于元泰定三年(1325)的天津天后宫④笔者在天津三岔河口调研时遇到一位张姓老人,他已经年逾八十,1976 年迁居至此。在交谈中,老人提到最早的大直沽天妃宫建于元代延祐年间,“当时的娘娘是从福州和莆田那边传过来的”。此资料源自2019 年5 月31 日笔者在天津三岔河口的调研记录。为例,其修建年代早于天津设卫筑城时间⑤明永乐二年(1404)正式建卫。,民间亦有“先有天后宫,后有天津卫”的俗语。天津(旧称“直沽”)作为连通海运和河运的关键,在漕运中不得不随时面临着“风涛不测,粮船漂溺者,无岁无之”的处境,“间亦有船坏而弃其米者,后乃责偿于运官;人船俱溺者始免”。[10]这些船工与商人只能求助于海神,逐渐形成了“不拜神仙不上船”的习俗,加之元代漕运所用舟师水手多来自闽浙一带,世代信仰海神妈祖,由此,妈祖信仰便随着海运船只来到了天津地区,并得以不断发展。天津的信仰景观是伴随海运而来的闽浙海神妈祖崇拜与碧霞元君信仰体系相交融的结果;可以说,海神崇拜与北方山神信仰交融涵化,迭代生成了天后宫中“山海互融”的民间信仰景观。
如描绘清末天津民众纪念妈祖诞辰的《行会图》⑥该作品为纸本,设色,现存89 幅,每幅纵63 厘米,横 113—115 厘米。除年久底纸变黄发旧及少部分画面残损外,保存基本完好。全图所绘参加行会的各种组会共117 个,所绘人物4350 多个,民间歌舞、杂技节目近70 个,涉及乐器20 多种。参见参考文献[11]。第八十六图中绘有一驾华辇及四驾宝辇,华辇驾乘为妈祖娘娘,四驾宝辇上依次是送子娘娘、子孙娘娘、斑疹娘娘、眼光娘娘,且送子娘娘前为“慈悲相”,后为“愤怒相”,意在“恫吓天后宫里那些不愿到人间投胎的小孩”。[11]再如天津天后宫西配殿的“王三奶奶”。“王三奶奶”⑦相传王三奶奶是香河县庞各庄人,自幼学会了跳神、顶仙,在她八十五岁去妙峰山参拜时去世,之后附体巫婆谈及她本为东岳大帝的第七个女儿,从此王三奶奶在妙峰山碧霞元君殿和天津天后宫受到供奉,其职能也由治病逐渐发展为生育、婚姻等。参见李世瑜口述、李厚聪记录:《天后宫里要不要王三奶奶?》,《2006 中华妈祖文化学术论坛论文集》,内部资料,2006 年,第153 页。的崇拜范围大致为京津一带及沿途各县,其与天后宫中的天后、关帝、财神、观音、西海龙王共享世人香火供养。这种“山海互融”的民间信仰景观连缀着运河流域民众共有、共享的精神家园,海洋文化与山地文化融合与互动下形成的民间信仰与习俗,通过“庙祭”“春秋谕祭”“庙会”及民众日常的民俗活动,以祭祀、花会传统和歌舞为载体,在重塑人们对天津天后宫这一独特文化景观的理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纽带。
此外,运河流域文化景观的“交互性”也体现在文化景观与民众日常生活的交融互塑。如在中国首部实景园林昆曲《牡丹亭》的表演中,媒介作为一种“为观念的生活世界(life world of ideas)提供给养的技术资源”[12],将“传统一桌二椅式的单一舞台”[13]转换为实景园林,实现了“昆曲和园林双遗产的结合”[14]。“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桃红李白岸柳青,百鸟千花醉”,随着昆曲缠绵细腻的唱腔响起,水景、实景、灯影、倒影交相辉映,《牡丹亭》中的婉约情致和跌宕人生经由声音及视觉景观弥散于由实景与昆曲所编织起来的视听空间网络,相较于以往戏曲表演中对“舞美”“灯光”“音响”的重视,实景《牡丹亭》显然更为看重这种“共生”景观的叙事性。同时,将观者与演员的场景置于一个实景园林之中,这种存续空间的交互,使其表演又增加了一重日常的“真实”,为昆曲《牡丹亭》的表演增添了一层生活的暖意。
综上所述,无论是广布运河流域的红楼梦文化景观,还是海运、河运及地域文化熔铸的天津天后宫,《牡丹亭》与园林、日常生活交融而成的文化景观,我们看到,它们都超越了地域、族群的文化景观,对其理解、阐述乃至建构,都须从“整体性”出发,注重“流域”共性及“人—地—水”的互渗交融。
三、共生发展:大运河流域文化景观的实践路径
大运河流域的文化是在文明互鉴、文化交流中形成的,因而运河流域的文化景观在呈现出文化多样性的同时,其生成、演化又彰显了流域文化的共生机制。“共生”作为生物学概念,本指不同物种的生物个体保持机体的互相接触而生活在一起的系统,日本建筑师黑川纪章在其著作《新共生思想》中明确提出共生观和共生城市,他将佛教的“共存”与生物学的“共栖”重叠组合创造出“共生”理念,此理念在景观领域指不同景观在“兼容并蓄”的精神内核之下形成一种协作关联性,同时实现自我发展的均衡。[15]在其著作中,黑川纪章提出“与创造自然相关联的共有空间(中间领域)”,他认为:
自然保护,不只是一味地呐喊保护、保留乡下的森林,而是应该提倡在东京这样的大城市里面,创建新的森林这一类有创造性的设想。[16]
由于运河流域互相浸润与连通的文化特征,坚持人与自然、景观之间的“共生”成为确保其文化“交互”的整体性及延续性的合理路径,也是实现人与自然、景观融合及交互的重要理念。如何在运河流域文化景观建构中实现“创建新的森林”这一设想,是其共生发展的关键所在。
运河将流域内的自然景观和民众连接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内部凝结着共同价值、经验、期望和理解的意义体系。[17]因此,文化景观的共生发展应当“顺天应时”,在延续自然景观内生逻辑的基础上,运用充满“记忆点”及“可识别性”的景观元素,促进景观内部的“自我更新”,推动人与自然、景观之间的“共生性”发展。
以大运河杭州段文化景观的共生模式为例,其对山水环境、传统建筑、信仰空间等景观进行了统筹考虑,在宏观层面上,对大运河杭州段流域的山体、水系、植被进行整体生态建构,确立“一带、一轴、一心、一岛、一区、一湾”为核心的区域布局,以“大运河文化带”为支撑,推进“文化+产业”发展。[18]在微观层面,遵循滨水景观“图形—背景”关系,营造“内眺式”运河滨水空间,并采用“借景”“留白”“对比”等诗性方式设计“道路—河道引导的‘城市山林’式景观”[19],于细微处体现景观与运河文化的共生。同时,在滨水区域与新建区域之间设立“景观生活复合带”,作为新旧空间的缓冲与协调;在葆有城市便捷性的基础上,使城市空间与运河景观“接驳”,虽在城市,却颇有山林深寂之趣。流域内保留或修复的清代至民国时期的街巷格局、生活景观,以及街巷中零星分布着的建筑、园林、塔庙等各类景观,共同形成了城市景观基底①如祥符老街在保持祥符桥、两户清末的民居、粮仓、茧房和公社的原貌前提下进行拆迁改造,被打造成以民俗技艺为核心的沉浸式体验胜地,成为桥西、小河直街、大兜路后的又一历史街区。,共同构筑“全域没有围墙的博物馆”[20]。
此外,大运河杭州段在景观设计中对于运河流域工业遗产②工业遗产作为人类文明在工业化阶段的证据,以工业景观的形式分布在不同的地理空间中,实际上提供了人类在工业文明发展阶段的确凿的时空线索,是工业现代化的有形标志物。参见张悦群、高宇:《关于工业遗产作为城市记忆容器与文化载体的研究》,《包装工程》2017 年第10 期。的创造性继承也有力地推动了文化景观的“活化发展”。如杭州大城北示范区作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杭州段的核心承载区,老棉纺织厂、桥西土特产仓库等老建筑、工业遗存,已经蜕变为以本地国家级、浙江省级非遗项目阵列为主的博物馆群落,在整体景观协调、平衡理念的基础上,推动原有建筑空间“活化”与“新生”。如尊重现有园区规划格局、建筑空间和工业建筑特征,对老厂房进行保护性利用。“炼油厂文化地标”“杭钢遗址公园”“大运河博物馆”“生态艺术岛”“运河湾片区”等项目内部随处可见对现代工业美感的追求,通过设计创造与工业遗产进行对话;有效利用不同地块工业文化景观的标志物营造“共有”“共建”“共享”的文化记忆,并通过相应的空间、材质、肌理以及公共艺术手段强化文化理念传承;通过融入艺术生活主题,用景观感知的手法呈现“共享”内蕴。
然而,在运河流域文化景观的具体实践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种种矛盾与困难。首先,要注意到景观建构中的“孤岛化”问题,关注不同景观之间的边界过渡及文化景观如何“赋能”城市、乡村建设等问题;其次,要关注到具体实践中的“失序”问题,以整体性、观赏性、实用性为基础,在视觉表征之外,重视声音景观的融合及共生;再次,需要使文化景观与运河、地域(城市或乡村)空间、民众紧密联结,打造“人—地—水”互渗交融的共生空间。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考虑对“人”的把握,不能止步于“深入民间”,而是应当通过运河流域文化景观建构推动文化景观与城市空间的互融,使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实现与运河的共生。以绍兴运河园为例,其与附近的北辰半岛花园小区有一小门连通,小区沿运河而建,临河建有滨水景观,居民们仍旧依靠“流动的水”清洗蔬菜瓜果、刷洗碗筷等,失去航运功能的运河仍然在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维系着人们日常的衣、食、住。[21]其次,实现“流域”内部的贯通,无论是步道的铺设,还是水上巴士、轻轨交通等各种类型的路网建设,都需要做到融合畅通。再次,重视运河流域互相浸润与连通的文化特征,注重文化标志物的选取,充分挖掘兼及地域和流域的民俗元素,用景观感知的手法呈现“共享”内蕴。在未来的发展中,运河流域文化景观建构需要坚持以“人”为核心,通过各类文化景观的“交互”发展,凝聚共识,建设良性发展的运河生态,努力探索出一条“差异互补”“互联互融”“求同存异”的共生之路。
限于讨论主题及篇幅,本文仅就景观特征及交互性稍作梳理,对文化景观以何种姿态存续于大运河文化遗产文化保护实践,人与自然、地域、景观之间的共生在不同文化空间内部的演述方式等问题则另辟文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