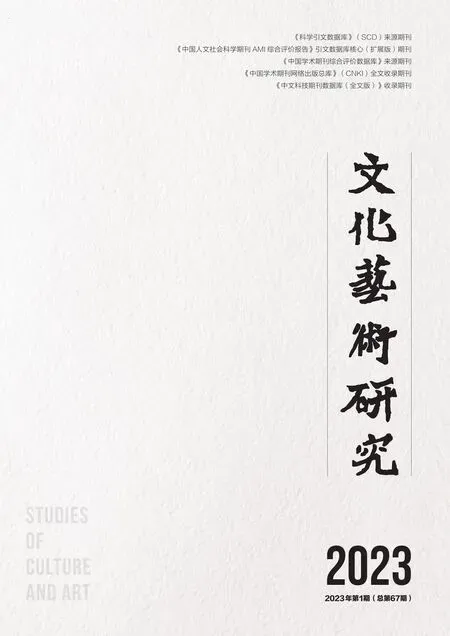末日焦虑、自我降维与精神贫困的时代病
——《三体》文化现象忧思
2023-09-21夏德元
夏德元
(上海理工大学 出版印刷与艺术设计学院,上海 200093)
一
近来,根据刘慈欣同名科幻作品改编的影视作品《流浪地球2》和《三体》的热播,在互联网上再次引发一波关于生存与人性、科学与人文、想象与现实等问题的讨论热潮,其影响之广泛和深入,俨然形成了一个“现象级”的文化事件。
读过小说《三体》的人,想必对书中提出的“宇宙社会学”及其基本假设并不陌生。刘慈欣在《三体》中描述了一个文明间充满敌意,如黑暗森林一般的宇宙。他假设这个宇宙中每个文明都有这样的共识:第一,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第二,文明不断增长和扩张,但宇宙中的物质总量保持不变。因此,每个文明为了自身生存都对其他文明保持时刻的警惕与猜疑;又由于落后文明随时可能发生技术突发性进展,形成对先进文明的优势,从而对其造成威胁,所以先进文明也没有丝毫的安全感。最终,每个文明的选择都是以先下手为强的策略消灭一切其他文明。“宇宙就是一座黑暗森林,每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人,像幽灵般潜行于林间,轻轻拨开挡路的树枝,竭力不让脚步发出一点儿声音,连呼吸都小心翼翼……他必须小心,因为林中到处都有与他一样潜行的猎人。如果他发现了别的生命,不管是不是猎人,不管是天使还是魔鬼,不管是娇嫩的婴儿还是步履蹒跚的老人,也不管是天仙般的少女还是天神般的男孩,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开枪消灭之。在这片森林中,他人就是地狱,就是永恒的威胁,任何暴露自己存在的生命都将很快被消灭。”[1]这就是作者所构想的宇宙社会生态。
不得不说,这样一种宇宙图景并不是人类喜欢的,但是作者通过情节的展开告诉读者,不管你是否喜欢,这就是我们所生活的宇宙的真相。因为宇宙中可能存在许多个高级文明体,他们都遵循同样的宇宙社会学原则,要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下去,就必须互相猜疑,在一连串的猜疑链中,参与零和博弈。一旦建立在猜疑基础上的相互制约失衡,就会发生你死我活甚或同归于尽的决战。更可怕的是,这样的猜疑,不仅存在于不同的星球文明体之间,也发生在地球人内部。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为了自己的生存,地球人之间也会毫不犹豫地互相猎杀,能活下来要么是因为“先下手为强”,要么完全出于侥幸。其实,按照目前人类关于宇宙图景的认知,宇宙中的物质总量虽然是恒定的,但是受光速的限制,宇宙中文明体的增长和扩张范围也是有限的,况且宇宙之浩渺,总有一些文明体之间是永远不可能短兵相接的。正如刘慈欣作品的英语翻译者、同为科幻作家的刘宇昆所言:“任何配得上自己名字的智慧生物,其思维都与宇宙本身一样广博。”[2]而所谓“黑暗森林”的假设从根本上就不成立。刘慈欣之所以要做这样的设定,只能说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罢了。
关于这部作品的创作初衷和创作过程,从刘慈欣的采访中可以看到。“他写小说时,先提出一个世界设定,然后按照这个设定去推导,得到某种结论。一些读者认为故事太绝望和黑暗了,但刘慈欣说,推导出的就是那么一个结论,所以写出来就是那个样子”[3],可见,刘慈欣创作小说确实是“主题先行”的,而主题先行正是一种典型的寓言式写作。事实上,虽然“影射”不被认可为一种“美学概念”[4],但文学史上也有许多优秀作家并不忌讳自己的作品具有隐喻意味,比如创作了政治讽喻小说《1984》《动物庄园》的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谈到创作动机时写道:写作动机主要有四种,包括“纯粹的自我中心”“审美方面的热情”“历史方面的冲动”和“政治方面的目的”。其中,政治方面的目的是“希望把世界推向一定的方向,改变别人对他们要努力争取的到底是哪一种社会的想法”。但是,寓言式写作的通病,往往在艺术性上有所欠缺,所以他总是力图做到“使政治性写作成为艺术”。[5]
从奥威尔作品的接受史来看,他的努力似乎没有白费——读过《1984》的读者,恐怕没有对书中塑造的“Big Brother”形象怀有好感的。反观《三体》,作者在书中所构想的“黑暗森林法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弱肉强食论调,是“落后必挨打”的陈腐观念,照理说应该受到批判。但出人意料的是,这个法则不仅在文学评论中得到一些学者的默认,在现实生活中还成为一些企业领导人的经营指南和管理信条,在互联网社交媒体上,更是受到大批网民的热烈追捧。
出现这种情况,我觉得不只是读者的鉴赏力出了问题,而更是与作者本人的创作理念有着密切的关系。刘慈欣曾在接受记者访谈时说道:“科幻文学从本质上说,就是把现实中人放到非现实的环境中,然后产生故事,这是它的基本原理。而且,你可能注意到,不管是科幻小说,还是奇幻小说,其设定背景90%都是专制社会,很少有民主社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道理很简单,为了故事好讲。”[6]从这段表述看,他似乎只是为了便于讲故事才把人物安排在了“黑暗森林”之中,其实不然。因为他在早些年与江晓原教授的酒吧对话中,就对自己的创作观有过充分的剖白。在被问及其作品是否经历了一个从乐观到悲观的演变时,刘慈欣坚持认为“写科幻这几年来,我并没有发生过什么思想上的转变。我是一个疯狂的技术主义者,我个人坚信技术能解决一切问题”。在与科普作家董仁威的对话中,刘慈欣则明确表示:“我对人不感兴趣,我只对科学感兴趣!这才是我的科幻观!”他甚至认为,如果科学不能解决一切问题,那就解决问题产生的根源;如果科学不能帮助人们找到人生的目的,那就“利用科学的手段把大脑中寻找终极目的的这个欲望消除”。[7]
二
刘慈欣的上述观点,其实不就是现实生活中广受网民诟病的“不能解决问题,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的翻版吗?这样的论调,不用细思,就能让人感受到彻骨的寒冷。由此可见,刘慈欣把人放在极端环境中展开故事,不是意在唤起人们对极端环境的憎恶并努力改变它的愿望,而是对这种环境带着几分欣赏和陶醉,因为他真切地认为:“其实人性这个概念是很模糊的……人性中亘古不变的东西是什么?我找不到。”因此,他在回答江晓原关于其作品为什么能成功时说:“正因为我表现出一种冷酷的但又是冷静的理性。而这种理性是合理的。你选择的是人性,而我选择的是生存,读者认同了我的这种选择。套用康德的一句话:敬畏头顶的星空,但对心中的道德不以为然。”[7]
刘慈欣化用的是康德在著名的三大批判之一《实践理性批判》一书结论开头所说的一段话:“有两样东西,我们愈经常愈持久地加以思索,它们就愈使心灵充满日新又新、有加无已的景仰和敬畏: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居我心中的道德法则。”[8]在这里,康德实际上讲到了两种自律。其中,对宇宙星空的景仰,是作为地球智慧生命代表的人类的自律;而对心中道德法则的敬畏,则是作为人类社会普通一员的个体的自律。从伦理的角度来说,前者是一种宇宙伦理自觉,后者则是一种社会伦理自觉;从美学角度看,前者是宇宙审美,后者是社会审美。景仰和敬畏,就是我们面对自然对象和社会现象时应该秉持的审美原则。很显然,刘慈欣非常自觉地选择放弃道德法则。他甚至在与江晓原的那次对话中,以思想实验之名,主张为了所谓人类文化的传承而毫不犹豫地吃人。
有人可能会为刘慈欣辩护说,他设想的是一种极端的情况,是站在宇宙的宏观尺度做出的明智选择。对此,借用中国近代哲学家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提出的“人生四境界”说来回答:“人与其他动物不同,在于当他做什么事时,他知道自己在做的是什么事,并且自己意识到,是在做这件事。正是这种理解和自我意识使人感到他正在做的事情的意义。”“这些意义的总体”构成了人生的四种境界,包括“一本天然的‘自然境界’,讲求实际利害的‘功利境界’,‘正其义,不谋其利’的‘道德境界’,超越世俗、自同于大全的‘天地境界’”。[9]在这四种境界中,最值得重视也最富有哲学意义的正是“天地境界”,因为人不但是社会的人,而且是宇宙的人,他应该而且能够有更高的境界,那就是天地境界。“大全”就是宇宙,即无限和永恒,追求并实现无限和永恒,才是人生的最高目的。
相反,把宇宙想象为零和博弈的黑暗森林,则不仅是对创生人类的宇宙特性的“有罪推定”,也是对人类灵性和前途命运的自轻自贱。事实上,正如钱谷融先生在《论“文学是人学”》中所指出的:“一切被我们当做宝贵的遗产而继承下来的过去的文学作品,其所以到今天还能为我们所喜爱、所珍视,原因可能是很多的,但最最基本的一点,却是因为其中浸润着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因为它们是用一种尊重人同情人的态度来描写人、对待人的。”[10]我们说文学是人学,是指文学要反映人类的喜怒哀乐,要张扬人性的真善美,或者从对假恶丑的描写中让读者生出对真善美的向往;任何文学作品,如果背离了这样的审美原则,就不是好的文学,甚至不能归入文学。
一些人可能对此不以为然,认为刘慈欣的作品显示了中国人毫不逊色于世界一流科幻作家的非凡想象力,《三体》的出现,“与中国作为大国崛起有着某种时间上同步性的特征,这从其中拯救世界和人类文明的英雄主人公汪淼、罗辑和程心等皆为中国人即可以看出。这一时代性征反映了作者对中国作为大国崛起的充分信心及其因之而来的世界政治格局必然重整的期望……”[11],他们为这样的作品走向世界而欣喜若狂。殊不知,《三体》的对外输出,不仅无助于和平崛起的大国形象的树立,反而暴露出其中隐含的诸多既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相背离,又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激烈冲突的扭曲价值观。从《三体》走红这一文化事件中,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判断——如果说贫穷曾经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那么,“精神贫困”则正在让我们的想象陷入迷狂,乃至心甘情愿地自绝于人类。正如江晓原教授所担忧的,如果认为人类的终极目的只是生存繁衍,“为了生存在极端情况下可以毫不犹豫地把身边的美女吃掉”,或者“赞成在人们脑子里植入芯片,这样就可以完全听命于政府,团结抵抗灾难”,那“这种行为本身就是灾难”。[12]摒弃了属于人的道德,活下去的也已经不是人类。
刘慈欣的问题在于,他把根据极端情况推导出来的“黑暗森林法则”扩大为一种普遍宇宙规律。根据他的逻辑,即使我们尚未面临世界末日的威胁,但因为文明会不断扩张,而宇宙中的物质有限,所以人类迟早会面临生存危机。因此,人类为了自身的存续,必须把一切都建立在这个“迟早要发生”的生存危机上。为了亿万年之后可能发生的生存危机,文明、道德、正义等一切都可以牺牲。这种把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建立在“大灾变”基础上的所谓“冷酷的但又是冷静的理性”,实际上是一种早就被中国古人所唾弃的杞人忧天式的末日焦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网曾发表对法国社会学家弗朗西斯·沙托雷诺的专访文章,驳斥人类即将毁灭的各种“灾变论”。沙托雷诺认为,关于“人类世”的讨论虽然不乏科学意义,“但是利用这一名词预言末世的那些人,可能会扭曲这些解释——这种做法会适得其反”,“未来仍然是开放性的。每一位人文主义者都有义务证明灾变论预言者之谬”。[13]
1816 年10 月28 日,黑格尔在海德堡大学发表的“哲学史开讲辞”中说:“时代的艰苦……使得人们没有自由的心情去理会那较高的内心生活和较纯洁的精神活动,以致许多较优秀的人才都为这种艰苦环境所束缚,并且部分地被牺牲在里面。”[14]北京大学叶朗教授则在21 世纪前夕表达忧虑:“当今世界的一个严重问题是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失衡……黑格尔所描绘的19 世纪初期的这种社会风气,在人类即将进入21 世纪的时候,不仅重新出现了,而且显得更为严重了……这样发展下去,人就有可能成为马尔库塞所说的单面人,成为没有精神生活和情感生活的单纯的技术性的动物和功利性的动物。因此,从物质的、技术的、功利的统治下拯救精神,就成了时代的要求,时代的呼声。”[15]
三
《三体》不仅设想了宇宙社会发展前景中最糟糕的一种可能,还为这个社会中的战争设想了一种致命的战法——维度攻击,又叫降维攻击。谁掌握了一种致命武器“二向箔”,谁就可以将宇宙中的三维物体降为二维平面,从而使整个太阳系变成如凡·高《星空》般的图画,所有的生命都会消失。不仅如此,维度攻击还是一种同归于尽的攻击,发起攻击的一方所在的空间迟早也会跌入二维空间。只有先把自己降入二维,掌握在低维度生存的技能,才可以避免这种同归于尽的结局。且不说这里有一个巨大的漏洞(二维生物没有办法发起对三维世界的攻击),单是“二向箔”的理念就是一个非科学的设计:按照已知微观粒子的形态,哪怕是最小的粒子也只能存在于三维空间,也就是说任何微小的粒子都是有体积的,所谓二维平面、一维直线和零维圆点只不过是一种数学概念。基于这一点,毋宁说刘慈欣所设想的“降维攻击”不过是如“潜规则”和“血酬定律”般的隐喻,它虽然不能让太阳系变成一张画片,却可以像“厚黑学”一样,真的被人类当做“比烂”和互害的武器。
我们知道,历史上高阶文明败于低阶文明的事例不胜枚举,而社会成员间的降维攻击也屡屡奏效:比如“虎落平川被犬欺”;比如“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比如统治者采取弱民、贫民、疲民、辱民、愚民、虐民政策,将民众置于物质匮乏、精神贫瘠之境,令其丧失做人的尊严;比如拥核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逼迫无核国家放弃对入侵的抵抗……但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些现象的存在,不仅不能说明其合理性,反而说明反抗的必要。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威廉·福克纳在1951年5 月28 日的一次演讲中说:“我们的危险是,今天世界上的一些势力,它们企图利用人的恐惧心理来剥夺他的个性、他的灵魂,试图通过恐惧与贿赂,把人降低为不会思考的一团东西。”“那是我们必须加以拒绝的,倘若我们想改变世界,使它让人类能和平、安全地生活下去的话。”[16]在福克纳看来,人类值得拯救也是可以拯救的,前提是不能心甘情愿地被一些势力降维为“一团不会思考的东西”。
其实,统治阶层对民众的降维攻击与民众的精神贫困是互为因果的。按照贝尔纳·斯蒂格勒的判断,当下的消费主义社会迫使人们进入一个“普遍精神贫困”的时代。“知识的普遍丧失……不仅使劳动者的个人技能成为明日黄花,与之一起消退的还有各种人生知识和理论知识。”[17]而早在100 多年前,马克思就对被压迫而不思反抗并幻想着一个救世主的人们提出了批评:“他们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块小得可怜的土地上,静静地看着整个帝国的崩溃。”[18]对于自身的地位、命运和发展,“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19]这种甘于精神贫困的状态,就是自我降维;主动放弃做人的尊严,必然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令人忧虑的是,这样的自我降维在粉丝文化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在围绕《三体》所进行的站队式讨论中则表现得尤为突出。在江晓原与刘慈欣的对话发表之后,江教授立即遭到一大批《三体》粉丝的咒骂,就是因为他不同意跟刘一起“吃人”。在我所能看到的任何一篇讨论《三体》价值观或意识形态隐喻的文章下面都有粉丝们武断的质疑乃至恶毒的诅咒。一位粉丝留言说:“老谈人性人性的!请先问问什么是人?什么是人性?你之所以能在这谈人性,就是人性自古就只有一条铁律,那就是生存与繁衍……”即便无话可说,他也要质问一句:“你写这篇文章是何用意?”如此看来,虽然刘慈欣的作品与其创作观并非完美自洽(他宣称自己是极端的技术主义者,认为技术进步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而他的作品又是悲观绝望、找不到出路的),但是他的作品所得到的读者反馈却是他所期望的。
可是,在这样的作者与读者(观众)的迷狂共振之中,文学何在?文化何为?人又在何处?或如徐英瑾教授所指出的,按照《三体》的逻辑,恐怕不仅是物理学不存在,哲学也不存在了;而照此逻辑再推演下去,必然是“人类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