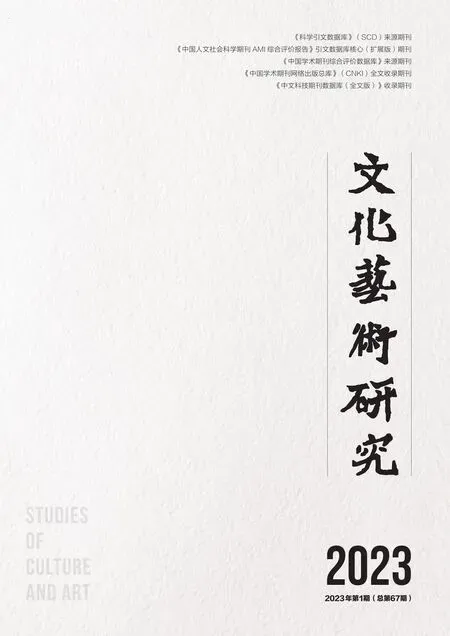《三体》里的哲学:不存在啦!*
2023-09-21徐英瑾
徐英瑾
(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上海 200433)
一
哲学与文学的关系一直很密切。按照主流的美学理论,哲学理论与文学往往讲的是同一个道理:只是哲学诉诸理性,文学诉诸感性,路径不同却目标一致。因此,在正常情况下,阅读被公认的经典文学作品并不会给哲学家带来“违和感”。甚至一些哲学家自己也搞文艺:哲学家塞涅卡与萨特都是戏剧高手;黑格尔虽然不直接搞文艺创作,但其哲学著作里也常会提到一些文学桥段,如《安提戈涅》与《拉摩的侄儿》。马克思年轻时候也想做诗人,后来虽然没做成,但其哲学著作的文笔也是一流的。
但对于“哲学、文学一家亲”这条定律来说,刘慈欣的《三体》可能是一个例外。这或许是部公认的科幻经典,否则也不会被翻拍成影视剧——但作为哲学工作者的我却感到自己的确非常难以吞咽《三体》的世界观。换言之,如果这部小说的世界观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全世界范围内哲学系教的哲学——从孔子、孟子、亚里士多德到马克思、海德格尔就全部错了。我个人可不愿意承担这个代价,而且我隐隐怀疑看不到那些愿意付出这个代价的人是否真正理解从孔子、孟子、亚里士多德到马克思、海德格尔的哲学到底在说啥。
先从最基本的事项开始说。《三体》的基本世界观是“黑暗森林法则”:宇宙中各个文明为了自保,就要毁灭别的文明,然后只要发现别的文明的坐标,就要去消灭之。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原则,因为该原则预设了:试图摧毁其他文明的文明很难主动发现自己所要摧毁的目标。然而,假若你的科技树已经高到只要发现别人的坐标就能将其“团灭”的地步的话,你怎么会连主动发现该文明的能力都没有呢?如果大家没听明白我提的问题,我就换一种方式问:假设你是U 国的指挥官,你的任务是要摧毁入侵你国的R 国的高价值军事目标,那么对于你来说,是发展出发现敌人的科技产品来得容易呢,还是发展出摧毁敌人的科技产品来得更容易?我想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发现敌人的科技更容易被发展出来,而要搞定摧毁敌人的科技就难多了——因为发现目标所需要的能量整合与物质投送能力要远远小于实际摧毁目标(举个例子吧,“八·一三”抗战的时候,中国空军即使很清楚停在海上的日本“出云”号的位置,但也很难消灭之)。①我能想到的最符合“黑暗森林法则”的既有战例,乃是发生于1942 年11 月13 日的瓜岛海战。当时夜黑,日美两国军舰无法识别敌我,只好根据“谁暴露位置就朝谁打”的策略进行战斗。此次战斗美军实际损失高于日军。但即使是这一战例,也不是在《三体》预设的那种信息条件下进行的,因为美国海军与日本海军当时都知道两国早就在外交上彼此宣传了,而且,双方交战的真实目标也不是消灭完整意义的对方文明,而仅仅是争夺作为日军进犯澳洲之门户的瓜岛。而且,至少就美军而言,对于被俘虏的日军也给予了应有的人道主义待遇(如果他们能够抓到俘虏的话)。
如果有的读者还是不理解我这个反驳的思路的话,我只能搬出老祖宗孙子的《孙子兵法》了。孙子云:“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换言之,一个文明要有把握消灭另外一个文明,就得确信自己有对手十倍或者以上的能力。但问题是:该文明是怎么知道这一点?即使在地球上,一个国家要摸清另外一个国家的真实军事实力都是很难的,比如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之前,谁知道小小的以色列可以强到一国击退五国?所以,要摸清对方的实力,就需要大量的试探与试错时间——而《三体》却预设你一发现对方坐标就要团灭之——问题是踢到了铁板被反杀咋办?先调查个一百年再思考对策不好吗?按照孙子的思路,这样缺乏纠错机制且鲁莽行事的文明,应当早早灭亡才是符合天道的(我隐隐听到达尔文在此也鼓掌了:不愧是孙子啊!)。
从这个角度看,“黑暗森林法则”就包含着一个逻辑上的倒错,即将应当随后建造的二层楼当成一层楼来造。从哲学角度看,逻辑上的倒错是很致命的硬伤,所以读到这里,我的脑子就被卡住了(我很惊讶于小说中的罗辑能够接受这套逻辑)。②当然,有人也可以这样反驳我的立论:按照《三体》的假设,比较落后的文明随时会有“技术爆发式进展”,使得其与先进文明的差异变得很小,因此,出于“先下手为强”的心理,较为强大的文明也要迅速灭亡这个比较落后的文明。但且不提“技术爆炸”为何一定会促发侵略心理(请看后文讨论),先进文明测度落后文明的“落后”程度的过程也是需要消耗时间的,而不能采取“发现即开火”的模式。
接下去问题又出现了:黑暗森林法则预设了宇宙的资源是有限的,因此,各个文明为了抢夺有限的资源必须互相消灭。有这几个问题:第一,谁告诉你宇宙的资源是有限的?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里就告诉我们:宇宙是否无穷大,时空是否是无限的,都不是人类理性能够回答的问题,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给出一种武断的见解,康德就不答应。③这就是著名的康德“二律背反”理论中的一部分。对于相关背景知识的系统化解读,请参看:Sadiq Jalal Azm, The Origins of Kant's Argument in the Antinomi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第二,资源的本质是啥?人力资源不是资源?智力资源不是资源?两个文明如果互相学习各自提高科技树的话,难道不会集体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让双方都得利?第三,提高科技树的本质是啥?难道一定是消耗更多的资源吗?恐怕不是吧,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并减少对环境的污染,难道不是科技树提高的一种具体体现方式吗?如果事情真是这样的话,那么,科技树的提高为何一定会带来资源的紧张,并最后导致“先下手为强”的心理的出现?如果上述我对于科技树提高这件事的理解是对的话,那么,即使宇宙的资源是有限的,黑暗森林法则的可成立性也会大打折扣。
二
上面的哲学反思主要动用的是逻辑学与形而上学的资源。正如一些读者所可能预料到的,我马上要讨论伦理学问题了。《三体》预设了外星文明的高度反伦理性——为了自己的生存可以毫无顾忌地消灭他者——但这个设定其实也会引发进一步的概念矛盾。
为了使得我的论证更有说服力,在此我暂时不预设“任何智慧生命都需要伦理”这一点,而接受刘慈欣描述的“三体世界”:在该世界中,由于三颗恒星所组成的星系系统所具有的复杂性,行星的温度变化毫无规律,因此,在行星上出现的智慧生物必须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拼命生存与发展(写到这里,我靠着强大的毅力才终于迫使自己不去想“如此混乱的行星运动轨迹如何保证稳定大气层的存在”这个问题①虽然在小说中,三体人被设定为具有在恶劣环境下通过“脱水”获得休眠机会的能力,但由此得到的休眠体是否可能在极端物理条件下生存,依然是令人困惑的。而且,任何生物的生存都需要复杂生态链的配合。因此,从理论上说,三体星球上的所有生物都必须掌握“脱水生存大法”,否则,三体人独自脱水是毫无意义的。但完全不可能掌握历法的低等三体生物如何可能知道“脱水”的合适时机呢?)。而也正因为生存环境的严酷性,三体人的伦理规则在我们看来就是反伦理的:他们没有闲暇与艺术,并会毫不犹豫地处死任何一个对整体发展没用的个体。毫无疑问,他们的社会制度很难是民主制的(甚至是原始社会的那种粗陋民主制),因为民主决策需要的时间成本,他们是无法支付的。
不过,科技树的生长必须依靠大量的试错成本的付出——大家想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德国就发展出飞翼技术,但到了今天,真正掌握隐形飞翼制作技术的国家还相当稀少,这又是为何?这是因为:技术发展的每一步都是坑,而且,都要很多科研失败去证明“这是坑”,后人才能绕过去。现在问题来了:谁又是对三体人的技术发展没用的人?是那些被证明掉入坑里的人吗?但如果没有他们的付出,后面的人又如何将这些坑绕开呢?再者,谁知道那些失败过的人不会咸鱼翻身呢?所以,从原则上看,三体人就无法认识到到底哪些人是对其科技发展有用或者没用的——因此,他们就无法使用刘慈欣所建议的方式而去随时抛弃社会负担(这使得我想起日本电视剧《帕累托法则之误算》里的一句台词:虽然我们抽象地知道社会上有八成的人是吃闲饭的,但是我们不知道具体是哪八成)。相反,假设三体人具有超能力知道哪些人未来一定是有用的,那么,为何他们又不能将这种超能力立即用来发展科技并在此过程中绕开所有的坑呢?
好吧,为了继续下面的讨论,现在我又强迫自己没有看到上面的二难选择,而是咬着牙预设三体人的世界的确存在着一种“无用者立即死”的恐怖社会现实(不知怎的,我脑海里突然出现了电影《辛德勒的名单》里那个用狙击步枪随时杀死动作迟缓的犹太人的纳粹军官)。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科技还可能在短暂的时间间歇里发展起来吗?
从科学在地球上的发展情况来看,恐怕很难。科学的根子在哲学,而哲学起源于惊异与闲暇,而不是恐惧。伟大的科学发现往往起源于不经意的灵感,而灵感的积累又得靠闲暇(比如,如果门捷列夫忙到无法睡觉的地步,他又如何在梦里看见元素周期表?),请问,这样的规律是否适用于外星文明?至少我相信事情是这样的。伟大的科学发现往往起源于伟大的假设的提出,而伟大的假设本身只能是想象力的产物。从神经科学的角度看,想象活动需要各个脑区之间的协同工作,而长期从事奴隶般劳动的人因为工作的单一性,多脑区的协调力自然是很差的。从这个角度看,以奴隶方式从事劳动的三体人发展出高科技的概率极低。
说到这里,读者或许已经明白我的大致用意了:高科技的发展是必须要有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与之配合的,而三体人的社会却没这种环境。同时,宽松的社会环境又与社会对于个体自由与安全(包括人身安全与财产安全)的各种保障相联系,这也就倒推出了社会的伦理性对科技的反哺作用。而这一点在地球文明上也早就得到验证了:很多科技史家认为,英国之所以成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促发国,其对于发明专利的保护制度可谓功不可没。[1]而保护发明人的工作热情,不搞盗版,这本身就是一种伦理精神(而不仅仅是一种法律要求)。然而,刘慈欣的三体人却是彻底反伦理的:三体人没有五险一金,没有工伤赔偿金,他们都是耗材——遑论专利制度以及与之配套的海洋法体系(我说过了,三体人没时间搞这些貌似无用的社会工程)。因此,三体人的科技世界的社会学土壤所展现出来的特性,与我们已知的主流社会学、伦理学知识都高度冲突。
说到这里,有些人或许会反驳我说:你说的这些大都是文科知识,用文科知识讨论科幻小说,有意思吗?我个人觉得这个问题很无聊。现在人类知识的发展已然交叉到了这个地步,文理分得那么清楚有意思吗?比如,博弈论究竟是文科的还是理科的?与其思考这个无聊的学科归类问题,我们还不如来问一个具体的问题:《三体》所展现的地球人与外星人之间的博弈模式,符合博弈论吗?
我的答案是否定的。众所周知,要在博弈中避免陷入囚徒困境(即双方互相出卖,最终导致双方都受到极大损失),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就是消除怀疑,增进互信。地球上的高等文明都发展出了一套增进互信、减少误判的社会学机制,比如共同的语言、共同的艺术欣赏习惯、共同的饮食与服饰,以及共同的宗教,等等。这些社会学机制的运作都能大大增加个体对于文化共同体的从属感,由此使得社会内部减少内耗。从这个角度看,那些三体人所鄙视的文艺活动,恰恰是能够使得地球人生存的重要保障。但在《三体》的世界中,地球人与外星人之间出现互信的机会是非常稀少的——虽然在小说第二部中外星人与地球人通过掌握彼此摧毁的能力而勉强实现了和平,但这种脆弱的和平又在第三部中被轻易颠覆了。从既有的博弈论知识出发进行推理,我们会发现小说的结尾必然是绝望的——没有人能够幸存下去,特别是在第三部小说里出现的“降维打击”技术的威胁下(拥有降维打击能力的外星人没事打击别人的动机是什么?你会因为觉得你比蚂蚁高等而一天到晚踩蚂蚁玩吗?)。
三
写到这里,可能又会有人反驳我了:为何科幻小说家不能写一个绝望的结尾?为何要假设地球上的所有伦理法则,在别的地方也成立?既然小说的第一部就将“物理学不存在了”这个让人震惊的想法抛给了读者,为何我们不能继续设想“哲学不存在了,社会学也不存在了”?
我的答案非常简单:即使是科幻小说,也是写给地球人看的,因此,小说创作必须考虑到特定的社会功能。举个例子来说,虽然历史上有大量的小说家都喜欢写悲剧,但悲剧的本质毕竟是“让美好的东西被粉碎掉,由此让你更珍惜美好”,而不是激发读者的破坏欲。因此,那些过于宣扬暴力的小说,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儒家说的“发乎情,止乎礼义”,也是这个意思。具体到科幻作品上,科幻作品的社会功能也主要有两项:第一,传播科学知识;第二,探索在与现有技术条件不同的条件下,我们是否还能保持人性——请注意,这种探索的目的乃是为了最大程度地保存人性,而不是摧毁之。
很多优秀科幻作品都体现出了这两种社会功能。以《火星救援》[2]为例:这部小说既带给了我大量很靠谱的关于火星的天文学知识,也促使我思考这样两个伦理学问题:第一,一个宇航员在队员很难对其救援的情况下,应当选择自杀还是继续努力维持自己的生命?第二,在我们知道有一个宇航员在天外“落单”的情况下,是否值得调用国家级别的资源对其进行营救?对于这两个问题,这部小说给予了读者明确的答案:第一,自己的生命是最宝贵的,只要有一线希望,就不要放弃;第二,队员的生命也是无比宝贵的,只要资源允许,就要努力施救。这部小说的结尾其实是带给了读者这样一种安全感:发展科技,就是为了每一个个体的安全,没有一个人会被拉下。
但《三体》带给了读者一种绝望感:你不能相信任何人。且不说地球人不能相信三体人,地球人的太空战舰之间也会因为争夺有限的物资而互相开火。正如霍布斯所言,“人与人之间如狼与狼”。进而言之,小说中某些情节的设定,甚至会诱发民众产生不信任自己政府的危险情感——比如,小说中设定M 国国防部长秘密制定计划,要将一部分士兵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其“幽灵化”(我暂时不想解释“幽灵化”的科学含义,恕我驽钝,我没理解),以便与外星人作战。我们很难担保不会有部分心智脆弱的读者在读了这些桥段之后,会产生如下奇怪的想法:我们的政府是不是也在秘密制订一个将民众幽灵化的恐怖计划呢?换言之,通过小说这个媒介,作者可能是将他本人对于人类的不信任投射到了社会的层面上,由此导致恐慌扩大化。这种恐慌既会削弱人民对于自己的政府的信任,也会破坏政府成员彼此之间的信任,其实隐隐带有“祛除社会架构之复杂度”的意味。
一个文明的整体战斗力,在根底上看的是社会组织的丰富程度。举个例子,太平洋战争之前日本之所以轻视美国,就是认为美国人是花费大量时间去享乐的花花公子,而日本人才是地球人中最像三体人的,全国上下为打仗做准备,个个忙得像奴隶。但当时日本人缺的是什么?是社会组织的丰富度。换言之,军国主义的社会架构将所有资源都变成军队资源,而民间却没有冗余资源(比如,当时全日本会开飞机的几乎都是军人),因此,一旦政府的资源被消耗掉,战争就输定了。而美国民间的航空力量却在不占据国家预算的情况下,预备了大量的飞行员——这些人可本就是抱着“玩”的心态去学习飞机驾驶的哦。从这个角度看,类似三体人的竭泽而渔的社会组织,只能像程咬金的三板斧那样在短暂的时间内体现出一点点优势,而根本无法保持这种优势——而这一点本身既在秦朝的短命中得到了验证,也在日本法西斯的失败中得到了验证。由此,我们也应当理解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为何是“自由人的联合体”了——因为无论共产主义社会是什么,它肯定不会让个体生活在感到“自己随时会被出卖”的恐惧中。最后说一句,在刘慈欣的小说里,他几乎没考虑到外星人的文明能够进化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可能——然而,按照马克思的学说,文明的科技水平的提高与人道水平的提高本该是相辅相成的(譬如,恰恰是因为封建社会比奴隶社会更人道一点,其生产力才更发达,因为人的主观能动性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释放)——由此推算,那种远超目下地球人水准的外星科技,也应当与远超目下地球人水准的道德伦理相匹配。换言之,一个进化到共产主义阶段的外星人文明,恐怕不可能来团灭地球人吧!相反,他们更应当主动告诉我们进入共产主义的正确道路。但是,这种对于外星人的善意估计在《三体》中却基本是付诸阙如的——这究竟是因为作者本来就不相信马克思主义呢,还是因为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适用于整个宇宙的普遍真理呢?这个问题就留给他自己去回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