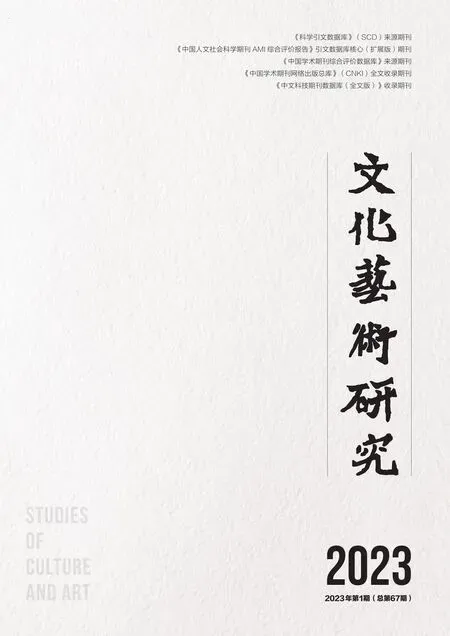沟通即文明:《三体》内外的媒介和传播
2023-09-21邓建国
邓建国
(复旦大学 新闻学院,上海 200433)
《三体》是一部关于communication(s)的科幻小说,是一部“宇宙传播学”小说。Communication(s)有“交通”(物资的运输、媒介)和“沟通”(精神的运输)两个含义,而整部《三体》的预设背景和情节发展都围绕着该词的两个意义提出和推进,矛盾也因此而生。
一
《三体》用communication(s)来定义文明及其先进或落后。比如以下对话:
审问者:你了解三体文明吗?
叶文洁:不了解,我们得到的信息很有限,事实上,三体文明真实和详细的面貌,除了伊文斯等截留三体信息的降临派核心成员,谁都不清楚。
审问者:那你为什么对其抱有那样的期望,认为它们能够改造和完善人类社会呢?
叶文洁:如果它们能够跨越星际来我们的世界,说明它们的科学已经发展到相当的高度,一个科学如此昌明的社会,必然拥有更高的文明和道德水准。[1]
这里,小说以作为“交通”含义的communication(s)来判断文明的发达程度。这很常见。在历史上,对空间距离的克服能力的增强,无论是步行、骑马、(蒸汽)轮船和火车、喷气式飞机等,都被视为文明飞跃的标志。
当然,这段对话的最后一句(也是关键一句)有明显的逻辑问题。叶文洁将科技发展水平等同于文明和道德水平,就无法解释“高尚的野蛮人”和“野蛮的文明人”现象。完全可能存在着这样一种情况—— 一群“文明人”集中力量发展科技,对外野蛮侵略,正如康拉德在小说《黑暗的心》中描述的,欧洲殖民主义者以一种至高无上的观念作为他们的信仰和支撑,以传播文明、帮助落后民族的名义来实行他们对“黑暗的”非洲人民的残酷统治,一时间让人分不清谁文明,谁野蛮。
《三体》中还提到,三体人有两种高效的沟通方式。一是通过脑电波实现所想即所说。这种心灵感应(telepathy)的交流效率远大于地球人的语言文字交流的效率。因为这种透明的交流方式,三体人个体完全没有自己的想法,阴谋诡计也无从产生,所以地球人的“面壁计划”才可能对三体人构成威胁。二是通过体表的类镜面结构进行远程传输。为了抵抗三体世界多个太阳同时出现带来的高温和强光,三体人的身体表皮进化出一种类镜面结构,三体人利用它的光谱进行沟通和传播,原理类似于现代计算机之间的通信。多个三体人还可以组成“三体人列计算机”——例如三千万个三体人凭借体表的变化形成面积巨大的反射镜面,聚焦光线,快速传输信息。脑电波和体表的类镜面结构让三体人彼此可以像“天使沟通”一样心心相印,畅通无阻,使得三体文明一开始就进入信息时代,这也是三体人科技被认为远超人类的根本原因。在这里,《三体》透露出一种“媒介和传播技术决定论”的色彩。但鉴于这些技术对过去和未来人类文明的至关重要性,这种决定论与马克思的生产工具决定论一样,并非毫无道理。
但是,如果说宇宙文明间的相处遵循的是“发现即消灭”的“黑暗森林”法则,三体人脑电波和镜面沟通在提高个体间沟通效率的同时,也必然导致三体人心灵之间的“黑暗森林”法则——三体人强者对弱者个体思想上的异端也是“发现即消灭”。这必然导致一个心灵(mind)对另外一个心灵的操控,因此三体人处于一个科技发达、沟通野蛮的极权社会便不难理解了。
作为地球人,我们一直对“太少的沟通”和“太多的沟通”有所顾虑。太少的沟通会导致人际关系的疏离,太多的沟通则会导致一方对另一方的操控。由于个体间身体的隔绝,我们一直哀叹心为形役,认为身体导致我们之间“太少的沟通”,希望摆脱其牢笼,实现目击道存的沟通理想。同时我们还埋怨言有尽而意无穷,劝告人们不要过分依赖媒介,而要得鱼忘筌,得意忘言,“不要因为贪恋路上的美景而忘记我们真正要归去的故乡”(奥古斯丁语)。媒介之于我们,既是桥梁,又是沟壑。只要有更好的依凭,我们就会弃旧媒介如敝屣,去追求更高、更快和更强的“杀手级”新媒介(比如脑电波和体表的类镜面结构),希望能借助它们瞬间冲破重重障碍(空间、时间、物理和心理的障碍),直达边缘,直击人心,夷平差异,传播普世价值,怀敌附远,实现人际和谐和世界和平。
但同时,我们也对“太多的沟通”充满恐惧,害怕强大的媒介侵入大脑,操纵心灵,推行霸权,消灭个体自主性和地方性。例如,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认为,广播技术在观众与明星之间假造出一种互动关系,这是在制造“虚假的身体”。他认为,广播的危险不在于它能煽动乌合之众,而在于它能将听众塞进毫无反思的安稳的蚕茧或虐待狂般的狂笑中。他指出,发达媒介社会里的大众文化催生了所谓“退化性听众”(regressive listeners)——那些张牙舞爪,陷入虚假极乐的人。他说,“文化工业”的诡计在于,诱发虚假需求并满足之,以平息受众的可能反抗。
“太多的沟通”推至极端,则完全消灭了语言(最终消灭身体)这一“言不尽意”的媒介。但我们应该意识到,正是人的身体的隔绝和语言的“不透明”,形成了人类不同的自我、自主性和隐私观念。我们都有念头一闪但欲言又止的经历,也可能因自己说出去的话如泼出去的水一样不可收回而感到后悔。人类之间(以及三体人之间)完全即时和透明的沟通会让关系更融洽还是更具敌意,会导致信息强者(the information haves)对信息弱者(the information have-less)的侵占甚至奴役吗?[2]三体人中心化的极权社会组织形式为我们提供了答案。我们可以想象,三体人的脑电波和体表的类镜面结构恰如现代社会的“文化工业”和今天甚嚣尘上的社交媒体。在“太多的沟通”中,强者侵入和操控众多弱者的身体和思想,形成了一对多(one-to-many)的专制传播和政治制度。因此我认为,对地球人而言,即使脑电波(脑机接口)和镜面沟通在技术上可能,也并不一定要实现它们,因为这不只是技术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和伦理问题。
二
光作为媒介的局限性形成了宇宙中不同的诠释社群。《三体》中,刘慈欣借叶文洁之口,假设了“宇宙社会学”的两个重要概念:“猜疑链”和“技术爆炸”。“猜疑链”是指,在communications 受到光速限制的情况下,浩瀚宇宙中的不同文明处于不同的“诠释社群”(interpretative community),因此一个文明无法知晓另一个文明对自己是善意还是恶意的,一个文明也无法知晓另一个文明认为自己是善意还是恶意的。由于猜疑链的存在,不同文明间永远无法达成绝对的信任,唯一保险的对策是一个文明必须对其他文明实行“发现即消灭”的“清理原则”,所以文明间永远处于无所不用其极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霍布斯语)中。这里,《三体》预设了交通/沟通是宇宙文明间关系的决定性因素,交通即沟通,有沟通即有和平,无沟通便有战争。实际上,小说的这一底层逻辑并不严密,比如人类和蚂蚁可以说是两个无法沟通的文明,但人类见到蚂蚁的第一反应并不一定是将其碾死,反而还可能认为,人类和蚂蚁两个物种或文明同处于地球生态中,能发挥各自的作用,虽然影响链条很长,但毕竟相互依赖,所以值得保持和平。这是另话。
“相对论也是传播学”(彼得斯语)。爱因斯坦的伟大发现之一是时间和相应信号速度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宇宙只能在速度有限的前提下与自身交流,因为信息的移动速度无法超过光速。而对宇宙深空而言,光速还不够快。爱因斯坦认为,在宇宙中不可能存在标准时间,因为不可能存在着一个对宇宙中所有点都绝对有效的“现在”。[3]396
这意味着,媒介的到达能力与“诠释社群”的范围相互建构。无论是教堂钟声(上帝福音)、大炮射程、驿站邮路、无线电波还是公路高铁,其所达范围既是物质运输和投放的范围,也是中心对边缘的影响力范围和精神文化共享的范围。到目前为止,地球上实现“瞬间到达”(貌似无时差但实际有)的媒介只有无线电波(光速),所以我们才有“地球村”之感。但在浩瀚无边的宇宙中,光速作为传播媒介的速度还远不够快,传输与接收之间存在明显的时间差,这导致任何宇宙文明都不可能试图通过传播来建立“宇宙村”。
如何理解?不妨想象一下,地球和三体星系之间的每一次信息交流即使以光速传播都需要3 年(或任何其他数字),二者都持续发送和接收,由于传收间的时间差,二者很快会无法区分哪个信息是一方对另一方“此前”信息的回复,哪个信息是一方“此后”对另一方新发起的信息。对此,我们可能会说,如果地球人和三体人在自己发送的信息上打上时间标记(time stamps),那么他们收到信息后各自将其按时间先后排序解读,就不会陷入信息混乱了,我们的“包交换”互联网通信就是这样的。但这需要地球人和三体人共享一个“标准时间”来标记信息。而要在宇宙中彼此距离超过光年的两个文明间实现这一点,需要找到一个比光速还快的媒介。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对以光速前进的两个时间进行“对表”,我们必须具备一个比光速更快的媒介,但这样的媒介目前还未被发现。所以,地球文明和三体文明之间注定不可能共享一个标准时间[3]419,从而也无法给传收信息打上时间标记,也因此注定属于不同的诠释社群,无法相互理解。
三
Communication(s)对《三体》的全面渗透还体现在所谓“先验型媒介”上——三体世界对三体人的身体和意识的本体性建构,以及因此造成的三体人和人类之间的沟通难题。
《三体》没有具体描述作为地外生命三体人的模样,因为作为地球人类的叶文洁(包括刘慈欣)确实无法精确想象出他们的样子。对未曾经历的,我们就无法想象,即使能想象,也只是基于对已有经历的延伸。韩非说,画鬼魅易,画犬马难。既然不存在现实版本的鬼,我们就完全可以脱离现实胡乱地想象(画),也就无所谓逼真与否;但犬马是现实存在的,对其描画,人们就会有是否逼真的期待。
科幻小说是一种“想象和奇观”(speculation and spectacle)的结合,其想象显然不同于“画鬼”,而是要受到一定规则的约束,做到情节真实和自洽。“真实”指小说是基于当前现实和现有科学规律对“近未来”进行合理想象;“自洽”指小说情节内部各部分之间不相互冲突。“真实”是“自洽”的基础。那么,对地球人从未见过的三体人(外星人)的样子,我们如何做到“真实”地想象?
在今天的世界中,媒介(ITCs)弥漫渗透,已经成为新的自然,但其实,“自然”也是一种媒介。作为“先验媒介”(media a priori)[3]395,“自然”塑造着其中的生物的身体(眼耳口鼻以及大脑),决定了其必然以特定的器官(媒介)来沟通和传播,这也意味着,媒介与传播方式是与具体物种相关的(species-specific)。这导致跨物种的沟通成为不可能——如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所说,我们不可能想象成为蝙蝠(马或章鱼)会是什么感觉。
既然环境塑造了生物,或者如斯宾塞说,生物的器官(功能)是其对所处环境的反应,我们就可以反过来从三体人所处的环境(三体世界)来推测三体人的样子。三体世界属于地外环境,正在经历所谓“三体恒星乱纪元”带来的酷寒和酷热,多半还缺氧、高压,时而高亮,时而黑暗。地球上也有相似环境,例如深海,黑暗、低温、高盐和高压,因此产生了适应这种环境的生物(灯笼鱼、囊喉鱼、章鱼等),它们大多眼睛完全退化,身体细小柔软,缺乏钙质骨骼,耐高温、耐高压、耐酸碱和耐盐。此外,在地下黑暗环境中生活的有睡鼠、蚯蚓、蝰蛇和鼹鼠等动物,视力退化,但其他感官强大。在南美洲和中美洲干旱地区则有耐干旱和耐低氧的“清道夫”(甲鲶)。
我们对三体人的想象可以基于对以上恶劣环境中的生物特征的极端推演。例如,为了适应三体星系乱纪元地狱般的自然环境,三体人可以保持长时间睡眠,可以随时抽干身体水分进行纤维化收缩,遇水即可复原,因此其身体主要以软组织细胞和纤维化的骨质结构为主,这样才能够快速脱水或者浸泡复原;其皮肤应该是类似海绵的块状细胞皮;三体人的体形中等,不如恐龙般巨大,也不如地鼠般极小,通过分裂繁衍,在每一次进化中,除了保持其纤维状身体构造,它们的体型外观都不相同;“脱水存储”成为三体延续其文明(transmission of culture)依赖的媒介,他们建造出大量坚固的“谷仓”,用这种“容器型技术”[3]156储存脱水后的三体人;它们还建造出各种“阿兹特克金字塔”(时间偏向的媒介),其尖顶高耸出行星表面,其底部深入行星内部,以此来抵御残酷的自然环境。
环境塑造了身体,身体决定了传播,因此,媒介及传播方式与具体物种相关。生物在判断来者是敌是友时,总是先打量对方是否与“我”在身体和沟通方式(语言)上相似。伍迪·艾伦(Woody Allen)认为,如果一个动物长得像鸭子,走起路来像鸭子,叫起来像鸭子,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它就是一只鸭子。人类在判断同类和异类时,也是依据这一常识。我们总是通过来者的身体外形、内部构造和沟通方式来判断其是否非我族类,而绝不会试图与一条蚯蚓交流。
三体环境塑造了三体人与地球人迥然不同的身体和意识,因此造成了三体人和人类之间的沟通难题,造成了对地球人而言,“三体人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毁灭你,与你何干”的可怕局面。但根据《三体》的描述,人类文明中有一个人见过三体人,那就是云天明,而云天明能够在三体世界一直生活下去,并且很受后者的欢迎,说明三体人和人类可以沟通。这是否意味着三体人的身体结构和地球人的身体结构,或者说三体环境和地球环境的差别可能并没有那么巨大?这是《三体》情节中的又一个矛盾。
弗里德里克·基特勒说,媒介学是所有其他学科的元学科,因为所有学科都涉及媒介。杜汉姆·彼得斯说,天文学以宇宙光为媒介,历史学以地上地下记录为媒介……在我看来,《三体》中建构的“宇宙社会学”其实就是“宇宙传播学”。
四
布鲁克斯·兰顿(Brooks Landon)曾简明扼要地总结科幻电影的特点:“科幻电影既有叙事又有奇观,既有艺术上的愉悦又有垃圾般的娱乐,既诉诸观众的智识又诉诸观众的情感,既鼓励观众的自我逃避又鼓励观众的自我启蒙。而恰恰是这种‘既……又’冲动,使科幻电影具有了内生的矛盾性。”[4]科幻小说的另一个基础性矛盾是,它通过各种科技来展现未来世界的盛大奇观,但是大部分科幻小说又试图揭示未来科技给我们带来的异托邦可能。
美国实证主义的传播学追求的是确定性,因此,其传播理论中有一系列理论以此为预设,属于“降低不确定性理论”(theories of uncertainty reduction)。这些理论视沟通中的矛盾和悖论为“异数”,着意于剔除它们,以实现清晰沟通的目标。然而,热力学第二定律表明,世界的模糊和混乱远多于清晰和有序。正如“差异是我们进行沟通的前提和获得快乐的源泉”(伽达默尔语),矛盾和悖论也具有巨大的生成性(generative),能激发大量的思考、交流乃至辩论,有利于人类增进相互理解。在春秋战国时期,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以邓析和公孙龙为代表的名家,通过矛盾和悖论方式展现出世界和言语的多样性,给我们带来的智识上的启示要比儒家和法家等多得多。
《三体》作为一部科幻文学,本身恰如布鲁克斯所说的充满着矛盾。例如,除了前文所说的“猜疑链”以及地球人云天明与三体人的沟通外,小说主人公叶文洁也是一个认知矛盾、角色矛盾的人物。叶文洁是物理学家叶哲泰的女儿,叶哲泰坚持不肯向非理性的狂热屈服而被批斗致死,这使善良而温和的叶文洁对人性失去信心,认为人类堕落不可自救,只有借助外力冲击才能变好。叶文洁通过自己在天体物理学上的非凡成就与三体人建立了联系,并以冷酷的理性将其引到地球,希望三体人能引导人类更好地发展。如此做后,她一直处于道德内疚中,但这种内疚很快就被她看到的人类的新的丑恶消解了,最终叶文洁成为地球三体组织的领导者。
《三体》和相关衍生品的改编和传播大幅扩大了其受众基础,各种受众对其内在的矛盾性做出选择性解读,每个人都形成了自己的“三体宇宙”,自然也就引发了各种争议。
我认为,《三体》的获奖和跨媒体创作火爆,固然证明了中国科幻创作和传播的长足进步,但也显露出一些隐忧。例如,它产生了一些《三体》迷。这些人坚信小说中基于猜疑链的“黑暗森林”法则(实际上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不仅将其套用在人际关系上,甚至用来看待国际关系,将国际社会视为弱肉强食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的动物世界。[5]这使人想起2015 年因电影《狼图腾》上映而被一些人热议和推崇的“狼性文化”。“弱肉强食”“狼性文化”“黑暗森林”“发现即消灭”“真理只在大炮的射程范围内”等说法,原本是强者在侵略弱者后为自己辩护时提出的极具迷惑性的借口,如今却不断从尚未真正强大的中国人的口中说出,这种制造分裂甚于制造和谐的现象,不免令人担忧。由此看,如果说《三体》刻画了三体人和地球人之间的沟通难题(the problem of communication),《三体》的火爆传播和引发的争议也令人遗憾,又毫不意外地折射出地球人之间的“沟通难题”,这也让我们担心地球“文明”是否会沦为科技发达、沟通野蛮的三体“文明”。
最后,我认为,当下“三体”IP 日益火爆也与“媒介和传播”有着密切的关系。首先,《三体》小说被誉为全球第一华语科幻小说,曾在2015 年获得第73 届雨果奖。这无疑必须感谢《三体》的英文译者刘宇昆,是他高超的跨文化传播能力提升了《三体》的海外影响力;其次,《三体》的跨媒体叙事(包括电影、电视剧、动画片以及衍生品等),以及跨机构共创和跨平台营销也很成功,如《三体》电视剧由中央电视台、腾讯视频、三体宇宙公司、咪咕视讯和灵河文化联合出品,由腾讯视频、咪咕视频和CCTV-8 联合播出。亨利·詹金斯认为,“融合、集体智慧和参与”[6]56是融合文化中三个重要特征。“更宽泛地讲,融合是指:多样化的媒体系统共存,媒体内容横跨这些媒体系统顺畅地传播流动。在这里,融合被理解为一种不同媒体系统之间正在进行的过程或是一系列交汇的发生,它不是一种固定的联系。”[6]409由此看,融合创作(co-creation)和融合营销(co-promotion)都极大地提升了《三体》的知名度。
总结而言,无论是情节设计、冲突设定、叙事逻辑、人物刻画、共创营销还是受众影响,无论是从正面还是从反面,《三体》均证明了媒介与传播在过去、现在和未来都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