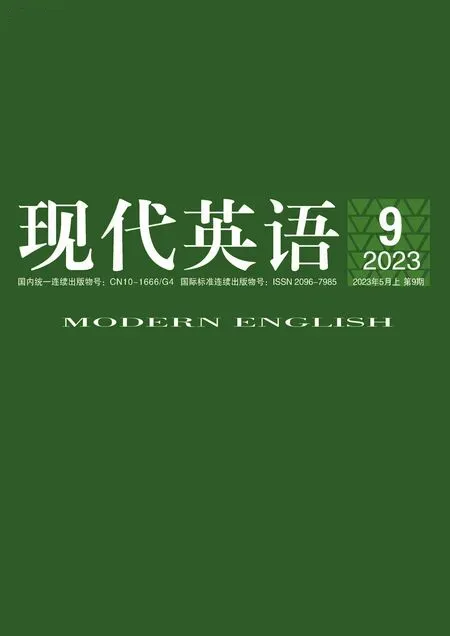《红楼梦》文化负载词英译研究综述
2023-09-10杨萌
杨 萌
(兰州交通大学,甘肃 兰州 730000)
一、 引言
《红楼梦》被誉为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学界对其内容本身及其衍生主题的研究形成了一门独立的学问,即红学。 《红楼梦》翻译学是红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红楼梦》翻译的译学研究将是空洞无力的[1]。 《红楼梦》英译经历了三次大的译介活动,第一次是1830 ~1893 年,共有四个译本,是片段的节译。 第二次是1927 ~1958 年,共有三个译本,全部是《红楼梦》的改编。 第三次是1973 ~1982年,出现了两部完整而各具特色的英译本:一部是霍克斯和闵福德合译的The Story of the Stone,另一部是中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和戴乃迭合译的A Dream of Red Mansions。 其中最受国内外翻译研究者及红学研究者关注的当属《红楼梦》的两个全译本,即杨译本和霍译本。
文化负载词指的是最能体现语言承载文化信息、反映人类社会生活的词汇[3]。 《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文化的百科全书”,书中包含的文化负载词数量众多,含义繁杂,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是翻译的一大难点。 对《红楼梦》英译本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研究始见于2000 年张红艳的《试评红楼梦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一文,此后该话题的研究逐年上涨,在2021 年达到了顶峰。 笔者以“文化负载词翻译” 和“红楼梦” 作为主题词,在中国知网(CNKI)平台上共检索出72 篇论文,其中期刊论文50 篇,学位论文21 篇,会议论文1 篇。 这些文章根据研究内容可分为三类,即《红楼梦》文化负载词英译理论的运用、《红楼梦》文化负载词英译内容研究及《红楼梦》文化负载词翻译策略与方法的研究。
二、 《红楼梦》文化负载词英译理论的运用
《红楼梦》文化负载词英译的本质是跨文化交流。 探究《红楼梦》文化负载词英译实践离不开理论的指导。 在72 篇有关《红楼梦》文化负载词的论文中,从理论视角探析《红楼梦》文化负载词英译的论文有26 篇,涉及16 种翻译理论和理论视角,例如生态翻译学、目的论、关联理论、文化翻译观等。 其中运用得最多的当属目的论和文化翻译观理论。
目的论始于20 世纪70 年代,由德国功能主义翻译学派代表人物汉斯·弗米尔(Hans J. Vermeer)提出,该理论认为翻译是一种基于源语文本的有目的的行为活动,决定翻译过程的最高准则是整个翻译行为的目的。 基于该理论,周阳[11]从社会、语言、思想意识和技术经济四个文化系统对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两个英译本(杨译本和霍译本)中的文化负载词进行了详细的对比分析,认为杨氏夫妇试图保留原文的文化特色,主要运用了异化手法。 霍克斯则是为了使译本通顺,流畅,便于读者接受,多用归化手法。 两个译文都成功地实现了其目的和功能,都是成功的译本。
文化翻译观始于20 世纪80 年代,由英国翻译家苏珊·巴斯奈特提出。 巴斯奈特认为,翻译并不是单纯的语言行为,而是深入文化背景下的内部交流。 佘丹和蒋萧[7]以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观为视角,探讨中医药文化负载词的英译策略,认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灵活运用了直译、意译和变译等翻译手段,在保证源语信息传递的同时,使译文在目的语中达到了与源语对等的文化功能。 吕晓华[5]基于文化翻译观角度,解读了文化负载词的含义,并通过对比不同的译本,探究了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 文章认为在物质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上,杨译本采用的是直译法,而霍译本采用的是意译法;在精神文化负载词的处理上,杨译本采用了意译法,霍译本采用了直译法;在制度习俗文化词的翻译上,杨译本采用的是意译法,霍译本采用的是直译法。两个译者对《红楼梦》的文化负载词翻译作出不同的尝试,都有各自的优势和不足。
三、 《红楼梦》文化负载词英译内容研究
在72 篇相关文章中,探究《红楼梦》文化负载词具体内容英译的论文有15 篇,其中一部分研究从宏观角度出发,将某一类文化负载词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例如社会文化负载词,物质文化负载词等;另一部分研究从微观角度出发,例如花卉文化负载词、动物文化负载词、饮食文化负载词等的研究。 该类研究主要聚焦于文化负载词的语义内涵及文化内涵,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例如:
2012 年,刘建娜[4]从花卉文化的角度出发,以文化图式理论为基础,对《红楼梦》的翻译进行对比研究。 该研究首先对《红楼梦》中花卉的文化内涵进行了探讨,然后探讨了花卉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方法,通过将杨译本和霍译本进行对比,提出了《红楼梦》中花卉文化负载词翻译的五种方法,即直译、转换、意译、直译加注和音译。
2017 年,张岩和陈建生[10]使用语料库工具,采用定量和定性的研究方法,重点从类符/形符比、平均词长和词汇密度等方面来比较和分析杨译本和霍译本物质文化负载词在翻译上的语言特点。 研究发现,霍译本在物质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上做了更多的解释,且其语言更加富于变化;杨译本则倾向于选用文学性更强,较为复杂的词语,许是意在把中华传统文化原汁原味地传递给西方读者。
2021 年,关迎紫[2]以纽马克翻译理论为框架,探究了霍译《红楼梦》中养生饮食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 该研究得出以下几个结论:(1)《红楼梦》中的养生饮食文化负载词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鲜明的民族特征,这对译者来说是巨大的挑战。(2)霍克斯的译文中主要存在语言误译和文化误译两类误译。
四、 《红楼梦》文化负载词翻译策略与方法的研究
翻译策略一般分为归化和异化。 “归化”和“异化”概念首次出现在翻译理论家韦努蒂1995 年出版的《译者的隐身》一书中。 “归化”就是遵从目的语读者的语言表达习惯,尽量用读者所熟知的语言进行翻译;而“异化”就是以源语读者的语言表达习惯为皈依,尽量保留源语文本的语言表达。
2011 年,钱亚旭与纪墨芳[6]采用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红楼梦》中五类物质文化负载词在霍译本中的译文进行了对比分析和定量统计:归化手段占比52.49%,异化占比38.59%。 异化策略之音译法、直译法以及归化策略之解释法、替换法、增译法、减译法和组合法,但是其中主要集中在替换法(38.42%)和直译法(35.68%)上,可谓归化异化,平分秋色。
2013 年,徐晨龙[9]从文化负载词之于翻译的困难出发,论述了文化负载词的定义及特征。 在此基础上,对《红楼梦》中出现的部分包含动物形象的句子进行整理,对其中出现的以动物形象为喻体的文化负载词进行分析,结合杨译本中对这些动物类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方法,总结出了三种翻译动物类文化负载词的方法,即保留动物原有形象直译、根据动物意向内涵意译以及只译出部分动物形象。
2017 年,汪敏飞[8]从翻译适应选择论的角度分析杨译《红楼梦》中汉语文化负载词的英译特点和翻译策略,认为在《红楼梦》的翻译中,杨宪益、戴乃迭夫妇主要采用了以源语文化为中心的直译方法,以较高的整合适应选择度实现了文化负载词汉译英在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的最佳转换。
五、 《红楼梦》文化负载词翻译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一)研究视角狭小
在现有的《红楼梦》文化负载词英译研究中,大致仅有翻译策略与方法研究、翻译理论研究和语义内涵及文化内涵研究三个研究视角,其中翻译理论研究又占据了绝对数量。 因此研究视角不仅狭窄且不平衡。 视角创新不足,将会导致该领域研究停滞不前。
(二)译本研究单一
从所收集的论文可以窥见,现有的研究对象全部集中在《红楼梦》的两个全译本,虽然这两个译本流传最广、影响最深,但在《红楼梦》漫长的译介过程中也涌现出了许多其他优秀且有研究价值的译本,忽略这些译本将使该领域研究显得过于单薄,同时也是研究界的一大损失。
六、 对《红楼梦》文化负载词英译研究的建议
(一)加大研究力度
文化负载词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准确、深刻地在异语中再现其文化内涵是翻译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关键所在,也是帮助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有效手段。 《红楼梦》被誉为“中国古典文化的百科全书”,文化负载词蕴含了其文化精髓,故精深庞杂、数量众多,是翻译时的一大重难点。 因此,研究者应加深对该领域的重视程度,加大研究力度,力求创新,令文化负载词的英译研究更上一层楼。
(二)拓宽研究视角
现有的《红楼梦》文化负载词英译研究视角局限,学者应大胆踏出舒适圈,挖掘更多研究层次、深耕研究内涵、拓宽研究意义,不要将翻译研究局限在翻译理论和语言文字转换上,可以与社会学、传播学、哲学等学科有机结合,交流合作、博采众长,碰撞出更多的火花。
(三)丰富研究译本
学者在研究《红楼梦》文化负载词英译时,固化思维明显,总是选择固定的两个译本作为研究对象。 因此,学者应该试着去挖掘除了两个全译本以外的其他译本的研究价值,以更新颖的研究视角、更深刻的研究力度分析和研究其中的文化负载词英译,并且可以进行译本间文化负载词英译的对比研究,使《红楼梦》英译的研究更加百花齐放。
七、 结语
《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理应以最好的面貌走向世界。 该书中包含的文化负载词精深庞杂、数量众多,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里里外外,是中国珍贵古典文化精髓的集结。 在翻译时要采取合适的翻译策略,以忠实地再现其文化内涵为皈依,以目标语读者的接受度为准绳,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效解决。 学者应大胆突破学科间的壁垒,跨学科、多层次、多角度地进行研究,在原有的杨译本和霍译本研究的基础上,继续挖掘其他译本的研究价值,丰富研究内容,以更好地讲述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