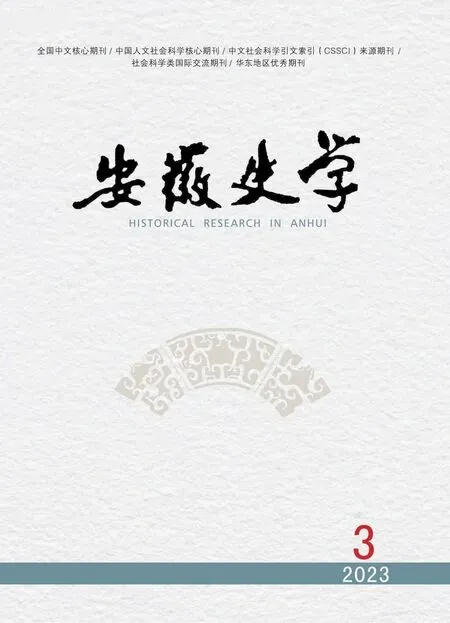战争、政治与传染病防控:战时澳大利亚政府对本土疟疾疫情的应对(1943—1944)
2023-09-05徐友珍曾泳心
徐友珍 曾泳心
(武汉大学 历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疟疾是人类最古老的疾病之一。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定义,疟疾是一种由疟原虫属寄生虫引起的威胁生命的疾病。它通过受感染的雄性按蚊(Anopheles)叮咬传播给人类,初发症状包括发热、头痛和寒战,若治疗不及时很可能发展成严重疾病,甚至导致死亡。(1)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Malaria,July 26,2022,https://www.who.int/zh/news-room/fact-sheets/detail/malaria,2022-09-29.疟疾不仅在平民中广泛传播,更是与人类的战争如影随形。太平洋战争期间西南太平洋战区美澳联军就因疟疾盛行而损失惨重,尤其是在新几内亚等地澳军中爆发的疟疾不仅造成澳军战力严重受损,而且导致疟疾向澳本土蔓延,波及北领地、昆士兰州以及西澳大利亚州等澳北地区。对于这场疟疾造成的影响,时任西南太平洋盟军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A.MacArthur)曾表示,他对击败日军信心满满,但是对能否打败疟疾忧心忡忡。(2)Medical Department,United States Army,Preventive Medicine in World War II:Communicable Diseases-Malaria,Washington,D.C.:Office of The Surgeon General Department of The Army,1963,p.2.而具有政治和医学双重背景的澳大利亚前总理、时任战争咨询委员会成员厄尔·佩吉( Earle Page)爵士也表示:“疟疾对于澳大利亚本土的入侵将和日军的入侵一样危险和影响深远。”(3)“A New Invasion Menace”,June 29,1943,NAA:A2680,4/1944,NAA,Canberra.
迄今为止,国际学界虽然对当时西南太平洋战区盟军中肆虐的疟疾及其应对问题有一定研究,然而对于疟疾疫情波及澳大利亚本土的后续发展则鲜见涉及。中国学术界不论对盟军中还是澳大利亚本土的疟疾疫情及其防控问题均未见论及。(4)相关代表性成果参见:Allan S.Walker,Clinical Problems of War,Sydney:Halstead Press,1952;Mary Ellen Condon-Rall,“Allied Cooperation in Malaria Prevention and Control:The World War II Southwest Pacific Experienc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and Allied Sciences,1991(46);John T.Greenwood,“The Fight against Malaria in the Papua and New Guinea Campaigns”,Army History,2003(59).笔者通过耙梳相关档案文献发现,蔓延至澳大利亚本土的疟疾疫情因为与当时的反法西斯战争和澳大利亚国内政局密切关联而促使联邦政府突破宪法权限,开展了针对平民的疫情监测,并通过推动联邦政府与州的合作,以及军民联动在战时实施了一系列综合性防控措施,一定程度上介入传统主要归属州权的公共卫生领域。此举不仅有效遏制了疟疾在澳大利亚本土的大面积流行,而且对当时澳大利亚国内政治和公共卫生服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以及虐疾病防治均有影响,是澳大利亚历史、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流行病防治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前人更多关注前线军队中的疟疾疫情而对澳大利亚本土疟疾防控问题鲜见涉及,可能正是流行病防治研究中常见的悖论:是时澳军中的疟疾流行造成了重大影响,因而更易受到关注,而疟疾在澳大利亚本土的蔓延因及时有效的防控并未形成大规模流行,因而很容易被视为普通的公共卫生事件而被忽视。然而流行病防控的意义恰恰在于防患于未然之时,从这个意义上讲,澳大利亚本土疟疾疫情能够及时得到控制本身值得研究。
鉴于前述理由,本文尝试主要依托相关一手资料,尤其是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馆藏档案,将澳大利亚政府对本土疟疾疫情的防控置于当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与澳大利亚国内社会政治互动的特定时空框架之下,系统探究相关史实,深入揭示贯穿其中的战争、政治与传染病防控的关系,以期推进相关研究。
一、新几内亚澳军疟疾疫情的爆发及其对澳大利亚本土的威胁
疟疾是人类最古老的疾病之一,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具杀伤力的疾病之一。它不仅在平民间广泛传播,更是与人类的战争如影随形。曾供职于英国皇家陆军医疗队和伦敦皇家陆军医学院的梅尔维尔教授(C.H.Melville)称:“战争中疟疾的历史几乎可以看作战争本身的历史。”(5)Ronald Ross,The Prevention of Malaria,New York:E.P.Dutton &Company,1910,p.577.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线战场交战双方军队中总共报告约2万例疟疾病例。(6)Rebecca M.Seaman,ed.,Epidemics and War:The Impact of Disease on Major Conflicts in History,Santa Barbara:ABC-CLIO,2018,p.247.太平洋战争期间,仅美国海军中就新增11.3万例疟疾病例,损失331万个人工,对美军造成巨大的打击。(7)Christine Beadle,Stephen L.Hoffman,“History of Malaria in the United States Naval Forces at War:World War I Through the Vietnam Conflict”,Clinical Infectious Diseases,1993(16):322.缅甸战役中严重的疟疾疫情曾导致中、美、英医学专家于1943年3月汇聚加尔各答,探讨如何“开辟抗击疟疾的第二战场”,以应对盟军“最危险的敌人——疟疾”。(8)“Allies Open Second Front Against Malaria”,March 3,1943,NAA:A2671,106/1943,NAA,Canberra.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澳大利亚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一员。1939年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后,澳大利亚派出4个步兵师、海军舰队和空军加入英国远征军,听从英军调遣,远赴中东和欧洲等地与德、意法西斯军队作战。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3个月内先后攻占菲律宾大部、香港、马来亚、新加坡、印尼和缅甸等地。英军的惨败使澳大利亚失去了英国传统的海上保护,尤其随着日军攻占与澳大利亚大陆隔海相望的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的部分岛屿之后,日军的潜艇、飞机多次袭击过澳洲大陆,澳大利亚为寻求美军的安全保护,提议罗斯福总统将盟军西南太平洋司令部设在澳大利亚大陆,得到罗斯福总统采纳。由此澳大利亚与盟军西南太平洋司令部密切合作,不仅借以获取安全保障,同时成为盟军在太平洋战场反击日军的前沿阵地和战略后方。(9)参见姜天明:《澳大利亚联邦史略》,辽宁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0、144—147页。
澳军在世界各地同法西斯作战的同时,亦频繁遭遇疟疾侵袭,尤其是在新几内亚作战的澳军罹患疟疾的问题更为突出。历次战争经历表明,疾病是热带地区军队损员的主因。(10)“Review of Disease Experience in New Guinea in R.A.A.F”,December 13,1942,NAA:A5954,473/4,NAA,Canberra.新几内亚与澳大利亚北部隔海相望,属热带气候,沿海地区年均温度和湿度分别为80华氏度(约26.7摄氏度)和85%,南部海岸遍布难以穿越的沼泽,内陆山区被茂密的热带雨林覆盖。这种气候和环境条件适宜按蚊繁殖,增加了疟疾流行的风险。(11)Medical Department,United States Army,Preventive Medicine in World War II:Communicable Diseases-Malaria,pp.515-516.根据1942年12月4日澳大利亚集团军总司令托马斯·布莱梅(Thomas Blamey)上呈澳大利亚总理约翰·柯廷(John Curtin)的报告,米恩尔湾澳军已有三分之一感染疟疾,在布纳澳军疟疾问题同样严重。(12)“T.A.Blamey to J.Crutin”,December 4,1942,NAA:A5954,473/4,NAA,Canberra.
虽然伴随疟疾的流行,人类对疟疾的认识在不断加深(13)1880年,法国军医阿方斯·拉韦朗(Alphonse Laveran)在病患血液中发现导致疟疾的寄生虫。1887年,由于其高传染性,疟疾与肺结核、肺炎和儿童肠道疾病并列为重大传染病。随后在1897—1898年间,英国医学研究人员罗纳德·罗斯(Ronald Ross)发现疟疾由蚊子进行传播。而英国昆虫学家里卡德·克里斯托弗斯(S.R.Christophers)和孟加拉公共卫生局主任查尔斯·本特利(Charles A.Bentley)则进一步确定了按蚊是疟疾传播的主要病媒。参见:“The Bombay Medical Congress”,February 27,1909,NAA:A1,1910/1887,NAA,Canberra; “Malaria In Italy:A Lesson in Practical Hygiene”,March 31,1909,NAA:A1,1910/1887,NAA,Canberra.,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人类应对的手段依然有限。最初的措施仅是警告民众远离按蚊繁殖的低洼湿地,直到19世纪20年代奎宁被成功提取出来用于治疗疟疾,逐渐成为人类防治疟疾的基本手段。然而疟疾防控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对病媒按蚊的控制、个人基本健康的维持以及关键的抑制性药物治疗等等。二战期间,新几内亚澳军最初采取的是通过日服小剂量的奎宁和阿的平以避免疟疾的急性发作,但这通常无法使人体从根本上完全摆脱寄生虫,防止复发,只是将其减少到人体免疫系统可以控制的程度。(14)“Review of Disease Experience in New Guinea in R.A.A.F”,December 13,1942;“Prime Minister’s Department Cablegram”,December 14,1942,NAA:A5954,473/4,NAA,Canberra.随后澳军医疗部门逐步认识到在疟疾防控问题上,除抑制性药物外,还应辅以其他手段,例如维持士兵身体健康、控制按蚊滋生地、消灭帐篷内成蚊,使用防蚊服、蚊帐、驱蚊霜,并将营地的选址与按蚊滋生地保持距离等方法。但此时新几内亚澳军因防控药物和设备的严重短缺而难以有效地解决疟疾防控问题。(15)“Review of Disease Experience in New Guinea in R.A.A.F”,December 13,1942,NAA:A5954,473/4,NAA,Canberra.
新几内亚等地军营中的疟疾流行不仅严重影响军队战力,而且使澳大利亚本土面临威胁。由于疟疾潜伏期一般几周甚至更长时间,大量军事人员从疟疾高发区进入澳大利亚本土,很可能造成疟疾在澳本土大面积传播。事实上,随着军人病患频繁往返于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本土,澳大利亚大陆,尤其是与新几内亚隔海相望的澳北地区疟疾流行风险激增。历史上,疟疾就曾零星地或在澳大利亚北部局部地区,诸如昆士兰州、北领地和西澳大利亚发生过,这些一般是因为人口的临时聚集引发,例如新矿区开采和铁路建设等,病源多来自国外。二战前,澳大利亚唯一已知的疟疾流行区是位于沼泽地带的凯恩斯。虽然在1942年5月,一种良性间日疟便开始流行,波及数百平民,但是本地感染病例开始出现在北领地的凯瑟琳和阿德莱德河地区,以及昆士兰州的汤斯维尔、塞勒海姆和布里斯班地区则是大量来自新几内亚、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军人,以及从西南太平洋地区的难民到来之后。有证据表明,感染源多是军营中感染了疟疾的军人,尤其是正在那里的医院接受疟疾治疗的军人。(16)“Report on Malaria by Sir Earle Page Principal Recommendations”,June 3,1943,NAA:A2680,4/1944,NAA,Canberra.
不过,澳大利亚北部地区的疟疾病问题虽然早有发生,但鲜见引起联邦政府的重视和干预。例如1908—1909年间,鉴于澳大利亚北领地曾出现多例疟疾死亡病例,时任澳大利亚中央卫生委员会主席拉姆齐·史密斯(W.Ramsay Smith)博士提议联邦政府采取预防措施,但联邦政府认为存在疟疾风险的地区范围有限(北纬20度以北),考虑到人烟稀少,且居民主要从事畜牧业,未予采纳。(17)“N.J.Moore to The Prime Minister of the Commonwealth,Melbourne”,September 1,1909,NAA:A1,1910/1887,NAA,Canberra.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澳国内医学工作者将数以百计关于热带疾病和传染病的报告提交至联邦政府案头,但这些报告均未被审议和采纳。(18)Department of State,Proceedings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es on Tropical Medicine and Malaria(Volume Two),Washington,D.C.: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48,p.1474.
二、厄尔·佩吉报告与柯廷政府的立场转变
新几内亚澳军的疟疾疫情引起了柯廷政府和战时主要决策机构战争咨询委员会(19)1939年9月15日,即大战爆发两周后,联合党孟席斯政府宣布成立战争内阁(The War Cabinet),作为澳大利亚战时核心决策机构。在1940年9月的大选中,孟席斯得益于2位无党派人士的支持得以保持政权,这种状况促使其延揽反对党工党领袖柯廷入阁。柯廷拒绝入阁,但是建议组建由政府和反对党成员联合组成的战争委员会。孟席斯采纳柯廷建议,于同年组建了战争咨询委员会(Advisory War Council)。战争咨询委员会由总理主持,除内阁成员外,还包括反对党的领袖和3位成员。1941年10月,柯廷当选总理后,各方同意将战争咨询委员会的决定视为战争内阁的决定,只把一些事务性工作交给内阁处理。这意味着战争咨询委员会在许多方面取代了战争内阁。因而战争咨询委员会在战时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参见:John Curtin Prime Ministerial Library,The War Cabinet and Advisory War Council,https://john.curtin.edu.au/behindthescenes/cabinet/index.html,2022-10-05.的重视。1942年12月8日,战争咨询委员会专门讨论了澳军总司令布莱梅呈报的澳军疟疾问题,尤其军队病损与战损之比为6:4的数据引起澳军总参谋长的担忧。而前总理、时任战争咨询委员会成员佩吉也表示在东非战役中,死于疾病的部队是战斗的两倍,新几内亚战场的情况与之类似。更为严重的是,疟疾患者在治愈后如果被送回热带地区可能再次发作,因而由热带疾病导致的损伤将极大地削弱用于防御澳大利亚北部的有生力量。(20)“Advisory War Council Minute(1105)”,December 8,1942,NAA:A5954,473/4,NAA,Canberra.对于该紧急情况,澳大利亚总理、战争咨询委员会主席柯廷要求澳军提供调研报告,说明疟疾发病率、人数以及与战斗伤亡的关系。(21)“Advisory War Council Minute(1104)”,December 8,1942,NAA:A5954,473/4,NAA,Canberra.
来自军方的报告显示新几内亚澳军疟疾问题的严重性。根据澳军上呈柯廷的报告,1942年1月至10月,包括米恩尔湾在内的新几内亚澳军战斗伤亡只占总伤亡人数的4.4%,而热带疾病占入院人数的42%。截至11月底,疟疾病例总数不少于7841例。1942年11月米恩尔湾的数据显示发病率为千分之1244人,或者说疟疾所造成的人力损失超过100%。此时澳大利亚和美国的三个师正与小股日军作战,日军大量增援部队抵达帝汶岛。为了确保盟军补给线和澳大利亚本土的安全,澳军必须集中兵力将日军逼退,但疟疾对于其战力的消耗使澳军的胜算降低。(22)“Prime Minister’s Department Cablegram”,December 14,1942,NAA:A5954,473/4,NAA,Canberra.
紧迫的战争需要促使柯廷政府高度重视澳军的疟疾防控问题。鉴于当时澳军和美军奉行不同的政策,为获取适用于澳军独立的医疗建议,以有助于疟疾病患的康复,特别是减少康复周期和在温带、热带地区的治疗问题,1943年4月13日,战争咨询委员会委托佩吉对此进行调研,并给政府提供报告和对策建议。(23)“Minutes of Advisory War Council Meeting,April 13,1953”,April 13,1943,NAA:A5954,814/2,NAA,Canberra.柯廷政府对佩吉的调查给予大力支持,不仅在其前期准备中委派高级医官作为佩吉助手,而且亲自与麦克阿瑟沟通,请求其为佩吉的调查提供支持,后者安排美国远东陆军参谋人员协助佩吉。(24)“John Curtin to General Macarthur”,April 17,1943;“Douglas Macarthur to John Curtin”,April 20,1943,NAA:A5954,473/4,NAA,Canberra.4月29日,佩吉抵达布里斯班开启调查,并于5月13日完成。(25)“Advisory War Council Minute”,May 13,1943,NAA:A5954,473/4,NAA,Canberra.
此时佩吉能够得到柯廷政府的委任和大力支持,与其专业背景和政治履历有关。佩吉是澳大利亚政坛的风云人物。从政之前,他已在新南威尔士建立了一个大型医疗与外科医院。从1920—1939年一直是澳大利亚乡村党(现国家党)领袖,曾代理两届政府总理,并在1939年短暂担任过总理,此后又担任过诸多重要职务。1942年出使英国期间,他不仅以澳大利亚代表身份参加英国战时内阁和太平洋战争委员会,而且获得英国皇家外科医学院授予的荣誉院士头衔。(26)Br Med J,“Obituary:Sir Earle Page,P.C.”,British Medical Journal,1961(2):1787.尽管1942年8月27日柯廷在对外解释增补佩吉为战争咨询委员会成员的理由时称,仅是希望佩吉在英国的经历能够有助于政府处理战争问题(27)“Statement by The Prime Minister”,August 27,1942,NAA:A2684,1227,NAA,Canberra.,但实际上此举更多牵涉澳大利亚的国内政局。由于以罗伯特·孟席斯(Robert Menzies)为首的联合党激烈抨击工党柯廷政府的战争政策,并经常无故缺席战争咨询委员会会议,甚至呼吁提前举行大选,给工党柯廷政府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增补佩吉为战争咨询委员会成员有助于获取他背后的乡村党势力在议会和各项战争事务上对政府的支持。柯廷此举也被外界视为“几个月来联邦政治中最重要的举措之一”。(28)“Storm Over Page’s War Cabinet Post”,August 28,1942;“National Govt.Hopes”,August 29,1942,NAA:A2684,1227,NAA,Canberra.而作为享有盛名的外科医生,佩吉对政治的理解也有异于传统政客之处。他曾表示,外科训练在政治领域是无价之宝,因为在那里非常需要却很少做的事情就是在医治之前先做诊断。(29)Br Med J,“Obituary:Sir Earle Page,P.C.”,British Medical Journal,1961(2):1787.
佩吉在对澳军的疫情调查结束后便明确主张加强对澳大利亚本土疟疾流行风险的防控。在他看来,此时新几内亚澳军在军队医疗部门的努力下疟疾致死率已大为降低,但澳大利亚本土疟疾传播的风险却有扩大趋势,尤其严重的是澳北地区。例如,昆士兰州在1942年之前的17年里仅通报106例疟疾病例,但在1941—1942年便有182例,到1943年6月已达699例。(30)“Memorandum for The Secretary,Department of Defence”,July 22,1943,NAA:A2680,4/1944,NAA,Canberra.有鉴于此,佩吉主张应保护澳大利亚本土平民免受疟疾的侵害,并认为“疟疾对于澳大利亚的入侵就像日军的入侵一样危险和影响深远”。(31)“A New Invasion Menace”,June 29,1943,NAA:A2680,4/1944,NAA,Canberra.为此,佩吉基于实地调研,为澳大利亚本土疫情防控提出了具体方案,并于1943年6月初呈递柯廷政府。其核心举措包括如下方面:
第一,隔离病源,严格管控往返于新几内亚与澳大利亚的军事人员。新几内亚军人病患,除非疟疾反复发作,以致无法继续服役才获准转移至澳大利亚境内,包括患有严重贫血或恶性疟疾,康复周期长的人员;虽经抑制性治疗但仍复发发烧,无法服役的人员;未定期服用阿的平的人员;并发黑尿热的人员。(32)“Report on Malaria by Sir Earle Page”,June 3,1943,NAA:A2680,4/1944,NAA,Canberra.
第二,消除病媒,加强对平民的疟疾知识普及以及军民对接。澳大利亚,尤其是北部地区存在多种类型的按蚊是传播疟疾的主要病媒。为消除病媒,需要在汤斯维尔、凯恩斯等按蚊繁殖沼泽地实施排水计划和其他根治计划。各级民政部门需要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并与军事防疫行动密切合作;民政部门负责对受感染区域平民进行预防疟疾的宣传和教育,尤其是针对在校儿童。(33)“Premiers’ Conference,1943”,July 12,NAA:A2680,4/1944,NAA,Canberra.
第三,实施标准化治疗。疟疾患者应服用奎宁10格令(gr.X),每日三次,连续3日;服用阿的平0.1克,每日三次,连服5日;服用扑疟喹啉0.01克,每日三次,与每日15格令(grs.XV)的奎宁合用,连续5日;最后是在严格监督下服用维持剂量的阿的平0.1克,每周6日,共持续6周。(34)“Report on Malaria by Sir Earle Page”,June 3,1943,NAA:A2680,4/1944,NAA,Canberra.
第四,保障抗疟药物及相关物资供应。考虑到占世界奎宁产量90%的爪哇在1942年3月被日军占领,建议改从英美进口。战前日本是世界灭蚊喷剂主要成分除虫菊的来源地之一,战时状态下亦改从另一主要产区肯尼亚进口。由于澳大利亚标准蚊帐供应紧张,当时使用的大部分仍是租赁的劣质蚊帐,而主产地英国又将原有蚊帐产能转向生产军需用品及战争工业,作为替代,建议大力推动国内制造商扩大对标准蚊帐的生产。(35)“Report on Malaria by Sir Earle Page”,June 3,1943,NAA:A2680,4/1944,NAA,Canberra.
第五,出台相关国家安全条例,赋予军方、联邦政府和州医疗当局监测和治疗在联邦内潜在或已出现疟疾问题地区平民的权力。这也便于卫生当局监测所有退役但被怀疑患有潜伏性或活动性疟疾的士兵。(36)“Premiers’ Conference”,July 6,1943,NAA:A2680,4/1944,NAA,Canberra.
佩吉的建议引发战争咨询委员会的讨论。受制于联邦宪法和反对党的压力,柯廷一开始对针对平民的疫病防控犹豫不决,表示联邦政府缺乏执行佩吉建议案的宪法权力。(37)“Warns on Malaria”,June 28,1943,NAA:A2680,4/1944,NAA,Canberra.这主要是因为,在澳大利亚联邦制度创设之初,各州代表倾向于借鉴美国模式,将联邦政府主要职权限定于国防、外交和外贸等领域,公共卫生管理主要由各州全权负责。(38)郑寅达、费佩君:《澳大利亚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64页。受制于此,除了联邦直辖的首都领地以及北领地外(39)首都领地及北领地分别于1911—1988年、1911—1947年间由联邦政府直辖。参见:Jeremy Moon and Campbell Sharman,eds.,Australian Politics and Government,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209;p.224.,联邦政府介入公共卫生问题将不可避免地引出联邦与州的权限问题。除此之外,柯廷也忌惮反对党的压力。以孟席斯为首的反对党频繁攻击柯廷政府利用战时权力推行有利于工党的政策,严厉批评工党图谋将各州权力向联邦政府转移。(40)“National Govt.Hopes”,August 29,1942,NAA:A2684,1227,NAA,Canberra.
对于柯廷的犹豫不决,佩吉首先据理力争。他向柯廷表示,一旦疟疾在澳大利亚扎根,每年用于防治的费用将与战前的国防开支比肩。若不及时采取行动,战后数月内将有数以万计的军队需要继续维持军事管控状态,以确保平民的抗疟疾治疗。相较而言,现阶段采取防控措施的代价要小得多。况且平民罹患疟疾将严重削弱战力,对平民的疟疾防控关乎国防,联邦政府有权处置,“真正的危险是缺乏时间而非权力”。(41)“Warns on Malaria”,June 28,1943,NAA:A2680,4/1944,NAA,Canberra.佩吉的主张得到军方的呼应。陆军部长弗兰克·福德(Frank Forde)表示陆军医学专家认同佩吉对疟疾危险性的认识,但认为防控重点应放在按蚊大量繁殖的北部地区,因为南部不存在疟疾传播的风险。(42)“Protecting Civilians from Malaria”,June 30,1943,NAA:A5954,473/4,NAA,Canberra.
与此同时,佩吉也诉诸舆论。佩吉将其关于加强澳北部平民疟疾防控的言论,甚至其与柯廷交谈的细节刊登在《悉尼先驱晨报》等澳大利亚主流报纸上。《悉尼先驱晨报》随之频繁强调应防止澳大利亚北部地区平民感染疟疾,必须消灭按蚊,并对携带寄生虫平民进行治疗直至痊愈。(43)“Malaria Danger in Australia”,June 30,1943,NAA:A2680,4/1944,NAA,Canberra.当时南澳大利亚州最大的地区性报纸《边境观察报》及时刊登了佩吉关于疟疾入侵的警告。(44)“Danger from Malaria”,The Border Watch,June 29,1943.墨尔本《阿格斯报》则刊载了佩吉对柯廷关于在疟疾防控上联邦政府缺乏宪法权力等观点的回应。(45)“Action to Combat Malaria Urged”,The Argus,June 28,1943.澳北部乃至位于新几内亚的众多报纸也广泛报道了佩吉关于疟疾对澳大利亚本土危害的言论。(46)“Malaria Menace”,Queensland Times,June 28,1943; “Malaria Menace,Sir Earle Page’s Warning”,Warwick Daily News,June 28,1943;“Fears of Malaria”,Townsville Daily Bulletin,June 28,1943;“Dr’s Malaria Warning”,Guinea Gold,June 29,1943.《每日电讯报》则更为尖锐地指出,澳大利亚北部已出现大量疟疾病例,但联邦政府的应对难以让人满意,甚至暗讽政治家现在还有更为重要的事情要考虑,就是为大选造势。(47)“Warns on Malaria”,June 28,1943; “A New Invasion Menace”,June 29,1943,NAA:A2680,4/1944,NAA,Canberra.
面对佩吉的力争及国内舆情反应,柯廷开始慎重考虑本土疟疾防控问题。作为对1943年6月佩吉建议案的回应,7月2日,柯廷决定在有总理和澳大利亚六个州的州长参加的总理会议上讨论如何保护澳北部平民免受疟疾侵害的问题。(48)“Memorandum for The Secretary,Department of Defence”,July 2,1943,NAA:A2680,4/1944,NAA,Canberra.当然,促使柯廷迈出重要一步的因素除了来自政府内外的压力,也与柯廷政府的内在驱动有关。其内在考量主要有二:
其一,满足迫在眉睫的军事和民生需求是关键推动力。赢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保障澳大利亚本土安全是工党安身立命之本。1940年6月柯廷主持召开的工党特别会议宣布摒弃孤立主义立场,“致力于赢得战争”,不仅会继续支持向海外派兵,而且将增强本土防卫力量。工党鲜明的反法西斯立场助力柯廷赢得了大选。(49)John Edwares,John Curtin’s War,Sydney:Penguin Random House Australia,2017,pp.350-351.而彼时的现实是,新几内亚作为澳大利亚的屏障,一旦失守将使本土直接暴露在日军威胁之下。而新几内亚澳军对日作战有赖于澳大利亚本土的后勤补给以及可供休整、集训的基地。由于交通上的便利,澳北地区建有众多重要的军事基地、港口和拥有大量为之服务的平民。(50)“John Curtin to General MacArthur”,April 17,1943,NAA:A5954,473/4,NAA,Canberra.倘若该地区遭受疟疾的侵袭,不仅这些军事基地和港口处境危险,而且在丧失为战争服务的劳动力的同时,还需抽调大量资源用于平民的医疗救助,增加本就短缺的抗疟药物需求,从而影响新几内亚澳军的疟疾防控和治疗,进而增加军事失败的几率。况且,此时澳大利亚社会舆论批评柯廷政府防疫不力,甚至宣称是否解决疟疾关乎即将到来的大选。(51)“Should We Have Dodged Malaria”,Circular Head Chronicle,June 30,1943.因而无论是战争失败或是无视民意都可能使工党失去大选。故在1943年7月竞选演讲中,柯廷就提出“赢得战争与和平”和“为平民服务与满足平民需求”的政策目标。(52)“Federal Election,Party Policy”,Bowen Independent,July 30,1943.
其二,利用战争扩张联邦权力,并在战后巩固联邦政府的执政地位。虽然在起草宪法时各州代表尽可能保留各州权力,但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联邦政府就不断尝试扩张权力。(53)Alan Fenna,“The Centralization of Australian Federalism(1901-2010):Measurement and Interpretation”,The Journal of Federalism,2018(49):36.柯廷政府对于在公共卫生领域掌握更大的话语权有着强烈意愿。(54)“Australia’s Health Conference in Canberra,Federal Government’s Interest”,The West Australian,May 28,1941.1942年,总理会议在讨论增加联邦政府权力提案时,已宣布公共卫生问题由联邦政府和各州共同处理。柯廷政府也计划在战后继续扩大联邦权力,而公共卫生领域是重要目标之一。(55)“Curtin’s 14 Points to Implement War Aims”,The Workers Star, December 12,1943.为此,柯廷通过报纸正面回击了孟席斯对联邦政府集中州权的批评。
三、联邦政府有关澳大利亚本土疟疾防控措施的出台与实施
柯廷政府基本采纳了前述佩吉提议的疟疾防控方案,并就此在总理会议上与各州州长讨论。柯廷在1943年7月14—15日的总理会议上向各州州长提出了旨在保障澳大利亚本土平民免受疟疾侵害的问题,强调“如果疟疾在全国范围内流行,人口质量和数量都将受到影响”,希望各州能与联邦政府合作。而各州州长也意识到疟疾对平民和军人的严重威胁,同意与联邦政府合作对抗疟疾,疫情较重的昆士兰州州长弗兰克·库珀(Frank A.Cooper)甚至表示,将要求地方当局承担治疗疟疾病例的费用,因为这样可倒逼其为节省巨额治疗费用而重视防控措施。同时,州政府也将作出重大贡献。(56)“Memorandum for the Secretary,Department of Defence”,July 22,1943,NAA:A2680,4/1944,NAA,Canberra.此后战争咨询委员会同意实施这些措施,称赞佩吉提交了一份“全面且有价值”的报告。麦克阿瑟也表示完全同意佩吉所建议的措施。(57)“Douglas MacArthur to John Curtin”,July 27,1943; “Secretary,A Dvisory War Council to Earle Page”,October 20,1943,NAA:A2680,4/1944,NAA,Canberra.
然而联邦政府内部却在国家安全条例的赋权对象上出现分歧。卫生部反对将权力留给州政府,也不赞同军方、联邦政府和州医疗部门联合,而主张赋权军队医疗部门独立处理,认为这样可以避免可能产生的行政混乱,而且相比之下,陆军部是唯一具备足够知识、经验和人员的部门,可快速有效地完成防控任务。(58)“Minister for Health to J.Curtin”,July 12,1943;“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Department of Health Memorandum”,July 6,1943,NAA:A2680,4/1944,NAA,Canberra.但柯廷却反对赋权军队医疗部门,坚持由州政府负责。其所持理由,一是战争内阁已就平民和军人权利做了规定,即未经战争咨询委员会授权,不得通过命令或条例影响平民权利和将特权授予军事人员。(59)“Note for Prime Minister”,July 15,1943,NAA:A2680,4/1944,NAA,Canberra.二是针对平民的疟疾防控不仅是战时问题,也是战后问题,仅仅依靠行使战时权力无法解决。由于国家安全条例涉及对平民的调查、隔离和治疗等强制性措施,联邦政府虽可动用战时权力予以执行,但考虑到疟疾问题在战后仍将继续存在,而平民健康问题本属各州管辖范围,由各州直接负责顺理成章。最终,柯廷政府决定在《1939—1943年国家安全法》(60)1939年二战爆发时澳大利亚联邦议会通过的《1939年国家安全法》赋予联邦政府“保障公共安全”“保卫联邦”和“顺利进行战争”的权力。此后该案再次进行修正,联邦政府的权力进一步扩大。参见:R Else Mitchell,“Transitional and Post-War Powers in the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1947”,The Canadian Bar Review,1947(25):858.框架下制订针对疟疾防控的国家安全条例,并赋权各州政府。(61)“Memorandum for the Secretary,Department of Defence”,July 22,1943,NAA:A2680,4/1944,NAA,Canberra.
然而国家安全条例的制订并非一帆风顺。7月15日,柯廷要求卫生部和陆军部合作制订赋权州政府的国家安全条例。(62)“Mr.Mclaughlin to the Prime Minister”,July 28,1943,NAA:A2680,4/1944,NAA,Canberra.但陆军部长于8月4日向柯廷呈递的国家安全条例草案却将所有相关权力赋予陆军医疗部门。在柯廷坚持下,卫生部重拟条例并于10月正式公布,内容包括:联邦卫生部长可发布命令,宣布对受疟疾影响地区采取特别防控措施;该地区卫生官员有权要求居民接受医学检查、治疗以及临床和细菌学检查;未满16周岁人员监护人在收到上述条款规定的书面通知后,应确保未成年人接受检查或治疗;凡不遵守上述条款通知者,即属犯罪。同时,在医院或其他场所接受疟疾治疗的人员,不得在未获得医学许可下离开;接受检查或治疗的人员不需承担任何费用,包括住宿费用;不得针对联邦、州卫生官员依例进行医疗检查、治疗移送或拘留在医院及其他场所提起诉讼,但在州长认定无故被移送或拘留者将获得相应赔偿。(63)“National Security(Malaria) Regulations”,August 1943,NAA:A2680,4/1944,NAA,Canberra.
在相关防疫方案的贯彻执行方面,联邦政府、州政府、地方当局进行了最大程度的合作,从而形成了区域性综合防控,具体措施体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多措并举,消除病媒。其一是昆士兰州政府启动的灭蚊工程补贴计划,得到多数地方当局的支持,为此耗资20万英镑。(64)“Checking Malaria,Government Plans”,Daily Mercury,November 1,1945.二是实施大规模排涝计划。由于凯恩斯、汤斯维尔等地沼泽排涝需要全盘规划,立足长远,不仅牵涉联邦与州,而且涉及跨区域、跨部门合作。经过多方协商,1943年9月,昆士兰州政府、联邦军事当局和联合工务委员会在资金、人力以及工程等方面的方案达成一致,开始整治凯恩斯、汤斯维尔的沼泽地。(65)“E.M.Hanlon to A.T.Callaghan”,October 30,1945;“Health Plams Stem Malaria”,April 26,1944,NAA:A2680,4/1944,NAA,Canberra;“Success of Drainage Scheme”,Cairns Post,October 26,1945.三是普及相关防疫知识,为此,联邦卫生部出版了《澳大利亚与新几内亚疾病的中间宿主——蚊子》和《荷属东印度疟疾的中间宿主》等公共出版物。这些册子均由悉尼公共卫生和热带医学学院的昆虫学专家泰勒(F.H.Taylor)主编,其对澳大利亚按蚊分布和习性有较为深入的研究。(66)“Malaria in the Civil Population,February 1944”,February 14,1944,NAA:A2680,4/1944,NAA,Canberra.
第二,灵活适用国家安全条例。1943年10月国家安全条例公布后,除昆士兰及西澳大利亚州表示认同外,其余各州均以本州不存在按蚊为由拒绝立即宣布其为“疟疾区”。即便某些州此后并未为了实施国家安全条例而宣布其为“疟疾区”,但在面对突发状况时,也能及时援引条例内容处理疫情。譬如1944年3月,悉尼两个社区出现疟疾病例,悉尼卫生官员立即下令对这两个社区潜在病例进行全面排查,同时启动了对病媒来源的调查,从而避免了悉尼出现大面积感染的情况。(67)“Contract Malaria in Sydney”,March 10,1944;“Malaria Risk Low in Sydney”,March 11,1944,NAA:A2680,4/1944,NAA,Canberra.4月,凯恩斯要求所有平民接受血液测试,以发现疟疾携带者,呈阳性者将得到免费治疗。(68)“Anti-Malaria Measures”,The Northern Miner,April 4,1944.
第三,增强抗疟物资和药品供给。澳大利亚供应—运输部与医疗器械控制委员会(MECC)共同发布命令,将战时配给平民的小部分奎宁转成疟疾防治专供。澳大利亚本土药品零售和批发商也将原本供应军队的少量奎宁以及扑疟喹啉转向供应平民。通过与英、美进一步交涉,1943年底澳大利亚阿的平的供应得到极大改善,陆军部随即拨出10万片用于平民防治。(69)②“John Beasley to J.Curtin”,August 25,1943,NAA:A2680,4/1944,NAA,Canberra.经过与美国等盟友的多番交涉,澳大利亚将除虫菊的供应由1943年4月的159吨提升至12月的234吨。而供应—运输部还扩大国内标准蚊帐制造商名单,在1943年下半年将原本每周2000—3000顶的产量增至4000—5000顶。(70)“John Beasley to J.Curtin”,August 25,1943,NAA:A2680,4/1944,NAA,Canberra.
第四,对疟疾患者严格进行治疗。联邦卫生部对从新几内亚疫区返回澳大利亚本土的部队采取最佳治疗方法并维持抑制性药物的剂量。而对于那些刚退伍和季节性休假返回澳大利亚本土,并可能患有潜伏性疟疾的军人进行密切追踪,为应对因此带来的突发状况,联邦卫生部向为平民服务的医师发送权威的治疗方案,以及将相应的治疗药物分发至全国各地的无障碍中心。(71)“Malaria in the Civil Population”,February,1944,NAA:A2680,4/1944,NAA,Canberra.
第五,军民合作研发抗疟新药。1943年下半年,由澳空军医学部主任费尔利(Neil Hamilton Fairley)牵头,依托凯恩斯综合医院医务人员成立了一个医学研究所,与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MRC)和美国相关医学研究机构合作测试抗疟新药,其中氯胍(Paludrine)的测试至关重要。攻关阶段测试结果显示65名恶性疟疾患者,64名被治愈。对此,氯胍的发现者英国科学家戴维(D.G.Davey)称赞道:“我们在6个月内就学到了在普通方法下可能需要数年才能学到的东西。”此时氯胍的效果优于所有已知抗疟药物,对于恶性间日疟疾具有真正的预防作用,并能够在治疗中实现根治。(72)“Australians Lead Malaria Fight”,The Daily News,October 22,1945;“World’s Wonder Anti-Malaria Drug”,Morning Bulletin, February 20,1946.
由于上述综合防控措施的实施,疟疾疫情防控取得重大进展。1944年2月,联邦卫生部对外宣布,由于卫生部门和军事当局采取有效防控措施,疟疾在澳大利亚本土大规模传播的风险已大大降低。(73)“Malaria in the Civil Population”,February,1944,NAA:A2680,4/1944,NAA,Canberra.随着疟疾疫情形势的好转,相应的防控措施逐渐被解除。首先,澳北部主要州逐步停止为平民提供疟疾相关的检测服务。1944年5月27日,昆士兰州凯恩斯卫生部门发布公告,通知部分区域居民于29日晚前往预定站点接受最后一次检查。(74)“Civilian Malaria Survey”,Cairns Post,May 27,1944.其次,各部门基本停止了对本土疟疾防控的介入。1945年10月,为澳北部沼泽治理计划服务的军人陆续撤离。(75)“E.M.Hanlon to A.T.Callaghan”,October 30,1945,NAA:A2680,4/1944,NAA,Canberra.虽然在澳大利亚议会通过的《1946年国防(过渡条款)法》中,《国家安全法(1939—1943)》的部分条例得以延续,但关于疟疾防控的国家安全条例则未被列入新法案,且在1946年12月31前自动失效。(76)Defence(Transitional Provisions) Act 1946,December 14,1946,http://classic.austlii.edu.au/au/legis/cth/num_act/dpa1946771946369/,2022-11-03;R Else Mitchell,“Transitional and Post-War Powers in the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1947”,The Canadian Bar Review,1947(25):859-868.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随着疫情形势好转和战时状态的结束,联邦政府推动的防控措施大多不得不终止,但疟疾防控意识和部分举措仍得以延续。譬如澳大利亚各州政府仍继续采取对病媒进行调查等防治措施,社会也存在“为了国家未来的健康和效率,疟疾防控既不能忽视也不能拖延”的呼声。(77)“Malaria May Be Danger”,The Farmer and Settler,October 20,1944.各级政府应对突发疫情的经验丰富了,能力亦得到提升。有关环境改造、疾病诊治和药物研发之类的措施依然继续进行。1945年底,虽然参与澳北部沼泽综合治理工程的军人陆续撤离,但各州政府仍集中财力继续对沼泽地实施永久性整治。(78)“E.M.Hanlon to A.T.Callaghan”,October 30,1945,NAA:A2680,4/1944,NAA,Canberra.1953年,由昆士兰医学研究所领衔组建了一支疟疾流调队,吸纳人才入营接受培训,并重新研究战时澳北部有效实施疟疾防控的问题。(79)“Malaria Control Company”,Daily Mercury,October 17,1953.氯胍等新抗疟药物则在澳大利亚被广泛应用于疟疾的防治。(80)“Paludrine and Malaria”,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July 12,1947.
结 论
战时澳大利亚政府对本土疟疾疫情的防控主要缘于在新几内亚对日作战的澳军中爆发的疟疾疫情。此次疫情不仅造成澳军大量非战斗损员,而且导致疫情向澳本土蔓延。工党柯廷政府赋权具有政治和医学双重背景的前总理、时任战争咨询委员会成员佩吉前往调研并提出对策。佩吉在实地调研结束后提议加强对澳大利亚本土疟疾流行风险防控,尤其是与新几内亚战局休戚相关的澳北地区。佩吉相较于其他热带医学专家对政治运作的熟谙使其建议更易引起柯廷政府的重视,澳大利亚本土疟疾防控问题因而得以被提上联邦政府决策高层的议事日程。虽然柯廷政府囿于宪法权限和忌惮反对党的压力,一度对联邦政府介入可能触及平民权利和传统主要归属州权的公共卫生领域持谨慎态度。但在佩吉诉诸民意,得到军方支持,并引发澳国内舆论高度关切的情势下,出于军事需要和民生考虑,尤其是巩固工党执政地位和扩张联邦权力的内在驱动,柯廷政府转向在联邦宪法的基本框架下,积极推动联邦与各州协同行动,同时促进军民联动,在澳大利亚本土,其实主要是疫情风险最大的北部地区实施综合性防控。其措施主要包括隔离病源、消除病媒、实施标准化治疗、保障抗疟药品和物资供应,尤其是军民合作研发抗疟新药,以及制订实施针对疟疾防控的国家安全条例等等。到1944年初,澳大利亚本土疟疾疫情得到有效控制。随着疫情形势的好转和战时状态的结束,联邦政府推动的诸多防控措施逐步终止,但由此开启的流行病防治理念和实践仍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延续。
整体而言,战时澳大利亚政府对本土疟疾防控的重视程度、涉及范围和政策力度,以及手段的多样性皆具开拓性。这些努力不仅在战时保障了澳大利亚本土民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使社会秩序平稳运行,而且由于澳大利亚本土疟疾防控的实施和推进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世界疟疾防治,以及澳大利亚国内联邦制度调整和政局变动的总体进程之中进行的,其影响超出一般的公共卫生事件本身,主要体现在:
首先,它有助于战时工党执政地位的巩固和联邦权力的扩张。巩固执政地位和赢得大选是促使柯廷打破惯例,决定于1943年7月中旬召开总理会议重点讨论平民疟疾防控问题的重要影响因素。因为按照惯例,总理会议应与贷款委员会(Loan Council)会议同期举行,但后者因大选而推迟。柯廷此举虽然也曾遭致政敌的攻击。如乡村党副领袖约翰·麦克尤恩(John McEwen)就公开批评柯廷在大选前单独召开总理会议是错误的,而柯廷则回击麦克尤恩“与现实脱节,一心想着赢得选票”。(81)“Malaria Warning”,The Telegraph,July 8,1943;“Protecting Civilians from Malaria”,Border Morning Mail,July 9,1943.乡村党党魁阿瑟·法登(Arthur Fadden)也在竞选演讲中声明,将比柯廷政府更为妥善地处理新几内亚澳军疟疾问题。(82)Australia Federal,Election Speeches,July 22,1943,https://electionspeeches.moadoph.gov.au/speeches/1943-arthur-fadden,2022-12-13.但总理会议及时达成实施防控措施的决定向外界释放出积极的信号,有助于缓解舆论压力,助益大选。8月21日,柯廷工党政府在大选中以压倒性优势击败由法登领导的反对党联盟。战时联邦政府利用战时状态和民意,适时介入公共卫生领域,不仅是战时联邦权力扩张的重要表现,而且对战后政府在公共卫生领域发挥影响力提供了先例和经验。
其次,澳大利亚政府对本土疟疾流行风险的有效防控也有助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其意义体现在多个方面,诸如降低了澳军在后方集训期间感染疟疾的风险;节省下来的民用保供药品和物资需求还能补给新几内亚及其他地区,以满足军需军用;为身患疟疾军事人员返回无感染风险基地治疗提供便利,避免重复感染和出现黑尿热等较为致命的并发症。(83)“Strategical Considerations in Relation to Malaria”,June 3,1943,NAA:MP729/6,42/401/420,NAA,Canberra.逐步消除疟疾风险的澳北部地区则成为盟军休整和蓄力的安全大后方。根据美军军医诺曼·柯克(Norman Kirk)的说法:“在西南太平洋地区,疟疾是我们最大的问题,大约14000名军队伤员被空运至澳大利亚和一些较大岛屿的基地医院接受治疗。”(84)“Battle Casualties Less than Deaths Due to Illiness”,Visayan Shinbun,September 9,1943.而日军对疟疾的应对则相形见绌。一方面,日军因在童年时并未感染过疟疾,缺乏免疫力。而在西太平洋地区,除赤道以北某些岛屿,如关岛、特鲁克岛、威克岛和瑙鲁,以及加罗林和马绍尔群岛外,日本占领的地区几乎都是疟疾区,其中许多是高风险疟疾区,因此日军疟疾伤亡比例也相当高。(85)“Earle Page to J.Curtin”,June 3,1943,NAA:A2671,106/1943,NAA,Canberra.另一方面,战争初期日军指挥官轻视疟疾的危害性,感染疟疾的士兵依然被留在医疗资源匮乏的前线,而非疏散至野战医院,不仅导致疟疾病例激增,军队战斗力下降,而且在撤退时因运载车辆有限,重症患者甚至需拄拐步行,后果或是自杀或是在美澳盟军轰炸下死亡。(86)Steven Bullard,“‘The Great Enemy of Humanity’:Malaria and the Japanese Medical Corp in Papua,1942-1943”,The Journal of Pacific History,2004(39):217-218.
再次,它为世界疟疾防治做出了一定的贡献。第二次世界大战波及世界各地,诸多重大军事行动都在疟疾高发地区展开。由于人员的高度密集和全球范围内流动、居住环境和医疗卫生条件的恶劣、战争带来的伤病,以及营养及医疗物质的短缺等等诸多因素,疟疾病流行成为战时和战后诸多国家面临的公共卫生难题。而澳大利亚在应对疟疾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不仅能够助益自身战后公共卫生事业,而且有助于世界疟疾病防治的进步。根据澳军医疗服务总局局长罗伊·伯斯顿(Roy Burston)说法,英国、美国均采用了澳大利亚的疟疾防治技术,并承认凯恩斯的疟疾研究所的研究对太平洋战争有着突出的贡献,甚至认为,在热带医学领域澳大利亚处于世界领先地位。(87)“Australia Leading World in Tropical Medicine”,News,July 12,19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