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曲水诗序”的创作及艺术特色
2023-09-01盛箐
盛 箐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上巳节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的民俗节日,曲水流觞是上巳节十分流行的文化活动。士族文人常于上巳节相聚宴饮,于曲水流觞、祓除不祥的同时,相继赋诗以助雅兴。这不仅留下了许多诗歌作品,还随之诞生了一批以“曲水”为题的诗序作品。中国古代文人有意识地为自己的诗歌或诗集作序,大约是从晋代兴起的。存于西晋、东晋与南北朝时期的八篇“曲水诗序”是魏晋南北朝诗序发展的典型案例。这些诗序除了拥有共同的上巳节主题之外,还鲜明地体现出了各自所处时期文体发展、文学语言、思想潮流的大致面貌,非常具有研究的价值。

一、“曲水流觞”风俗与“曲水诗序”的创作情况
(一)上巳节“曲水流觞”风俗的形成
农历三月三日上巳节有相当长的渊源,可追溯至先秦,最早还未与曲水流觞联系在一起。宋人王楙《野客丛书》卷十六“上巳祓除”条有载:“自汉以前,上巳不必三月三日,必取巳日。自魏以后,但用三月三日,不必巳也。”[3]173-174三月上旬的第一个巳日即为“上巳”,而农历三月三多逢巳日。魏晋之后,三月三日与上巳合并,每年三月三即为上巳节。先秦时期,人们在上巳节多于水边招魂续魄、祓除灾气,《太平御览》卷五十九引《韩诗外传》记载:“溱与洧,三月桃花水下之时,众士女执兰拂除。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日,此两水上招魂,拂除不祥也。”[4]284此外,高禖祠祀、偶合求子也是三月上巳的重要活动,《周礼·地官·媒氏》记载:“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5]511-513人们认为三月三水边衅浴是偶合生子的佳期,因此在三月三往往临水浮煮蛋和红枣,让入水的妇人争食,以求子嗣,如西晋潘尼诗所云:“素卵逐流归”[6]70。再往后,这样的习俗便又与曲水流觞的游戏结合了起来,成为了上巳节的主流。
(二)魏晋南北朝“曲水诗序”的创作情况
随着曲水之宴流觞赋诗的游戏在文人雅士之间蔚然成风,以三月三日上巳节为主题的文学创作也成为了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文化现象。《初学记》《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多部类书均设有“三月三日”条,其下又有诗、赋、序三小类,与兰亭雅集相似,这些作品中最后能够真正大放光彩的往往不是诗歌,而恰恰是诗序。
如今可以看到的最早的曲水诗序为西晋程咸的《平吴后三月三日从华林园作诗序》,其内容短小,语言精练,表现出早期诗序的典型特征。此序今文已有讹脱,能够看到的最早版本为《北堂书钞》卷第一百三十二仪饰部三·帘三“张朱幕延群臣”条下所引:
平原(2)“平原”应为“平吴”之误。参见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9月,第552页。后三月三日从华林园作壇宣宫,张朱幕,有诏乃延群臣。[10]2ɑ
严可均《全晋文》卷四十四亦载此文,并言“旧写本如此,讹脱无从校正”,此外其又录入了陈禹谟本《北堂书钞》所载:
平原邑三月三日,从华林园作壇,建仙宫,张朱幕,诏延群臣作诗以颂之。[1]1709-1710
严可均认为此版本盖为陈禹谟臆改,不足取信。不过程咸的原诗也是五言四句的小制:“皇帝升龙舟,待幄十二人。天吴奏安流,水伯卫帝津。”[2]552从残余的文字及诗歌内容来看,该序原文不会太长,极可能与陈禹谟删补后的篇幅相近。此次上巳节华林园之会应由晋武帝司马炎举行,具体日期不详。除此序外,王济《平吴后三月三日华林园诗》、荀勖《三月三日从华林园诗》应为同时之作。
南北朝时期流传至今的曲水诗序共四篇,有袁淑《游新亭曲水诗序》(刘宋)、颜延之《三月三日曲水诗序》(刘宋)、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萧齐)、萧纲《三日侍皇太子曲水宴诗序》(萧梁)。四篇诗序中,王融序与颜延之序成就较高。颜延之为刘宋时期文坛领袖,李善《文选》注引裴子野《宋略》曰:“文帝元嘉十一年,三月丙申,禊饮于乐游苑,且祖道江夏王义恭、衡阳王义季,有诏会者咸作诗,诏太子中庶子颜延年作序。”[7]645所作即为《三月三日曲水诗序》。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后来居上,李善注引萧子显《齐书》曰:“武帝永明九年,三月三日,幸芳林园,禊饮朝臣。敕王融为序,文藻富丽,当代称之。”[7]647二人序文同为应制之作,风格也较为相近。萧纲序则本事不详,最初应收于《梁简文帝集》,后是书散佚,此篇亦散见于类书之中,《艺文类聚》卷四岁时部所记最早,其篇幅不长,内容狭窄。袁淑《游新亭曲水诗序》本事亦不详,最早见于《太平御览》卷三五八兵部八十九,只有十六个字:“离榭修幕,陵隧弥阜,镳容旆彩,裛野丽云。”[4]1648比起序来更像是诗。
总体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八首以上巳节为主题的曲水诗序变化明显、脉络清晰,同一时段的作品也往往表现出相近的风貌特点。
二、“曲水诗序”思想内容的发展变化
西晋曲水诗序作于帝王诏宴群臣的曲水之宴。至东晋,随着门阀士族权力地位的提升,曲水宴饮随高门士族从皇家园林走进自然山水,曲水流觞的文化内涵也在此时确定下来。南北朝时期,时局混乱,曲水宴集也重回皇家园林,成为帝王与士族群臣之间维系政治亲密的重要场合。上巳雅集是魏晋南北朝曲水诗序创作的唯一主题,而各期上巳集会的性质也就决定着曲水诗序的基本内容特征。
(一)西晋:直述缘由,言简意赅
诗序在一开始只是对诗歌题目和内容的补充,是我们了解诗歌及其本事的重要依据。吴承学在《论古诗制题制序史》中提出:“诗人写作自序风气更主要是受到儒家《诗经》阐释学的影响。”“除受到经学影响之外,诗序的出现可能受到赋体的一定影响”[15],“经”和“赋”中的序催生了诗歌中的序,也产生了受“经”影响和受“赋”影响的两种诗序类型。他还强调:“可以肯定为诗人自拟的叙事式小序,大概在晋代开始流行,这与诗题制作情况大致相同。”[15]程咸《平吴后三月三日从华林园作诗序》很能代表这一时期诗序体裁的普遍特征:内容上叙事简短,语言风格则全为散体,只有不到三十字,却也简练地说明了作诗的时间、地点、人物、作诗原因,从中依稀可见史笔的风格。换而言之,这时的诗人写作诗序完全是功能性的补充,就像早期的志人志怪小说只是为了把故事记录下来一样,诗人还没有产生要在诗序中赋予自身独特思想感情的想法。也是出于这个原因,这个时期诗序的篇幅大都比较短小,也就更谈不上结构、笔法了。
(二)东晋:篇幅扩大,写景抒情,寄托玄思
到了东晋,受赋序影响较深的长篇诗序占了主流,曲水诗序可算是其中表率。徐公持曾指出:“从汉末开始,历曹魏西晋,大约在一百年的时期内,诗与赋的交流次第展开。交流的形态大要有二:一曰诗的赋化,二曰赋的诗化。”[16]而“受赋序的诗序则较长委曲详细,主要阐释创作缘起,有较明显的叙事成分在内,内容比较灵活详实,更符合‘知人论世’的批评原则,故后人诗序多采用此方式。”[15]西晋程咸序的两个版本都不到三十字,而相同主题下,王羲之与孙绰的《三月三日兰亭诗序》分别为三百二十五字、二百二十三字,明显属于受赋序影响的类型。
东晋的两篇曲水诗序能够取得较高的成就,离不开对西晋石崇《金谷诗序》的效仿。罗宗强认为,金谷宴集在两方面留下了深远的影响:一是士人流连山水的心态,一是诗文创作作为流连宴乐的雅事出现。[17]121正是受到了金谷宴集的启发,东晋文人自发流连自然山水、雅集作诗之事就逐渐蔚然成风了。再加上皇权的羸弱,门阀士族的强势,使得士族文人之间的上巳集会压倒了帝王的宴请,成为了东晋上巳节雅集的主流。他们在三月三日出游踏青,纵情山水,在河边“曲水流觞,列坐其次”,酒杯漂流至身前则须赋诗,不能则罚饮。在这种场合下,文人得以畅叙幽情,清谈玄学,曲水诗序的内容也就随之一变。
王、孙二序在结构上都可分为两个部分:一为写景叙事,一为理论阐发。王序先写景后议论,而孙作则相反。王羲之对于自然山水的描写名动天下:“此处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1]1609“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1]1609视角由近及远,由小及大,颇有超然之感。孙绰序有:“高岭千寻,长湖万顷,隆屈澄汪之势,可为壮矣。乃席芳草,镜清流,览卉木,观鱼鸟,其物同荣,资生咸畅。”[1]1808视角由远及近,贴近自然,写得清新明丽。可以看出,二者写景都意在表现自然山水的秀丽可爱,风格也很相近,与《金谷诗序》那种景色名物的獭祭已迥然不同,很能体现出东晋士人趋于崇尚明秀、高雅的审美趣味。
徜徉山水引发的是对于世界和人生的感悟。石崇《金谷诗序》“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1]1651算是表达了对生命短暂易逝的感叹。相比之下,王序与孙序对所思所感着墨更多,竟占全文篇幅的大半,几乎成为文章的主体。沈约说:“有晋中兴,玄风独振,为学穷于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驰骋文字,义单乎此。”[19]1778在玄学思潮背景下,王、孙二人诗序的思想高度超出了年命之悲的层面,进入了形而上的思考。
王羲之序中所发,紧紧围绕“生死”二字,由眼前的美景和盛会联想到的是情随事迁,老之将至,如“曾不知老之将至”“已为陈迹”“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1]1609,在快然自乐的背后是深沉的年命之悲。但其“俯仰之间”“情随事迁”“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1]1609等快意流畅的文字带给人阔大的时空感,减弱了死亡的沉重,“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1]1609,背后是逸少旷达的人生态度。文势一放一缓,抑扬起伏,生死苍凉以快意出之,为读者留下了豪放恣肆的精神气魄。故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卷七评:“通篇着眼在死生二字。只为当时士大夫,务清谈,鲜实效,一死生而齐彭殇,无经济大略,故触景兴怀,俯仰若有余痛。但逸少旷达人,故虽苍凉感叹之中,自有无穷逸趣。”[20]287-288浦起龙《古文眉诠》卷四十二也说:“非止序禊事也,序诗意也。修短死生,皆一时诗意所感,故其言如此。笔情绝俗,高出《选》体。”[21]3b石崇序比之右军,确实弗如远甚,正如苏东坡所言:“季伦之于逸少,如鸱鸢之于鸿鹄。”[22]2220其高下如此。
孙绰是当时著名的玄学家,也是玄言诗风的代表之一,文风中也带着老庄影响的痕迹。孙序开头便提出山水可移人性情的主张,人一如水,因停滞流动、遭际境遇的不同,性情、清浊也就不一。老子《道德经》有云:“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又不争”[23]31,人正是要借山水的自然情趣“于暧昧之中,思萦拂之道”,陶冶自身性情,解除心中郁结。末段又在对自然万物的观察中,生发出庄子的齐物思想:“齐以达观,决然兀矣,焉复觉鹏鷃之二物哉?”[1]1808当然,综观孙序所论,虽然精妙有致,却也失于寡淡无味,文学感染力远逊于王羲之序。《世说新语·轻诋》载孙绰“时咸笑其才而性鄙。”[18]720此序亦可看出其长于思虑而性情平庸的一面。
从思想史来看,王、孙二序的背后,是时代思潮由个体意识的觉醒进一步上升到了玄学的境地,其高度与西晋诗序自不可同日而语。诗序发展到东晋,叙事、议论、抒情兼备,已不再拘于对诗题的简单补充,而拥有了自身独有的思想内涵。
(三)南北朝:奉承应制,宫廷赋颂
南北朝时,曲水燕集的形式再次发生了变化。东晋灭亡后,政治局势更加动荡不安,庶族将领的权力又在不断攀升。“王与马共天下”的格局一去不返,为了维系贵族的政治地位,上层士族需要比过去更加积极地维系和皇室的关系。于是,上巳节集会也就成为维系政治亲密,歌颂、妆点政治合法性的场合。在皇家的召集下,士族文人聚于皇家园林中,置席设筵、引流曲水、群臣献诗,天子敕令一人作序。“流觞曲水”不再于自然山水中进行,而是多在皇家园林中由人工引流成席,颜延之序“阅水环阶,引池分席”句即是;赋诗的性质也不同以往,往往事先准备好可能要呈上的诗作,或早早请人代笔,如谢朓就有《三日侍华光殿曲水宴代人应诏诗》十章和《三日侍宴曲水代人应诏诗》九章。
曲水诗序的创作境况与曲水宴诗相似,由于是应制之作,形式化的痕迹很重,与东晋曲水诗序呈现出迥然不容的面貌。颜延之《三月三日曲水诗序》的写作背景,李善《文选》注引裴子野《宋略》曰:“文帝元嘉十一年,三月丙申,禊饮于乐游苑,且祖道江夏王义恭、衡阳王义季,有诏会者咸作诗,诏太子中庶子颜延年作序。”[7]645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的写作背景,李善注引萧子显《齐书》曰:“武帝永明九年,三月三日,幸芳林园,禊饮朝臣。敕王融为序,文藻富丽,当代称之。”[7]647颜延之、王融的序文最直观的变化就是文章体制的再次加长,从二三百字扩展到逾千言。同时在内容上,南北朝曲水诗序的内容风貌也与东晋时期大相径庭,从写景抒情一变而为称颂圣明。至于萧纲《三日侍皇太子曲水宴诗序》,其内容也已经言明宫廷宴游的性质。只有袁淑《游新亭曲水诗序》:“离榭修幕,陵隧弥阜,镳容旆彩,裛野丽云”[4]1648或还保留着“携朋斯郊野,昧旦辞廛郭”[9]66的文人雅集之趣。但那终归不是主流,可暂且放下不论。
南朝曲水诗序大体上可分为歌颂帝王圣德与描写宴游排场两个部分。在介绍宴饮集会的时间地点时,东晋二序只用三言两语,而南朝曲水诗序却要进行一番铺陈,感念一番太平气象。颜延之序从“晷纬昭应,山渎效灵”到“以望属车之尘者久矣”[7]645-646;王融序从“四方无拂,五戎不距”到“信可以优游暇豫,作乐崇德者欤”[7]650-651,均有几百字的篇幅,二人用如此冗长的篇幅来描绘繁荣景象,似都在强调:在这太平盛世之中,优游作乐,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是皇帝开明的治理,给臣民带来这样享乐的机会。而在描绘集会之景时,他们的描写则侧重于夸张铺排,如颜延之序从“既而帝晖临幄”到“故以殷赈外区,焕衍都内者矣”[7]647一段,就从阵仗之威、筵席之盛、乐舞之美、嘉宾之多等方面进行了一番夸饰,其着意便是在于称颂皇家风采。而王融之序不仅更长,在这方面更是不惜笔墨,极力塑造盛世景象:
于时青鸟司开,条风发岁。粤上斯已,惟暮之春。同律克和,树草自乐……既而灭宿澄霞,登光辨色。式道执殳,展軨效驾。徐銮警节,明钟畅音……尔乃回舆驻罕,岳镇渊渟。睟容有穆,宾仪式序。授几肆筵,因流波而成次;蕙肴芳醴;任激水而推移……有诏曰:今日嘉会,咸可赋诗。凡四十有五人,其辞云尔。[7]651-652
全段包含四个段落,其视野由外而内,以佳节时令切入,将芳林园内霞光、阵列、陈设、物产一一罗列,再写到宫廷仪仗的威严,再聚焦曲水之会的盛大,最后说到有诏赋诗,极尽铺张扬厉之能事,故何焯说:“颜、王二序,皆出班、张。”[24]963
要之,随着曲水集会性质的转变,曲水诗序的主旨也完全从东晋的记游与议论,转为了歌颂圣明、粉饰太平。如果说东晋曲水诗序整体特色靠近山水游记,那么南北朝时期的曲水诗序则更像是庙堂赋颂。因此清代李兆洛《骈体文钞》将颜、王二序置于上编,列卷三“杂飏颂类”中。按李兆洛的说法,上编之文,“皆庙堂之制,奏进之篇,垂诸典章,播诸金石者也”,是“拜飏殿堂,敷颂功德,同体对越,表里《诗》、《书》”的文章。[25]8所谓“杂飏颂类”也就是不用颂名但实为颂体的文章。可见南北朝时期曲水诗序的赋颂化特征是有目共睹的。
三、“曲水诗序”艺术形式的嬗变
曲水诗序的思想内容随上巳雅集的性质而不断发展变化的同时,其艺术形式上的不断进步也非常值得注意。从西晋至东晋再到南北朝,曲水诗序在对偶、用典、音律的技巧上愈发圆熟,骈俪化的程度也不断加深。
(一)骈偶程度的加深
序体源于史传,一开始就带有古文的基因,《史记》中就已有《太史公自序》。最早的诗序《毛诗序》和早期赋序也都以散体为主,因而诗序在发展的初期,其文体风格也继承早期序体的简练朴素,叙事则简洁洗练,记言则明白晓畅,行文自由,奇句单行。程咸序就文字简短、记事简练,有若史笔。而到了东晋,曲水诗序在内容体制不断丰富的同时,文体风格也不再依循曾经史传之序的散体传统,开始产生骈俪化的发展态势。
一些学者将王羲之《三月三日兰亭诗序》视作纯粹的散体,甚至将这一点视为此序未入《文选》的理由。如陈衍就认为:“昭明舍右军而采颜延年、王元长二作,则偏重骈俪之故。”[26]1590陈中凡也说《兰亭序》的文体是“纯粹的散文”,不是当时流行的骈体,故不入选。(5)其实其所引《游石门诗序》一篇也并非“通篇丽词骈句”。参见陈中凡选注:《汉魏六朝散文选》,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11月,第274页。[27]274然而观其正文,此序实际上已经出现了一些偶对的特征,只是未占全文主体,如“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已经是相当整齐的对偶了。更严谨的还有:“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等,无论是字数还是词性都做到了两两相对,上下两句加起来表达的也是同一个意思,符合骈文的规范。再看开头的山水描写:“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此地有崇山峻岭”“亦足以畅叙幽情”,“亭”“岭”“情”同韵;“岁在癸丑”“映带左右”,“丑”和“右”同韵,读来清新流丽。又如:“暂得于己(仄),快然自足(平)”“所之既倦(仄),情随事迁(平)”“俯仰之间(平),已为陈迹(仄)”“列叙时人(平),录其所述(仄)”“后之览者(仄),亦将有感于斯文(平)”,这些对句末字平仄相对,又产生了抑扬起伏的效果。虽然这些对句还不占全文主体,但骈偶句式的运用和带有韵律的用字,正是骈体文的特点,说它是一篇“纯粹的散文”未免有失偏颇。故清代李兆洛将此序作为“缘情托兴之作”编入《骈体文钞》,赞其“雅人深致,玩其抑扬之趣。”[25]414总的来说,王羲之《三月三日兰亭诗序》骈散兼行,或至少可以说是带有骈化特征的散文。
孙绰《三月三日兰亭诗序》则已经完全是一篇纯正的骈体文。四六相对的偶句占了文章的主体,不仅以两个句子来表达一个意念,属对也工切流利,所谓“至魏晋群才,析句弥密,联字合趣,剖毫析厘。”[28]588不过用典还比较少,还没有体现出骈文辞藻富丽的特点。蒋伯潜、蒋祖怡认为,晋代骈文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仍以纤巧和妍丽来争奇斗胜,第二个时期虽然叙述起来仍用骈俪的体裁,但是已经不过于重视文字的美丽、修辞的精妙了。于是,就文章的本体而言,骈文渐渐走入了束缚的路。[29]21-22孙绰《三月三日兰亭诗序》语言清丽却耽于说理,似可以佐证这一趋势。而南北朝时期的曲水诗序,其骈俪化的程度对比东晋时期又大大加深了,这一方面在于用典,另一方面则在于声律说的运用。
(二)用典水平的提高
颜延之诗文,前人最称道之处即为“密”。沈约说:“爰逮宋氏,颜、谢腾声。灵运之兴会标举,延年之体裁明密,并方轨前秀,垂范后昆。”李善解释“体裁明密”为:“体裁,制也。谢承《后汉书》曰:‘魏朗为河内太守,明密法令也。’”[7]703然则“明密”实为针对文章之言,《诗品》云:“其源出于陆机。尚巧似。体裁绮密,然情喻渊深,动无虚发,一句一字,皆致意焉。”[30]351可见他们都是注意到了颜延之文学风格之“密”。这种“密”主要就是典故的厚密,在颜延之《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中有鲜明的体现。如:
南除辇道,北清禁林,左关岩隥,右梁潮源。略亭皋,跨芝廛,苑太液,怀曾山。[7]646
“辇道”出自司马相如《上林赋》“辇道纚属”,“禁林”出自班固《西都赋》“集禁林而屯聚”,“左关岩隥”出自《穆天子传》“天子东升于三道隥”,“右梁潮源”出自司马相如《难蜀父老》“关沫若,梁孙原”,“略亭皋”出自《上林赋》“亭皋千里,靡不被筑”,“跨芝廛”出自曹植《洛神赋》“税驾乎衡皋,秣驷乎芝田”,“苑太液”出自《汉书》所载太液池,“曾山”或为其所包环之山。这段文字一句一典,读来顺畅,且典故并不艰深,所用皆为当世最为著名的作品,裁切也较为得当,让人一眼便能明了。“明密”二字可谓评价得恰到好处。
王融同题作品在当时被评为“文藻富丽,当世称誉”,其风格上与颜序一脉相承,皆为整饬典丽的作品,在用典的艺术技巧上更是超越前作。首先,王序用典的厚密程度超越颜序,如:
褰帷断裳,危冠空履之吏;彯摇武猛,扛鼎揭旗之士。[7]649
“褰帷”出自《后汉书》卷三十一《贾琮传》,“断裳”出自《汉书》卷七十七《盖宽饶传》,“危冠”出自《说苑·善说》,“空履”出自《汉书》卷七十二《王贡两龚鲍传》,“彯摇”出自《史记》卷一百一《卫将军骠骑列传》,“武猛”出自《后汉书》,“扛鼎”出自《史记》卷七《项羽本纪》,“揭旗”出自《论衡·效力篇》。短短二十字,竟填入八个典故,达到了一句两典的密度,典的密丽程度上已经做到了极致。
其次,王序在对典故的熔裁上超过颜序。颜序用典多出自文赋,而王序用典却多出于史传,除典故更加艰深外,对于典故运用水平的要求也高了一层。如颜序“辇道”“禁林”等词直接从“辇道纚属”“集禁林而屯聚”中裁剪而来;而王序所用词语则出于熔铸,如“褰帷”一词,出自《后汉书》卷三十一《贾琮传》:
时黄巾新破,……乃以琮为冀州刺史。旧典,传车骖驾,垂赤帷裳,迎于州界。及琮之部,升车言曰:“刺史当远视广听,纠察美恶,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于是州界翕然。[31]1112
王融将一百多字的史传典故熔铸为“褰帷”二字,既能抓住故事重点,又能找出最具代表性的意象,可见对于典故的熔炼十分纯熟。后文“断裳”二字又出自《汉书》中盖宽饶的故事,“褰帷”与“断裳”不仅在字面意义上相对,而且在典故内容上也能以贾琮和盖宽饶并举,可谓是表里皆对。两个词语组成一句,四对四,六对六,二十字用八典,又全部表达了文武皆才、政治清明这一个意思。王融序为千字长文,不仅典故数量多如繁星,还能做到典与典之间熔裁得当、编织得体,可见在用典上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当然,典故过于繁冗,造成读者理解的困难,也招致了后人的批评。何焯评王融序:“其藻愈肥,其味愈瘠”[24]963,这也正是钱基博所说的:“自来为骈文者,非博之难而雄伟难。然不雄而博,喜用古事,弥见拘束。”[32]124不过这毕竟是当时的一种普遍风尚,《南齐书》卷四十七《王融传》载北朝使者评价王融序:“昔观相如《封禅》,以知汉武之德,今览王生《诗序》,用见齐王之盛。”[33]821可见不只是南朝,同一时期南北两地对于文章的审美倾向都偏于形式上的唯美。
(三)平仄声律的运用
南北朝曲水诗序艺术形式的另一大进步是声律的运用。作为永明声律说的初创者之一,王融对平仄四声的规律是很有心得的,其诗序虽然还是无韵,但已经能见到他对平仄四声的注意。声调精致的骈文,一句之中,依韵脚平仄,平节与仄节交替;一联之间,上句与下句平节仄节相反。王融此序对平仄声律的运用虽然还没能达到后世骈文完全成熟的境地,但可以看出已经有所接近了,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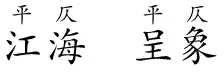

句中已经做到了平节仄节的相对,只是一联之内上下句还不能平仄相反。更严谨的又如:







一句之中平节仄节几乎全部相对,一联之内上句与下句平仄分布也接近完全相反,只有末句略有瑕疵。这样的句子已经十分接近后世那些音调完美和谐的骈文了,对比前代颜序之类作品,在音律的运用上已经有了明显的进步。
萧纲的《三日侍皇太子曲水宴诗序》虽短,但在平仄押韵上也有较为精彩的表现,可以看出骈文声律运用水平的发展:




平仄韵律完全相对,完美符合平仄要求。可见南北朝曲水诗序在声律进入骈体文的历史进程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总而言之,南北朝时期的曲水诗序由于上巳节性质的变化,在内容上走入了宫廷化、赋颂化的道路。但另一方面,这些诗序却在骈文语言的革新上发挥了作用。对偶、用典、声律都较前代有了长足的进步。正是出于这些探索,唐代骈体诗序的创作才能集前人大成,与盛唐气象结合,产生出如《滕王阁序》那样对偶、用典、平仄、韵律都完美纯熟的作品。
四、结语
从西晋程咸《平吴后三月三日从华林园作诗序》到梁代萧纲《三日侍皇太子曲水宴诗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八篇曲水诗序变化明显、脉络清晰。体制上,曲水诗序由《诗小序》型的简短发展至赋序型的冗长;内容上,它们由无甚作意的释题说明发展到寄托玄思,最后归于奉承应制;艺术形式上,曲水诗序由散体逐渐发展至骈体,对偶、用典、声律的技巧不断进步。
将曲水诗序置于诗词序体的发展史当中,我们还可以发现,它的山水宴游书写主题影响深远,甚至宋代词序中最优秀的作品,如姜夔《湘月·五湖旧约》序、《庆宫春·双桨莼波》序、周密《乳燕飞·波影摇涟甃》序、《三犯渡江云·冰溪空岁晚》序等,也都不离这一主题。诗词序文中最好的作品往往是对山水宴游的书写,这是一个很独特的现象。曾有学者提出宋词小序是晚明山水小品之先声的说法,但通过对魏晋南北朝曲水诗序的考察,或许这一“先声”的判断还可以提前。
当然,孤立地看待文体的特征是意义有限的,只有把某种文体放在整个文体系统中,在其它文体的参照下,对文体特征的辨析才会更有意义。作为一种从“副文本”发展而来的特殊文体,诗序如同一面镜子,从多种角度映照着诗、文发展的兴衰,为我们研究古代文体的发展带来了新鲜的视角。西晋以前不讲格律、对仗古拙的古体诗对应了当时的散体诗序;东晋玄言诗和山水诗的盛行催生了记游写意的长篇诗序;南北朝宫体诗的流行,也带来了诗序的骈俪和赋颂化,永明声律说的兴起也渗入到诗序的写作当中。曲水诗序作为魏晋南北朝诗序中成就突出的一支,忠实地记录了魏晋南北朝文坛的革新与流变,是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发展史的经典案例,具有独特的文学史价值。从这个角度来看,它们仍有许多值得研究、探索的余地,留待方家进一步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