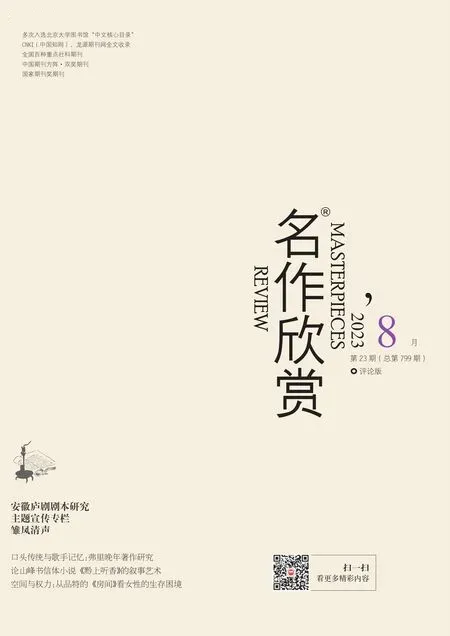《二马》中马威的妥协式“出走”
2023-08-25李娟聊城大学山东聊城252000
⊙李娟[聊城大学,山东 聊城 252000]
近代以来,社会被新文化、新鲜事物冲击亟待转型,造成了继承制度的变化,人们的家国观念随之转变。国家衰落与礼教可耻是“五四”兴起的家国话语,它与人的主体意识觉醒共同构成了“五四”启蒙话语体系。因此这种话语体系的颠覆以及重新建构,使得新文学抛弃了宣讲传统儒家继承故事的文学理念,应运而生的是反继承叙事占据创作的主导地位,于是新文学中的大批青年被塑造为与父亲决裂、放弃家族遗产,拒绝成为封建家庭继承人的出走者形象,这一批出走者的形象被称为“出走一代”。国内语境的“五四”时期新文学小说中,“出走一代”身上大多肩负着启蒙责任,他们的启蒙话语声音虽然微弱,并没有彻底完成启蒙使命,但是点燃了一群青年反抗父权制度投入革命事业的热情,彼此传递足以形成星星之火待以燎原。
老舍创作的《二马》中也塑造了一个出走者形象——马威,与以往他所写的出走者不同的是《二马》中的马威是老舍立足于国外语境所创,语境的转移以及文化的冲击使得马威负荷的精神重担与老舍笔下其他出走者形象有些不一样的内容。本文试图讨论老舍塑造的一系列出走者的出走意识,并从一个侧面着重描述《二马》中的马威为何是妥协式的出走方式,并没有主动承担起“五四”话语体系中体现的启蒙责任,从而陷入了迷茫自困的精神境地。
一、老舍小说人物萌动的出走意识
打开老舍的小说,很多篇章中都塑造了出走者的形象。20 世纪中国小说中出走者的归宿主要有三种:一种是走出封建家庭,开始自己革命独立的生活;一种是回归封建家庭;一种是离家流浪。基于此以老舍《四世同堂》《老张的哲学》和《离婚》中的出走者形象为例探索老舍所传达的出走意识。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军阀混战造成革命之风兴盛,出走者则是走出家庭投入到社会革命之中。逐渐形成了惯用的叙事思路,即逃离传统家庭,肩负起扭转社会现状的任务,独立成长蜕变,并且找到与之并肩战斗的情感伙伴,踏上追求自己革命理想的道路。我们把这种模式称为“出走——成长”模式,其实质是浪子不回头。老舍以自己亲身投入战斗的这段经历为原型,塑造出《四世同堂》中祁瑞全就是这样的典型革命浪子形象。他的出走虽然也与家族的矛盾有一定的关系,但更为重要和直接的原因是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的召唤。他的出走,是舍“家”为“国”的出走。从根本上讲支撑他们在困苦,艰辛,甚至血与火的生活中生存的精神支柱,就来自于曾经抚养了他们、给了他们生命的家。所以他们的身体虽然在外流浪,但他们的精神却在家。他们沐浴着新时代的文化,也承载了源远流长的中国家族文化的优良传统。他也就在这种流浪中获得了两重重要的身份,这就是《四世同堂》中祁瑞全的大哥祁瑞宣评价老三(祁瑞全),是祁家的,也是民族的英雄。离家出走后的流浪,使出走者完成了从家族的人到民族的人的转换,也使他们由此而获得了坚实而崇高的生活信念,使他们个人的独立生活,具有了社会与时代的价值。
在“五四”文学的出走浪潮中,出走者发现个人的努力在现实面前是徒劳的,无力去改变什么,于是,从呐喊,到彷徨最后则是回头。这类回归的出走者老舍对应的是《老张的哲学》中的王德,病入膏肓的他被父母安排冲喜,斩断了与李静爱情结果的最后一丝可能,在自我的消磨中,慢慢麻木掉了。于是老舍在文中这样评价王德这类的出走行为,“浪子回头,青年必须经过议会野跑,好像兽之走圹。然后收心敛性地作父母的奴隶,正是王老夫妇所盼望的”①浪子回归家庭失去如同野兽一般的野性,进而被驯化为失去了主体意识的努力,这种情节得以窥见“五四”一代的作品中,有关于“浪子回头”的反传统叙述。传统的浪子回头叙事中,回头的浪子意味着重生;现代的浪子回头故事中,回头的浪子意味着被驯服。这里面的根本原因是家不可回。家不再是那个能够给子女提供最后庇护的场所,而是一个吃人的魔窟,正如王德的那颗年轻有闯劲以及理想爱情的心已经死掉了。
离家流浪是老舍小说中最常见的出走方式,这样的出走没有明确的目的,这类出走者的出走动因最大可能是对自己的生活处境不满,自己的生活理想被现实生存空间挤压,因而选择出走,并非是想要主动承担起变革社会的任务,这也就与第一类革命出走为社会启蒙有所不同。他们的出走前路是迷茫的不知何向的,出走的结局可能是回归模式中等到对外面世界失望之后的浪子回头,也可能革命出走模式中投身于革命之中,但是作者都没有指明这类出走者的出路在哪儿,留给读者遐想的空间。老舍主要通过刻画《老张的哲学》中的李应、《离婚》中的老李以及本文中所要具体阐述的《二马》中的马威,来展现离家流浪的出走者心路历程。《老张的哲学》中的李应没有办法给叔父还钱,赎出身陷囹圄的姐姐,没有胆量手刃老张。被人性、社会道德、自然法则制约的李应,找不到救他人之法,也对自身产生了怀疑,最终达到难以自救的地步,因而选择出走。然而《离婚》中的老李是一直在寻求诗意的理想式人物,他对自己婚姻的不满,对自己的工作环境不满,自己在北平的唯一诗意具象化的马少奶奶,甘心对自己丈夫的背叛妥协屈服。老李在北平最后的诗意破灭了,选择了回归乡土,回归民间,民间成了退守的堡垒,把对启蒙思想的解构,反现代化的情绪推到了高潮。
三类出走者的形象展现了老舍的出走意识,他们的出发位置都是由家庭开始,选择的前路以及目的地各不相同,或是以家庭为动力源投入革命,或是出走失败回归家庭甘心成为家长的奴隶,或是为现实空间挤压流浪出走不知所踪。
二、马威绝望下的妥协式自救——出走
《二马》中马威选择的道路延承了离家流浪的出走模式,马威的人物成长背景设置在英国,所以马威出走的动因比单纯的反叛传统文化更加复杂。《二马》开篇便是以马威的仓皇逃跑开始,他就像为老舍拉开《二马》世界的拉幕人,写作镜头由点及面,呈辐射状地对英国伦敦白天的生活风貌展开了油画般写实的临摹,马威低迷的个人情绪与英国整体高涨的生活热情格格不入,也预示着马威作为一个异乡者最终无法融进英国的生活状态的悲惨结局。
《二马》也是终结于马威对伦敦的惨痛告别,马威的逃亡时间选择在了黑夜的伦敦,这时写作镜头独留下马威一人,马威个人的孤寂与夜色融为一体,文中写道:“他面前只有三个影儿:一个是无望的父亲,一个是忠诚的李子荣,一个是可爱的玛力。父亲和他谈不到一块,玛力不接受他的爱心,他只好对不起李子荣了!走!离开他们。”②亲情之间的责任、个人情爱的失意,以及对知己好友的背叛,使得他无法面对事实,不得不用逃避做结。对父亲的失望以及恋爱的不幸是他叛逃的主因,对好友的背叛产生的愧疚让他理想主义的希望破灭。
马威的出走沿其叛逃的主因依托文化漂泊感来分析,主要有两点:
其一,新文化与封建文化之间的冲突,具体表现为亲缘关系的父子矛盾。老马是封建文化的守墓人,而马威则是新文化以及西方教育下的新青年,他的思想观念、生活态度都与父亲产生分歧,而身份上的“父子”关系使得双方的对话并不处在平等的位置上,于是这些观念上的矛盾被压制在马威心中无处宣泄。马威虽然不认同父亲但确是传统意义上的孝子,为了保障二人在异国他乡的吃穿用度,独自承担起店铺的生意,同时他想去读书去做事业过自己的生活,做理想中的爱国青年,而老马执着于弄盅酒充穷酸做官,因此他内心鄙夷自己的父亲,发生工人打砸事件以后他本想振作起来重振铺子,却无奈于自己父亲软弱要卖铺子。这些压抑在马威心中成为无法排解的父子矛盾,不仅削弱了马威的文化归属感,还使马威与父亲之间产生了隔膜。
其二,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马威虽然接受着新文化教育,但是生长在中国骨子里还是有着中国人的气节,在异国他乡中接受外邦人对中国的丑化,深深的文化失落感和文化自卑感挤压着他的精神空间,他虽然认同西方文化某些观念,却也不满异族对中华民族的偏见。不彻底的西式文化教育和骨子里中国人的气节冲撞着他的内心,互相博弈造成极大的精神内耗。面对双重“二元对立”的困境,爱情的不幸是马威出走的最后推手。他极力想要与玛力成为恋人,可是囿于英国人狭隘的民族主义,害得他单相思成疾,一度在李子荣的劝慰下,他的思想发生了一些转变,而优柔寡断的思虑使得他在玛力与华盛顿订婚以后,又困在情爱的旋涡中。
马威是生活在重重矛盾中的中国青年,无力解决生活的困境,只能选择逃避自救,逃避的背后其实是对于身处环境的一种唾弃或者无力感。马威就像老舍笔下《四世同堂》的祁瑞宣,还有《离婚》中的老李,他们都是世俗意义上公认的好人,但是脱离这个身份,他们都是想得太多而不知道怎么去做的理想主义者,是被动妥协式的人物,带着点不反抗的意思。所以同时老舍评价马威:“他是个空的,一点也不像个活人。”马威的出走是老舍对马威人物形象成功刻画最好的交代,是其性格塑造的必然结果,也是老舍给予马威无法解决内心的文化困境的一种生活选择。
三、通向迷雾的出走前路
老舍在《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解释道没有续写马威逃亡的那一部分的原因,“离开伦敦,我到大陆上玩了三个月,多半的时间是在巴黎。在巴黎,我很想把马威调过来,以巴黎为背景续成《二马》的后半。只是想了想,可是:凭着几十天的经验而动笔写像巴黎那样复杂的一个城,我没那个胆气。我希望在那里找点事作,找不到,马威只好老在逃亡吧,我既没法在巴黎久住,他还能在那里立住脚幺!”③这样看来,《二马》应该在老舍的创作预期之中的上半部。尽管如此《二马》的留白式结尾,为读者想象人物命运提供了无限可能。
狭小的精神空间挤压着马威的生存空间,他从伦敦出发,无论是逃亡老舍计划中的巴黎还是欧洲的哪个方向,都摆脱不了文化交流精神沟通的怪圈,摆脱不了对异质文化的警戒,所以马威带着走向何处的困惑出走伦敦,前路是弥漫着迷雾的不确定。
这种迷雾实际上氤氲着老舍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思考,老舍真实地写出了处在双重文化矛盾之中的青年马威,被阴翳的父权体制下封建礼教文化氛围所影响,这当然有老舍本身的创作环境以及个人写作经验的缘由。除此以外,依据马威内在的文化“漂泊感”溯其本源,是对西方文化的自动疏离,否定文化对话,同时对本国文化敏感和异国对国人的歧视使马威内心惶恐不安,而他骨子里残留的些许文化自信心不足以丰盈他的民族自信心,使得他本人处于一种与现实割裂脱节的状态,从而达到对自我的厌弃,此番矛盾心态直接隔绝了外来文化对自身的影响。
老舍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与鲁迅“拿来主义”中的占有、鉴别、挑选之道有异曲同工之妙,近代许多作家思考了如何对待文化遗产这一问题。老舍认为,凡是文化不论民族都应进一步进行甄别,而不应盲从地无条件接受或是全盘否定。马威虽然身在异国他乡,被外国文化环境影响,但是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缺少理性色彩,不但不能与之进行真诚的平等交流,还煎熬于自身的双重文化矛盾的困境中。理想主义者的身份让他深陷现实的泥沼,最终他选择以出走的方式来逃避自己的现状,其中实则蕴含着老舍对于两种文化的反思。不“出走”活不下去了,可是“出走”的结局如何,所以老舍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
四、结语
老舍小说中塑造的三类出走者,展现的出走意识,串联起了家庭、自我与国家。而《二马》中的马威则是属于离家流浪式的出走者,并没有肩负起社会启蒙的任务,完全是出于内心的双重文化冲突,内在的迷惑让他逃亡的方向被迷雾遮住,看不清方向,隐含着老舍对中国人在异乡的深切同情,也隐含了对中西方文化的反思与思考,既不能故步自封,完全拒绝文化交流,也不能崇洋媚外,丧失中国文化自信,文化交流过程中应该以平等包容的方式,消除狭隘的民族偏见,倾听双方的声音。
①② 老舍:《老舍全集(第1卷)·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4页,第614页。
③老舍:《老舍全集(第16卷)·文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