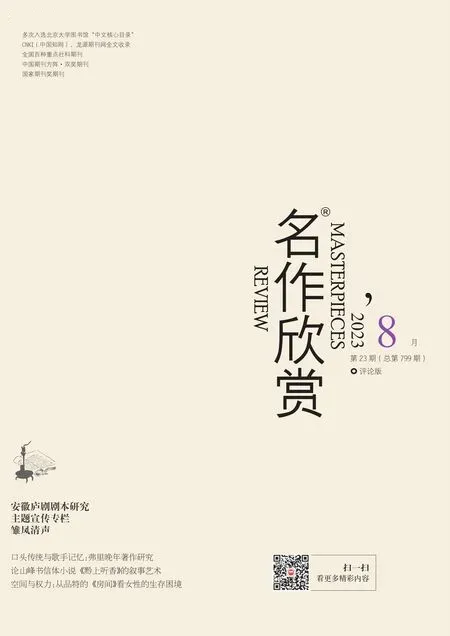霍夫曼斯塔尔对“宏大形式”的追寻:克服现代意识危机的一种尝试
2023-08-25李莉西安外国语大学西安710128
⊙李莉 [西安外国语大学,西安 710128]
纵观奥地利著名诗人、剧作家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Hugo von Hofmannsthal,1874—1929)一生的创作,引人瞩目的是1900 年以后他由诗歌、抒情诗剧的创作逐步转向大众戏剧、哑剧和歌剧等舞台表演艺术。对他来说,无论是表现沉重题材的悲剧、宗教剧和政治剧,还是相对轻松、充满诙谐幽默的喜剧,抑或是更多借助音乐、身体姿态的歌舞剧和哑剧,这些舞台表演艺术形式都是戏剧艺术的一个分支。在霍夫曼斯塔尔看来,戏剧舞台上发生的一切本身就是生活的表现。这种与大众的交流方式直接又简单,不同人物形象通过语言、姿势、音乐及舞台道具给观众带来更多视觉和心理触动。“戏剧是唯一保留下来的一种将我们人类喜怒哀乐全部连接起来的艺术形式。”①它将人类的欢乐、好奇、笑声,以及对情感的渴望、兴奋与节日结合在一起,跨越时代和种族的界限,深深根植于千百年来的文化之中。他认为,作家对戏剧本质了解得越多越深刻,就越有可能摆脱自己时代的局限性。戏剧不同于诗歌和小说,更多的是一种基于现实生活可感可观的再创造,比通常所说的精神更神秘,观众对它的接受却更加直观和感性。由此,霍夫曼斯塔尔对戏剧艺术的探索和尝试更进了一步,转入对宏大形式的探求,以便超越之前的诗体剧小型体裁:“我当时怀有急切的愿望,力图驾驭(宏大)戏剧形式——而不是诗体剧。”②这一尝试促使他主动面向古代神话,首先将古希腊悲剧家索福克勒斯视为同时代人的典范,在继承文化遗产的同时又赋予神话人物以新的时代意义。这是他针对自己与时代所出现的语言危机和意识危机做出的有效尝试。
一、宏大形式之内涵
霍夫曼斯塔尔提出宏大形式的概念,源于他对古典文学和世界文学的深厚积累,以及他对总体艺术作品(Gesamtkunstwerk)的追求和对宏大宇宙观的渴望。首先,仅宏大形式这一概念的字面意义就说明了诗人对艺术形式的刻意追求。所谓宏大,就是比喻事物的气势宏伟和巨大;所谓形式,这里必然是指艺术形式,具体到戏剧方面,便是指戏剧的种类和形式。结合诗人所生活的时代,把这个概念理解成“大剧”(或艺术剧)更为贴切。所谓大剧,就是包容多种艺术手段的、表现心理情感冲突、注重人物的内在情感和思想表现,从而淡化了戏剧情节的现代戏剧,简称为现代心理剧。与此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诗人本人的艺术追求,宏大形式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古典文学、对异域文化/文学素材的汲取、吸收和利用。从这个意义上讲,霍夫曼斯塔尔对宏大形式的追求,意味着他在新的创作阶段对艺术戏剧的探寻和尝试。此外,对他来说,宏大形式只能在神话中才能实现,因为神话能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打破个人和集体、过去和现在之间的界限,“唯有神话包围的地平线能将全部文化运动凝结成统一的整体”③。只有在神话的语境中才有可能将现实社会中的矛盾对立连接成紧密的整体。宏大形式也意味着对独幕剧规模的拓展和扩充——他早期的诗体剧均为独幕剧,剧情时间的延展,以及布局上的扩展,即由短小的诗体剧转向真正意义上的戏剧形式。
纵观西方戏剧的发展史,西方戏剧从古希腊的命运悲剧、到15 世纪以后的性格悲剧、然后到现代时期的心理悲剧、最后到当代的抽象剧、荒诞剧等,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古希腊悲剧被认为是西方戏剧的起源,享有崇高的地位。鉴于当时社会历史条件发展的限制,古希腊戏剧家将个人遭遇的苦难归因于命运的戏弄,悲剧冲突主要表现在主人公(一般是英雄)与命运抗争而引起的冲突。但同时,他们也在人的自由意志与命运冲突的过程中表现出崇高而严肃的悲剧主题,以此来探讨人的终极命运,给予人们积极面对生活的勇气。大约14 世纪起,为了冲破中世纪封建神学的阻挠与压制,新兴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开始寻找自身发展的新途径。他们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在淹没已久的古希腊罗马文化中发现了新世界,由此展开了一场在欧洲大陆影响深远的文艺复兴运动。在这场思想变革中,戏剧这一艺术形式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创新和发展。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随着科技的进步、经济的发展,人逐渐沦为机器和金钱的奴隶,失去了个人的价值和尊严,丧失了感受美好事物的能力,内心越来越扭曲变形,从而陷入深深的信仰/精神危机之中。人与自我、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冲突日益显著,人自身的生存问题成为很多剧作家创作的表现主题。同时,此时也是精神分析学影响力日益扩大的时期。西方现代心理悲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这样的一种悲剧着眼于表达人的心理、命运、精神、生存困境和存在价值等根本问题,将悲剧性视为人生原本的底色,并赋予人类以崇高和美的价值。此外,现代作家还认为悲剧是由人性的内在特性所造成的。这样的悲剧人物都表现出一种畸形、病态的心理状态。此类现代心理悲剧体现了剧作家对现代人灵魂的探索以及对现代人精神困境的关注。
从西方文学的整体发展态势看,从古典时期(古希腊罗马时期)的英雄主义题材(爱恨情仇)、到近代的性格题材(情绪)、到现代的心理题材,以及当代的非理性题材,经历了一个内倾化的演变过程;其审美原则也从古典文学的以雅为美的艺术品位逐渐演变成了现代文学以来的以真为美的艺术品位,其艺术形式的流变轨迹大多取决于某种审美原则的影响。西方现代派文学主要采用暗示、象征、变形、意象等手法来挖掘现代人的心理世界,大多表现荒谬、混乱、猥琐、邪恶、丑陋、没落、颓废、绝望等意识特征。维也纳现代派也不例外,表现对象不外乎颓废、没落、内心矛盾、精神失落感等,只不过采用了唯美的形式。霍夫曼斯尔的创作主题便是现代人徘徊于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之中所表现出来的失落和颓废情绪。然而,作为一个积累深厚的学者型诗人,他要以古典美的形式来进行艺术创新,首先要从古典戏剧艺术中汲取营养,于是便突出了纯艺术的特性。总之,霍夫曼斯塔尔的作品显现了内倾、颓废、唯美的特点。他虽有现代生活体验,但却表现出修复传统的倾向。
二、宏大形式之神话元素
世纪转折时期现代社会的种种矛盾冲突、传统价值观念的崩塌和个人主体意识危机,促使霍夫曼斯塔尔转向古典,即古希腊神话和古希腊悲剧,以寻求精神导向,他亦试图在神话的重塑中来实现延续传统的可能性。于是,希腊戏剧成为其追求宏大形式的产物,表现出他在世纪之交时期对古代神话艺术进行再创造的热情尝试。对他来说,宏大形式意味着对优秀文学传统的研究与学习,并能为己所用,其中最受瞩目的传统时代是古希腊、文艺复兴及巴洛克文学,由此他创作了多部取材于古希腊神话的戏剧和歌剧。这种在历史遗产中寻求创作素材的现象也是1900 年前后很多作家的选择,比如,比利时剧作家莫里斯·梅特林克(Maurice Maeterlinck,1862—1949)、英国作家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1854—1900)以及奥地利作家阿图尔·施尼茨勒等,霍夫曼斯塔尔尤其表现出对古希腊神话的偏爱。尼采曾在1872 年发表的《悲剧的诞生》中论述:“如果没有神话,每种文化都会失去其健康的、富有创造性的自然力量:唯有神话包围的地平线能将全部文化运动凝结成统一的整体。”④霍夫曼斯塔尔对神话的理解无疑受此影响,在神话的语境里所有的一切都可能成为紧密相连的整体。在《友人的书》(Buch der Freunde,1922)中霍夫曼斯塔尔写道:“神话是所有虚构的事物,你作为生者参与其中。神话中每个事物都有两层相互矛盾的含义:死=生,与蛇斗争=恩爱相拥。因此神话中万物都处于平衡状态。”⑤由此可见,在霍夫曼斯塔尔眼中,神话具有化解矛盾的功能,他意欲通过这种理想的艺术形式来回应世纪转折后处处充满各种矛盾冲突的社会现实。
霍夫曼斯塔尔在1894 年1 月18 日的日记里第一次提到要对欧里庇得斯的戏剧《阿尔克斯提斯》(Alkestis,B.C.438 年)进行再创作,并在之后的一次回顾性文章中将此描述为“对古代神话再创作的初步尝试”⑥,表明了他对戏剧舞台效果的强烈追求。甚至在此之前,霍夫曼斯塔尔就已表现出对戏剧及舞台表演的特殊偏爱。比如1892 年初,他针对女演员埃莱诺拉·杜塞的演出写了两篇评论性文章,其中强调将戏剧作为一种酒神式的节日来庆祝:“本周在维也纳,我们数以千计的人过上了一种如同在雅典庆祝酒神节日的欢快日子。”⑦由此不难理解,这位年轻诗人在早期作品中一再强调心醉神迷的酒神时刻,并努力寻求以一种创造性的参与舞台艺术的方式。他对欧里庇得斯戏剧的改编不仅为自己创造了一个研习戏剧艺术技巧、探索舞台实践的机会,而且还对生与死的关系等重大主题做了更深入的思考。《阿尔克斯提斯》并不是霍夫曼斯塔尔首次探索戏剧形式的尝试,甚至在更早的时候他就已在抒情剧中以古人的宏大戏剧形式为典范来训练自己的戏剧技巧,同时也视这些丰富的戏剧材料为自己创作的肥沃土壤。
尼采曾指出过神话的原型特征,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更进一步阐明了神话的基本特质。在分析悲剧产生原因的过程中尼采借用神话人物说明了人的心理因素:酒神狄奥尼索斯的原始、野蛮、暴戾、迷狂的激情,日神阿波罗的规范、典雅、明朗的气质;同时,他把诗人的创造归结于梦境的学说也涉及了心理学的范畴,对当时的文艺思想界产生了很大影响。此外,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也同样借用神话原型人物(俄狄浦斯、厄勒克特拉)阐论了人的心理特征。这种对人自身的心理和潜意识领域的探索和发现是19 世纪末期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进步和发展的成果,无疑折射出西方世纪转折时期的时代特征。从这个层面上来说,霍夫曼斯塔尔接受了尼采和弗洛伊德关于心理学说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世纪之交的人们在文化中认识到了自己,尤其是通过神话认识到了自己,如霍夫曼斯塔尔所言,是“一个生活在梦幻、恐惧、迷茫和渴望中的人,并因为自己的卑微和丑陋从不敢正大光明地把这一切解释为本能”⑧。从早期戏剧创作开始,霍夫曼斯塔尔越来越关注人的内心生活。他的希腊悲剧表达了当代人的身份问题,从中也显露出他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接受。弗洛伊德将神话描述为一种在文化发展过程中被压抑欲望的表达,并将集体神话的形成与个体梦想的产生进行了类比,指出成年人的梦主要从童年经历中汲取素材,而神话则是人类历史上童年阶段的产物。根据这一主张,弗洛伊德希望最初构想的精神分析学说被理解为“对非理性的理性且有意识论述”⑨。“与梦一样,神话也是一种精神分析启蒙的材料,借助它把一种黑暗而混乱的语言变成一种透明而合理的语言。”⑩1922年,霍夫曼斯塔尔在他的第二封《维也纳的信》中对神话的诗学分析和精神分析做了明确的区别:弗洛伊德和之前的诗人们一样,拥有一把打开巨大秘密的钥匙,尽管他以探险家的大胆和狂热对这把钥匙做了充分的使用说明,但是诗人们却被禁止使用它,除了用一种特别隐秘的方式。事实上,霍夫曼斯塔尔在其戏剧作品中反复引入精神分析理论,特别是在他的悲剧创作方面更是把现代意识起源问题表达得极为充分。
希腊神话的永恒力量克服了时间和空间的距离,使古代英雄人物的命运也能直接、生动地展现在当代的舞台上,并从生命深处揭开了人的命运的面纱。按照尼采的说法,在酒神的魔力下,个人和宇宙之间的界限模糊了,仿佛玛雅人的面纱被撕破了,只在神秘的原始同一(Ureinen)前闪闪发光。⑪霍夫曼斯塔尔感到,这种以神话为基础的酒神智慧在与英雄命运的交融过程中清晰地显现出来,也成为他转向希腊悲剧、力图通过悲剧艺术把人对生命的敬畏以及生活的不确定性搬上舞台的重要原因。
三、宏大形式之悲剧精神
霍夫曼斯塔尔之所以选择在古希腊悲剧中探寻宏大形式,是因为其主题本身就蕴含着宏大、高尚的人生主题,并且致力于追求一种永恒的精神境界。此外,悲剧在创作形式上要精密构思和巧妙布局,不能是自由散漫的灵感和华丽辞藻的堆砌。通过悲剧,观众更容易认清人生实苦的真相。但是,古希腊悲剧具有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使得观众从中获得肯定人生、抵抗残酷现实的勇气,进而达到一种心理状态平衡的悲剧审美效果。
为了更好地阐释霍夫曼斯塔尔为何要在悲剧中探寻宏大形式,就必须先理解古希腊悲剧的起源。根据尼采关于悲剧艺术的学说,古希腊悲剧源于希腊两种自然的艺术倾向,即阿波罗精神和狄俄尼索斯精神。前者是希腊神话中的日神,代表着静穆的美,是冷静而理智观察世界的一种精神,在艺术形式上大多呈现为造型艺术;后者则是酒神,代表着生命的活力,表示一切非造型艺术。当两种精神相互结合,便出现了希腊悲剧。所以说,希腊悲剧是美与力的综合,既包含阿波罗梦幻式的美,又拥有狄俄尼索斯醉狂式的力,于是就产生了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净化力量。原始的狄俄尼索斯精神实际上是一股生命的过剩力量,它不受任何限制,表现为毫无节制的纵欲,而纵欲的结果就是痛苦。古代祭祀后的狂欢就是这种纵欲的表现。而当狄俄尼索斯的醉狂力量获得阿波罗梦幻世界美的形象后就得到了节制;同时,阿波罗精神也获得了狄俄尼索斯式的生命力。至此,二者相辅相成,达到一种合一的境界,这样,希腊悲剧就拥有一种肯定生命的悲剧精神。
回顾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西方历史便不难发现,自然科学和工业技术的迅猛发展推动着社会文明和进步,也带来工业的进步,而工业的进步又创造了繁盛的机械文明。生活在文明迅速发展的现代人崇尚知识,崇尚功利主义,追求物质享乐,一切都以现实功利为目标,但又缺乏人生理想,更缺乏一种面对苦难忧患而创造人生的精神。可以说,悲剧中的狄俄尼索斯精神已经被追求现实功利的理智之手扼杀了,余下的只有阿波罗的冷静和理智。霍夫曼斯塔尔重新改编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悲剧,显然不是要重扬古希腊的和谐之美,而是为了借用现代主体的形象去探寻丧失已久的悲剧精神,而这种悲剧精神则存在于古希腊悲剧的宏大形式之中。当时著名的作家、语言与文化评论家卡尔·克劳斯曾讽刺霍夫曼斯塔尔是“从事改编的作者,拔去动物尸首的尊贵皮毛,以便在其中安葬可疑的尸体”⑫。对此,霍夫曼斯塔尔并不否认自己的“创作意图完全缺乏虔敬”,但是他“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对我们时代的人产生影响”,并且相信,他的新作“对于将来的读者肯定会十分明显地带有其创作时期——20 世纪初——的特征。在我看来,古希腊人物仿佛是永恒的容器,代代新作家总可以在里面盛放新的灵魂内容”⑬。
悲剧作为一个美学范畴,其本质是采用诸如灾难、痛苦、毁灭、死亡等的否定形式间接地肯定了人类创造的自由;悲剧固然会给人们带来沉重、压抑的感受,但人们通过悲剧也能反观自身,从而在实践活动中不断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同时,悲剧集中体现着崇高的精神,无论是古典悲剧中所代表的抗争精神,还是近代悲剧中主人公所体现的伦理意义,抑或现代悲剧所展示的现代人精神上对自由生存和完整个性热切的渴望和追求,都无一不体现出悲剧所蕴含的崇高美学内涵,即人类反抗命运的崇高精神。霍夫曼斯塔尔作为一位情感细腻、感受力敏锐的诗人,在世纪转折之际更是想要在古希腊悲剧经典中给同时代人以启示和警醒,让生活于无神殿堂之中的现代人既能看到人之有限、异化、缺憾、孤独与不完善,也能由此鼓起勇气,在有限之中创造无限,于无意义之中创造生命的价值。
文艺复兴以来,西方人一直高举着理性的大旗,追求着人的独立与自由,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却逐渐陷入价值的相对主义和存在的虚无主义。人对理性主义的过分推崇导致了对人自身存在的遗忘以及人生意义的失落。于是,现代人逐渐在精神和心理上遭遇种种困境和危机。在世纪之交的现代社会中,个体与异化的社会之间、感性与理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霍夫曼斯塔尔通过对古希腊悲剧的改编,生动地折射出了现代人所遭遇的精神上的痛苦、迷惘、焦虑和孤独。比如戏剧《俄狄浦斯与斯芬克斯》的主人公俄狄浦斯作为自由的个体拥有自由的意志,本来有很多选择,但他的最终选择可能引发的冲突结果是无法避免的悲剧。作为维也纳现代派杰出代表之一的诗人和剧作家,霍夫曼斯塔尔用现代戏剧形式重新阐释古希腊悲剧,为原有的悲剧人物赋予新的历史内涵,透露出20 世纪初的人性挣扎状态以及现代人对自我价值的肯定与坚持。这种以古喻今的创作方式体现了他对宏大形式的探寻尝试,并借此表现现代人对自己所面临现实生存困境所做出的思考与探索,显示出诗人对现实世界的审视保持着一种批判意识和反叛精神。
总括地说,霍夫曼斯塔尔是被当时的社会现实所触动,在现代人文科学(马赫的感觉学理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尼采哲学等)的影响下,运用了古希腊悲剧的艺术资源,创作出一部部表现现代人精神困惑的作品。他是一位非常具有传统文化意识的诗人,自认有责任和义务将传统文化发扬光大,因而认真地向伟大的文学先辈学习。对他来说,宏大形式不是刻意追求形式完美、传统情节结构被分解、具有唯美主义特征的抒情诗剧,而是在继承和发展古典悲剧题材和形式的基础上着力表现现代人的生活情感。因此,他所崇尚的宏大形式大多既有古典悲剧那种艺术剧的古代神话素材和艺术表现形式,又特别显著地赋予剧情与人物本时代的色彩。
①Hofmannsthal,Hugo von &Borchardt,Rudolf: Breifwechsel,Hrsg.von M.L.Borchardt und H.Steiner,Frankfurt 1954,S.111/112.
② Hofmannsthal,Hugo von: Briefe II 1900—1909,Wien 1937,S.161.
③④ Nietzsche,Friedrich: Die Geburt der Tragödie.unzeitgemäße Betrachtungen I-III(1872—1874),Hg.von Giorgio Colli und Mazzio Montinari,Berlin/ New York:De Gruyter,1972.S.141.
⑤ Hofmannsthal,Hugo von: Reden und Aufsätze III,in:Gesammelte Werke in zehn Einzelnbänden,hrg.von Bernd Schoeller,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Frankfurt a.M.1980,S.257-258;S.309;S.376.
⑥⑪ Hofmannsthal,Hugo von: Reden und Aufsätze II 1914—1924,in: Gesammelte Werke in zehn Einzelbänden,hrg.von Bernd Schoeller,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Frankfurt a.M.1979,S.130;S.192.
⑦⑧ Hofmannsthal,Hugo von: Reden und Aufsätze I 1891—1913,in: Gesammelte Werke in zehn Einzelbänden,hrg.von Bernd Schoeller,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Frankfurt a.M.1979f,S.475;S.527.
⑨ Starobinski,Jean: Literatur und Psychoanalyse,Frankfurt a.M.1973,S.99.
⑩ Rutschky,Michael: Freud und die Mythen,S.224.(Zit.Nach: Michael Worbs,Mythos und Psychoanalyse in Hugo von Hofmannsthals Elektra,in: Tohmas Anz(Hg.),Psychoanalyse in der modernen Literatur,Würzburg 1999,S.6)
⑫ Nietzsche,Friedrich: Die Geburt der Tragödie,Kritische Studienausgabe,hg.von Giorgio Colli und Mazzino Montinari,München 1988,S.29.
⑬ Kraus,Karl: Die Fackel,Mai/1912,S.3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