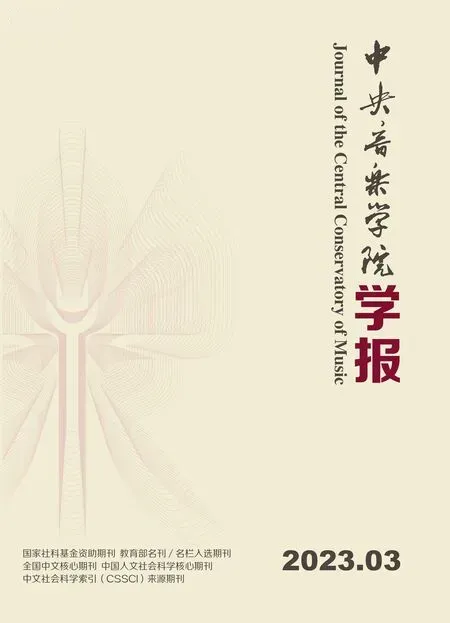两性对歌礼俗:门槛、区隔与匿名化
2023-08-24肖璇
肖 璇
两性对歌是中国民歌研究“返本开新”的领域。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学者在“语境疏离的文本收集”(1)指的是以收集民歌歌词、旋律等为主要手段的文本化研究,而民间信仰、民俗活动和节日庆典等文化语境并非主要的关注对象。“多声部音乐”“风俗音乐”“民族志个案”等调查和研究中均对两性对歌有所涉及(2)肖璇:《近代学术转向下对歌研究的四种取向:中国两性对歌研究述评》,《民族艺术研究》,2017年,第3期,第146—154页。。只是以往的“文本收集”常常视对歌为“礼”的反面或被压制的民间文学传统(3)如歌谣运动时期民俗学家们“眼光向下”的歌谣收集(部分为对歌)一方面受到西学影响,另一方面是重新思考学术精英所鄙视的民间文学。以“民”的立场批判礼教,为的是整理国故,构建新学。因此我们看到《歌谣周刊》的《发刊词》上表达了来稿者“不必自己先加甄别卑猥或粗鄙的歌谣而尽量录寄”的愿望,这也就有了后来钟敬文因涉及出版情歌《吴歌乙集》)被中山大学辞退的事件。可参阅施爱东:《顾颉刚、钟敬文与“猥亵歌谣”》,《读书》,2014年,第7期,第2—11页。,或将对歌作为婚、恋、性爱的“风俗音乐”“民族志个案”(4)参阅杨沐:《性爱音乐活动研究:以海南黎族为例》,《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6年,第3和第4期连载;杨民康:《中国民歌与乡土社会》,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年,第166—180页。,更多着墨于两性交换和社会团结功能方面,较少关注其所包含的以礼就俗、俗定礼成的过程和地方文化创造。笔者“返本”后的再出发缘于2006年至今多点、持续地关注中国境内两性对歌的活态传承,将之与历史文献和其他民族志材料对勘来拓展民歌研究的视野和思路;并于近年来逐渐意识到,两性原则作为传统对歌的第一原则,对立统一的两性声音和社会性别交织在交友、婚恋和人生礼仪等社会空间演述(5)民俗学倡导的“以演述为中心的方法”,是将关注点从文本化转移到情景化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空间来观察文化表达和口头交流的过程,并形成了口头演述的诗学和文化表演的符号学两种研究方向。详见朱刚:《作为交流的口头艺术实践:剑川白族石宝山歌会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81—98页。中,以传统音乐表演的空间安排为表象,两性道德(6)两性道德指的是两性互动交往、恋爱婚姻活动中的善恶价值思想、观点和理论体系。它在一定社会条件下以规范和引导人们的两性行为准则,并通过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和内心信念的维持发挥作用。参见王伟、高玉兰:《性伦理学》,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7—38页。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普遍认同道德是一种文化实践和文化秩序,对于促进社会有序团结和持续进步发挥作用。决定了男女空间分布、演唱方法和禁忌等等对歌的体化实践(7)与以文字为主的刻化实践相对,体化实践指的是音乐作为身体行为的一种文化传承。。除了被学者们视为禁忌的两性亲密交往性俗,公共生活的情歌对唱更多指向了以“物”与“非物”为中介建构的行动伦理和歌唱礼俗。从乡村礼俗与礼仪到中华文明,对歌的礼俗互融,勾连历史和现实、中心与边缘,与20世纪初汉学家葛兰言在《诗经》《礼记》之外探讨中国早期社会形态、中国文明的源与流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
一、“物”的区隔与对歌礼俗
什么是好的对歌?除了超越日常语言的歌与诗,对歌盛行地区的人们认为,好的对歌要含蓄、有门槛。两性对歌的门槛除了符合社区道德理想和交往评价,还有即兴与演唱的难度等级。节庆、婚礼等时空中,人们访寨做客的对歌产生第一类对歌门槛,即主家在寨门、大路空间转换处设置绳子、人墙等路障,以歌盘问和唱答戏谑的方式迎客入门,如西北莲花山花儿会以及西南侗族聚居区的拦路对歌;第二类为对歌的能力要求,如歌唱和即兴对歌的押韵、编词、典故和破句等等,它是音乐文化传统的内容与核心,也是个人需要通过学习和传统文化的浸润来跨越的对歌门槛。本文着重讨论的是有序时空中“物”与“非物”的匿名性和两性区隔的第三类对歌门槛,它矗立在情感需要和道德伦理之间,以与社会规范不相害的两性交往方式形成地方歌唱礼俗,守护着共同体的长期价值。
(一)可见的门槛:门板和花伞
每当夜幕低垂,贵州东部苗族姑娘的笑声穿过木屋,引来男孩循声而至。他们在姑娘卧室房外敲窗或以哨音呼唤。姑娘通过召唤的韵律和节奏决定开窗与之展开隔窗夜谈、轻声对歌,还是闭窗谢绝非姻亲团体、本村男孩的邀请(8)简美玲:《贵州东部高地苗族的情感与婚姻》,贵阳:贵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6—37页。。壮族干栏建筑的下层圈养牲畜、堆放杂物,侧有斜梯直达上层,前堂与两侧耳房贯通。微光下,男人围坐在上层前堂和火灶旁,女人耳房坐唱。20世纪70年代以前广西靖西一带的人们往往对家屋内男女面对面对歌持负面评价:怎么会有姑娘这么勇敢,竟敢和男人并排坐着“吟诗”,因此常见的对歌画面是从外村请来的女歌手坐在灶台边,男方则在屋外的树下隔着紧闭屋门与女方对歌(9)陆晓芹:《“吟诗”与“暖”:广西德靖一带壮族聚会对歌习俗的民族志考察》,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99页。。家屋夜歌几乎都会涉及双方交情的内容,横亘在两性间的对歌障碍和门槛在壮族许多支系都存在。而空间分立的另一面是自由对歌,不仅未婚男女青年有对歌的自由,已婚男女也不乏情歌对唱。如果道德是对自由的约束,那即兴自由对歌的边界在何处?
身处西北花儿会现场,只见花伞的海洋与如潮的歌声相映成趣。李璘于20世纪90年代在甘肃岷县拍摄临水对歌的男女,每当他举起镜头,女歌手就用伞遮挡,一旁男歌手道:“浪会(10)岷县日常俚语的“浪”有闲逛、玩乐之意;“会”为“花儿会”;“浪山”即为花儿会期间大家到郊外转悠、玩乐和歌唱的行为。唱花儿,你们公家人最好不要掺和,相片放在电视上,人家两口子就要打架呢”,“浪会还抬录像机,不知录下谁家婆娘”(11)李璘:《乡音:洮岷花儿散论》,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3页。。采风工作尚未开展就遭奚落。日常遮阳避雨的花伞是参加花儿会女人的随身必备之物,一方面青年男女通过对歌交往,女人在伞下偷窥男方的表现,花伞下的女性尽显内敛与矜持。另一方面当对歌遭遇私情主题,伞作为身体的延伸,成为女性的掩护。(12)肖璇:《中国节日志·二郎山花儿会》,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9年,第118页。父系外婚制社会,“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13)李安宅:《〈礼仪〉与〈礼记〉之社会学研究》,2005年,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第60页。,西北洮岷地区汉族和藏族女性不可在娘家门前的歌场上对歌,因为如碰见自家兄弟,双方会很尴尬,伞又有了遮面避嫌的作用。传统社会的女性隔绝于地方节日公共时空,只是“唱花儿”的诱惑难以抗拒,胆怯羞涩的女人们生怕被熟人撞见,把整个身体埋在了花伞下,将声音和面孔隐藏在了花伞背后。
婚姻家庭的禁忌和规范作为重要文化现象,时常体现在对歌过程和行动伦理中。两性对歌不以婚姻为界线,但婚姻制度划定了参加聚会对歌人群的范畴,以及可对歌的“对子”——两性对歌组合,他们是“唱”“应”的固定搭配,或对歌中虚拟恋爱的对象。一般而言,越往差序格局(14)费孝通以差序格局来概括中国社会根据生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社会关系的图景。在他看来,以“己”为一枚石子,生育和婚姻结成的网络如同石子丢入池塘形成的同心圆波纹,一圈圈推出去,越推越远,越推越薄。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5页。同心圆的外圈越是对歌最安全的人群范围,只是不同族群的婚姻生育制度体现了不同差序格局的远近秩序,直接影响了可对歌交往和搭伴结群的对象。以兼具对歌传统和双居制(15)双居制,指的是在中国南方少数民族传统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女子婚后常住娘家的习俗,苗族人称“坐家”,惠东地区称“不住家”,等等。学者一般将其称为“不落夫家”。的苗族和壮族为例,外婚制的壮族和交表婚的贵州苗族均规定同寨人之间不可对歌。苗族的平表同性亲属(16)平表存在于同性同胞的子女之间,交表存在于异性同胞的子女之间。平表和交表作为人类学亲属称谓体系的一对分析概念,常常与联姻之间构成逻辑上的内在关联,两者分别对应着“姨表婚”“姑舅表婚”,比如苗族交表婚强调的是平表直系为不可婚亲属范畴,但交表之间可以构成姻亲的关系。而可婚和不可婚的亲属关系影响着两性对歌的组队和对手的分类。可以搭伴参加歌会,但对歌须在具有交表姻亲关系的异性间展开(17)简美玲:《贵州东部高地苗族的情感与婚姻》,贵阳:贵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5页。。壮族遵循的则是平表和交表异性间均不能对歌,但同性、非姻亲间可结群参加对歌(18)不仅平表和交表的同性亲戚之间可以组队结伴、甚至母女也可结伴访村参加对歌。。贵州南部侗族从“近地缘内婚制”的“同村同姓不婚”,转变到“同村同姓开亲”的破姓婚姻(19)近地缘内婚,是指南部侗族普遍存在的村落内或与临近村落的内部通婚制度。侗族经历了“同村共姓不婚”到“同村同姓开亲”的转变过程,谓之“破姓婚姻”。详见杨晓:《嘎老音乐传统与侗人社群认同:以贵州省从江县小黄侗寨为个案的考察与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第223—225页。,则是以具父系四代血亲家庭关系为对歌禁忌,而同村父系四代血亲之外的未婚男女均可展开对歌。对歌非未婚男女的专利,情歌对唱也未必导向现实的恋爱和婚姻,中老年人以歌养心,许多族群的已婚男女可以与不同村落非婚姻圈的人对歌。
差序格局是一种社会结构特征,也是“以‘己’为核心的血缘与地缘的社会关系分类”(20)周飞舟:《慈孝一体:论差序格局的“核心层”》,《社会科学文摘》,2019年,第5期,第55页。。已有的民族志资料显示,在壮族“同俗同歌不同调”的对歌传统中,曲调、组合方式表征传统社会的通婚与互惠交往圈(21)“同歌同俗不同调”,是指对歌曲调差异表征着社会交往圈和以地域为单位的社会关系缔结,即便是同一族群的对歌也可能形成歌词和歌俗类似、但曲调迥异的地方音乐。肖璇:《同俗同歌不同调:中国两性对歌的共享与差异》,《中国音乐》,2016年,第2期,第113页。,侗族的“果布冈”“相度”“为也”的对歌传统也建构着家庭、同寨和地缘寨际间人与人交往的有序时空。在血缘与地缘结合的乡土社会,除了两性亲密关系缔结,对歌是个人社会化的中介,人们于对歌交织的集体生活之网和纵横的十字差序格局中“推己及人”,在不同人群中锚定与自己结伴对歌与交情的对象,并借由公共场合的对歌,青少年熟知亲亲、尊尊、长长和男女有别的秩序原则,学习超越居住地两性互惠交换的对歌交往。
门板与花伞又不断提醒我们对歌时空所蕴涵的性别和要遵守的规则。“白天和晚上唱的不一样,白天唱的内容比较风流,称为日歌。晚上唱歌要讲究辈分,有一定忌讳,称为夜歌。”(22)受访人:陆某某,采访者:肖璇,时间:2012年1月27日,地点:广西平果县陆某某家中。老人是日歌的主体和对歌活动的积极组织者,但在两性日、夜对歌以及野外、室内的两两相对的时空维度中,情歌对唱一定要避开老人。白天年轻人到广阔的野外对歌,双方对歌很快从“相遇”进入“交情”,且有些日歌有反叛传统婚姻伦理的内容,为了避免“戏谑轻薄而忘敬”,有些族群有专属于白天的情歌,这种歌既不能在夜晚唱,也忌讳在隐蔽的地方对唱,只能白天在远离村庄和长辈视线的非私密场合唱。(23)罗汉田编撰:《平果壮族嘹歌·日歌篇》,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1页。夜晚青年人移步本属于老人和孩子的空间,人们常常选择褒(赞)歌或历史叙事长歌,夜歌后半部分才真正展开交情歌的对唱。遵循男女有别、长幼有序原则,各族群有不同的夜歌对唱礼俗。比如苗族的交情歌必须在天亮前结束,为的是男性歌者不在清晨遇到女性歌者家的老人和弟兄;壮族和西北洮岷地区汉族的女人不能在父亲和丈夫的家人面前对歌;不落夫家的贵州东部高地的苗族姑娘生孩子以后就获得老人的身份而不能参加对歌。饭养人,歌养心,壮族族群男女结婚生子后仍可以自由对歌,只是一般不参加跨日超长时间的夜歌对唱,壮族老人夜歌的缺席显然也有着年龄体力的考量。虽然对歌歌俗各族群有异,门板与花伞背后的“礼不逾节,不侵侮,不好狎”,男女大防、长幼有序等等的对歌行动伦理均有着儒家礼俗传统的影响。
(二)对歌的礼俗与族群互动
中国古人很早就有了自然环境为音乐风格之要素的文化生态观点。先秦以“风”作为民歌的总称。汉代《说文解字》提及“汉地理志曰,凡民函五常之性,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24)〔汉〕许慎:《说文解字》,〔清〕段玉裁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76页。。“以歌为俗”的认知最早也见于汉代。《风俗通义》言:“俗者,含血之类,像之而生,故言语歌讴异声,鼓舞动作殊行,或直或邪或善或淫也……”(25)〔汉〕应劭撰《风俗通义》,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影印本,长沙: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2页。。对既“风”且“俗”的民歌,历代士人的阐释并不止步于此,所谓“上以风化下”“礼俗以驭其民”“以俗教安”,目的是将君子之德入化于民。20世纪初的现代民俗学家则从礼教的批判和上升的“俗”出发,分析“以俗释礼”“因俗制礼”“以俗就礼”等礼与俗的概念流动以及多种互动方式(26)胥志强:《现代民俗学中的礼俗互动问题》,《民俗学》,2022年,第6期,第116—118页。。从乡村习俗到上古道德体系和中国文明,葛兰言解读了官方和民间庆典的一致性(27)〔法〕葛兰言:《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赵丙祥、张宏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73、146页。,而在更多的人类学家眼中,野蛮人的文化是礼与俗的复合体,李安宅和江绍原于是将“礼”作为一种大于儒家伦理的文化范畴(28)转引自胥志强:《现代民俗学的礼俗互动问题》,《民俗学》,2022年,第6期,第117页。。
2014年后,“礼俗互动”研究形成的民俗学学术新动向(29)2014年起,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相继召开“礼俗互动:历史学与民俗学的对话”(2014)、“礼俗互动:近现代中国社会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2015)、“礼俗传统与中国社会建构”(2020)。2016年至今,学者们以《民俗研究》为平台发表多篇文章。,在于此概念具有的双重学术潜力。首先是学者们发现礼俗互动不仅在民间信仰、民间艺术和民间社会等不同层面存在,且在“礼”“俗”的话语与规范、分合与互动等多维度,都具有描述和分析的范式潜力;其次礼俗互动因呈现国家微整治和民间互动(30)张士闪:《礼俗互动与中国社会研究》,《民俗研究》,2016年,第6期,第14页。的超稳定社会结构而区别于西方政治(31)李向振:《礼俗互动:作为一种中国社会研究范式的可能性分析》,《民俗研究》,2023年,第1期,第80页。,又具有了建构本土学术话语的潜力。礼俗互动显现的泛礼主义亦见于中国古代音乐文献,如《左传·召公二十五年》载:“……为九歌、八风、七音、六律以奉五声”(32)〔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卷第五十一),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0年,第2108页。。当代的音乐学家考证了九歌、八风、七音、六律的形态为何(33)黄翔鹏:《“唯九歌、八风、七音、六律以奉五声”:〈乐问——中国传统音乐百题〉之八》,《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如何“保持宫系”以“奉五声”的实践(34)樊祖荫:《“奉五声”与“变五声”——“二变之音”在五声性七声调式中的作用》,《音乐研究》,2020年,第1期,第53—64页。。笔者也注意到了“奉五声”完整表述的前半句——“是故以礼奉之”,即不同地区音乐实践要以“五声”表征的“礼”为准则,这是“奉五声”的社会文化根源。从黄翔鹏等人研究雅俗乐对立层面的传统音乐,到项阳以乐籍制度和“用乐”看到俗乐和礼乐的一致性,民族音乐学家意识到传统音乐与民间礼俗的相依共生,但乡土音乐如何在礼俗中呈现?如果说“礼”为“作乐”的依据是一种内隐的礼学实践,其相对于“行乐”包含的“与谁一起唱、什么时候唱、什么场合唱”的外显歌唱礼俗则更加不易察觉,以上可见的对歌门槛作为日歌和夜歌时空转移和互换的文化习俗,以及它所形成各族“同中有异”的对歌交往礼俗,却是非音乐学专业调查者易体察到的歌唱场景。
另外,“华夷之辩”曾以“礼”为依据,只是在“礼”的正统和纯洁话语下,“用夏变夷”的文明教化无远弗届。“少数民族受汉族儒家伦理观的影响始于秦汉”(35)杨国才:《儒家伦理道德对少数民族的影响》,《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第5页。。除对歌门槛内外比如“男女不杂坐、戏谑而不忘敬”的行动伦理外,传统社会的青年男女经由对歌自由恋爱后,仍遵守“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36)〔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曲礼上》,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0年,第1241页。。有些族群在对歌通往婚姻路上,更保留了汉族“遣媒通辞、用雁送礼,执雁请问女名”(37)李安宅:《〈礼仪〉与〈礼记〉之社会学研究》,2006年,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第41页。的传统。例如在广西龙州壮族布岱族群“官郎接宝玉”婚仪中,“官郎”为媒人,“宝玉”即包着新娘生辰八字的布包子。整个过程众人以歌代言,众人除了展开入门歌、敬祖贤歌和六礼歌等(38)该族群的婚礼对歌包括入门歌、敬祖贤歌、拜堂歌、酒席漫歌、六礼歌,开担歌、交干湿钱歌、新娘拜祖歌,其中入门歌、酒席漫歌、开担歌为对歌形式。布岱族群的婚礼对歌资料由广西龙州文化馆农瑞群提供。的跨日超长仪式性对歌以外,官郎还要唱“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的汉族传统婚姻仪式六礼的内容;“歌中见礼”的对歌礼俗也贯穿一个人出生、成人、婚姻到死亡的生命历程。如《礼记》所载的“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许嫁,笄而字。”(39)同注②。对歌地区每个人在长辈允许下参与的第一次对歌就是一次成年礼,成年礼之后即被社区接纳进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比如进入青春期的海南黎族男女被长辈准入青年公房“隆闺”,获得与异性青年恋爱和对歌的机会(40)“隆闺”意为“无灶的小屋”。按黎族传统,孩子到了青春期,就不在父母家中睡觉,而须男女分开,另筑小房供其睡觉及寻偶。杨沐《性爱音乐活动研究(上)》,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第74页。。
对歌礼俗超越族群,涵化或汉化包括从中心到边缘、自上而下的制度推行,也有少数民族自觉学习汉族的文化习俗和社会构建方式。且在族群的礼俗互动中,不全然是中心到边缘的单向影响,汉族也曾部分吸收少数民族的文化。比如南北朝时期婚礼就曾吸收了少数民族的坐鞍等婚仪内容(41)王贵民:《中国礼俗史》,台北:文津出版社印行,2003年,第22页。。于是我们看到,一方面在族群间的互动与交流中,婚姻由媒人提亲、纳六礼习俗的传统婚仪在汉族已难得一见,却保留在许多少数民族的婚俗中;而另一方面儒家古礼中“婚礼不举乐”(42)同注⑦,第41—42页。传统和后来汉族地区的大肆婚礼用乐,是否又受到了周边少数民族的影响?且各族群在何种情况愿意接受和学习外来的礼俗,何种情况视自己的民仪民风为最高,而有意维持本族群的礼俗传统?对歌给人文社会学科留下了进一步探讨中国族群间礼俗互动的新视角和契机。
二、假声的匿名化与表演
我老家没有歌书,全部用假声,以前唱歌,我妈就是很风流的歌手。妈妈和奶奶还为了我吵架。因为我爸爸在隆林当干部,我妈在农村干活,爸爸几年不回家一次,我妈就晚上出去唱歌。她每天晚上都背我去,她唱歌,我在旁边睡,她们隔着门板唱,一个男的在正堂外面,女的在房间里面唱……(43)受访者:农某某,访谈人:肖璇,访谈时间:2012年3月12日,访谈地点:同车去往那坡黑衣壮调查的路上。
(一)听得见的门槛:对歌时空与声音对策
与老人和孩子处同一家屋的公开对歌有着严格的规范,门板与花伞的空间区隔因此具有“男女不杂坐”和“戏谑轻薄莫忘敬”的道德化意义。从前居住在平果县新华镇的壮族布傲支系很少在歌圩上对歌(44)笔者调查的广西平果县新安镇中桥、新华一带壮人长时间遵循夜间对歌传统,但随着社会变迁,对歌仪式小型化,这些地区的人们开始往来平果多个歌圩对歌。,男性歌者一般围坐在前堂,与两侧耳房的女性对唱,一道虚掩的门将男男女女隔开。除了遵循夜晚家屋内隔着门板对唱的传统,布傲支系的男人采用与女人同腔同调的假声对唱。所谓“一种方言一种歌”,虽然歌俗、对唱形式类似,当操其他方言的壮族人形容他们歌唱声音像猫叫时,笔者又一次体会到对歌演唱方法与曲调所建构的亚族群认同。
男女嗓音在对歌中和谐一致,向来是民间歌手的追求。无定谱定调的即兴对歌,男女歌手时常根据对方的嗓音调整自己的发声,他们耳朵分辨对方的音高和音量,极力使自己的声音向对方靠近。不同的是,西方歌剧、二重唱和通俗歌曲男女对唱中,男声既演唱舒适又听觉和谐的音区一般比女声低一个八度,而笔者调查的中国西南西北几个对歌盛行地区的人们更趋向于男女同腔同调的兼容与和谐。从器官发声原理来看,两性声带和喉头的构造不同,因男性长厚的声带特性,假声向来被认为是男声的“不习惯声区”。男性“假声化”或“女性音化”的歌唱,是有意识以“不习惯音区”演唱时,环甲肌无意识施加纵向压力,声带抻长,两片在张力下变薄的声带边缘相碰,而不充分的声门关闭,形成了“高、尖、细”高频振动的女性化声音。跨越性别的假声歌唱包括中国西北洮岷地区以“啊欧怜儿”曲调对歌的汉族和藏族族群,当地人以“扎刀令”“尕刀子音”称之,还有贵州省丹寨县苗族嘎闹支系、黎平县侗族“鸟翁”的夜间对歌,广西龙州地区以“龙州调”对歌的壮族布侬支系,闽东畲族对歌等等。从16世纪末西方阉人歌手的假声男高音到中国传统戏曲男旦的小嗓,以及现代声乐探索以“关闭唱法”和“面罩唱法”的技术获得头声的手段来看,虽然不同文化土壤造就了男声假声化的社会功能和审美差异,但均指向了男声假声化所需的演唱技术。如果说音乐的本质在于表现,匿名化的假声对歌却是以牺牲个性表达为代价,那对歌盛行地区的人们何故选择此种丧失声音个性且“不习惯音区”的歌唱行为?
发生在家宅内部的夜歌并不完全是长夜漫漫的情歌对唱。一般晚餐后主家就开始请歌,除了主人一家,家屋还坐满了前来听歌的同村邻人和外村客人。上半场歌手们一般选择所有人都适合听的褒(赞)歌、叙事歌或历史长歌,只有当大部分听歌者回屋休息、老人和孩子们睡去,双方才展开两性交情的对歌。在壮族自治区北部称此歌为“文歌”,壮族自治区南部称之为“诗跟”。除了帮工和节日对歌,传统壮族社会夜歌有时源于某村的小伙子对其他女性歌唱群体中的一位有意思,男性小团体组织了一场属于年轻人之间秘密的夜歌。上半场赞歌和叙事歌的对歌结束后,其他伙伴识趣借故离开,家屋内的年轻人以假声小声地对唱只需两个人懂的情歌。一假到底的歌唱没有明显的换声区与换声点,隐藏了性别辈分、年龄和音色等声音的个体特征,如虚拟网络的匿名化交往。对假声的这种遮蔽和掩盖的功能性解释也常见于平果新安壮族、贵州省丹寨县苗族和黎平侗族的民族志中。
同是假声对歌,西北洮岷地区的花儿歌手选择唱法时相对灵活。他们往往根据白天和夜晚、家屋和野外的时空变化,在真声位置的假声、纯假声和真声的三种声音属性中转换。在“时空—声音”的选择框架中,女性的声音性别较为固定,但男性可选择超越社会性别的“女性化音”,也可选择利于野外传播和震撼听感获得的“男声假声化音”或称为假声位置真声唱法。如甘肃洮岷地区的人们在野外劳动和山间以“扎刀令”对歌时,他们大多采用岷县人称为“高尖音”的假声位置真声唱法展开歌唱,此种“假而不虚”的声音,有着结实的真声音色和高亢凌厉的听感,符合人们对男女嗓音的性别想象,且利于野外劳作隔空对唱的声音传播,以及吸引人墙、形成大的歌摊的节庆公共场合的对歌。而面对面对歌人们有时也采用真声,当地人称“平音”。野外采取何种方法视空间特点及歌手当时的状态而定,“应和方”一般紧随请歌方的唱法,以形成和谐的对歌声场。岷县花儿对唱为一种“对起要对罢”的竞技游戏(45)“对起要对罢”指的是对歌作为一种竞唱游戏,意味着歌手接受挑战之后需遵循平行、对等和持续性原则。肖璇:《中国节日志·二郎山花儿会卷》,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9年,第246页;肖璇:《在歌唱与游戏之间》,《民族艺术》,2013年,第1期,第125—129页。,其中唱法也是对歌竞争的因素之一,如果一方以“高尖音”起唱,另一方以“平音”对过去,在对歌游戏中将被视为战败方。但一旦转到夜晚家屋内对歌,人们一般采用“低音”对唱。只是“低”非音域概念,而是音量大小,当地又称小唱,低音就是假声演唱位置的“虚声”对歌。结合既往的不同族群对歌民族志资料,首先,全假声听不清男声和女声、年龄几何,谁家姑娘(女人)在和小伙子(男人)对歌,规避了老少同一家屋的尴尬;其次,假声遮蔽真意,因为在某些以交表、村寨内婚为优先婚姻的族群对歌中,假声匿名的个体是处于媒妁婚下、已订婚或不落夫家的男女青年(46)朱腾蛟:《假声歌唱与两性相与:贵州平架嘎琵琶个案调查研究》,《中国音乐学》,2016年,第3期,第136页。,对歌制度化谈情导向的私奔婚,抗拒了族群主流的婚姻理想,为对歌自由且婚姻自主的个体情感释放寻找到了出路;再次,天生好嗓音的歌者在对歌群体中总是占少数,但假声可掩嗓音之不足,且声带局部闭合的全假声歌唱技巧也可让人在气息少、声带“轻压力”的状态下工作,避免长时间真声歌唱给声带带来的水肿、充血和疲劳。低耗的全假声歌唱,聚散依依的跨日超长持续性两性对歌在中国多个族群中发现。
(二)声音面具与对歌的双重表演
在萨利希人斯瓦赫威面具研究中,列维-斯特劳斯延续了神话与社会制度关联的结构主义路径,当他将“物”的造型艺术进行语义学分析时,可见的面具开口说话(47)列维-斯特劳斯以双关语“面具之道”(La Voie des Masques)起书名,因为法语“la voie”(道路)与“la voix”(声音)是同音,他言外之意就是“面具是发声的”,因为斯瓦赫威的面具承载着神话情节、族群互动和道德伦理等诸多信息。〔法〕克罗德·列维-斯特劳斯:《面具之道》,张祖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页。。除了可见的物和行为等因素,人类往往依靠神话和音乐等口述传统,在符号和声音制造的想象共同体中结群。对歌求偶促进族群繁衍和维持,一旦情欲泛滥即对公共道德和社会秩序构成挑战。一边是对歌中理想的完美情人,一边是与歌场一墙之隔的老人与孩子。集体歌唱兼顾婚姻制度、交往伦理以及情感的抒发,可听的声音露出可见的面孔。
真声展示自然之我,假声产生于两性间互动。跨越日常交往和非日常艺术的表演理论,20世纪70年代就已受到戏剧、社会学和民俗学等等学科的青睐,民俗学口头程式和表演理论侧重于交流,社会学和女性研究则侧重社会互动中的表演,而以非日常音乐活动为对象的民族音乐学恰恰对它的关注较晚。在欧文·戈夫曼等社会学家展开的现象学社会分析中,社会行为由他人期待决定,人们以符合社会角色的要求行事(48)〔加〕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冯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2页。。个人的行动向来有社会关系维持、社会信任获得等方面的考量,即“镜中之我”的理性驱使。在公共的两性对歌交往和互动中,刻意去做什么以求“知礼懂礼”“以礼行事”的社会评价未必是大多数人的选择,但不尊重老人、不懂对歌礼数一定会成为集体生活的意外事件。维持一般社会交往的体面,就意味着人们要遵循可对歌的对象、对歌时空等等的行动伦理,以及老人面前不唱情歌,屯里有人去世禁歌数月,如果对歌人群中有人戴孝则需在室内挂白布等等的对歌禁忌。理想型人格和社会期待“缺席地在场”,导演和控制着参加对歌的每一个人。
真声隐于假声之下,对歌在性别和嗓音之共性下展开,但门板和音声遮蔽下的表演,一旦泄露就有难堪的危险,恰如社会互动表演中“前台与后台”“假声假扮”与真实的两个世界。男女以歌相交,除了相互欣赏即兴创编能力外,能与心中“人靓歌美”的完美歌者对歌是每个人的愿望。外村人寄宿在村子里,晚上主家邀请本村的男青年到家屋来与外村人对歌,“村里面有人来了,我们去唱歌吧”,一群人往主家家屋走来,渐近家屋后他们驻足开唱,里间的女孩静静听着屋外男孩持续不懈地邀歌,只有等到女孩开口应唱,男子才能进屋。跨日对歌的夜歌长大,双方时常唱到天亮仍不知对方真实容貌、年纪几何,产生不少夜间对歌趣闻:农某某所在村庄的小伙子有一天邀请外村的年轻女子来村里唱歌。那天大家酣唱到天亮仍未有结束的意思。作为小学教师的农某某需清晨赶路到村小上课,女方知情后立即进入到分别歌。歌落音散,农某某走出堂屋,身披曙光走上田埂。女子禁不住冲出隔间,跑到家屋外一睹与自己一夜对歌的男子,引来众人哄笑。农某某因此看见与自己一夜对歌的女子,心里颇感失落。原来村里人下帖请的是年轻女子过来对歌,年轻女子不精于编词,为了不失村誉,她们带上本村对歌经验丰富的年老的女歌手一同前来对歌(49)受访者:农某某,访谈人:肖璇,访谈时间:2012年2月10日,访谈地点:农某某家中。。
与目前民族音乐学以表演为中介、体验为中心、关注的音乐行为过程(50)萧梅、李亚:《音乐表演民族志的理论与实践》,《中国音乐》,2019年,第3期,第5—14页。不同的是,早期音乐学家如赵如兰等人借用民俗学的表演理论来阐释花儿歌手与听众之间的微妙关系(51)赵如兰:《莲花山花儿会:关于表演的环境研究》,转引自柯杨《诗与歌的狂欢节:花儿与花儿会之民俗学研究》,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50页。。后又相继有民俗学研究者运用表演理论展开了湖南盘瑶坐歌堂(52)郑长天:《瑶族坐歌堂的结构与功能:湘南盘瑶冈介活动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99—163页。、云南剑川白族对歌口头艺术研究(53)朱刚:《作为交流的口头艺术实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97—114页。。而在民俗学表演理论话语之外,以性别对立为第一原则的对歌,更接近非日常和虚拟关系建构的表演。比如日歌是情人见面唱的歌,但对唱日歌的人不一定是情人。白天对歌由男性独白表演“浪歌”到双方“和歌”,当对歌“对子”一旦形成,即使初见的陌生双方,也需很快进入由浅入深的两性交往角色中。如南部壮族的崇左部分地区对歌由“诗面新”(54)男子搭讪时唱道:“陌生面人肉如花,问妹生人哪里来,阿妹陌面哥生面,如同树木长各山。”女子此时如果有意,就假装“索花”并应唱:“走路来见花枝红,妹拿竹竿想去摘,哥若有心给一支,拿回挂在神桌前……。”开始,进入“初交”“试探”(55)男歌手唱道:“初次相交初次交,阿妹好比鸟吃果、你有旧友未分断,一边又去找新欢……。”,到“正交”(56)女歌手唱道:“阿妹痴心来交你、仿佛青蛙盼露水,一天不见阿哥面,心痛如同失父母……。”,直至“诗成婚”“诗交死”的情感层层推进,两性在歌声的伪装中展开从初见、相恋、分别的公开调情。真实和表演世界的区别在于,佯装和虚拟的恋爱不必导向实际的婚姻和恋爱。两性对歌更不乏戏剧化表演桥段,如龙州壮族“乃桌歌”就有“埋菜埋情”和“芭蕉戏情”,人们借助芭蕉叶、扣肉等道具,完成请歌、应唱等仪式性对歌(57)“埋菜埋情”和“芭蕉戏情”,指的是壮家族对歌“戏情歌”的两种方式:“下芭蕉结”和“埋菜”。当主家把芭蕉叶打成四方结放在酒碗、汤碗等容器中,则暗示有人有意与客方对歌交朋友,或者想延续对歌的时间深入交往,此时接受芭蕉结的客方要以歌的形式唱出心中所想;如主家在客方盛米饭的碗中埋下以红丝线串起的扣肉,“埋菜”意味着“埋情”,暗示主家待嫁女儿看上客方的小伙子,欲在对歌中进一步增进了解。肖璇:《夜歌与乃桌歌》,萧梅主编《大音》(第十一卷),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6年,第101页。,而仪式的本质就是表演。人们借助门板花伞和声音佯装,遵循对歌的程式和套路,在超越日常的诗化语言和曲调旋律中,在歌词互押、唱法协同和多声协作中展开对歌,恰如演员在舞台上对搭互动,完成想象和虚构世界的创造(58)傅谨:《论对搭在表演中的重要性》,《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2022年,第3期,第18页。。
假声模糊声音性别、消散声音个性,在集体对歌的社会生活时空中,无论是长幼有序的行动伦理,还是媒妁婚姻下的个体情感抒发,假声都充满礼的精神和“镜中之我”的社会表演。对歌能作为群体交往的方式在于歌中见俗,行中有礼,得益于对歌社会互动和伪装公开谈情的双重表演都在一方礼俗的注视下。道德人类学常将自由看作个人根据社会道德自主行动的一种能力,是因为每个人都具有与善良和好德性相联系的能动性,在自由与道德、人性流露和情感控制之间,焕发出美与善的光芒。
结 语
对歌因门槛和禁忌而存在,两性区隔和声音的匿名化源于情欲羞愧的人性化自我和社会化自我的距离。情欲是自然的律令,但若没有文化的调谐,情歌在公共生活中便没有足够的合法性。本文所述的对歌门槛为可见的“物”的屏障,它因让两性在男女有别和长幼有序的范畴对歌交往而被认为是好的对歌要素之一;而同腔同调的假声歌唱弱化音量、掩盖性别,跨越的是道德和技术的双重门槛。门槛的隔离产生神秘和想象,此时对于即兴歌唱而言,感觉往往比理性更为有效。农某某失望于眼前不是对唱时心里想的那位女子,只是当眼睛和耳朵被遮蔽后,门槛制造的完美情人想象激发了口头传统的创造力,让即兴歌唱源源不断地持续,人们沉浸其中共赴一场完美的对歌之旅。
对歌礼俗兼顾情感与理智,与交互歌唱中自由与约束并置的乐和诗的运用相得益彰。文化选择和维持往往要与社会制度相协调适应。以礼抑欲,门槛昭示了对歌为社区允许的两性正统交往,社会也将两性对歌制度化地纳入正常秩序,在“礼”与“浪”(59)“浪”为“玩耍”的地方性概念,偏重于非理性的、人的本能和情感需求。之间隔离出一个两性情感交流的声音世界,个体也因此抒发着对未来生活的向往。在两性区隔和模糊共性的歌唱面纱下,伪装的声音来自情感与规范间的张力,而野外苍劲有力的假声利于公共生活表演,全假声省力的发声技巧维持着跨日超长时间的对歌传统。因此门槛不仅是协调婚姻家庭、社会制度和个人情感抒发的策略,且为一种音乐文化的传承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