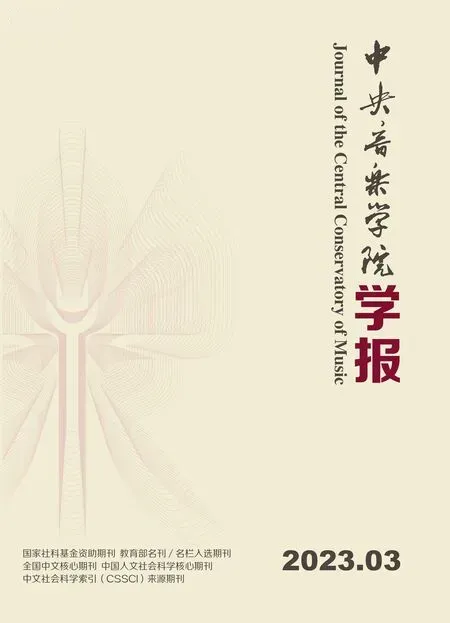“第三空间”下的旅游音乐表演
2023-12-21张林
张 林
近年来,与音乐表演以及文化建构相关的话题逐渐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不过,学界更多的是从“非遗”传承与保护的视角去看待这些现象,一般将其定位于官方、学者、草根阶层的共谋,讨论偏重于局内人、主位认同视角。但是,一次偶然事件促使笔者对此重新思考。
2017年,笔者在巴厘岛旅游区拍摄一个乐队的表演时,素未谋面的乐队女主唱突然转过脸对笔者演唱流行歌曲《小薇》,而笔者也非常自然地被带入了表演的语境跟着一起演唱。此时,因同时具有了旅游者与表演者的双重身份,笔者的身份变得比较模糊。如何从理论上对这种表演文本进行解释?这也是困扰笔者多年的一个问题。近些年来,由于文化与旅游结合的加强,许多音乐表演多少都受到旅游因素的影响,但当下国内从旅游角度对音乐表演与文化建构的研究尚不够深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没有从新的视角去分析已经有别于传统音乐文化的当代旅游音乐表演。为此,笔者先对当下旅游音乐表演研究中遇到的困境进行分析,再借用“旅游凝视”理论并从“第三空间”的视角进行探讨,或许会将旅游音乐表演看得更为清晰。
一、旅游音乐表演研究的困境
一般而言,传统音乐尤其是民间仪式音乐、节庆音乐具有鲜明的地方性特征,作为“小众”音乐文化持续了千百年。随着它们陆续登上表演的舞台,曾经仅为少数局内人享有的文化逐渐被更多的人所了解。同时,一些断裂的传统音乐经过重新建构,也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不断上演。当然,这些可能仍然无法满足当今社会需求,于是,一些“发明的传统”顺理成章被搬上了舞台。它们不仅逐渐步入城镇化进程,还多少享受到当地保护。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小众”音乐文化便趋向于大众化。
与旅游结合是“小众”音乐走向大众化的重要途径。因为旅游表演的需要,许多地域性传统音乐走出“闺门”而登上旅游音乐表演的舞台,同时,其也经历了一个“去语境化”与“再语境化”的过程。当它们从一个空间进入另一个空间,从一个自给自足的“熟人”社会走出来展示,自然会经过一番修饰。当然,它们还经常以“非遗”的称号向外界展示自己历史积淀之深厚。针对这种情况,学界曾从本体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角度进行过讨论,但是,旅游音乐表演具有鲜明的混杂性,很难通过地方性——外来性、大传统——小传统、地域性——跨地域性、主文化——亚文化等现有诸多分类方式予以清晰解释。于是,从主位视角去分析为何当地人会使用这些音乐便成为学界的一个研究方向,由此文化认同自然而然地成为近年来受到关注较多的话题。
不过,笔者认为从文化认同这一主题进行研究亦存在不足之处。尽管学界认识到认同的阶序性特征,并将其细分为族群认同、地域认同、民族认同、历史认同、宗教认同、国家认同等多种层次,但除了主文化所反映出的国家认同外,对其余认同的研究仍然主要以被研究群体的传统音乐观念为依据,而不能体现被研究群体传统属性的音乐则很难被纳入研究的范畴。一如前文提到的流行歌曲《小薇》。对于在旅游音乐表演中使用的相隔千里之外其他民族、地域的音乐或是大众耳熟能详的流行音乐,研究者很难从曲调分析中发现其有何重要价值。因此,在过去的仪式音乐研究中,这种情况在“核心——中介——外围”的分类中多数被当作可变性、可替代性较强的外围音乐进行处理,一般不做深入分析。那么,这些音乐在旅游表演中究竟有没有意义呢?实际上,过去的研究并没有更多从旅游的角度认识这些问题。此外,一般而言,完成一次舞台表演需要表演者与观众共同参与,而完成一次旅游音乐表演,表演者和旅游者两类人群缺一不可。亦即,旅游音乐表演的整个过程实际上是由建构者、表演者、旅游者共同合作完成。但是,之前的研究似乎对旅游者的影响关注不足。
另外,除了旅游景区,还有一些民俗活动虽然发生在相对原生的环境下,但和旅游结合仍然较为紧密,在表演时除了面对局内人,还要面对旅游者、记者、学者等不同身份的局外人的凝视。这种情况下,当旅游者这一层身份进来以后,他们对音乐表演是否产生影响?事实上,“非遗”音乐文化搭上旅游的列车不免要面对旅游者的凝视,表演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协商行为,从而产生多个类似但不同的表演文本,只是学界对于此类问题较少予以关注。针对此现象笔者认为,借用“旅游凝视”理论,从“第三空间”的视角切入方能看清诸多音乐的文化身份,以及各方对旅游音乐表演及其文化建构产生的影响。
二、“第三空间”理论与旅游音乐表演研究的适配
哲学中认为,时间和空间是物质运动的存在方式。相比于历史学研究范畴的时间,空间一般属于地理学研究范畴。在对人类历史和社会进行阐释时,空间长期淡出主流人文社科的视野。而随着研究范式地转移,空间逐渐成为人文社科重要的内在理论视角,学术研究在“历史——社会”二元基础上加入了“空间”概念,形成“历史——社会——空间”三元的研究转向。1996年,爱德华·W.苏亚(Edward William Soja)在《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中梳理了第三空间的性质,给人文社科各领域带来了新的视角。
苏亚认为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可能是首位洞察到第三空间的学者。列斐伏尔指出了三种不同的空间,即“空间实践、空间的再现、再现的空间”(1)〔美〕爱德华·苏亚:《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陆扬、刘佳林、朱志荣、路瑜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83页。。以此为基础,苏亚将“空间实践”重新界定为第一空间,是物质的空间,如建筑、剧院、音乐厅、服饰、表演等,它偏重于“视觉”,是最易被“旅游凝视”的对象。苏亚称“空间的再现”为第二空间,是想象的空间,属于精神层面,可以是旅游者凭借经验或者通过媒介宣传而产生的对旅游地的印象,也可以是国家空间、民族空间、地域空间、宗教空间等与文化认同相关的认识。(2)由笔者参考众多相关文献根据理解梳理而成。
苏亚的第三空间与“再现的空间”类似,他认为“第三空间和列斐伏尔的那最具包容性的社会空间概念都包含三种空间性——感知的、构想的与实际的,谁也不具有内在的、先天的优先地位。”(3)同注①,第87页。第三空间拆除诸如主体——客体、物质——精神、中心——边缘等二元辩证的藩篱,不仅将真实与想象包含在内,又将二者融合并超越生成一个实际的社会空间。其外观和意义摒弃了二元对立,依靠多方协商而成,并具有转换生成新的外观和意义的潜能动力。正是由于第三空间具有“协商”的特质,与“旅游凝视”理论具有暗合之处,才使它具有了解释旅游音乐表演可能性。
1990年英国社会学家约翰·厄里提出(John Urry)的“旅游凝视”(tourist gaze)理论是旅游人类学研究的重要理论之一。初期,有些学者认为旅游者是主动而非被动、是肉身的多感官体验而非以视觉为中心的,而厄里的“旅游凝视”理论偏重于视觉感受,导致了身体缺席,具有局限性。所以,后来一些学者就从“表演”的视角对旅游文化进行研究,因而产生了旅游研究向“表演”的转向。之后,厄里“旅游凝视”理论的概念和内涵也有所拓展,不单指“凝视”这种视觉方面的动作,而是一种与旅游相关的欲求、动机、行为的融合以及抽象。(4)王宁、刘丹萍、马凌等编著:《旅游社会学》,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13页。当今,学界已经总结出了多种凝视类型,既有游客凝视,也有当地人凝视(同义词还有“东道主凝视”“反向凝视”)、专家凝视、隐形凝视、双向凝视。(5)吴茂英:《旅游凝视:评述与展望》,《旅游学刊》,2012年,第3期,第107页。可以说,对旅游文化的研究已经涉及到旅游场域几乎所有的文化身份。
所以,凝视除了视觉之外,更隐含着通过观察、揣摩对方需求以更好地行动起来进行相互适应的含义。因此,在旅游音乐表演研究中,凝视与表演就具有某种暗合之处,二者都讲究通过多方的亲身参与实践来审视文化的互动与生成。因为多方的凝视,才有了为适应彼此需求而产生的表演文本。除此之外,国外表演理论对旅游者——当地人、主人——客人等二元对立思维进行了反思,强调表演生成的空间性和地方性,论及了生产消费涉及的协商,并促成了旅游表演的不断生成。在笔者看来,这已经涉及到第三空间的研究。
第三空间为旅游音乐表演的研究打开了一扇窗户。不过,虽然苏亚打破了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在包含并超越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的基础上,从亦此亦彼的角度思考第三空间,但是,他并没有给第三空间一个明确的界定,只是畅想了其无限开放的可能性。这也许是虽有少数从事旅游学研究的学者涉入(6)阳宁东、杨振之:《第三空间:旅游凝视下文化表演的意义重解——以九寨沟藏羌歌舞表演〈高原红〉为例》,《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1期;杜彬、李懋、覃信刚:《文旅融合背景下旅游第三空间的建构》,《民族艺术研究》,2020年,第3期。,却还较少被音乐学学者所关注的原因之一。
为更好地理解第三空间的特征,笔者对此先做一下界定,下文再详细分析其特征。笔者认为,对于旅游音乐表演而言,第三空间是在多方相互凝视下,建构者、表演者与旅游者互为主体、互为他者,从而打破了“中心——边缘”“我者——他者”“主体——客体”“全球——地方”“传统——现代”等二元模式的类分,进而形成的一个多方相互协商、合作的音乐表演空间。第三空间不只是地点的变化,还包括因各种碰撞、协商、交融而带来的身份变化。其表演生成的音乐文本具有差异性、边缘性、时空并置等特征。
三、“第三空间”下旅游音乐表演的若干特征
尽管苏亚没有给第三空间一个明确的界定,但他通过梳理蓓尔·瑚克斯(Bell Hooks)、安妮·弗蕾德堡(Anne Friedberg)、爱德华·沃第尔·萨义德(Edward Wadie Said)、霍米·巴巴(Homi K.Bhabha)、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等人的研究,进而说明了第三空间的一些特征。这在打开无限想象的情况下,也为从第三空间视角分析旅游音乐表演提供了理论依据。
(一)差异性
在论述第三空间的若干研究中,苏亚曾认为萨义德通过对殖民主义空间实践及相应表征的批判,解构以“想象地理学”为基础的各种东方主义二元对立,从而打开了后殖民主义空间,具有了第三空间的特征。同样,在对“历史主义”批判中,萨义德力图解除普遍历史主义塑造的中心,超越西方社会与亚洲社会的二元对立,使边缘群体(这里主要指东方——笔者注)具有自主意识。(7)〔美〕爱德华·苏亚:《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陆扬、刘佳林、朱志荣、路瑜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76—180页。其中主要涉及到差异性问题。
萨义德论述了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差异性建构。西方带着发达社会的优越感,通过各种方式、甚至想象并创造一个与西方不一样的东方。东方亦被想象成浪漫的、异国情调的、风景秀丽的,或低级的、落后的、怪异的形象。(8)〔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49页。总之,在这一过程中东方成为被表述、被想象的对象,是西方社会对历史发展的一种回望。萨义德对这种东方主义(Orientalism,或译成东方学)进行了批判。另外,厄里在对“旅游凝视”的论述中,指出其性质之一是“反向的生活性”,认为“差异性”是定义旅游的关键,表现在人们离开自己日常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去异地凝视不同的事物或景观。(9)王宁、刘丹萍、马凌等编著:《旅游社会学》,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12页。显然,通过文化接触而形成文化冲击是旅游者主要目的之一。
在中国,由于与外界的凝视对接,当地人也按照外界所描述的形象进行了他者化建构。除了地域性音乐文化建构外,各少数民族的族性音乐文化建构中这种特点更加鲜明。由于少数民族多生活在边远地区,在进行民族识别时大多还保持着相对滞后的生产生活方式,因此,相比之下少数民族具有了“内部东方主义”的一些形象。许多情况下,对于广大旅游者来说,民族旅游也是一个了解其他民族文化、满足猎奇心理的理想场所。而许多少数民族地区为了迎合旅游者的这种凝视,进行“自我东方主义”“内部东方主义”的旅游文化建构,甚至自己虚构一些形象,使民族旅游不仅充满原始、神秘、野性的文化想象,也有单纯、温婉、多情、能歌善舞的少数民族姑娘的唯美形象。
如据杨民康的研究,20世纪中叶出现的布朗族“新[索]”(情歌)与传统风俗歌“老[索]”(拜年歌、佛教舞蹈歌)本非同一艺术品种,经过1964年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之后,随着“新[索]”与外界接触机会增多,进而被评估和改造进入到一个他者化的进程,至20世纪末已经在布朗山寨广泛传播开来。但经过“非遗”保护的纠偏,该族群内部又有了新的认识,将“新[索]”冠以“拜年调”(“新[索]”属于情歌,不属于真正的传统,于是当地人将“新[索]”冠以“拜年调”之名以彰显这一文化具有“原生性”特点——笔者注)之名参加原生态民歌比赛并在旅游表演中接受旅游者的凝视,从而形成了中国少数民族中比较常见的“内部东方主义”现象。(10)杨民康:《云南布朗族风俗歌[索]的变异过程及其异文化解读》,《中国音乐学》,2011年,第1期,第67页。内部东方主义不只是中国独有,在其他国家也有存在。如过着采集狩猎生活的南非昆桑人常被认为是原始人的典型,但一些资料显示,他们实际上曾经生活在富足的环境中,之后为了发展旅游被迁至环境比较原生的卡拉哈里沙漠中生活。(11)〔美〕丹尼逊·纳什:《旅游人类学》,宗晓莲译,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2页。这也是为了迎合旅游者的凝视而做出的“内部东方主义”行为。
多数人都有历史情结、怀旧心理,因此,旅游者除了去发现其他民族文化,还有一种去寻找往日时光的情结。他们不仅想在现代社会下体验传统,在人为的建构外发现“原生”,还想在残缺的现实外捕捉唯美,在喧嚣的生活外寻找宁静。这种心境体现了追求我者与他者、历史与当下、传统与现代的差异体验。为了迎合旅游者的这种凝视,当地人进行了返璞归真的表演建构,尤其在民族旅游上,在“内部东方主义”的思维下为游客建构了一个具有“异域风情”的他者。这是多方凝视下协商的结果,这种差异性建构使旅游音乐表演具有了第三空间的特征。
东方主义之所以存在,其根源在于西方中心主义,东方只是被描述的对象,而西方才是叙事的中心。实质上,在论述东方的时候,东方自身反而是缺席的。东方主义是西方中心主义叙事下的产物,萨义德借用其回应的是西方中心主义,而不是假定的对象——东方。可以说,萨义德对东方主义的批判是想通过对既定学术权威的挑战以达到对其进行重新解释,其实质是对中心以及传统力量的反抗。而以“内部东方主义”思维进行旅游音乐表演时,行动者是局内人,其对抗的主要指向并非传统,而是现代,是在与现代化以及全球化的对抗中寻找自己的身份定位并争取更多的生存资本。这类表演中蕴含着的“内部东方主义”与历史上的东方主义最大的不同在于,东方主义只是西方的主观建构,是强加给东方的一种地理和历史想象,而“内部东方主义”表演与建构并非自说自话把意志强加给对方,而是面对旅游者凝视下的协商行为,是一种多方共同建构的结果。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只有从第三空间下去观察才能了解其表演的实质。
(二)边缘性
就透露出具有第三空间的意识来说,蓓尔·瑚克斯与霍米·巴巴对文化的理解有相通之处。蓓尔·瑚克斯在《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FeministTheory:FromMargintoCenter)中透露出对第三空间的理解。“我们既从外面往里看,又从里面往外看。我们既关注边缘也关注中心。我们二者都了解。”(12)转引自〔美〕爱德华·苏亚:《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陆扬、刘佳林、朱志荣、路瑜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26页。这种边缘性具有彻底开放性,对于新的创造具有无限可能性,具有了第三空间的意识。霍米·巴巴将第三空间(13)据爱德华·苏亚说,他在《第三影院问题》中《理论的责任》一章看到霍米·巴巴第一次使用“第三空间”一词。参见〔美〕爱德华·苏亚:《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陆扬、刘佳林、朱志荣、路瑜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82页。定义为一种“生产性空间”,他认为,虽然这一空间中含有多元的文化,但其并非是用文化相对主义观点将文化看成多元性共存,并依据每一种文化存在的差异而分门别类地放置,而是要超越这种文化相对存在的认识,用一种新的混杂性的身份进行重新阐释,这种混杂性构成了文化的“第三空间”,这也与瑚克斯的边缘性第三空间相呼应。(14)〔美〕爱德华·苏亚:《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陆扬、刘佳林、朱志荣、路瑜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80—181页。这也侧面说明第三空间是具有创造性和可能性的空间,具有文化再生的能力。由于具有开放性,第三空间的文化将永远处于一个未完成状态,而就旅游音乐文化而言,边缘性对于建构者、表演者、旅游者有以下不同特征。
1.建构者和表演者所用音乐的杂糅
对于建构者与表演者来说,边缘性体现了所用音乐文化的杂糅,这与霍米·巴巴的第三空间高度契合,他以混杂性理论为基础,指出“混杂性指向一种既非内在文化又非外在文化的情境,它是一种处在边界线上的第三空间,站在这个边界线上,一个人同时既在内又在外。”(15)周宪:《文化研究关键词》,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22页。霍米·巴巴想通过混杂性构筑第三空间,进而消解文化本质主义,但他也指出了文化发展的本质,即几乎没有单纯的、一成不变的族群文化。以此来观看当今的旅游音乐表演,可以发现其动态的建构过程与杂糅的实质,以及边缘性特点。
新宾满族与汉族在传统婚俗仪程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如都有打下处、憋性、秤挑盖头、坐福、跨马鞍、开脸、梳头、回酒等环节,这是不同族群之间高度涵化的事实,已经体现了混杂性特点。如今,重构之后的满族婚俗用乐,不仅使用满族秧歌、满族歌舞和用满语演唱隐喻萨满祈福的《阿察布密歌》,还使用汉族吹打乐《抬花轿》。其中,满族秧歌、满族歌舞表演虽然戴上了满族的帽子,但其表演中所显示出的借鉴其他民族文化和为了适应社会发展而重新建构的痕迹非常明显,实质上是高度涵化以及现代化的一种文化。可以看出,虽然婚俗特征赋予了其满族的身份,但未能掩盖其所用音乐文化的混杂性实质。
正是由于仪式的仪程以及用乐具有了地域、族群之间的跨文化性质,使旅游音乐表演具有了混杂性特点。实际上,仪式的建构者与表演者亦非都是满族人,他们的身份在很大程度上亦具有杂糅的特点,也具有第三空间的文化特征。
2.旅游者具身性的阈限体验
阿诺德·范·杰内普(Arnold van Gennep)认为,所有“通过仪式”或“转换仪式”都有分离、边缘(或阈限)、聚合三个阶段。(16)〔英〕维克多·特纳:《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黄剑波、柳博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4—95页。这是过渡礼仪的基本特征。其中,相比于分离(阈限前)和聚合(阈限后)比较稳定的状态,在阈限时期,仪式主体的状态则含糊不清。当然,过渡礼仪含义较为广泛,它可以包含因地点、状态、社会位置、年龄的每一变化所实施的礼仪。亦即,过渡礼仪除了文化意义中的人生转折点,还包括如升迁、乔迁等诸多变化时举行的活动。由于旅游中确实存在反结构化现象,有些旅游人类学者把旅游者的体验也当作过渡礼仪看待。
纳尔逊·格雷伯恩(Nelson Graburn)将旅游看作是神圣旅程,是一种“世俗仪式”,“(旅游归来后)我们已经不是我们自己。我们经历了生命的再创造后已经成为全新的人。”(17)转引自张进福:《作为仪式的旅游》,《世界民族》,2013年,第5期,第42页。丹尼逊·纳什(Dennison Nash)也认为旅游者经历了隔离、阈限(身份、状态等比较模糊的过渡阶段)、再整合三个阶段。旅游者所经历的陌生情境,类似于“阈限”的体验状态。(18)〔美〕丹尼逊·纳什:《旅游人类学》,宗晓莲译,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2页。可知,旅游可被看作是一种具有个人过渡的仪式。当然,旅游人类学中指的是整个旅游的过程,其包含的内容远比音乐表演多。但是,旅游者参与音乐表演,尤其是与民俗结合在一起的音乐表演,确实是与仪式神圣性更为接近的阈限体验。
在田野考察时,外地学者其实也扮演着旅游者的角色。2016年,笔者考察辽宁新宾满族自治县大琵琶村的撵鬼活动,加入秧歌队伍后,笔者实际成了撵鬼队伍的一部分,在异乡仪式中经历了一次反结构。2019年,笔者考察浙江泰顺三魁镇祭拜陈十四娘娘仪式,所有人都要提前沐浴,笔者亦是如此,其间亦随着道士的唱经进行跪拜并默默祷告。两个活动都在元宵节举行,伴随着节日的仪式感,笔者体验了仪式的神圣性,也获得深刻的阈限体验。
上述两个仪式的举办地处于相对原生的环境中,每年会吸引一些旅游者观看。还有一些表演虽然是在旅游区,但为游客设计了互动环节。福建小黄山畲族风情村开发的初期活动内容不多,重点挖掘畲族婚嫁项目供游客参与,让游客从服饰、歌唱(对歌、山歌)、舞蹈、婚嫁中感受畲族特色。实际上,畲族新郎和新娘的装扮非常受游客喜爱,多数人就是为了体验畲族婚俗表演而来。兰林友借用爱德华·布鲁纳(Edward M.Bruner)的边界区(border zone)概念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认为旅游恰似即兴剧场,只是将舞台设在边界区,表演队和游客即是演员,虽然是舞台化的表演,实际上双方都已经与现实生活剥离。(19)兰林友:《小黄山畲族风情村:符号盗用、表述真实与文化消费》,《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第38页。
上述例子说明,除了观看表演,旅游者还有机会参与表演,除了一般旅游意义上的阈限体验,还有民俗仪式的阈限体验。建构者搭起一个框架,其实是搭建了一个“阈限”体验的平台,以便旅游者深度参与。与日常生活相比,阈限具有反结构特征,在结构与反结构的转换之间,旅游者获得一种不同寻常的人生经验。来自各方的旅游者可能会进入同一个阈限,使本来地域性较强、参与者较少的一些仪式随之变成了共享的文化。这样旅游音乐表演就成了一个“边界区”,在阈限中,人们日常社会中的身份被打破,仪式表演赋予了他们另外一种角色。贫与富、主与客、我者与他者等二元对立变得模糊,参与者具有了边缘性特征,来自五湖四海的旅游者进入了相对平等的“第三空间”。上文提到的巴厘岛乐队演唱《小薇》,实际上,表演者针对笔者模样进行“说唱脸谱”的同时,也成功搭建了一个表演框架,使笔者亦能够参与其中。由此,男声——女声、外国人——印尼人、咬字清晰——咬字含糊、游客——非游客等数对二元关系在由这一框架所形成的“边界区”中被融合并超越。
为什么要设计仪式活动让旅游者参与?实际上是想让游客得到具身性体验。法国现象学家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在《知觉现象学》中,系统讨论了身体与“具身性”的相关问题。他认为身体是每个人体验世界的一般方式,身体通过行为来表示新的意义,如舞蹈表演。在意义的生成中,任何思维活动也代替不了身体的体验,体验是对意义的加强。(20)〔法〕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94页。“从具身的角度看,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并非世界的镜像,而是身体构造和身体感觉运动系统塑造出来的,这就把握了具身性的基本含义,从而明确了它所指向的身心关系。”(21)胡艳华:《身体与具身性》,《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第12页。梅洛-庞蒂指出了亲身体验的重要性,他解决了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的身心二元学说,即身心的分离与对抗存在的逻辑困境。虽然具身性一元论解释了这一问题,但在笔者看来,它不仅超越了身心二元论,而且包含了身体和意识,已经达到了第三空间的认知。许多地区建构一些表演框架,注重旅游者参与,实际上是为了满足旅游者的具身性体验,尤其在一些仪式表演中,通过使具身性与阈限体验合二为一,从而使旅游者获得更深层的感受和印象。
(三)时空并置
摒弃二元对立关系是第三空间的主要特征,其中时间——空间的二元关系亦是主要探讨对象。苏亚认为,安妮·弗蕾德堡在探索巴黎街市中的“第三空间”景观特征时,通过对“橱窗购物”的“虚拟运输机器”展开全景式的纵深世界,使时间——空间的约束被打破。(22)〔美〕爱德华·苏亚:《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陆扬、刘佳林、朱志荣、路瑜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49页。安妮·弗蕾德堡通过电子屏幕这一“窗口”进行视觉上“虚拟旅游”,屏幕就像“虚拟运输机器”,随着屏幕的滚动,不同时间以及不同空间的东西都在这一“虚拟运输机器”上出现。与此类似的是福柯对异托邦(Heterotopia)(23)福柯提到乌托邦和异托邦这一对概念,乌托邦是不真实的地方,而异托邦是真实的地方,同时它又可以包含其他真实的地点,这些地点在异托邦中并置,各自清晰可见。的描绘。福柯提到,带有神圣色彩的二元对立现象控制着人类生活,如神圣空间与世俗空间、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城市空间与农村空间等,但世人的去神圣化(即二元对立)意识仍有所欠缺,这需要导入隐秘的世界,即列斐伏尔所指的“再现的空间”。福柯认为异托邦在所有的文化和人类集团中均会存在,其中一个特点是,一些本身并不相干或并不相容的空间可以在一个真实的空间中聚集、混融、并置。福柯想打破空间中含有的二元关系时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时间性。因此,异托邦与异时间(24)异托邦与时间片段有关系,为了对称,福柯称之为“异时间”。有特别的联系,异托邦可以因时间片段的无限累积而容纳不同时间性的文化,并将这些文化聚集。(25)同注①,第201—203页。可以看出,福柯引入时间性,并非将时间——空间二元对立化,而是将二者融合,使处在不同时间和不同空间的东西并置在一起成为一个新的事物。因此,异托邦与安妮·弗蕾德堡的“虚拟运输机器”都体现了时空并置的特点。它们都具有第三空间的特征。同理,第三空间下旅游音乐文化的协商也体现在表演中各种文化的跨时空重组。如由“做春福”发展而来的浙江省温州泰顺“百家宴”,本是三魁镇张宅村的传统仪式,其目的为“聚宗亲、商族事、祈上苍、保平安”,每年在张氏宗族内部举行。“百家宴”美食活动的前身为张氏家族聚集一起共进午餐的“祠堂酒”。因受旅游文化的影响,至今“百家宴”已成为融美食、表演、信仰、踩街为一体的元宵节民俗活动,2009年已成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笔者于2019年对“百家宴”进行考察,从中可以看到官方的高度参与,活动由泰顺县委宣传部、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三魁镇委员会、三魁镇人民政府主办,张宅村、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承办。在舞台表演环节,有三魁镇戬州官洋村畲族舞龙、走马灯、观音拳、木偶戏《徐策跑城》(由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泰顺县木偶艺术剧团”包日拼表演)、木偶写字、八宝宫灯等传统节目,还有广场舞《城市山林》、童声独唱《云彩里的歌》、时尚京韵模特走秀(泰顺县育才小学)、主题歌曲《作客百家宴》等现代节目,构成了传统与现代的组合,而活动中的传统节目均为泰顺县里的各级“非遗”项目。这些来源不同的文化汇聚于张宅村进行表演也具有了跨地域性质。另外,戬州官洋村畲族舞龙表演的参与,也使这一活动具有了鲜明的跨族群特点。总之,受旅游影响,在各方的凝视下,该活动在表演中纳入了许多其他地方的“非遗”元素,“百家宴”的实质已经超越了张宅一个村落、一个宗族内部的活动,它扩大了最初“做春福”的内涵,已经成为一项跨时间、跨地域、跨族群的文化表演,成为村落、乡镇、县、市甚至省级的文化名片。
辽宁抚顺新宾皇寺(泛指地藏寺和显佑宫)举办的“清皇故里祭祖大典”则体现出鲜明的跨宗教特点。这一仪式的建构体现了多方相互凝视的互动过程。仪式是2012年在当地旅游局的推动下由辽宁抚顺新宾地藏寺通过嫁接“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的程序建构而成,初为佛教举办的“大型祭祖法会”,效果超过预期。2013年,显佑宫在对这一仪式“凝视”之后主动申请加入,旅游局、宗教局同意扩大该仪式的规模,于是在“祭族安位”环节出现了佛、道轮流登场做法事的场景,形成同台祭祖的现象,仪式具有了跨宗教特点。其中,代表显佑宫的道教表演者来自不同道观,虽然全部为全真教派的道士,但全真教演唱的经韵分十方韵和地方韵,区别较大,实际上无法同台表演。而在表演中,高功杨法红以及道士马兴宇、张兴宸、张兴安、丁桂英来自铁岭崔陈堡观音阁,他们演唱的是东北韵,道士徐义元来自何处与演唱何种韵不详(可能来自天津嵛山派),但他们的人数达不到登台做法事的规模,于是加入了来自武汉长春观演唱十方韵的两位道士范信斌、迟信觉。(26)来自于2015年8月13日笔者在显佑宫采访时道长马法哲对于相关视频的讲解。虽然同台表演,但实际上,在高功领唱的东北韵中,两位演唱十方韵的道士无法真正融入。尽管如此,仪式音乐表演已经形成了跨流派的事实。因此,就整个仪式表演来说,同时具有跨宗教、跨流派的现象。
在凝视和协商的过程中,为了让表演满足多方的需求,进而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旅游音乐文化建构实际上把身边可用的各种资源进行组合,使旅游音乐表演具有了时空并置特征,进而出现跨时间、跨地域、跨族群、跨宗教、跨流派现象。
在旅游文化建构中,在多方凝视之下,旅游音乐表演体现了较为复杂的文化特征。差异性特征更多体现了音乐的地域性、民族性,音乐作为文化符号迎合了旅游者欲意了解其他文化的心理需求。边缘性特征可以为旅游者营造一个参与的平台,让参与者增加了具身性与阈限体验。时空并置特征是多元文化的展示,主要是旅游地各种“非遗”文化(包括音乐)的集中展演,旅游者“足不出户”即可享受来自当地的文化盛宴。正因为上述文化建构中的诸多特征,使旅游音乐表演中出现跨时间、跨地域、跨族群、跨宗教、跨流派的复杂现象。这些构成了“第三空间”下旅游音乐表演的若干特征。在此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特征可能会在同一场旅游音乐表演中发生,这实际上也反映出在多方凝视下第三空间旅游音乐表演的协商特质。
四、“第三空间”下旅游音乐表演的双面社会影响
由上述分析可知,从“第三空间”视角对旅游音乐表演进行观照,实际上是把旅游音乐表演看成了边界区。在第三空间下,官方、学者、草根、记者、考察者、旅游者的影响或隐或显错综交织,各种被征用、借用、吸收、改造的文化片段经过对话、协商后形成互渗、互融、共生的杂糅状态,在解构二元对立的情况下形成多元与开放的空间,并生成新的文化意义。实际上,文化建构均伴随着文化认同,旅游音乐表演中体现的差异性、边缘性等也与文化身份、文化认同相关,那么,从“第三空间”下看文化认同有什么特点,有什么现实意义?笔者认为可从正反两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是正面意义。由于旅游文化的来源比较多元,所以会形成“认同差序”现象。国家认同、宗教认同、地域认同、族群认同、民族认同中的多个可能会在同一场旅游音乐表演中出现。尽管这些文化来源比较复杂,但总体来说可分为主文化和亚文化两种。主文化反映出国家认同的趋向,即便是中国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种类的旅游音乐表演,但塑造的国家认同是一致的,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当代旅游文化建构大多离不开官方的支持和参与,因此许多旅游音乐表演中都会有主文化出现。同时,旅游音乐表演又体现出鲜明的地域特征或民族风格,尤其是少数民族旅游音乐表演可能更为复杂。笔者曾认为“无论塑造何种层次的文化认同,一个完整的少数民族仪式一般不能缺少原生层音乐文化来体现其族性,即族群认同元素不能缺少。”(27)张林:《音乐如何与认同接通——以新宾满族音乐文化体系建构为例》,《民族艺术》,2020年,第6期,第159页。另外,“人有个性,音乐也有个性;至于音乐个性,它的一个重要陈述理由便是民族,而民族化个性中至少有一个人文地理的 ‘空间’概念。”(28)彭兆荣:《族性的认同与音乐的发生》,《中国音乐学》,1999年,第3期,第52页。族源(时间性)和地缘(空间性)好比音乐的两翼,让音乐文化披上了一层原生的外衣。因此,族源意识与地缘情结是当今中国旅游音乐表演的基本倾向。但是,主文化塑造的国家认同具有一致性,相比之下,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种类的亚文化所塑造的宗教认同、区域认同、族群认同、民族认同多数情况下是不同的。即如上文所分析,旅游音乐表演具有差异性特征,并因此出现多彩的民族风。因此,就全国范围来看,便形成了国家认同的一致性与其他认同的多元性,呈现出旅游音乐表演的多元一体格局。而旅游音乐表演中的协商意识也无形中促进了中国音乐文化的交往、交流与交融,进而夯实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
另外,旅游音乐表演中也存在消极的一面。如有些旅游区的音乐表演因过分迎合旅游者的凝视,导致其受到外力影响太多而无法全面真实地呈现其民族特色和地域性特征,甚至会产生一种伪文化,无疑对传统文化造成一定的伤害。正如兰林友认为“民族文化的舞台化呈现改变了地方文化,冲淡了地方文化内涵,更消退了文化内涵的神圣性……甚至,有时候民族身份或族群形象被缩减为单一的、偶尔的民俗表演。”(29)兰林友:《小黄山畲族风情村:符号盗用、表述真实与文化消费》,《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第35页。另外,有的旅游音乐表演会借用其他民族的原生态形式,其实当地并不存在这一民族,从而对游客产生误导。还有“内部东方主义”因遭遇现代社会发展而出现了颇为尴尬的局面,为了追求差异性,音乐表演时会过分依靠视觉类显性文化作为辨识依据,部分地方的音乐会、吵子会、舞龙、舞狮表演者都穿上了复古的侠士服,头系头巾,腰间扎上腰带,小腿扎着脚绑,颜色以黄色、红色为主。但这些服装均是统一批发的商品,大同小异,反而在视觉上造成了均质化倾向。
结 语
学界近年来对旅游音乐文化的关注稍有不足,正如杨民康所说,“传承、建构、创新”三类研究中存在“两头热、中间冷”的现象,对于旅游音乐文化缺少足够的关注。[注]杨民康:《少数民族当代节庆仪式音乐与民族文化身份建构——以西南少数民族音乐的研究实践为例》,《中国音乐》,2020年,第1期,第11页。但需要明确的是,虽然旅游音乐文化存在鲜明的建构特征,但并非某一方所为,一次旅游音乐表演文本的生成是多方参与的结果。其中,游客参与了旅游音乐表演的共谋。因此,如果仅从“非遗”、保护、传承、创新等视角进行切入,则忽视了旅游音乐表演与文化建构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旅游者,也就忽视了旅游凝视下多方的参与和互动。而将旅游音乐表演放置到第三空间,则是将所研究的对象放到一个动态发展的视角下去观察,显然,旅游音乐表演处于未完成状态,学术研究也具有更大的开放性。如此,本文尝试为旅游音乐表演与文化建构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提供了一些新的分析框架,这也是本文花费大量篇幅对第三空间进行浓墨重彩描述的原因。同时,笔者也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可以关注到这一领域,进而将旅游音乐表演与文化建构的研究不断推向深入。
建构者、表演者与旅游者通过多方相互凝视形成互为主体、互为他者的一种关系,建构了一个协商、合作的旅游音乐表演空间。在这一空间中,由于两种(或多种)身份在边缘地带相遇并发生协商,产成了新的表演空间,即第三空间。第三空间涵盖并超越了物质的和精神的空间,突破了二元对立,在这种情况下因表演生成的音乐文本具有差异性、边缘性、时空并置等特征,进而音乐表演呈现出跨时间、跨地域、跨族群、跨宗教、跨流派等现象。从整体来看,中国旅游音乐表演因涵盖主文化和亚文化两种类型而强化了中国音乐文化认同的多元一体格局,有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