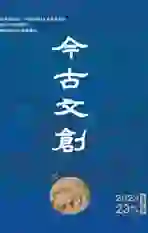《儿童法案》中主人公菲奥娜的人生困境
2023-08-07张媛
张媛
【摘要】英国当代著名作家伊恩·麦克尤恩的新世纪新作《儿童法案》,以主人公菲奥娜·迈耶的职业经历和家庭生活构成小说的清晰叙事线索,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揭示麦克尤恩对现代人生存困境的重视,帮助读者直接进入女主人公在现代社会、婚姻家庭和自我选择的世界,一起思考如何在人生困境中寻找与他人的情感共鸣和自己真正的生存价值,敢于表达自己,勇于走出人生困境。
【关键词】伊恩·麦克尤恩;《儿童法案》;困境
【中图分类号】I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23-0025-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23.008
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1948—)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国文坛的最著名的作家之一。从“恐怖伊恩”(Ian Macabre)到“国民作家”(national author),麦克尤恩的创作主题经历了从乱伦、暴力、怪癖、谋杀到多元社会话题的转变。“他坚持不懈地用艺术方式追寻与审视历史进程、表达思想,并通过绘制、窥测与再现等方式切入人物内心世界,与世界对话,在后现代语境下表达和反思人性,希望人类从失意和彷徨中得到救赎。”[1]32小说《儿童法案》将主人公菲奥娜·迈耶在现代社会、家庭婚姻和自我调节等问题的纠结和内心世界的波澜起伏刻画得淋漓尽致,帮助读者直接进入女主人公的心理一起思考这些人生困境。
一、职业与家庭的外在冲突
在职业生涯和家庭环境之间,一个成功的现代女性形象的背后隐藏着看不见的情感障碍和注意不到的裂痕。小说《儿童法案》的主人公菲奥娜·迈耶是一位五十多岁的白人女性,作为当代成功职业女性的典型代表,她是一位主持家庭事务的高等法院法官。在职业生涯中,菲奥娜坚定和理智,以公正和理性的判断赢得了人们的尊重。然而,当社会的发展为新世纪女性在社会结构中的表现提供多种机会和可能性的同时,她们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艰难处境。巨大的工作压力和复杂的工作环境挑战着女性在家庭生活中扮演的传统角色,她们在平衡工作和家庭的道路上举步维艰。因此,工作和家庭两个不同领域的角色压力在某些方面是互不兼容的。在成功事业的背后,菲奥娜被工作和家庭的冲突不断折磨,也被婚姻的混沌深深困扰。毋庸置疑,担任多个角色极大程度上消耗一个人有限的时间和精力,在一个角色中花费的时间不能用于构建另一个身份的其他任何活动,而当代女性肩负着比以往更多的责任,社会的生存困境加重她们的负担。菲奥娜具有超凡的职业素养,完全可以胜任艰苦劳累的法院法官的工作。正因为如此,她忙于自己的时间安排,不能专注照顾自己的小家庭,无暇顾及丈夫的不满和情绪变化。当杰克提及他们之间的亲密,她发现自己“忙得不可开交,许多事情都记不起来了”[2]10;在日常生活中,她不记得小物件放在哪里,也不记得自己最后一次把花放在她房间的花瓶里。菲奥娜的种种行为典型地代表了高水平职业女性的普遍生存状态,当杰克突然向她抛出婚姻的危险信号时,她无法意识到他们之间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
比起时间的超负荷,工作的压力更能阻碍菲奥娜履行家庭责任,也可能导致家庭破裂。传统上由男性占据的高等法院工作,菲奥娜与其他男法官一样,将大部分时间投入到复杂的案件中,承受着巨大的舆论压力和公众的关注。法官的角色要求她和其他男同事一样理性和冷静。因此,菲奥娜表现出一种在普通女性身上少見的强烈阳刚之气,她“撰写的判决书行文明快,紧凑得体,用语得当,切中肯綮,反讽中不失温暖,即便她不在时也受到大家的推崇”[2]15,独特出众的专业素养甚至超越了周围的男同胞。这个社会的男子气概不可避免地会让人联想到权力的概念。菲奥娜在法庭上的权力带来了当事人的尊重,而事业上的成功也为她在社会上带来了相对优越的社会地位。强大的角色掩盖了她在婚姻中作为妻子的角色,以至于面对个人家庭问题时,她可能会不知不觉地地表现得像一个严肃的法官。在他们的对话中,菲奥娜总是扮演法官的角色,居高临下地谴责丈夫的无礼行为,却忽略了夫妻间冲突背后隐藏的情感危机,似乎没有反省为什么杰克会提出开放式婚姻的荒谬提议。相反,她坚持认为杰克是一个背叛者,把现在的幸福生活撕成碎片,指责他的不道德行为。在菲奥娜的心中,对与错有明确的纪律界限,丝毫没有关注到伴侣的情绪变化和他们之间的情感问题。菲奥娜难以处理职业工作与私人生活之间的角色变换也抑制了她对周围人的情感关怀,无法从孤立的个人世界走出来,接触更广阔的外部世界。
总而言之,工作与家庭的冲突无法让菲奥娜自如地进行角色转换,她裹挟在家庭和社会两者之间,“在各种身不由己的身份转换中晕头转向,受制于传统伦理道德的辖制”[3]88,法官的理性思维剥夺了她的许多情感参与,很难体会到爱人的感受,关注到他人的情况,触及生活的美好。
二、妻子与丈夫的内在分歧
菲奥娜是高等法院的法官,杰克是温文尔雅的考古学教授,尽管两人都是当代社会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的代表,但他们仍然无法摆脱传统的家庭体质。在一定程度上,深藏不露的父权意识可能会阻碍形成平等、有效、感同身受的沟通方式。即便菲奥娜的社会地位相当高,经济完全独立,但她仍然很难应付丈夫的不忠,也很难接受离婚后的可怕局面。杰克以公开婚姻为借口,设想在不离婚的情况下发生婚外情,面对妻子的生气和大喊大叫,坚持说:“我需要这婚外恋。我五十九岁了,这是我最后的机会。我还想听听来世生活的迹象呢。”[2]9杰克的抱怨印证了在父权意识形态中夫妻关系中的丈夫持有的传统观点,即“男人高于女人,女人是男人财产的一部分。”[4]8他抱怨过去是菲奥娜忽视了他的生理需求,没有遵守妻子应该遵守的义务。在此基础上,杰克认为存在外遇理所应当,为自己的不忠行为开脱,坚持一夫多妻制的合理性。“你不是告诉过我说长期婚姻中的夫妻追求的是兄弟姐妹的状态?菲奥娜,我们已经到达那种状态。我变成了你的哥哥。我们的家非常温馨甜美,而且我爱你,但是在我死之前,我想要一次轰轰烈烈的婚外恋。”[2]11“杰克的问题在于其身份与行为在其道德规范上逆向而行:他不仅逃避自己作为丈夫的责任,而且还试图以妻子兄长的身份来取代其丈夫身份,为肆意追求感官刺激的欲望,他还故作聪明地试图用理性掩盖非理性,任由其身上的兽性因子主导人性因子。”[5]55杰克也在无形之中暴露了男性控制家庭的想法,他很少努力去同情他的妻子,或者在忙碌而紧张的生活中重获与菲奥娜的快感和共鸣。在与杰克分开的日子里,菲奥娜也经常反思自己的行为,是否真的缺乏对丈夫的关注。杰克的出轨给她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她也失去了来自丈夫的强大情感支持。
没有孩子的事实也给菲奥娜造成巨大的心理负担,影响她与家庭的情感联系。“母亲和父亲的形象反映了我们对于作为父母的女人和男人的共同理想、标准、信仰和期望”[6]859-860,在为人父母的过程中,夫妻之间的亲密情感通常会加强。然而,菲奥娜并没有一个稳定的核心家庭,一次又一次的推迟生育,到了中年,没有孩子的状态演变成夫妻之间明显的情感沟壑,家庭关系因此变得松散和冷漠,“不和谐的情绪出现后又消退,总是在惊吓甚至恐惧的时刻重复出现。”[2]33菲奥娜没有自己的孩子,缺少倾诉的对象只能加剧她对丈夫的不满。不过,成年的孩子也可以充当沟通的桥梁或夫妻之间的情感妥协,因此侄女们的探望或多或少地重新点燃了她对家人的关心和温柔。每次当孩子们来到他们的房子里时,菲奥娜变得柔和,不自觉地对杰克的孤独感到难过。当她在婚姻中倍感孤立无援时,有一种感觉,这“本身就是一阕赋格,一次奔逃——这种鸣奏曲式格外常见,而她此刻在极力抵制——逃离天命”,“现在的一切都是她的报应:必须独自面对这场灾难,没有懂事成熟的孩子关切地打来电话,没有孩子们撂下手头上的工作、召开紧急餐桌会议,给他们愚蠢的父亲讲明道理,把他拉回这个家庭。”[2]34作为法官的菲奥娜一心想要升职,经过一场场棘手的案件的磨炼,到达事业的巅峰,却未料到在某种程度上,孩子的缺席弱化了配偶之间成功的共情体验,与婚姻中夫妻间不可避免的疏离密切相关。
夫妻之间的争执是解构相互关怀的内在障碍。婚姻关系中的弱势地位和没有孩子的缺憾给菲奥娜造成了情感上的危机,被迫选择在沉默中应对不和谐的相处。菲奥娜和杰克的关系是消极的。菲奥娜认为自己工作之余倾尽所能照顾家庭,许多事情无须表达,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事业的紧迫性模糊了家庭的重要性,杰克的不忠违背关爱的本质,二人渐行渐远。
三、自我与共情的相互矛盾
如果一个人以自我为中心,那么他对他人的共情就会大大减少。在人际关系中,菲奥娜是一个利己主义者,容易忽略他人的感受和情况。在她的童年时代,自我为中心的鲜明性格特征早已塑造成型。十三岁的小菲奥娜非常享受在医院的一段短暂时光,因为在压抑和阴郁的病房里,虚弱濒死的女人们把她看作一个可爱的小姑娘。她喜欢医院的氛围,因为唯有自己能得到所有人的喜爱和关注。然而,小菲奥娜并没有感受到这些深受癌症折磨和死亡威胁的悲伤。她理所当然地接受别人的照顾,却忽略她们的疾病和痛苦。小菲奥娜和朋友们把病房当成了一个有趣的地方,“坐在病床边恣意嬉闹,为一些不值一提的小事压低声音咯咯发笑”[2]61,她们的无忧无虑与“病房另一头隔着帷幕的重病患者发出沙哑的呻吟”[2]61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以,菲奥娜结婚后,依然难以想象别人的困境,强烈的自我中心意识无法从他人为主的视角出发,建立人际关系。此外,共情在亲密的关系中很难进行,因为妻子和丈夫受制于各自的性别、思维模式和价值观,从而无法产生换位思考的结果。对于菲奥娜来说,高度的自我意识使她难以理解丈夫争执时的情绪和立场;从一个法官的思维出发,她很清楚杰克想通过提出开放式婚姻的荒谬建议来引起她的注意力的真相,可是习惯了从自己的角度审视婚姻,反而倍感愤怒和无助。尽管杰克在争吵中退缩,寻求双方的妥协,但菲奥娜不愿放下自尊,仍把自己放在首位,同时她的冷漠、固执和自以为是推着杰克越走越远,他们的关系不断逼向冰点。菲奥娜认为杰克的背叛对她来说是莫大的耻辱,她宁愿掩盖真相,也不愿让自己成为同情的对象。她担心这对她成功的司法生涯是一个巨大的否定,她只想远离婚姻危机,逃离焦虑的生活状态。她把自己关起来,与那些可能给她提供帮助的人保持一定的距离,“她有三个朋友,她可以给她们中的任何一个打电话倾诉,但她没法忍受听见自己向她们解释她的境遇,没法忍受让她们相信这些都是改变不了的实情”,“她在空虚无聊寂寥麻木中度过了这个晚上”[2]41,不愿走出自我塑造的孤独世界。
长期的自我保护会导致人困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心理空间。随着年龄的增长,菲奥娜对自己日渐衰老的身体极为不满。基于对自己的鄙视,她倾向于把婚姻危机归咎于美丽外表的丧失和杰克对年轻女性的痴迷。“当丈夫转身背对她时,她有一种冷冷的被抛弃的预感,感到丈夫抛弃她去找一个年轻女人的耻辱,感觉到即将被抛弃,无用而且孤独。她自己是不是该迎合他想要的一切,很快,她放弃了这种想法。”[2]10-11菲奥娜非常惧怕听到杰克不再对其感兴趣的残酷事实,拒绝与他进行任何深入的交流,参与他的精神和情感活动,自我封锁在一个充满否定和怀疑的压抑空间。因此,她的孤独感愈加强烈,拒绝向别人打开自己的内心,寻求安慰和情感共鸣。更糟糕的是,长期处于一个封闭的心理环境和负面的情绪状态,菲奥娜会更加焦虑和抑郁,无法摆脱被抛弃的恐惧。事实上,菲奥娜也尝试突破自我,向杰克吐露自己的情感秘密,尽管她始终坚信在这场荒谬的家庭闹剧中,自己才是真正的受害者。面对真正的婚姻问题,菲奥娜此前从未试图向杰克倾诉自己的感受,也未曾要求他对自己的决定做进一步的解释,她所做的只是无视不堪和逃避麻烦。与此同时,她又困顿在无用无助的假设中,一遍又一遍地考虑这些想法,质疑自己是否能够努力去修复这段关系。另一方面,菲奥娜也不能坦诚地告诉丈夫婚姻生活之外的其他复杂情感。无论是双胞胎分离案带来的创伤,还是宗教家庭的子女教育案的事实,抑或是触动她内心深处的男孩亚当,杰克全然不知。然而,亚当的去世给她当头一击,菲奥娜被迫在自我和共情的矛盾中打破僵局。音乐会结束后,悔恨、内疚和失去的情感迸发,菲奥娜无法承受如此沉重和复杂的折磨,最终向杰克寻求安慰和同情。那一刻,她在丈夫面前脱下所有的伪装,希望最亲近的人理解自己藏在心底最隐秘和最尴尬的情绪。面对菲奥娜的坦白,杰克备受感动,想更多地了解她的经历和一切,给她一个依靠的肩膀。这无疑是故事结尾最美好的走向。
四、结语
“贯穿麦克全部作品的一个重要主题是人与人的关系”[7]26,《儿童法案》刻画了一个典型的女法官在与自我,爱人和周围人相处过程中的矛盾,深刻反映了现代人特别是女性的生存困境。正因为小说中没有直接给出女主人公在现代社会、家庭婚姻和自我调节等问题上的确切答案,才能引起我们的思考,如何在当代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和独立的个体空间里找到与他人的情感共鸣和自己真正的生存价值,在困境中给自己一个相对完美的身份定位,努力从生活中收获一些温暖和爱。
参考文献:
[1]杨金才.21世纪外国文学研究新视野[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版),2015,18(01):32.
[2]Ian,McEwan.The Children Act[M].London:Vintage, 2014.
[3]易扬.嬗变与不变——读麦克尤恩长篇小说《儿童法案》[J].书城,2017,(08):87-88.
[4]Sultana,Abeda.“Patriarchy and Womens Subordination: A Theoretical Analysis.”The Arts Faculty Journal(July 2010-June 2011):1-18.
[5]尚必武.兒童福祉的意义探寻与守护方式:麦克尤恩新作《儿童法案》中的伦理身份与伦理选择[J].外国文学研究,2015,(03):53-63.
[6]Thompson,Linda and Alexis J.Walker.“Gender in Families:Women and Men in Marriage,Work,and Parenthood.”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51.4 (1989):845-871.
[7]蓝纯.伊恩·麦克尤恩其人其作[J].外国文学,1998, (06):2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