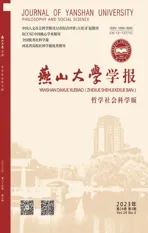安大简《仲尼曰》文本、主题与性质研究
2023-08-07代生
代 生
(山东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仲尼曰》是一篇新公布的孔子语录文献,与《论语》《礼记》等文献记载有相同或相近之处,又有不见于传世文献的内容,对研究孔子思想及流传等问题具有重要价值。如整理者所言,“简文原无篇题,不分章,内容为孔子言论,共25条,除一条开头为‘康子使人问政于仲尼’外,其他简文均以‘仲尼曰’起始。”[1]这是《仲尼曰》篇行文的突出特点。从行文方式、主旨等方面和《论语》等进行比较,不仅有助于了解该篇的主旨、性质,还能够解决学术史上的一些问题。
《仲尼曰》原文不分章,整理者以“条”作为文本组成。我们认为,命名为与传世文献相近的“章”,能够较好地反映文本的内容组成,因此可以《论语》“篇—章”的分类方式将该篇划分为25章,并有文末“仲尼之耑(短)语也,朴慧周极”的评语。
一、 行文特点与主题分析
《仲尼曰》中,孔子的言语多是以对比式结构出现的。据笔者统计,在25章中至少有23章出现正反、排比的言语方式,并可以按照不同的“主题”进行划分。下面试对出现次数较多的几对“主题词”进行分析。
(一) 君子与小人
在儒家视野中,“君子”是一个重要概念。孔子就曾教育弟子子夏“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可知在孔子看来作为儒者已有“君子”和“小人”之分。日常生活中的“君子”“小人”更是孔子所要强调区分的。根据黎红雷先生统计,在《论语》中,“君子”出现107次,“小人”出现24次,“君子”与“小人”同时对举者有19处。[2]从这一统计可知,“君子”与“小人”的对举占了很大部分。在《仲尼曰》篇25章中,“君子”一词出现达6次,“小人”一词出现4次,其中有3次是“君子”和“小人”对举的。一般认为,《论语》中的君子大体有三种内涵,一是道德层面的,二是居高位者,三是兼而有之。在此可以对本篇中“君子”和“小人”的内涵进行分析。
第三章的记载是:
仲尼曰:“君子溺于言,小人溺于水。”[3]43
单纯从该章文本中并不能认定“君子”的内涵,但此章可与《礼记·缁衣》“小人溺于水,君子溺于口,大人溺于民,皆在其所亵也”参照,这里的“大人”依照古注为执政者,那么“君子”当属于道德层面。又如第十九章记载:
康子使人问政于仲尼。曰:“丘未之闻也。”使者退。仲尼曰:“视之君子,其言小人也。孰正而可使人闻?”[3]44
在该章中,孔子认为季康子看起来像个“君子”,但其所言之事体现出他却是“小人”。这里的“君子”“小人”都指季康子(也可能是使者,详下讨论),无疑既指社会地位又多赋予道德内涵。
再如第八章:
仲尼曰:“君子之择人劳,其用之逸;小人之择人逸,其用之劳。”[3]43
这里“君子”与“小人”对举,但又说“君子”“小人”都可以“择人”而“用之”,可见二者都非单独的道德、地位层面能涵盖,而是兼而有之,因为只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官吏们才能选人用人。孔子还特别重视“君子”的自我修养,如第七章提出“君子所慎,必在人之所不闻与人之所不见。”[3]43强调体现“君子”品格的应该是在人们所不容易看见、了解的地方,实际上是指“慎独”。第十章中,孔子教育弟子:“弟子如出也,十手指汝,十目视汝,汝乌敢为不善乎!盖君子慎其独也。”[3]43-44两章所言一致,是孔子要求弟子做一个“光明正大”的“君子”。
此外,第三章记载孔子所言“去仁,恶乎成名?造次、颠沛必于此”[3]43。该章又见于《论语·里仁》:“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对比可知,第三章省去了两个“君子”,这里强调的也是“君子”的行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违仁”,否则就不是“君子”。
综合本篇来看,孔子特别强调“君子”的修为,故而一再引述。他判断“君子”的标准是:能够少言而多行,注重选贤任能,要见善以思,不断反思提升,还能做到“慎独”。
(二) 善与不善
《仲尼曰》中,出现次数较多的还有“善”一词,共出现6次;“不善”出现3次。“善”的词性不同,有动词义,表善于、擅长,如第十二章:
仲尼曰:“晏平仲善交哉!久狎而长敬。”[3]44
这里的“善交”即表示晏子善于交际。也有名词义,如第十五章载:
仲尼曰:“君子见善以思,见不善以戒。”[3]44
该章的“善”与“不善”对举,整理者引《论语·里仁》“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及相关注释,训“善”为“贤”,可从。又如第二十一章有“见善女弗及,见不善如袭”的记载,也应训读为“贤”。第十七章言“管仲善善哉,老讫”[3]44,其中的“善善”,是指喜爱、善待贤人,进一步引申为重用贤能(详下文论证)。另外,第二十二章中孔子提出:“小人乎,何以寿为?一日不能善。”[3]44该章中的“善”,当为名词动用,即为善、行善。
本篇中,“善”的主要含义为“善人”,指代“有德之人”,孔子引述这些内容要求“见善以思”,躬省自己,要努力做到“善”;对于“不善”要“戒”、要警惕,这也是一种修为。
(三) 仁与不仁
“仁”被学者认定为孔子思想的核心,但孔子对“仁”的判定往往是多层面、多角度的。《仲尼曰》篇中“仁”出现4次,“不仁”出现2次。
第四章记载孔子说:“去仁,恶乎成名?造次、颠沛必于此。”[3]43此章可与《论语·里仁》篇对读,孔子认为君子如果没有了“仁”,就不能称为君子了,无论在什么环境下都是如此,都不能离开“仁”。这其实是强调君子和“仁”的关系,也是逆境下为“仁”的要求。
第六章载:“伊言咠,而禹言丝,以治天下,未闻多言而仁者。”[3]43孔子列举古圣贤行为来讨论“仁”,认为“多言”不能成为“仁”,《论语》有“巧言令色鲜矣仁” “刚毅木讷,近仁”的记载,就将“言”与“仁”联系起来,二者表达的意见是一致的。
第十一章“仁”和“不仁”各出现2次:“仁而不惠于我,吾不谨其仁。不仁〔而〕不惠于我,吾不谨其不仁。”[3]44有关此章,侯乃峰认为应该是出现了讹误,原文当为“仁而不惠于我,吾不谨其仁。不仁不〈而〉惠于我,吾不谨其不仁。”即“抄写者将其中的‘而’字误写作‘不’”,将之翻译做:“作为仁者,如果对于我没有施予什么恩惠,我也就没有必要对他表示恭敬;如果有不仁者对于我施予恩惠,我对于他的不仁之举也不会表示恭顺。”[4]我们认为,他提出抄手误写的说法可从,但对“谨”的理解还可以讨论。相较而言,陈民镇认为“堇”当训读为“隐”,翻译作“‘仁而不惠于我,吾不隐其仁’,谓仁者未惠及我,我并不因此掩其仁德;‘不仁而惠于我,吾不隐其不仁’,谓不仁者虽施惠于我,我却不能因此掩其不仁的一面。”[5]这一说法较为合理。这反映出孔子评价人的“仁”与“不仁”,并不以自己受惠于人与否而改变,也不轻易许“仁”,足见他对“仁”的笃信与追求。
(四) 言与行
在《论语》中,孔子特别重视言行,如《学而》篇载:“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子路》篇说“言必信,行必果”。《里仁》篇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等等。可以看出,在孔子看来要言行一致,二者关系上,要少说多做看行动。《仲尼曰》中“言”出现8次,如第一章孔子就说“华繁而实厚,天;言多而行不足,人。”[3]43即花盛开而果实丰硕是天的“功劳”,人却是说得多做得少,强调“行不足”是人的缺点。第三章又说“君子溺于言,小人溺于水。”[3]43强调即使是君子,也往往不能做到谨言慎行。在第六章中,孔子以伊尹(或者说尧)、大禹为例,认为他们出言谨慎,才能治理好天下,而多言难以成为仁者。将“言”的多寡提升到修身之“仁”和治理国家的能力上,可见其重要。
尚需要讨论的是第十九章:
康子使人问政于仲尼。曰:“丘未之闻也。”使者退。仲尼曰:“视之君子,其言小人也。孰正而可使人闻?”[3]44
有关该章,整理者注释说:
此条简文见于《论语·颜渊》:“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文字出入较大。……“视之君子,其言小人也”,意谓:看他样子像个君子,听他说话却是个小人。或认为简文“中尼”脱重文符号。[3]50
周翔等先生将该章译为:“季康子派使者向孔子询问政治。孔子说:‘我对政治没有了解。’使者走后,孔子说:‘我把季康子看作君子,可他的话却是小人做派。哪个正直的人会派人来问(政治问题)?’”同时,他还提出另一种解读方案:读“正”为政,“意即什么政治问题可以派人来问?是以反问句表达对季康子派人问政的批评。言下之意,政治是严肃的大事,执政者若真心关注就不该派人来问而应亲自登门求教。派人问政足见其对政治的关心只不过流于表面,故为小人之举”[6]。
我们认为,整理者提出该章与《颜渊》篇季康子问政有关不一定可信,二者的联系恐怕仅是季康子向孔子问政而已。周翔先生把“正”理解为“正直的人”颇感扞格,这和主题似乎没有关系。而理解为“什么政治问题可以派人来问”“政治是严肃的大事,执政者若真心关注就不该派人来问而应亲自登门求教”看似有理,但从文献记载可知,季康子向孔子问政,既有当面的,也有派使者来的。如《左传》哀公十一年记载说:
季孙欲以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仲尼曰:“丘不识也。”三发,卒曰:“子为国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对。而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访焉?”弗听。[7]
从这一记载来看,孔子同样是很生气,但不是认为季康子没有亲自前来问政(从传世文献看,孔子似乎也未必拘泥于此节),而是对所“言”之事——用田赋表达不满。他对冉有所说的“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以丘亦足矣”也可与《仲尼曰》“视之君子,其言小人也”进行比较,都是认为季康子所为非君子。据此我们认为,“其言小人也”之“言”指代所言不合礼之事,所以孔子回答“未之闻”。
还有一种解读,即孔子批评的未必是季康子,而可能是其所派使者,使者应是季康子的家臣,从外貌穿戴看起来像个君子,但说起话来却像个小人,或许还显示出对孔子不恭敬的态度,所以引起孔子不满。“孰正而可使人闻”应理解为“孰政而可使人闻”,孔子认为这样的人怎么能告诉他如何为政呢?季孙氏作为鲁国的执政者,家臣众多,或许不乏其父季桓子的家臣阳虎之流,又有公之鱼等对孔子思想不以为然者。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季桓子临终之时,曾嘱咐季康子要重用孔子,季康子尊照父意准备召回在外周游的孔子,却被公之鱼劝阻:“昔吾先君用之不终,终为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终,是再为诸侯笑。”[8]稳妥起见,季康子只是征召了冉求。
我们认为以上两种解释都能讲得通,但对“言”字的含义就有了不同理解。由于文献不足且缺少具体背景,只能存疑待考。
总的来看,《仲尼曰》的记载再次展现了孔子重行轻言、谨言慎行的言行观,与《论语》所载并无二致。
(五) 古与今
“厚古薄今”是孔子及儒学学派的重要思想特色。众所周知,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并将他们统治的时代划分为“大同”“小康”社会,对这两个时代充满了期盼。春秋晚期诸国争霸、礼崩乐坏,这应该是孔子厚古非今的重要原因。
孔子自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论语》中就多次出现“古”与“今”的对比,认为古人守礼,《阳货》篇有这样的记载: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无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荡;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
该章的“古”“今”对比就出现4次,“古”“今”差距十分明显。《仲尼曰》篇有2次“古”“今”对比,即:
仲尼曰:“古之学者自为,今之学〔者〕为人。”
仲尼曰:“古者恶盗而弗杀,今者恶盗而杀之。”[3]44
此外,又有第二章记载“於人不信其所贵,而信其所贱”[3]43,有学者认为“於”字为“今”字[9],亦有道理。该篇虽然没有强调“古”,但有“今”即暗含了与“古”的对比,该章还有信与不信、贵与贱的鲜明对比。
二、人物评价凸显文本主题
孔子教育学生、表达自己的思想,除了说教式的训导,还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品评人物的方式进行的。根据学者的统计,《论语》中孔子评价的人就有155个[10],有尧舜等古圣贤,也有汤、文武、周公等政治人物,他们都是被孔子当成学习榜样的。还有与他时代相隔不远的政治家,如管仲、子产、晏婴等,孔子也曾给予较高的评价。
《仲尼曰》中涉及的人物有尧、大禹、伯夷、叔齐、管子、晏婴、史鱼、季康子及使者、颜回、子贡等。孔子对尧、禹的评价甚高,如《论语·泰伯》篇评价尧:“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赞美大禹说“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仲尼曰》第六章记载孔子的话:“伊(尧)言咠,而禹言丝,以治天下,未闻多言而仁者。”认为尧和大禹出言谨慎才能治理好天下。该章主要是针对“多言”而论的,孔子认为仁者应该“谨言慎行”,强调尧、禹都是如此,从上引《泰伯》篇对尧和禹的描述来看,尧为政时颇有“无为而治”的特点,大禹致力于治水,孜孜不懈,而不注重享受,这些与《仲尼曰》所载有略近之处。从《仲尼曰》对人物的评价中,可以看到“作者”的评价,凸显了该篇的主题,我们试举几例进行说明。
(一)对伯夷、叔齐的评价
有关伯夷、叔齐的评论见于第二十一章:
仲尼曰:“见善女弗及,见不善如袭。堇以避难静居,以成其志。伯夷、叔齐死于首阳,手足不弇,必夫人之谓乎?”[3]44
此章内容见于《论语·季氏》,所言大致相同,孔子认为伯夷、叔齐虽然饿死,但他们“堇以避难,静居以成其志”,是真正的“善人”。这一点又见《微子》篇:
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
孔子所言“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恰是对《仲尼曰》所载伯夷、叔齐行为的精准评价!
(二)对管子的评价
对管子的评价,见于第十七章:“管仲善,善哉,老讫。”整理者的意见并不一致,其中一种意见理解为“管仲仁善,得以寿终”,解读“老讫”为寿终;另一解读方案又将“老讫”读为“小器”,翻译为“管仲善良是善良,但是器量狭小。”[3]44,49
对此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如王宁先生认为:
此条整理者作了大量的注释,仍觉不安。疑“善=才”当读“善言哉”,与简7“晏平仲善交才(哉)”的句式略同。此处之“善言”与《管子·戒》“孙在之为人也善言”的“善言”同;“老讫”一句与简7评价晏子“善交”的话“旧(久)狎而长敬”类似,是评价管仲“善言”的话,或是“老而讫”的减省,或是写脱“而”字;“讫”疑读为“忔”,《广雅·释诂一》《玉篇》皆训“喜”,则此二句大意是说管仲是个会说话的人,越老说话越让人喜欢。[11]
王先生的说法具有启发意义,但也未必中的。我们认为,此句应断句为“管仲善善哉,老讫”,但“老讫”还应理解为寿终,所谓“善善”,第一个“善”字当为动词义,第二个为“善人”,可理解为第十五章“君子见善以思”中的“善”字,训读为“贤”。该句是说管子善待贤人,最后也得善终。第十二章评价“晏平仲善交哉!久狎而长敬”[3]44,与此近似但也有不同。孔子为何这样评价管仲,可以从管仲与齐桓公的事迹中寻绎出依据。如《管子·戒》篇记载管仲病重,齐桓公前去慰问并请求他推荐可以辅佐自己的人,管仲说“鲍叔牙之为人也好直,宾胥无之为人也好善,宁戚之为人也能事,孙在之为人也善言。”还评价鲍叔牙“好善而恶恶已甚”,评价隰朋时强调“以善胜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养人者,未有不服人者也。”与此同时,还要求“桓公去易牙竖刁卫公子开方”。但齐桓公最后没有坚持下去,又任用了这些佞臣,造成自己“死七日不敛,九月不葬,孝公奔宋,宋襄公率诸侯以伐齐,战于甗,大败齐师,杀公子无亏,立孝公而还。”[12]
仔细体会这段记载,不难发现《仲尼曰》对管仲的评价是以上述史事为背景的,管仲在临死之前,坦诚相待,推荐了“善人”并指出他们也有不足,“好直”“好善”等词与《仲尼曰》“善善”内涵相近,或者说“善善”即“好善”,故而该章意在管仲能够帮助齐桓公选人用人。相比较而言,齐桓公任用佞臣,却让自己的一世英名毁于一旦,留下了一个烂摊子,也即“齐桓九会,卒然身杀”,不得善终。这一点《吕氏春秋·先识览》讲得更为清楚:
管仲对曰:“愿君之远易牙、竖刁、常之巫、卫公子启方。”……公曰:“诺。”管仲死,尽逐之。食不甘,宫不治,苛病起,朝不肃。居三年公曰:“仲父不亦过乎!孰谓仲父尽之乎!”于是皆复召而反。明年,公有病,常之巫从中出曰:“公将以某日薨。”易牙、竖刁、常之巫相与作乱,塞宫门,筑高墙,不通人,矫以公令。……公慨焉叹,涕出曰:“嗟乎!圣人之所见,岂不远哉!若死者有知,我将何面目以见仲父衣乎?”蒙袂而绝乎寿宫。虫流出于户,上盖以杨门之扇,三月不葬。[13]
这应该是《仲尼曰》“含而未露”的“言外之意”。在前述二十一章中对伯夷叔齐的评价也见于《论语》,但其所记为:“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其斯之谓与?”是将齐景公事迹和伯夷、叔齐事迹进行对照,而《仲尼曰》只叙述了伯夷叔齐,省略了齐景公。这些减省与《仲尼曰》篇的“作者”要简洁行文,凝练主题,突出强调伯夷叔齐、管仲有关。
(三)对弟子颜回和子贡的评价
颜回和子贡都是孔子最为信任的弟子,《仲尼曰》篇中也有对他们的评价,分别见于第九、二十两章,先看第二十章:
仲尼曰:“一箪食,一勺浆,人不胜其忧,己不胜其乐,吾不如回也。”[3]44
此章与《论语·雍也》所记一致,整理者已有较好的分析,其中需要注意的是“吾不如回也”一句,孔子明确表达在安贫乐道这一点上比不上颜回,孔子对颜回的评价可谓高矣!这让我们想到了《论语·公冶长》篇的记载:
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
这里也是将颜回和子贡进行比较,其中该章最后所言“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学者们有不同解读。如汉人包咸说:“既然子贡弗如,复云吾与汝俱不如者,盖欲以慰子贡心也。”这是认为孔子为了宽慰子贡而提出孔子和子贡“俱不如”颜回。晋人缪播则提出:“回则崇本弃末,赐也未能忘名。存名则美著于物,精本则名损于当时,故发问以要赐对,以示优劣也。所以抑赐而进回也。”认为孔子意在褒颜回而贬子贡。宋人朱熹则训“与,许也”[14],即赞同,认为子贡所言有理,孔子赞同子贡的看法。后世学者所持观点大致不出如上范围,可以看出,后儒尊崇孔子,提出种种理由为孔子回护,都没有“坦诚”点出孔子认为自己不如颜回。从《仲尼曰》所提供的材料来看,孔子明确表示在某些方面不如颜回,承认“师不必不如弟子”,《论语》“吾与女弗如也”当理解为孔子告知子贡,自己和子贡都比不上颜回。两篇联系起来,可以看出孔子宽广的胸襟和实事求是的态度。
再看第九章:
仲尼曰:“回,汝幸,如有过,人不堇(谨)汝,汝能自改。赐,汝不幸,如有过,人弗疾也。”[3]43
这也是孔子将子贡和颜回两位弟子进行比较,孔子只是用了“幸”与“不幸”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在他看来,二人的差别分别是“人不谨汝”“人弗疾也”。两条都是外在因素,我们认为,这可能与当时颜回、子贡的社会地位有关,而并非学术专长。《论语·先进》篇记载孔子评价二人:“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在当时,颜回居于陋巷,可谓“安贫乐道”,没有什么社会地位;而子贡通过经商,积累了不少财富,社会地位较高。所以孔子认为由于二人地位的差别,当颜回有过错时,周围的人会不留情面地指出其误,促使颜回改正;而子贡人缘广、地位高,多为之回护,对子贡来说却是不幸的。
通过以上讨论可以看出,《仲尼曰》以“善”作为重要关键词,评论伯夷、叔齐时,赞美他们“见善女弗及,见不善如袭”,当遇到“不善”之时,避居以成己志,充分注意到了伯夷、叔齐饿死首阳山的事迹来完成自己的“判断”;而在评价管子时,以管子与齐桓公“身后事”的对比行文,强调管子能够“善善”即注意举荐贤能获得善终,而齐桓公在任贤上未能“从一而终”落得凄惨下场,两则内容凸显了该篇重用贤能的主题。《仲尼曰》中孔子对颜回的评价,让我们看到孔子“自叹弗如”、实事求是的态度,可以解决《论语》学史上的一些争议问题;对颜回、子贡“过”问题的比较可以让我们更多了解孔子对“过错”观念的认知。从某种程度上说,《仲尼曰》所记是对《论语》相关记载的进一步解释和阐发。
三、 余论
根据整理者的研究,《仲尼曰》文本和《论语》《礼记》《大戴礼记》相同或者相近的大致有17章,我们认为除了第十九章“季康子使人问政”实际与传世文献并无联系外,其他16章确实可以参照。这些资料与传世文献相比,第七、十二、十三、十四、二十、二十二章在文字表述方面略有差距,但差别不大;第一、二、三、四、五、二十一章则在文字、行文以及内容多寡上有较大差别,尤其在内容上都明显少于传世文献,或者可以看作是传世本的缩减。
从《仲尼曰》所关注的内容来看,志为君子、修身成仁、谨言慎行、为善任贤等等是孔子所重视的。该篇行文多以“君子—小人”“善—不善”“仁—不仁”等对比的方式呈现。从文本来源看,《仲尼曰》所载不一定是出自《论语》《礼记》,但至少可以知道他们有着共同的史料来源。从行文来看,《仲尼曰》的文本,为了强调整齐性、对比性、简洁性和主旨的凝练,多是对原有资料的摘引,因此与传世文献相比,大都删减了部分内容。其论述,又多引古圣先贤行迹作为例证,并非简单直白的训诫。据此,我们可以认为,《仲尼曰》是一种围绕孔子言论进行的主题凝聚的文献摘引,这也与该篇最后所言“仲尼之短语也,朴慧周极”[3]44一致,或许可以说明该篇的成书时间不会太早。
附记:本文写作尾声时,陈民镇先生惠赐大作《论安大简〈仲尼曰〉的性质与编纂》,其就《仲尼曰》的主旨、编纂、时代等问题进行了很好的研究,尤其是关于年代的判断言之有据,颇多创见。笔者同时亦以初稿呈奉,我们阅读对方文章后发现部分观点“不谋而合”,但论证却“互为补充”,其文刊于《中国文化研究》2022年冬之卷,特记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