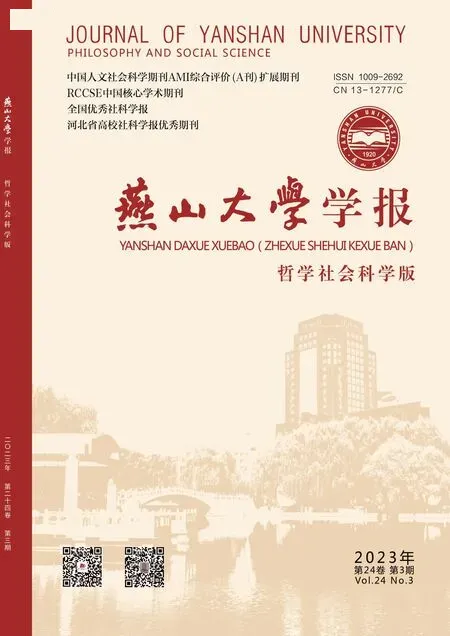后心学时代的朱陆之辩
——以整庵与南野关于“性”“良知”之辩为中心
2023-08-07陈力祥
陈力祥,陈 平
(湖南大学 岳麓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明代前期,理学的发展以程朱理学为主流,明中晚期,姚江渐起,大有取程朱之学而代之之势。彼时之学界,争讼纷纭,宗程朱者批陆王为禅机,宗陆王者讽程朱以支离,莫衷一是。罗钦顺(号整庵,1465—1547)有见于心学流衍中出现的诸多问题,撰《困知记》对陆象山、王阳明一系的心学思想进行批判。整庵认为,心学最大的问题是心、性不分,甚至只言心,不言性。如,他指出:“盖心性至为难明,象山之误正在于此,故其发明心要,动辄数十百言,亹亹不倦,而言及于性者绝少。”①继而又指出:“佛氏有见于心,无见于性,象山亦然。”②象山之学只言心,不言性,所以整庵认为象山之学与禅学无异。自然,同属于心学的阳明之学,也被整庵归之于禅学,成为了《困知记》的批判对象。整庵曰:“佛氏之所谓性,觉而已矣。其所谓觉,不出乎见闻知觉而已矣。”③又指出:“《传习录》所云:‘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又云:‘道心者,良知之谓也。’又云:‘良知即是未发之中。’……此皆以知觉为性之明验也。”④整庵批判象山只见心而未见性,批判阳明是心性不分,两人都已偏离儒学正道,堕入了禅学。欧阳德(号南野,1496—1554)不满于整庵以阳明“良知说”为异端的论断,乃致书申辩。二先生之论辩是理学史上继朱陆之辩后,理学和心学的一场重要交锋。清代学者张贞生在《困知记》序文中指出:“明之有整庵,非犹夫宋之有晦庵哉?……晦庵之在宋,整庵之在明,皆于异学争鸣之日,独排群议,引人归实。”⑤张贞生将晦庵、整庵并提,认为两人在尊正统、批心学、辟异端方面厥功甚伟。从心学和理学的论战史来看,整庵与南野以“性”“良知”为交锋点的论辩,可看作是后心学时代对朱陆之辩的继承与延伸。这场论辩从认识论、工夫论而上达于本体论,不仅延续了朱陆“尊德性”“道问学”之辩,更是对理学和心学中的核心概念进行了条理鲜明的辨析,并且都对自己所秉持的学术立场之核心思想进行了发展或修正。因此,无论是对理学还是对心学,这都是一次理论完善与重构的机会。
一、认识论维度:“良知是知觉”与“良知是性”之辩
整庵与南野的论辩是由认识论开始的。整庵注意到:禅宗的理论多有附会儒家学说之处,因此,学者多为其所惑,特别是有明以来,不少学者“复潜有衣钵之传,而外假于道学以文其说”。⑥这实际上已经将矛头指向了以阳明及其弟子为代表的心学一派。整庵认为:“佛氏之所谓性,觉而已矣。其所谓觉,不出乎见闻知觉而已矣。”⑦儒家和禅宗都讲“性”,但是儒家所讲的“天命之谓性”的“性”与禅宗所谓“见性成佛”的“性”是有区别的。禅宗强调主体的“觉”,认为主体一旦达到“觉”的境界,就是达到了成佛的境界。但是禅宗所谓的“觉”,其判断标准来自于主体本身,并且依赖于主体之耳目手足,可以看做是主体的感官接之于外界事物后所产生的感觉,即所谓的“闻见知觉”。尽管禅宗有所谓“法离见闻觉知”的说法,但是整庵认为,“闻见知觉”与其所谓“明觉”其实只是一物而已。禅宗言“作用是性”,又说“作用”是“在眼曰见,在耳曰闻,在鼻辨香,在口谈论,在手执捉,在足运奔”⑧之类的见闻知觉。实际上,这种感官知觉与儒家所说“性理”的“性”完全不同。虽然整庵的论断是要辟“异端”,但是其话锋也同时指向了以王阳明、湛甘泉为代表的心学一系,因此,他认为“良知即天理”的说法就是“以知觉为性”。本质上来说,整庵认为阳明所谓的“良知”就是“知觉”。
南野不同意整庵以“良知”为“知觉”的看法。南野在给整庵的信函中,首先对知觉与良知两者之内涵做了分判,认为“知觉与良知,名同而实异。⑨”对“知觉”与“良知”的区分,其实是要在本质属性上将感官所产生的知觉与理性(主要是道德理性)相分别开来。具体说来:“凡知视、知听、知言、知动,皆知觉也,而未必其皆善。良知者,知恻隐、知羞恶、知恭敬、知是非,所谓本然之善也。”⑩可见,南野所理解的知觉是指“视听言动”一类的感官知觉,而良知则是“知恻隐、羞恶、恭敬、是非”的道德理性。其后,南野又对感官知觉与道德理性做了性质的区分:依赖于感官所产生的知觉并不一定是善的,但是“知恻隐、知羞恶、知恭敬、知是非”的道德理性则必然是善的,南野称之为“本然之善”。最后,南野指出,尽管“知觉”和“良知”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但两者也是紧密联系的。这表现为:“良知”的呈现依赖于“知觉”的产生,是非善恶的道德判断不能离开视听言动。南野曰:“就视听言动而言,统谓之知觉;就其恻隐、羞恶而言,乃见其所谓良者。知觉未可谓之性,未可谓之理。知之良者,盖天性之真,明觉自然,随感而通,自有条理,乃所谓天之理也。”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说,“良知”包含在“知觉”中,“知觉”不能称之为“性”,也不能称之为“天理”,但“良知”则可以称之为“性”,由此,“良知”即是“天理”,而非“知觉”。
整庵对此不以为然,认为孟子所谓的“良知”与视听言动之“知觉”是一致的,并非在“知觉”之外又有一个“良知”。整庵以佛教认识论为例,指出:“楞伽有所谓真识、现识及分别事识三种之别,必如高论,则良知乃真识,而知觉当为分别事识无疑矣。”佛教《楞伽经》将认识分为真识、现识、分别事识,其中“真识”类似于真知,也就是佛教所谓“明心见性”的“性”;“现识”即耳目等感官功能所产生的知觉。显然,整庵认为人的认知不可能分别出“知觉”与“良知”来,“知惟一尔,而强生分别,吾圣贤之书未尝有也”。正是因为“知觉”与“良知”都是一个“知”,所以将“良知”当做“天理”是混淆了体用之间的差别。整庵强调:“盖天性之真,乃其本体,明觉自然,乃其妙用。天性正于受生之初,明觉发于既生之后。有体必有用,而用不可以为体也。”“性”是体,“觉”是用,两者截然分判。不仅如此,从先后性来看,“性”的存在不依赖于主体知觉,它是在主体知觉产生之前就独立存在的先在之物,而“觉”则是在主体的感官功能发生作用之后才发生的。整庵之所以要突出地强调这种体用先后的差别,实际上是要确立道德理性的客观性、先在性与绝对性。在整庵这里,道德理性的存在不仅不依赖于感官知觉,而且在地位与先后顺序上也要高于且先于感官知觉。
南野意识到,析“知觉”“良知”为二,不免让人割裂二者之关联。为回应整庵“知惟一尔”的论断,在接下来的论述中,南野进一步阐发了“知觉”与“良知”的内在关联,以此来辩驳整庵“良知即知觉”的责难:
某之所闻,非谓知识有二也。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知,不离乎视听言动;而视听言动,未必皆得其恻隐、羞恶之本然者。故就视听言动而言,统谓之知觉;就其恻隐、羞恶而言,乃见其所谓良者。知觉未可谓之性,未可谓之理。知之良者,盖天性之真,明觉自然,随感而通,自有条理,乃所谓天之理也。犹之道心人心,非有二心;天命气质,非有二性;源头支流,非有二水。
如果说在前面的论辩中,南野更强调“知觉”与“良知”在具体性质上的区别,那么在这段陈述中,南野则更加注重“知觉”与“良知”的联系。南野认为,良知的呈现不能离开视听言动,也就是说,道德理性的产生是需要依赖感官知觉的。尽管视听言动未必能直达本然之善,但是,“知”包含了视听言动之类的感官知觉,也包含了“知恻隐、羞恶、恭敬、是非”的道德理性。因此,以感官知觉为代表的感性认知与以道德判断为代表的理性认知共同组成了“知”。当认知发用于视听言动的时候,主体的感官知觉产生了;当认知发用于道德判断的时候,主体的道德理性产生了。南野还以“道心”“人心”为类比:“道心”与“人心”两者都是主体“心”的作用,从源头上来论,是一本二殊,因此,“知觉”与“良知”从根本上来说,都源自于“知”本身,是“知”这一源头的两条“支流”。继而,南野又从体用的角度将理论做了进一步推进,所谓“体用一原,体之知即用之知,则亦本无二知”。何以体现“体用一原”,南野论证道:
凡所谓日履者,吾心良知之发于视听思虑,与天地人物相感应酬酢者也。夫人所以为天地之心、万物之灵者,以其良知也,故随其位分日履,大之而观天察地,通神明育万物,小之而用天因地,制节谨度,以养父母,莫非良知之用。离却天地人物,则无所谓视听思虑感应酬酢之日履,亦无所谓良知者矣。……良知必发于视听思虑,视听思虑必交于天地人物。天地人物无穷,视听思虑亦无穷,故良知亦无穷。
良知的呈现要通过视听思虑、感应酬酢等方式体现出来。不难看出,南野所构建的良知理论体系并不是纯粹向内的,而是外向于天地万物、人伦日用的,这体现出其哲学思想鲜明的实践性。南野不否认天地人物是主体感知的来源,认为当主体感知到外在世界的时候,良知自然能够根据不同的情况作出相应的反应。伦常日用的产生是内在良知与外在知觉共同作用的结果,主体的内在良知只有在人的视听思虑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事物后才能呈现出来,而呈现的结果就是“事君当忠、事父母当孝”这样的伦理纲常。
在这一层面的论辩中,整庵的主要目的是要厘清儒学所说的“性”与禅学所谓的“性”之间的差别。整庵看到了感性和理性之间的沟壑,并且驳斥了感性认知的不可靠性。整庵意识到,认识论的问题必然会上升到本体论,他所遵循的是朱子的理性主义原则和客观性原则:一是通过主体感官获得的知识不可靠,不能上升为“天理”;二是主体的认知具有差异性,认知的结果是主观的,而“天理”是客观的。整庵之所以判“良知”“知觉”为同一“知”,就是要从根源上杜绝将主观认知或感性认知当做理性认知的可能性。南野则试图以“体用一原”来打通知觉与良知的沟堑。阳明虽然主张“良知不由知识闻见而有,而知识闻见莫非良知之用”,但是阳明又认为:“一有私欲,即便知觉,自然容住不得矣”,甚至提出:“凡知觉处便是心,如耳目之知视听,手足之知痛痒,此知觉便是心也。”按照阳明的说法,“知视听”“知痛痒”的“知觉”也可以称之为“心”,阳明又谓“心即理”,那么从逻辑上来说,则“知觉”亦可称之为“理”。这说明阳明确有知觉、良知混沦一体的倾向,这也是整庵对阳明“良知说”进行批判的一个重要原因。将知觉与良知混沦一体,也就意味着感性和理性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这将导致在认识论上滑向主观主义。南野对“良知说”的贡献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以“体用一原”的理论阐述了“知”“良知”“知觉”三者之间的关系,这样一来,“良知”与“知觉”之间的关系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二是,将“良知”的呈现放之于道德实践当中,这意味着只有在道德实践中,通过感官所产生的感性认知与“良知”所特有的“知恻隐、知善恶”的道德认知才能打并一块,圆融贯通。
二、工夫论维度:格物穷理与发明本心之辩
正是因为有了认识论的差异,所以在工夫论上,二先生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思路。整庵认为:认识的对象不是主体的知觉,而是外在于主体的客观天理,因此要穷究物理,博通典训,然后贯通主客。南野认为:事有善恶,致知就是要将主体内心“知恻隐、知善恶”的本然之善扩而充之,不让内心的良知有所亏歉和遮蔽。这种差异具体又从两方面展开:
首先,在“物论”,即所格对象上,二先生的理解不一致。事实上,在朱学与王学之较量中,“物论”之差异正是二者学术差异的一个重要体现。如朱子曾明确指出:“凡言物者,指形器有定体而言,然自有一个变通底在其中。”朱子在这里将“物”定义为“形器”“有定体”,这说明朱子对“物”的理解更侧重于具体的客观事物,如朱子所说的“气”或“器”。而具体的形器是外在于主体的,也就是说格物者与所格之物之间有非常明确的界限,朱子的这一理论曾被阳明批判。阳明的学生徐爱曾以“先生‘止至善’之教,已觉功夫有用力处。但与朱子‘格物’之训,思之终不能合”请教阳明。阳明回复曰:“朱子格物之训,未免牵合附会。”随后,徐爱终于悟出了朱子与阳明在“格物”论上的差别:
爱曰:“昨闻先生之教,亦影影见得功夫须是如此。今闻此说,益无可疑。爱昨晓思格物的‘物’字即是‘事’字,皆从心上说。”先生曰:“然。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于事亲,即事亲便是一物……所以某说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
徐爱发现,朱、王在“格物”论上的对立源自于两人对“物”之理解有差异。阳明显然是更侧重于从人伦日用的层面去阐述“物”,因此,在格物穷理的立场上他主张“夫求理于事事物物者,如求孝之理于其亲之谓也。”阳明的意思是,格物穷理不能离开主体本身,因为伦理道德规范本身就是源自于主体的道德性,所以,阳明认为:“物者,其事也。”从朱子的“凡言物者,指形器有定体而言”到阳明的“物者,其事也”,可知,理学与心学在“格物”论的理论基础上之分野已昭然呈现。
整庵以《周易》为理论依据,指出:“《彖传》有云:‘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此天理之在万物者也。吾夫子赞易,明言天地万物之理以示人,故有志于学者,须就天地万物上讲求其理,若何谓之纯粹精,若何谓之各正。”整庵明确提出“理”在万物,而不在人心,这是为“理”确立客观性原则。因此,整庵认为学者格物以求理,是要在天地万物上去寻求天理。由于从天地万物当中所格致的“天理”没有掺杂人的主观意欲与立场,因此,是纯粹精微、无所偏倚的。整庵意识到,如果将“天理”安置于人心当中,那么则会产生“道理全在人安排出,事物无复本然之则”的后果。
南野则循阳明一路,更加明确地将“物”规定在人伦日用之上,他指出:“物者,事也。思虑、觉识、视听、言动、感应、酬酢之迹者也。上而天子之用人理财,下而农商之耕凿贸易,近而家之事亲事长,远而天下之正民育物,小而童子洒扫应对,大而成人之变化云为,莫非思虑、觉识、视听、言动、感应、酬酢之迹,皆其日履之固然而不可易者。然而有善有恶,有正有邪。格物者,为善而不为恶,从正而不从邪,随其位分,修其日履,循其良知之天理,而无所蔽昧亏歉者也。”南野在这里不仅进一步肯认了“物”就是治国理政、洒扫进退之事,甚至还指出“物”有善有恶,有正有邪。物之善恶正邪,阳明未有论述,朱子更不曾云。南野的说法有直接融合主客的倾向,这其实是要为“良知即天理”树立理论依据。正是有了这个理论支撑,在工夫论上,南野提倡内向寻求进而扩充良知的修习方法。他指出:“致知云者,非增广其见闻觉识之谓也。循其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知,而扩充之以极其至,不使其蔽昧亏歉,有一念之不实者。”致知并不是简单地拓宽自己的见闻之知,而是要遵循内心所固有的善性(四端),不断扩充,以到达极致,不让自己内心的善有一丝蒙蔽。
其次,基于“物论”之差异,二先生在如何“格物”的问题上也产生了显著的分歧。整庵承朱子“理一分殊”之说,指出:“盖此理在天地则宰天地,在万物则宰万物,在吾心则宰吾身,其分固森然万殊,然止是一理,皆所谓纯粹精也。”主宰天地万物的是同一个“理”,因此,尽管天下万物形形色色,但是从其根本上来讲,有蕴含着“理”这一实体。整庵认为,理是客观的,万物同具一理,但良知是主观的,“今以良知为天理,即不知天地万物皆有此良知否乎?天之高也,未易骤窥,山河大地吾未见其有良知也。万物众多,未易遍举,草木金石吾未见其有良知也。求其良知而不得,安得不置之度外邪!”若说草木金石都有良知,无疑会堕入泛神论,因此,从这个角度看,良知并不具有普遍性,不能把良知当做天理。正是基于这一理论前提,整庵指出,格物之功就是要“穷究物理、博通于典训”:
圣贤经书,人心善恶是非之迹固无不纪,然其大要,无非发明天理以垂训万世。世之学者,既不得圣贤以为之师,始之开发聪明,终之磨礲入细,所赖者经书而已。舍是,则贸贸焉莫知所之,若师心自用,有能免于千里之谬者,鲜矣。
经书所纪者,都是人心善恶是非,但是其核心要义是要阐明“天理”以教后世之学者。在依靠经书的前提下践履工夫,才有可能豁然贯通。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经书是给学者提供了一个入学的门径和为学的目标。如果找不到为学的门径和目标,那么必然会导致师心自用,谬之千里,最终学无所成。
整庵不仅指出了“穷究物理、博通典训”的重要性,还指出了王学“易简工夫”的弊端:
然“易简而天下之理得”,乃成德之事。若夫学者之事,则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废一不可。循此五者以进,所以求至于易简也。苟厌夫问学之烦,而欲径达于易简之域,是岂所谓易简者哉!大抵好高欲速,学者之通患。
从为学次第来看“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五者不可偏废,而“易简”是在踏踏实实做好了五种为学功夫之后所达到的一种自然状态,所以,“易简”并不是工夫。整庵所主张的是由博而约,因此他认为,学问思辨的工夫尽管看起来繁琐,但是对于学者来说却十分的必要,因为只有在泛观博览,穷究物理之后才能达到豁然贯通的境界,做到主客、物我不二。整庵也看到了当时学者急功近利,投机取巧的为学之风所带来的弊病:“盖方是时,禅学盛行,学者往往溺于明心见性之说,其于天地万物之理,不复置思,故常陷于一偏,蔽于一己,而终不可与入尧舜之道。”人人皆在心性上做文章,但鲜有人能沉下心去穷究“天地万物之理”,所以长此以往便陷溺于空谈心性,奉主观之体验为天理,这显然与儒学所主张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之工夫背道而驰。
南野认为,学问思辨都是明善之工,是要知晓本然之善,而本然之善就是良知。这个理论基础决定了南野在工夫论上必然走向自省内求之路,南野的逻辑是:“良知,至易至简,而其用至博……夫学者学其所不能,良知之用至博,皆不学而能者也。”良知之发用近而知孝亲敬长,远而知仁民爱物,这说明尽管“良知”归约起来是至易至简的,但是却又能在伦常日用当中应付自如。因此,良知虽谓之简,但其用不可谓不博。因为良知是人人所固有的,是人的内在道德理性,因此是不学而能的。此处要注意的是,南野虽然认为良知是不学而能的,但是,他同样强调良知是会被私欲所遮蔽的,所谓“蔽于私而后有不能,则必学而后能”。南野意识到,如果单纯强调良知的道德属性或过度提升其绝对性,那么必将导致整庵所谓的“师心自用”之后果。所以,南野并不否认在“学”上下功夫的重要性,甚至认为“离本然之善,则别无可学可问之事;舍学问之繁,则别无至易至简之功也”。从学问的目的来看,是要达到“本然之善”的境界,从学问的工夫来看,易简之功也要通过增长知识来实现。发明良知与学问思辨的工夫并不割裂,相反,对为学者来说是相得益彰的。为学要达到本然之善的境界,只不过,如果不先发明良知之至善本性,而贸然去学,那么最终只会导致“真妄错杂,善恶混淆,必有不知不明者”。因此,南野所要强调的并非是发明良知与学问思辨何者更重要的问题,而是两者先后的问题,亦即工夫次第的问题。
二先生于工夫论层面的论辩是要解决朱子学与阳明学长期对立的一个焦点问题——格致工夫与发明本心的对立问题。显然,无论是整庵还是南野,均无意于抛弃其中之一以论格物之精义。二先生之分歧在于,格致与发明到底何者在先。整庵进一步发展了朱子认识论中的客观性原则,以“天地万物”为格物对象,认为格物就是要以天地为参照,进一步确立了天理的客观性、纯粹性。整庵的思想呈现了明代理学走向气学的倾向。
三、本体论维度:天理与良知之辩
整庵在《困知记》中指出,阳明所谓“良知即天理”是“以知觉为性之明验”。南野也指出:“心性理气之辨,其要欲学者识取本性,体认天理,而知所用力。”因此,整庵与南野在认识论与格物论上的分歧,最终还是要归因于二人在本体论上的分歧。值得注意的是,二先生本体之争以心、性的展开为依托,最终回归于“天理”“良知”之争。具体说来:理学重性,朱子曾指出:“论性,要须先识得性是个甚么样物事。程子‘性即理也’,此说最好。今且以理言之,毕竟却无形影,只是这一个道理。在人,仁义礼智,性也。”朱子承程子之说,认为天理体现在人身上就是仁义礼智之性。而心学重心,阳明有言:“心即理也;学者,学此心也;求者,求此心也。”阳明认为,仁义礼智都是具于人心而不假外求的,因此,学者所孜孜以求的天理都在人心之中。
整庵之所以认为阳明所谓“良知即天理”是“以知觉为性”,是因为他对“心”“性”等范畴做了明确的区分:
道心,性也;人心,情也。心一也,而两言之者,动静之分,体用之别也。
也就是说,“心”是唯一的,但是之所以有“道心”“人心”之别,是因为“心”有动静和体用之分。显然,道心是“寂然不动”者,是体;“人心”是“感而遂通”者,是用。因此,可以认为道心是天理,而人心则不是天理。整庵继而又对“天性”“明觉”做了一一分辨:
天性正于受生之初,明觉发于既生之后……所谓“人生而静,天之性”,即天性之真也;“感物而动,性之欲”,即明觉之自然也。在易大传,则所谓“天下之至精”,即天性之真也;“天下之至神”,即明觉之自然也。在诗大雅,则所谓“有物有则”,即天性之真也;“好是懿德”,即明觉之自然也。诸如此类,其证甚明,曾有一言谓良知为天理者乎?
在这段论述中,我们可以粗略地总结出“天性”之于“明觉”来说,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其客观性、先在性。“天性”在人受生之初便已存在,这也说明天理的存在是不依赖于主体的,整庵将这种客观性称之为“有物有则”。从这个层面看,整庵更加明确地对主客体进行了区分,天理的客观性不仅在于它先在于主体,也在于它的“寂然不动”,更在于它是对宇宙客观原则的呈现,因此,主体的良知不可当做天理。进一步讲,天理的运行依照客观条理,而良知正是天理在主体之上作用的结果。整庵之所以要将天理规定为“静”,是因为静的属性是恒常的,统一的,所谓:“至理之源,不出乎动静两端而已。静则一,动则万殊。在天在人,一也。”天理作为至高原则,不管在宇宙万物,还是在人类社会,都具有唯一性和绝对性。整庵认为,“误认良知为天理,于天地万物上,良知二字自是安着不得,不容不置之度外尔。圣人本天,释氏本心。”儒家所讲的天理,是本之于天的,而佛教却把心作为最高的原则,这是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天地万物,异彩纷呈,不可以用“良知”二字来安顿。显然,整庵在这里是借批评佛教的本体论来批评王学的理论立场与佛教本体论瓜葛不清的现状。
南野则试图以“体用一原,动静无端”来取消体用、动静之间的对立。因此,对良知和天理的关系,南野论之曰:“盖天性之真,明觉自然,随感而通,自有条理者也,是以谓之良知,亦谓之天理。天理者,良知之条理;良知者,天理之灵明。知觉不足以言之也。”南野赞成整庵的观点,即一般意义上“识痛痒、知冷暖”的知觉是不可以当做“性”的,因而也就不可能当做天理。但是,良知与知觉不同,良知是纯粹至善的知,而知觉则不一定,因此良知就是道德本体,就是天理。为回应整庵“良知不可谓之性”的诘难,南野提出:“又尝自念,孟子论性善,以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为言,程门学者,亦以乍见入井,其心怵惕,为天理之自然,所谓良知者也。故窃意良知二字,正指示本性,而使人知所用其力者。”可见,良知的存在是先天的,它具备至善的道德属性。南野进一步阐释了知与性的关系:“性非知则无以为体,知非良则无以为性”。综合来看,南野要阐明的是,良知与天理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天理是良知呈现的内部依据,良知是天理的表现形式。南野否认以绝对动静的观点去考察本体的状态,因为良知作为本体是动中有静,静中有动的:
静而循其良知也,谓之致中,中非静也;动而循其良知也,谓之致和,和非动也。盖良知妙用有常,而本体不息,不息故常动,有常故常静,常动常静,故动而无动,静而无静。故凡动而无静、静而无动者,物也。良知,新知神明,妙万物者也,“体用一原,动静无端”者也。
本体具有恒常性,那么,本体的运行也就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事物可以用动或静的状态来表示,但是良知的发用却是不会停止的,这种恒常的状态是稳定的,因此,本体的状态是“动而无动,静而无静”。
总之,从二先生对“天理”“良知”的论述中,不难看出,二先生关于本体的探讨并不是完全在同一层面。整庵显然更侧重于讨论宇宙本体,因此他认为“圣人本天”,天理是客观的。而南野则侧重于讨论道德本体,他认为在天地之中,“人”是天地之心、万物之灵,是宇宙当中最重要的存在。而主体之所以能够通过观察天地万物之情状,知晓天地之大道,或根据天地之运行化育的规律,制定伦理道德规范,无非是因为良知的作用。“人心”在己,“天”在外,而且,从宇宙万物运行的特点看,都是良知之发用,因此体悟到了良知也就体悟到了天理,良知没有与天地万物相割裂,它恰恰就是天理本身。
四、结语
罗整庵与欧阳南野的辩论可以说是明代哲学史上朱子学和阳明学的一次重要辩论。二先生尽管都秉持着各自的学术立场,但是也并非是完完全全地恪守朱子或阳明的学术理路,双方对朱子学和阳明学核心概念的论辩有攻有守,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朱子学和阳明学的革新。
整庵以理气论为基础,批判了阳明学甚至是明代以来哲学中存在的诸多弊病。一方面,整庵认为,阳明之学,以知觉立教,混淆了人心、道心,最终会滑向异端。借批判王学直达本心的易简工夫,批评了自心学滥觞以来,学界当中存在的轻视格物致知工夫,轻视博通典训的现象。他痛惜于当时学者急于求成,师心自用的急躁学风,批判了将主观感知当做天理,导致物我不分,以自我感知为中心的唯我主义。另一方面,整庵也意识到朱子学天理、人心二元、主客对立的矛盾,在与南野的辩论中他清晰地认识到,如果人与天理相割裂,则必将导致入圣无门的后果。整庵认为天人物我之间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因此他更加重视主客之间的相互融合。但是,整庵始终以客观主义的原则对“理”进行规约,认为理在万物,而不在人心,所以体认天理就必须有扎实的格物工夫。当然,从整庵重视“物”,重视理的客观性来看,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朱子学和阳明学的弊端皆已显露的情况下,整庵试图以气学来拯救儒学的思想倾向。
从南野对阳明之学的辩护来看:一方面他更加明确地厘清了“知觉”与“良知”之间的界限,极力遏制将主观感知当做道德本体的倾向,竭力避免心学滑向佛学;另一方面,尽管南野认可“良知说”,但是同样也重视“学”“格物”“修善”的工夫,认为只有修其善以去其不善,方可体悟良知之妙境,工夫的作用在发明本体的过程中是十分重要的。南野还将良知的呈现放之于“日履酬酢”当中,所谓:“离却天地人物,则无所谓视听思虑感应酬酢之日履,亦无所谓良知者矣”,这就意味着,离开了人伦日用这个实践基础,良知就不会呈现。在南野这里,良知不是放任的,而是有所约束的,良知的呈现要依赖工夫,良知的展开需要依赖工夫。以工夫来规约本体,这就为体认本体提供了一条明明白白的途径,这不仅说明了良知并非是虚无之物,也说明了伦常日用对于良知的呈现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毫无疑问,南野的理论是要对王学发展到后期逐步放任、沦为狂禅的现象进行纠偏。
注释:
①[明]罗钦顺著;阎韬点校:《困知记》,中华书局,2013年,第45页。(注:以下凡引《困知记》文献,均采用此版本,且只注明书名及页码。)
②《困知记》,第148页。
③④《困知记》,第70页。
⑤《困知记》,第251页。
⑥《困知记》,第60页。
⑦《困知记》,第61页。
⑧《困知记》,第63页。
⑨[明]欧阳德著;陈永革编校:《欧阳德集》,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12页。(注:以下凡引《欧阳德集》文献,均采用此版本,且只注明书名及页码。)
⑩《欧阳德集》,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