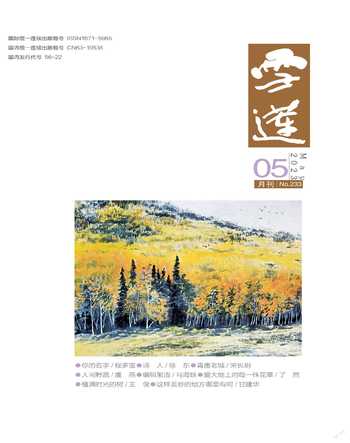植满时光的树
2023-08-06王俊
棠 梨
我们去学校读书,要经过那棵棠梨。它长在伯母家菜园的边上。乡下的家禽家畜多半放养,不围进圈里。牲畜常常趁人不备,钻进园中糟蹋蔬菜。伯母便在棠梨的周围种了许多棵枳树。枳树三面围拢,拥簇成篱笆的形状,是菜园的一道绿色屏障。棠梨迎着阳光生长,树干笔直,令枳树自渐形秽,褪去锋芒,变得谦卑起来。
棠梨虽然长得高大,却并没有获得村人的高看一眼。在我的童年记忆中,棠梨背负着一个贱名字:狗屎梨。以狗屎作前缀,与那些好吃的梨区分开身份,表达的情感一目了然。一次,伯母在菜园地里除草。偶尔抬头,望见棠梨密密枝叶飘逸出团团绿云,忍不住说道:“狗屎旺狗屎梨。”“旺”是动词,展现了被滋养对象的勃勃生机。伯母说这话是有依据可循的。不知什么缘由,村里的狗都喜欢跑到棠梨树底下拉屎撒泡尿。棠梨不负众狗的期望,春天的暖风一吹,枝干渐渐抻开,由褐色变成浅色,一天天柔软起来。
清早,我们背着书包蹦蹦跳跳走在小径上。棠梨的枝桠斜斜地探向路面,挡住了去路。细碎的花朵浩浩荡荡地缀满枝头,一窝蜂似的嬉闹着聒噪着。棠梨和桃树、梨树一样,绿叶总是靠后冒出来,花朵先开为敬。目之所及,每条枝干都濡湿着雪的洁白。花朵开得密不透风,阳光穿透不了,只能伸出微软的小舌头舔着。不一会儿,阳光有了微醺之意,呼出来的气息幻作一个个泡泡,全是浓酽的甜味。我们穿过棠梨花影,碰碎了阳光的泡泡,浑身沾染上甜甜的香气。站在花下,想起“盛极”二字,低回不已。“彼尔维何?维常之华。”有比棠梨开得更盛的吗?有吗?我痴迷棠梨的盛放,好几个傍晚,什么都不想,站在树底下,任由那一片片洁白,慢慢在心底铺展。而后,由心底自在地升起,融进头顶上的朵朵白云。春风骀荡,花朵飘落,晃悠悠地流入沟渠。傻傻的我多么希望那些花朵在枝头上慢慢开,多停留一会儿,不要那么快颓败。花朵的生命是如此的短暂,它可以闪耀春光乍泄的美好,也蕴含着零落无人问的淡定。
古书《西溪丛语》中认为牡丹的雍容之态,当为贵客,梅的清远雅致,博得清客之名,却把棠梨列为鬼客。我颇喜欢棠梨的别名,契合了某种神秘的气息。明明花开得灼艳,一切是那么美,偏偏遮掩不住凄迷和哀婉。棠梨是蒲松龄笔下的聂小倩,浑身充满邪魅之气,让人心猿意马。眼前浮现出一个园子,采采卷耳的女子倚着棠梨花枝,凝望远方,沉思。一片片花瓣恰似平平仄仄的诗句,满园都是簌簌而落的寂寞。花依然绽放昔年的明丽,人依然是旧梦中的那人。这景落入诗人的眼中,仿佛是唐代,又仿佛是宋朝,遂有了迷离,有了挥之不去的怅然若思。篱笆边的马蹄声近了,远去了。地上皆是素洁的花瓣,暗香浮动,一如清凉的月色。
时光低吟,绿叶长出来,满树荡漾起层层波浪。一粒粒青果被绿叶掩着,几乎不为人察觉。等我们惊讶发现青果时,它们已经长至乒乓球般大小。可是,青果的脾气大,心眼小得很,容不得孩子们站在树下评头论足。往往怒从心生,不再继续蹿着成长。插完晚稻秧苗,棠梨的果实上多了几道暗红色的纹路。日渐成熟的香气到处弥漫,仿佛人世所有的日子都值得去期盼,去等待。祖母说,果子到了时辰,都喜欢红脸,爱散发迷人的香味,这是丰收的讯息。
事实上,棠梨开出的花非常美丽,果子实在不敢恭维。依祖母说,甘蔗不能两头甜,哪有好事都占尽的道理。棠梨的外形看起来与梨颇相似,但皮肉与梨相去甚远。棠梨瓷实,邦邦硬,投掷地上,能砸出一个小窝来。其果肉粗粝,汁水少,嚼在嘴里干干的,涩涩的,无味得很。无怪乎村人叫它狗屎梨,大有深意存蔫。后山林子里的鸟雀没有人类娇气,自是不会嫌弃棠梨的不是,窺探到丰收的讯息,全飞出来了,云集在棠梨的枝头上。啁啾若阳光一样穿过树叶的缝隙,悉数泻漏下来。鸟雀拍拍翅膀,啄啄果子,然后鸣叫。我和表弟拿着弹弓跟着鸟雀来到棠梨树下。表弟是我姑姑的大儿子,家住河北——村庄的四周满是被河水冲上岸的砂砾。一年下来,田里打不出几担粮食。正月里,姑姑回来拜年,将表弟和一头老水牛留给了祖母。表弟和村里的孩子一同上山放牛。放完牛,他去地里挖蚯蚓,捉蚂蚱,或是跳进池塘里摸螺蛳,采菱角。祖母管不住表弟,骂他是野孩子。表弟发现林子里的鸟雀和树叶一样多,便偷来舅公家平车轮子上的橡胶,制作了一把弹弓。
“看,好多鸟,好多果子。”表弟仰头望了望树上的鸟雀,又瞥了瞥压弯枝桠的果子,情不自禁地吞咽了几下口水。他把弹弓别在裤腰上,朝掌心吐了两口唾沫,双脚一蹬,就爬上了树。表弟再滑下树来,兜了一怀棠梨果子。来不及清洗,抓起就往嘴里塞。“咯嘣”,果皮差点把表弟的门牙硌坏。他吐掉满嘴的渣,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祖母笑着打趣他:“你真是狗屎梨,好看不中用。若是好吃,它长在路边上,别人不识,偏等着你去摘?”
祖母教我们把棠梨果与冰糖一同放入锅里煮。煮透了,果子酷似晶亮的琥珀,味道极佳。印象里,我们围着灶台,不时地掀开锅盖,察看棠梨果子煮烂没有。祖母坐在小板凳上往灶膛里送木柴,看着我们急不可耐的样子,嘴角弯成了柳枝上的叶子。我和表弟把煮出来的水装进碗里,再添水进锅。一碗接一碗,即便喝掉最后一碗,犹难罢嘴,只好捧着喝过的空碗,舔完碗沿,舔碗底。如今回想起来,疑心自己的味觉是遗留在那段旧时光里。因为我时常感觉不到现在水果的香甜,吃不出它们该有的味道。
棠梨材质坚硬,是难得的好木头,适合打家具。村里的姑娘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家人便备下棠梨木打嫁妆。邻居家的明叔成婚,新婶子进门抬来的五斗橱,就是棠梨木打的。每次走进他们的房间,看着五斗橱亮着清幽莹润的光泽,我的心里便盼着自已快长大,能拥有棠梨木的嫁妆。岂不知,四季轮转,草木更迭。长大意味着与童年、少年有关的象征物,都会在时间的惯性里走完人生的最后旅程,悄然作别西边的云彩。而这一切,我们对此无能为力。
数年后,一个风雨交加的夜里,菜园边上的棠梨轰然倒下。折断的枝干横在路中央,荡然的树墩处汩汩流淌的汁液,像极了它告别人世流下的泪水。十二岁的我经过那里,想到它再也不能衍生新生命了,心里突然痉挛了一下。由一株棠梨,我读到了生命以及世事无常。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那株棠梨倒下后,村里其他的棠梨像是约好了一般,陆陆续续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没了踪迹。当然,和它们一起离开我们的,还有祖母。万物大抵有自己的命数——人和棠梨终究归于大地,终将成为过去。
乌 桕
辛弃疾在《临江仙·戏为期思詹老寿》中写道:“手种门前乌桕树,而今千尺苍苍。”我们都知道,辛弃疾生逢乱世,少年时意气风发,中年后一直没有得到朝廷的眷顾,无奈之下归隐田园。卜居上饶的铅山瓢泉,他建了屋宇,种下乌桕。树木慢慢成长起来,气象森然。站在树下,辛弃疾想起豪情受挫,不免仰天感叹:“七十五年无事客,不妨两鬓如霜。”一棵树,不管曾经拥有怎样的无限风光,最终都无法抵挡韶华的流逝,人又如何能躲得掉这个生命过程呢?一襟晚照,徒留满腹心事寄乌桕。读辛弃疾的词,觉得他活得实在太辛苦了,理应借助乌桕一吐为快。
且看同样人生不得意,同样偏爱乌桕的陆游。晚年,陆游定居山阴。一日,途经一湖。夕阳西下,秋水泛着金色的涟漪。到处是枯枝败叶,一派萧索的景象。秋风乍起,吹起陆游飘飘衣袂,随之而来的是深入骨髓的凉意。蓦然,一株株经了霜的乌桕笼着耀眼的光华出现了,孤独而沉郁的心好像触摸到一丝暖意,遂作《晓晴肩舆至湖上》。眼处心生。与其说陆游看到的是绮丽的乌桕,还不如说是看到自己真实的内心。人在面对美的时候,总会牵动无尽的愁思。那些所思,那些所感,欲说还休,欲说还止。当然,能说出来的愁就不是真的愁了。那种愁,无疑是结了痂的伤口,痛早已长进了身体里。愁思落在心头,便是沦为天涯人,饱尝人间的悲苦。说到底,愁绪是相通的。只不过陆游用情至深,那落寞凄冷的心绪犹如一根线,隔了近千年以后仍在缠呀绕呀,千转百回。一不小心,寸断了柔肠。
宋朝的文人若是走投无路,一江春水如何载得动那个“愁”字?在颇多彷徨的日子里,一次次朝乌桕的张望,使得他们积郁内心的愤懑脱口而出。个人化的情绪与水色、天色、秋色融合在一起,缔造了宋朝诗词中卓然而独立的气息。黑暗里,文人们孤绝的身影徘徊在天地之间,一种很浓很浓的哀愁和忧伤如大潮奔涌,扑向了他们和他们的时代,直至淹没。到了清朝,李渔在《闲情偶寄》中曰:“木之以叶为花者,枫与桕是也。枫之丹,桕之赤,皆为秋色之最浓。”李渔坦言,自然界予于树木之美,无非是两种呈现,一种以花的嫣然百媚的姿容吸引众人的眼球;一种是如枫树和乌桕那样,花朵过于平凡,容易被人忽略,只能仰仗叶子,历经时间的熔炼,逐一铺陈出荡气回肠的生命色。
乌桕是我的老相识。儿时,家门前的一条公路两旁种着乌桕。但那时我有眼不识嘉木,浑然不知它是充满诗意的树,只晓得跟在村人屁股后面,喊它勾子树。为什么叫勾子树?勾住人的眼和心嗎?勾子树最美的时光莫过于深秋了。那些开花的树木经受不起秋的销蚀,狼狈地退出舞台,而勾子树汇聚春夏阳光的灿烂,一步步走向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它们一开始有点娇羞,流泻着一小片的初红,好像孩童踮起脚尖遥望远方想念什么人似的。时间未到,勾子树绝不会将心底的秘密轻易示人。稍等些时日,霜愈重,哗啦啦地喷射出一片片黄和红,恍然是燃烧的晚霞,稳稳地栖落在公路边。萧瑟的秋天被勾子树掀开一角,里面驻了一缕缕光。但勾子树的美远不止这些。冬日,枝头上结的蒴果自然裂开,露出洁白的籽。远远望去,分不清是雪在恣意飞舞,还是梅花在散淡地开着。傍晚放学后,我们爬到枝丫上,采摘白籽。白籽装满书包,不急着回家,趁着天色淡黑,一路小跑,钻进镇上香烛作坊的院子。香烛作坊常年收购白籽,用以制作蜡烛。镇上有几家的灯亮了,光线都溜到柏油马路上来。我们每个人的手中攥着拿白籽换取的几张毛票,脸上流露得意的傻笑。暮色苍茫,沉沉地压着勾子树。万千枝条附满了一个个黑魆魆的影子,将乡野渲染得幽静淡雅起来。一群孩童默默走着,不感觉恐惧,心底反而流淌着音乐般的宁静。
日子在乌桕黄了又红中笃定地过去。很快,我的童年就结束了。记不清是从什么时候起,少年的我执意不肯穿那些颜色鲜艳的连衣裙,迷恋藏青色的棉麻衣服。我的心里充满了忧郁,变得沉默寡言,多愁善感。一种不确定的迷茫和恐慌,让我感到莫名的压抑,喘不过气来。我对伙伴们的游戏失去了兴趣,每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偷偷读《红楼梦》。某一日,我们全家坐在饭桌上吃饭。九月的黄昏,空气里酝酿着桂花的芬芳。母亲望着我日渐消瘦的脸庞,说道:“你去县城吧,那里书多。”母亲的话传入耳中,我却不敢接,埋头扒拉碗里的米饭。母亲只上过小学,却坚信书中自有千钟粟。她认为我之所以不快乐,是书读得太少造成的。
于是,每个周六,我都会早早起床,一个人独自乘客车去县城。县城西路有家诚章书屋。书屋以老板郑诚章的名字命名。郑诚章是旅美华侨,书籍进货的渠道比其他书屋的广。诚章书屋不仅有那个年代大陆畅销的小说、散文,诗歌等作品集,还有三毛、席慕蓉、萧丽红、余光中、蒋勋等台湾作家的代表作品。而且那时县城好多书屋找不到的外国文学作品,在他家的书屋都能看得到。这样的书屋,没有哪个爱书的人不喜欢。人被书屋里的墨香浸染久了,会觉得一辈子待在这里是件很美的事。我甚至一度艳羡扎着羊角辫的收银员,只管打扮得干干净净,整天和书打交道。
记得临近寒冬的一个早上,我走进书屋,随意挑选三毛的《雨季不再来》,寻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在地上铺着手绢,坐下。我仿若一尾沾着水珠的鱼儿,无拘无束地游弋在三毛的文字里。一本书翻完,三毛的悲欢犹如毛茸茸的苔藓占据了我的心。这片苔藓遇到了好天气,长势茂盛。倘若心有大地那么宽广,苔藓必定泛着幽幽的绿光,蔓延到天涯海角。我怅然地叹口气,下意识地抬头看了看墙上的钟。天哪,离回家的末班车行驶的时间仅有十几分钟了。赶不上车,晚上我就得露宿街头。我顾不上三毛的忧伤,慌忙冲向车站。
那天,坐车的乘客很多,脚都挪不开。我被人流挤到车尾,有如一张薄纸片,贴在了窗玻璃上。狭小的空间里,充斥着呛人的烟味和浓烈的体臭味。车子启动,目送县城渐渐远去,隐在我心底的忧伤忽然藏不住了,酷似一头小野兽吼叫着跳出来。公路两边的勾子树叶无着无落地飘坠,轻盈如蝴蝶。一些饱满的白籽躁动不安,蹦出蒴果,在铺着沥青的公路上滚来滚去。我看着它们,仿佛看到多年后自己的另一种存在形态。眼眶无端一热,泪水就溢出来。车里人声鼎沸,没有人留意我的忧伤和泪水,就如我们看到勾子树的美,却从不会去审视它真实的生命。
上高中的时候,读周作人的散文集,我终于把旧时的勾子树与乌桕对上号了。我有好多年没有看到它们了。老家公路两边的乌桕后来被砍掉,种上小白杨。这几年,行道树又换成了女贞。母亲说:“现在谁家还点蜡烛。镇里的香烛作坊早就倒了。”
我有一个画家朋友。每个季节,她踉踉跄跄地拽着风跑,试图用画笔记录下大自然的美。前年秋杪,她带我到武夷山下的一个小村庄写生。在村庄的山坡上,我再次遇见乌桕,黄得秾艳,红得彻底,层叠着蓬勃的生命气韵,仿佛时光交替。我的内心湿漉漉起来,那是属于辛弃疾和陆游的乌桕,也是属于我童年、少年时期的勾子树啊!尽管时光馈赠它们各自的悲欢,但仍向着秋天的深处闪耀灼人的光焰。
风自远古吹来,吹过乌桕曾经的喧哗和落寞。想起从少年到中年,不过隔着一株乌桕的距离,泪水簌簌落满山坡。
桐 树
雨一层一层下起来。窗前的桐树躲也不躲,迎了上去。不一会儿,每一片宽大的叶子密密甫出晶莹的水珠。水珠有大有小,有胖有瘦,却一律顺着叶脉朝叶尖的方向拱去,横一行,竖一行,如同书写一封长长的信。那是有多浓郁的情意和深沉的心事啊!雨中的桐树,疏离了喧嚣,漫漶着略微带野性的清芬。桐树是《诗经》里的嘉木,自带深意,蕴含着人间的情和爱。
我出神地望着窗外,听着雨打桐树,发出金属般的音质。宁走到我的身边,扑闪着大眼睛,轻声说道:“桐树长得真好看,多像着一袭青衫的书生。”我盯着宁的大眼睛看,她的眼睛长得清澈,宛如山野里的一汪泉水。两年前,宁高考落榜,被身为村支部书记的父亲安排进了学校当代课老师,与我成了办公室里面对面的同事。我问宁:“要不要出去走一走?”雨天,碰巧我们两人都没课的时候,共一把伞,以桐树为起点,走到学校后面的田畈,然后绕过一个小池塘,再返回。我们踩着水珠,一边走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宁尽管没有读过大学,但她读过不少文学作品,会写诗歌,会吹口琴,很有文艺范。我尤其羡慕宁的口琴吹得好,有一阵还向她学习吹口琴。可惜在音乐方面,我缺天赋,一直不开窍。吹了几天,把嘴角都吹出了水泡,还是吹不成调。一路上,我们聊童年和成长,聊文学和远方。偶尔,宁红着脸会聊她的未婚夫。
宁少与人交往,视我为朋友,把心底的秘密告诉我一个人。宁并不爱家里张罗的未婚夫。她和他无太多的交集,只在镇里的小饭馆吃了一顿饭,双方的父母就定下了这门亲事。我在宁的房间里见过男子的照片。矮矮胖胖,头大如簸箕。男子其貌不扬,但还算有胆有识。中学毕业去了珠海,靠打工赚了第一桶金。之后,自己做老板,经营一家家具店。听说在县城买了两套房,身价已经过了百万。在那个年代,他堪称成功人士,是典型的钻石王老五。宁嫁过去,不用奋斗,就过上锦衣玉食的阔太太生活。宁却不以为意,觉得爱情无关物质。她向往的爱情恍若一场春风,将人心吹软,所有的华美刹那间只为一个人盛放。记得一个傍晚,学校里的人都走了,空荡荡的。宁端了条长凳子,我们头抵头坐在桐树下读席慕蓉的《七里香》。夕光柔柔地穿过桐树,掉落在书页上,恰似時间数着一行行字在跳格子。当读到《无怨的青春》,宁的音量突然提高了许多:“在年轻的时候,如果爱上一个人,请你,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她站起身,风将满头的黑发吹得飞起来。良久,宁微侧过脸,像是同我说话,又像是喃喃自语:“柠月如风,莫负之。”我有一种隐隐的心疼。书上说,浮世三千,要以温柔相待的那个人,是一旦遇见了,就如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从今往后,眼里心里全是他的身影,绝不悔衣带渐宽。只是,尘世间哪有这般好的爱情呢?《红楼梦》里的宝玉与黛玉一见倾心。黛玉是真心独爱宝玉,宝玉却是和袭人相处久了,就有了肌肤之亲,看到宝钗也会想入非非,甚至对金钏儿调情,害得人家跳井身亡。我们究竟该相信有交心的爱情,还是该不相信呢?
到了夏天,桐树长得愈发茂盛,叶子渐渐挤满了办公室的窗户,若一匹锦缎笼在窗上。宁忙碌起来了。镇里组织各个学校参加文艺汇演,宁被选派表演吹口琴。每天,她上完课,就骑着自行车赶往镇里的大礼堂去排练。我们单独相聚的机会变得很少了。有一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看书。宁敲开我的房门,手里举着她奶奶做的新茶,笑嘻嘻地说:“我给你作伴来了。”
一片片清香的茶叶在沸水中依次舒展了身姿,有的沉入了杯底,有的浮出了水面。宁坐在床边,心神不宁地喝下一杯又一杯茶。我掩了嘴,冲她笑道:“这是茶,不是解愁的酒。”短短两个星期,我发现宁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每每和我聊天时,总会眯着眼,走了神,朝一个方向发呆。我扳过她的肩膀,逼视着她。她的心乱了,脸上蓦然飞起一片红云。我不再说话,安静地等着她吐露心声。宁犹豫了好一会儿,才咬着我的耳朵说喜欢上一个中学老师。那天,她走进排练的大礼堂,看见台上有个年轻的男子穿着长衫在清唱《尘缘如梦》。仿佛所有的时光都凝固了,世界静止不动。他的英俊挺拔,他的磁性声音,都让宁怦然心动,手脚变得冰凉。宁淡淡地笑道:“他如果穿长衫,定是《胭脂扣》中的张国荣。一回眸,满山的花都开了,涌动芬芳。”排练结束了,宁看到男子推着自行车站在树底下,像是等谁。等宁走过去,男子主动搭讪道:“你的口琴吹得真好听。”男子是中学的语文老师,姓陈。陈老师一日不见宁,就给她写一沓厚厚的信。每张信纸的右下方,都用红笔画着两个圈。一个是大圈,套着一个写着“宁”字的小圈。我和宁都知道,两个圈足以表达浓烈的情意。暗示着一个灵魂踏遍千山万水,终于寻找到了另一个与之相契的灵魂。他中有她,她中有他,不分生死。恍惚间,我想起了暮春桐树开花的样子。等许多花开尽了,桐树才铺好阵势,满不在乎地绽放,与春天的明媚抢夺光芒。它们开得太炽热了,每一片花瓣都染着春的风日洒然,无限地美着。
文艺汇演后,宁和陈老师的事传到了她的父母耳中。一个星期一早上,学校举行升旗仪式。宁的父亲骂骂咧咧地闯进学校,当着全校师生的面,强行将宁带回家。这个干了一辈子村支部书记的老头,觉得自己的颜面被女儿丢尽了。他甚至觉得宁放着好好的福气不去享受,都是代课惹出来的祸。
最后一次见到宁,是在一个黄昏。宁提着一个行李箱,跑来告诉我,她和家里闹翻了,把婚事也退了。我没想到,宁平常看起来文文静静的样子,却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我拉住宁的手,避开办公室同事们的异样眼光,来到桐树下,压低语气问道:“你知道陈老师考取研究生吗?”宁点了点头,笑着回答我:“知道啊。他走的那天,还是我偷着送他上的火车。”我蠕动了一下嘴唇,很想对宁说,你哪里知道有多少人在背后等着看笑话?在俗世的眼光中,毕竟一个代课老师和研究生,是门不当户不对的事。但我终究还是没有将这些肤浅的话说出口。宁说:“我这辈子跟定了他。我要去他的城市找一份工作。”我至今不能忘记宁眼中闪现的那一抹温柔,仿若桐花淡黄的蕊,擎着春天的欢喜。这庸常生活中的深爱,狂热得教人动容。夕阳将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打在桐树泼洒在地上的浓墨上,就成了它的一部分。宁走了不久,我也离开山村学校,进了城。
一晃好多年过去了,每逢佳节或是我的生日,宁会寄给我贺卡和小礼物。每张贺卡上,她都写尽了对桐树下那段时光的怀念。宁和陈老师最终执手相牵,成了眷属。我相信,宁一定会一直幸福下去。因为是她,让我看到美好爱情的存在。现在,我居住的房子窗前,亦有一棵桐树。若是雨天,我就会对着它轻轻说道:“你长得真好看,多像穿一袭青衫的书生。”
【作者简介】王俊,作品见《人民日报》 《文艺报》《散文》《湖南文学》《美文》《安徽文学》《山东文学》《星火》《四川文学》等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