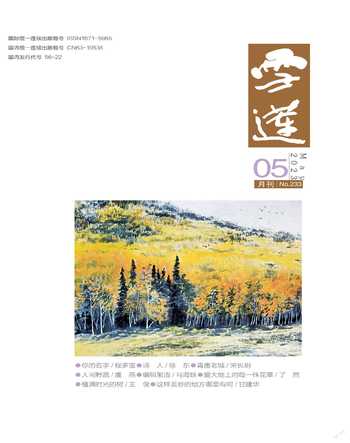母亲的棉田
2023-08-06郁小尘
春暖花开的时节,我从深圳回到故乡。见到母亲时,她正弯腰在村头的麦田里挖荠菜。看到我,母亲拎着装满荠菜的篮子,沿着地垄沟一路小跑过来,老远笑着说:回来了!总算回来了!春日的阳光打在母亲头发上,头顶灰白的银丝在阳光下闪着亮光。我接过篮子,拍掉母亲身上的泥土,母亲拉着我的行李箱,我挽起她的胳膊,我们沿着开满鲜花的田间小径,朝家中走去。
母亲显然很高兴,一路上有着说不完的话。她说,听说你要回来,我跟你爸兴奋得几宿没睡好觉,挖了不少荠菜放在冰箱里,巴望着你早点回来,吃上三月的荠菜。还记得吗?小时候你最爱吃荠菜了,我做的荠菜面条和荠菜饺子,你跟弟弟总是抢着吃。回到家,母亲开始择菜、剁馅、和面、擀皮,不大工夫便端出两盘荠菜饺子。
我在家的日子,母亲变着法子,做不重样的饭菜:摊煎饼、烙果子、煎菜盒、做蒸菜,这些我多年没吃过的食物,母亲让我尝个遍。看着母亲忙碌的身影,我能感到她发自内心的快乐。我说起小时候她送我的“小花狗”玩具,母亲哈哈大笑,说,这么多年了,想不到你还记得。
是啊,怎能不记得呢?小时候,我最羡慕同村的小伙伴翠翠。翠翠的爸爸在县城做工人,每次回家,总会给她带好吃的食品和好看的玩具。这些玩具吸引着我,引得我常往翠翠家跑,围着她的玩具转。母亲早已看出我的心思,那天吃午饭时,她说,妈妈也有玩具要送你。翠翠的玩具只能看不能吃,妈妈送你的玩具,既好看又好吃。她掀开锅盖,从热气腾腾的蒸笼里,捧出一只“小花狗”。“小花狗”自然是面做的:花白相间的身子,两只耳朵一白一黑,白色的鼻子中间,调皮地嵌着一片黑色,两枚红枣做成的眼睛,高高翘着的小尾巴,活灵活现,跟真的一模一样。我也有玩具了!我兴奋得跳起来,捧着“小花狗”往翠翠家跑,惹得翠翠非要拿她的玩具跟我交换不可。
我自小迷恋故事书和连环画,看起书来常不记得吃饭和睡觉。家里没书看,书多半是从小伙伴们那里借的,有时没看完就被要走,想着后面未知的故事情节,我难过得直掉眼泪
一天,母亲从地里回来背回一大捆茶树,进门就乐呵呵地说:村口有人在收茶树呢,干的五毛钱一斤。等卖茶树换了钱,我带你进城买书看。这种名叫“茶树”的植物,我至今不知它的学名,它生长于老东沟的沟边,自东向西绵延五六里地,据说是一种药材,洗干净蒸了晾干,可泡茶喝,有降火、利尿的功能。后来,陆续有开三轮车的城里人来村子收购茶树,二十多斤湿茶树能晒一斤干的茶树,村上人大都嫌太便宜没人愿意去拔。每次去地里做农活,母亲总要带一个大蛇皮袋,在收工时拐到老东沟拔茶树,回家时扛回一大袋茶树。母亲把茶树洗干净蒸了晾干,把卖茶树的钱一分一分积攒起来,每隔两三个月,她会在星期天带上我进城,把我带到电影院门口长长的书摊前,笑着说:想看什么,自己挑。我一口气挑了二十多本故事书和连环画,像捡到宝贝一样高兴。那时,无论生活多苦,日子多难,母亲想方设法从牙缝里省出钱,给我买书看。看到我捧着书看得顾不上吃饭,笑着问:娃,书里说的啥?母亲没上过一天学,不认识字,她对有学问的人十分敬重,总希望我将来成为有学问的人。
母亲喂养一群鸡,鸡下的蛋,她从舍不得吃,但每星期都要给奶奶煮几个鸡蛋。奶奶总是把鸡蛋藏起来,趁母亲不在身边时,悄悄塞给我和弟弟。母亲偶尔也会炒一盘鸡蛋,她把放干的馒头揉成碎末,打两个鸡蛋进去,兑少许水,再放上油盐和葱花,这样能炒出一大碗鸡蛋,吃起来酥香可口。
逢年过节,母亲总是变着法子,做一餐好吃的饭菜来改善一家人的生活:三月三包荠菜饺子,五月端午炸油馍,八月十五炕干饼,春节做蒸菜,母亲用一双巧手,把普通的饭菜,做出极其鲜美的味道。比如平常的豆腐,经过母亲的巧手,变成麻辣豆腐、家常豆腐、清炖豆腐、水煮豆腐等风味不同,口味迵异的佳肴。母亲在灶前忙碌,我和弟弟像馋嘴的麻雀围着锅台边,叽叽喳喳说个不停。在那物质生活极为匮乏的年月,我家不富裕的生活在母亲的巧手打理下,变得有滋有味。
年轻时的母亲,梳着两条又粗又长的辫子,嫁到王庄时,村里人都惊叹道:多像豫剧《朝阳沟》里的银环。但母亲不是银环,戏里的银环出生城市,不会做饭做农活,母亲农活、针线活样样拿得起放得下。
我的外婆在上了岁数后,无数次在我面前提起我母亲,叹息道:我生的这五个孩子,她干活最多,出力最大。七八岁就顶个大人。那时,你大舅在郑州帮工,你外公不理农事,地里活全是我一个人干。她是老二,要带你二舅、小舅、小姨,是姐姐,亦是母亲。哪个哭了,她要哄;哪个没鞋子穿了,她要做;哪个衣服破了,她要缝。家里有好吃好穿的,都给了弟弟妹妹,最重的活,她一个人包了。从12岁起,她就去三里外的宋庄挑水,一天往返四趟,压得个子不长,几个兄妹属她个子最矮。除了做家务,还要帮我做农活,被耽误了一天书也没读。这辈子,我最对不住的人便是她了。时值春天,院子中的月季花开得正艳,引来一群蜜蜂和幾只蝴蝶。外婆迎着阳光的眼睛湿润了,她撩起衣角偷偷擦眼泪。
从我记事起,父亲很少在家,他在外面做手艺活,用赚得不多的钱补贴家用。奶奶岁数已大,我和弟弟都还年幼,家务活和农活全压在母亲一个人身上。好在母亲心灵手巧,做事麻利,别人锄了一遍的地,她已是锄过二遍三遍了。母亲常说,“杂草不认爹和娘,耕作到家多打粮”,田地糊弄不得,人勤快了,地里庄稼才能收成好。
母亲的勤劳是出了名的,我家地里的庄稼在村上是长势最好的,收成自然也是最好的。每年青黄不接时,总有粮食不够吃的人家来我家借粮,母亲总是慷慨予以借出。记忆中,母亲永远是忙碌的,她每天早早起床下地干活,吃了午饭又匆匆下地去,天不黑不回家。她从地里回来,我和弟弟早已入睡。
母亲做农活是一把好手,她割麦子的速度,村里男女劳力无人能及。麦收时节,母亲是不回家吃饭的,我和奶奶把做好的饭菜送到地里。奶奶挎着篮子,扭动小脚小心翼翼在前面走,生怕不小心饭菜溢出。我拎着装凉茶的水壶跟在奶奶后面。一望无际的麦田像金色的毯子在面前铺展开来,麦香和着泥土的气息扑面而来,母亲脖子上搭条毛巾,弯着腰,左臂揽起麦子,右手迅速拉动镰刀,麦子纷纷倒下,她揽起麦子放成一堆,然后割第二垄第三垄。母亲挥动镰刀,身子随着金黄的麦浪起起伏伏,汗水顺着脸颊滚落下来,一滴一滴,落在黑褐色的土地上。我鼻子酸酸的,走过去轻声说:妈,该吃饭了!她用毛巾抹一把脸上的汗,头也不抬地说,割完这垄就吃。
麦收时节,母亲像连轴转的陀螺,割麦、捆麦、装车、拉车、摊场、打场、扬场、堆麦垛,一刻不停地忙碌,再苦再累,她从不抱怨,每天都乐呵呵的。母亲常说,土地是宝贝,可金贵着呢,只要人勤快,土里就能刨出食来,能刨出金疙瘩来。母亲还说,人活着哪有不干活的?不干活,一家人吃啥喝啥?愁眉苦脸是一天,欢欢喜喜也是一天,我们为啥不乐呵呵过一天呢?
在所有的农作物中,母亲种得最多的是棉花,较其他农作物,棉花更能卖上“好价钱”。春天的时候,母亲用棉籽育上棉苗,待棉花苗长成后栽进棉田,接下来浇水、施肥、锄草、喷药、打顶,看着它由一棵小幼苗逐渐成长,最终开花结果。棉花的种植工序极其繁杂,从育苗到摘收,正可谓“棵棵皆辛苦”。棉田要施足底肥,深耕细作,才能保证苗期早发,根深叶茂。每年春节过后,母亲便开始忙碌,她要趁父亲在家之时,把一年积攒的农家肥全部运到棉田里,把棉田耕作好,为后面栽种棉苗做準备。接下来,运肥、撒肥、耕地、打坷垃、耙地,父母起早摸黑在棉田里忙碌。待拾掇好棉田,也就进入了三月份,父亲收拾行李要出门了。接下来的农活,便由母亲一个人完成。她把收藏的棉籽拿出,在阳光下仔细挑选籽粒饱满的棉籽做种子,春分前后,把棉籽埋进土里,浇上水,上面用塑料薄膜覆盖,每隔几天通一次风,浇一些水。母亲如伺候初生的婴儿一般精心守候棉苗,一天去地里看几次。待棉籽出土发芽,长出叶片,叶片长大变成叶子,她撤去塑料膜,趁棉苗通风那几天,背上耙子到地里,把棉田里鸡蛋大小的坷垃再打一遍。待棉田收拾平整,棉苗移植出来,母亲便开始栽种了。
栽种棉苗是最为费力费时的,要保水保墒,才能保证棉苗稳健成活。栽种一棵棉苗,要浇一大瓢水。水是从地头的沟渠里,或是更远的池塘运回。运水的工具,有劳动力的人家,采用较为先进的方法:在架子车上放一个经油罐改造的大铁桶,把水装进铁桶,套上耕牛,拉进地里;另一种最原始最费力的方法,用扁担挑水。母亲一个人拉不动架子车,只得用担子挑。她担着桶走到池塘边,岸很高,她需把水桶放下,跳下岸,打满水,再一桶一桶提到岸上。母亲身材瘦小,把水桶提到岸上,需很大力气,她把水桶拎起,放在池塘边的石头上,然后双手棒起桶身,往岸上放。一挑水压在肩上,起步时,步行紊乱,担子总是左右摇摆,母亲的身子随之左摇右晃。她甩开手,迈开大步疾走,担子终于平衡下来。母亲一口气把水桶担到地里,放下扁担,轮起锄头刨土挖坑,再一瓢一瓢浇水,然后放苗。给棉苗封土时,为了省时省力,她跪于地上,身子前倾,匍匐大地,双手揽土封苗,为了多封几棵棉苗,母亲胳膊伸得很长,似乎想把整个大地拥入怀里。浇完一担水,封好土,她又去挑水了。一担水顶多浇三十多棵棉苗,一天要挑多少担水,母亲记不清。挖土、栽苗、担水、浇水、封土,母亲起早摸黑,整日在棉田里忙碌,一天下来,肩膀红肿,腰酸背疼,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一块棉田,从浇水栽种,通常要花七八天时间,母亲种了四块棉田,前前后后要一个多月的时间才能栽种完毕。棉苗栽种完毕,母亲浑身的骨头像散了架,躺在床上动也不动一下。来不及好好休息,接下来,又要追肥、除草、整枝、掐条、打药、打顶。经过多道繁杂的工序,棉株终于开花结果了。棉花开花结桃之际,正是棉铃虫肆意横行的时候,棉铃虫繁殖能力极强,隔三天就要喷洒一次农药。母亲通常选择在中午喷洒农药,因为中午杀虫效果最好。她戴着草帽,身穿长袖,顶着烈日酷暑在棉田里喷洒农药,有几次差点中暑。待四块棉田喷一遍,第二遍又要开始了。
一般农户都嫌种植棉花费事,没多少家愿意种植,但再苦再累,母亲总会坚持种棉花。棉苗栽下,母亲的心思全在棉花田里。七月下旬,棉花开始陆续吐絮,母亲的棉田,朵朵棉花肆意绽放,大片大片的白,似天上落下的白色云朵,铺天盖地,无边无际,这是何等圣洁、醒目与壮观!母亲立于地头,眺望着她日夜劳作的棉田,开出花,结出果,脸上的笑容如山花般灿烂。
棉花的采摘工作是漫长持久的,时间长且紧。摘棉季节,母亲守着棉田,夜以继日劳作。她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在太阳没出来前,用架子车拉回一车吐白絮的棉花桃。我和奶奶在家里剥棉花。母亲又去下一块地摘棉花了。母亲摘棉花时,腰间系一个长长的围裙,她将围裙揽起对折,用绳子绑在腰间,左手摘左边的几垄棉花,右手揽右边的几垄棉花,棉花开的植株高低不同,摘棉花时,她伸长手臂,时而弯腰,时而蹲下,两手同时行动,身手灵活快捷。摘好的棉放入围裙内,待腰间的围裙里放满,她小心翼翼把棉桃倒入大箩筐里,然后接着采摘。母亲做农活简直是个天才,把我和父亲远远抛在后面。我们一垄还没摘完,她已摘了三四垄。天完全黑下来,母亲才从地里回来,匆匆吃过晚饭,又开始剥棉花。如遇天气不好,母亲整夜在棉田摘棉不敢睡觉,因为棉花最怕雨淋,变了品质。棉花盛开的季节,地里的棉田像个聚宝盆,总有摘不玩的棉花,今天摘完,明天又灼灼开放。棉花一茬一茬地开放,母亲一天一天地忙碌,她从不叫一声苦。忙碌一季下来,可卖得三五百块钱。母亲把钱一分一分积攒起来,累积了几年,我家终于住上了青砖绿瓦的新房子。
家里有辆纺车,不知什么时候传下来的,久经使用,手柄磨得又光又亮。奶奶一年四季坐在草垫上纺棉花。冬季农活少的时候,母亲让奶奶晚上早些睡觉,接替奶奶纺棉花。我半夜醒来,常常听到嗡嗡的纺线声。黑夜迈着步子冲进大地,月亮从半开的窗棂边探出头来,月光跑进屋子,母亲身着粗布碎花棉衣的身影,镀上了一层银光。母亲如莲般端坐在纺车前,右手摇纺车,左手捏着棉花捻子,纺车转动,捻子吐出棉线,如蚕吐出的丝,均匀而绵长。待到左手抽线抽满长度时,右手一回,纺车旋即倒回个半圆,纺车扇片把套在上边的引弦拉着车头上的铁锭子迅速倒转起来,母亲左手轻轻一扬,抽出的线规规矩矩地缠绕在锭子的线穗上。母亲捏棉花捻子的左臂举起、放下,时高时低,周而复始,在空中划着优美的弧线,在墙壁上投下好看的影子。母亲粗长的辫子随之转动。棉线缠在棉锭上,结成线穗,像半斤重的萝卜一样,底平体圆,头部呈椎形又尖又合式,精美好看。每上满一个线穗,母亲小心翼翼把它卸下来,摆放一边,有时一晚上能纺出四五个线穗。母亲把线穗放在织布机上,织成布,染了颜色,最后做成衣服。布的颜色,蓝色黑色居多,红色绿色也有。母亲把棉线染成各种颜色,在织布机上织成五颜六色的棉毯,铺在床上,舒适而好看。母亲把粗布做成棉衣,虽然只是黑的蓝的颜色,母亲总能让衣服锦上添花。她在我的衣服上面,绣了多彩的蝴蝶和七色的花朵,奶奶的衣服,母亲更是自出心裁,那镶嵌的好看布扣,成了美丽的装饰,让蓝布粗衣变得如此与众不同。
年年岁岁,岁岁年年,母亲一年年在地里劳作,我家的生活一天天在发生变化。从草房子到瓦房到平房到三层楼房再到县城的房子,母亲守着田地,用勤劳的双手给我们营造一个虽不富裕,但充满温馨的家。当我们一天天长大,母亲却一天天老去。
我出嫁那年,母亲选出上好的棉花,做了八床厚厚的棉被给我做嫁妆。母亲说,买的被子虽好看,但不及自己做的棉被暖和。家里没啥稀罕的东西陪送你,这些被子,是我亲手种的棉花,一针一线缝起的,我把全部的心意都装进被子里了。“被子”同“辈子”,是要陪伴你一辈子的。抚摸着柔软的棉被,望着母亲满是皱纹的脸和松树皮般布满老茧的手,我的眼睛湿润了。
近两年,弟弟的孩子在县城读书,母亲便住进城里,每天接送孩子上学。一生劳作的母亲舍不得老家的田地,周末骑电车回家做农活。她把小区后面的一片空地开垦出来,一边种了蔬菜瓜果,一边种了花生、红薯、萝卜,还有一小片棉花,每天在地里除草、施肥、捉虫、整地精耕细作。与田地打了一辈子交道,上了岁数,母亲越来越离不开土地。
【作者简介】郁小尘,女,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在《短篇小说》《奔流》《雪莲》等刊物发表小说和散文,著有散文集《时光谣》。现居深圳宝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