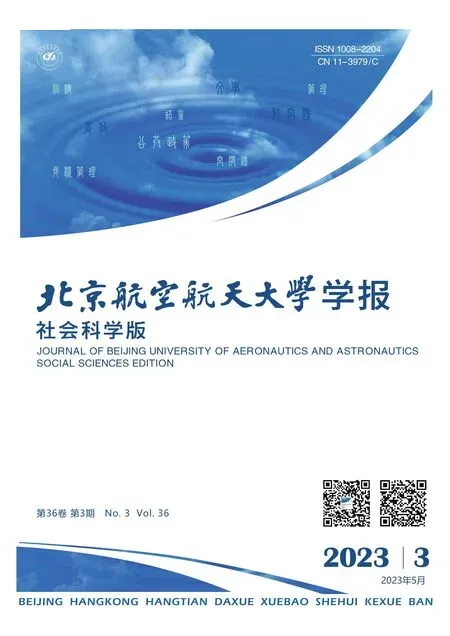探究卢曼早期法律思想的宗旨与意义
——在纪念卢曼《法社会学》出版50 周年纪念研讨会上的致辞(摘编)
2023-08-06季卫东
季卫东
(上海交通大学 凯原法学院,上海 200030)
一、写在前面的话
2022 年12 月11 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泮伟江教授策划和组织的“卢曼早期法律思想与方法——纪念卢曼《法社会学》出版50 周年学术研讨会”隆重召开,使得对社会系统理论抱有浓厚兴趣的老中青三代中国研究者能够聚集在一起,纪念卢曼的《法社会学》出版50 周年,探讨他的早期理论和方法。我认为,这个北京隆冬的雅集活动本身呈现出如下三点深远的历史意义:
首先,今天的研讨会标志着中国法学界的学说继受进入一个新阶段。它昭示:对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思想家进行解读不再像过去很长一段时期那样大而化之,更不应该停留在进行先入为主的意识形态化批判层面。它昭示:中国有些青年研究者在非常认真地、精密地推敲某种重要的一家之说,甚至以此为终身志业,并且形成了一个学术共同体,尽管还是很小众的。这对于学术传承和深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当然,我们同时也要小心预防在不经意间把这种卢曼社区塑造成一个完全自我指涉的封闭系统,甚至变成某种带有佛教密宗色彩的神秘小圈子,以至于让其他人对那些过度符码化的语言博弈及其超级循环侧目而视。
其次,从这次研讨的内容构成来看,既广且深,自成体系,可以作为法的社会理论在中国复兴的一个标志。实际上,只有通过恢宏的社会理论,只有通过二阶观察和反身性沟通,才能使那种容易流于碎片化、技巧化的法律实证研究获得分析框架和有待验证的各种假说。尤其是卢曼从生命科学、脑科学以及计算机科学的前沿动态及时汲取了灵感和概念,使他的法社会学理论能够超前适应数字信息化时代的需求,也能与中国方兴未艾的文理交叉融合的新文科构想一拍即合。
最后,卢曼本人是法律学科班出身,很重视对法律问题的探讨,从所有权、契约到程序公正都有非常精辟的论述。从在座有些研究者的发言题目也可以看出,法的社会理论与法律解释学主流之间其实存在很广阔的对话空间。因此,这次研讨会的召开也标志着社会法学与法教义学之间开始出现“眉来眼去”的合作默契,甚至构成一场超越疫情影响的线上学科交融“婚礼”。正如卢曼的同胞兼同行赫尔曼 ·康托罗维奇早就巧妙预言过的那样:没有法社会学的法教义学是空洞的,没有法教义学的法社会学是盲目的。两者构成法律运作机制的绝配,可谓佳偶天成!
二、卢曼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
我第一次见到卢曼是1987 年的盛夏,在神户举行的IVR 法哲学和社会哲学世界大会上,他应邀来做主旨演讲,主要以所有权为例阐述社会系统理论与法教义学之间的关系。欢迎晚宴期间,卢曼的《法社会学》的日文版翻译者、东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六本佳平特意把我带到卢曼面前加以介绍,当时只是互相寒暄而已。第二年樱花时节,卢曼应邀再次访问日本,到京都大学来做了一系列闭门讲座,参加的都是相关领域的专家,研讨会的规模与今天这个研讨会获准进入腾讯会议室的人数差不多。此次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和交流,还请他在日文译著《法律系统与法律教义》的扉页上做了签名留念。
作为学术泰斗,卢曼的人生其实是平淡无奇的,除了其收藏的九万张知识卡片的整理箱归属权存在争议之外,几乎无法找出能够充分满足窥私欲的故事和逸闻来。实际上,所有光彩夺目之处,都被一笔一画勾勒在他的思想画像里了。追踪卢曼的思想发展轨迹,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20 世纪60 年代至70 年代中期。在这一阶段,卢曼出版了早年的代表作《目的概念和系统理性——目的在社会系统中的功能》[1]。但这本书立刻被德国以及海外的学界打上了“社会工程”的烙印,有些研究者指责卢曼只注重系统整体的合理性而忽视了个人的主体性和自发性。在这一阶段,卢曼因为与哈贝马斯的那场著名论战而名声大噪,但也因为哈贝马斯对关于“危机控制”一段论述的引用和批判而被人贴上了“社会技术”信徒、保守主义者的标签,甚至大有被逐出“社会理论”教门之势[2]。《法社会学》德文初版于1972 年付梓,因此很典型地反映了卢曼第一阶段的思想特征,关键词包括从结构-功能主义到功能-结构主义、“功能等值”、“功能替代物”、系统对环境的“复杂性缩减”等[3]。
第二个阶段是20 世纪70 年代中期至80 年代前期。这是卢曼思想的转折点、过渡期。在这一阶段,著名的闭环化“自我指涉”概念开始凸显,而那种俨然居高临下的“复杂性缩减”概念开始渐次退隐到背景之中。在这一阶段,卢曼还特别关注法律系统运作中虚拟与悖论及其解脱的意义,最让人津津乐道的就是他那篇关于法官为解决遗产分配难题而借用第十二匹骆驼,在圆满结案后再把它归还给主人的妙文[4]。就像徐志摩形容的那样,法官“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那匹骆驼“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卢曼从那匹仅仅作为象征性符号的骆驼身上发现:系统只有以某种悖论为基础才能发挥功能。但是,悖论其实也会妨碍决定。为此,需要外部观察者,并把这种视角再转化为决定者的“自我观察”。
第三个阶段是1984 年《社会系统》这本书在德国出版之后[5]。在《社会系统》中,新概念“自创生性”铿锵登场,使卢曼的画风骤然一变。学界把这种变化称作卢曼的“自创生转向”。就在贡塔 · 托依布纳殚精竭虑,以这个概念为核心建构法律自创生系统理论之际,卢曼本人则周游列国布道,因而先后在日本的神户和京都访问并顺便给了我一次享受亲自接见、亲自解说的机会。实际上,卢曼本人也以自创生概念为极轴,对既有的理论框架进行了重构,形成了《社会的法律》[6]等一系列“社会的什么、什么”著作,对经济、科学、艺术、教育以及法律等不同功能系统逐一进行分析。可以说,从京都挥手一别的1988 年至他去世的1998 年这十年间,正是卢曼理论集大成的时期,他晚年的思想之花都渐次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三、卢曼早期思想中埋下的伏笔
应该怎样理解卢曼不同阶段的学说及其相互关联?实际上,20 世纪70 年代中期之后的两个思想阶段,即便有所谓“自创生转向”之议,也没有真正修改乃至否定第一阶段的主张,而只是把第一阶段论述中已有的或者潜在的想法,通过新的概念和命题展现出来加以强调而已。例如,在《法社会学》第4 章,卢曼明确提出了法律系统把一个过程运用于自身的“反身性”概念,强调法律实证化的本质在于开放各种变化可能性,从决定者和受决定影响者的双重学习过程发现学习型法律的规范生成机制,这里已经为关于“自我指涉”和“自创生系统”的命题群埋下了伏笔[7]。
如果说“复杂性缩减”更侧重系统作为整体自上而下地控制这个侧面,那么也可以说“自创生”更强调自下而上地涨落和涌现对系统的影响。但是,在卢曼的视野里,这两者并不矛盾,因为复杂系统的秩序正是在混沌的边缘形成,通过对过剩的可能性进行选择而实现重构和维持稳定。他从期望结构的角度来把握事实认知与规范约束,在期望、期望的期望、期望的期望的期望这样无限反馈的互动关系中找到作为社会最小单位的沟通,并通过沟通在社会系统中为主体找到了立足点,为意义脉络找到了在期望结构中的功能定位,为选择机制找到了反复重组的契机。因此,可以说,在卢曼的早期思想里,还可以进一步找到解答后续各种理论谜语的重要线索以及理论创新的方法。
在我看来,这正是纪念卢曼《法社会学》出版50 周年、探讨他早期法律思想的宗旨所在,也是此次研讨会的学术价值所在。相信这样一场跨越时空的风云际会,必将在卢曼理论研究的历程中留下一群中国学术骑士的深刻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