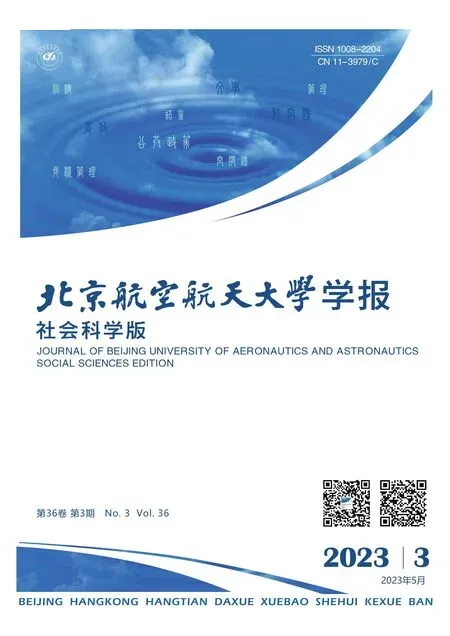晚明儒者管志道的学思历程探析
2023-08-06王硕
王 硕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北京 100083)
晚明儒者中多奇俊人物,管志道(1536—1608 年,字登之,江苏太仓人,世称“东溟先生”)便是其中之一。东溟修习儒学,同时亦出入佛老,以促进三教对话为己任,提出了一套内容丰富、面向多元、重视析理且颇具特色的三教融合论,留下了逾百万言的著述。从其与他人的往来信牍中可以发现,东溟与同时代的重要思想家多交往密切,且曾作为多场学术论辩的核心人物,如与顾宪成、高攀龙的“无善无恶”之争,与许孚远、李材、万廷言、王锡爵等的“乾卦义理”之争。然而,在《明儒学案》中,东溟却被划入他本身极力排抵的“泰州学派”。在介绍其人其学时,黄宗羲没有摘引任何语录,只以约百字一笔带过,并给予了极其负面的评价:“著书数十万言,大抵鸠合儒释,浩汗不可方物……所言亦只是三教肤廓之论。 ”[1]东溟之所以有如此遭遇,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在于他突破了多数儒者容纳、吸收佛道教义的最大限度。在传统学术“醇正-驳杂”“正统-异端”的二分标准下,东溟的思想形态与理论贡献难以得到充分认识和公允评价。随着明清之际的政治变革与学术转型,东溟的实际影响也被“泰州”“狂禅”一类的抽象标签所淡化和遮盖,从而长久地隐没在晚明思想世界的背景中,不为人所瞩目。直至近代,才有学者开始注意到东溟,并对其思想地位进行提揭。例如,钟泰先生曾谓:“《明儒学案》评东溟所言为‘三教肤廓之论’,此是梨洲不通释典之故,实则明儒中能会通儒释、穷极理蕴,未有过于东溟者也。 ”[2]日本学者荒木见悟也认为,东溟可谓晚明思想界的“飓风之眼”[3]。近年来,随着阳明后学研究不断向深处推扩,部分二、三传弟子乃至旁支流脉都渐渐走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其中,黄宗羲圈定的“泰州学派”受到了颇多关注。此派思想家多具有鲜明的个性,他们的“组合”引发了学界有关王学分系以及明代思想叙事范式的激烈讨论。由于被划为“泰州学派”之一员,东溟在这番热闹中也是频受点名,但对其思想开展个案研究者依然屈指可数①。笔者先前已对东溟思想的一大重要面向即三教合一论进行了简要介绍[4]174-181,于此拟转换视角,对其思想探索的整个过程开展历时性考察,勾勒并划分其学说萌芽、转折、发展、成熟的不同阶段,从而呈现其思想源流与学说概貌。通过这一研究,以期能够增强研究者们对东溟思想的了解与兴趣,使其进一步深入丰富而复杂的晚明思想世界,为其窥见此一时期儒学多元展开的动力与趋向助力。
一、早年经历与理学自修
明嘉靖十五年丙申(1536 年),东溟出生于太仓州(今江苏太仓)一个普通的农籍之家,家族上推五代都无人获得过士籍。他天资聪颖,自幼便对超越之存在表现出极大的好奇心。在与友人周弘礿(字元孚,号二鲁)的信中,他曾自述道:“为儿童时,每望日月星辰之上,而疑其有异境;亦望目前所接人物之外,而疑其有异人。雅不喜与群儿嬉戏,而胸中常若有乐意然者。 ”[5]698这种沉静内敛的性格特征以及探究终极的天然喜好,可以说是其后来产生三教分合、宇宙终始之问的最初源头。
东溟六岁就傅。弱冠以前的他并不着意于考取功名,而是以博学多识、了悟性体为志。在广泛涉猎的过程中,他接触到周敦颐、张载、邵雍、二程、朱熹等理学家的著作,尤其喜好研读《太极图说》《皇极经世》一类艰深晦涩之书。由于这些书无关科举,东溟时常受到师长责骂,但他却不以为意,反而“因思古之作者何人哉?而以第一等事让人也”[5]698-699。即便是在以应试为目的的阅读中,东溟也在思考终极问题。例如,他在学习《性理大全》时,受北宋儒者陈烈“静坐以求放心”一案的启发,曾做过百日的灭念工夫。通过这次静坐实践,东溟自觉妄念稍净,有所进益,却仍未能真正豁见性体:“予当总角时,颇慕濂洛之学,尝于《性理大全》中,见陈烈苦无记性,有所省于孟子‘求放心’之说,遂释卷静坐百日,此后一览无遗。亦以灭念之功效之。念不能灭,则寄心于一字,如‘清’、‘虚’、‘空’、‘一’等类,念亦稍净,然而未见性体,功夫无凑泊处。 ”[6]2-3
但弱冠以后,东溟在学问上有放松之态,且转而歆慕长生之术,期盼科举高中。作为家族中少有的读书种子,为实现亲人的殷切期望,东溟压力倍增。他自叹俗念丛生,精神上也不再有和乐顺适之感:“念日散,虽亦效嚬儒先,以尊孔孟、辟佛老为话头。而以禀气之素弱也,亦慕长生。又以小试之不利也,尤羡高第。自慨凡念满腔,何以迈今追古,居恒悒悒不自适。 ”[7]75
管氏一族无家学传统,所居乡里又罕有大儒良师,因此,东溟人生的前二十余年,基本处在一种学术自修的状态中。他虽在习举业之余,对广博的道学世界进行了独立的探索,但由于缺少师友的指津,所学十分驳杂,且未能对性体有深切的会悟。他本人在追忆时常常慨叹少时“苦无启我以入路者”“工夫无凑泊处”。而就此一阶段的思想立场而言,东溟服膺濂洛关闽之学,“程朱之所是亦是之,程朱之所非亦非之”[5]728。他持理学正统立场,强烈排斥佛老二氏。有关早年的辟佛主张,东溟曾回忆道:“尝研《性理大全》一书,有触于张子《正蒙》中道理,而猛然起辟佛之念焉。却嫌韩子《原道》、《论佛骨表》之为浅,欲深入其室而攻之。 ”[5]750
二、心学提点与悟机初开
嘉靖四十二年癸亥(1563 年),耿定向(1524—1596 年,字在伦,号楚侗,世称“天台先生”)以督学按临昆山,时年二十七岁的东溟受其知遇,拜入其门。在得遇恩师前,东溟曾在梦中获得三重“闻道之兆”。在晚年撰写的自传中,他对这三个梦境进行了追忆。限于篇幅,于此仅举其中之一为例:“身行阛阓中,见督学使拥道前来,一时万户俱闭,唯有一门尚开,即趋而避之。登其堂,摆有三层神位。前两层皆菩萨塑像,最后一层,则三尊佛影像也。予先入佛座下,向左蹲立。学使随入,与吾对立。有供果从佛位撤下,余拾三果,学使倍之。 ”[6]3-4古今中外的许多思想家都曾有过在梦中获得灵感或启示的经历,但东溟写下这段文字时,距离梦兆发生已经过去了数十年,可文字却依然十分具体生动,连数字、方位等细节也皆历历在目。一般而言,人在梦醒后常常只能忆起梗概,而无法复原出梦的完整内容,且这种模糊的记忆也很容易在短时间内被人遗忘。东溟能够进行如此清晰的描述,虽不排除他有及时记录梦兆习惯的可能,但终究难免有后期想象加工之嫌。换言之,他的解梦之说,极有可能是其思想体系成熟后的“投射性”诠释。然而,倘若搁置对此段文字可信度的质疑,单就所记录的梦兆数量之多、立意之高来看,便知受学于耿定向,对东溟一生而言是何等的重要。他曾自述曰:“未遇之先,虽读诗书,心花难发……及遇督学耿恭简公,进以求仁之学,恍然有悟,放心不期收而自收。 ”[6]2-3
嘉靖四十三年甲子(1564 年),东溟秋试落地,奉老师之命前往留都(今南京)明道书院担任都讲,这段经历对他来说可谓是思想转进的一大界碑,故在此详引其自述,曰:“明年为嘉靖甲子大比之年。既落榜,蒙师召入明道书院中,迪以求仁之学。偶读师所自状,寝席间理会‘明哲’意旨,心花忽开,刹那间若另换一乾坤也者。于时方悟孔子志学关窍,凡六经四书疑义靡不豁然。侧听一切先达同志绪言,皆若灌我以甘露也。除师教外,则唯受盱江罗先生之警策居多,而夹持则李翰峰、李茹真、杨太岳、焦漪园诸丈之助不浅焉。时有泰州布衣王东崖者,心斋之子也,朝夕凡二十日。接其言,恍然如在阳明、心斋授受之际。其指点当下本体尽亲切。究到圣学神化处,辄曰:‘揣摩不得。’然则道岸作何究竟乎?”[7]76
在明道书院问学期间,东溟延续了早年穷究性史的兴趣,仍以对心性本体的解悟为核心课题与最高境界。耿定向认为“孔门宗旨,归于求仁”[8]217,东溟遂在此一头脑下开始了对心性新一轮的体察。上文提到的“明哲”意旨,也是耿定向的一大主张。《诗经 · 大雅 · 烝民》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中庸》引述此句谓:“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而后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谓与!”耿定向起初对此处引《诗经》之意甚为不解,后经反复咂摸,最终悟入“明哲之体”:“夜来伏枕,时反身内观,一无所有,唯此些子炯然在此。始信人之所以为人者,唯此明哲体耳。此体透彻,此身乃为我有,是以大哉之道属之圣人。理会至此,不觉手舞足蹈于衽席间也。 ”[8]288东溟有省于老师的经历,很快也产生了“恍然如在太虚中,无我无物”[6]5的体验。
除了老师的启迪,东溟还与焦竑(1540—1620 年,字弱侯,号澹园,又号漪园)等同门学友相与切磋,并得以结识当时的多位名人宿儒。例如,耿定向曾延请与阳明高第王畿(1498—1583 年,字汝中,号龙溪)并称“二溪”的罗汝芳(1515—1588 年,字惟德,号近溪)前来讲学。其后,罗汝芳与耿定向在南京的明道书院联举讲会,泰州学派的王襞(1511—1587 年,字宗顺,号东崖)也参与其中。东溟自认从罗汝芳处获益更多,二人此后始终保持着密切的交流,直至罗汝芳去世。在与王襞朝夕相处的二十天中,东溟如沐春风,“恍然如在阳明、心斋授受之际”[7]76。但从他回忆时所说的“其指点当下本体尽亲切,究到圣学神化处,辄曰‘揣摩不得’”[7]76可以看出,东溟虽由此一段学习而对阳明心学的本体与工夫有了亲切、深入的了解,但却并未完全接纳心学的主张及成为阳明的追随者;他虽受师友的提点与夹持而心花忽开、有所悟入,但却并不满足于当下的体验,而欲进一步追究宇宙的最高本源。这一时期的东溟在思想进益的同时,也陷入更大的矛盾与困惑,无法自解。一方面,他十分自信,认为自己已经把握了儒学的关窍:“真信得孔子之志学,曾子之唯一贯,不过如此而已。 ”[9]36另一方面,他又怀疑圣人之学不当止步于此:“却疑天纵如夫子,志学又先我十余年,乃迟至七十而始从心不逾矩,何也?”[9]36他心中仍留有并不断迸发出“道岸作何究竟”的追问。
在东溟看来,拜入耿门乃是他学问定向的最初机缘,也是天命的安排,正所谓“得遇恩师岂偶然,三现奇征显宿缘”[6]4。他曾在多处记述中,将此机缘描述为自己排斥佛道与融贯二氏之间的一个分水岭:“将壮,偶入弇山人之戏论曰:‘儒家安能以道理胜佛?除是韩文公所谓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如祖龙焚坑手段,乃能以势力胜之耳?’于是疑心隐隐然起:岂佛氏果有入微入妙之言,足以动高明之士耶?则又念弇山人,文豪也,见地岂逮程朱?闢佛之念转切,徒以未尝多阅其书,不敢轻议其理,默而含之有年。及遇天台先生,既有悟入处,然后取其书而阅之。每到说心说性去处,则字字句句,若道着我胸次中事,而后悔从前之见之狂且陋也。 ”[5]750但笔者认为,明道书院的这段经历虽是东溟学思历程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但相对他会悟三教共法,提倡儒释道合一的最终主张来说,此间的思想转进只能算作一个过渡准备阶段。其真正放弃辟佛立场,进而证明儒释教理相契,仍有赖于下一阶段的思想突破。
三、证合三教与潜心实践
经过两三个月短暂而充实的书院修习,东溟于当年(1564 年)腊月辞别一众师友,乘舟归乡。途中遇到衲僧明德,相与盘桓数日:“甲子冬,虽稍有悟,而心体未成一片。阻风仪真江边,偶遇牛山衲僧明德,能言单传大意,及火场炼磨消息,大有助于性体。始知百尺竿头,尚有进步去处。 ”[6]5明德来自伏牛山,其与东溟所言“单传大意”“火场炼磨”皆为禅宗旨意。东溟借助禅门的修炼法门体证自身心性,在先前心学式体验的基础上又有所进益。这使得东溟更加坚定了继续探求性宗的信念,同时也对佛教产生了好感与兴趣。
嘉靖四十四年乙丑(1565 年),是东溟学思历程上的又一个重要时间点:“馆毂锡山华氏。有旧馆宾曰钱斋长邻虚者,颇研二氏之学,以《楞严经》授余读之。展及‘七征八还’,茫然自失……而昨年所得于师友者,却是进而不能前,退失故武矣。 ”[7]76-77《楞严经》虽是大乘佛教典籍,但深为晚明儒者所喜。东溟在此提到的“七征八还”,指的是佛陀与弟子阿难“七处征心、八还辨见”的故事,二人的问答条分缕析,层层深入,为的是破除人的妄想攀缘,见得常住真心。原本经过前一个阶段的进益,东溟自觉已趋近心性本体。而今《楞严经》对妄念的省察与勘破却完全出其意料,佛教析理的全面与细腻程度更是超乎儒家之上。这使得东溟产生了如丧故我、茫然若失的感觉。由于释门工夫效验显著,他依照《楞严经》的指津,在身心修炼上又产生了几番进跃。而先前受明道书院师友夹持而获致的体验却很难更上一层,再有突破。
通过阅读《楞严经》,东溟一方面对心体的澄明状态益有所悟,另一方面也更加明确与向往超越现世的理想境界,认为在理学与心学之外,仍有向上一着:“于时乃不敢以所闻自足,而悠然起究竟一大事之思矣。 ”[6]6这两方面促使他放弃了先前对二氏的否定态度,“始信孔、释之无二心,而幼年力排二氏之念除矣”[9]37,并从“心体”问题切入,开始重新思考三教之同异。为了实现自己的为学目标,东溟愈加刻苦地锻炼习气,穷究性命,“不解衣而坐卧者经年”[10]37,同时开始广泛结交缁衣黄冠,涉猎佛道经籍,如《维摩诘经》《法华经》《坛经》《悟真篇》等,认为“一一若道我心上事”[9]37。
隆庆元年丁卯(1567 年),第五次乡试落第的东溟受邀至中吴书院任主讲。他这样概括自己当时的思想状况:“于时课业专本儒宗,治心兼资禅理。锐志求出生死,绝意世间诗文著述之事。然于三教圣人之彼不碍此、此不碍彼,彼能用此、此能用彼,孰权孰实、孰主孰伴,则犹未究其指归也。 ”[10]37可以看到,此时的东溟学行断为两截,并已在立场上偏向佛教,他不仅在心性修养方面采用禅宗路径,更以出世、了生死为究竟志向。不过,他并未放弃自己的儒者身份,而是希望调和三教关系,只是尚未找到实际的证合处。
直至隆庆三年己巳(1569 年),东溟应恩贡入北京,才因偶然的机缘而猛然有所觉悟:“游西山碧云寺,暇索《华严经》阅之。不半晌,豁然若亡其身,与太虚合,照见古往今来一切圣贤出世经世、乘愿乘力、与时变化之妙用,大概理则互融,教必不滥……种种出没、种种张弛,各有条理,难可思议。此无他,群龙不可为首也。 ”[10]37-38东溟在翻阅《华严经》经文后,联想及《周易》乾卦所谓“用九,见群龙无首,吉”与“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在他看来,乾卦六爻所对应的潜、见、惕、跃、飞、亢六龙,时位虽不同,但却均属龙德。这正如佛教的菩萨神祗一般,各个部类、称号、样貌以及解脱法门虽不相同,却均悟入佛陀功德智慧之大海,于毘卢遮那如来的海印三昧中炳然齐现[4]174-181。东溟由此意识到,古往今来一切圣贤皆在十方世界中隐现出没,各自化现其身。他们的现世姿态与立教宗旨之所以迥然有别,是因为所乘愿力与所应时机不同。这种种不同只是权法上的差异,究其实地,皆达致修行之最高境界。因此,孔子、释迦、老子之间绝无高低优劣之分,此即“群龙无首”之真意。可以说,透过《华严经》省及《周易》“群龙无首”之旨,从而提出“三圣平等说”,正是东溟证合三教一致的最初触发点。从此说出发,可以衍生、发散抑或推导出东溟学说的种种面向、种种立场,可谓是其横说竖说、四方打开之理论原点。东溟自己也曾指出:“乃群龙无首一句,实是千圣之大关键处。不透此关而论圣学,则孔子敦化川流之脉络,终不白于天下。 ”[11]9
经过“群龙无首”之悟,东溟的学问又是一转,其思想的根本立场与基本框架自此确立。在这之后,东溟进一步精研义理,不断沉淀。与此同时,他还开始倡导一种偏重收敛与实行的工夫论:“今日之道枢,不属见而属惕;今日之教体,不属悟而属修。 ”[11]35一方面,这是他为了对治狂伪世风而开出的药方;另一方面,也是他基于个人际遇与自我省察所得出的结论。东溟认为,自己先前过于偏重对心体的觉悟,而忽视了真切的行动。这种重解轻行的做法导致自己始终难以革除固有的习气。并且,他自认早年过于张扬,如在少年时便立“三不朽”之志,“妄拟《论语》、《学》、《庸》诸篇可以述而作也”[5]698。在中吴书院讲学时,东溟曾劝勉诸生要有“遯世不见知而不悔”(《中庸》)与“杀一不辜得天下而不为”(《孟子》)的胸襟,方才能够载道、立身。离开书院后,他深刻反省自己好为人师之病:“发念从今以后,不复受讲学门生。拟藏身于宗教两门中,锻炼习气。 ”[6]6
隆庆五年辛未(1571 年),东溟终于得中进士,走上仕途。他颇具治才,能以身使官,在任期间,可谓政绩斐然。万历六年戊寅(1578 年)二月,神宗大婚后,他上疏条陈九事,讥切时政,力劝君主躬揽朝政,无使大权旁落。次年八月,再陈风纪未尽事宜。东溟的直言敢谏触怒了他的座主同时也是当朝首辅张居正。万历八年庚辰(1580 年),正值壮年的他在大计中以老疾致仕。归乡后的东溟在修身实践上,主要以销宿垢、树阴骘为目标。他积极参与佛经刊刻、地方慈善与护法活动。但这些行动,特别是天池道场一事,使他卷入了僧人与乡绅的利益冲突,从而备受讽议。仕途的挫折与实践的困境,都促使东溟愈加低调内敛,转向潜心自修。
四、晚年使命与立言事业
万历十六年戊子(1588 年),此时的东溟早已解组还山。他断绝文墨之念多年,却突然忆起七年前梦境中“道存济世”一语,进而觉悟到自己应当承担起承续大道的责任,故又重新萌生立言计划。
万历十七年己丑(1589 年),年逾半百的东溟梦到已经过世的罗汝芳,并通过梦境中罗师的嘱托之语,进一步明确了自身使命,即“以西来之意合圣宗,以东鲁之矩收二氏”[7]81。此时的东溟已渐渐从修习佛道法门,转入儒家之庸言庸行。他开始相信,通过修习儒学即可直证大道,而不必要借助佛教。对于孔子“下学上达”之旨,东溟的认同愈来愈深,自述“不习坐禅念佛,亦不习采药养丹,纯向孔子下学上达处用力,颇有欲罢不能之意。端为见得菩提妙心,尽在孔子一贯中;普贤行愿,尽在孔子从心矩中。不必外求,不必外慕”[5]712。
于是,自是年(1589 年)起,东溟下定决心,要将自己多年的体悟付诸文字。他笔耕不辍,并与同时代思想家相互切磋、往复论辩,其思想日趋完善与成熟。经过数年的努力,东溟撰成了大量著述。其中存世者共二十九种,逾百万言,大抵可分为七个类型—— 一是疏解儒家经典:《易测六龙解》(1593 年)、《六龙剖疑》(1602 年);《论语订释》(1597 年);《大学测义》(1606 年)、《大学订释》(1606 年)、《大学辨义》(1606 年)、《辨古本大学》(1607 年);《中庸测义》(1607 年)、《中庸订释》(1607 年);《孟义订测》(1608 年)。二是专论佛道二氏:《宪章余集》(1597 年)、《续宪章余集》(1603 年);《觉迷蠡测》(1600 年);《题龙华忏仪》(1607 年)。三是专论三教关系:《续原教论评》(1602 年)。四是综合问答论辩:《师门求正牍》(1597 年);《问 辨 牍》(1599 年)、《续 问 辨 牍》(1600 年);《惕若斋集》(1597 年)、《惕若斋续集》(1606 年);《理要酬咨录》(1602 年)、《酬咨续录》(1605 年);《 謕 余 音》(1606 年);《论 学 三 劄》(1607 年);《析理编》(1607 年)。五是专论礼法制度:《从先维俗议》(1602 年)。六是议论时政:《奏疏稿》(1587 年)。七是自传:《步朱吟》(1603 年);《我执公参一状命儿勒小像上》(1605 年)。这些晚年写就的文字,集中呈现了东溟思想的成熟面貌。
五、结语
在七十余年的生命历程中,东溟始终保持着一种穷究天道性命的兴趣。早年的他服膺濂洛关闽,排抵佛老二氏,以博学多识、窥见性体为志。后拜耿天台为师,与罗汝芳、王襞、同门焦竑等共同论学。与其他理学家一样,东溟也浸润佛老多年。不同的是,东溟与佛教的纠缠更深,以致突破了儒家思想的部分边界。年逾知命,东溟思考与修行的重心又逐渐回归儒家。可以说,东溟历经半生求索,几度思想转折,方才找到了精神的归宿。在此过程中,他为了分判三教同异、摆脱自我怀疑,围绕儒、释、道三种文化传统对宇宙、人生、社会根本问题的不同回答,进行了长时且深入的思考,并对当时的焦点议题和社会现实保持了高度的关注。世界万物的起源、善恶报应的机制、心性的本质与作用、修行的路径与境界、道统与治统的关系、礼俗与政教的重建……都被他纳入讨论的范畴。对东溟学思历程的呈现,使世人对这位较为陌生而又饱受争议的儒者有了更多的同情和了解,同时也丰富了对晚明思想世界之复杂性与多样性的认识。
注释:
①就东溟思想研究的学术专著而言,颇具代表性的除了荒木见悟的《明末宗教思想研究——管東溟の生涯とその思想》(东京:创文社,1979 年)之外,还有吴孟谦的《融贯与批判——管东溟的思想及其时代》(台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2017 年),魏月萍的《君师道合:晚明泰州学者的三教合一论述》(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6 年)以及魏家伦著,王硕和王坤利译的《晚明地方社会中的礼法与骚动:管志道〈从先维俗议〉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