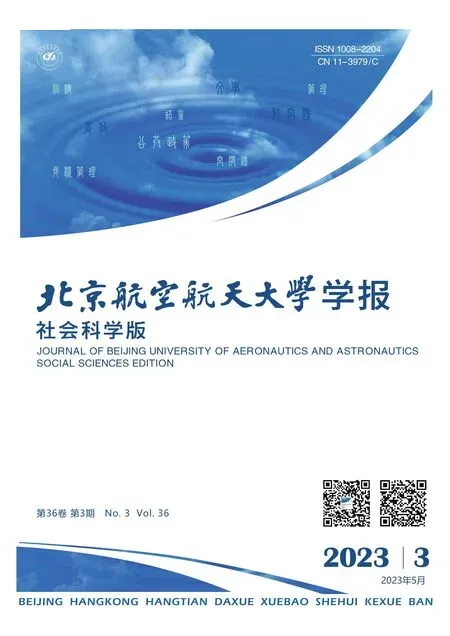马克思有无生命观?
——对两种论争的批判性考察
2023-08-06张懿
张 懿
(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1)
针对“马克思主义是否存在人学空场和生命哲学”的问题,国内外学术界曾经有过激烈的争辩和广泛的讨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至关重要,它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质、价值旨归和问题指向。实际上,在通读马克思的经典文本之后可以发现,生命观是真真切切地内在和蕴涵于马克思的整个思想理论体系之中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摆脱生命的奴役与压迫、实现生命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一以贯之的思想主旨[1]。
历史上,有关马克思的思想与人学生命思想之间的关系,主要存在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种是有些学者囿于“唯经济决定论”和“唯科学主义”等的偏见,误认为马克思根本没有人学生命思想;另一种则相反,一些学者基于对《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等马克思早期著作及其思想的发现和重新解读,又将生命哲学相关思想抬高为马克思主义的唯一巅峰成就,并据此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抽象的人道主义学说。其实这两种观点都是对马克思的严重误解,均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事实,这里有必要在进行相关考察后予以澄清,还其本来面目,尽量客观、中正地评价和明晰生命哲学思想在马克思的整个思想理论体系中的历史方位和价值意义。
一、观点一:误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与生命哲学思想绝缘的
这种观点错误地认为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是一种“唯经济决定论”或“唯科学主义”,只见物而全然看不见人,难以在其中觅得人文关怀或生命关照的踪迹,理论本身就存在着人学生命思想的空白和缺席。相关论点主要集中体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将唯物史观误解为“唯经济决定论”。一些西方学者在审视唯物史观时,往往只看到或过度强调当中蕴含的经济因素及其作用机制,而完全无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中所论述的非经济因素也具有的反作用,因此,片面地以“唯经济决定论”来称呼马克思主义的整个思想理论体系。例如,在对待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问题上,罗素将其称为“经济史观”,波普尔将其称之为“经济主义”等。此类论调认为,马克思过分地重视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而忽视了政治、文化、思想、观念、科学等的更基础和更具绝对性的决定作用,因此,不应该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奠基于物质资料的生产或社会的经济条件,而是应将思想观念置于社会历史发展的主导地位,让思想来引领、决定和主宰经济发展及社会进步[2]。
其二,指认马克思主义存在着“人学飞地”。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让-保罗 · 萨特一方面高度肯定了马克思主义有关人的论述的合理之处和重要价值[3]7,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当时他们那个时代不可超越的理论[3]2;另一方面又指出,马克思虽然曾经确有关于人的存在思想的形成,但后来又消失了,马克思自己弃绝和取消了关于“人”的主观性的探索和询问[3]129,而只关注事物的客观性和自然界的本来面目,以致变成了一种绝对知识的体系、纯粹的客观真理[3]3,所以马克思的思想中存在着人学的空场。让-保罗 ·萨特还以自身的“平均数”理念批判了恩格斯的“社会历史合力论”思想,认为在现实的社会集合体里,个人往往不能正确全面地认识自己,因此,这个社会对象是除却了作者的人工作品,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发展合力思想事实上也没有将作者、作者的作品及其“人性”列在之内[3]9。总之,让-保罗 · 萨特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只是看到了“物”却忽略了“人”,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这一空白需要用存在主义的人学来进行填补[3]134,若要完成这一“关于人的存在的计划”,就必须要坚持主客体相互作用的“现代认识论”,避免陷入唯心主义的幻想,真正阐明现实的人[3]3;如此一来,主客体就不会被割裂或分离开来了[4]114-116,而实现了辩证统一[3]128。
其三,攻击马克思主义谓之为“科学拜物教”。法国存在主义的另一位杰出代表人物梅洛-庞蒂(Merleau-Ponty)更是直言马克思主义实是一种“唯科学主义”,即“科学拜物教”,攻击马克思主义将“人”与“物”混淆起来的机械性和刻板性,甚至直截了当地指出,在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发展史上,每当革命意识游移不定的时候就会蹦出科学的拜物教……“唯科学主义”实际上就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异化或物化现象,它将人看作“物”而不是“人”,剥夺了人的现实性和主体性权利[5]。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还有奥地利的学者鲁道夫 · 希法亭。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实证的和现实主义的唯物主义学说,马克思的整个思想理论只是一种客观的科学,不带任何价值判断[6],即认为马克思主义不闪现一丝人文评价色彩[4]116-117。
其四,认为马克思主义与“生命哲学”无涉。马克思的生命观在思想实质和理论视域方面均实现了对西方生命哲学的多维度超越[7],但不得不说,盛极一时的西方非理性生命哲学的确影响了人们对马克思生命观的科学理解和全面深度探索,甚至一度遮掩了马克思生命哲学思想的理论魅力。一方面,西方非理性生命哲学曾经的鼓噪叫嚣在某种程度上隐没了马克思生命观的独特光芒色彩,因为有西方生命哲学思想研究的“前车之鉴”,使得人们后来罕有提及马克思的生命哲学思想,偶有提及也格外羞涩或者是带有显得有些底气不足的难为情[8]。另一方面,基于西方非理性生命哲学抽象化理解人之生命的“唯心主义”性质的影响,一些人往往先验地认为生命哲学就是“唯心”的,而作为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肯定没有生命哲学思想。其实这也是一种误解,没有人规定说生命哲学只能是唯心性的,也不是说一种理论一旦跟“生命哲学”挂上钩就注定是非理性的。实际上,不管是从广义还是狭义上,生命哲学都绝不仅拘囿于非理性主义的框架之中。例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庄子生命哲学一直以“非理性”或“反理性”著称,但他极其善于通过感性形式的“寓言”来表达理性内容的思维;孔子的生命观以往被人们定性为“理性主义”,却亦十分重视对感性生命的阐发,强调生命之理性力量与感性内容的结合;西方生命哲学思想流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威廉 · 狄尔泰也只是不满于“唯理性独尊、唯理性至上”,但并不偏执地排斥理性,而是主张将生命的感性因素与理性因素融贯统合起来,形成一种“心理生命”[9]。
二、观点二:误认为马克思人学生命思想是一种抽象的人道主义
与观点一截然相对,观点二的持有者则以《手稿》文本为由头,或认为人学生命相关思想是马克思一生之中的唯一最高成就,并将其“美名化”为一种抽象的人道主义,或极力主张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的对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对立等,造成一种混淆视听的效果,具体可以区分为三种不同的解读模式:
首先,“两个马克思”对立的解读模式。大致有两种类型:一是以齐 · 朗兹胡特和迈尔等为代表,他们极力抬高和鼓吹《手稿》在马克思整个思想发展历程中的至高地位和价值,盛赞这部著作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启示录”“新的福音书”,“包括了马克思的全部精神视野的唯一文献”“标志着马克思成就的顶点,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而且极力贬低马克思晚年时期的作品,认为晚年时期的马克思完全放弃和背叛了其青年时期关于人的理想,转而沉溺于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无病呻吟”,仅仅呈现出了创作能力的衰退、削弱和停滞。此外,他们还指出,通过全面考察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可以发现,经恩格斯、列宁等固定下来的马克思的全部观点现在都改观了,这些解说者们对马克思的精神思想的了解具有严重的局限性和贫乏性[10]286-297,由此,不仅人为地制造了青年马克思和晚年马克思的对立,还制造了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对立等。二是路 · 阿尔图塞对“断裂论”的阐发。虽然路 · 阿尔图塞也认为晚年马克思与早年马克思是对立和决裂的,但他对早年马克思和晚年马克思的评价呈现出了相反的模式,即认为晚年的马克思的创作才可以真正称得上是一种科学的历史理论,早期以价值主题为中心的著作是不成熟的见地,马克思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从早年人本主义阶段向晚年历史科学阶段的断裂和跃升[11]。可见,上述两种“对立论”的解读模式均割裂了人的价值因素和科学因素,只是二者对于早期马克思和晚期马克思的褒贬评价不同罢了。
其次,统一的“人本主义”的解读模式。这种解读模式的重要代表人物有列斐伏尔、埃里希 · 弗洛姆、马尔库塞等,他们拒不承认“两个马克思”相互对立的悖论,认为早年马克思和晚年马克思的思想实际上是一脉相承、完全统一的,统一于《手稿》的理论主题即人本主义之中。正如埃里希 · 弗洛姆所言,早年马克思在《手稿》中所阐述的人的基本思想和老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表达的思想,并没有本质的区别[12]206,都是有关真实的、个体的人的存在问题[12]143,亦可称为彻底的人本主义[13]。在他们看来,马克思的真正目标不是使人单纯地获得物质利益方面的满足,而是得到精神的解放和超脱,彻底实现个人主义[12]150,因此只有一个马克思,也就是作为人本主义的马克思,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先知的救世主义[12]152。他们认为,唯有青年马克思的《手稿》中的人本主义才能代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和宗旨,而晚年时期的马克思的著作和理论研究都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是对《手稿》逻辑的深化提升和进一步展开。显而易见,上述观点认为,全部时期的马克思都是对人的价值主题的系统阐发和详细论述,马克思人学生命思想中的科学因素也完全从属于价值因素的范畴。
最后,抽象的“人道主义”的解读模式。不论是“两个马克思”对立论,还是“两个马克思”统一论,两种解读模式的共同之处在于:对早年马克思及其《手稿》思想主题的解读往往是限于异化的扬弃和人的本质的复归,且又陷入了抽象的“人道主义”模式。例如,齐 · 朗兹胡特和迈尔认为,《手稿》以哲学观念为始发点,径直地经过人的自我异化达到人的自我实现和无产阶级社会[10]285。亨 · 德曼强调,《手稿》背后隐藏的是马克思伦理的、人道主义的动机[14]。Bigo 及Tucker 也认为,《手稿》表明了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道德学家、伦理学家[15]或宗教思想家之类的人[16]。就连对马克思进行人本主义化解读的弗洛姆也直言不讳地指出,马克思事实上是用世俗的语言表达了一种与唯物主义的实践、与我们这个时代的唯物主义哲学恰好相反的精神存在主义,马克思的哲学其实是精神性的唯心主义,它本质上是一种建立在人的学说上的社会主义[12]151-152。不管他们承认与否,在上述“两个马克思”对立论和统一论的“人本主义”的解读模式的视域内,青年时期的马克思在《手稿》中的思想理论都只是沦谪为了一种较为抽象的人道主义学说,还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现实的人道主义,因为青年时期的马克思还没有完整地形成对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和人的问题的科学、全面、系统的认知。除此之外,南斯拉夫的“实践派”哲学、苏联戈尔巴乔夫时期的“人道的社会主义”等无疑也皆是对抽象的“人道主义”这一解读模式的反馈和印证。
三、客观解读马克思人学生命思想:对上述两种错误观点的回应
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马克思主义难道真的是人学生命思想的绝缘体、与生命哲学思想毫无关联吗?马克思主义是否确实是“唯经济决定论”“唯科学主义”呢,抑或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抽象的人道主义?在解读马克思思想的过程中,是否真实存在着“两个马克思”对立论、马克思与恩格斯对立论等,有必要于此作出相应的说明和阐释。
首先,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唯经济决定论”,也非“唯科学主义”,人学生命思想是内在于马克思的整个思想体系之中的。一是马克思主义不是“唯经济决定论”。经典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阐述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互动作用关系,指出经济是社会发展基础性的、归根结底意义上的决定性因素,但并没有说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唯一决定性因素。事实上,马克思不仅强调人类物质生产和生活资料的满足,也强调在此基础上人的发展需求和意义需求的实现。二是马克思主义也不是“唯科学主义”。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纯粹的科学拜物教本身就是难以成立和自相矛盾的,因为马克思一生所孜孜追求的即为实现全人类的解放,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旨归和目的指向,可见,这种思想并非一种不带任何人文关怀色彩的唯实证主义理论。而且,某些西方学者之所以误解马克思是唯科学主义者,是因为他们根本不了解马克思的人学生命思想,也没有弄清楚作为科学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的本真内涵和真正本质[4]117-120。三是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生命哲学空场。对人之生命存在的关照、对人之生命本质的探析、对人之生命价值的确证和对人之生命意义的追寻等生命哲学问题融贯马克思理论探索过程的始终,只是成熟时期的马克思不再沿袭青年时期从人性的异化及扬弃的角度来论证人之生命的解放的做法,而是通过深入剖析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规律来探究生命主体获得解放的条件。因此,无论如何都否定不了马克思的人学生命思想的存在及其丰富的内涵。
其次,《手稿》中所阐发的思想不是马克思的唯一最高成就,绝不能将马克思主义等同于一种抽象的人道主义学说。一是要客观地评价《手稿》的历史地位及作用。认为《手稿》是马克思的巅峰之作或低谷之作,都难以称得上是对《手稿》的科学、中正的评价,这反映了不同评价背后相应的解读模式的差异,即“以西解马”与“以苏解马”的对峙[17]。应当说,《手稿》肯定不是马克思的唯一最高成就,但也应是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关键的文本,对唯物史观的形成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虽然其亦有不成熟之处,但是不能否定其所具有的特定意义和重要价值。因此,应将《手稿》置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和马克思主义整个发展史中来进行辩证的评价和全面的审视,既不应过分美化它,也不应极力丑化它,而是应实事求是地看待它。二是马克思主义绝不是一种抽象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不能归于抽象的人道主义行列,因为它从来都是立足实际又具有超越特质的、客观的、脚踏实地的理论,其人学生命思想更是建立在科学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并没有体现出任何的抽象性的特点;相反,它从分析“现实的人之生命”出发,将人之生命放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等多重关系场域中来进行历史性、整体性的考察,致力于实现人的生命的自由全面发展,这种理论是完全可以与抽象的人道主义划清界限的。
最后,不能主观地将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对立化,或者将马克思与恩格斯对立化,应整体性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一是不存在“两个马克思”。一些学者将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科学的马克思与人文的马克思对立起来,往往是绝对化地割裂了人的价值因素与科学因素的辩证统一性。然而,马克思一贯化的思想体系并不能被分裂开来,而是实现了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的有机融合,万不可用马克思的科学精神来否定其人文理想,也不能以其人文关怀来否定其科学理念。马克思主义是一块整钢。不可否认,马克思的思想确实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发展过程,但绝对不存在前后相互对立、完全割裂或是中途彻底“改旗易帜”的情形,因为马克思的目标始终如一、信念从未改变。二是不存在“马恩对立论”。一些学者借机挑拨马克思的思想与恩格斯的思想之间的分离,竭力制造两人在哲学观、自然观、历史观、共产主义信仰等问题上的“全面对立”[18],这显然也是不成立的。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联合创立的科学的理论,二人的观点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因为在各种专业领域方面互相帮助和研商探讨早就成为了他们的习惯[19]。正如Hunley 在其相关著作中所论证的主旨一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极为广泛,有着密切的学术伙伴关系,而且马克思也不是一个能够轻易容忍他人的观点与自己截然不同的人,然而马克思却能与恩格斯长久地保持着和谐的关系,这本身就说明了他们在学术上的根本一致性[20]。三是整体性理解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既不是“唯经济决定论”或“唯科学主义”者,也不是抽象的人道主义者,更不存在前后期的人格分裂或理论断裂,马克思就是思想一贯的马克思,是一个为实现人类的解放而奋斗不渝的坚定的共产主义者,马克思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位创始人恩格斯的思想是相契合一致的。应整体性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主题和一以贯之之道,既要理解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整体性,也要理解马克思人学生命思想的整体性,并注意把握二者之间互构共融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