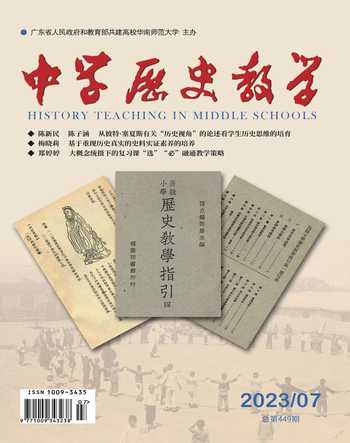问题导向下的《汉代讲经图》研读
2023-07-31莫亮
莫亮

在义务教育历史教科书七年级上册第12课《汉武帝巩固大一统王朝》课后活动中有这样一个题目,要求学生根据《汉代讲经图》,说说汉武帝对儒家的态度,并指出图中的“经”主要是何内容。笔者在使用此图时,本想一图多用,一是说明汉武帝对儒家的态度,二是作为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术的背景来使用。不料,在让学生猜测图中经书的载体是“册”还是“纸”时,有学生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既然是册,说明当时还没有改进造纸术,那我们可以称呼此图为‘西汉讲经图吗?
细细思考,这个问题实际上隐含了几个层面的问题。第一,这幅图出自何时?也就是说其拓本画像砖是成砖于东汉还是西汉?如果成砖于西汉,易于解释汉武帝对儒家的态度以及为什么使用册而不是纸。第二,如果成砖于东汉,是否可用于证明汉武帝对儒家的态度?如果不妥,又当如何解读?第三,是“册”就一定说明当时没有改进造纸术吗?如果改进了造纸术,为什么使用“册”而不是纸?
一、定时间:成砖于西汉还是东汉?
画像砖“产生于西汉,盛行于东汉,魏晋之际仅有个别实例”[1]。就出土地点而言,画像砖在全国分布范围广泛,但又呈现出散乱而集中的特点,“主要在鲁南苏北,豫南鄂北,陕北晋西北,川渝地区四个中心区附近。每个中心区域在时间延续、内容承载、装饰花纹上各有特色。”[2]
既然画像砖的时间延续与出土区域、内容承载、装饰花纹有内在联系,笔者开始从这几个方面入手,来进行判断。在高文《四川汉代画像砖》[3]一书中,虽收录了此砖,但没有记录出土地点。几经周转,笔者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馆藏文物中找到了该画像砖,其名字是《汉讲学画像砖》,也未标注出土地点。但根据它和一同收录在《四川汉代画像砖》一书的《讲学》画像砖的馆藏地,基本可以推测,该画像砖是出土于川渝地区的。
为了进一步缩小范围,笔者将目光投向了砖的形制和内容。从出土地和砖的大小来看,“画像砖墓仅限于川西平原及其附近的一带,四川其他各地尚未有发现。”也就是说,川渝地区虽然区域较广,但画像砖墓的出土相对集中,可分为三个大的区域类型,成都区、广汉区和彭山区。而“成都区的画像砖均为约40厘米见方的方砖……成都附近各县(如广汉、德阳、彭县、新津、邛崃、彭山、宜宾等县)所出的画像砖,均为长约46—47厘米,宽约26—27厘米的长方形砖(有的还稍小),而绝无方形的”[4]。在艺术表现方式上,成都类型的画像砖多以线條为主,题材上,较多反映政治生活、思想意识,关于生产劳作较少,往往单独一个砖面表现一个完整内容。[5]《汉代讲经图》画像砖(39.5×45.5cm)为方形砖,以简单线条勾勒了师徒几人讲学场景,一砖单独成画,符合出土于成都地区的汉代画像砖的一般特征。所以,基本可以确定它出土于四川成都区。
成都区的画像砖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冯汉骥根据砖室墓的建筑、葬具与葬器的演变,将四川砖室墓的发展分为西汉晚期、新莽至东汉初期、东汉中期、东汉晚期四期。在墓室出土文物中,“所有的画像砖均系东汉后期和蜀汉时期的作品——条形画像砖或者稍早——大致相当于公元二世纪后半叶至三世纪前半叶”[6]。在此基础上,袁曙光将四川出土的画像砖分为四期,东汉中期、东汉晚期、三国时期、六朝时期。之所以能确定第一期是东汉中期,是因为有与“永元元年”(公元八十九年)纪年砖共同出土的画像砖。东汉晚期是四川画像砖的成熟期。[7]至此,我们可以断定《汉代讲经图》拓自至早东汉中后期的画像砖。
二、观全貌:能否证明汉武帝崇儒?
既已厘清该画像砖成砖于东汉中晚期的成都,我们是否可用它来说明汉武帝对儒家的态度?在查证过程中,可以看到不同书籍对此画像砖的命名各异,但无一例外都聚焦于“讲经”“讲学”。在旧版高中历史教材人教版必修三中,对这幅图的注解则直接是“成都西汉文翁石室授经讲学图”。
文翁何许人也?他是汉景帝末年治蜀兴学的名官良吏。班固曾如此评价他,“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8]。故有“文翁化蜀”一说。班固还记载了汉平帝对文翁进行祭祀表彰,蜀地吏民为其立祠堂的史实。联系该画像砖的成砖时间和出土地点,以及文翁对蜀地文化的积极影响,我们可以推测此画像砖大概率是东汉时当地人为了纪念文翁所造。
暂且认可这一推测,但以此来说明汉武帝对儒家的态度,不够严谨。从时间上来看,文翁与汉武帝虽有时间交集,但其治蜀主要发生在景帝末年,他创办地方官学的时间早于汉武帝,“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9] 。所以,文翁并非受汉武帝影响才在蜀地推广儒学,该画像砖无法作为汉武帝推崇儒学的直接证据。
此说若不成立,我们可作何解?文翁所处的景帝时期,黄老之学盛行,其特征是“因循”和“无为”,而循吏“文翁在蜀实行教化则是本于他个人平素所持的信念;这种信念只能源于当时在社会上流行的儒教大传统”[10]。可见,在汉武帝尊崇儒术之前,儒学就已经有了一定的社会发展基础,儒学进取有为之道,符合中央集权家国同构的社会要求。
如果本砖内容不是以文翁为主题,那又当如何解读?它最有可能反映的是东汉当时的社会面貌,我们也可联系其他同类型画像砖进行考察。以讲经为题材的画像砖在四川多地都有出土,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收录了三幅一模一样画面,但尺寸大小不一的《汉讲学画像砖》。
除了散布于四川外,相似主题的画像砖在河南、山东也被发现。蜀地的特殊之处在于它远离以黄河流域为基础的华夏文化中心,有相对独立的文化系统。但正是在这片中原视域下的“蛮夷之地”,多地出土了同一主题但画面各异的画像砖。从这些发现中,我们可窥东汉读经兴教之盛。
再细看《汉代讲经图》的画面,我们还可进一步挖掘。“左边榻上坐着讲学的老师,老师头上方格形器物,是用来挡灰的‘承尘。下面席上环坐着六位学生,双手捧着竹简,正凝神静听老师讲学。”[11]教师盘腿而坐,学生环绕跪坐式的布局,以及专门为教师设置“承尘”,这都从侧面说明了汉代尊师重道的社会风尚。[12]
综上,《汉代讲经图》虽然无法直接说明汉武帝对儒学的态度,但我们结合出土文物和文献资料,双重考察,它确可以反映当时儒学发展的情况,给其命名为“讲经”或“讲学”是有道理的。
三、辨细节:纸与简牍的博弈
简册是汉代书籍的标志,《汉代讲经图》中学生腰间挂的书刀,也可证明图中经书的载体是册而不是纸。众所周知,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术,与《汉代讲经图》成砖年代同属东汉中后期。如果该砖描绘的是西汉文翁讲学场景,用册争议较小;如果是描绘东汉中后期的习经情形,既然汉和帝已下令推广蔡侯纸,“自是莫不从用”,为何图中使用的不是纸呢?
纸的出现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不及蔡伦改进造纸术,纸张已经被用来抄写经书了。《后汉书·贾逵列传》记载:“奏,帝嘉之,赐布五百匹,衣一袭,令(贾)逵自选公羊严、颜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与简纸经传各一通。”[13]此处简纸便是竹简和纸的合称。
虽然东汉时纸的书写功能增强,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蔡伦改进造纸术后,纸张已经完全取代简牍,应用于中国各地的书写了。到了403年,东晋豪族桓玄仍下令以纸代简,“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纸代之”[14]。可知,纸与竹简的并用存续了较长时间。《汉代讲经图》画像砖所铸时,是竹简与纸的混用时代,所以用册不用纸并非不可解释。
为何在造纸术已然改进的情况下,简牍没有即时退出历史舞台?实际上,造纸术的改进与发展,在时间上,存在一个工艺不断精进的过程,在空间上,存在一个从北向南扩展的过程。质量和产量是制约纸普及的重要原因。蔡伦改进造纸术后,褚皮纸发展较快,但纸的区域性特点也很明显。即便蔡伦改进的褚皮纸具备原有麻纸所没有的先进之处,但也不代表各地都在使用蔡侯纸。曹魏时期,山东地区出现了造纸名家左伯,他“所在的胶东,汉以后直到宋代仍以麻纸称著”[15]。各地的文化、技术发展进程不一,极有可能在蔡伦改进造纸术后的一段时间内,包括《汉代讲经图》出土的四川在内的区域,并未将纸作为书写载体的首选。
我们不能单纯地用线性的眼光看待历史,认为造纸工艺发展后,各地均迅速采用新型纸张作为书写载体。除了本文述及的时空因素外,简牍本身的优势、人们的书写习惯、“帛贵纸贱”的思想观念等方面都会影响纸的普及,在讨论汉代造纸问题时需要多重考量。所以,《汉代讲经图》恰恰成为了当时竹简仍在四川地区使用的有效证据。
用图证史首先要对图片产生的背景做分析,《汉代讲经图》虽然是图像史料,但研读时,需要追本溯源,确定其作为实物史料的拓本画像砖的成砖时间。而后,从砖面内容中提取有效信息,结合时代背景和其他文献史料,了解命名原因,分析能否得出教材题目中的结论。如若不能,我们可如何使用本则史料,它还能“证什么”“释什么”。
对该画像砖的解读,经历了从时空背景解读画像砖本身内容,又从其内容折射时代其他事物发展的历程,由表及里,从宏观到微观再到宏观。作为史料的画像砖与其他同时代的事件构成了一個整体。德罗伊森说:“个别的事物只能在整体中被理解,而整体也只能借着个别的事物来理解。”[16]画像砖正是这“整体中的个别事物”,而推动个别事物与整体都被不断深入理解的背后动因是解读者的提问。史料价值的高低很大程度上掌握在解释者手中,而解释者提出的问题决定了史料阅读的质量和信息的提取。
【注释】
[1]《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画像石》,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6页。
[2]李炖:《形象史学视角下的中学历史教学中的汉画像石应用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16年硕士学位论文,第32页。
[3][11]高文:《四川汉代画像砖》,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年,三二、三三。
[4][6]冯汉骥:《四川的画像砖墓及画像砖》,《文物》1961年第11期,第36、39、40页。
[5][7]袁曙光:《四川汉画像砖的分区与分期》,《四川文物》2002年第4期,第28、30页。
[8][9][东汉]班固:《汉书》卷八十九《循吏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627、3626页。
[10]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41页。
[12]柳玉东、逯爱英:《<讲经图>与汉代教师地位》,《南都学坛(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此文对此有详细论述,本文不展开说明。
[13]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239页。
[14]徐坚:《初学记》卷第二十一《文部·纸第七》,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517页。
[15]潘吉星:《中国科学技术史·造纸与印花卷》,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83页。
[16][德]德罗伊森著,胡昌智译:《历史知识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