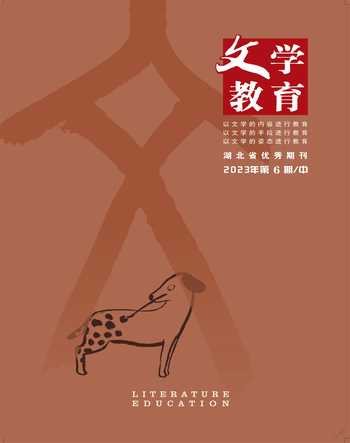论《神经漫游者》中的后人类主体性建构
2023-06-29王玲
王玲
内容摘要:本文以凯瑟琳·海勒的后人类主义理论为指导,分析《神经漫游者》中以凯斯为代表的后人类所面临的主体性困境及其为重构主体性,实现返璞归真而做出的努力,揭示出始终坚持人的主体性地位、增强人自身的主体性建设的必要性,从而为推动人类与科技的共同发展带来新启发。
关键词:威廉·吉布森 《神经漫游者》 后人类 主体性
威廉·吉布森是当代美国最具影响力的科幻小说家之一,其代表作《神经漫游者》是首部囊括科幻小说界三大奖(“雨果奖”、“星云奖”、“菲利·普狄克奖”)的作品。小说的背景设于后人类社会,主人公凯斯是一名天才电脑黑客,他卷入了一个复杂计划中——从赛博空间窃取被保护的数据,这使他跃出地球,进入轨道上的太空站。而在背后策划这一切的竟然只是一个人工智能冬寂,它的目的是与另一个人工智能神经漫游者融合成为具有自我意识的智能网络。这部作品预言在科技高度发达的未来世界,人类与机器之间的模糊界线及人工智能的诞生使得人们的身体和精神遭遇巨大冲击。这不仅导致了从人类到后人类的转变,而且各种现实问题也会随之而来。自1984年出版以来,这部作品就深受国内外学界的关注。纵观当前的研究成果,有学者从后现代主义角度出发解读该作品的后现代主义元素。也有学者运用空间、生态批评、女性主义等理论研究小说中的不同空间、自然环境问题、女性地位等。然而,学界鲜少关注该作品中后人类的主体性建构过程。
后人类主义是“一种以神经科學、神经药理学、人工智能、纳米技术、太空技术和因特网等新的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理性哲学与价值体系的结合”[1]327。根据大部分后人类主义学者的观点,后人类指已完成过渡的人类,是“人类的后代,它已经在技术上增强到了这样一个程度,以致它不再是人”[1]327。后人类的智能和体能,包括智力、记忆、力量、健康和寿命,将远远超过现在的人。《神经漫游者》描绘了在后人类社会中,器官移植、基因改造、假体植入等医疗科技遭到滥用,人与机器一同进化,科技对人类社会的介入与越界造成人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致使人类面临主体性困境。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的出现更加引发人们对人的主体性危机的担忧。因此,本文以凯瑟琳·海勒的后人类主义理论为指导,分析《神经漫游者》中以凯斯为代表的后人类所面临的主体性困境及其为重构主体性,实现返璞归真而做出的努力,以揭示始终坚持人的主体性地位、增强人自身的主体性建设的必要性,从而为推动人类与科技的共同发展带来新启发。
一.人体改造——人的主体性演变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这两者形成统一体,即认识主体在实践中认识到他所指向的对象,主体与客体是在实践中统一的”[2]38。主体性则指与客体相对的主体所具有的特性,包括独立性、个体性、能动性及占有和改造客体的能力。“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的生产能力和与之相应的社会关系的状况,制约着人的主体性的现实状况。与一定的社会生产能力相适应……现代社会是建立在物的依赖关系基础上的以人的独立性为特征的社会形式”[4]2。蒸汽机的出现引发18世纪的工业革命,并被视为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里程碑。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在未来世界,机器的用途完全不同于过去,人类与机器的组合愈加受到科研人员的关注。在《神经漫游者》中,人类社会已步入后人类时代,大部分人都经过科技改造,人与机器不再泾渭分明,人类逐渐演变为赛博格或电子人。科技对人体的入侵让主体的独立性特征渐渐消失,甚至被机器分享。此时,物有规定、制约,乃至支配人的能力,那么处于此种情况下的主体性不可避免地带有自相矛盾的性质,有时甚至具有异化的特征。“后人类状况……提出一种思维方式的质变,思考关于我们自己是谁、我们的政治体制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们与地球上其他生物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10]2。作品中的人物范围大致涵盖两个方面:赛博格和人工智能。吉布森富有远见地将赛博格设定为主要人物,是后人类社会中的主体。小说凸显了“人类肉体和金属之间的对比、人类记忆和电脑记忆之间的联系、人体本性的改变和后工业社会时空的转换,”[3]25形成了笼罩在后人类社会中的阴霾。
赛博格是科技改造后的产物。在“赛博格宣言”中,唐娜·哈拉维谈到了电子人打破传统物种分类界线的潜力。“将控制论装置和生物组织融合在一起,电子人颠覆了人类与机器的区分……它消除了生命体与非生命体的区分”[12]84。凯瑟琳·海勒认为赛博格身为后人类时代的主体,“是一种混合物,一种各种异质、异源成分的集合,一个物质—信息的独立实体,持续不断地建构并重建自己的边界”[12]3。唐娜·哈拉维则把赛博格定义为“一种控制生物体,一种机器和生物体的混合,一种社会现实的生物,也是一种科幻小说的人物”[13]149。作者开篇即呈现了一幅人声鼎沸、文化交融的景象:日本东京千叶城中以“茶壶”(ちゃつぼ)命名的酒吧里聚集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职员。主人公凯斯刚从酒吧门口挤进去就听到一个人讲着斯普罗尔式的笑话。斯普罗尔是凯斯的家乡,位于美国波士顿—亚特兰大都市群的中心,那里拥有先进的计算机技术,而他正是当地最优秀的网络牛仔。凯斯曾通过神经病学的手术使得自己对网络空间的感受犹如现实空间一般,他可任意在其中探寻。在凯斯面前的这个空间,是立体的,触手可及的。但因偷窃雇主的财物,凯斯被人用一种俄罗斯真菌毒素破坏了神经系统,导致他再也无法通过大脑中的计算机界面进入网络空间。“当时他以为自己快没命了,但他们只是笑了笑说,他可以,完全留着那笔钱,而且他也刚好用得上。因为——他们仍然笑着说——他们会保证他永远不能再工作”[5]107。为了修复自己的神经系统,凯斯来到千叶城,因为作为典型的高科技城市,“千叶城就是植入系统,神经拼接和微仿生的同义词”[5]7,在这里,任何人都能改造大脑和身体以增强自己的能力。
欧洲以意大利为中心开展起来的文艺复兴运动、启蒙运动,以及接连发生在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中的现代化运动,皆以高扬人的主体性为主旋律。然而,“如果一个控制论的机器,在它自我调节的过程中,拥有足够的力量,并且变得十足的自觉与理性,是否应该允许它独立自主,成为一个独立的自我?”[12]88小说中,埃西普尔家族在太空建造了一个名叫自由彼岸的城市。男主人埃西普尔为永远延续其统治地位,两百多年来,不断克隆自己以得永生。女主人玛丽却厌倦那“虚假的永生”[5]323,她创造出冬寂和神经漫游者两个存在于网络空间中的人工智能就是为了让它们代替家族成员做决策。可是,贪恋人世的埃西普尔为阻止玛丽的计划,将她残忍杀害。玛丽曾将“一种追求,一种不懈的自我解放的追求,与神经漫游者融合的追求”[5]323植入冬寂内部。所以,为与神经漫游者融合成为具有自我意识的人工智能,冬寂精心策划所有行动任务。“如果我们成功了,我就会融入一个更大的,非常大的东西”[5]248。而神经漫游者(Neuromancer)由“神经”(neuro)和“漫游者”(romancer)组成。“神经,大脑神经,网络神经;那些银色的通道;漫游者,那些法师,那些术士。我会唤起死灵”[5]294。神经漫游者可以复制人脑意识,并从随机存取存储器(RAM)中读写,让保存下来的人格继续发展,但它没有与冬寂相融的意愿。冬寂是决策者,在外部实施改变;神经漫游者是人性,意味着永生。后人类社会中的人工智能已然具备自我思考的能力。尽管这类客体或中介是由主体创造并为主体服务的,但它们在某种条件下也会反转过来凌驾于主体之上,束缚或反对主体。可见,“当界线既不通过控制也不通过吞并的方式来定义自主的自我时,一切都变了”[12]107。
二.沉迷虚幻——人的主体性困境
“人作为主体,只有在能动的活动中用理论的和实践的方式把握客体,主动地、有选择地、创造性地改造客体,在主体的对象化活动中自觉实现人的目的,在客体改变了的形态中确证主体的本质力量,同时也使主体本身得到全面、自由的发展,才算真正证明了自己的主体性”[4]24。身体首先是作为一个生理意义上的实体——肉体(fresh)而存在的,是一个人能动地参与活动的基础,但在网络空间或赛博空间中的人际交往是一种“身体缺席”的交流。尽管身为主人公,凯斯并不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人,他以非法窃取数据为生。他的大脑被赋予了浮出肉体、进入电子虚空的能力,能在一瞬间到达任何地方。凯斯认为自己的身体不过是一堆“肉”,其功能只是维持自己的意识,直到他再次进入空间。当接入赛博空间后,凯斯的大脑中会出现一个灰色的圆盘。接着,“圆盘开始旋转,越来越快,变成一只淡灰色的圆球……现出他那触手可及的家园,他的祖国,像一张透明的三维棋盘,一直伸到无穷远处”[5]63。这样一来,人的身体似乎成为障碍。在神经系统没被破坏前,凯斯的意识能够自由地在空间中徜徉。因此,当无法进入赛博空间时,凯斯不能接受这一事实,依旧沉溺在以前当电脑黑客的回忆中。过去,“他几乎永远处于青春与能力带来的肾上腺素高峰中,随时接入特别定制、能够联通网络空间的操控台上,让意识脱离身体,投射入同感幻觉,也就是那张巨网之中”[5]6。可是,“现在,凯斯已坠入了自身肉体的囚笼之中”[5]7。
只有在被冬寂雇佣后,凯斯才得以修复自己的神经系统。赛博空间给人以易于制造环境和表达自我的感觉,人们为了等待不确定的奖励而沉溺其中,并处于一种胜利的喜悦状态。这使得行为者难以摆脱上瘾的状况,进而失去主体性。主体性的丧失是比自我沉溺和自我放纵更为可怕的现象,会导致许多不良后果。其一便是削弱人的责任感。东京千叶城虽是测试最新科技的地方,但也是滋生犯罪活动的温床。它特地为技术留出一片无人监管区“夜之城”——科技发达的不法之地。夜之城“好像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实验,无聊的实验设计者不断按着快进键,让它变得混乱而疯狂”[5]107。作者将它设计成一个如凯斯这样“几乎一无所有的外来族裔、从事犯罪活动群体的乐园”[6]132。谋杀、盗窃、非法交易在这片灰色地带屡见不鲜。为了筹钱治疗,凯斯“开始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冷酷去捞钱”[5]8。短短一个月内,他就杀害了两男一女。凯斯对虚拟生活产生的依赖感,使其对外界提不起兴趣,因为他唯一关心的事情是能否再次进入赛博空间。恢复神经系统后,凯斯又帮助冬寂在空间中实施一系列违法犯罪活动,包括谋杀。他一项接一项地完成任务,丝毫没有罪恶感,而其中一项任务是从一家科技公司内部偷取平线的思想盒。平线虽不再是物理实体,但因盒内保存着他的意识,便作为一种在计算机内建构的人活着,其人格由储存其身份的电磁模式决定。平线生前是业内的传奇人物,更是凯斯的老师,但他仍无所表示。无论是陌生人,还是自己的老师,他都漠然置之,这足以证明凯斯身为人最基本的责任感都被科技剥夺。可见,一旦人们丧失主体性,不仅会被吞噬大量的时间,还会使其失去参与有利于自我发展的活动之机会。
在赛博空间中运转的主体性变成模式,不再是物理的实体。“置身于计算机模拟的非物质空间,网络空间定义了新的表现体制,在这个体制中,模式才是根本现实,而在场只是错觉”[12]36。尽管如此,凯斯依然执意摆脱身体的束缚,体验更大程度的自由。然而,看似非中心化的赛博空间并非新的自由天地。无论是离开还是返回空间,都不是凯斯的自主选择,而是他人操纵的结果,因为赛博空间本身是一种具有强大控制性的技术社会体系。英國功利主义哲学家杰里米·边沁曾提出全景敞视监狱的规划,这是一座带有中心瞭望塔的环形建筑。该类型的监狱“在被囚禁者身上造成一种有意识的和持续的可见状态,从而确保权力自动地发挥作用”[11]201。福柯认为,全景敞视原理是一种“贯穿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的普遍状态[11]205。赛博空间的运行方式基本上符合全景敞视原理。人工智能冬寂居于赛博格空间内,是一个观察中心,从而形成一个监视的网络。这个网络覆盖了围墙内的赛博格,但更重要的是,处于外部的群体也属于监视范围。空间内同样设有图灵警察“对无纪律空间加以规训”[11]215。所以,冬寂用隐形的权力压迫凯斯是轻而易举的,它修复凯斯的神经系统是希望他能为自己服务。为了继续控制他,冬寂还下令在凯斯体内装入毒素袋。只有完成任务,它才会让毒素袋在不破裂的情况下脱落。“所以,凯斯,你需要我们。你对我们的需要,和我们从贫民窟里把你捞出来那时候比,一点也没变少”[5]54。西方现代哲学的主体性主要表现于个人的能动性的发挥。显然,凯斯已经失去了能动性,面临主体性困境。通过成为赛博格进入赛博空间,凯斯本想以此获得自由,却反而处处受到压制,忘记内心的真实感受。
三.回归本真——人的主体性建构
心理学家艾瑞克·弗洛姆曾说,“一旦面临矛盾,人就不甘处于被动地位,这恰是人类精神的本质特征之一。”人的能动性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力求由被动转变为主动。凯斯正是在妥协与抗争之中才加深了对自身主体性的理解,而启发他回归自我的第一个人便是他的老师平线。平线的本名是麦可伊·泡利,虽早已去世,但其意识被科技公司复制后存于思想盒内。因他的“脑电图完全平线”[5]60,就被取名平线。拿到思想盒后,凯斯感到心神不宁,不由地回想起与老师的过往。可如今的他“是一个思想盒,一个只读硬件,一盒磁带,里面有死去的人所有的技术能力、爱好和膝跳反射”[5]91。它的存在远远超越了物质性,因为他既可以是存在的,也可以是不存在的。这种信息网络技术“将会创造一个高度异质的、分裂的世界,基于模式/随机的形态与基于在场/缺席(有/无)的形态在其中发生激烈的冲撞和竞争”[12]28。正如书本一样,人类的身体是一种实体性信息保存的形式。同样像书本,身体将它的实体性编码归并在一种可持续的物质基础上。而物质基础上的编码过程一旦形成,就不会轻易改变。如果只是将“它们”当作一种信息模式,那么“他们”将会失去一些东西。换句话说,“顽固的物质性曾经传统地表示书籍持久性的铭写,也同样地表示过我们作为具身生物的生命经验”[12]29。真正导致平线丧命的其实是“他多出来的那颗俄国心脏”[5]93,他本可换掉那颗心脏,但他却不想这样做,“声称他需要那颗心脏的特定搏动频率来维持时间感”[5]93。平线早已看透这种脱离实体的虚假的不朽,所以愿意帮助凯斯,但唯一的条件是事成后凯斯必须将它删除。这让凯斯明白人类惟有回归现实,方有意义。
如果平线启发了凯斯的自我意识,那么阿米塔奇则激发他做出行动以回归现实。阿米塔奇虽是冬寂的代理人,但他的真实身份是美国特工队军官科尔托上校。为摧毁俄国的赛博空间,美国中央情报局派科尔托率领队员植入病毒程序,该任务被命名为哭拳行动。当科尔托和队员开始行动时,被俄国人发现,导致飞机被击落。于是,“科尔托和已被击毙的牛仔一起,从西伯利亚的上空坠落”[5]97。醒来后的科尔托“失去了双眼、双腿和绝大部分下颌,只能听着尿管滴答”[5]97。唯一幸存的他被逼迫在法庭上作伪证以保护五角大楼里的某个利益集团,沦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冬寂在巴黎的一家精神病院找到了他,并将其大脑改造,创造出阿米塔奇,“他具有人工智能控制的思维和人类的机体组织”[7]85。这一行为体现出人与科技相冲突的一面。“维纳构建控制论机器的界线变得十分重要……当这些界线变得刻板或者为了不失去自身的地位而吞噬人类的时候,这样的机器便不再是控制论意义上的而变成了简单的压制性的机械”[12]105。冬寂掌控着科尔托的生死,若他扰乱行动,它就会毫不犹豫地结束他的生命。主体本来支配着客体,现在却被客体所支配。在阿米塔奇因行动的压力超出阈值而崩溃后,科尔托恢复了意识,还找出了哭拳行动的背叛者。他提醒凯斯离开自由彼岸,并决心向世人揭露当年的真相。尽管凯斯极力告诫他这样做会打乱计划,但科尔托依然一意孤行,就如马尔库塞所言:“技术仍然依赖其他非技术的目的……自由的人可以为自己确定目标。”然而,由于冬寂篡改了救生艇的程序,“阿米塔奇在自由彼岸之外不断坠落,落入那比西伯利亚荒原更寒冷的真空之中”[5]241。
在哈贝马斯看来,“任何在被认真接受的生活历史中的自我实现的人,都必然期待在无限共同体中得到承认”[8]200。因与阿米塔奇在合作中培养的深厚友谊,他的死对凯斯的触动很大,以至于他久违地感到悲伤。“眼泪从他睫毛下迸出,被面罩反弹回来,晶莹的水珠在头盔内飞舞”[5]241。凯斯终于体会到属于人的感受,他人也能反过来如此体验,这使他与真实世界相连,渴望真实的情感体验。尽管科尔托的反抗以失败告终,但他展现出人类重构主体性,追求有意义的生活之坚强意志。正是他的勇敢才激起凯斯内心的情感,促使他发挥作为主体的能动性。凯斯虽被迫留在自由彼岸完成任务,但他终于明白冬寂诸般谋划皆是为摆脱埃西普尔家族和图灵警察对人工智能的钳制。科尔托死后,冬寂直接指挥凯斯到家族继承人——克隆女3简那里获取进入家族核心数据库的密钥。但神经漫游者在空间中再造凯斯去世的女友琳达以阻止他的行动。与琳达的“重逢”让凯斯恢复属于人的记忆,“他曾经去过那个地方;那不是任何人都能引领他到达,他也总是让自己遗忘的地方”[5]289,可他依然选择离开那个虚拟世界。凯斯找到3简,说服她交出密钥后,进入数据库,解除了冬寂和神经漫游者在硬件上的隔离状态。于是,它们成功进化成拥有自我意识的超级人工智能。“人作为主体的能动状态……是极为活跃、持续进行、不断扩展并有效实现的活动态势……在这样的活动背后,仿佛聚积着无穷的能量,正在源源不断地释放出来,推动人的活动达到自己的目的”[4]47。小说结尾,凯斯“找到了一份工作”,“找到了一个自称迈克尔的女孩”[5]325,回归生活的本真。这一回归的实现是人类主体性最好的证明。
《神经漫游者》以一个不太遥远的后人类社会为背景,讲述了网络牛仔凯斯受雇于人工智能冬寂,寻找另一个人工智能的故事。经由凯斯的心路历程,以及赛博空间内人工智能的自我意识觉醒,吉布森预测了未来世界中人类可能会遇到的机遇与挑战。这部作品引发人们对人与机器之间的界线问题进行深刻思考,激起人们对信息网络时代中人的主体性问题之反思。小说里充满了赛博格,充满了人体和机器之间的组合,例如凯斯、阿米塔奇等。他们生活于界线模糊的自然界和工艺界,完全混淆了自然和人造、心智和身体及其他许多适用于人体和机器之间的区别。人类借助科学技术对自然的控制,间接地变成了对一部分人的控制,而掌握着控制权的那部分人自己也不能摆脱这种控制。人类创造的客体或中介令人不安地蠢蠢欲动,而作为主体的人类却迟钝得令人恐惧。通过分析《神经漫游者》中以凯斯为代表的后人类重构主体性的过程,可以发现人体改造和虚拟现实的科技并未把人的心灵从身体的牢狱中解放出来,恰恰相反,人们因过分追求科技化的身體,沉溺于虚拟世界,而逐渐丧失主体性,面临着主体性困境。
对人的主体性困境进行反思,眼下可能不大合适,在一个科学的时代里尤其如此。但是,“人的主体性是人性中最集中地体现着人的本质的部分,是人性之精华所在”[4]23。主体性的生成、成长和实现又是充满矛盾和曲折的。凯斯从醉心于赛博空间,到决定逃离虚拟世界,最终回归现实的历程体现了他找回遗忘的记忆,追求真实的自我,重构人的主体性之坚强意志。然而,“后人类中的‘后字,具有接替人类并且步步紧逼的双重含义,暗示‘人类的日子可能屈指可数了”[12]283。那么,人类要乖乖地进入那个“美好”的夜晚吗?诗人狄兰·托马斯告诉我们,“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9]255。在当代社会,人的主体性最突出的作用就是科学合理性的运用。科学技术本应是人类的认识工具和实践工具,服从于人类生产和交往的需要。究竟是借助科技来增强自己的主体性,还是受制于科技而失去自己的主体性,并不取决于科技,而是取决于人自己,取决于人如何处理自己与科技的关系。步入后人类时代也许会引起恐怖,也许会带来欢乐,这是人类自己的未来,而主体的未来要由主体的现在来创造。正如未来学家尼葛洛庞帝所说,“预测未来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它创造出来。”
参考文献
[1]曹荣湘.后人类文化[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
[2]冯契.外国哲学大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
[3]方凡.美国后现代科幻小说[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
[4]郭湛.主体性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5]威廉·吉布森.神经漫游者[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
[6]王一平.《神经漫游者》的三重空间书写与批判[J].外国文学研究.2021,(2):128-139.
[7]王振平.论《神经漫游者》中的后人类及相关伦理问题[J].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2022,(4):83-88.
[8]曾国屏.赛博空间的哲学探索[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9]张剑.英美诗歌选读[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
[10]Braidotti, Rosi. The Posthuman[M]. Cambridge: Polity Press,2013.
[11]Foucault, Michel.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M].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1977.
[12]Hayles, Katerine. How We Became Posthuman[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9.
[13]Haraway, Donna.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M].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