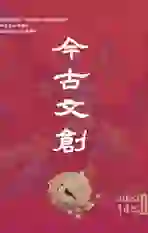陈忠实《白鹿原》中的女性悲剧意识
2023-05-31付小菲
【摘要】 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对女性的形象塑造上体现了他浓郁的悲剧意识,作者在作品中赋予了对女性深深的同情并且对女性命运的不公提出了抗议。《白鹿原》之中的一个个女性人物成为推动作品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封建教条下,很多女性的性格被压抑、思想被扭曲,甚至有人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封建制度的反叛者田小娥,一次次与命运抗争却最终被吞噬,死后还被镇妖塔镇压;悲惨的大家闺秀冷秋月,过于顺从封建传统伦理,最后被自己的正常的需求逼疯;热情的革命者白灵,作为理想主义的代表,却由于过于突出,最终还是悲剧结尾。田小娥、冷秋月、白灵三人,身份不同性格各异却同样被社会现实击打,作者的痛惜哀婉与悲剧意识在小说中呼之欲出。
【关键词】 女性悲剧;封建传统;悲剧意识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14-0022-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14.006
巴尔扎克说:“小说是一部民族的秘史。”[1]《白鹿原》在娓娓道来中展现了人民的生存处境与情感状态。在对女性的描写上,小说书写了不同女性几乎同样悲惨的命运,由于传统的贞洁观对女性的束缚与压抑,作为弱势的她们只能顺从,尽管她们有的迈出了反抗的第一步,但都遭到了封建伦理观念的抨击与社会的反噬。《白鹿原》不仅仅向我们展示了传统女性的血泪与屈辱,更重要的是其浓郁的悲剧意识引发了我们对女性身份地位以及悲剧命运的关心与思考。
一、悲剧女性代表——田小娥、冷秋月、白灵
(一)封建制度的反叛者——田小娥
田小娥是勇敢的,她努力地追求爱情,渴望摆脱自身的困境。尽管她美貌有主见,生活赋予了她一些美好,但最终却没有赋予她好的命运。
田小娥从一开始的出场便是悲剧。她在最美的年纪却被父亲卖给了郭举人,不仅要遭受冷眼,而且要受尽屈辱与虐待。与此同时,家里所有的人都把这件事情当作是一个笑谈,在黑娃出现之前,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体谅她的不易。遇到黑娃之后,她认为自己遇到了真爱,便主动出击,初尝甜蜜之后,黑娃却一再的懦弱,使她受尽苦楚,就连她被带回原上,也是受尽了冷眼。白鹿原是一个人杰地灵之处,在族长白嘉轩的管理之下,这个地方一切井井有条。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却无法接纳一个受过苦楚的女子,所有人都觉得她“不洁”,却没有想过这一切并非她的错。
一方面,她勇敢地突破封建礼教,不顾一切与黑娃私奔,在白鹿原上住在一个破窑洞里,却感到心满意足。在黑娃出逃之后,在鹿子霖的教唆之下,她拉白孝文“下水”,后来她发现被鹿子霖利用了的时候,直接将尿浇在了鹿子霖脸上。田小娥没有受过新式的教育,她的行为可能并不是那么的文明,但是她却以自己的方式坚守内心的善良,比如即便她恨白嘉轩,但是当白家出事的时候,还是贡献出了自己的鸡蛋,还对白孝文充满了负罪感。表面上,她确实是不贞洁的,与多个男人发生关系,但是这只是她生存的一种方式,她被鹿子霖诱骗上床,因为恨极了白嘉轩而勾引白孝文,最后却也把自己的全部幸福押在白孝文身上,甚至怀了白孝文的孩子。从这方面而言,她是勇敢的,也是善良的,所做的一切不过都是为了生存和追求幸福。另一方面,与时代的浪潮相悖,想要冲破巨大的封建礼教,那她的命运一定是悲剧的。她多次想与白鹿原抗争,多次想要追求幸福,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愿望,最后却把她送向了死亡。在活着的时候,她是男人泄欲的工具。就像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对女性地位的评价:“男权主义者在‘女人身上只见‘女,不见‘人,把女人只看作性的载体,而不看她独立的人格。”[2]無论是最初的郭举人、黑娃,还是后来的鹿子霖、白孝文,都在利用田小娥的身体,达到或身体或利益上的满足,可是一旦危难之时,她就变成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最后,她凄凉的死在窑洞之中,死后还被镇妖塔压住,成为原上的“妖女”。《白鹿原》中,有一段比较奇幻的描写,田小娥借助公公的口发出自己的怨恨:“我到白鹿村惹了谁了?我没偷掏旁人一朵棉花,没偷扯旁人一把麦秸柴禾,没骂过一个长辈人,也没搡戳过一个娃娃。大呀,俺进你屋你不认,俺出你屋没拿一把米也没分一根蒿子棒棒儿,你咋么着还要拿梭镖刃子捅俺一刀?大呀,你好狠……”。[3]在田小娥的句句控诉之中,悲痛与讽刺,浮上水面。她不贪图名利,如果她能够嫁得一个如意郎君,如果她可以入得一个正常家庭,被白鹿原所接受,那么她应该也是相夫教子安然度日之人吧,可是她最终却被封建传统活活吞噬。
(二)悲惨的大家闺秀——冷秋月
冷秋月是在冷先生的精心呵护之下长大,她知书达理,性格温和。在出嫁之前她都没有出过门几次,一直被冷先生以三从四德所约束,严肃的家风之下,塑造出了冷秋月这样的大家闺秀。如果说田小娥是封建制度的反叛者,而造成最后被吞噬的悲剧,那么冷秋月的悲剧,便是她太顺从于封建制度,顺从于父权夫权,爱上一个自己不该爱的人,最后像她的名字一样凄冷无比。
冷秋月不像田小娥一样,需要去努力生存。她以一个“大家闺秀”的身份出场,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下,嫁给了鹿子霖的儿子鹿兆鹏,也就是她悲剧的开始。婚后,她像所有贤良的儿媳妇一样,孝顺公婆,谦卑有礼。即使丈夫无比冷淡,她还是一心为丈夫着想,从没有提出过分的要求,在表面上她无欲无求。内心里她渴望和鹿兆鹏有正常的夫妻生活,渴望得到丈夫的关心和爱护,渴望正常的性生活,甚至当她看见田小娥的时候,一方面觉得恶心,另一方面她又“嫉妒起婊子来了,她大概和黑娃在那孔破窑洞里夜夜发羊痫风似颤抖”。[4]在她与黑夜无尽的抗争之时,公公鹿子霖的醉酒直接将她的欲望推向了高峰,她甚至幻想与公公交合,最终在鹿子霖“你才是吃草的畜生”这样的暗示下,她彻底疯了。她内心的贞节观被打破,自尊被撕裂,彻底成为婚姻的牺牲者。在“疯言疯语”下,被父亲的“一剂药”毒哑,最终死在了一个沉寂的夜里。
冷秋月不像田小娥,更没有办法变成田小娥,从小严格的家风使她没有办法做出违背伦理道德的事情,更没有办法接受一纸休书,只能抱着从一而终的态度生活,而公公的轻贱直接冲破了她内心的自尊。除了公公的轻贱、丈夫的冷漠、父亲的不理解,这悲剧背后的一切主要归咎于残忍的封建礼教,活活地扼杀了一个鲜活的生命,结束了她短暂的一生。
(三)热情的革命者——白灵
与冷秋月和田小娥相比,陈忠实先生是偏爱白灵的,使她成为美和正义的化身。在家做女儿时,她受尽宠爱,长大后她思想解放,追求自由,和自己的父亲白嘉轩有完全不同的想法。“在书中以白灵为主的女性形象如一道闪电,撕破了封建社会的黑云,并且展现出了对理想社会的一种追求。”[5]
白灵从小作为家里最小的女儿,性格活泼,是家里长辈的掌上明珠。她不仅是第一个没有裹脚的女孩子,长大之后还进入私塾读书。在读书的过程之中,她有了很多自己的思想,但是这些思想与父亲完全相悖,当继续读书受到父亲的反对之后,她以死威胁父亲,才得以继续读书。她本与鹿兆海相爱。但发现自己和鹿兆海加入了完全不同的党派的时候,坚决地与鹿兆海分道扬镳,阴差阳错之际,认识鹿兆鹏,后来与鹿兆鹏产生爱情,并孕育一个孩子。国共合作之后,她积极地投身于革命,在面对无数次的危险之时,她始终坚持自己的理想信念,并因此多次得罪了她的父亲,过于突出她得罪了一些人,酿成了悲剧,最终的悲剧令人惋惜,白灵这朵正义之花就此陨落。
以上列举的三个女性是完全不同的个体,却代表着不同的群体。她们有的悲剧从出生就开始,有的悲剧是从长大开始;有的被封建思想所吞噬,有的为自己的革命理想所献身;有的只想安稳度日却备受打压,有的只想夫唱妇随却无法实现…… 从整体上,《白鹿原》之中女性的结局让人感觉到悲哀,因为无论这个女性是怎样的,好像都没有什么出头之日,也没有什么独立个体。
除了以上列举的例子,其他女性也没有逃脱悲剧命运。比如书的开头:“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6]让人实在无法理解,六房女人丧命,对于男人来说,竟然成为炫耀的资本。又比如白孝文的媳妇儿,白孝文夜夜纵情,白孝文的奶奶卻只训斥这个做孙媳妇的,难听的话脱口便出,好像面前的不是孙媳妇,而是一头牲口。后来土匪打劫,白孝文媳妇被强奸,可当他看到那个场景时,第一反应是呕吐,并不是去安慰自己的妻子,之后这个女人的结局也必定是走向死亡。各种女性的例子数不胜数,她们大多在蒙昧悲剧状态之中,过完自己的一生,大多数的女孩子在家遵从父亲出嫁遵从丈夫,一旦自己的婚姻生活不幸,那生活就没有人出头之日。从这些女性的悲剧命运,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重视他人生命与个人意志的现代社会远未到来,女性解放还远未完成[7]。
二、浓郁的悲剧意识
悲剧意识是对悲剧现实生活的深刻体验,是在悲剧性现实生活中产生的悲情,它代表了人类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必然冲突;表现了人类在苦难面前勇敢地斗争、反叛、积极地寻求自我救赎;它表现了苦难生活的艺术激情和勇气。[8]《白鹿原》中,我们可以看到女性为了生存也有过自己的反抗,并不是所有的女性都是逆来顺受的,她们也有努力冲破封建教条的想法,但是最后失败了,这种悲剧意识在“这没有最终胜利的希望但又永不妥协的奋斗之中才表现的最充分”[9]。
《白鹿原》创作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时期,一方面,很多封建残余思想还没有消除;另一方面,新的思想文明冲击着人们的意识。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人们的精神文明产生了极大的迷惘,人的生存理想应该如何实现?女性的地位和身份应该如何看待?最后,这所有的问题,都会在社会的曲折发展之中得到一一的回答。
陈忠实先生的《白鹿原》对女性的形象塑造上体现了他浓郁的悲剧意识,而这种悲剧意识主要体现在女性命运的悲剧上。作者在阅读县志时,发现在“一部二十多卷的县志,竟然有四五个卷本用来记载本县有文字记载的贞妇烈女的事迹或名字”[10]。这些女性用自己一生的命运为赌注,只是为换来一个“贞洁烈女”的空号,她们用自己鲜活的生命守着一个又一个漫长的黑夜,却要把个人的欲望压抑在心底的最深处,莫言的《红高梁》中记载了妇女晚上睡不着数豆子的场景,应该也是那个时候许多妇女的常态吧。作者在作品中给予了女性深深的同情并且对女性命运的不公提出抗议,田小娥如花似玉的年纪,却要嫁给70多岁的郭举人,而郭举人只是拿她的身体做一个“泡枣”的工具;冷秋月夜夜独守空房,大家闺秀却受到丈夫的冷落,婚后并无过错,却一直承担着婚姻的代价,最后活活地被自己的欲望、被周围人的冷漠逼疯,而父亲为了保住整个鹿家的名节,不深究女儿在“疯言疯语”的背后也说出了鹿子霖不可告人的秘密的事实,直接给女儿送上猛药,将她毒哑。
如果说来自社会的压抑和他人造成的女性悲剧令人叹惋,那么女性对悲剧的不自知则将这种悲剧意识进一步加深。在文中“白赵氏”和“白吴氏”是封建纲常三从四德的守护者。在白嘉轩的前六个女人相继死后,母亲“白赵氏”直言女人“不过是窗户糊的纸”。在丈夫死前,她完全顺从于丈夫,从不参与族内大小事,而丈夫死后,这样一个小脚女人在家里稳如泰山,认定给儿子传宗接代是家庭的唯一大事。当白嘉轩的前几房太太相继去世之后,原上疯传着白嘉轩的风言风语,原上的很多人不愿意再嫁女儿,吴掌柜因得了秉德老汉的恩情,在喝酒言欢的过程之中,就把罂粟种子和女儿许给了白嘉轩,在白家这边,吴掌柜是仁义的,可是到了女子这边,相当于父亲把她的性命压在了自己的恩情上。新婚的当夜,白吴氏拒绝同房,腰上挂着桃木棒槌,说百日之后才可以同房,可是换来白嘉轩的暴怒之后,她唯一的独立意识也被击破,即使冒着生命危险也满足丈夫的私欲,这种独立意识一旦放下便是一辈子。就连最后躺在床上奄奄一息,想要见女儿最后一面,也被丈夫安排的理由欺骗,白嘉轩一生挺直的腰杆儿,都不肯因为妻子的死弯腰一次,可是对于白吴氏而言,这一生她嫁给白嘉轩感到无比满足。
作者以浓厚的悲剧意识,书写了这些女性悲惨的一生,通过这些女性的命运,批判了儒家伦理纲常“三从四德”“存天理灭人欲”。在人们思想不断解放的同时,封建传统伦理观念依然在一些人的心中根深蒂固,时时刻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甚至影响了女子的一生。传统伦理道德之下,温顺听从的女子是锦上添花,而稍具有独立意识的女性便是红颜祸水。
作品中这种浓郁的悲剧意识,能够让我们在悲剧的过程之中感受到信仰和力量。《白鹿原》中,有些女性也会做出一些反抗,作者以不断描述社会的“丑恶”来对比个人斗争的“美丽”,以书写女性地位来激发女性的反抗与人民的思考。全书整体悲凉冷漠的基调之中渗透着一代又一代的女性对个体生命理想的执着追求,她们的努力为后世女性解放做了铺垫。
参考文献:
[1]陈忠实.白鹿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2]波伏娃.第二性[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3]陈忠实.白鹿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4]陈忠实.白鹿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5]秦艳红.对《白鹿原》中白灵形象的分析[J].课外语文(下),2016,(7):69-72.
[6]陈忠实.白鹿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7]吴成年.论《白鹿原》中三位女性的悲剧命运[J].妇女研究论丛,2002,(6):39-44.
[8]梁雪梅.论《白鹿原》的悲剧美学[J].文学教育(上),2021,(12):19-21.
[9]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2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
[10]陈忠实.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写作手记[J].小说评论,2007,(04):44-50.
作者简介:
付小菲,女,汉族,山东临沂人,山东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