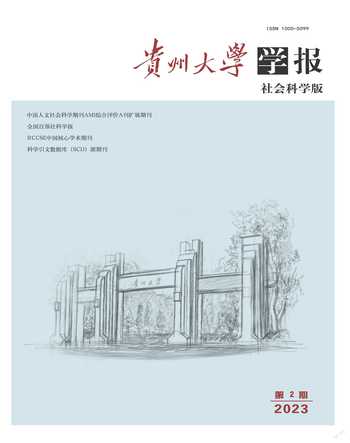嵌入性视角下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的实践逻辑及反思
2023-05-30田鹏
田鹏
摘 要:
“十四五”期间,易地扶贫搬迁群众社会融入和共同富裕的后续扶持压力依然很大。构建科学合理的后续扶持体系,在迈向共同富裕新征程中兼具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研究将后续扶持演化周期划分为脆弱性治理和可持续发展两个阶段,从扶持客体、扶持主体及扶持机制三个维度构建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实践逻辑的分析框架。从脆弱性治理到可持续发展,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实践呈现出扶持客体动态性、扶持主体多元化、扶持机制协同性、政策路径系统性等特征。嵌入性视角下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的实践逻辑主要包括后续扶持理念多元多维转换,后续扶持资源要合理有序流动,后续扶持政策风险要科学有效防范等,真正实现“搬得出、稳得住、有就业、逐步能致富”的目标。
关键词:
易地扶贫搬迁;嵌入性;后续扶持
中图分类号:C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23)02-0057-11
一、问题的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2月25日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指出:“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标志着我们党在团结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同时,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异、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仍然任重道远。”[1]5《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显示,截至2020年底,我国易地扶贫搬迁规划建设任务已全部完成,累计建成易地扶贫集中安置区约3.5万个,建设安置住房266万余套,960多万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全部入住并实现脱贫。另外,在此过程中还配套新建或扩建中小学和幼儿园6 100多所、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2万多所、养老服务设施3 400余个、文化活动场所4万余处。同时,加强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成效显著,出台了就业帮扶、金融帮扶、社区管理等一系列具体支持政策措施,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中劳动力就业比例达到73.7%,搬迁贫困家庭中有劳动力家庭就业比例达到94.1%。
但是,无论从区域分布还是安置规模抑或群体特征上看,实现全面脱贫目标后,搬迁群众脱贫基础仍然不牢固,安置地产业基础在搬迁前后未发生根本性改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仍相对不足。另据统计,960多万搬迁群众中,60岁以上老年人约占四分之一,妇女超过40%,他们就业能力弱、返贫致贫风险高[2]。这些问题均表明,“十四五”期间易地扶贫搬迁群众社会融入和共同富裕的后续扶持压力依然很大。因此,如何完善科学合理的后续扶持机制,构筑搬迁群众稳定脱贫和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在迈向融合发展的共同富裕新征程中就兼具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从理论视角及分析框架上看,当前学界关于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的代表性理論视角主要包括空间变迁、社区治理以及社会融入等。空间变迁视角持有者认为,易地扶贫搬迁本质上是传统村落共同体空间解体与现代性导向的新型地域社会空间再造的辨证过程,地理空间、社会空间和表象空间的结构失衡,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面临的核心症结[3];因此,有效发挥空间变迁及其再生产机制对易地扶贫搬迁及其后续扶持稳定减贫的政策效应,就必须聚焦后续扶持过程中空间再现、空间实践以及再现空间的辨证互构和协同作用[4];另外,还要在此过程中注重带贫主体、扶持主体等多元利益相关者的主体性空间再造[5]。社区治理持有者认为,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面临的突出问题是现代化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效能不足,这主要是由搬迁过程中采用运动式治理与搬迁后新社区采用常规化治理之间的功能失调、资源错配及其结构失衡导致的[6];因此,要切实发挥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对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作用,就必须在后续扶持过程中回归搬迁安置社区的共同体本位,从社区主体培育、社会空间营造以及公共政策供给等方面入手,构建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良性互动的新型现代社区治理体系[7]。
与空间变迁、社区治理相关的另一个重要视角是社会融入视角。社会融入视角将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视作搬迁群众再社会化的动态过程[8],实践中搬迁群众社会融入阻碍因素既包括客观环境和外在条件变化带来的不适应、不协调,也包括公共服务、生计能力、产业发展以及权益受损等方面产生的制度性不充分、结构性不均衡[9];因此,新时期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要结合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聚焦搬迁群众生计能力和可持续发展,围绕有效融入迁入地经济社会发展,从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和心理融入以及可持续发展能力等方面同步推进[10],培育社区共同体意识、增强社区归属感和凝聚力,促进搬迁群众经济、社会、文化、心理等多个维度的社区融合及社会融入,最终实现其内生性、可持续高质量发展[11]。
从逻辑起点和研究进路上看,空间变迁、社区治理和社会融合三种视角各有侧重。空间变迁视角聚焦易地扶贫搬迁过程中行政、经济、文化、生态等多维空间再造,侧重于搬迁前后地理空间转换与安置区社会空间营造。社区治理视角凸显易地扶贫搬迁过程中传统村落治理模式与现代社区治理体系之间的内在张力,尤其表现为迁出地与迁入地之间因机制转型不顺、政策衔接不畅,以及由此引发的“两头跑”“多头管”等治理难题。社会融合视角基于搬迁群众市民化进程中的主体性建构,从经济、社会、文化、心理等多个维度,考察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的应然样态和实然路径。总体来看,既有理论视角和研究进路对于全面深入理解易地扶贫搬迁的政策过程、实践样态及其后扶路径均有良好的学理启示。
但是,从现实经验和演化规律来看,共同富裕背景下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需要延续精准扶持理念,客观把握搬迁动员、稳定脱贫、可持续发展到社会融入全生命周期演化规律[12]。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从后续扶持行为属性及其演化规律上构建易地扶贫搬迁融合发展与共同富裕的理论视角与研究进路;另一方面,从类型学上全面把握易地扶贫搬迁多元化推进模式及不同扶持阶段,精准构建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机制及其政策体系。一言蔽之,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具有社会行动的多重性、演化规律的周期性以及融合发展的必然性等基本特征,需要超越空间变迁、社区治理和社会融合等既有理论视角及其分析框架,构建一个涵盖扶持主体、扶持要素、扶持机制的整体性理论视角,以及从稳定脱贫、能力发展、社会融入到共同富裕全生命周期的动态演化分析范式。
鉴于此,本研究首先借鉴新经济社会学嵌入性理论,提出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的嵌入性理论视角并阐释其理论意涵及实践样态。其次,基于嵌入性理论视角,从扶持诉求、扶持主体和扶持机制动态演化角度出发,将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划分为脆弱性治理和可持续发展两个阶段,构建不同阶段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的差异化制度设计和政策路径。最后,从后易地扶贫搬迁时代共同富裕大格局出发,锚定巩固扶贫搬迁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战略定位,聚焦扶持理念、扶持资源和扶持体系,构建新时期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机制演化的实践逻辑。
二、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的分析框架:嵌入性视角的启示
1.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嵌入性的理论意涵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乡村振兴局等20部委颁布的《关于切实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指导意见》(发改振兴[2021]524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指出,“十四五”时期如何高质量推进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构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成效机制,关键要结合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战略,聚焦原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大中型安置点,按照分区分类、精准施策的原则做好后续扶持的顶层设计;同时,紧紧扭住就业这个牛鼻子,多渠道促进就业,强化社会管理,促进社会融入,真正实现“稳得住、有就业、逐步能致富”。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明确指出:“要切实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各项工作,让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对易地扶贫搬迁群众要搞好后续扶持,多渠道促进就业,强化社会管理,促进社会融入。对脱贫县要扶上马送一程,设立过渡期,保持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1]7
作为一项政策性很强的综合性社会工程,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行为具有其独特的理论属性。从现实经验来看,2021年伊始的五年过渡期内,后续扶持首先要紧紧围绕实现可持续生计和综合性就业这一迫切诉求,增强产业培育、生计转型和职业发展的带贫、益贫效应;因此,后续扶持离不开必要的经济基础和物质保障[13]。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的社会、生态、文化和心理等其他多重属性,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产业支撑和就业保障作为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但以非农产业和多元就业为导向的经济制度基础,也不能脱离后续扶持所处的特定阶段和政策环境。质言之,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行为表现出经济、社会、文化、心理等多维面向和多重属性,且不同属性及其扶持行为之间具有很强的辨证互构性,不仅表现为后续扶持从稳定脱贫、能力发展到社会融入全生命周期的动态性、阶段性,也集中体现在后续扶持机制中政府、市场、集体、家庭等多层级、多元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及协同推进。
卡尔·波兰尼用嵌入表达这样一种理念,即经济是从属于政治制度、宗教信仰和社会文化的[14],而将嵌入概念引入新经济社会学的则是马克·格兰诺维特。作为一个整体性理论分析框架,格兰诺维特的嵌入概念试图调和社会学与经济学里的过度社会化与低度社会化之理论张力,在微观社会行动和宏观社会结构之间开辟一条相互关联的理论通道,并将个体能动性置于特定社会经济网络及关系结构之中,既聚焦社会网络对个体行动的结构性制约,又强调个体行动对其所处结构制约的主观能动性[15]。作为一种理论视域和研究范式,格兰诺维特的嵌入性理论采用关系主义理论范式和结构—能动研究进路,聚焦社会结构与个体能动之间多重关联及辨证互构的动态过程。本研究在此意义上构建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嵌入性理论视角,其理论意涵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作为一种社会行动具有嵌入性特征。作为社会行动的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本身是一系列理性行动的社会建构及其主体性实践,具有显著的建构性、主体性特征;但是,这种主体性社会构建无法完全遵循扶持主体自身的主观动机和理性意志开展,而是在后續扶持全生命周期演化不同阶段及其时空环境的现实制约下进行的;因此,扶持主体的社会行动实质是在特定社会环境、制度体系和利益联结等体制机制因素及其结构性制约下的策略性实践。另外,作为社会行动的后续扶持也可以通过搬迁安置区和搬迁群众等扶持客体的反身性实践作用于其所处社会环境与结构制约,尤其体现在为适应特定产业模式、生计能力、治理体系等现实诉求而进行的主体性调适和政策性帮扶[16],目的就是为了最大程度激发政府、市场、社会、集体等多元扶持主体内生动力,优化后续扶持公共政策绩效,提升后搬迁时代相对贫困治理效能,从而实现主观能动性建构对客观结构性制约的反作用。
第二,正因为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内在属性及其实践意涵均表现出显著的嵌入性特征,在全面把握后续扶持及其机制演化的实践逻辑时,新经济社会学意义上的嵌入性理论所提倡的关系主义研究范式就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嵌入性理论倡导的关系主义方法论及其动态化研究进路,要求精准识别后续扶持全生命周期演化过程中多元扶持主体之间的利益结构和关联式,既包括结构功能层面后续扶持不同行为主体之间的经济性、社会性、文化性等多重实践关联;也包括后续扶持全生命周期演化过程中多元扶持主体之间的利益关联及其动态互构,形成政府、市场、社会、集体等不同主体扶持机制的协同效应[17]。一言蔽之,嵌入性理论视角决定了唯有关系主义的动态分析范式才能客观系统地把握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行为的内生属性及其机制演化的实践逻辑。
第三,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动态实践过程中的行为嬗变、结构转型与机制演化,在经验层面遵循新经济社会学意义上的嵌入性理论逻辑。后续扶持主体、扶持对象、扶持内容、扶持方式、扶持期限以及扶持效果等,均无法脱离其所处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扶持要素的制度环境和演化阶段;换言之,后续扶持“脱嵌”将导致供需结构失衡和政策效能低下。构建高质量后续扶持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既不能揠苗助长,违背全生命周期演化的实践规律,也离不开必要的产业基础和就业保障;同时,要真正实现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助力融合发展和共同富裕,就必须以县域融合和人的城镇化战略为契机,从“搬身体”“搬物体”到“搬人心”“搬文化”[18]。因此,后续扶持行动嵌入性决定了必须将其多元实践模式与扶持机制,内嵌于政府、市场、集体、家庭的实践关系中进行系统性、动态性考察,避免孤立化、静态化处理后续扶持模式转型与机制演化的实践过程。
2.“客体—主体—机制”三维一体: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的分析框架
《指导意见》指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切实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持续巩固易地扶贫搬迁脱贫成果的关键是分区分类、精准施策,应当从促进更充分更稳定就业、推动后续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构建开放融合的安置社区以及推动大型搬迁安置点新型城镇化建设等六个方面入手,紧紧抓住就业这个牛鼻子,多渠道促进就业,强化社会管理,促进社会融入,真正实现搬迁群众的“稳得住、有就业、逐步能致富”。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是多元扶持主体在既定时空环境和制度约束下,基于利益结构均衡化和扶持效应最优化的动态建构,其实质是空间、要素、主体在特定时空条件和理性视域下的综合性实践。因此,兼具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等多重属性的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的社会行动及其演化机制,无论在产业培育、生计转型、公共服务、社区治理、社会融入,还是在扶持资源配置、扶持行动价值导向以及扶持机制协同演化等方面,都应当遵循嵌入性实践规律,不断进行体制机制创新,强化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等多重扶持机制的合力效应。
2021年伊始的五年后续扶持过渡期内,要基于搬迁群众脆弱性治理、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以及在地化、融合化主体性重塑的不同演化阶段,培育后扶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新产业、新业态和新动能,抓住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契机,提升搬迁群众人力资本和可行能力;同时,持续激发调动市场、政府、社会、集體、家庭等多元扶持主体的内生动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后续扶持治理共同体。因此,本部分基于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嵌入性特征,遵循从脆弱性治理到可持续发展再到全面融合与共同富裕的全生命周期演化规律,从“扶持谁”“谁来扶”“如何扶”以及“如何退”等现实问题出发构建本研究分析框架。
第一,扶持客体。扶持客体回答的是“扶持谁”的问题。作为主体行动和社会建构的后续扶持及其现实诉求,无法“脱嵌”于其所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和后续扶持演化规律,尤其是从易地搬迁到融合发展进程中乡土性空间消解与现代性社区重建引发的结构冲突及其社会风险[19]。从发生学角度来看,作为一种整体性社会建构和系统性政策实践的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诉求的生成与演化,受到城乡关系、空间资源、生计模式、治理体系、文化心理等多重因素制约。同时,后续扶持诉求不仅表现为个体、家庭、社区、县域四位一体的静态结构,更是一个动态的社会变迁和主体嬗变过程。随着安置区基础设施、产业结构、公共服务、治理体系、文化建设等不断完善、日趋健全,以及搬迁群众市民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扶持诉求也呈现出个性化、多元化、专业化。“重建设、轻运营”“重硬件、轻服务”“重行政、轻市场”“重外驱、轻内生”等传统扶持理念、扶持手段、扶持资源以及扶持机制都需要不断创新,以适应新诉求、新环境带来的新挑战。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诉求不断演化过程中,还必须凸显弱势群体脆弱性风险治理的现实诉求,尤其是老年人、妇女、儿童以及劳动力缺失家庭。
第二,扶持主体。扶持主体回答的是“谁来扶”的问题。嵌入性视角下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主体的功能结构及价值属性,受政府、市场、集体、搬迁群众等不同因素影响;后续扶持主体结构、利益关联及其演化机制,是政府主导、市场驱动、村社资源、家庭网络以及搬迁群众自主实践等多重逻辑的动态互构。回归中国扶贫政策演进尤其是搬迁扶贫的历史沿革可以发现,搬迁主导者从群众自发与政府引导到政府主导与群众参与,再到政府主导、市场驱动、社会参与、群众自愿,市场化、社会化的多层级扶贫搬迁后续扶持体系不断完善,从计划经济模式下政府包办的救济式扶持,渐次转向开发式扶贫方针下以可持续生计能力为导向的规范化、制度化扶持体系[20]。随着精准扶贫战略及其后扶贫搬迁时代到来,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延续精准扶贫理念,扶持主体呈现出多元化、协同化,包括迁入地与迁出地政府,迁入地市场、迁出地村集体、迁入地社区以及包括社会组织、群团组织、志愿组织等在内的社会力量。因此,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战略及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有效衔接,必须从扶持主体的多元化、协同化、专业化等方面入手,构建政府、市场、社会、集体、家庭等多主体、多层次、专业化的后续扶持体制机制及政策体系。
第三,扶持机制。扶持机制回答的是“如何扶”以及“如何退”的问题。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诉求社会建构与扶持主体功能属性两个层面的嵌入性,进一步强化了后续扶持行动微观层面的嵌入性特征,具体表现在后续扶持机制及其演化规律上。从现实经验来看,扶持主体与扶持机制具有高度关联性,政府、市场、社会、集体、家庭以及搬迁群众个体等多元扶持主体,在实践中有其自身独特的扶持机制;不同扶持主体都可以在后续扶持不同演化阶段发挥其比较优势和特定的作用。随着后续扶持不断深入,扶持主体的功能结构及其演化机制应当呈现政府、市场、社会、集体、家庭的联动协调与良性互动。具体而言,在脆弱性治理阶段,政府依然需要扮演主导者角色,尤其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跟踪帮扶、多元就业动态监测和风险预警等方面,务必压实各级地方政府主体责任;同时,强化行政主导治理机制,在搬迁群众脆弱性治理,致贫返贫与返迁回迁的风险治理、群体性事件的应急治理等方面,都应当体现政府主体责任和行政主导机制。在可持续发展阶段,政府主导的行政机制应当转向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新型职业农民等多元带贫主体,通过市场化、竞争化的资源配置机制,发挥它们在巩固脆弱性治理成效、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强化扶持主体协同效应、优化扶持利益联结机制等方面的比较优势[21]。另外,可持续发展阶段,政府应当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模式、完善公共服务以及创新基层治理等方面,继续发挥其特定作用,而非通过其“有形之手”直接配置扶持资源。集体组织应当以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为契机,保障搬迁群众合法权益,营造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多元融合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构建有利于搬迁群众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的制度环境和政策体系,为后续扶持“去身份化”和搬迁群众“社会性断奶”并顺利过渡到共同富裕阶段奠定扎实有效的社会基础和制度保障。
三、脆弱性治理与可持续发展: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的经验阶段
1.脆弱性治理
脆弱性治理阶段是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实践演化的首要阶段。搬迁群众脆弱性治理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面临的现实挑战,即如何防止后搬迁时代出现大规模返贫、致贫和返迁、回迁等脆弱性问题及其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风险。就现实经验而言,脆弱性治理阶段的搬迁安置社区呈现原子化、碎片化特征,集中表现为搬迁群众定居率低、旧村庄拆旧复垦率低、权益保障认知度低、生计能力分化程度高、新社区组织化程度低以及基层治理效能不足等现实困境。从扶贫诉求来看,该阶段最核心的扶持诉求就是刚刚完成易地安置的搬迁群众生计脆弱性导致的脱贫成效不稳定,以及刚刚完成组织“翻牌”和制度“移植”的搬迁安置社区因无法有效运转导致的治理效能不足,尤其是迁入地和迁出地之间的“两头治”问题[22],这些问题既会影响到后续扶持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预期目标的达成,进而影响扶贫搬迁脱贫稳定性、可持续性,更重要的负面效应和社会风险表现在搬迁安置社区建设和基层治理方面,实践中大规模返迁、回迁和致贫、返贫不但会起到负面示范效应,还会削弱搬迁群众对新社区、新生活、新未来的自信心。
从扶持主体及其作用机制来看,脆弱性治理阶段应当延续精准理念,继续压实并发挥政府“有形之手”在脆弱性治理、应急性治理、风险性治理等方面的主体责任和主导作用,在精准识别搬迁动员和易地安置过程中空间变迁和要素整合产生的连带性问题和社会风险的基础之上,通过面向家庭、个体、社区等不同层面脆弱性的多元化治理,统筹人、地、钱、业等地域构件和空间要素,重构人口搬迁、土地复垦、生态治理、就业保障的良性互动以及致贫、返贫监测预警动态机制。因此,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脆弱性治理阶段,应当聚焦人口搬迁、村落解体及安置区重建初期面临的生计能力弱、治理效能低、迁出地与迁入地资源要素无法有效整合,以及由此引发的脆弱性、风险性,建立健全空间联动、权益转移、政策衔接、机制完善的脆弱性扶持政策体系及其风险治理机制。
2.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阶段是在巩固脆弱性治理成效基础上,进一步聚焦内生性发展和可持续性发展两种能力。在巩固拓展脆弱性治理阶段性成效基础上,以家庭生计能力、社会政策机制以及社会心理体系为实践抓手,重建搬迁安置社区新型社会生活共同体,提升搬迁群众自主发展能力与可行性能力。就现实经验而言,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的可持续发展阶段,虽然已经有效规避了脆弱性治理阶段面临的一系列社会风险,但从可持续性和可行性两个方面的能力建设来看,该阶段搬迁安置社区和搬迁群众依然面临从劳动力密集型向人力资本密集型就业结构及其高质量职业发展转型的强烈诉求。可持续发展阶段搬迁群众不仅满足于“有就业”,或者是在政府主导下的“政策性就业帮扶”,如制度设计明确规定的有劳动力的搬迁家庭实现至少1人就业[23];而且更加关心如何实现可持续、高质量的“好就业”。实践中这一矛盾集中体现在后续扶持政策体系中就业技能培训的供需结构失衡。另外,搬迁安置社区在可持续发展阶段面临的扶持诉求也已经从脆弱性治理阶段的组织“翻牌”和制度“移植”,过渡到如何通过党建引领、民主协商、服务创新、民族互嵌以及文化涵养等多元化方式实现新型社会生活共同体重建。
可持续发展阶段的政策瞄准和目标导向是在巩固脆弱性阶段扶持成效的基础上,聚焦并强化搬迁群众可持续生计、制度性保障等主体性能力建设。该阶段要强化搬迁群众家庭可持续生计能力和市场化导向职业发展体系,具体包括集体产权改革、可行性能力建设以及社会化、市场化导向的可持续产业就业和高效能社区治理,从而有针对性地解决可持续发展阶段面临的政治参与脱嵌、生计系统脱嵌与社会网络脱嵌等一系列现实困境[24]。从扶持主体及其作用机制来看,与脆弱性治理阶段政府主导的行政扶持机制不同,可持续发展阶段应当转向政府与市场良性互动、高效协同的扶持格局,既要进一步发挥政府在搬迁群众合法权益保障及其可行性能力建设方面的基础作用,更要利用好市场这只“无形之手”在搬迁群众高质量就业、现代性嬗变和主体性重塑等方面的比较优势,通过优化营商环境、改善创业生态、创新市场服务等多种方式优化扶持资源配置机制、提升扶持政策效能,最终与政府这只“有形之手”一道形成可持续发展阶段后续扶持合力效应。
四、从脆弱性治理到可持续发展: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的实践逻辑
1.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的实践特征
首先,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客体呈现动态演化特征。从脆弱性治理阶段到可持续发展阶段,不同演化阶段和扶持周期里后续扶持的问题导向和实践重心大相径庭,脆弱性治理阶段要解决“稳得住”的问题,处理的是那些直接影响到搬迁安置社区稳定和搬迁群众切身利益的现实问题,如返贫致贫、返迁回迁以及由此引发的社区治理“空心化”“无主体化”等。可持续发展阶段则要回应“有就业”和“逐步能致富”的政策目标,实践中以千方百计实现“一户一就业”为基本目标,在此基础上通过人力资本提升和职业能力培训逐步转向高质量就业,即从单纯家庭就业诉求导向下的生存理性到可持续生计能力发展下的经济理性,再到可行性能力和福利权利保障下的社会理性。同时,可持续发展阶段的搬迁安置社区建设,也在有效规避了村落解体和社区重组过程中面临的一系列社会风险基础上,转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因此,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机制演化的首要特征就是扶持诉求的社会性建构和动态性演化。
其次,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主体多元化、扶持方式专业化趋势显著。具体到后续扶持的不同演化阶段和扶持周期里,脆弱性治理阶段的扶持机制以政府主导和行政动员为主,无论是政府在搬迁安置社区基础设施配套、返贫预警監测、就业持续跟踪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还是政府在搬迁安置社区综合治理、社会稳定风险防范与化解方面的主体责任,都凸显了与其他扶持主体和扶持方式相比,政府主导及其行政动员在脆弱性治理阶段的基础地位和比较优势。但是,政府主导与行政动员的扶持机制在可持续发展阶段的比较优势,逐渐被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联合体以及新型职业农民等多元化带贫主体取代,通过构建政府、市场、社会、集体等多元扶持主体良性互动、协作共进的“大扶持”格局,才能真正实现脆弱性治理阶段向可持续发展阶段的顺利过渡,并为后续扶持“去身份化”和“社会性断奶”奠定扎实可靠的政策基础和制度保障。
最后,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系统工程。实践中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机制还表现出显著的联动性特征,从脆弱性治理到可持续发展,从扶持初期聚焦“稳得住”和“有就业”,再到扶持后期凸显“逐步能致富”的扶持效应,后续扶持的联动性主要表现在政策目标、权益保障和治理体系三个方面。不同扶持阶段政策目标具有较强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即“稳得住”“有就业”和“逐步能致富”的政策目标本身就有梯度性和层级性,能够很好地引领后续扶持脆弱性治理和可持续发展两个阶段的顺利过渡和有序衔接。后续扶持在搬迁群众合法权益保障方面也具有联动性特征,实践中主要表现在迁出地权益流转和迁入地权益落实之间的存续和转移,以及迁出地享有的“两不愁三保障”与现行帮扶政策平稳过渡到迁入地并继续享受,尤其是承包地流转和集体资产分配权益在“三权分置”和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大背景下,转换为迁入地助推搬迁安置社区融合发展并实现共同富裕的动力机制和制度保障。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助力社区治理体系重建的联动性体现在传统村级治理模式与现代社区治理体系之间的有效衔接,由此助力搬迁安置社区社会生活共同体营建,为提升后续扶持政策效能奠定良好的组织基础和社会环境。
2.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的实践逻辑
从政策目标及其非预期性后果来看,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应当有其特定的行动边界和扶持期限,政策实践中要时刻警惕后续扶持的非预期后果,以及外部扶持和自主发展的内在张力。因此,结合后续扶持行动嵌入性理论视角及其机制演化的实践特征,基于巩固易地扶贫搬迁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逻辑起点,从扶持理念、扶持资源和扶持体系等维度构建迈向共同富裕的后续扶持机制演化实践逻辑。
首先,“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后续扶持理念要多元多维转换。基于融合开放的共享发展理念,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应当从“物”的单向扶持转向“人”的全面发展,从指标化的“数字”扶持转向可持续性“赋权”与“增能”的协同推进。具体到政策实践层面,要从贫困治理逻辑转换、可持续生计能力建设及融合发展等多维综合扶持理念出发,一方面要关注就业扶持和可持续生计能力建设,培育壮大县域经济,依托大数据平台、互联网+以及微信群等新型媒介传播方式,搭建用工信息平台,培育区域劳务合作品牌,创新以工代赈、扶贫车间以及社区公益性岗位等方式,强化搬迁群众就业扶持;同时,还必须从基础设施、产业集群、营商环境、市场服务、数字治理等方面,支持迁入地县域融合以及区域协调发展,特别注重特色产业的壮大发展,支持搬迁群众自主创业。另一方面,健全巩固后续扶持成效的常态化机制,保障搬迁群众合法权益,维护搬迁群众在迁出地的集体经济成员权益,健全社区公共服务,包括保障适龄儿童就近接受义务教育,提升基本医疗保障水平等,确保搬迁群众与迁入地群众平等共享公共服务资源和改革发展成果。另外,转换后续扶持理念还不能忽视搬迁群众主体性重塑问题,强化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从动机、认知、情感以及自我概念形成等方面进行积极干预,构建心态协同下后易地扶贫搬迁时代共同富裕大格局。
其次,从搬人、搬物到赋权、增能,后续扶持资源要合理有序流动。基于后续扶持机制演化的经验阶段及其实践特征,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要强化空间联动与资源配置良性互动的意识。实践中要以迁出地和迁入地空间联动、协同扶持的现实诉求为导向,强化效能优先理念,创新资源配置模式,重构并优化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资源配置机制,真正实现搬人、搬物与赋权、增能协同推进,切实保障搬迁群众合法权益,尤其是他们在迁出地享有的诸如承包地、山林地的退耕还林、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草原生态保护、耕地地力保护等各种农业牧业补贴和生态补偿。从制度路径来看,后续扶持资源要合理有序流动,一方面,要客观把握易地扶贫搬迁全生命周期演化的应然规律,从治理空间贫困、生态贫困和资源贫困的绝对贫困,到治理能力贫困、关系贫困、权利贫困和文化贫困的相对贫困,再到融合发展与共同富裕背景下的共建共治共享,后续扶持政策瞄准与资源配置要紧紧围绕这条演化主线,精准识别后续扶持不同阶段的价值导向与目标定位,切实有效提升后续扶持政策实效和治理效能。另一方面,要从工作体制转换、政策措施衔接、组织结构联动以及制度功能耦合等方面入手,锚定社会融合和共同富裕的终极目标,构建政府、市场、社会、集体、家庭等多元协同、良性互构的政策扶持体系与资源配置机制。
最后,从可持续发展到有序退出,后续扶持政策风险要科学有效防范。整个“十四五”时期都是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的过渡期,过渡期内要确保扶持政策的连续性和扶持制度的稳健性;但是,也要防止后续扶持行动的非预期后果,尤其要高度警惕扶持资源配置和福利供给过程中的“身份化”“符号化”甚至“污名化”。过渡期扶持政策目标和制度设计必须遵循后续扶持嵌入性演化的应然规律及其经验特征,锚定后易地扶贫搬迁时代共同富裕大格局,从公共政策、产业发展、社会心理等维度完善后续扶持开放包容、融合共享的新发展格局。具体到实践层面包括: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建立健全更充分、更均衡、高质量的稳定就业体系;贯彻落实协调发展理念,综合建立新产业、新业态、新市场、新经济多维一体后续扶持的新型可持续发展体系;贯彻落实绿色发展理念,健全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治理体系;贯彻落实开放发展理念,重塑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开放融合的新型社会生活共同体;贯彻落实共享发展理念,协同推进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与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有效衔接。质言之,共同富裕背景下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的嵌入性行动和周期性演化,要求决策部门和实施机构在实践过程中务必警惕扶持行动的非预期后果,切实转变扶持理念、整合扶持资源、衔接扶持政策、优化扶持体系,确保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行动及其扶持机制强化正功能、警惕隐功能、规避负功能。
五、结论与反思
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行动的嵌入性及其动态演化,使其在扶持周期、扶持资源、扶持内容、扶持主体、扶持机制以及扶持期限等方面表现出动态性、联动性、衔接性。本研究基于后易地扶貧搬迁时代的共同富裕这一大背景,反思性借鉴新经济社会学嵌入性理论视角及其关系主义研究范式,以“扶持谁”“谁来扶”“如何扶”以及“如何退”等现实问题为导向,从扶持客体、扶持主体、扶持机制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出发,构建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机制演化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将后续扶持的演化周期划分为脆弱性治理和可持续发展两个阶段,系统阐述后续扶持嵌入性行动及其扶持机制在两个不同阶段里的实践样态和演化机理;同时,锚定后易地扶贫搬迁时代共同富裕大格局,从巩固易地扶贫搬迁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战略定位出发,围绕扶持理念、扶持资源和扶持体系等维度,构建新时期后续扶持机制演化的实践逻辑。
首先,就社会行动属性及其扶持演化机制而言,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具有新经济社会学意义上的嵌入性特征。关系主义分析范式及其辨证互构研究进路,对于科学研判和全面把握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机制演化的实践逻辑具有重要理论启示和现实借鉴。从理论意涵和实践样态来看,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的嵌入性主要表现在扶持行動结构二重性,以及扶持主体、扶持客体、扶持内容、扶持机制和扶持期限之间的辨证互构与良性运行。一言蔽之,嵌入性视角下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是政府、市场、集体、社会、家庭、搬迁群众等多元行动主体及其理性行动,与时空情境、政策环境、制度体系、利益关联及其行动规则等结构性制约之间的能动性建构。从行动边界和扶持期限来看,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行动及其政策实践必须警惕“等靠要”“扶持养懒汉”“扶持身份化”,甚至“扶持污名化”等非预期后果。换言之,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必须设定扶持期限,并且要为搬迁群众“撕标签”和“社会性断奶”提供充分的社会环境和制度保障。因此,基于后易地扶贫搬迁时代共同富裕大格局,本研究将后续扶持演化周期划分为脆弱性治理和可持续发展两个阶段,从扶持客体、扶持主体及扶持机制三个维度构建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机制演化实践逻辑的理论分析框架,采用关系主义分析范式系统阐释脆弱性治理和可持续发展两个不同阶段扶持的经验样态和实践逻辑。
其次,从扶持阶段和扶持诉求的现实经验及其演化规律来看,实践中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在脆弱性治理和可持续发展阶段呈现显著差异性。脆弱性治理阶段后续扶持的核心诉求是搬迁安置社区和搬迁群众因可持续发展能力缺失导致的脆弱性及其社会风险治理。从村庄到社区的易地搬迁,导致传统村庄组织解体、村级治理失效,城镇化集中安置与“大杂居、小聚居”居住模式,使得搬迁安置社区虽然已完成群众搬迁和人口聚居,但在地化、融合化的社群组织机制和社会网络体系仍旧缺失,社会生活共同体导向的公共性及其行为规范阙如,搬迁安置社区脆弱性显著。从市民化转型和主体性嬗变来看,搬迁群众从农耕生产方式脱离,从传统人口资源环境互动方式中易地迁移至一个陌生的社会生态体系中,人力资本缺失与生计方式转型会直接诱发搬迁群众返贫致贫和返迁回迁,搬迁群众贫困脆弱性特征十分明显。因此,脆弱性治理阶段扶持诉求直接表现为搬迁安置社区“空心化”“无主体化”“低效能化”等治理困境,以及搬迁群众返贫致贫、回迁返迁及其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风险。可持续发展阶段是在巩固提升脆弱性治理阶段实践成效基础上,进一步聚焦搬迁安置社区内生发展能力和搬迁群众可行性能力,扶持目标瞄准现代化社区治理和可持续发展两个基础能力上,完善后易地扶贫搬迁时代个体—社区—县域融合共享、共同富裕的新型发展格局,为构建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的退出机制奠定必要的组织基础和制度保障。
再次,从扶持主体结构和扶持机制演化来看,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主体和扶持机制呈现多元化和多样化,且随着后续扶持经验阶段转换,扶持主体结构及其扶持机制均呈现动态演化的实践特征。脆弱性治理阶段,政府是最主要的扶持主体,行政动员下的扶持资源配置模式在搬迁群众返贫致贫、返迁回迁以及“空心化”社区治理中具有其独特的比较优势。实践中依托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通过构筑返贫帮扶监测机制、易地扶贫搬迁高质量发展监测机制和就业动态监测机制“三张网”,沿着精准扶贫理念开展精准后续帮扶,取得了良好的扶持成效。同时,该阶段政府的主导作用还体现在搬迁安置社区治理能力不足导致的稳定风险化解,尤其是搬迁群众因利益受损和心理应激导致的群体性事件。可持续发展阶段,应当构建政府、市场、社会、集体等多元主体联动扶持、协同运作的“大扶持”行动网络。该阶段政府依旧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关键是要在营造优质市场环境、创新现代治理体系、构建融合共享发展格局等方面压实各级政府的主体责任,而非通过行政动员、行政指令直接进行扶持资源配置。可持续发展阶段更需要龙头企业、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新型职业农民等多元化带贫主体,通过构建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带动搬迁群众从单纯接受扶持到主动对接市场、提升经营能力,让搬迁群众在与带贫主体互动过程中树立竞争意识、风险意识、责任意识。同时,该阶段还要通过培育社区公共精神并强化社区主体在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上的重要作用,尤其要借助集体产权制度和“三权分置”改革,强化搬迁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为后扶持阶段融合发展和共同富裕奠定必要的制度保障。
最后,共同富裕背景下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机制演化的制度路径,应当从扶持理念、扶持资源和扶持体系等方面入手,遵循后续扶持嵌入性行动特征及其扶持机制动态演化的实践逻辑,构建政府、市场、社会、集体、搬迁群众多元协同的“大扶持”行动网络。切实转变扶持理念,从单纯扶持家户生计到社区内生发展能力和可行性能力提升,从浅层次器物与技术扶持到共同富裕背景下社会融合和全面发展的体制机制建设。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必须锚定国家宏观战略转向,结合乡村振兴和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以人的搬迁带动资源有序流动,通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公共服务机制创新、社会治理体系健全等一系列配套举措,践行协调发展、绿色发展理念,实现巩固易地扶贫搬迁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另外,赓续脱贫攻坚精神,接续推动千万易地扶贫搬迁逐步迈向共同富裕,还必须坚决贯彻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理念,从贫困村到搬迁安置社区再到“去身份化”与“撕标签”后的常态化社区,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必须构建有助于搬迁安置社区开放融合、包容共治的新型治理体系。既要加快补齐制约共同富裕的壁垒和短板,尤其是安置社区现代化基础设施壁垒和均衡化公共服务短板,还必须从共同体本位出发,重构以党组为核心、居(村)委会和居(村)监委会为基础、群团组织、社会组织、物业服务企业和志愿组织共同参与的“一核多元”共治体系。从贫困户到搬迁群众再到新市民,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要围绕助力人的全面发展这一宗旨,结合以县域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加快推动易地扶贫搬迁人口市民化进程,为构建后易地扶贫搬迁时代共同富裕大格局奠定良好的社会心理基础。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40.
[3]刘少杰.易地扶贫的空间失衡与精准施策[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6):45-50.
[4]何瑾,向德平.易地扶贫搬迁的空间生成与减贫逻辑[J].江汉论坛,2021(5):139-144.
[5]王寓凡,江立华.“后扶贫时代”农村贫困人口的市民化——易地扶贫搬迁中政企协作的空间再造[J].学术月刊,2020(12):160-166.
[6]谢治菊.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治理困境与对策建议[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1(15):112-127.
[7]张磊,伏绍宏.移民再嵌入与后扶贫时代搬迁社区治理[J].农村经济,2021(9):17-25.
[8]谢晓洁,谭政.三度空间建构视域下易地扶贫搬迁城镇化集中安置群体再社会化实证研究[J].云南社会科学,2021(6):149-154.
[9]黄祖辉,吴沁霞,祁琪.易地扶贫移民的社会融合——基于贵州省黄平县的实证分析[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46-57.
[10]董运来,王艳华.易地扶贫搬迁后续社区治理与社会融入[J].宏观经济管理,2021(9):81-86.
[11]陈宣霓,陈涛,彭凯平.构建“心态协同”下后易地扶贫搬迁时代共同富裕大格局[J].宏观经济管理,2021(10):33-39.
[12]涂圣伟.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的政策导向与战略重点[J].改革,2020(9):118-127.
[13]徐进,李小云.论脱贫的稳定性与减贫动力变化的若干问题[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6):33-42.
[14]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冯钢,刘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15.
[15]马克·格兰诺维特.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M].罗家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10-12.
[16]武汉大学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研究课题组.易地扶贫搬迁的基本特征与后续扶持的路径选择[J].中国农村经济,2020(12):88-102.
[17]渠鲲飞,左停.协同治理下的空间再造[J].中国农村观察,2019(2):134-144.
[18]贵州省生态移民局.聚焦高质量 强化硬措施 持续推动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走深走实[J].宏观经济管理,2021(9):23-26.
[19]吴新叶,牛晨光.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的紧张与化解[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118-127.
[20]郭占锋,张森,李轶星.中国扶贫移民40年:轨迹、经验与展望[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5):37-47.
[21]王晓毅,阿妮尔.从“超常规”到“常规化”:驻村帮扶如何助推乡村治理现代化[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6):62-70.
[22]许汉泽.“后扶贫时代”易地扶贫搬迁的实践困境及政策优化——以秦巴山区Y镇扶贫搬迁安置社区为例[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29-41.
[23]郑娜娜,许佳君.易地搬迁移民社区的空间再造与社会融入——基于陕西省西乡县的田野考察[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58-68.
[24]刘金龙,金萌萌.易地移民搬迁能实现“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吗?——基于陕南S县的调查[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32-43.
(责任编辑:王勤美)杨 洋,杨 波,张 娅,王勤美,蒲应秋
Popu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beddedness
TIAN Pe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Nanjing,Jiangsu,China,211108)
Abstract:
Within the 14th Five-Year Plan,high pressure remained in the aspect of the follow-up support for the relocated people of poverty alleviation,namely,their integration into local society and common prosperity. Building a reasonable follow-up support system is of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n the new journey towards common prosperity. This study divides the follow-up support evolution cycle into two stages: vulnerability governanc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and construct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the follow-up support practical logic of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from support object,support subject and support mechanism. From vulnerability governance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it presen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ynamic support objects,diversified support subjects,synergy of support mechanisms,and systematic policy paths. The practical logic of follow-up support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beddedness mainly includes multiple and multidimensional transformation of follow-up support concepts,the reasonable and orderly flow of follow-up support resources,the reasonable and effective prevention of follow-up support policy risks etc. In this way,we can ensu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location,stability,and employment,which aims at ultimate prosperity.
Key words:
reloca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population; embeddedness; follow-up support
收稿日期:2022-12-22
基金項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跨县搬迁社区治理与后期扶持研究”(21&ZD183)。
作者简介:
田 鹏,男,江苏镇江人,博士,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