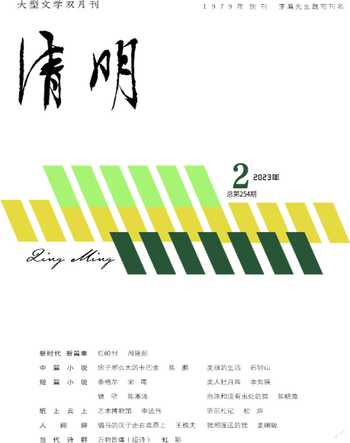把威士忌买来家里
2023-05-30孙鹏飞
孙鹏飞
我和李衣是在省里的一次笔会上认识的。那会儿我写了一些中短篇小说,发表后也没什么名气,做了几个网大电影,让人贴上了“脑子拿去涮海底捞”的标签。之后我有心投身院线电影。李衣在北京,我在青岛。笔会见面之后,我们合作了一次。他们公司过去是做唱片的,和港台艺人合作,现在改做院线电影。过气歌手想弄一部让他再火一次的青春片,用自己的成名曲作为电影名字,正四处寻找枪手。我是在李衣的朋友圈看到的。我主动联系李衣,问他最近咋样。他正受胃病困扰,拿了几服中药自己在家熬,跟我说差一点就喝死了。
那会儿正是影视行业蓬勃向上的时期,一部网大策划费能拿到五位数,我对村里人宣称是躺着挣钱的。我那会儿和女朋友在偏远的崂山租了宽敞的海景房,试过一个月不到公司,或者连续两个月下午三点到公司坐一小会儿。我没有抽烟的习惯,但是开会一定要夹一支烟,静待实习生探身过来毕恭毕敬地点上火。来找我们投电影的不乏是来洗钱的。洗钱也都得托关系。膀粗腰圆、成群结队的阔佬看不到剧本和演员,钞票先盲投进来,最后打了水漂是常有的事。
和李衣聊了会儿有的没的,谈到了正事。歌手要一个双性恋的故事,我问李衣敢不敢和我一起试试,李衣说,值得一试。
李衣之所以这么爽快地答应,我猜吸引他的是题材。他把剧本当成艺术了,偏偏我们需要的是商品。他们导演逼他改过二十遍稿子,跟他拍了桌子,他也跟导演拍了桌子。他在公司的处境并不乐观。
我问他最近读些什么书,他说了一堆小众名字,有一本是艾米·亨佩尔的英文原版小说集。他想写个五六万字的中篇,预祝自己三十岁生日快乐。我直言,这个长度可不好发表。他说,不为发表,试试超越自己。
我和李衣给歌手写的剧本没收到全款,歌手躲起来了。半年后我被人赶出了影视公司,而李衣也从北京回到青岛,在西海岸的天目山路租了间房。我常常找他喝酒,后来我俩合租。
又隔了半年,五官酷似周传雄的马洛老师加入了我们。马洛是我的学长,这次是系主任撮合的会见。马洛弄起了自己的工作室,他是带着项目来的:海内外知名的第六代导演海选剧本,讲一群迷茫的都市青年流浪到夏威夷结婚的事。我们凑在一起,连夜攒出了大纲,马老师把稍显美中不足的故事发给他的工作室,之后我们苦等消息。两周后姓周的制片人和马老师联系,说创意还行,值得一试。然后没了下文。
再有动静是入冬之后,制片人表示愿意买我们的剧本。制片人在电话里邀请编剧过去跟组,打磨剧本余下的部分,但是经费有限,只能请一个编剧。
我们仨谁去呢?
马老师在镜子前刷了牙,以往他只在创作的时候刷牙。他敲字会不由自主地舔牙齿,舔得整排门牙又细又长。
马老师说,活儿是我联系的,我应该去。
我坐在马桶上看着他。
他收拾房间时,把两条新床单留给了我。
之后我和李衣坐吃山空。我们讲究,抽包烟,不低于五十。我有辆大奔,酒醒后我就带着李衣再去喝酒,次次喝到凌晨。西海岸这边近两年才开发,路上人少车少,监控也少。我们常常是醒来就不记得前一晚怎么回的家。然后我的车子也撞毁了。
我女朋友找了新的男朋友。知道她找男朋友的那晚,我酒后返回住处,把车子停在路中间,第一次觉得這世界上存在的一切都是彻头彻尾的骗局。李衣跟我谈了会儿未来,他认为还是要老老实实做剧本、写小说,至于能不能卖钱,我们能不能红,不归我们掌控。天亮之后就是未来了,黑暗全部消失,阳光强劲灿烂。
下了几场雪,屋子里只有一个暖风机。把威士忌买来家里,兑着冰红茶喝最舒服。我一喝酒就喝到大醉,酒醒后我穿着睡衣仰躺在沙发上,捧着平板反复看一些近来卖座的古装剧。老实说我那点钱挥霍得差不多了。打电话问我妈要钱,我妈转了一千元过来。我把钱原封不动转给房东之后,决定去办张信用卡。
没事做的时候,我和李衣常常玩一个游戏,有点像田忌赛马。我们一人说一个导演,然后比较他们在圈子里的分量。我说杜琪峰,李衣说张艺谋。我说许鞍华,李衣说陈凯歌。最后一组是王家卫和贾樟柯。就这三组在海内的影响力来说,我都输了。
我当时被公司赶出来,是因为抄袭。我抄了导演的构思,拿出来当小说发表了。因为导演的构思非常脑残,而涉及的几个人物又是我提供的,本来可以做成大碗面,结果弄成了袋装方便面。我不甘心,却也没有实权,只好权宜改成小说。
我和李衣每天都投简历,但网大、短视频文化一类的公司也都在裁人,他们自己人写的东西都用不完,不想和我们无名小辈合作。倒是有公司愿意对李衣网开一面,李衣的作品拿过一些行业奖,他们尊重李衣。但是对于上了黑名单的我,他们极力拒绝。
平安夜那天,马老师回来了。他说,周制片把剧本买了,戏杀青就打钱。马老师的黑眼圈比过去重,他跟组两个月没睡过一天好觉。这次来是因为他的工作室接到一部偶像剧,有个年过四十却有着演员梦的女人,愿意拿六千万出来,做二十集网剧。马老师请我们去烤鱼店吃了一条四斤重的烤鱼,然后我们回去攒大纲。
马老师说,遇到行业寒冬,没几天好混了,咱们要么不做,要做就做点业绩出来。李衣说,你一张嘴全是废话。马老师说,咱们写点不同的,反类型的偶像剧,咋样?我不想冒风险,毕竟做剧本不需要讲文学性。李衣觉得有挑战性,值得一试。
李衣写男一线,马老师写男二,我写男三。各自分工,便动手创作。第一稿被中年女人退了回来,她要的是甜甜的女主,打不死的杉菜那一类的。她建议我们看完两版《流星花园》再说。到了第二稿,剧情损伤大半,只剩下一些徒有其表的套路。中年女人说,男女主在一起太快了,要拆散到最后一集。
第三稿的人设、故事走向定好位,又发现了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我们无法往里面填充更多细节。马老师和李衣都是钢铁电线杆直男,没接触过所谓的女朋友。
不知不觉马老师的胡子又冒出一大截,整个下巴像他的羽绒服那般乌黑。他说,我们需要恶补偶像剧。他推荐了海量的日剧、韩剧、美剧、英剧,还从网上订了成吨的青春小说。
我负责看小说,把其中用得着的桥段标注出来。李衣负责开二倍速看剧。但是下午光线好的时间李衣都用来看书。我推门喊李衣吃饭,十次有九次见他在看书,另一次是见他写小说。我说他自私,大家一块做事情,不能只顾自己。李衣实在不想看这些同智商作斗争的后现代剧,只好改成他看书,我看剧。
起初我只是把偶像剧当成偶像剧,看着看着有几集也开始跟着男女主的情绪走,尤其是日剧《外貌协会百分百》的最后一集。男主同时交往很多个女友,但是每一个女友他都一样宠爱。他和女主说,我爱你,也爱她,你受不了,就分手吧。女主同他分手,带着失去爱情后的形体回到正轨。我松了口气。可是紧接着寂寞排山倒海而来,明明两个人在一起很开心,为什么要一个人孤独?最终女主找到男主,继续着这份共享的爱情。看来爱情是罂粟。
韩剧《今生是第一次》也让我颇感震撼。年轻人住不起房子,假结婚,为的是和自己的另一半平摊房租。一个严肃的主题,竟然用轻喜剧的方式呈现了出来。爱情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少部分人的奢侈品,穷人只是金钱的奴隶。
李衣和馬老师睡主卧,我睡次卧。马老师不怎么回房间睡觉,他半坐半躺在客厅沙发上,人裹在被子里,累了就眯会儿,醒着的时候就敲字,能由晚上八九点写到凌晨四五点钟。他写这种低龄的东西,写着写着能自己笑出声。他语重心长地说,越早混出名堂越好。
记得我们系主任曾说,宁浩还找过马老师谈合作。
马老师的头发、脸皮都油乎乎的,他常年不洗头不洗澡就把棉帽子扣在脑门上。他的羽绒服脏兮兮的,油污让面料变得漆黑反光。他终日套着它,在玻璃窗外飘着雪花的凌晨和傍晚晃悠。我听见他在阳台和周制片套话,钱已经打过来了,他说准备分给我们。
我们一夜未睡,凌晨五点我们仨并肩横行在大马路上。马老师说,你俩只要好好跟着我干,保证钞票大把大把地来。他背着个书包,里面装着三万元。他说要我们感受一下人民币的分量。我提溜了会儿,轻飘飘的。其实对方打来五万元,他只分给我们一人一万元。
马老师问我们,吃过的最贵的一盘菜多少钱。李衣说,在北京那会儿,住在通州,但是顿顿都要到三里屯吃。
我记得我们给歌手写剧本的初期,我和李衣吃炸酱面,从北京的六环一直吃到王府井。
一提起昔日辉煌我就保持着理性,我们都还年轻,还会再富起来的。大前年我一年挣了十六万元,半年不到都花出去了。这笔钱要是还在就好了。上帝总是用周期性洪水或其他灾难的出现,使人类复归文明的开端。
之后我们谈论着这边房租这么贵,和住在乡下也没有多少区别呀,多么不值当。李衣也想离开这里。李衣说,分到这笔钱我想撤了。同时他劝我俩做点别的。
马老师说,偶像剧怎么办?
李衣想了想说,你俩来吧。
我跟李衣说了五万元的事,李衣倒是对钱没有过多想法。之后我问马老师能不能再分点,毕竟累死累活呕心沥血。马老师说一共就给了两万八千元。他脸蛋红扑扑的,狡黠的眼神让我想起小学课本里的狐狸与乌鸦。他说快过年了,要是骗我们立马让车轧死。说到这里他话锋一转,说我是让上一个公司赶出来的,诚信绝对有问题。他叫李衣不要再相信我,有什么点子千万不要和我说,因为我会抄。我一脸尴尬地在他俩中间插科打诨,马老师说,你没必要笑,真的。
马老师去北京了。
李衣回淄博老家写小说去了。从前那边有个蒲松龄,也挺能写的。
我以前一个哥们儿,是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的,一直叫我过去。但我投奔他有点晚,他已经转行卖玩具了。快过春节那几天,系主任联系我,说是去内蒙古拍片,春节期间的报酬尤其丰厚。我应承下来。
我联系李衣,他的钱也用完了。他问我为什么不留在家里过年,我说以前不懂什么叫离别,而今故乡于我,只有冬夏再无春秋。要是再过几年,或许家乡都要丢掉了。
我俩约定在济南见面。已到年底,城市张灯结彩,处处是节日气息。村镇更不必说,就是天空中也显出新年将至的气象来。到了河北张北县正是除夕夜,剧组派人来火车站接我们。路过乡镇上的小卖部,我买了很多饼干,背包鼓鼓囊囊都塞满了。后面几天,盒饭供应不及时,我就和李衣吃饼干度日。不跟组时,李衣就在蒙古包里写小说。
导演住在我们旁边,他来看我们。他两手握了握李衣的手,然后又握我的手。他的手又厚又暖,像是铁匠的手。他说,你俩看下大纲,给女一再加点戏。
李衣说,你们自己觉得这戏反胃吗?
李衣环顾着他们。
半夜里李衣突然坐起来说,他不想做了。我极力劝说他。毕竟他几句话就能让笔下的人物立起来,我没有这个本事。而且这次的钱也好挣,套的是成龙《十二生肖》的壳子,找到国宝,然后上交,然后我们就能拿到钱。这次错过了,下次这种好事可说不准哪年哪月。
这次的执行导演是青岛请来的,和我曾是同事。他比我大十五岁,大家都喊他龙哥。他参加一个电影展,要求剧本是原创,不能改编自小说啥的。他的电影还没拍完,我就把同名小说发表了。就是因为这个我被赶出了公司。
天微亮他们往车上搬道具,李衣也帮着他们搬。我抄着手在旁边溜达,呼出一长串白气。龙哥大声嚷嚷,好让整个剧组都听见。他说,看看那位编剧干活什么态度,你们再看看这位,艺术家,战地记者,公子哥。
我笑说,你吵啥,你是来遛弯的?
从背后上来个场务推了我一把。
这次的场务是龙哥从青岛找来的,和龙哥一条心,传言这出戏忙完了,他会收拾我。这话传了几天,再到我耳朵里,就成了要让我变成二等残废。
连着几天刮大风,导演一直坐在显示屏前面搓脸,我溜达来溜达去混日子。龙哥权力很大,一有时间就骂人。群演不够,导演叫场务通知我们几个幕后人员参演。我们站成一排,龙哥教我们呐喊。我呐喊力度不够,他让场务单独训教我。我和场务独处,老实了很多,等到上镜,嗓子都喊劈了。
龙哥奚落我,为这部戏贡献了可圈可点的演技。
李衣忙里偷闲,把五万多字的中篇写完了。他说自己对于文字的锤炼已经炉火纯青,他将是下一个冯内古特。我不知道冯内古特是谁,他说我从小让港台文化侵蚀,像是活在偶像剧里,没什么脑子。
我是吃港台文化长大的,但是港台文化可不是一无是处。我俩比较着改革开放后内地和港台的电影,我说了几部港片,他斥为糖水。糖水最受大众欢迎,但是好电影应该是醇酒。
不久,男一号吊威亚出了事故,之后整个剧组放大假。我们从外面弄了些红薯,撒上白糖在炭火堆里烤。其间副导演喊我们过去,说是改戏。我一个人去的,回来后红薯都吃完了。
红薯是外面捡来的,估计被老鼠啃过。在这之前,我还犹豫要不要吃。
我问李衣,红薯有什么不对吗?
他说,你觉得这个世界有什么不对吗?
我说,你别执迷不悟了,艺术是茶余饭后的催眠。改变世界的还是商业,还是一件件商品。
他咂咂嘴說,在宇宙中,你总可以将一个事件解释为由另一个更早的事件引起的。但是只有当宇宙存在某个开端时,才能用这种方法解释它本身的存在。任何理论都是临时性的,你永远不可能证明它。不管多少次实验的结果和理论相一致,你永远不可能断定下一次的结果不和它矛盾。
他一说话,我感觉脑袋都大了一圈。
隔天李衣没起来,我自己去领的盒饭。我回来后他说他发烧了。这边离医院远,他睡了一天,吃晚饭依然没精打采。盒饭远途运来,到我们手里早放凉了。菜肴都油腻腻的,吃起来像是草根、肉冻。一盒饭没吃完,他吐了起来。
他嘴角挂着唾沫丝说,最近太累了,胃病又犯了。
女演员来要烟,我们聊了会儿。她是李衣的老乡,住在我们前面,入夜我们都能听到她叫床。她说,来这里快两个月了,是个人都有正常的生理需要。我说,我也有。我很含蓄地表达了自己乐于助人的想法。
她笑着问我李衣咋了,我说发烧。她建议我们去趟医院。我说,李衣体质差,一年到头都这样。
最后我还是找到导演请假,说是带李衣看病。导演对于戏的结尾很不满意,自己动手改了几稿,仍不满意。他说,已经从外面另请了编剧,你们忙自己的事情吧。这话是说给我听的,说完又叫副导演安排好我和李衣,之后权力下放到龙哥手里。
天微亮,看得见点点星光,龙哥弄来辆货车,我们披着军大衣挤在冻白菜堆里。路上下雪,车子慢行,我和李衣又玩起了田忌赛马的游戏。我说了三个导演,张艺谋、陈凯歌、贾樟柯。就在我以为他会说徐克、林岭东、吴宇森,并且稳操胜券时,他说的是李安、侯孝贤、杨德昌。
我不服气,不管怎么说,都是商业影响着艺术。
李衣说,不管你往哪个方向看,远处的星系都正急速地飞离我们而去。
到了医疗室,李衣去问医生要退烧片。这边诊所太偏了,年后没什么人,就一个医生值班。龙哥跟我聊起来,他流着清鼻涕,说他也半年多没戏可拍,都是我害的。我给他讲我喜欢的名导的故事安慰他。杜琪峰当年都交不上房租了,一样不忘初心,坚守本我,终成大导。我劝他别再吃垃圾食品,年纪不小了,做一顿正餐请观众吃。
李衣服用了退烧片,我和他离开了剧组。
到了张北县,搭上动车赶往青岛。我怀疑李衣烧迷糊了,他似乎不喜欢吃动车上的饭菜。我说,怎么了,不好吃吗?他说,不是不好吃,怎么说呢,就是我感觉不太好吃。路上他又吐了,吐得座位和走道都是。窗外飘着雪花,旅客上上下下。到了青岛,我们叫了出租车回西海岸。
一路上都是红色的鞭炮碎屑。
我和李衣谈论了会儿过去都喜欢的几部故事片,李翰祥和麦当雄拍的为佳。我说,麦当雄弄的几个片子,制作水准一点不输好莱坞,但是叫好不叫座。李衣说,艺术滋养着商业,全世界都一样。
我说,一会儿买点威士忌,咱们回家喝。
再去诊所拿退烧药时,医生给李衣号脉。医生站起来说,你们抓紧去大医院,别耽误了。
之后我和李衣来到市医院。临近中午吃饭的点,到处排长队。交体检单时,医生以为打印机没墨了,让李衣再测一下血小板数值。李衣嘴唇破了,还是时不时咬着嘴唇。第二次测出的数据惊到我们了,每隔半小时,李衣的血小板往下掉一个数。医生给李衣输了液,为了保存体力,要他躺好,一动不许动。
我问医生到底怎么了,医生说,出血热。
我百度了下,出血热是由布尼亚病毒科引起的自然疫源性疾病。临床症状为发热、出血、休克和肾损害。我想起,可能跟老鼠啃过的红薯有关。问医生,医生也说鼠类是主要传染源。但是李衣的情况尤其糟糕。医生脸色煞白地问我们怎么不在内蒙古医治,我说那边医疗条件差。医生说,你错了,那边是高发区,治疗出血热经验丰富。咱们这个医院,倒是头一次见这种病。
黄昏时分,我们联系了李衣的家长。
李衣下葬那天我没去,到了晚上,我把李衣所有的东西捆成一团,等着来个什么人给他带走。买来的威士忌一直没来得及喝,我倒了杯酒站在阳台上,看着楼底下风尘仆仆的赶路人,一小口一小口地抿着。这之后我觉得一切都有点陌生。太年轻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有什么事情将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或者发生在别人身上。长大了才知道,这不叫悲剧,这是人间的正剧。天黑下来后,绵密的星系渐渐崭露头角,我想到了那句话,不管你往哪个方向看,远处的星系都正急速地飞离我们而去。
一年后,李衣的小说集出版了,一本精装书拿在手里沉甸甸的,我放在书橱最显眼的地方,每次看到,都会浮现李衣的身影。
责任编辑 刘鹏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