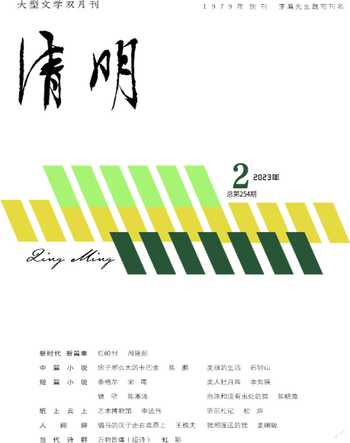镜听
2023-05-30陈湘涛
陈湘涛
鞭炮噼噼啪啪地响着,文楚贻仿佛蹚过了地雷阵。
彩珠筒都是冲着天上打的,小蜜蜂等花炮也只是在原地打转,唯有二踢脚和蹿天猴,一个声音粗野,像是埋伏在前方的劫匪,一个行动诡异,如同长途奔袭而来的流寇,让文楚贻时时提防,以致步履蹒跚。
走过了洋井,鞭炮声渐渐稀少。这是基建连的西北角,也是最早的居民点,如今早已破败不堪,只有两排房子毫无生气地躺在那里,默默倾听着远处的炮声。
老队长家就在第二排房子的第二家。掀起厚重的棉布门帘,推开木门,酒味扑面而来。
老队长李先辉坐在炉子跟前,一边烤着洋芋,一边喝着酒。
火炉连同火墙是连队人家的中央空调。铁炉形似水塔,两头粗中间细。下面四四方方,装着一个盛炉灰的方形抽屉。中间部分细长如同小蛮腰,里面担着炉条。炉条下部开有方形孔,火钩通灰、架鼓风机都要用到这个小口。上面是圆形炉灶,平时放着一圈套一圈的炉盘,烧水做饭时根据锅的大小,用火钩从中间依次取下合适的炉盘。烤馍馍片用全副炉盘,烧开水取中间两个炉盘,炒菜用铁锅取三个炉盘,蒸馒头用大铁锅需要取出全部的炉盘,只有这样才能最高效地利用火力。烤洋芋、烤红薯最简单,直接撂到盛炉灰的抽屉里,过十几分钟就可以取出来吃了。
李先辉家的铁炉平常,只是他烤洋芋的方法奇特——直接把带皮的洋芋放在炉盘上,一边烤一边翻身。见到文楚贻,他仰起头,让山羊胡子高高翘起来,漫不经心地问,吃了没?文楚贻注意到他根本没有用眼睛看自己,仿佛在跟铁炉上方的顶棚说话。
我爸不行了!文楚贻说。
李先辉仿佛没听到,自言自语地说,以前放炉灰里烤洋芋,是挺香,但四周烤面了,洋芋心却不面。等洋芋心面了,四周又烤干了。我今天换一种烤法试试。
我爸快不行了!文楚贻又说。
你在老家还有哥哥姐姐,有人埋就行。
文楚贻说,我想回老家。
李先辉嬉皮笑脸说,回呗,我批准了。
没跟你开玩笑。我算了一下,来回要花一千块路费。如果人活着,这一千块还不如直接寄给他,比人回去更管用。
我也没钱借给你。
我想让你告诉我,我爸还能活多久。
你爸能活多久,去问老家的人啊。
邮局初五才上班,我发不了电报,也收不到老家的电报。这几天我的左眼皮老跳……文楚贻一边说,一边哽咽着。
我自己什么时候死都不知道,怎么知道你爸能活多久?
我不管,你有文化,看书多,一定有办法。
你赖上我了?李先辉瞪着眼睛。
就赖上你了。前年夏天,我在打土块,你拍过我屁股,别以为我什么都忘记了。
你撅着个“沟子”,我以为是黄麻子呢。
我不管,拍了我屁股就是流氓。现在我不是要翻旧账,就是要你帮帮我。都说你是百事通,知天文晓地理,你给我指条路吧。
李先辉说,我自己都不信这个,骗你我不是人。
文楚贻咬着下嘴唇,迟疑了一会儿,突然跪到地上。李先辉“哎呀”一声,伸手去拉,不知有意还是无意碰到文楚贻的胸部,又忙把手缩回去。
我以前在书上看到过一个方子,准不准不知道。你等着,我去找本书。李先辉说。
他慢吞吞地从里屋床下拖出一只木头书箱,再从五斗橱里翻到老花镜,又颤抖着手,从书箱底部找出一本泛黄的线装书,翻到了其中一页,指给文楚贻看。书上写的是繁体字,文楚贻勉强能辨认出来:元旦之夕,洒扫置香灯于灶门,注水满铛,置勺于水,虔礼拜祝。拨勺使旋,随柄所指之方,抱镜出门,密听人言……她将书还给李先辉,瞪大眼睛看着他。李先辉解释说,这种方法,古人称之为“镜听”,也叫“听镜”“听响卜”,就是在除夕或岁首的夜里,抱着镜子偷听路人的无意之言,以此来占卜吉凶祸福。具体方法是将勺子放入盛满水的锅中——文中说的铛就是古人用的锅,跪拜许愿后拨勺旋转,然后按勺柄所指方向抱着一面镜子出门偷听,比如你听人在打麻将,有人说和了,那取谐音就是活了,说明你爸能活。
文楚贻眼睛一亮,说那你快帮我弄。
李先辉说,我家锅碗瓢盆都有,就是没镜子,我好几年都没照过镜子了。
文楚贻说,你等着。说完就急匆匆地往家赶。
李先辉望着她的背影,苦笑着摇摇头。
到了家门口,文楚贻听到炭池子里有声音。她大声喊了一声谁,却没人答应。她心怀忐忑地打手电照进去,看见老二祥云正在里面叮叮咚咚地敲煤。
祥云是个半聋子,只能听得到凑到他耳边说的话。
家里平时做饭取暖都用碎煤,碎煤中常常夹杂着泥土,火烧不旺。晚上盖着被子睡觉,不需要太高的室內温度,用碎煤仍有些奢侈,于是家家户户都会用细碎的煤渣“压炉子”,让炉火在燃与灭的临界点寂静地氧化,缓慢地释放出少许热量。过年时,文楚贻天天洗床单洗被套洗衣服,黄文楚天天炒瓜子炒花生炸萝卜丸子,都需要利火,就要用大块的煤了。
大块的煤都堆在炭池子深处,需要一手拎着榔头,一手提着煤桶,弓腰钻进炭池子深处,将里面乌黑发亮的大块煤砸成能够塞进煤桶的小块煤。烧这种煤块,铁炉最“利”。如果再配上鼓风机,还能够听到噼里啪啦的燃烧声。家里的煤用完了,三兄弟谁碰上谁去装,可是到了年三十晚上,老大祥雷晚饭都没吃就不知去向了,老三祥雨也在饭后跟着几个同龄的孩子串门去了,只有孤僻的祥云留在家里干一些杂活。文楚贻给祥云照着亮,看着他叮叮咚咚砸了一通,然后满面尘灰地从炭池子里钻出来,心里替他鸣不平——一个家就是个小连队,总有人会吃老实亏。
跟着祥云进了家,文楚贻看见黄文楚一边看电视,一边包着饺子。电视机里,一个来自台湾的歌手正在春节联欢晚会上唱歌:归来吧,归来哟,浪迹天涯的游子……文楚贻正想找个机会跟黄文楚吵架,就毫无征兆地关了电视。黄文楚看了她一眼,继续包饺子。文楚贻看祥云正在炉子旁敲煤,就用祥云察觉不到的音量跟黄文楚吵起来。
什么时候去办手续?
黄文楚包着饺子,一声不吭。
你放个屁行不行?
黄文楚放下手里的饺子皮,还是一声不吭。
文楚贻抓起面板上的饺子皮,用力揉成一团,像是打砖坯一样重重地拍在面板上。她从写字台上拿了镜子,匆匆往外走,突然看见祥云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黄文楚的身旁,一副惶恐的神情。
文楚贻忍着不哭,可走出家门终于落了泪。她心疼祥云,每次他们吵架,无辜的祥云总认为战争的根源是自己,常躲在一边偷偷淌眼泪。她也心疼黄文楚,无论受多大的委屈,总是一副天高云淡的样子,任由她撒泼。可是她又有什么办法?这样的男人,不逼着他去借钱,怎么能凑够这一千块钱呢!
她借着窗户透出的灯光,对着镜子龇了龇牙,看到一副狰狞的面目。和连队里其他妇女不一样,她凶过之后总爱自责,总要想办法去弥补。看来,有自省能力也不见得是好事。
折回李先辉家的路上,她东张西望,盼着能遇到祥雷和祥雨。小小的连队,四十多排房子,藏不住两个半大小子。只要他们跑出来玩,大概率会遇上。文楚贻想好了训他们的狠话,要训得他们抬不起头,乖乖地回家去和祥云玩。
果然,在俱乐部跟前,她看到了祥雨。祥雨夹在一群半大孩子中,麻雀一样群飞群落。看到文楚贻,祥雨兴奋地跑了过来。还没等文楚贻发火,祥雨就递过来一颗剥好的大白兔奶糖,蹦着跳着塞进了文楚贻的嘴里。
文楚贻含着糖,咬字不清地喝问,你在干什么?
祥雨兴奋地说,我们在等着换糖呢。
原来他们挨家挨户地串门拜年,转上一圈,棉衣棉裤的口袋里就塞满了牛奶糖、花生糖、水果糖、话梅糖、薄荷糖、高粱饴……糖果一多,交易就产生了。每种糖果都有身价和行情。最好的当然是大白兔奶糖,一颗可以换三颗普通奶糖。石河子产的高粱饴也是好糖,最少能换五颗水果糖。
一颗糖软化了一切,文楚贻也没有了骂人的心情,叮嘱说,早点回去吧,帮着家里干点活。
我今天才倒过污水桶。祥雨邀功说。
你爸在包饺子,你去帮他擀饺子皮。要是家里没啥活了,你也跟祥云一起玩一会儿。
祥雨嘴上答应着,可是转头又冲进换糖的队伍中去了。
李先辉酒已经喝好了,洋芋也吃美了,正坐在火炉旁打盹儿。看到文楚贻进来,他慢腾腾地用火钩钩下三个炉盘,又慢腾腾地将铁锅放到灶膛上,接着从碗柜里取出一个大海碗倒扣在锅里。他又取出一个白瓷调羹,放到海碗底上,一个简易的“司南”就制作好了。文楚贻见调羹和海碗上油光光的,就麻利地取出来,用清水洗净了,然后又毕恭毕敬地放入锅中。
李先辉用食指拨动调羹柄,文楚贻紧张地闭紧了双眼。调羹划动着锅里漫上来的水,哗的一声,停住了。文楚贻睁开眼,看见调羹柄指向西面。李先辉用干枯的手指指了指西面,说这是去小渠道的方向。文楚贻点了点头,又问镜子要怎么装。李先辉说,揣怀里就行。
文楚贻走在去小渠道的路上,想起刚才李先辉直愣愣地看着自己解开棉衣揣镜子的神情,觉得好笑。这个老头连动手的力气都没有了,现在只剩一双眼睛了。
在连队里,听墙根儿最好的位置就是后窗。连队的住房设计过于简单,后窗下就是卧室床铺,一些无聊的光棍汉,晚上就喜欢在人家后窗溜达,即使被人看见也无妨,谁还不能走个夜路了?
虽然是瓷勺指路,但文楚贻还是有具体目标的,那就是李四宝家。
李四宝是连队的二流子,天天在家里摆桌子打麻将,将小渠道东西两边的闲散青年都吸纳了过去。文楚贻记得李先辉提示的那句“和了”,打麻将总有人和牌,听到“和了”就等同于“活了”。
李四宝家的后窗竟然没有钉塑料布,果然如人所说——恶人火气壮。刚走到窗下,文楚贻就听见李四宝正在训骂另外一个人。
快死去!
文楚贻心里默默地说,刚才那句没听清,后面听到的才算。
对方默不作声。
你少给老子来这一套。
对方仍然不吭声。
现在就滚。
接着叮叮咚咚几声,李四宝往地上扔东西,或者用东西砸对方。
文楚贻正要转身离开,隐隐约约听到李四宝说到了黄雷子,具体说了什么没听清楚。在连队里,祥雷的绰号就是黄雷子。这个绰号部分继承自黄文楚,因为黄文楚绰号黄麻子,祥雷就被人叫作黄雷子。
文楚贻从后窗绕到前门,发了疯一样拍打着李四宝的房门。门自然是从里面顶着的,过了好一会儿才打开。文楚贻压住火,说我来找祥雷。李四宝冷冷地说,他不在。文楚贻推开李四宝就往里面闯,李四宝跟在身后也不说话。客厅里摆了两桌麻将,因为听到敲门声,桌上的钱都收起来了。这些人一看是文楚贻,纷纷把怀里的钱掏回到桌面上。
文楚贻又进了里屋,看见一个小伙子直挺挺地跪在地上,脸颊红肿,神情悲壮——这张脸很陌生,不像是周边连队的。
见挨打的不是祥雷,文楚贻松了口气,板着脸说,你告诉我祥雷在哪儿?
连队里的混混虽然好勇斗狠,但对长辈都挺有礼貌的。李四宝客气地叫了声阿姨,说我好几天都没见到祥雷了。
文楚贻因为刚才拍门用力过大,推人闯入过猛,现在不好轻飘飘地就走,只能再纠缠一会儿。她说,我听人说,他经常来这里。
听到这话,李四宝的耐心消磨殆尽,不客气地说,我正想找他呢。不瞒你说,上个月黄雷子打牌输了钱,在我家跪了半个晚上,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我看他可怜,又是从小一起玩到大的,就给了他一百四。他得了便宜不卖乖,还到处宣扬,现在全团玩牌的人都学会了,输了钱就去跪,玩苦肉计,以后谁还能赢钱?
文楚贻气得浑身颤抖,问祥雷输了多少钱。李四宝知道说漏了嘴,支支吾吾说没输多少,都还给他了。祥雷后面也没再来玩了。
文楚贻知道祥雷有时跟李四宝混在一起,又抽烟又喝酒,但因为他已经十七岁了,到了这个岁数的子女,連队里都不怎么管了,她也只好装聋作哑。现在祥雷干了这样丢人的事,带坏赌风这事她可以不计较,但他赌博的钱是从哪里来的?能跪一晚上要回一百多,输掉的不知道有多少。在连队,这么大的孩子突然有了钱,那只有一种途径——肯定是去偷了。
出了李四宝家,文楚贻告诉自己要冷静,先把老家的事情搞清楚再说。
左眼皮突然又开始跳了,一下催着一下,催得她心脏也打起了鼓。她仿佛看见父亲正躺在早已准备好的棺材里,面色发白,手脚冰冷——这副楠木棺材是前年春节她带祥雨回老家时和哥哥姐姐一起凑钱买的。
她从小到大不知道看过多少场葬礼。并不是她喜欢看,而是送葬时鞭炮不停地炸响,让村里每个人都不能置身事外。
老家的葬礼有几个重要的环节:先是“赶龙”,一路人浩浩荡荡,穿麻挂白,锣鼓喧天地去村东头的菩萨庙祭神,让死者的灵魂进入庙里,不致成为孤魂野鬼。“赶龙”回来之后还要“走九洲”。专门请来的师傅用石灰在坪上画好“九洲”,亲属抬着棺材走完画在地上的纵横交错的“九洲”,师傅会拿来扫帚与一壶水,边洒边扫,名曰“扫井”。之后兵分两路,这边吊唁还礼,那边送葬,全过程都得放鞭炮。
如果父亲真的走了,送葬时家中的儿女不全,会成为全家人的耻辱。可是回去又谈何容易?现在连队的效益不好,五年才能有一次探亲假。
进了李先辉家,文楚贻看见李先辉正坐在火炉边炒瓜子,一把锅铲上下翻飞,锅里焦香四溢。
你听见了什么?李先辉问。
你刚才教的方法不对。
怎么不对?
我现在说不好,你把那书找出来再读一遍给我听。
李先辉指了指里屋,说你自己翻去。
里屋只点了盏十五瓦的灯泡,昏黄暗淡。一张单人床,一张写字台,写字台上堆满了书。文楚贻闻到一股酸臭味,那是鞋垫在火墙上烤的味道。
这个懒鬼,过年也没有打扫过房屋。文楚贻暗暗许愿,如果这次真的听到好消息,如果老家那边应验无误,一定过来帮李先辉把床单被套都洗一遍。
文楚贻翻出那本泛黄的书,低头看了一会儿,说刚才没有洒扫,也没有置香灯于灶门,难怪听得不准。
李先辉苦笑了一下,说我今天扫过地了,家里也有马灯,只是没香。
文楚贻说,洒扫必须我亲自来,这样才灵验,再说你也扫不干净。你等着,我回家去取香。
她一路小跑回家,看见祥云已经睡了,安静得像个女孩子一样。黄文楚正在点钱,桌上放了一堆大大小小的票子。看见文楚贻,他说过年期间不好借钱,人家嫌不吉利,我先把班上的公款凑给你,等开了工,我再借钱填上,你别去借钱了。黄文楚是连队里的记分员,也兼管出纳,能接触公家的钱。他以为文楚贻是四处借钱去了。文楚贻眼睛湿润地说,我现在没想着借钱,只想知道我爸的死活。你先别管我,现在去把祥雷找到,别让他干混蛋事。
没等黄文楚追问干什么混蛋事,文楚贻就急匆匆地跑出了家门。
到了李先辉家,文楚贻先扫地后洒水,又在火炉旁点了香放了灯。李先辉家没有香炉,就找了一个碗,装了半碗炉灰,当作香炉。马灯也没处挂,就放在一个板凳上。她还在里屋火墙的缝隙里插了几支香,想冲淡李先辉鞋垫袜子的臭味。
这次是文楚贻亲自转的白瓷调羹,调羹柄指向了南面。
文楚贻问,如果打牌的人一直不说和牌,怎么办?
李先辉说,你听见谁家说“火”这个字也可以,火与活同音。谁家喊小孩用火钩通火,让你听到了也算。
基建连的南面是一大片杨树林。杨树林那端就是水电连了。文楚贻忐忑地走过洋井,向着不远处密集的灯光走去,一边走一边想着老家的父亲。父亲有文化,在乡里是赤脚医生,擅长治肝病。家中的四个子女,虽然都没有上高中,但在父亲的调教下,个个都懂事。可自己到了团场,照着父亲的方法去管教孩子,祥雷卻成了教育的失败品。在团场几乎有一条铁律——上梁不正下梁歪,不知道祥云祥雨以后会怎样。
正胡思乱想着,突然听到水塔后面有人窃窃私语。走近一听,竟然是祥雷。文楚贻正要尖着嗓子叫喊,又听到一个女孩子的声音,带着哭腔说,你要逼死我吗?
文楚贻顾不上判断这句话是凶是吉,只想听听是哪个姑娘。
祥雷说,我为了你命都可以不要,可你总看不起我。
那女孩说,是我爸妈看不上你,你说着说着又说到我头上了。
文楚贻听出这是顾老鸭的二丫头,和祥雷是初中同学。祥雷初中毕业后没有考上高中,只上了职高。这个丫头比祥雷有出息,上了高中,只是没有考上大学,进了省城一家培训学校学理发。说起来也可笑,她去省城一两个月,回来过年就进不了连队的旱厕了。一个大姑娘家,竟然跑进树林里方便。本来行踪挺隐蔽,但去的次数多了,终于让人撞见,成了全连妇女的谈资。这个姑娘长得挺秀气,见人也有礼貌,不知道什么时候跟祥雷谈起了恋爱。
祥雷说,你爸妈势利眼,现在什么年代了,还不让自由恋爱?
顾家二丫头说,我家不反对自由恋爱,但只能和上海人谈。
祥雷说,屁,我老家还是湖南湘潭的呢。
文楚贻心里骂道,这小子为了压上海人一头,故意把老家说错。他们的老家在湖南耒阳,离湘潭还远着呢。
顾家二丫头说,你懂个屁。
祥雷说,早晚有一天,你会后悔的。
顾家二丫头又说,废话少说,你先把借我的国库券还给我,万一我爸发现少了,非抽我筋剥我皮不可。
祥雷说我在做生意,需要抵押。等赚了钱就还回来。
想到祥雷输的钱应该是用顾家二丫头给的国库券换的,文楚贻心里踏实了些。但这笔国库券,早晚是要还给人家的。她看不起祥雷这种软饭硬吃的样子,就打算替祥雷解个围。就算家里的国库券不够还,也可以再想别的办法。
她悄悄绕到水塔背面,先咳嗽一声,故意问是祥雷吗?
祥雷听到后魂飞魄散,竟然撒腿就跑。
顾家二丫头也一声不吭地跑了,生怕被文楚贻认出来。
文楚贻知道祥雷注定要失恋。上海人家从不与连队其他省份的人家通婚,因为他们以后都是要返城的。虽然当时还没有任何落实返城政策的风声,但他们凭借着近乎偏执的信仰,成了“两千里外的守望者”。
文楚贻又来到了李先辉家。李先辉正在嗑瓜子。他腿上放着盛放瓜子的簸箕,右手递瓜子,左手接瓜子皮。等攒够一把,就扔进火炉里。看到文楚贻沉着脸回来,他说,这种封建迷信,还是别信了。
文楚贻说,不信,那我爸怎么办?
李先辉说,你信不信,你爸该怎样还会怎样。
文楚贻从怀里掏出镜子,摔在地上,哭着说,我两次听到的都不是好话。
李先辉看文楚贻一副哭丧样,突然心软了,只好说,你刚才别的都做了,好像没有虔礼拜祝。你看书上既然写这四个字,就必须有这个程序。你要对着灶下跪许愿,嘴上还要念念有词。文楚贻问,念什么词?李先辉说,当然是古人的词。他挪开腿上的簸箕,慢吞吞地站起来进了里屋。文楚贻跟过去,看见他伏在床下翻腾了一会儿,拿出另一本线装书。来到外屋,他翻开书给文楚贻看,是一首名为《镜听词》的诗,作者李廓,词下有一行小注:古之镜听,犹今之瓢卦也。
文楚贻说,要我背下来吗?
李先辉说,你转调羹前先读一遍,等出门时,就默念最后两句吧。
文楚贻跪在火炉前,前胸被烤炙得滚烫。她默默许愿:父亲平安无事,祥雷心想事成,祥云高高兴兴,祥雨快快长大。然后她接过李先辉递来的书,照着念了起来:匣中取镜辞灶王,罗衣掩尽明月光。昔时长著照容色,今夜潜将听消息。门前地黑人来稀,无人错道朝夕归。更深弱体冷如铁,绣带菱花怀里热。铜片铜片如有灵,愿照得见家人千里形……
文楚贻跪在地上,手捧着书,大声读了一遍。
李先辉说,可以了。
文楚贻又读了一遍……
李先辉明白了,她想把这首诗背下来。
不知道跪了多久,文楚贻只觉得脸和前胸快被烤化了。李先辉搀起她时,她的手脚僵硬。她看到李先辉的手紧紧箍着自己的胸,只是自己毫无感觉。她扬起手,转动起白瓷调羹。调羹在水中掀起一朵朵小水花,最终停下。
这次指向的是东面,是连队居民最集中的区域。
文楚贻推开李先辉,又从八仙桌上取了李先辉家的火柴。李先辉警觉地问,你拿火柴干什么?
文楚贻说,放火!我要让全连队的人都喊“着火了”。
李先辉扯着她的袖子说,你疯了,家家门口都有麦草,风一吹会烧一片的。
文楚贻说,我爸都快死了,我还管得了这么多!
李先辉说,你爸死了,你烧房子也没用。
文楚贻哭著说,我这个当女儿的,总要做点啥吧?
她一边说,一边推开了李先辉。见他又扑过来,她敏捷地闪到一旁,拉开了门,用脸顶着门帘子冲了出去。
李先辉伏在地上,喘着气。
门合上不到一分钟,又被撞开了。文楚贻携带着寒风涌进来。她指着门外,对李先辉喊,你听!
李先辉什么也没听到。
文楚贻抓住他的手,将他拖到门跟前,又掀起了门帘,说你再仔细听。
李先辉听到连队里一群年轻人正在唱歌,好像还有吉他的伴奏。
过了好久,李先辉才听清两句歌词:“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熊熊火焰燃烧了我的心窝……”
责任编辑 刘鹏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