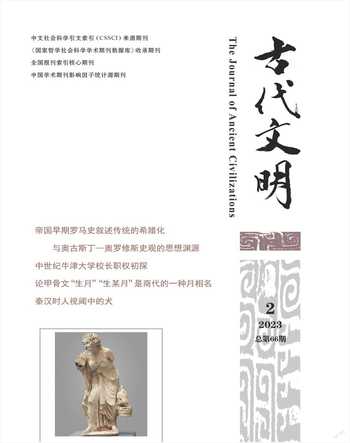秦及汉初外戚的政治平衡作用
2023-05-30张梦晗
关键词:外戚;政治平衡;秦始皇;吕后;沙丘政变
DOI: 10.16758/j.cnki.1004-9371.2023.02.010
一般认为,外戚登上政治舞台并形成较强势力,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发展日渐成熟的结果。尽管外戚自秦汉时期开始在中国历史上多有消极影响,但亦有其积极贡献,不能一概而论。秦及汉初作为外戚势力滋长的关键阶段,一向受到学界重视。以往学者对秦及汉初外戚的研究,主要是从制度等层面揭示外戚擅权的原因,另有部分研究侧重关注具有代表性的外戚人物;而从政治史的角度出发,将外戚置于一个比较长的时段,以充分考察其在政治格局中的作用与影响的研究则相对少见。值得注意的是,当君主对统治拥有绝对掌控力时,外戚其实可以成为维持政治平衡的重要力量。纵观秦及汉初的政治格局演生,不难发现外戚在长达百余年的时间里持续发挥着作用,并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一个很少为学者提及却又令人颇感意外的现象是,这一时期外戚势力的兴衰轨迹与政权发展的大致走向时常出现重合,其原因值得深入探索。本文就此略作分析,不当之处,祈请方家不吝赐教。
一、秦国外戚维持政治平衡的贡献
外戚政治作为中国历史上一种特殊的政治文化现象,始于战国中后期的秦国。尽管关于秦国外戚,时人范雎曾有“妒贤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的负面评价,1 但正如《史记·外戚世家》开篇所说——“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之君,非独内德茂也,盖亦有外戚之助焉”,2秦国外戚对秦的发展壮大实际也发挥了一定积极作用,尤其是在平定叛乱和维系政权平稳交接方面有其值得称道之处。
(一)秦国外戚平定叛乱的功绩
从秦昭襄王即位到秦始皇统一六国,秦国发生过三次性质严重的内乱,即季君之乱、成蟜之乱和嫪毐之乱。其中在平定季君之乱和嫪毐之乱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外戚势力发挥的积极作用。
季君之乱因秦武王死后的王位继承权而起。由于秦武王没有子嗣,他死后出现了激烈的权力斗争,最终武王的异母弟公子稷继位,是为秦昭襄王。公子稷之所以得立,离不开外戚的助力。史载“昭襄母楚人,姓芈氏,号宣太后”,“宣太后二弟:其异父长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冉;同父弟曰芈戎,为华阳君。而昭王同母弟曰高陵君、泾阳君”。在宣太后的亲族中,最具才干的是魏冉。他“自惠王、武王时任职用事”,在“武王卒,诸弟争立”的情况下将本不占优势的公子稷扶上王位。昭襄王二年(前305),“庶长壮与大臣、诸侯、公子为逆”,发动反对昭襄王的政变,又遭魏冉强力镇压:“诛季君之乱,而逐武王后出之魏,昭王诸兄弟不善者皆灭之,威振秦国。”
至于嫪毐之乱,则因嫪毐与帝太后私乱生子之事暴露而起。《史记·秦始皇本纪》详细记录了叛乱经过:
九年,彗星见,或竟天。攻魏垣、蒲阳。四月,上宿雍。己酉,王冠,带剑。长信侯毐作乱而觉,矫王御玺及太后玺以发县卒及卫卒、官骑、戎翟君公、舍人,将欲攻蕲年宫为乱。王知之,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卒攻毐。战咸阳,斩首数百,皆拜爵,及宦者皆在战中,亦拜爵一级。毐等败走。
嫪毐反叛前受命先发制人的昌平君和昌文君,不像魏冉那样声名显赫,《史记索隐》着重就昌平君作了解说:“昌平君,楚之公子,立以为相,后徙于郢,项燕立为荆王,史失其名。昌文君名亦不知也。”另外,在《索隐》对《春申君列传》的注释中,亦可见有关昌平君身世的记载:“楚捍有母弟犹,犹有庶兄负刍及昌平君。”针对《索隐》提出的昌平君乃楚考烈王熊完之子的说法,清人梁玉绳在《史记志疑》中曾予以批驳,认为“昌平君之称,考烈王子,未见确据”,
但他并没有否认昌平君作为楚公子的身份。考虑到安国君嬴柱系宣太后之孙,其正妻华阳夫人是楚人,根据楚、秦之间长期的联姻关系判断,出嫁秦王子的华阳夫人理应来自楚国王室。因此,无论昌平君是不是楚考烈之子,他与华阳夫人都应有血缘关系,他的外戚身份当无疑问。再加上昌平君平定嫪毐之乱时,华阳夫人早已升格为华阳太后,地位尊隆自不待言,此时昌平君(及昌文君)用事,甚至担任秦相,正是其以外戚身份掌权的证明。否则怎么会平白无故地让出身楚国王族的昌平君,在危急关头担负平定叛乱的重任呢?
由上可见,在两次动乱中,起到平息事态、保持秦国政治稳定作用的是外戚魏冉和昌平君。就叛乱的发动者而言,公子壮和嫪毐都有很强的个人实力。公子壮能够任庶长之职,“僭立而号曰季君”,说明他有领兵作战才能,并且在秦国朝野中具有一定威望;嫪毐在作乱前也处于权势的巅峰:“封为长信侯。予之山阳地,令毐居之。宫室车马衣服苑囿驰猎恣毐,事无小大皆决于毐。又以河西太原郡更为毐国。”“嫪毐家僮数千人,诸客求宦为嫪毐舍人千余人。”正因为如此,二者起兵反叛时得以联合其他多股势力,造成更大威胁。公子壮发动政变得到大臣、诸侯、公子支持,甚至武王生母惠文后也参与其中;嫪毐的同党亦多有在秦行政中枢任职者,如卫尉竭、内史肆、佐弋竭、中大夫齐等。可见魏冉和昌平君的对手绝非泛泛之辈,这更凸显了他们迅速平息动乱的重要功绩,即保证了当政者不被颠覆,能够持续稳定地推行其统治,并且令秦国免于陷入内部纷争的动荡局面。当然也必须看到,魏冉和昌平君等秦国外戚之所以能够顺利地平定叛乱,实际凭借的是最高统治者的支持,没有最高统治者授予的实权,一切便无从谈起——我们不能忽视这一基本前提,更不能对秦国外戚的权势作过高估计。
(二)秦国外戚维系政权平稳交接的作用
事实上,即便没有发生动乱,外戚在战国后期秦国最高权力的交接中也起到关键作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莫过于华阳夫人——正是她说服安国君将子楚立為太子,并加以大力扶持,从而奠定了从秦孝文王到庄襄王,再从庄襄王至于秦王政的权力交接次序。《史记·吕不韦列传》:
华阳夫人以为然,承太子闲,从容言子楚质于赵者绝贤,来往者皆称誉之。乃因涕泣曰:“妾幸得充后宫,不幸无子,愿得子楚立以为适嗣,以托妾身。”安国君许之,乃与夫人刻玉符,约以为适嗣。安国君及夫人因厚馈遗子楚,而请吕不韦傅之,子楚以此名誉益盛于诸侯。
兼及孝文王即位仅3天便撒手人寰,庄襄王在位也不到3年,故而可以想见的是,在华阳夫人由王后升级为太后的过程中,她还会凭借其权势地位为秦国王位交接的顺利进行提供保证。这从“孝文王元年,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褒厚亲戚”,“庄襄王元年,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而布惠于民”的记载中便可看出一丝端倪。不管是孝文王“褒厚亲戚”,还是庄襄王“施德厚骨肉”,以华阳夫人为代表的外戚势力都能从中享受到好处。可以说这是外戚与王权的一种相互确认,即外戚为王位交接提供保证,新王掌握权力以后又第一时间对外戚的地位给予肯定。同时在这里也不难发现,“先王功臣”与“亲戚”的重要程度相当。一方面,秦国的发展并不单纯依赖功臣或亲戚(其中主要应理解为外戚,当时秦国的宗室力量过于孱弱),二者皆有其相应贡献;另一方面,功臣与外戚也存在相互制约的关系。比如当宣太后和魏冉为首的外戚势力过分膨胀之时,范雎这样日益受到重用的“功臣”就向秦昭襄王进言:
臣居山东时,闻齐之有田单,不闻其有王也;闻秦之有太后、穰侯、华阳、高陵、泾阳,不闻其有王也。夫擅国之谓王,能利害之谓王,制杀生之威之谓王。今太后擅行不顾,穰侯出使不报,华阳、泾阳等击断无讳,高陵进退不请。四贵备而国不危者,未之有也。
昭襄王于是“废太后,逐穰侯、高陵、华阳、泾阳君于关外”。而当嫪毐势力登峰造极、威胁王权时,受命对他加兵镇压的又是外戚昌平君。这也证明秦王政继位以后,功臣和外戚并为引重的传统依然延续,最高统治集团通过掌握功臣与外戚间的平衡关系,确保政权在自己的控制下稳健运转。
毋庸置疑,秦国外戚也有其明显弊端。前引范雎“闻秦之有太后、穰侯、华阳、高陵、泾阳,不闻其有王也”之语,便足证秦国外戚的权势显赫,这对秦王的最高权威无疑构成了一定程度的挑战。但总体而言,不论是平定叛乱、保证最高权力顺利交接,抑或是与功臣之间既共同为秦国效力又彼此制约的关系,都充分显示出外戚在維持秦国政权稳定方面的积极作用,令秦国在内部出现问题时得以涉险过关。这也提示我们,秦国外戚看似手握大权,但实际上他们基本处于一种可控的状态,不会从根本上威胁秦王的统治。诚如孙家洲先生所说:
在出重手整肃魏冉和范雎之前,秦昭王都曾经以赋予高度信任、授予足够实权的方式,让他们自以为大得君宠,因而竭力辅政,有效地制造了君王与辅政重臣之间和衷共济的政治表象。秦昭王对魏冉的四度拜相,就是这样的笼络式手段,而力挺范雎“公报私仇”,更是这一统治手法的高明运作。严峻的制度制约,辅之以灵活的处理手法,造就了秦国的君臣关系既有“尊君卑臣”的规范,又有和衷共济的氛围,避免了出现“权臣”窃弄国柄而出现权力斗争,招致政局动荡的局面。
因此,秦国外戚不仅在某些关键时刻能够发挥维持政治稳定的重要作用,而且始终没有形成尾大不掉之势。
二、秦朝外戚式微对政治平衡的影响
外戚作为战国中后期秦国维持政治平衡的重要力量,在昌平君和昌文君之后便从人们的视线淡出,从此销声匿迹,史书中竟找不到秦朝外戚的相关记录。《史记·外戚世家》称“秦以前尚略矣,其详靡得而记焉”,以资料匮乏为由将汉以前的后妃、外戚一笔带过,便是明证。这不得不说是令人惊讶的,也是值得深入思考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我们认为,此系以秦始皇为首的秦国统治阶层权衡之后的结果,除了防止外戚擅权,主要原因有三。
其一,这应与秦在消灭六国、建立大一统帝国的新格局下,对外戚势力进行强力打压有关。秦统一后外戚的母国已不复存在,如果说在战国时代,母国多少还能为外戚的活动发挥支撑作用,那么等到六国覆灭以后,这方面的作用也丧失殆尽了。外戚势力的继续存在反而会变成一种潜在的颠覆秦帝国的威胁。昌平君反秦就是例证。尽管如前所述,昌平君曾平息嫪毐之乱并担任秦相,但他在秦灭楚的关键时刻背秦向楚,“反秦于淮南”,选择为了楚国而对抗秦国。这必然会极大影响秦始皇对外戚的态度,他很有可能将外戚一并视作六国残余势力。众所周知,在灭六国的过程中,秦人“堕名城,杀豪俊”,多有摧抑六国残余势力之举。如灭赵后将赵王迁驱至房陵,坑杀与秦王母家有仇怨者,迁赵国豪强贵族于葭萌;灭魏后处死投降的魏王假;灭齐后迁齐王建于共;等等。此外,里耶秦简、岳麓书院藏秦简中均有“从人”简。所谓“从人”,也就是主张合纵抗秦之人。杨振红先生指出:
“从”意为“合从”“从亲”,专指关东六国缔结盟约,联合抗秦。《岳麓秦简(伍)》013-018简表明,至晚在公元前228年秦灭赵以后便兴起从人狱,故赵将军乐突及其亲属、舍人均被列为从人,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通缉。从人狱波及全国、历时长久。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秦始皇对与山东六国联系紧密的外戚也曾严厉打击,以杜绝六国势力复辟的可能性。其中,战国后期屡屡成为秦国政治中优势力量、表现强势的楚国系外戚,应当是秦始皇重点打击的对象。昌平君反秦前被放逐便显露出了此种迹象。
其二,秦始皇的独断专行远远超过他的父辈和祖辈。一方面,秦始皇事无巨细皆要亲自裁决,正如侯生和卢生所说:“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已……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可想而知,外戚势力对秦始皇的统治而言不是必须的。另一方面,秦始皇对帝国的行政体制也颇为自信,特别是在推行郡县制方面表现出很大的决心,故而除了扶苏和胡亥,秦始皇几乎没有给其他子女以任何参与政治的机会。尽管丞相王绾曾公开建议立诸子为诸侯王,镇抚东方;博士淳于越也进言:“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但秦始皇不为所动。这不仅使秦“内亡骨肉本根之辅,外亡尺土藩翼之卫”,而且令本就受到打压的外戚势力毫无抬头机会。
其三,史书中关于秦始皇后宫的记载可能被有意删除了。这一推测同样基于从秦国到秦帝国的转变,以及秦对故六国的警惕防备。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毫不掩饰他对山东六国的鄙薄。在其巡游所立刻石的文辞中,六国君主的残忍无道和皇帝的辉煌功业总是形成鲜明对照:“六国回辟,贪戾无厌,虐杀不已。皇帝哀众,遂发讨师,奋扬武德。义诛信行,威燀旁达,莫不宾服。烹灭强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极。普施明法,经纬天下,永为仪则。”此外,还有不少在故秦地犯过错、政绩差或者身体欠佳的官吏,源源不断地被派往“新地”担任官吏。可见秦始皇既心怀强烈的优越感,又难掩其作为征服者的傲慢。在此种情况下,秦帝国皇室在血缘上与六国的联系就变得敏感起来。要让不屑与“六王”为伍的秦始皇承认,他的子女身上其实也流淌着六国血脉,大概是很不情愿的,这也与刻辞中描述的秦与六国势不两立、高下分明的情况有较大出入。又兼藤田胜久和李开元先生提出,秦始皇长子扶苏的生母或出自楚国王室。考虑到秦灭六国,楚国的反抗最为顽强持久,楚亡后楚地流传的谶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及“东南有天子气”,亦集中反映了楚人对秦的仇视。再加上故楚国幅员辽阔,东南的江淮地区距离秦统治中心比较遥远,是秦统治相对薄弱之处,是以类似扶苏为楚王女所生的信息,更需加以隐瞒,不便明确写在史书中。也许正是综合考虑过后,为避免对统治产生消极影响,秦始皇下令删除了史书中有关其后宫的内容。
总而言之,在秦统一六国的历史背景下,外戚势力的潜在威胁是秦的统治者无法忽视的。为了杜绝统治集团出现从内部被打破的可能性,确保对六国故地统治的稳定,秦始皇采取了坚决打压外戚势力的举措。也就是说,他宁愿舍弃外戚在维持政治平衡方面发挥的作用,也要铲草除根,不留后患。秦二世胡亥即位之初所下诏书便多少印证了这一点:
天下失始皇帝,皆遽恐悲哀甚,朕奉遗诏。今宗庙吏(事)及箸(书)以明至治大功德者具矣,律令当除定者毕矣,以元年与黔首更始,尽为解除故罪,令皆已下矣。朕将自抚天下。吏、黔首,其具(俱)行事,毋以繇(徭)赋扰黔首,毋以细物苛劾县吏。亟布。
同样是登基伊始,前揭孝文王“褒厚亲戚”、庄襄王“施德厚骨肉”,即使是秦始皇本人,也“委国事太后及大臣”,而年纪轻轻的二世皇帝却在如此重要的诏书中对宗室亲戚只字不提。这恐怕绝非偶然或疏忽,而很有可能是对先前秦始皇的某种既定路线的继承和贯彻。
我们认为,外戚式微造成的负面影响已远远超出秦始皇的预想,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秦朝的政治格局——最显著的影响莫过于在赵高和李斯篡改秦始皇遗诏,杀害扶苏、拥立胡亥时,朝野中缺少了重要的制约力量。这使赵高和李斯在发动政变前少了许多顾虑。赵高说:“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赐长子书及符玺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与高之口耳。”事实也确实如此。手中并无军权的谋逆者,在政变过程中竟没有遇到多少阻力,仅凭一封玺书就将扶苏置于死地,这不禁令人想起同样“矫王御玺及太后玺”为乱,却被昌平君、昌文君挫败的嫪毐。只可惜赵高和李斯谋逆时,已经不存在能够有效制约他们的外戚势力了。实际上,纵然沙丘政变是场政治阴谋而非明目张胆地起兵造反,也并非没有可疑之处。比如蒙恬就曾提醒扶苏:“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将三十万众守边,公子为监,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来,即自杀,安知其非诈?”甚至赵高自己也承认:“夫沙丘之谋,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故而假如扶苏身后有支持他的外戚势力存在,赵高、李斯矫诏前或许就要仔细权衡一下轻重,他们逼迫扶苏就范也不可能只是凭借一封玺书这么简单了。以赵、李二人的实力而言,即便成功一时,也很难保证胡亥可以顺利登上皇位并掌权。总之,尽管沙丘政变的发生可能与许多因素有关,但外戚势力在该事件中的缺席及其影响仍然值得关注。
进一步而言,即便对秦二世的统治来说,外戚势力式微也是相当不利的。秦二世对同父的兄弟姐妹大开杀戒,说明其统治地位并不稳固,参照秦昭襄王的先例,争取外戚势力的支持本是实现政治平衡、巩固统治的有效途径之一。然而,揆诸史实,我们却看不到任何外戚的身影。秦二世从始至终倚仗的都是赵高等人,直到最后身死其手,似乎都别无选择。
三、汉初吕氏外戚的勃兴与政治平衡
伴随着秦汉交接,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前揭秦为巩固新兴大一统帝国采取了严厉打击外戚势力的举措,可同样是在大一统的格局下,为什么继起的汉帝国却很快出现吕氏外戚干政的情况?就其根本而言,我们认为这应与汉吸取秦亡的历史经验和教训,重新回归战国后期秦国奉行的功臣与亲戚并为引重的路线有关。《汉书·诸侯王表》:“汉兴之初,海内新定,同姓寡少,惩戒亡秦孤立之败,于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余邑,尊王子弟,大启九国。”在汉初形成的内倚功臣、外封同姓诸侯王的政治局面中,吕氏外戚因为具有开国功臣和宗室外亲的双重身份而居于十分特殊的地位,这也为其势力的滋长提供了便利。
一方面,吕氏家族在汉朝夺取天下的过程中贡献颇多。
首先,吕后本人就是汉的功臣。刘邦起初亡匿“芒、砀山泽岩石之间”,正是吕后投合“东南有天子气”,称“季所居上常有云气,故从往常得季”,为刘邦在政治上的兴起制造舆论;“佐高祖定天下”后,吕后又亲自参与对异姓诸侯王的诛杀,“所诛大臣多吕后力”。
其次,吕后的亲族亦不乏因功封侯者。吕后的兄长周吕侯吕泽,便是汉高祖麾下的得力战将。《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记载吕泽“以吕后兄初起以客从,入汉,为侯。还定三秦,将兵先入砀。汉王之解彭城,往从之,复发兵佐高祖定天下,功侯”。可见吕泽不但战功显赫,为汉定鼎天下发挥过关键作用,而且手握重兵,甚至其行动还享有相当独立性。吕后的另一位兄长吕释之,也因“击三秦”“奉卫吕宣王、太上皇”得封建成侯。至于吕后的妹夫舞阳侯樊哙,更是刘邦集团无可置疑的核心成员之一。
由于同属功臣集团的缘故,吕氏外戚与许多朝廷重臣的关系密切。譬如在太子刘盈的废立之争中,吕氏外戚就得到张良、周昌等人的支持。功臣集团之所以力主立刘盈为太子,其中一个原因便是吕氏外戚并非攀龙附凤之徒,而是有实打实的功劳的。他们深知日后吕后在超拔自己亲族地位的同时,多少也会照顾到其他功臣的利益。是以当吕氏外戚迈开扩张势力的脚步时,功臣集团的反对力度是很微弱的,甚至还有人报以逢迎的态度。故此,也才会出现“大臣请立郦侯吕台为吕王,太后许之”,吕后随即下诏“差次列侯功以定朝位,藏于高庙,世世勿绝,嗣子各袭其位”的情况。这既是吕氏外戚与功臣集团的利益置换,也是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
另一方面,吕氏外戚对平衡守内的功臣和居外的同姓诸侯王也有重要价值。
汉初功臣集团在政治和经济上拥有强大势力:“有其功者上致之王,次为列侯,下乃食邑。而重臣之亲,或为列侯,皆令自置吏,得赋敛,女子公主。为列侯食邑者,皆配之印,赐大第室。”尽管汉高祖在位期间消灭了绝大多数异姓诸侯王,并代之以同姓诸侯王,但是功臣集团的力量仍然十分壮盛。据《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除去宗室和外戚,漢高祖时因功封侯者多达137人。考虑到宗室力量的分布并不集中,单纯依靠东方的同姓诸侯王可能导致中央出现内部空虚的漏洞,而沙丘政变已经证明,对权臣不加制约是极其危险的——吕氏外戚的作用由此得以凸显。《汉书·高帝纪》记录汉高祖离世前,吕后曾问及其身后的安排:
“陛下百岁后,萧相国即死,令谁代之?”上曰:“曹参可。”问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戆,陈平可以助之。陈平智有余,然难以独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
可见在确定未来主政大臣人选及执政次序的问题上,吕后是得到汉高祖授意的。汉高祖一来期望吕后与功臣和衷共济,二来将用人的最高权力交予吕后,亦表明他欲通过吕后约束功臣,起到“安刘氏”的作用。赵翼云:“孝惠既立,政由母氏,其所用曹参、王陵、陈平、周勃等,无一非高帝注意安刘之人。”吕后顺利践行汉高祖意旨的背后,实际体現了她对功臣精确有效的控制。虽然汉高祖逝世后,吕后曾与审食其密谋“诸将与帝为编户民,今北面为臣,此常怏怏,今乃事少主,非尽族是,天下不安”,但我们认为,这只是吕后因为即将独当大局,前途叵测,一时恐惧的情绪流露。
次及汉惠帝驾崩,由于其太子的来历不明,吕后自觉地位受到威胁。为了维持朝中力量的均势,尤其是制衡功臣集团,吕后遂广立诸吕为王侯。侍中张辟强曾向丞相陈平建言:“帝毋壮子,太后畏君等。君今请拜吕台、吕产、吕禄为将,将兵居南北军,及诸吕皆入宫,居中用事,如此则太后心安,君等幸得脱祸矣。”是知吕后最大的心腹之患正是功臣集团,而赋予诸吕权力,令之“居中用事”,能够有效缓解吕后的忧虑,吕氏诸王无一之国也正是因应于此。自高后元年(前187)四月封吕台为吕王,至高后八年封吕通为燕王,吕后共封立吕氏七人为王、九人为侯,包括“追尊父吕公为吕宣王,兄周吕侯为悼武王”。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具律》更是明确记录了优待吕氏子弟的法律条文:“吕宣王内孙、外孙、内耳孙玄孙,诸侯王子、内孙耳孙,彻侯子、内孙有罪,如上造、上造妻以上。”《史记·外戚世家》这样总结当时的局面:“及孝惠帝崩,天下初定未久,继嗣不明。于是贵外家,王诸吕以为辅,而以吕禄女为少帝后,欲连固根本牢甚。”吕思勉先生也说:“内任外戚,外封建宗室,此汉初之治法也。”有鉴于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王诸吕”仅仅就是为了吕氏一家之私,郦寄所说的“吕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议,事已布告诸侯,诸侯皆以为宜”,其实也不尽为虚言。在当时特定的背景下,因为吕后的存在,吕氏与汉家的利益在某种程度上是具有一致性的,“王诸吕”确实为巩固汉的统治发挥了一定功用,这一点不能轻易否定。
总之,吕氏外戚既凭借其功劳跻身汉的开国功臣行列,与一众汉的股肱之臣关系密切,又因宗室外亲的身份,而有机会在制约功臣集团的过程中进一步提升其地位。再加上“为人刚毅”的吕后长期执掌大局,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汉初吕氏外戚的勃兴。
不过,应该看到的是,吕氏外戚的权势与西汉中后期及东汉的外戚不可同日而语,即便他们侵夺了部分功臣和宗室的利益,也难以彻底垄断汉初的朝政。有学者指出,吕氏外戚摆脱不了刘姓皇权的附庸地位,“他们的势力仅仅局限于中央统治的上层,而在地方上是没有根基的,因而吕氏集团自始至终没有能够形成足以驾驭整个局势的力量”。吕后虽然在“擅废帝更立,又比杀三赵王”等事上恣意而为,但治国理政不敢稍离汉高祖时期的既定路线。吕后统治期间,汉的两大支柱力量——功臣和宗室的地位未曾受到根本性动摇。固然吕后称制后,吕氏外戚势力膨胀,令其双重身份属性逐渐褪色,自外于功臣和宗室集团,俨然成为左右帝国的第三股势力,但吕氏外戚实际并不具备同功臣和宗室集团抗衡的实力。《史记·荆燕世家》载齐人田生语:“今吕氏雅故本推毂高帝就天下,功至大,又亲戚太后之重。太后春秋长,诸吕弱,太后欲立吕产为吕王,王代。太后又重发之,恐大臣不听。”故吕后一死,破坏平衡的吕氏外戚立即被功臣和宗室集团联手消灭,便完全不可避免了。
四、结语
综上所陈,自秦昭襄王即位到秦始皇统治前期,凭借最高统治者的强有力支持,外戚在平定叛乱、保证权力顺利交接以及制约权臣方面发挥着持续性作用。但秦统一后,这样一种历史传统被人为地打断。虽然经过认真剖析,可以发现当中有其迫不得已的原因,但外戚的式微依然给秦帝国造成不利影响,即导致了政治上的失衡和危机来临时应变能力的欠缺。从宏观的图景来看,尽管历史在秦统一后进入了崭新阶段,但新兴的大一统帝国与战国之间依然有太多联系,可谓打断骨头连着筋,强行割裂便难免有得必有失。抑制外戚势力既体现了帝国为走出战国时代所做的努力,也成为赵高和李斯在沙丘阴谋得逞的原因之一。
迄于汉初,统治者吸取秦短祚而亡的历史教训,重新回归战国后期秦国奉行的功臣与亲戚并重的路线。由于兼具开国功臣和宗室外戚的双重身份,吕氏外戚在吕后称制期间盛极一时。然而,外戚势力的过度膨胀同样威胁统治稳定。当吕氏外戚从平衡功臣和宗室集团的力量转变为均势局面的破坏者时,也就不可避免地给国家带来祸患。尽管诸吕之乱最终得到平息,但吕氏开启的先声,为有汉一代层出不穷的外戚专政埋下了伏笔。
纵观秦及汉初外戚势力的消长,不论顿衰,还是骤兴,背后皆存在种种人为因素的推动。最初的设计总是好的,但道路走到尽头往往事与愿违,不是自断双臂,便是节外生枝。在政治格局的不断演生中,外戚势力的此起彼伏,都是早期帝制时代的统治集团不得不进行实验的结果——这多少也有助于解释两汉以后外戚活跃程度逐渐下降的原因。
[作者张梦晗(198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史学编辑,北京,102488]
[收稿日期:2022年11月13日]
(责任编辑:王彦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