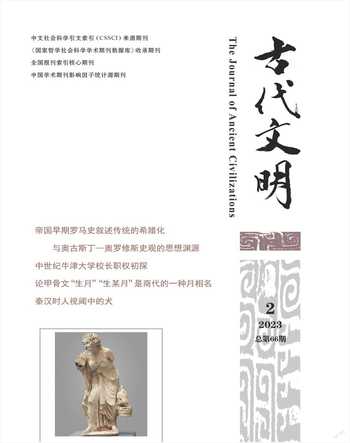《烹鲜纪略》所见清初华北地区的县域治理
2023-05-30赵士第
关键词:《烹鲜纪略》;县域治理;清初;崔鸣鷟;华北
DOI: 10.16758/j.cnki.1004-9371.2023.02.011
清代县政研究是探讨清代国家基层社会治理、官民关系、央地财政关系等问题的重要切入口。目前对清代县政及州县治理的研究多集中于清中后期,主要史料也多为地方档案、官员日记和官箴书等。由于清初地方档案和衙署文册的缺失,对清初州县治理的研究,目前尚有可挖掘之处。对此,清初州县官的施政书成为重要史料补充,但遗憾的是存留较少。笔者在查阅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善本、孤本时,发现一本名为《烹鲜纪略》的施政书。该书反映康熙初年崔鸣鷟历任山西河津知县和河南仪封知县、偃师知县期间的施政记录,可有助于窥探清初华北地区的县域治理问题。
一、崔鸣鷟生平与《烹鲜纪略》主要内容
崔鸣鷟,字卉庵,直隶内邱人,生于明天启三年(1623),耕读传家。中顺治丁酉科(1657)举人、顺治辛丑科(1661)进士,后赴都察院观政。康熙八年(1669),任山西平阳府河津县知县。在任期间,“首革陋规、杂派诸弊,均水利,正经界,严保甲,抑豪强,修学建桥,以次毕举。措置有方,事集而民不扰”。康熙十二年(1673)补仪封知县,整修河工,调节军民关系,整饬胥吏,邑人为之立德政碑。康熙十六年(1677),崔鸣鷟任偃师知县,“听讼立决,人称平允……训迪士子,文风丕振”。康熙二十二年(1683),任浙江处州府同知,“建学明伦,息讼弭盗,悉出至诚,无弗感化”,并解决宣平县逋赋问题。康熙二十八年(1689)任湖南衡州知府,曾受偏沅巡抚郑端之命,“馈帛粟请见王夫之”。康熙三十年(1691)补任江西广信府知府,“革除陋规,多惠政,重建钟灵桥,仅成三墩,以疾卒”。从其任职地的方志记载看,崔氏多被列入《名宦传》《循吏传》,卓有政绩。
《烹鲜纪略》是崔鸣鷟早年仕宦生涯的施政记录,全两册,现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全书不分卷。书前有作者自序云:
余赋性踈慵,声色玩好,泊乎无所尚,惟于诗书较癖爱,兼以累世积坟典,日与帖括为伍。余因得尚友古人,慱览载籍,然而过目多遗忘,不能成诵,间有所作,鲜深入,不可传,故不常作。惟不常作,益生疏懒,□□事推诿矣。一行作吏,遇有关于纲常名□,风俗民隐,不容无言者,公署中无可推诿,倩人为之,罕称意,弗获已,而搦管于酬酢杂沓中,任笔挥洒,真抒己见。其间体裁不一,繁简互异,当理与否,余不敢信。聊付剞劂,用质当世,以明余之存心与治事,如斯而已。
清代州县官被称为“入则日坐堂皇,理刑钱之争讼;出则巡视阡陌,察风俗之美恶”。从崔鸣鷟自序可见,该书是作者为官期间所作,多为职掌一方时直抒己见之文。而取名《烹鲜纪略》,则借用老子“治大国,若烹小鲜”的名句。卷末署“康熙庚申榴月之吉内丘崔鸣鷟题于古亳公署”,刊刻时间为康熙十九年(1680),即作者在偃师县知县任上。全书主要内容为作者在河津、仪封、偃师三县担任知县时的施政记录,大致分为4类,即:判牍、告示、公文、记文。
县域治理的主要内容一是刑名,二是钱粮,三是教化。同时,知县又有迎来送往之责,“正官无远近必亲往,加以奔走守候,尊卑酬应,戴星往返,惟日不给”。崔鸣鷟担任三县知县期间,正值清朝统治立足未稳,又逢“三藩之乱”,地方经费紧张,民生凋敝,前朝的各项陋规和各种问题亟需处置。
二、清初华北县域社会秩序的重建
经过大规模社会动荡,明末以来遗留的各种社会问题亟需解决,而朝廷各项举措也需落实在州县层面,实际的推动者往往是州县官。此种举措主要包括恢复生产、清理疆界、严保甲、兴教化、正风俗、抑制豪强、维护治安。崔鸣鷟在三县任职中,多有相关举措。
(一)劝课农桑与整顿赋税
历经明末清初战乱,华北人口减少、土地荒芜,必须劝课农桑,养民生计。为此,崔鸣鷟认为必须“重农桑、驱游惰、教树畜,以广孳息。崇俭朴、抑奢华、禁燕会,以苏物力,去其累害”。任职偃师县时,该地“邑无人烟,田园尽行荒芜”,他作为知县,“招集流亡,开垦熟地二百余顷”。此外,崔鸣鷟还劝民栽树,作为养民之计。他指出:“树木根深不怕旱涝,用广而利大”,尤其鼓励在“薄地、碱地及古路道傍、荒坡遥堤、五谷不生之处”大力栽种。“栽种至二百株以上者,该乡保登记上农夫簿内送县,有過免责一次,以酬其勤;其或懒惰全不栽植者,乡保登记游惰簿内送县,以凭查责。”又因农田灌溉之需求,崔鸣鷟将偃师县北邙山南麓温泉相度开渠,“以资灌溉”。为防止用水纠纷,他告示全县:“按地认工,按时浇地,安享自然之利,无事之福,倘有倚强凌弱,搀越截拦,独霸水利者,许下首使水之人同渠头禀官究治,仍罚本年不得使水。”
由于变乱导致人口失散,许多册籍不存,需先清丈土地,并划分等级。《仪封县志》载:“当明季,户口流亡,土田荒落,肃清为难。迨国朝初年,免荒征熟,弊去其已甚者,而犹未尽绝。至康熙间,按方定里,大为厘正,而后上、中、下错,赋役始均……”从《烹鲜纪略》内容来看,崔鸣鷟于此多有作为。
(二)严保甲与清疆界
康熙时期,清朝大力推行保甲,通行晓谕“直隶各省府州县乡村人等,切实遵行”。在河津县任内,崔鸣鷟“正经界,严保甲”。在偃师任内,他重视提防盗贼,提倡修建墙垣,护卫乡村。通令“各将本村庄住房以外公同乡保牌甲人等,相视形势,周围筑墙,墙外挑濠,大家鼓舞,齐力浚筑。墙要高厚,濠要宽深,不得临房太近,近恐伤屋,亦不得离房太远,远恐伤地”,规定“夜间关门上锁,各家轮流巡守,稍有声息,齐力堵御”。
清疆界亦尤为必要。位于河津县与万荣县交界的双营镇是基层市场交易频繁之地,集市发达,归属于何,需要清疆界,“保甲界牌,查循旧例,并无集市字样,因不得已而僭改数字,然又恐为左右所欺”。双营镇“津民以为属津,荣民以为属荣”,河津民众之言有府县志书可考,万荣县民则毫无凭证,但受价管业。崔鸣鷟查询保甲册得知,“双营保甲津民四百二十家,荣民止三十一家”,河津民人数多于万荣。请上宪定夺后,该地最后划归河津,从而解决纠纷。
(三)兴教化与正风俗
康熙帝亲政后,改变以往的高压政策,致力推行教化。而教化之所,重在学校,上谕称:“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崔氏任职的河津县,历经明末清初动荡,县学宫“鞠为茂草,败壁颓垣,荒凉满目,牛羊时出没其中,且旌麾无存,簠簋不列”。崔鸣鷟“自捐俸金,集士绅共商维新之举”,从而重建学宫。他还提倡衙署捐俸给县学生发油炭以“为霜天攻苦之资”,作为“鼓励风俗之一助”。
清初继承明制,还在州县大力提倡社学。崔鸣鷟任职偃师县时倡导“兴复社学以弘教化”,并在偃师县程夫子祠后社学内延师任教。
除学校外,自明代以来,乡贤祠、名宦祠等得以全面普及化和制度化,并与庙学紧密结合,发挥教化作用。偃师县乡贤祠建于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历经百余年,“邑祠又废”,崔氏在任内重修。再如偃师有两程夫子祠,后遭破坏。崔氏倡士绅捐助银钱,历经3个月重修,以“敦崇修举之意”。
崔鸣鷟还按照当时官方意识形态整顿地方风俗。河津县有“(女子)内外不避,盖亦寻常百姓之陋习”,必须惩治淫恶之人。而对当地再嫁有妇之夫和娶有夫之妻者,崔鸣鷟加以杖惩。针对当地轻生之风,“愚夫愚妇动以细故輙行自尽,殊为可悯”,更有甚者以尸体诬告或图赖他人以诈取钱财。于是告示民众,“嗣后凡有投井、自缢、服毒身死者,该地方赴县禀明,即时掩埋……决不差委相验,断布断棺,俾人咸知轻生者之无益而有损也,则所全活者多矣”。禁止以尸体讹财,有利于树立“轻生无益”的良好社会风气。
正风俗亦需要抑制豪强。河津县高家为土豪世家,“以叛犯之余孽,济恶两世,蚕食一方”,不仅霸种土地,且包揽钱粮征收,凭借宦势威逼立约,强吞弱业,崔鸣鷟按律依法惩处。再如仪封县卫廓有豪强,“数十年来依财势权,子母剥削穷民,习惯成性”,且诬告他人,最后被惩处。
从《烹鲜纪略》所载崔氏在华北三县的施政可见,清初州县经历了复杂的社会秩序重建过程,而州县是社会重建的基础单元,州县治理为立足未稳的清王朝继续推进全国统一创造了条件。
三、清初财政危机背景下的华北县域政务运作
清初大量用兵,軍费支出浩繁,导致州县财政紧张,因此筹饷纾困是当时施政的中心。虽然清初统治者标榜“轻徭薄赋”,但实际上依然按照万历时期的标准编订《赋役全书》,并将明末辽饷加派的数额变相融入。其中,顺治十四年(1657)编订《赋役全书》时“钱粮则例俱照万历年间……至若九厘银,旧书未载者,今已增入”。康熙初年,国家虽稍微稳定,但统治范围内“官贪吏酷,财尽民穷”。作为知县的崔鸣鷟感叹:“迩来逆氛未靖,军兴旁午,司国计者广开事例,屡裁存留,可谓利析秋毫矣。而国用仍然未足,民生渐至困苦者,其故何也?”清初州县并无独立财权,只是财政征收至中央的一个环节,所谓“州县财政”只不过是州县级政府所经管的财政事项。具体而言,除田赋征收外,州县还有积谷备荒、仓储建设、驿递经管等事务。而有漕省份及有河省份州县,还需经营漕务、河工等。《烹鲜纪略》对此多有反映。
(一)田赋征收与仓储建设
州县税收经管最为繁杂的项目即为田赋,清初继承明制,田赋一年分两次开征,春季为上忙,秋季为下忙。崔鸣鷟所治理的三县为二月开征,五月完成,八月接征,十二月完成,交由藩库。由于明末田赋征收的混乱,整顿征收则例尤为必要。以偃师县为例,在万历年间,偃师制定田赋征收的九等则例,至清初颁布《丈量率制》,折成一等上地征收,统一划定了亩制,在具体折征比例上“中地每一亩五分折上地一亩,下地每两亩三分折上地一亩”。偃师县“确定荒熟上中下三色地共五千七百八十九顷八十七亩三厘五毫,遵照《赋役全书》折成一等上地三千二百三十二顷九十九亩七分一厘二毫二丝四微”。崔鸣鷟奉命清查地亩,见偃师“冈陵重叠,硗确参差,瘠多肥少”,认为明代施行的“上一中三下五”的九等则例有其道理,并询问乡村老者,指出某地为中下、下下等,只征银一二分不等,但如果按清初定制五分行粮,“按册核地,不无缺额,而照则算粮,无异加赋,百姓困穷”,而“以一二分之地而行四五分之粮,是隐捏报之名而蹈捏报之实”,请求上宪能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酌情更改征税原则。
凡遭遇战争、灾荒等,朝廷要进行田赋蠲免,各州县官一旦遇灾必须报灾情和程度,迟报受罚。仪封县易受水灾,并有河工之累,丰年不免于饥寒,一旦遭遇旱灾,则麦田薄收。崔鸣鷟在任期间,曾上《请蠲坍塌地粮申文》,指出:“仪封县逼处河滨,中界黄流,两岸民田数十年来被水漂没,地主空包钱粮,血尽毛枯,无可呼吁。”他根据里民开报坍塌地数实际查访,“请题豁以除民累”。
除田赋蠲免外,当发生灾害时还有缓征作为补充。康熙四年(1665),康熙帝“谕令以后被灾州县,将当年钱粮先暂行停征十分之三,候题明分数,照例蠲免”。崔鸣鷟任职偃师时,正值“军兴旁午,需饷孔殷”,而当地“连年以来水旱频仍,小民勉强完粮,筋力已竭”,“十室九空,南坡一带草根树皮剥食殆尽,穷苦可谓极矣”,于是向上宪呼吁缓征钱粮,以度灾馑。
康熙帝还注重地方仓储建设,曾下诏寻求仓储建设之良方。河南灾害频繁,民众抵御灾害能力较弱,仓储建设成为灾前预防和灾后赈济的重要手段。清初在明末基础上已逐步建立起常平仓、社仓、义仓等仓储体系,尤以常平仓最要。常平仓仓粮大多为春夏出粜,秋冬收获时还仓。而一旦市价昂贵、民食拮据,则要地方官请求上宪减价平粜或赊米给百姓。崔鸣鷟任偃师知县时,积极建设仓储以备荒年。他认为,“偃民罔知节俭,素乏盖藏。丰稔之时,一年只供一年之用。去岁二麦不登,秋田先旱后涝,以致今春十室九空,称贷无门。有日不举火者,有掘食草根树皮者,村落之人率皆鸠形鹄面,气息奄奄”。加上“兵兴以来,民鲜积蓄,去年夏秋薄收,今春米价涌贵,嗟此孑遗,粒食维艰”,而“集市报称斗米粜银一钱八分,价值之高,数年罕见”。他为此建议平粜仓米,赊于百姓。仓粟米共1500石,正值国用匮乏之时,作为地方官不敢轻易请赈。为此,他主张“散粜仓米以济贫民……请每斗减去二分作价赊于贫民,以接三春而资耕耨”,甚至向上宪提出,“倘宪台或虑收获难定,偿还不前,卑职情愿代民赔补。”
(二)漕粮改折与河务治理
河南属有漕八省,崔鸣鷟任职的偃师县漕运负担严重。据方志记载:
本县正改兑漕米正耗及润耗米,共四千八百八十四石八升二合五勺七抄四撮,每上地一亩米一升九合七抄八撮六圭一粟七粒七颗,价照每石六钱五分折算……原定运米脚价银四百九十二两六分六厘八毫,增添脚价银九百四十三两一钱一分八厘六毫,共脚价银一千四百三十五两一钱八分五厘四毫,在粮驿道留用项下支领。
康熙时期有一定的裁减,“每年正耗漕米四千五百八十八石,额设米价等项共银四千七十两,于康熙十六年奉文每石核减银一钱四分,共节省银六百四十二两,又每石除余银一分,共银四十五两”。可见,清初已经施行用银买米上纳的办法。但折银后盘剥也加重,“除盘剥银六十七两零,润耗米银三百三十五两零,裁解粮道外,实在米价银二千九百余两,仍有囤夫盘剥等项种种,必不可已之费”,故而“粜卖漕米事,乃中州百姓大累”。至康熙十七年(1678),因军需紧急,买米银被充作军饷,故偃师“买米银不足二千两,该买漕米四千五百八十余石,未免拮据”。加之“荒旱薄收,米价涌贵,每石长至一两三四钱不等,较之往年将近三倍,此不敷之银为数甚多。取之于官,官无贴金之术”。此时朝廷要求运本色米,偃师县不得已称贷帮贴,多方凑办。时值春夏大旱,庄稼焦枯,秋螽叠生,食禾害稼,“米价较前更贵,灾重及民,闾间穷困,未有甚于此时者也”。在此情况下,崔鸣鷟恳题漕粮改折以苏民困,请求直接输银。崔氏考虑当时饷银需求下降,且米价上涨,称:“恳请上宪援例具题,痛切入告,将本年漕米改折解银,一转移间,可省中州无穷之财力,上无损于朝廷而下有造于百姓。”虽然漕粮改折未能推行,但偃师县自康熙二十四年(1685)题定改折,基本按崔氏之方案。
除漕运外,河工亦是清初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清初继承明末河工体系,贯彻“治河以保漕”的国策。顺治初,清廷设置河道总督,并于运河沿线的通惠河、北河、南旺、夏镇、中河、南河各设工部管河分司。康熙帝亲政后甚至将三藩、河工、漕务列为三大事。崔鸣鷟治理的仪封县(今兰考县)在清初时河工废弛,决堤频发,难以解决。如康熙初期爆发的蔡家楼决口,“邑地濒河,黄流漫溢,蔡家楼一带尤险,筑遥堤、挑引河,竭蹶工竣,而河患如故”。河工虽有治河专员管理,但实际运作中仍是摊派给所属州县,一县之正印官要负责辖区内的河工事务。河工离不开资金筹措、夫役征派和物料征集,蔡家楼决堤后,仪封缺乏软料,其中最重要的即柳枝。“柳枝不易腐烂,遇水则生”,但由于长期在河工中使用,民柳趋于减少。崔氏初任知县便面临这一难题。详文称:“河势顶冲,洪流溃涯,估计之物,俱已用尽,河主簿呼吁告急,卑职到任未及浃辰,不能为无米之炊,目睹危险,难需时日,是以一面详请一面分派。目今下扫防护所用,俱系详请续派之柳,若非此物,则防御无资,束手待溃。”于是向上宪申请续派柳料。而河道衙门柳料也不充裕,他遂建议暂借民间柳料,等河势平缓,不下埽料之日,设法陆续补还,而“其余剩者,计数存贮工所,以作来岁河工应用,至明春估计分派之时,按数抵数,接算减除,庶民不致重困矣”。于是发动本邑百姓“轮助柳料,以济急用,随派随催,随运随下”。康熙十二年(1673)九月十八日起至十月二十六日止,“共下埽十五个,共用续派大柳一万五千三百七十六束,芟二千四百七十六条,麻五千三百五十斤,椿六十一根”。以仪封之物还之仪封,河工完固,上下安全,也不存在私征伤民之举,“(民众)情愿输助柳料以完……乃阖县士民急公之义,事不相蒙,而诚意感通”。
针对蔡家楼决堤后的柳料不足,虽有民输民助,但并非长久之计。河南巡抚便在沿河之州县有根据工程缓急估计料数的想法。崔鸣鷟建议:“议定估计银两,先行请发委官,坐买柳料,交厂堆放。工急应手抢救,工缓节省存厂。存厂之物应于未烂之先,不拘本境别邑,在于有工之处通融动用,详请开销,庶不致有用之物置无用之物,而浥烂之患可除矣。又如原估之物用尽,而水势仍然泛滥,又须酌量情形,再为采买,以备急需,期于不误河工而止。”如果能将工料灵活通融处理,且年终可以奏销全部经费,即解决官员赔累之苦。而针对设官招商,崔鸣鷟提出,“今仪封无工,且据目前之情形,预料来岁之河势,十四年亦无工……当下无弊无工,事治民安,亦无所用其筹画(划)”。他的建议应更符合本县的具体情况。
(三)驿递经管
驛站是国家公文传递和物资递运的重要渠道。清初继承明制,对驿站颇为重视。然而清初因战事紧张,财政赤字严重,不得不裁减驿站经费。据刘文鹏等研究:“驿站经费大幅裁减主要集中在顺治九年至十四年和康熙平定三藩之乱期间。”至康熙十四年(1675),中央下令将全国各省驿传里马银的40%裁减充当军饷,对接递轿扛夫、接递皂隶和递马工食银也进行了裁减。驿递经费裁减影响了驿站的正常运转,很多省份驿马不足,难以应差。如顺治十二年(1655),户部尚书郎丘指出,湖南驿马不敷,正值军情紧急,应设法筹款买补。因此,清廷陷入了为充饷而裁减驿站经费,且又因军政事务不得不维持驿站运作的两难境地。这使得驿站在州县层面也成为重要政务之一。
河南地处要冲,沟通南北,清初驿站多达119个,根据地理位置和发挥的作用,分为极冲、次冲、稍冲和偏冲4个等级,但随着经费的裁减出现诸多弊端。崔鸣鷟任职的仪封县,“顺治初年,有司以驿站钱粮不敷供亿,遂令里书报户科,派民间养马应差,未及十年,幸邀停止。嗣后马匹喂于官廊,刍粟悉动钱粮,而圉人走卒工食皆于正项支给,同是无民瘠马。”可见清初仪封驿站之窘境。
针对驿站驿马增补问题,崔鸣鷟向上宪禀明详文。他指出:顺治时期仪封县共有24匹马,历经裁革、协济他县、跑伤倒毙等,只留存驿马7匹。而仪封是河工重地,大兵经过,部差至县换马,又成南北通衢。7匹马供东西南北之差,非常困难。同时因“三藩之乱”,“江西告警,大兵进剿,俱用仪封过渡,前站差官传旗背包引路,应用马匹不一而足,以及供兵必需之骑,并时云集东西辐辏南北交驰”。且“仪封南距雎州一百二十公里,北至东明一百二十里,站蹃遥远,行差必牵余马,方能胜任”。如今马少差紧,又历经跑伤倒毙,崔氏不得不将其从原籍(直隶内邱县)赴仪封上任时所带的四匹马入号,顶补行差。他因此请求上宪能增补驿马,以应对繁重的差务。
而驿站的运行除驿马外,尚有扛轿夫,用于招待伺候来往差使。清初仪封设有扛轿夫25名,伺候往来勘合差使,仅足供用。而在康熙时期为节约经费裁减大量扛轿夫的差役,一旦有公务,则采取发银雇觅的办法。但此项办法难以应付大量差使,且扛轿夫“不耕而食,不织而衣,耑以肩上为活计……有差之时,汗血交流,工食止供当下之用。无差之时,如无工食何以糊口”,一旦裁撤,扛轿夫也难以维持生计,故此回应上宪,不宜过多裁撤。
四、结语
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孤本《烹鲜纪略》展示了清初知县崔鸣鷟在河津、仪封、偃师三县的施政作为。所谓“万事胚胎,皆由州县”,历经明清鼎革,正值军兴旁午,百废待兴,清廷如何将施政理念推行至基层,州县可谓最为关键的一环。《烹鲜纪略》的成书背景在康熙八年至十八年间,是清朝从乱到治的关键时期。尤其华北刚经历动荡,明代弊政尚未消除,又恰逢灾荒战乱,治安不力,百废待兴。作为州县官的崔鸣鷟,先恢复生产、清理疆界、严保甲,再兴教化、理风俗、抑制豪强、维护社会治安,促进当地社会秩序重建。一个州县的政务运作,最重要无外乎钱粮和刑名。《烹鲜纪略》记载了有关田赋征收、仓储建设、漕运改折、驿递经管等有关州县财政的重要事务,为清初州县财政的研究提供了生动的例子。当然,书中的判牍案例,也为清初州县案件审判提供了鲜活素材,这有待以后进一步挖掘。
作为父母官的崔鸣鷟虽没有完全独立的施政权,但仍然有着强烈的地方保护意识。在当时军情紧急,财政危机的局势下,维护地方利益的举措执行起来势必会大打折扣,但仍体现出崔氏维护地方利益之意。当然,这也是地方官自身利益的考虑。如果为官不为地方争利,势必会遭到本地各种势力的反对。同时也可以看出,知县的政务运作,受到来自上宪各衙门的掣肘,有些详文常被驳回,更要应对上宪的各种考成。而县域内许多事务的推行也要依赖上宪的指示和地方士绅、百姓的支持。
[作者赵士第(1994年—),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32]
[收稿日期:2023年1月3日]
(责任编辑:李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