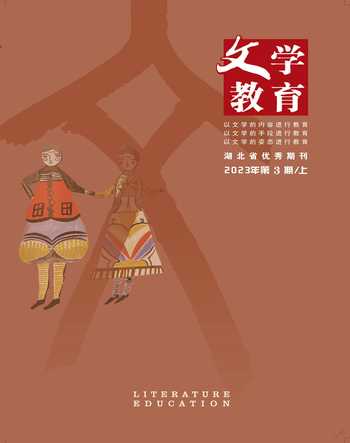孙频小说《丑闻》的女性叙事
2023-05-30廖瑞琳
廖瑞琳
内容摘要:作为女作家的孙频,以其独特的视角进行女性叙事,在《丑闻》这一中篇小说中以其冷峻、细腻的笔触来讲述女性的生存现状和对于女性悲剧命运的分析:寻求自身人生的尊严,以肉体之疼痛献祭苦难之灵魂。
关键词:孙频 《丑闻》 女性 身体叙事 寻求尊严
2008年开始创作的孙频延续了前辈作家对于女性群体生存状态的深切关注,同时也致力于探索女性如何实现成长与自我救赎的问题。作为孙频作品中主要表现对象的女性,始终笼罩在一层孤独而苍凉、隐忍又无奈的矛盾的人生状态之中。孙频以其冷静、细腻的笔触,让读者感受到女性竭力保护的个体尊严一点点泯灭,看着它们在矛盾不甘中又甘愿献出自己的偏执。正如孙频的《丑闻》中揭露了都市底层女性在面对时代和社会的冲突中普遍具有一种的自我妥协性,作者以理性观察着那些执着于他人认同的女性,也冷静的思考着如何为陷入困境中的人寻找救赎之路。
一.身体救赎
文学自诞生之初就与身体紧密联系,“‘身体是一个独特的文学考察视角,作家对人物身体的价值定位和叙写方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其对个体生命与社会关系的认知。”①身体作为叙事的部分,不仅是物质实体,更多的是指暗含多层隐喻的载体,因此身体叙事成为文学创作中所采用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从符号学角度看,身体作为符号文本存在,指向的不仅是符号本身的意義,更多的是作者根据个人和社会经验所赋予的广阔的内容和深刻的领悟,身体成为了“文学性的身体”。身体与性在孙频创作的短篇小说《丑闻》中,不同于《抚摸》中所采用的直白描写,作家更多的是采用了隐形的身体叙事。身体没有被直接的描述,但在全文中却作为一个意指符号存在,意指女性所处生存困境,尤其是缺失的女性主体意识。在《丑闻》中作家通过塑造主人公心理历程的变化展现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村女性在“征服”城市,寻找自身价值的过程中对于身体和精神逐渐丧失掌控权的过程,肉体逐渐独立出去成为了一只庞大的怪物。这也体现了女性难以清晰的认识自己、认同自己,始终沉浸在自卑与无奈中,最终也只能以身体为交换从同为农村人的水管工那儿获得些许安慰。
孙频写身体正应了拉康认为的镜像阶段的婴儿,他们看着镜子中的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和存在,只能将他人眼中的自己看作真实的自己,正如小说中张月如对于自神的认识都来源于他人的参照。当院长挑逗自己时,她认为自己是“姿色当属上乘,大约还有些风情”②,当酒馆老板周小华对她的崇拜退去时,“她甚至看到自己变得胸平腿粗外翻脚。她自己都快要厌恶自己。”②作家通过主人公以身体为代价满足欲望的方式将出身于农村的女性移植到城市的过程中个人被压抑的痛苦具象化,作为以高级知识分子的身份入住城市的张月如在社会压迫和个人欲望驱使下难以摆脱精神的枷锁,最终以出卖身体的方式沦为男性摆布的“他者”。作家想要借助女性身体这面镜子映照出女性对于自我认同的渴望和迷茫。同时也意图去引导读者深思女性以出卖身体拯救困境中自己的悲剧背后所隐含的深层原因,以期共同探寻出一条救赎之路。
二.个体沉沦
福柯认为,身体是一种产品,是在社会的规训和监视下形容出来的。③女性在社会关系中被定义为相较于男性的“第二性”存在,当社会环境与性别双重挤压之下的女性常常陷入伦理困境与灵肉悖论的矛盾中审视自己身体处境时,她们的形象却是借助于他者——男权文化来建构,女性自我的主体性也是外部符号体系一体化和形成的语言自我的集合体,这实际上是女性自我形象的偏离和异化的过程。④在这个过程中,女性往往将男性的眼光内化为自身的标准。在现实社会中,政治经济权力总是以男权为中心,女性以男性存在为前提,依附于男性权威的女性是难以获得自我的认同和主体性的架构,处于“他者”地位的女性常常以自我怀疑、压抑、惩罚的方式获得人生的快感。
孙频笔下的女性执着于内心的需求,不惜陷入异化的状态之中。孙频曾指出,女性在内心深处可能根本没意识到“她们是时刻准备着取悦男人的”。②这一点贯穿在作家创作中,在《丑闻》中,作为高级知识分子身份的张月如,作家却将其塑造为一个边缘性人物,受过教育从女农民成为女博士,有机会落根于大城市,但是又由于思想和文化上的不同在城市中显得格格不入,看似体面的工作但实则是捉襟见肘的生活使得她产生难以消解的自卑,在一边压抑自己内心,而一边又在不断膨胀自己的欲望的过程中产生异化。如何获得想要的尊严是主人公张月如考虑的问题,被压抑着的那种寻求和证明自身存在的欲望发生异化,张月如以身体作为筹码,企图依靠身体获得男性青睐和认同,当身体不能吸引男性时,她自身也将陷入低谷。由院长的即将“宠幸”而产生了薄薄的优越感与认同感,又因院长一夜情后的疏离而陷入自我怀疑的情绪之中,“莫非上床快也是由她的农民出身决定?”②明明厌恶低学历的周小华,而他的崇拜却让“她有了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感觉”②,正如她自己所说“当然她是被遇的那个人,对面走来的是谁并不重要”②,在院长那儿难以获得认同感的羞耻也因为周小华对于女博士身份的崇拜而消解,正如张月如所以为,“他越是急切强烈的想睡她,便越是让她有尊严感,准确的说,便越是让她的肉体有尊严感”②,在这种程度上,张月如认为女性的价值和意义由身体得到彰显,究其实质不过是女性以身体为筹码来获得男性对于自身的认同,女性存在也成为肉体存在,女性也沦成男性的依附品。正如福柯所认为“人体是权力的对象和目标”,而“这种人体是被操纵、塑造、规训的。它服从,配合,变得灵巧、强壮”,即“驯顺的身体”。③到了最后欲望变得极度膨胀想牺牲身体换来更多崇拜却也落空,最终也没有获得个体价值的认可,在生存困境和内心欲望双重挤压之下的身体成为女性存活于男权社会进行欲望交易的工具。
从张月如身上,能看到的不仅是男性对于女性的贬低,表象之下更为深刻的是在男性霸权的长期浸染下所产生的两性之间复杂、隐蔽且稳固的权力关系。作为受害者的女性没有去反抗身体沦为工具的命运,反而沉默的接受了父权所规定的身体认知准则,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逐渐内化了父权文化意识形态使之自动地施加于自身,并通过建立自我审视机制来规训自己的身体和思想,将自我客体化、对象化,致使个体性的丧失。⑤在女性被定义为社会的“他者”的观点之下,男性成为人类社会的代言人,而男性霸权也成为女性的无形束缚,即使女性早已洞悉,却还是自觉被驯服于男权权力意志之下,自觉被建构为男性标准之下的产物。正如张月如深知以身体为代价会带给她的耻辱与恐惧,但还是在社会与性别的压迫下沉溺其中,一方面展露出“男尊女卑”的传统伦理观的侵袭,即便是成为高级知识分子也难以逃脱这种观念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暴露了女性自身存在的弱点,将自身置于弱者的地位,将他人眼光内化为自身标准。
三.何以救赎
正因为“文学是人学”,人的发展也伴随着从身体到精神的多重困境,人们开始孜孜不倦的探讨人生困境的出路,而文学创作想要达成的目标就是为“人”寻找合适定位和独特的价值尊严。作家书写人的生存困境,其实也不过是为人类寻求救赎之路。孙频曾说:“突围与救赎几个字有大而无当的嫌疑,且显得老生常谈。但是我必须承认我几年写作中确实一直在孜孜以求地探索这个命题”。⑥在孙频的作品中我们不难看见其以女性视野对女性生存和精神状况的描写,尤其是对女性生命之疼的表现,所体现的是现代社会物欲追求所导致的灵肉失衡、异化甚至是分离。
在《丑闻》中孙频对于女性生存的探索不同于宏观的去探讨人类困境,而是以一个女性视野挖掘女性内部的精神世界。从张月如的心理活动中能够看出她自己清晰的知道自己对周小华充满着鄙夷,周小华对自己的冷落和自己卑微的乞求也是明白的,她让好友辱骂自己来获得自己心理上的安慰,“女人女人,你快骂我吧,快把我好好骂一顿,把我骂得狗血淋头才好,你就骂我是个贱货”。[1]无论是与院长还是周小华的关系中,作者即使给予张月如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清晰的自我认识,但依旧深陷其中,越是清晰的认识到自身行为的错误性越是具象化表现出女性在面对生存困境时无奈与痛苦,其悲剧意味也更为浓烈,作家想要袒露的女性生存状态与困境也更真实残酷。《丑闻》这部短篇小说中的女性渴求人生尊严,不惜以身体为代价满足灵魂的需求,一边想着获得,但一边又在不断地失去。在这样的过程中,孙频也在不断探索着女性如何自处、如何发现真实的自我,如何获得自身认同。然而女性在承受漫长的被奴役的痛苦后对男权社会即使有了清醒的认识,但她们不得不选择以身体作为主体,以“离经叛道”的形式来反抗,又由于这种反抗仅仅是来自身体的激烈反抗,所以并不能有效的建构起女性自身的价值。《丑闻》的最后张月如也曾忽然发现自己不需要陪伴,准备在绝对寂寞中消化所有的耻辱与恐惧。可是在生命财产受到其他男性威胁的重要关头,她依旧想要为自己的魅力做个测试,以求获得自我的尊严,以身体为赌注在同是农村人的水管工身上来争取些许自我。
由此孙频深知仅仅向读者袒露人生困境是不足够的,如何正视困境又如何走出困境才是创作应当达到的目标,所以孙频在创作中也在试图帮助人们寻找一条救赎之路。在《丑闻》中孙频不仅要描写女性生存困境,还要与读者探讨女性的救赎。在深受陀斯陀耶夫斯基影响之下的孙频采用了复调小说的特点进行创作。正如朱立元先生在《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中解释的,复调小说不存在以作者意识为统一的意识来展开情节、人物命运、形象性格,而是展现出不同的意识世界。如此复调小说主人公意识很少独立存在,往往与其他意识相互依存,意识之间的不断对话也就形成了复调小说的结构。⑦而这种对话被巴赫金概括为两种方式,一是人物之间对话;二是人物自身内心的对话。后一种对话方式又有两种表现形式,自己内心的矛盾冲突和把他人作为内心的一个对立话语进行对话,被称为双声语对话。在《丑闻》这篇小说中主人公张月如内心充满了与自己以及与好友解青燕的双声语对话,这明显的表述在她大量的心理活动之中,常常以自问的形式企图说服自己、挑逗自己。当张月如处于同院长或周小华这些男性之间的暧昧状态时,一面劝解和肯定自己,一面又在内心唾弃和否定自己。同时张月如的世界里也总是塞满解青燕的语言,她同这些言语激烈辩论,这些话语所提出的解决办法与她自己做的决定也大为不同,这样的话语触及人物内心痛处,与其内心意识相互渗透,相互呼应,将其内心活动的轨迹表现在对话之中,也展现在读者面前。作家有意识的透过张月如和解青燕的对话展示不同的思想意识,在两人对话中,睡与被睡这个论点的二元对立关系的背后是对于主体意识的追寻,在张月如偏执的寻求尊严的过程中,二人之间的对话使得作家在小说中塑造解青燕这一角色的意义彰显,从热切的想要寻个男友到最后意识并非真的需要,这或许可以看作是作家对于女性如何获得自身救赎的另一种探讨,从解青燕和张月如的对话由“和男人在一起女人才有存在感”到“其实你要的尊严和我要的陪伴都不过是我们内心的恐惧”②,她所说“好好想想你究竟害怕什么,先看清自己的恐惧才能真正的宽恕自己,不然你一辈子真的就是做奴隶的料了。不是男人的奴隶,而是你自己的”②。解青燕被作者塑造出来的一个冷清客观的旁观者,在女主每一個重要时段都能看到她的身影,她一针见血地告诉张月如“不是你需要和他上床,是你的尊严需要和他上床”②。作品的最后作者留下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局,在整部小说中作家以复调式的结构来讲述于讨论女性的生存与救赎问题,为读者在这一问题上的讨论留下更为观念广阔的空间。
综上所述,孙频的小说落脚于底层人尤其是女性的生存状态,在《丑闻》中以丰富的心理活动塑造出鲜活的女性形象,而这一形象的塑造孙频没有将矛头仅仅指向男权社会,而是回归女性自身,认为女性自身的定位以及对于男性的盲目认同才造成女性最深刻的悲剧。作者赋予主人公张月如的女博士和大学教师的身份,但是为什么作为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女性依然难逃认识和认同自我的困境,这是值得深思的。孙频的创作也并非完美,她在作品中过于执着困境带给人的疼痛,主人公一次又一次出卖自己的身体来换取那些足以证明自己尊严的虚无,即使是结尾部分也使主人公“以身殉道”、以身体为筹码引诱水管工证明自己,获得自身的认同后杀死水管工这样的结局了结全篇,孙频通过一个女人去挖掘女性关于尊严与羞耻的隐秘角落,正如孙频自己所说:“我写尊严和羞耻的时候本身就是在强烈的表达一种渴求,人类的一种基本渴求,就是有尊严地活着。”⑧但是这样的结局充满尖锐的疼痛与绝望。这或许也是孙频的创作缺点,过于执着的用笔来揭露人性的阴暗面而忽略人性中其他品质的存在,执着于写作的快感。尽管她也试图为主人公寻找突围与救赎,但笔下的张月如偏执的以身体为筹码证明自己的魅力与尊严使得这突围与救赎是最终是难以实现。
注 释
①刘传霞.中国当代文学身体政治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②孙频.疼[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
③[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2017.
④金阳平.拉康“镜像理论”探索自画像的自我异化的过程[J].新美术.2015(12):67.
⑤肖巍.身体及其体验:女性主义哲学的探讨[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6):4.
⑥孙频.女性的突围和救赎[J].名作欣赏.2014(25).
⑦朱立元.当代西方文学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08).
⑧孙频.走走.写作的时候,有没有快感很重要[J].野草,2015(5).
参考文献
[1]徐刚.苍凉而卑微的女性叙事—孙频小说论[J].百家评论,2013(2).
[2]马婧.孙频论:人的境况·边缘立场·历史意识——身处历史断裂地带的女性写作.新文学评论.2021(02):13-18.
[3]闫东方.八分之一的冰山——性别话语在孙频创作中的显与隐[J].长江文艺.2022(01):132-134.
[4]孙频.女性的突围和救赎[J].名作欣赏.2014(25)
[5]肖巍.身体及其体验:女性主义哲学的探讨[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6):4.
(作者单位:三峡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