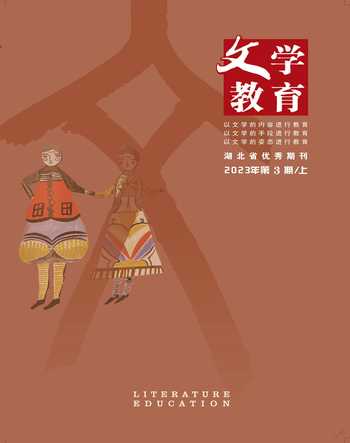论陆游词的用典艺术
2023-05-30韩欣容
韩欣容
内容摘要:词体地位的确立,大约在南渡之后。在南宋词坛上,用典艺术进入词的创作之中,成为南宋词坛词体创作的重要特色。以陆游为例,在其创作的145首词作当中,其中运用典故的词作多达百首。这些典故内容广泛,经史子集无所不涉。陆游的用典方法也灵活多变,有化用、反用、暗用、集用等。深厚的知識积累、江西诗派的影响、词学本身的发展规律以及寄寓现实政治感慨的需要,都是陆词用典艺术产生的原因。而用典的艺术手法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词的内蕴、扩大了词的广度与深度并提高了词的地位。对陆词用典艺术的研究,是我们探索陆游词作思想的必经之路。
关键词:陆游 词 使事用典
陆游作为南宋著名的爱国主义诗人,其诗作数量将近万首,然其词的数量却仅有百首,是诗歌数量的百分之一。由此可见,陆游是致力于诗歌创作,对词则是“用其余力”。“他(陆游)是以作诗的余事来作词的,论创作的态度,他原不及他的朋友辛弃疾那样倾以全副精力。”[1]11然数量的稀少却并未影响其词作的艺术高度。夏承焘在《论陆游词(代序)》中对前人的评价做了系统的阐释:“前人评论陆游词的,明代杨慎说它‘纤丽处似淮海,雄慨处似东坡。毛晋添一句说‘超爽处似稼轩。(毛刊《放翁词》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陆游欲驿骑东坡、淮海之间,‘故奄有其胜?而皆不能造其极。”[1]1前人对陆词的评价,给我们指明了陆词的艺术价值。陆词没有囿于艳情的篱墙之中,而是在词的创作中融入自己的情思与现实生活的感悟。可以说,陆游扩大了词的广度与深度。而陆游在扩大词体的表现范围时,常运用典故。在《放翁词编年笺注》所选的145(含1断句)首词中,133首都运用了典故,其使用典故的概率高达百分之九十。刘克庄《跋刘叔安感秋八词》称:“放翁、稼轩一扫纤艳,不事穿凿,高则高矣,但时时掉书袋,要是一癖。”[2]550这段话虽指出了陆游多典故运用的弊端,但也说明了陆游用典的数量之多。
一.数量统计
陆游博古通今,知识渊博,在典故的引用上经、史、子、集无所不入。笔者依照夏承焘、吴熊和笺注的《放翁词编年笺注》将陆游所引用的相关故事典故出处作了如下统计:《晋书》16次、《太平御览》11次、《后汉书》10次、《诗经》9次、《汉书》8次、《史记》《楚辞》5次、《新唐书》《南史》《搜神后记》《庄子》《唐传奇》4次、《论语》2次、《礼记》《列子》《战国策》《吴越春秋》《侍讲杂记》《拾遗记》1次。除了前代故事的引用,放翁也化用了前人大量的诗句,其中杜甫35次、苏轼11次、杜牧7次、李贺6次、王维5次、李商隐3次。在诗人诗句的引用中,以杜甫的诗句为最多。一方面,陆游师法曾几,而曾几是江西诗派前期的作家。江西诗派所崇尚的“一祖三宗”中的“一祖”,正是具有“诗史”之称的杜甫;另一方面,杜甫经历了唐朝的由盛转衰,在国家动荡不安的时期,他的诗歌多是表达战争的残酷,百姓的流离失所,以及自己救国济世理想的失望。而陆游与杜甫都处在国家动荡不安的时代背景下,尤其是从戎南郑归来之后,理想的破灭,使得陆游对杜甫的诗歌有了切实真切的体验。除了以上诗人,陆游还化用了黄庭坚、欧阳修、柳永、周邦彦、苏辙、张耒等人的诗句。
总而言之,陆词的典故运用在经史子集中均有涉猎,对前人诗句的化用也是博采众家。这不仅显示出陆游深厚的知识积淀,也从侧面说明了陆游将诗歌创作的手法,在无意识中运用到词的创作中来。
二.用典方法
陆游的用典虽然数量众多,但这并不是其词作用的主要特征。陆游用典的妙处在于能够将典故的运用和自己所要表达的思想情感有机的融合在一起,不是简单的堆砌,而是娴熟的驾驭运用。陆游能够运用自如,一方面来源于广博的知识深度,另外一方面是对典故运用方法的灵活使用。
(一)化用其意,若如己出
化用典故可以简单的对原典故增减变换或颠倒字句,也可对典故提炼、熔铸,只保留部分具有代表性的子句。在陆词中,化用典故的例子举不胜举。以其词《蝶恋花》为例:
桐叶晨飘蛩夜语。旅思秋光,黯黯长安路。忽记横戈盘马处。散关清渭应如故。
江海轻舟今已具。一卷兵书,叹息无人付。早信此生终不遇,当年悔草长杨赋。[1]105
这首词是陆游离开南郑后所作。词的上片回忆自己在南郑时金戈铁马的快意生活,下片转而写现在的“闲适”生活,抒发自己壮志未酬的悲愤之情。在词的下片,“江海轻舟今已具”典出苏轼《临江仙》:“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一卷兵书,叹息无人付”典出《史记·留侯世家》,汉代的张良在下邳圯上得一老人赠与《太公兵法》,后辅佐刘邦成就帝业;“早信此生终不遇,当年悔草长杨赋”典出《汉书》卷八十七《扬雄传》,扬雄作《长杨赋》来讽刺汉成帝的背离祖宗和不顾养民之道。在词中,陆游先化用了苏轼的《临江仙》来表明自己想要归隐江湖,但这种归隐并不是积极主动的隐逸,而是面对现实无可奈何之后的选择。陆游没有用转折的词语亦或是十分激烈的表达来给读者表明自己的真实想法,反而将自己的无奈用“一卷兵书”和“长杨赋”这两个典故来隐晦的表达出自己虽有凌云志,苦无报国势的悲愤心理。将自己今日无法报效祖国的悲愤之情和扬雄当年的创作《长扬赋》的无奈心情相融合,看似说扬雄之悲,实则诉自己之苦。
又如《感皇恩》:
小阁倚秋空,下临江渚。漠漠孤云未成雨。数声新雁,回首杜陵何处。壮心心空万里,人谁许!
黄阁紫枢,筑坛开府。莫怕功名欠人做。如今熟计,只有故乡归路。石帆山脚下,菱三亩。[1]96
词的上片,“小阁倚秋空”典出王勃《滕王阁》“滕王高阁临江渚”以及周邦彦《感皇恩》“小阁倚晴空”;“数声新雁,回首杜陵何处”典出杜牧《秋浦道中》“为问寒沙新到雁,来时还下杜陵无?”上片通过景物和典故的结合,追忆昔日,表达出自己想要收复北方,期望国家统一的理想。用“杜陵”代指“长安”,盼望南宋的统治者能从金人的手中收复长安。
词的下片,“筑坛开府”典出《史记·淮阴侯列传》“刘邦设坛拜韩信为大将军”,用韩信的故事点出自己的雄心壮志,自己也想同韩信一样,辅佐君王,功成名就。但自己却没有韩信那样的机遇,能够得到君主的赏识。只有“石帆山脚下,菱三亩”,这是积极的理想找不到出路,被迫要作出消极的归隐之计。故而在词的最后,陆游给自己的归隐生活画出一幅恬淡的图景,出现了一个江南水乡,菱地三亩的乡村景象。
这是陆游离开蜀地,东归之前,感慨壮志未成、欲思归去的词作。在词作中,放翁想要用归隐的方法来解决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上片以景入以情终,下片以情入以景终,情景交融,意境曲折,感慨深沉。
(二)反用其意,推陈出新
反用其意即反其意而用之,即作者心中所思所想与典故所呈现的情思不相一致,乃是相反。《临江仙·离果州作》就是其中的代表:
鸠雨催成新绿,燕泥收尽残红。春光还与美人同。论心空眷眷,分袂却匆匆。
只道真情易写,那知怨句难工。水流云散各西东。半廊花院月,一帽柳桥风。[1]37
词的上片,“眷眷”典出《诗经·小雅·小明》“睠睠怀顾”,《放翁词编年笺注》中注“睠睠”既“眷眷”,这是正用其意。词的上片从景色写入,由抒情结束。从暮春的落红写到自己对春天的眷恋与不舍,感慨春光易逝,故人易去。
词的下片,“只道真情易写,那知怨句难工”典出韩愈《荆潭唱和诗序》“欢愉之词难工,愁楚之音易妙”,这是对昌黎诗句的反用。陆游想通过“怨句难工”来抒发自己不忍分离、不愿分离的痛苦心情。下片由情写入,由景结束。虽然分离是痛苦的,但志在恢复的理想是让人充满希望的,故而陆游在结束时选取了“花院明月、柳桥清风”这一明快的景色作结束。
此词是陆游离开夔州,赶赴南郑的路途中,途径果州而作的一首词。南郑作为当时收复北方的前线,是陆游心向往之的地方,奔赴南郑也就意味着放翁距离自己收复北方的志向更进一步,故而整个词中所表达出来的基调是轻松且充满希望的。
(三)暗用其意,隐晦表达
暗用其意,一“暗”字则表明作者所引用的典故,从表面上不易看出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而是暗含在典故中,必须对其进行一番分析,仔细品味,才能真正理解其用意。如《鹧鸪天》:
懒向青门学种瓜,只将渔钓送年华。双双新燕飞春岸,片片轻鸥落晚沙。
歌缥缈,舻呕哑,酒如清露鲊如花。逢人问道归何处,笑指船儿此是家。[1]26
词中“懒向青门学种瓜”典出《三辅黄图》所载“东陵种瓜”的故事。东陵候种瓜表达的是对安稳生活的追求,陆游化用此典,看似是对隐居生活的向往,但联系词作创作的时间(乾道二年)背景便知,陆游是因免职而被迫归隐。这次的归来是被迫的,是消极被动的,并不是陆游自己积极主动的选择,而是迫于现实的无奈,不得不归家过渔隐生活。倘若我们对此词的创作背景以及陆游当时的创作心态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了解,我们就很有可能被词表面所运用的意象和语言所“蒙蔽”,而忽视了作者所要表达的真实意图。
又譬如《南乡子》:
归梦寄吴樯。水驿江程去路长。想见芳洲初系缆,斜阳,烟树参差认武昌。
愁鬓点新霜。曾是朝衣染御香。重到故乡交旧少,凄凉,却恐他乡胜故乡。[1]103
此词中“重到故乡交旧少,凄凉,却恐他乡胜故乡。”典出杜甫《得舍弟消息》“乱后谁归得,他乡胜故乡”。杜甫在诗中所要阐述的意思是,故乡经过战乱,早已千疮百孔、破败不堪,想归去却不得,不如在他乡暂且安身,是对已经发生事件的权衡比较;而陆游词中所阐释的意思是久别故乡,不知故乡是否早已物是人非,故友是否还在?故居是否完好?是对未来的深深担忧。虽然语句相同,但是旨趣不同,用“却恐”二字,表达出作者对回到故乡后的担忧,未来的不确定使得陆游产生了逃避心理,发出“他乡胜故乡”的感慨。亦属于暗用的一种。
(四)善于集结,巧于裁剪
集句为词即截取前人诗文单句,为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而拼接成篇,是艺术的再创造。虽然所集之句均来自前人之作,但若能使新作之词能够浑然一体、妙和无痕、情思连续,也能成为上等之作,让人耳目为之一新。只有达到这种程度,集句为词才算得上是一种艺术的再创造,不然只能视为百补破衲了。然而,若想作出集句佳作,并非易事。作者须博闻强记,涉猎广泛,且善于剪裁,巧于连缀。譬如《木兰花慢》一词:
阅邯郸梦境,叹绿鬓、早霜侵。奈华岳烧丹,青溪看鹤,尚负初心。年来向浊世里,悟真诠秘诀绝幽深。养就金芝九畹,种成琪树千林。
星坛夜学步虚吟。露冷透瑶簪。对翠凤披云,青鸾逆月,宫阙萧森。琅函一封奏罢,自钧天帝所有知音。却过蓬壶啸傲,世间岁月骎骎。[1]59
在此首词作中,“悟真诠秘诀绝幽深”典出《南史》卷七十六《陶弘景传》;“金芝”典出《晋代》王嘉所著《拾遗记》卷十;“九畹”典出屈原《离骚》:“余既滋兰木九畹兮”;“琪树”典出孙绰《游天台山赋》:“建木灭景于千寻,琪树璀璨而垂珠”;“星坛夜学步虚吟”典出刘敬叔《異苑》:“陈思王游山,忽闻空里诵经声,清远遒亮,解音者则而写之,为神仙声。道士效之,作步虚声也。”;“自钧天帝所有知音”典出《吕氏春秋·有始》以及《史记》卷四十三《赵世家》。在短短的一篇词中,竟有六个典故,真乃“掉书袋”也。虽然典故密集,但丝毫没有文字堆砌、生硬之感。反而将典故原有的深意与所作新词的情思熔铸在一起。其词可谓清新流畅,圆美流转如弹丸。
三.用典原因探微
(一)博古通今、厚积薄发
首先,宋朝实行重文抑武的国策,不仅宋太宗时期有兴文抑武的明确记载,民间广为流传的启蒙读物中也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3]74-76这样的词句。因此宋朝的士大夫多博览群书,通晓古今,具有极高的文学和艺术修养。陆游在其诗《老病追怀壮岁读书之乐作短歌》中写道:“少年志力强,文史富三冬;但喜寒夜永,那知睡味浓。”[4]1548又如在《示友》中所提及:“黃卷青灯自幼童。”[4]2806由此可见,陆游具有深厚的文学功底。而其词作中所引用典故出处之多,数量之大,不也正说明了陆游的博览群书、博闻强识么?而其深厚的文学功底不仅来自社会大势的影响,还源于家风的传承与自己勤耕不缀的努力。其次,印刷术的成熟和刻印技术的精进使得书籍的传播速度加快,学习成本降低。来新夏在《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指出:“(南宋)经史子集各类图书,中央及各地地方政权、教育系统、民间、私人、书商、坊贾,无不刻印。”[5]231图书的大量刻印使得更多的知识分子可以接触到图书资料。文人士大夫有了更多的学习材料和精力,这就使得士大夫能更好的阅读、思考前人的著作,进而进行借鉴学习,并在词中用典故的方式表达出来。
(二)江西诗派、潜濡默被
陆游师法曾几,曾几师法韩驹,韩驹又是江西诗派的前期作家,因此,江西诗派的理论贯彻了陆游文学创作的生命。江西诗派的“一祖”杜甫,就是陆游词中化用诗句最多的诗人;而江西诗派所主张的“点铁成金”“夺胎换骨”“无一字无来历”的创作主张也在放翁的词中得到具体的体现。陆游不仅用典数量多,而且用典的种类也繁多,经、史、子、集均有涉及。这不能不说明陆游受到曾几的影响之深。朱东润在其文章《陆游的创作道路》中指出“把陆游初学作诗之年和初识曾几之年纽在一处,我们可以看到曾几对于陆游的创作道路起了何等重大的影响。”[6]295而这种影响的深远,不仅体现在他的诗歌上,还体现在他以“余力”创作的小词上。
(三)词体流变、顺应规律
词作为一种文学体式,一开始是流传于民间的通俗文学样式,随着文人的加工和规范,词的语言也从通俗化逐渐走向典雅化。“词体地位的正式确立得到普遍认同,约始于南渡前后。”[7]141词体地位的确定,就将词从诗歌的附庸品中解脱出来。词不再仅仅局限于《花间集》词人们描写女性的娱情之作,而是从儿女柔情的藩篱中解放出来,走向更为广阔的天地。陆游在《诉衷情》中所表现的这种:“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1]124的豪情壮志,也成为词所描写的对象。词开始成为“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的陶写之具。[8]108其次,由于沈佺期、宋之问对声律规则的建构和发展,加上唐代“诗赋取士”的规定,在无形中将诗人对声律的规范使用重视起来,这为诗人创作曲调严明的词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词学本身的发展规律以及词体地位的提高,使得士大夫改变了对词作的创作态度。而声律的成熟又使得他们在创作中容易上手。因此,原来“诗词有别”的格局被打破,诗与词都成为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奇葩。
(四)曲笔达意、借古言怀
词发展至南宋,词家彼此讲究比兴寄托的手法,词人常借典故寄托自己的抑郁和悲愤,比兴寄托和典故有相通之处,也是放翁词用典较多的原因之一。之所以如此,这与他所处的时代有着密切关系。南宋王朝偏安一隅,苟且偷生。朝廷权贵,贪生怕死,享乐颓废而不关心国家政局。作为主战派的陆游遭到朝廷的冷落,不能收复失地的痛苦时时刻刻萦绕在他的心头。面对复杂的政治形势,士大夫们多缄默不语。自然,作为抒情的词作,也不得不委婉含蓄,曲笔达意,借古托今。保留了词体“要眇宜修”[9]226的品质。这就使得词中多借用古人、古事,多用典故了。
四.用典的作用
第一,用典艺术增加词的风雅特性,提高了词体的地位。唐宋词配合的主要音乐是燕乐。取名燕乐(亦作 乐、宴乐),因为它是宴享之乐。[10]4-6因此,唐宋词的出现是带有一定娱乐性情的意味。如康正果所言:“由于受到娱乐性音乐的限制,词这种新型的抒情诗从一开始便走上了‘词为艳科的道路。”[11]250这就使得词这种文体的地位,在最开始的时候就处于下风。这种所谓“低下”的出身,使得文人士大夫们都对词抱有一种偏见,而这种偏见首先反映在对词的称呼上,即将其称为“曲子词”“小词”“诗余”等。词为“诗余”的观念历代屡攻不破,它已经成为士大夫文人积淀日久的深层意识。[12]7在创作题材的选取上,均是囿于“美女歌妓”“宴会享乐”的藩篱之中。直到苏轼横刀跃马,踏上词坛,“指出向上一路”之后。人们对于词的描写范围才从“艳情”转向“真情”。而用典的出现,就是用“言志”的诗歌技巧来创作“娱情”的词曲之作,从侧面反映出文人士大夫在潜意识中逐步提高了对词的创作兴趣,词曲的创作不再是局限于歌儿舞女的宴席之作,而是开始融入作者的情思,词的境界开始提高,内蕴逐步丰富。词不再是明白晓畅的“白话”语言,而是具有了诗歌性质的言志抒怀之作。第二,用典的使用让词跳出“歌儿舞女”的藩篱之中,去除词体的浮艳之风,增加了词的厚重感,扩大其内蕴。相较于诗歌而言,词的创作因音律曲法的影响进而受到更多的“限制”。一方面,乐曲的流行为词的发展提供了摇篮;另一方面,其乐曲曲度、节拍、音律的多姿多彩,又使词体形成了“调有定句、句有定字、字有定声”的特点。[12]7词的创作就像是带着镣铐跳舞的歌女,如何在“方圆”之中既做到合乎规矩,又做到意义层次丰富多变?如何在有限的字数中传达无限的内蕴?这就需要化用前人的诗句和故事,以达到以有限的字数表达无限的韵味。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写:“文学家用古事以达今意,后世谓之用典,实乃修辞之法,所以使言简意赅也。”[13]144用典的作用就是在规定的范围和方圆之中,尽可能多层次、具象化的表达出作者的愁绪情思,让读者从固定的文本中,读出不同的感受与体验。而陆词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品之一,对陆游词作的赏析,有助于我们对词作的发展脉络进行全面的梳理归纳,同时亦是我们打开陆游思想世界的一把钥匙。
参考文献
[1]陆游著.夏承焘,吴熊和笺注.放翁词编年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2]孙克强.唐宋人词话[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1999.
[3]汪洙.神童诗[M].济南:齐鲁出版社,1998.
[4]钱仲联.剑南诗稿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5]来新夏.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6]朱东润.陆游的创作道路[C].中国文学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
[7]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8]刘熙载.艺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9]王國维.人间词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
[10]吴熊和.唐宋词通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11]康正果.风骚与艳情[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12]方智范.中国词学批评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13]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文心雕校[M].北京:中华书局,1962.
基金项目:陕西理工大学人文学院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RWXYCX2201),项目名称:陆游词典型意象及典故研究。
(作者单位:陕西理工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