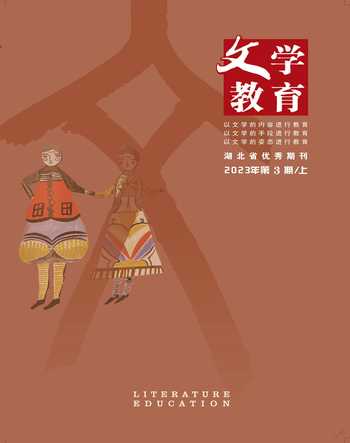拉康镜像阶段观照下《搏击俱乐部》的无我困境
2023-05-30韩星鹭
韩星鹭
内容摘要:恰克·帕拉尼克小说《搏击俱乐部》是其首部出版的长篇小说,其内容体现了对后现代社会中人的精神危机的思考。小说通过主人公创办搏击俱乐部前后的自述,叙述主人公与其分裂人格从合为一体到最终被替代的过程。从拉康镜像阶段理论来解读,这一过程正是在镜像阶段人们认识自我的过程,即由将镜像中的他者认同为自我,继而因对镜像的模仿而丧失自我,最终导致争夺自我控制权的异化结局,寓意着自我主体被镜像剥夺主体性的无我困境。
关键词:镜像阶段 恰克·帕拉尼克 《搏击俱乐部》 自我主体
雅克·拉康(1901-1983)是二十世纪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其于1936年在马林巴德举行的第十四届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年会上提出镜像阶段理论,并将之变迁为《助成“我”的功能形成的镜子阶段》一文选入其著作集中。拉康以6至18个月大的婴儿来阐释镜像阶段,当婴儿意识到镜子中的镜像就是自己时,会形成“我”的概念,并认为这是别人眼中的自己。在镜像阶段的发展过程中,自我与镜像的这种二元关系是建立在想象的基础上的,自我先接受视觉上带来统一性的镜像,按镜像的标准约束自己的言行,逐渐对完美镜像新生嫉妒或崇拜,其结果反被夺取自我。在文学界,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有相当程度的影响。随着工业化社会集约程度的提高,物质得到极大丰富的同时,与之共生的规矩与压力也形成了对都市人个性的极大约束,都市人在面临自我定位困境时的挣扎和迷茫成为后现代主义小说所喜爱的题材。
恰克·帕拉尼克(1962-)是美国当代后现代主义小说家,《搏击俱乐部》(1996)是其首部出版的长篇小说,并于次年获年度“西北太平洋书商奖”和俄勒冈最佳小说奖,为其自称为“犯罪小说”的一系列作品拉开了序幕。这些作品通常以被社会边缘化的人物作为第一人称,“使用极短的段落和句子,充满波普文化的指涉以及针对现状而发的玩世不恭的俏皮话”[1]237,表现出对物质主义肆虐的消费时代一种自毁倾向的抗击。《搏击俱乐部》以碎片化、失序化、解构深度与历史感的形式,记述了美国年轻白领、产品召回事物协调员乔与其因失眠症而产生的分裂人格泰勒之间一场关于自我认同及归属的博弈。本文运用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以小说《搏击俱乐部》为例,分析该小说通过分裂人格这一载体,探讨后现代语境下的年轻人从意识到自我的不确定性、自我被镜像所消解直至试图夺回自我的过程,以及镜像阶段中主体、镜像、自我三者的关系在其中的影响和体现。
一.亲近他者,认同自我
根据拉康的观点,自我诞生于人们从镜像中看到自己并从中认出自己的时刻。小说《搏击俱乐部》的主人公乔和泰勒·德顿本来应该是毫无交集的两个人,因为在沙滩上一次偶然的交谈而相识,按常理说,两者的缘分也应该就是这样擦肩而过。而事实是当乔的高档住宅因煤气泄漏被炸毁,其赖以标识其独特个性的所有物品瞬间毁灭,乔顷刻间一无所有时,他第一时间拨通了仅一面之交的泰勒·德顿的电话。伴随着电话铃的震响,乔想象着电话铃在泰勒租的造纸街上的房子里响起的画面,不断在心中默念“哦,泰勒,救救我吧……把我从瑞典家具中救出来。把我从聪明过头的艺术中救出来。”[1]44
这一看似不合常理的行为,对于乔来说却有其内在的合理性。此时的乔,生活枯燥泛味,没有爱情,也没有事业上的追求。如门房俯身在他肩膀上所说,“有很多年轻人不知道他们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年轻人,他们觉得他们想要这整个世界”。[1]44乔正是这样一个年轻人,正因为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故而即使花大量金钱和心血购置了一屋子高档家具,对自己来说,其实只是一大堆自己不想要的东西。当一切外在的物品都损毁后,乔并没有体现出因财富损失而造成的伤痛,他的忧伤更多的是对自我存在的担忧,并对自己曾经的对于以高档住宅为代表的完整性的追求在内心深处提出了质疑:“但愿我永不得完整。但愿我永不得满足。但愿我永不得完满。救救我,泰勒,把我从力求完满和完整中救出来。”[1]44。当联系上素昧平生的泰勒后,乔像久未谋面的老友那样放肆倾诉,并搬去跟他同住。这种莫名的亲近行为是乔已经逐渐将泰勒当做自我的镜像,并从一言一行上效仿泰勒的开始,尽管乔自身还不一定意识到。
在泰勒出现之前,乔没有亲人,没有朋友,只是都市中孤独生存的普罗大众之一员,面对繁重而又乏味的工作,沉迷消费而被消费品所控制,找不到自我的定位和存在的价值,这就为其分裂出第二人格创造了条件。拉康认为,“镜子阶段的功能就是意象功能的一个殊例。这个功能在于建立起机体与它的实体之间的关系,或者如人们所说的,建立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之间的关系”[2]86,“在这个模式中,我突进成一种首要的形式。以后,在与他人的认同过程的辩证关系中,我才客观化”[2]84。乔对泰勒无来由的亲近,正是由于他在无意识间将泰勒视作镜中之像,视作向往却不可企及、为其深陷物质主义的困境指明出路的、作为“所有次生认同过程的根源”的“理想我”[2]84。一种不被承认的、初次“获致镜中身躯形象的欢悦”在乔与泰勒的第一次照面中产生。当乔永无餍足地购买品牌家具,试图用一生的时间买齐装备,达成一种物质生活上的完美體验,泰勒以五根竖立的木头在沙滩上投下的巨掌影子告诉他,“一分钟的完美值得上你付出的努力。对于完美,你能期望的最多也就那么一瞬。”[1]28泰勒在无形间从内部打碎了乔的自我认知形象,并以一种相似,却又具备超越性的形态呈现在乔的眼前,将主体与镜像间的战火延续至乔今后人生中每一个自视的时刻。泰勒凭借亲身实践为乔绘制了一幅人与物和谐共生的蓝图。面对一个人类在支配物的同时饱受物的奴役、充斥着尖锐对抗与冷漠疏离的社会,乔迫切需要从泰勒身上寻得逃避异化的方法,他意识到过去的自我被捆绑于物质的表层之上,认为“那就是我整个的人生。所有的一切,那些灯具,那些椅子,那些地毯就是我。餐具橱里的那些盘子就是我。那些植物就是我。那台电视就是我。被炸了个干净的就是我。”[1]118然而那不过是一片易碎、不可倚靠的幻景,一场爆破便能让整个人生化作灰烬。
泰勒则相反,他住在造纸厂仓库旁的无主废屋中,没有固定工作,不受消费链条所牵绊。同时,他以自己的方式抗击着消费社会既定秩序:作为电影放映协会的放映员,他将单帧色情胶片接到宠物历险片中;作为市中心一家酒店的正式宴会侍应,他在浓汤中加入排泄物佐料。乔长久的压抑因泰勒的放纵打开了一个窗口,他逐步舍弃房屋、舍弃工作、舍弃一种约定俗成的规约,在对泰勒的效法与认同的过程中获益,委身于镜中之像的魔影,甘愿受其蛊惑。于是随着模仿行为的升级,乔逐渐将与己有别的他者误认为是内在的、对等同一的形象,将不确定的自我附着于他者的意志之上,不仅未能意识到泰勒仅仅是自己初始人格因失眠症分裂出的一个欲望投射,未能觉察到二者因镜像的对称属性而天然相隔的鸿沟,反以泰勒为中心将一切合理化,自此踏上自我疏离的单行道。
通过与泰勒的共生,乔的自我不再受缚于零碎的身体经验,亦或虚无的社会符号,而是被建构为一个完整的塑像、一抹永恒的幻影。正如拉康在《助成“我”的功能形成的镜子阶段》中所言,镜子阶段“对于受空间确认诱惑的主体来说,它策动了从身体的残缺形象到我们称之为整体的矫形形式的种种狂想。”[2]87主体在镜中被整合,构成自恋的具体化形态,由此在自我与镜像之间生发出一种爱欲式的关联。然而,这段关系中含有侵凌性的成分,即鸠占鹊巢的隐患。乔虽对此有所预感,“有句老话,说的是你总是杀死你爱的东西,其实,这话反过来说也成。确实,你也总是被你爱的东西杀死。”[1]205但他仍旧沉湎其中,并未意识到,占据其理想位置,填满这缺失裂口的终究是一个非我之物,而此时主体却在其“伪我”的外表下轻易卸除防备,将其误认为自己的真在,导致真正的自我与之疏离,被镜像暗中摄取了主人性,已不在此处。如福原泰平在《拉康:镜像阶段》中所描述的,“作为自我的东西的形象中出现在我们面前,它具有镜像这一想像的底图,在主体还没有注意到它时夺走了我们的本质。换言之,自我就是在形象中呈现出来的外观华丽的令本人称心的假面,它将时空固定在那里,作为在想像中呈现出来的东西,具有浓厚的呈现价值。因此,它与神经病的症状相同,像假面一样显示出无言的向心力,默默地显示自身,什么也不肯说。”[3]51
二.嫉妒他者,丧失自我
拉康指出,“我的形成是以一个营垒甚至一个竞技场来象征的。从内场到边墙及外缘的碎石地和沼泽,这个竞技场划分成斗争的两个阵营,主体在那儿陷在争夺遥远而高耸的内心城堡的斗争中”[2]87-88。自我借助镜像的反射作用而生成,必然是一个“依赖而非独立的建构”[4]63。但同时,自我亦是一种误认的功能,一种想象的功能,使得破碎的主体在镜中照见完整,并维持着主人性可以被占有的幻象。为此主体不得不通过长久持续的争斗,一次次将其从镜像的阵营暂时性地拉扯过来,自我却“只能以渐近线的方式重新加入到主体的生成中,而不能与之完全同一”[4]63。
就乔而言,这场自我争夺战的枪声自其与泰勒创办搏击俱乐部的一刻起便已打响,并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为了更多地了解其自身,乔与泰勒一同将这个地下俱乐部创立起来。搏击俱乐部是一个没有利益,没有竞技的场域,有的只是“被历史忽略”[1]184、远离战争、信仰与英雄主义、追求物质享受的一代年轻人从压抑匮乏的生活中暂时挣脱,在肉搏的疼痛里获取自身存在的体验。“搏击俱乐部就像教堂里一样有各种语言歇斯底里的喊叫,星期天一觉醒来,你会觉得自己得救了。”[1]52乔在身体的破损中感受真实,感受自我,被泰勒身上强烈的自我毁灭倾向所吸引,认为“当时,我的生活看起来真是有点太完满了,或许我们一定得把一切都打破,才能把我们自身中一些更好的东西给逼出来”[1]53,由此在与镜像无限趋近的道路上愈行愈远,甚至为没能争到泰勒的注意而感到“激愤、燃烧的受挫感”[1]61,自觉“在这个世界上跟泰勒比起来我一钱不值”[1]159,于是逐渐抛弃工作,疏离理性、秩序与精英主义,转而投身于一种泰勒式的野蛮。
然而,正如主体与镜像始终不可能获取完全的同一性,乔与泰勒的意志始终存在分歧。乔的成长轨迹与泰勒截然不同,所接受的教育也完全不一样,更不用说两者在事业上的差异。对于乔来说,循规蹈矩是他一直以来的生活原则,他对现实处境虽然困闷但却从不敢表露出来,刻意地追求精致生活也只是他内心空虚的释放。当和泰勒在一起后,他能体验从未尝试过的无拘无束自由酣畅的感觉,可以做出连自己都觉得疯狂的行为,以自己貌似失去理性的行为去反抗社会对他的边缘化,但这一切都是在一个理智的框架内的。泰勒则不一样,他不是以一个真实的社会人的形象出现,而是乔内心深处不受控制的欲念的实施者,必然会突破乔的理性窠臼。泰勒将所有的法律、道德、秩序的规约都视同无物,其行为会伴随着乔的纵容而肆无忌惮,就像一枚出膛的炮弹,其飞行轨迹和最终会造成的损害已不受控制。
如果说乔的反抗是一种有道德的、有原则、以不危害他人生命为底线的叛逆,那么泰勒的反抗便是一种非原则化的、不惜以他人为牺牲品的狂欢,他们注定渐行渐远。当泰勒用碱液在乔手上烙下象征“沉到底”[1]81的疤痕,乔感到“附着在泰勒那个吻痕上的碱是一堆篝火,是烙铁或是原子反应堆在我手背上烧灼,感觉上却像在距我几英里远的长路尽头。泰勒要我回来跟他并肩一道。我的手却在离去,越来越小,在长路尽头的地平线上”[1]78。随着二者之间的差异性不断增加,乔察觉通过搏击俱乐部这一蛛丝般的秘密网路,泰勒早已在将触手延伸至自己所不可知的更遥远、更辽阔的疆域,将俱乐部成员发展为一个以“全面并且马上摧毁文明”为目标,自称“破坏工程”[1]135的组织,且泰勒成为了所有成员眼中的传奇,而乔却被消影于无形,“我是乔伤透了的心,因为泰勒把我甩了”[1]146。
此时,乔的存在被这一镜像切实地抽离,自我被彻底剥落了主人性,沦为一具本质虚无的空壳。不知不覺间,泰勒的意志已深入乔的内部,“我嘴里冒出来的都是泰勒的话。我是泰勒的嘴巴。我是泰勒的双手”[1]171,但这并非乔所预想的恢复或找回自我,相反,这是一种来自外部的、充斥着尖锐对立的入侵。镜像哗地拉开竞技场的帷幕,显示出破坏性的本质及足以凌驾于主体的力量,劫持了自我,彻底背叛了主体的信任。然而,乔拒绝接受失势的真相,坚持解释“这都是梦。泰勒是一种心理投射。他是一种分裂性人格违常。一种精神性神游状态。泰勒.德顿是我的幻觉。”[1]185,盲目地自我安慰道,“是先有了我”[1]185。在乔的纵容下,泰勒以难以想象的速度扩张了破坏工程的领土,“在一百个城市,搏击俱乐部在没有我的情况下照常运行”[1]199,而乔过早放弃了抵抗,任凭泰勒恣意行动,无形间交出自治权。在拉康的观点中,“主体这时也不能说自己最亲近的人是外部的人。主体确认自己为外部的他者的像会将自己暴露在无的危险下,但顽固地不承认这一点,也就迷失了自己的本质”[3]47。
三.击败他者,异化自我
泰勒是乔自己创造出来的人物,是受其欲望驱使而分裂出的第二人格,他所表现出来的神秘、暴力、反叛、自由与激进等个性特质正是本体“想摧毁物欲世界去寻找理想中的精神世界”[5]的欲望体现。乔对现实世界是失望的,泰勒的价值观反映了这一代人的精神危机——“我们这一代并没有一次大战,或是大萧条,不过我们却有一次精神上的大战。我们有一次反对当今文化的大革命。这次大萧条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拥有一次精神上的大萧条。”[1]164乔精神空虚重度失眠,是泰勒将他从病态的追求完满中拯救出来,从搏击中体会到胜利的快乐;乔对老板唯唯诺诺言听计从,是泰勒让他体验了领导的滋味;乔按部就班循规蹈矩,是泰勒教唆他在暴力与破坏中宣泄压抑的情绪,这一切都是乔“想要泰勒”[1]7的理由。
当乔逐渐对搏击丧失兴奋感时,泰勒曾询问他在殴斗时真正打的是什么,乔则不加掩饰地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想法。他想“摧毁一切从未归我所有的美好事物”,“想让整个世界万劫不复”,“想把这个世界炸毁,使它不再受到历史的束缚”。[1]133在此之后,一切都有了质的变化,泰勒发明了破坏工程,成员们的相互斗毆已不能满足泰勒日益膨胀的胃口。在破坏工程的突击委员会,每个人通过抽签的方式被派遣每周的任务。这些任务往往以恶作剧的形式体现,且超越法律的羁跘,构成一幅无政府而有组织的混乱画面。乔一时的口舌之快一步步变为现实,他和泰勒的搏击俱乐部在危险的道路上越滑越远。
但是,乔终究还是个理性的人,当泰勒的行为越来越过激,越来越不受控制,这违背了乔的原则性,也让乔意识到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这个世界发了狂。我老板死了。我的家没了。我的工作没了。而我要为这一切负责。”[1]214不管实施起来有多难,乔都不能放任泰勒夺去自我,必须制止泰勒的暴行。
拉康在《精神分析中的侵凌性》一文中指出,“产生那个被人称之为自我的那个情感组织的活力和形式的就是个人自定于一个将自己异化的形象的情欲关系。”[2]103-104当自我将一个使自己异化的形象放置在“理想我”之位的同时,主体与他者之间紧绷的关系也由此转向了内部,在自恋与侵凌性如同一枚硬币“正反的两面”[6]413的矛盾作用下,形成一种兼有情欲与敌对的内在张力。“这个张力决定了他对别人欲望的对象生发出欲望来。在这儿,原始的协力迅速演变成侵凌性的竞争,从这个竞争产生了别人、自我和对象这个三元组。”[2]104
这一形式呈现在乔与泰勒之间一场主体为从镜像处夺回被掠去的自我而赌上性命的决斗中。在乔反复的询问中,他发现,在搏击俱乐部的成员口中,泰勒消失了,甚至连是否存在过都成了疑问。乔意识到泰勒是其分裂人格,一对矛盾的共同体,白天由乔做主,夜晚由泰勒接手,然而主人格并未在主导权上抢占任何优势,由于长久以来的放任,分裂人格已足够强大,反将主人格打回到自我残缺的原形,近乎顶替主人格的存在,认为“没准儿你是我精神分裂产生的幻觉呢”[1]185,并提出公平竞争,“看看最后剩下的是谁”[1]186。
“自我认同所固有的侵凌性使主体既不能容忍体现了理想自我的他人,这种他人比自己优越,也不能容忍将自己视为理想自我的他人,这种他人比自己低劣;尽管他非常珍惜自己的生命,但为了获得确定不移、完满自足的自我意识,他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去斗争。”[7]73正如马元龙在《雅克·拉康:语言维度中的精神分析》一书中阐释的,拉康认为,主体的自我认同内在固有一种“死不足惜”的侵凌本能。小说中乔最终采取了一种死不足惜的极端方式,把枪抵在面颊内侧扣动扳机,使泰勒误以为自己必死,从而以自杀的方式杀死了泰勒。
小说的结局中,乔依然活着,破坏工程的成员将他藏了起来,为他提供治疗与照顾,对他表示怀念,期待他的回归,一切仍然按照他所安排的计划进行着。乔虽然杀死了泰勒,但也注定无法回归社会,回归过去的生活。从双重人格的角度来说,乔杀死了一个不听话的泰勒,以后可能创造出一个更听话的泰勒;也可以说,乔异化成了泰勒,乔取代了泰勒,将自己活成了泰勒,因为他人的期待逼迫乔成为泰勒,也因为乔根本不想回去,不想回到那个生不如死的真实人生。在恰克·帕拉尼克的笔下,主人公乔是都市中挣扎生存的芸芸众生的一个缩影,连名字都是那么简单平凡而易于被忘却,正如自我在镜像阶段的构建过程,在主体与他者的认同和反抗中,无法寻回自我的主体终究将自己异化成了镜像,被镜像剥夺主体性而陷入无我困境。
参考文献
[1]恰克·帕拉尼克.搏击俱乐部[M].冯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2]雅克·拉康.拉康选集[M].褚孝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3]福原泰平.拉康:镜像阶段[M].王小峰,李濯凡译.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4]严泽胜.穿越我思的幻象:拉康主体性理论及其当代效应[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
[5]姚伦燚.寻找另一个自己——从《搏击俱乐部》说开去[J].戏剧之家,2018(35):72-74.
[6]吴琼.雅克·拉康:阅读你的症状(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7]马元龙.雅克·拉康:语言维度中的精神分析[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
课题项目:本论文属于广东省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语用与翻译”(编号:2022SFKC044)的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