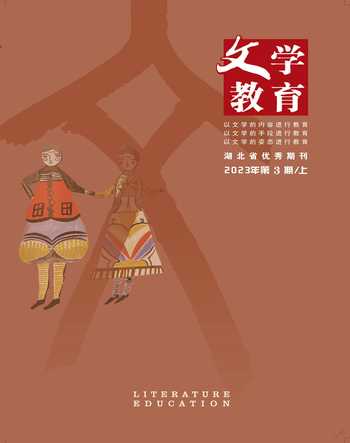《幽灵旅伴》中黑色欧洲史的重构
2023-05-30刘晓蔓
刘晓蔓
内容摘要:英国当代小说家伯纳丁·埃瓦雷斯托于2005年创作的第三部小说《幽灵旅伴》是对白色欧洲神话的颠覆与对黑色欧洲史的重构。作者在小说中通过再现欧洲早期非洲旅居者的幽灵重现了被主流历史掩盖的黑人痕迹,颠覆了欧洲历史的“白色神话”,重新建构了欧洲大陆上的黑色存在史。历史决定着记忆,记忆构建着历史,本文将历史与记忆结合起来以文化记忆为切入点,从欧洲宫廷史、奴隶史和艺术史三方面探讨了对欧洲历史的重构,解决了当代英国黑人移民缺失的民族归属感,体现了作者对边缘群体和被遗忘群体深切的人文关怀。
关键词:伯纳丁·埃瓦雷斯托 《幽灵旅伴》 文化记忆 黑色欧洲史
英国当代黑人女作家伯纳丁·埃瓦雷斯托(Bernardine Evaristo)于2005年出版了一部散文间或诗歌的小说《幽灵旅伴》,该小说以20世纪80年代为背景,讲述了加勒比英国裔在伦敦从事金融行业的斯坦利(Stanley)和来自利兹的加纳裔英国爵士歌手杰西(Jessie)因为一场意外而开启的穿越欧洲之旅。随着旅途的开始,斯坦利一路上见证了欧洲大陆上飘荡着的黑人幽灵,并且与他们展开对话,揭开了尘封在历史的尘土中的黑人历史。该小说是埃瓦雷斯托所有小说中唯一一本在国内有中文译本的作品。该小说一经出版就引起了学界的广泛讨论,Karen hooper称这部小说为“通向落满灰尘的欧洲档案馆之旅”(Hooper,2006:3)。Jennifer guitar也将这部小说描述为“诗歌和小说的混合体,探索者着欧洲幽灵般的黑人历史”(Gustar,2015:433) 国内最早研究《幽灵旅伴》的王卉教授则将目光放在了小说中最具代表性的英国黑人形象——“黑女士”身上,不仅从女性主义角度讨论了女性被物化和异化等问题,还从民族角度深入分析了民族归属感问题。埃瓦雷斯托通过《幽灵旅伴》的创作重新将散落的历史碎片拼凑了起来,重现了黑人在历史上留下的足迹和印记,拼凑了一幅完整的历史图景。
目前,不少学者都关注到了该小说诗歌间或散文的写作手法以及身份和家园等主题,但是从文化记忆理论为出发点对小说中黑色欧洲史的重构问题谈及的还较少。法国著名社会主义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是记忆研究领域最重要的学者之一,他在1925年发表的《记忆的社会框架》一直“探索着个人活动和社会历史之间的辩证关系”(Apfelbaum,2010:80),开启了不同于弗洛伊德和荣格仅停留在个体层面的“集体记忆”研究。哈布瓦赫将记忆研究从狭小的心理学中解放出来,还将记忆分为“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高萍认为哈布瓦赫这种对生理主义和个体主义的反思和扬弃,是哈布瓦赫集体记忆研究的起点(高萍,2011:112)。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在哈布瓦赫的研究上进一步发展,重点提出了记忆转换的载体“记忆场”(sites of memory)的概念,他将“记忆”和传统的历史联系在了一起,是对哈布瓦赫记忆“重构”理论的延伸发展。本文拟从哈布瓦赫记忆理论中的“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以及皮埃尔·诺拉的“记忆场”内容解读小说作者从欧洲宫廷史、奴隶史和艺术史三方面对黑色欧洲史的重构。
一.个体记忆对欧洲宫廷史的重构
《幽灵旅伴》中男女主人公在穿越欧洲的旅行途中,一直被黑人幽灵萦绕。在埃瓦雷斯托的小说中出现的黑人幽灵有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的黑女士露西;法国王后的情人黑侏儒纳波,以及他们的私生女路易斯·玛丽,法国军队的第一个黑人上校约瑟夫·布洛涅,吉里奥·德·美第奇和非洲女奴西蒙内塔的私生子弗洛伦萨黑人公爵阿莱山德罗等。从这份名单中可以看出,小说中出现的黑人幽灵大多涉及了欧洲宫廷中的一些人物,为欧洲的混血遗产和通婚历史提供了充足的证据。在斯坦利穿越欧洲旅途过程中他们依次出现,通过与斯坦利的交谈过程中,回忆在欧洲宫廷中留下的痕迹。个体记忆是指“一种位于个人头脑中的记忆,通过这种记忆,这些个人对属于他们个人经验的事物有所了解”(Geoffrey,2013:4)。逝去的黑人无法以正常的方式讲述自己个人的经历,只能通过与男主斯坦利的谈话回忆着自己过往的历史,“借助幽灵的存在来表现逝去的过往”(王卉,2021:137)。当前西方普遍接受的观点是,英国有色人种的出现始于20世纪40年代的战后移民潮涌入英国而成为劳工,因此非洲英国移民是开始于1984年搭乘帝国疾风号到英国的加勒比劳工。但是弗莱尔在《持久的力量——英国黑人历史》试图将3世纪的北非士兵纳入英国的历史书写中,伊姆蒂亚兹·哈·比·卜在《英国档案馆里的黑人生活——从1500到1766》中重新构建起了16和17世紀的黑人存在史。“正如塞缪尔·海因斯指出‘记忆是我们保存或恢复过去以及恢复时间的心智能力”(Grenn,2004:37)。与这两位英国史学家一样,埃瓦雷斯托在小说中灵活运用黑人的个体记忆构建起了具体的非洲流散者形象,并通过这些个体的个体记忆还原了欧洲宫廷的真实历史,打破了种族纯洁的神话。
《幽灵旅伴》中第一个涉及欧洲宫廷秘史的黑人幽灵就是法国王后和她的情人侏儒纳波生下的私生女路易斯·玛丽。在参观凡尔赛宫时,斯坦利与玛丽相遇了,玛丽告诉斯坦利,因为身份的特殊,她从小就被丢弃在“雷修道院,在它冰冷的石墙内,度过了一生”(埃瓦雷斯托,2010:114)。法国王后去世后骨灰被安置在银盒子里,棺木庄严安置,正式的哀悼仪式,与自己高贵的母亲法国的王后相比,拥有黑人血统的玛丽则“被埋在了修道院教堂后的一块空地里”(115)。至于她的父亲纳波,书中写到“后来那个矮个男人就消失了,在历史上销声匿迹”(119)。在历史上销声匿迹,说明没有任何文字记载,官方历史也不允许任何人记住这段历史,仿佛这个人在历史上就没有出现过,他们在历史上的痕迹被法国主流历史给抹除了。哈布瓦赫也指出“个体记忆正是各种不同社会记忆的交叉点”(冯亚琳 阿斯特莉特,2012:23),正是通过玛丽个体记忆,埃瓦雷斯托颠覆了法国宫廷的种族神话,让深藏在黑暗中的黑人找回了自己被掩盖的身影。除了法国,埃瓦雷斯托在小说中还在意大利英国等国家的宫廷史为黑人的存在和归属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在她的笔下,弗洛伦萨的公爵阿莱山德罗是混血儿,是教皇克莱门特七世基里奥·德·美第奇与来自非洲的女奴西蒙内塔的后代。英国的夏洛特女王,前德国梅克伦堡-施特雷利兹的夏洛特索菲亚公主,在她的笔下变成了一张“标准的黑白混血儿的脸”(318),并且还继承了15世纪葡萄牙皇家摩尔人血统。克莱门七世是15世纪-16世纪的人物,而夏洛特女王更是流淌着15世纪摩尔人的血统,这说明早在15世纪或是更早在欧洲就有黑人存在,有效的推翻了西方声称的有色人种的出现始于20世纪40年代的说法。这些宫廷秘史都是斯坦利在穿越欧洲途中与这些黑人幽灵通过交谈得知,他们通过他们的个体记忆还原了真实的历史,因为他们的存在就是打破欧洲官方历史最好的证明。埃瓦雷斯托“不仅打破了种族纯洁的神话,而且还在欧洲社会最高阶层的核心——在其贵族和高级知识分子中,为黑人创造了空间!”
二.集体记忆对欧洲奴隶史的重构
在《幽灵旅伴》中,黑人幽灵不仅背负着被遗忘和抹杀的历史的个人记忆,黑人群体的集体记忆还承受着主流历史书写的奴隶史。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因此历史的记录方式也由胜利者决定。身为弱势和边缘群体的黑人群体丧失了书写历史的机会,历史的话语权导致黑人群体只能记住掌权者让他们记住的历史,没有历史的传承和记录,真实的历史会随着一辈人的消失也随之消逝。传统的奴隶叙事都会在某种程度上迎合白人社会的传统价值观,而埃瓦雷斯托在《幽灵旅伴》中从黑人群体的集体记忆出发,真正从黑人内部解读他们的思想,揭开了隐藏在历史面纱下的黑人奴隶史。哈布瓦赫在《论集体记忆》中详细说明过“集体记忆不是一个给定的概念,而是由社会构建的概念,虽然集体记忆在一个连贯的人群中持续存在并且从基础中汲取力量,但是作为群体的个人会记住”(Halbwachs,1992:22)。斯坦利在穿越欧洲的旅途中通过与黑人幽灵的交谈了解到了他们背后的黑人历史。在《文化记忆理论读本》中也谈到“我们从自己与见证者属于同一个群体并从特定的角度共同思考的那一刻起,就与这个群体建立了联系,并把自己视作他们的一体,把自己与他们的过去统一起来。”(冯亚琳 阿斯特莉特,2012:50)斯坦利本来就流淌着非洲的血液,作为加勒比和英国人的后代,从见到游荡在欧洲大陆上的黑人幽灵时,他就找回了自己的身份和归属,成为了他们中的一员,见证着历史背后真正的奴隶史。
根据哈布瓦赫的理论,记忆是具有社会性质的,记忆的遗忘和变形都源自于“社会框架”的消失和变迁。社会框架具有多种形式,最基本的就是通过与他人的交流。斯坦利在法国巴黎的幽灵咖啡馆偶遇了法国的第一位黑人上校约瑟夫·布洛涅。从咖啡馆的名字我们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幽灵聚集的地方,作者为咖啡馆这样命名其中的含义自然是不言而喻的。约瑟夫因为黑人族群的历史和足迹在欧洲大陆上逐渐泯灭倍感痛心“我患上了名字健忘症/我请求你。让我重新拥有这段记忆”(埃瓦雷斯托,2010:147)。 刚毅的民族精神让他记忆中始终留存着非遗黑人的历史片段,为了阻止官方历史继续将非裔群体的历史痕迹抹去,他请求朋友赫克托为他写传记。约瑟夫回忆着黑人群体在圣多米尼亚残酷的奴隶制度。根据约瑟夫回忆,圣多米尼克的奴隶制度是最残酷的,种植园的牲畜都比奴隶待遇要好。为了满足西方人对甘蔗的贪欲,数百万的黑人遭到了奴役,他们的双腿因为要捣碎甘蔗而变得霉烂。被刀子割开的舌头它被慢慢地撕开就像粗燥,多汁的丝兰果肉。但是这些非裔群体遭受的非人的奴役在官方历史的记载中却没有详细记载,可是黑人群体会记得,约瑟夫“他的思想情感和关于奴隶贸易的/罪恶总结以及他们所遭受的非人待遇,这些法国领土上的罪行,都是他亲眼见证”(146),“我们的回忆总是集体性的,并经由他人重新从我们的记忆中唤醒”(冯亚琳 阿斯特莉特,2012:49)。那些触目惊心的画面,都是圣多米尼克真实又残酷的奴隶制度。掌握着历史书写的权力的西方殖民国家对黑人群体在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残害和蹂躏的历史被长期压制和掩盖,但是通过约瑟夫为代表的黑人幽灵群体回忆重现了圣多米尼克对黑人的剥削和残害。哈布瓦赫表示“集体记忆不是给定的,而是一种社会构建的概念”(Halbwachs,1992:22)。非裔黑人群体在集体记忆的帮助下,恢复了属于他们这个群体的社会框架,记忆帮助他们构建着历史,黑人幽灵群体又为非裔黑人在欧洲大陆的存在史提供了支撑。通过历史碎片的拼接他们重构了自己的历史,并且亲眼见证了黑人民权运动为他们争取到的人权和正义。他们来到了黑人民权运动的高潮60年代,与运动带来的一船“长着非洲头型未经加工的头发”(228)的非洲同胞,还喊着那令人震惊的口号“黑就是美”(228),宣扬着“我们非洲文化”的那种民族自豪感,在这样一个跨越时间,跨越空间的时刻,他们不仅戳破了欧洲官方的虚假历史,还重构了民族的社会框架,书写了民族的历史,为自己赢得了在欧洲大陆上的一隅之地。
三.记忆场对欧洲艺术史的重构
欧洲官方历史不仅从象征着国家权力核心的宫廷史和宏观的历史方面对黑人的存在史予以否认,在代表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现象的艺术史方面也抹除了黑人的存在和他们对艺术发展的影響。历史影响着记忆,记忆构建着历史。记忆在历史洪流中的转换变得尤为重要。记忆转换的关键就是具体的载体。哈布瓦赫曾指出“如果一个真相根植于群体记忆,它需要以具体的形式体现在一个事件、一个个体,或是一个地点中”。(Halbwachs,1992:200)但是对于记忆转换的载体,哈布瓦赫在他的研究中没有进一步说明。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在哈布瓦赫的研究上进一步提出“记忆根植于具体、空间、姿态、意向和物体”(Nora,1989:9)记忆场包含的范围很广,可以是实体的物品和地点、象征性的意象、功能性的指向。因此,建筑,诗歌,地点等等都可以是记忆场。
埃瓦雷斯托在小说中首先提到的记忆场所就是建筑对历史的影响。斯坦利的父亲克拉斯福德,作为一代移民在英国居住的房子在作者的笔下被描绘为“参差杂乱”、“黝黑”、“废墟”,从这些形容词可以看到,作为有色人种在英国的居住环境的整体氛围是压抑的,颓废的、死气沉沉的,可以看出有色人种在英国仍处于边缘群体,他们无法进入城市的繁华和中心地带。反观斯坦利的公寓,整个住所“纯然白色”(埃瓦雷斯托,2010:28),连墙壁的白色都能有好多不同的形容词“骨白、铅白、浅白、银白、粉脂白、钡白、锑白、钛白、锶白、巴黎白、锌氧白、锌硫白”(28)。斯坦利作为二代移民,在英国从事着金融行业,在社会上算得上是中产阶级。英国社会对于社会上优秀的年轻人似乎从小就一直灌输着以白为美的观念,想要与一切有关“黑”的事物隔绝开来。因此在还未开启欧洲之行的斯坦利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对他意识形态以及价值观的影响。但埃瓦雷斯托在写作中又暗示了英国白色神话还是没能摆脱黑人的影响。斯坦利居住的公寓叫“百丽宫”是伦敦一处著名的公寓楼,“‘百丽宫”在‘blackheath的位置,这个名字来源于古单词‘dark soil”25。“记忆场所就是自己的报告人,就是提示自己的标记,很纯的标记”(冯亚琳 阿斯特莉特,2012:111),这个地理位置似乎就是在提醒着黑人在其中的影响,在提示着自己在英国的身份和地位。在科多巴,斯坦利发现摩尔人统治了西班牙有八百年之久“光科多巴一地就有数百的商店、街灯、图书馆,到处都是空调、中央供暖设备,冷热水管道通进房屋,医药和科学方面也很先进”(183)。科多巴一地的发展离不开黑人其中的贡献,但是在历史的记载中却没有了黑人的踪迹,斯坦利谈到就连学校教书的历史老师也不会教授相关的内容。在格拉纳达,他还参观了阿尔罕布拉宫,这座宫殿由摩尔国王与12世纪和13世纪修建,是西班牙摩尔建筑的典范。但是格拉纳达最终被基督徒征服,他们的民族被打败了,建造的宫殿也被损毁,摩尔人被伊丽莎白女王赶出了西班牙,摩尔人的身影就消融在了历史中。斯坦利在旅行途中探究着历史,历史也在以幽灵般的方式试探着他。“记忆场就是民族历史的片刻”(111)。记忆场凸显着历史,而记忆场所的消失促使一个族群失去了历史。通过斯坦利的欧洲之旅的见证,格拉纳达在历史的河流着又恢复了曾经的辉煌美丽,摩尔人通过往日修建的宫殿这样一个记忆场所,让时间停滞了,阻止了记忆的遗忘,重构了被欧洲官方抹掉的历史。艺术史结合人类活动的背景,在历史的框架中去探索视觉产品,这种方式“可增强我们对人类其他历史和创造性的理解”(马明明,2009:256)。诗歌和画作是艺术表达最基本的方式,又是记录历史变迁的特殊记忆场所。俄罗斯文学之父普希金在埃瓦雷斯托的笔下变成了拥有埃塞俄比亚血统的混血后代,母亲捷斯达·奥西波弗娜被人称为“美丽的克里奥尔”。他于1827年创作《彼得大帝的黑奴》,宣扬身为黑人的自豪感“我是个黑人我自豪!大声说吧,我是个黑人我自豪!呀噢噢啊啊”(266)!普希金遗传了老一辈黑人的身体特征因此在家族中不受待见,排斥他的非洲特征,画家为他画了一幅肖像画,记录了他的容貌,于是他写了一首“我的肖像画”的诗,目的就是想让后代知道他的非洲轮廓会怎样地流传好几百年。面对批评家们对自己非洲祖先的嘲讽,他用“我的家谱”一诗作答,描述了黑人祖父与沙皇的亲密关系关系,有力的回击了他们的质疑。他一直不放弃寻找自己黑人族裔之根一事,也通过这些诗歌和画作证明了历史上黑人留下的足迹。记忆场所是记忆与历史的相互交替,是两个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冯亚琳 阿斯特莉特,2012:107)。记忆和历史相互定义着对方,历史决定了记忆场所,记忆场所又影响着历史。
小说《幽灵旅伴》用黑人幽灵的个体记忆重构了欧洲的宫廷历史,以黑人幽灵群体的集体记忆再现了欧洲奴隶史的残忍,让黑人历史中的记忆场所为民族的自主权发声。埃瓦雷斯托通过从代表欧洲权利与形象的宫廷,欧洲官方书写的奴隶史,以及代表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现象的艺术史三方面彻底颠覆了主流历史书写的黑人历史,掌握了书写历史的自主权,再现了被时间和历史所抹杀的黑人历史片段,重构了欧洲大陆上的黑色存在史,也帮助了当今欧洲大陆上的黑人群体获得了他们所急需的名族归属感,体现了她对边缘群体的深切关怀。
参考文献
[1]Apfelbaum E. Halbwachs and the social properties of memory[J].Memory:Histories,theories,debates,2010:77-92.
[2]Geoffrey,Cubitt. History and Memory[M].New York:Manchester University
[3]Grenn, Anna.Individual Remembering and 'Collective Memory': Theoretical Presuppositions and Contemporary Debates[J].Oral History Society,2004,32(2)35-44.
[4]Gustar J.Putting History in Its Place: An Interview with Bernardine Evaristo[J].Contemporary Women s Writing,2015,9(3):433-448.
[5]Nora, Pierre.“Between Memory and History:Les Lieux de Memoire”[J].Memoryand Counter-Memory,1989,26(1)7-24.
[6]Halbwachs, Maurice. On Collective Memory[M].Trans.Lewis A. Coser.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
[7]On the Road: Bernardine Evaristo interviewed by Karen Hooper[J].The Journal of Commonwealth Literature,2006,41(1):3-16.
[8]Saroukhani H. Vehicular Cosmopolitanism:The Car in Bernardine Evaristos Soul Tourists[J]. Etudes anglaises,2017,70(1):11-27.Press,2013.
[9]Tournay–Theodotou P. Reconfigurations of “home as a mythic place of desire”:Bernardine Evaristos Soul Tourists[M].Projections of Paradise.Brill,2011.
[10]伯納丁·埃瓦雷斯托.张琼译.《幽灵旅伴》[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0.
[11]高萍.社会记忆理论研究综述[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03):112-120.
[12]冯亚琳 阿斯特莉特.埃尔.《文化记忆理论读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13]王卉.《幽灵旅伴》中的莎士比亚黑女士[J].国外文学,2021(02):136-145+
160.
[14]马明明.西方艺术史观念的变迁轨迹[J].科教文汇(上旬刊),2009(01):256+258.
(作者单位:大连外国语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