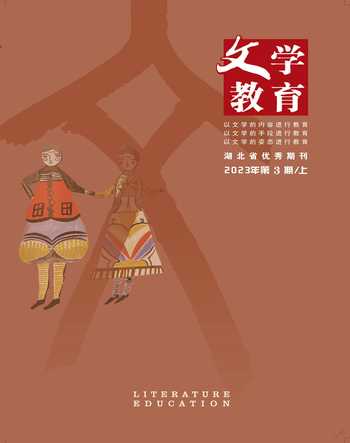张爱玲《花凋》中的“物”叙事
2023-05-30年东敏
年东敏
內容摘要:张爱玲一向善于意象的描摹,《花凋》叙事细腻且延续了张爱玲一贯的写作风格,日常的“物”在小说中兼具审美与叙事作用,推敲其中的“物”叙事,不仅能够洞察张爱玲叙事艺术的精妙,更能感受其创作主旨的深远。
关键词:张爱玲 《花凋》 物象 叙事作用 叙事内涵
《花凋》对物象的描写主要围绕川嫦的生命轨迹展开,除了镜子等蕴含古典内涵的意象外,服装、灯具、照片、鞋子等日常用品也被赋予多重意蕴,人物的潜意识在物与人的“互文”中折射出来,命运悲剧也得以强化。
一.呈现环境与塑造人物
通过服装与家具的细节描摹,《花凋》生动地呈现出郑川嫦的形象与家庭环境。川嫦在家里七个孩子中排行第四,“在姊妹中轮不着她算美”,她捡姐姐们不喜欢的衣服穿,少有修饰自己余地,性情在家里也不很惹眼。“于是川嫦终年穿着蓝布长衫,夏天浅蓝,冬天深蓝,从来不和姊妹们为了同时看中一件衣料而争吵。”会见情人章云藩时,小说也对川嫦的穿着进行了细致描述:“她这件旗袍制得特别的长,早已不入时了”,“想必是旧的,既长,又不合身”,穿这件衣服是 “因为云藩向她姊姊说过:他喜欢女人的旗袍长过脚踝,出国的时候正时行着,今年回国来,却看不见了。”[1]这里对服装的描写刻画出川嫦委曲求全的性格,以及主体性缺失的生命状态,川嫦在青春的年纪但不具有生命活力,“她是没点灯的灯塔”。
川嫦为什么呈现出这种生存状态?小说又通过诸多物象,展示她的家庭环境。川嫦的父亲郑先生是个知道酗酒妇人和鸦片、却又有着孩子心的遗少,当川嫦病重需要西药医治时,他仍在抱怨“做老子的一个姨太太都养活不起”,“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将郑先生的阴森、怪异刻画出来,浓缩着家庭病态和时代畸变,暗示川嫦压抑的生活环境。
对川嫦与云藩在郑家客厅相处时的细节性场景呈现,更是通过“电灯”“项圈”与“客厅”等物象浓郁而颇具象征氛围地展示出郑家的病态。“客厅里电灯上的磁罩子让小孩子拿刀杖搠碎了一角,因此川嫦能够不开灯的时候总避免开灯。屋里暗沉沉地,但见川嫦扭着身子伏在沙发扶手上。蓬松的长发,背着灯光,边缘上飞着一重轻暖的金毛衣子,定着一双大眼睛,像云雾里似的,微微发亮。”[2]这里日常生活场景被赋予象征意味,破碎的灯具、昏暗的客厅均指示着郑家的压抑与混乱。接着又通过云藩的眼睛展示川嫦:“川嫦正迎着光,他看得清楚她穿着一件葱白素绸长袍,白手臂与白衣服之间没有界限;带着她大姊夫从巴黎带来的一副别致的项圈,是一双泥金的小手,尖而长的红指甲,紧紧扣在脖子上,像是要扼死人。”[3]这里的描写完全不像一位情人的视角,加之昏暗、空阔而杂乱的家作为背景,显得异常破败与压抑,而“像是要扼死人”的“项圈”更是隐喻病态生存环境、暗示川嫦的悲剧命运,小说这样描写川嫦病重的形象:“她爬在李妈背上像一个冷而白的大蜘蛛”,川嫦的身体的病态被直接刻画出来,让人不寒而栗,同时令人联想到卡夫卡笔下异化的甲虫。“人物的服饰、饮食、住宅,均为携带意义的符号,与物相关的行为,如物的保有、持用、分享、馈赠、消费、呵护和毁弃等,更值得做深入文本内部的细究和详察。”[4]电灯、项圈与蜘蛛在此既展示人物的生存环境,又是主体的外化。
在昏暗的客厅中,云藩以为川嫦要开灯,结果她却是扭开无线电,并说自己的理想是“希望有一天能开着无线电睡觉”,这些细节都暗示着郑家的杂乱与压抑,以及川嫦对自由与自我的渴望。然而张爱玲通过服饰与神态已传达出川嫦的孱弱与软弱,她绝不敢为自己读大学的梦想而反抗,心甘情愿进了“新娘学校”,在病中延挨生命的萎谢,实则肺痨并非仅是川嫦死去的因素,它还是故事矛盾与情节张力的触发点,更凸显着家庭对她的摧残。“一直以来,人们都习惯于援引结核病和癌症[作为隐喻],来谴责那些具有压抑性的习俗和空想,压抑力量被想象成一种环境,它使人丧失活力(结核病),或使人丧失灵活性和冲动(癌症)。”[5]郑家阴森怪异,住洋房、打牌,家具却是借来的,灯具破碎,大狗如一个棕毛毯,仆人的薪水也拖欠很久,郑氏夫妇矛盾重重。川嫦的病暗合家庭的压抑与病态,身体疾病同时是旧式家庭扭曲的隐喻。川嫦健康的身体日渐丑陋、凋零,也隐含着张爱玲的悲观与深刻,她塑造过很多被家庭残害的子女形象,曹七巧、姜长安、姜长白、聂传庆、顾曼桢,他们或是在家庭的摧残下身体渐渐委顿,或是经受难以言说地精神创伤。
二.展露欲望与女性命运
张爱玲曾在《自己的文章》中说:“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朴素,也更放恣的。”[6]《花凋》正是以川嫦的爱情为切入点展开人物的悲剧、刻画欲望之荒凉。
在对川嫦与云藩未能得以展开的爱情的描写中,张爱玲展示了具有内在“主体性”诉求的川嫦欲望破灭的过程。“物只有作为与人有关,尤其是与需求、欲望等有关的隐喻与象征,才会在叙事中获得特别的意义,成为耐人寻味的符号。”[7]首先,小说通过对“打空气针”“枕头套”“照片”的描述,巧妙地映射了川嫦的心理变化。云藩给川嫦打空气针诊治时作为医生的身份,时刻提醒着川嫦是病人,她越喜欢章云藩,就越“不大乐意章医生”。因而云藩打空气针过程中的接触使她非常煎熬,她担心“他未来的妻太使他失望了吧?”展示出川嫦对自身失却女性“吸引力”的忧虑。于是她总是将手放进枕头套,露出手臂等着云藩干涉,“折中”地实现被关怀与爱的“权利”,但是“越急越好不了”,川嫦的“脸像骨格子上绷着白缎子”,眼睛是灯花烧成的“两只炎炎的大洞”。云藩最终交了新女友,川嫦“大约断定”自己的病是无望了,健康时的“照片”可以说是川嫦在爱情与尊严中作的最后挣扎,她刻意把曾经的照片压在桌子上,却被云藩的新女友余美增说“像个囚犯”,且“比本人还胜三分”,川嫦的自尊心遭受重大打击。
当疾病将川嫦的自尊与爱欲都剥夺,生命的晦暗与脆弱尽现。“《传奇》里有很多篇小说都和男女之事有关:追求,献媚,或者是私情;男女之爱总有它可爱的或者是悲哀的一面,但是张爱玲所写的绝不止此。人的灵魂通常都是给虚荣心和欲望支撑着的,把支撑拿走以后,人变成了什么样子——这是张爱玲的题材。”[8]张爱玲的小说总是铺排着明暗两条线索,明线是爱情悲剧,潜隐其中的暗线则是对人性的透视、对欲望的解构。
张爱玲坦言“我喜欢素朴,可是我只能从描写现代人的机智与装饰中去衬出人生的素朴的底子。因此我的文章容易被人看做过于华靡。”[9]事实上,对众多物象的细致刻画极易导致叙事的“华靡”,但也正是张爱玲“描写现代人的机智与装饰”的重要策略,书写物并赋予物启示意义,合乎张爱玲的创作观,她不愿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10],而要在人生的“底子”中展示“不安全”与“破坏”,呈现人物悲剧。在《花凋》中,张爱玲即通过众多物象,刻画了川嫦及郑家的表面的华靡与内在的荒谬、主体欲望的诉求与本质的空洞、生存世界的纷繁与悲凉。
其次,小说对“打空气针”“枕头套”“照片”的描述也暗示女性主体性的缺失与可悲命运。川嫦在与云藩的恋爱中自始至终是寻求认同的一方,病后她更加渴望得到认可,这也加速了她的死亡。因为“在传统宗法社会里,女性是依据男性的喜好被赋予种种合法化的性质:美丽、温柔、顺从……再看疾病缠身又久治不愈以后的川嫦,被遗弃是她必然的命运”“张爱玲选择了迥异于宗法正统身体并被正统身体认为是怪诞、丑陋的身体,在二者的冲撞中,丑怪身体所象征的反支配、非正统的潜文化的力量,通过男女两性在宗法社会中由于身体,性的不同而形成的不同的文化价值认同之间的对话,以不为正统文化认同的怪诞、丑陋身体打破正统身体的独白,振荡、颠覆正统身体所象征的话语权力专制。”[11]无论是于家庭与社会环境,还是川嫦的内心世界,父权制都是潜在而自觉的“规则性”存在,她的死亡是必然的;川嫦母亲的诉苦也反映这一女性命运,郑夫人一面希望女儿好好念书自立,一面也只得接受丈夫姨太太的孩子,并放任女儿们延续与自己相似的人生,她认为自己可以凭借劳动生活,却为了孩子牺牲了一生,也正揭示了“给‘爱和‘母性赋予象征性的价值并将其推向神坛,实际上是长久以来榨取女性劳动的意识形态机制。”[12]但她没有反抗,这一命运仍在郑夫人女儿们的身上延续。
福柯曾探讨主体在不同的时刻与制度条件下是如何确立的,他认为这一确立与“自我技术”(一切文明中的对个体进行建议或规定的一系列措施)相关,而自我既是“行为工具”也是“行为主体”,[13]《花凋》则可视为表现一个主体被动又自觉地被“规约”以至毁灭的文本。由此可见,张爱玲对物的描写不仅投射着主体欲望,还转喻了“规约”对主体的压抑与摧残,反映出个体的生存与精神局限。
三.营造生命绝境
开篇的天使石雕与结尾的皮鞋可以说是《花凋》中最引人沉思的两个物象。张爱玲在开篇便对天使雕塑这一物象进行了细致描摹,美丽、宁静、冰凉,郑家对逝去的川嫦的怀念透出反讽意味;结尾“看起来很劳”“可以穿两三年”的皮鞋,又反衬着生命的脆弱。
张爱玲显然不止步于技巧层面的物象描摹,她还试图通过物的描写,传达生命的哲学思考。《花凋》最初发表于1944年3月《杂志》第12卷6期,但在之后的文集中《花凋》为修改后的版本,变化主要为结尾部分。
发表于《杂志》的最初版本这样描写郑夫人在家中找到川嫦的场景:郑夫人跟进房来,待要盘诘责骂,嫦川(排版错误)喘吁吁靠在枕头上,拿着把镜子梳理她直了的鬈发,将汗湿的头发编成两根小辫。郑夫人忍不住道:“累成这个样子,还不歇歇?上哪儿去了一天?”川嫦手一松,丢了镜子,突然搂住她母亲,伏在她母亲背上放声哭了起来,道:娘!娘,我怎么变得这么难看?她问了又问,她母亲也哭了。
可是有时候川嫦也很乐观,逢到天气好的时候,枕衣新在太阳里晒过,枕头上留有太阳的气味。郑夫人在衙堂外面发现了一家小小的鞋店……[14]接下来便是川嫦突然的死亡。
在后来修改的版本中则这样描写:郑夫人立在楼梯口倒发了一会楞,方才跟进房来,待要盘诘责骂,川嫦靠在枕头上,面带着心虚的惨白的微笑,梳理她的直了的鬈发,将汗湿的头发编成两根小辫。郑夫人忍不住道:“累成这个样子,还不歇歇?上哪儿去了一天?”川嫦把手一松,两股辫发蠕蠕扭动着,缓缓的自己分开了。她在枕上别过脸去,合上眼睛,面白如纸,但是可以看见她的眼皮在那里跳动,仿佛纸窗里面漏进风去吹颤的烛火。郑夫人慌问:“怎么了?”赶过去坐在床头,先挪开了被窝上搁着的一把镜子,想必是川嫦先照着镜子梳头,后来又拿不动,放下了。现在川嫦却又伸过手来握住郑夫人捏着镜子的手,连手连镜子都拖过来压在她自己身上,镜面朝下。郑夫人凑近些又问:“怎么了?”川嫦突然搂住她母亲,呜呜哭起来道:“娘,我怎么会……会变得这么难看了呢?我……我怎么会……”她母亲也哭了。
可是有时候川嫦也很乐观,逢到天气好的时候,枕衣新在太阳里晒过,枕头上留有太阳的气味,窗外的天,永远从同一角度看着,永远是那样磁青的一块,非常平静,仿佛这一天早已过去了。那淡青的窗户成了病榻旁的古玩摆设。堂里叮叮的脚踏车铃响,学童彼此连名带姓呼唤着,在水门汀上金鸡独立一跳一跳“造房子”;看不见的许多小孩的喧笑之声,便像磁盆里种的兰花的种子,深深在泥底下。川嫦心里静静的充满了希望。[15]
通过比对可以发现增改部分主要为两个场景,一是川嫦疲乏地到家后突然发觉自己变得很难看,张爱玲连用多个“我怎么会”传达川嫦的绝望与痛苦;二是病中的川嫦对房间外美好与活力向往与羡慕的细节,这时的川嫦乐观、充满希望。在扩充的两个场景中,分别通过“镜子”与“窗户”呈现了川嫦的绝望与希望,“镜子”映射了川嫦对自己生命的绝望,“病榻旁的古玩摆设”般的“窗戶”又展露出川嫦对生命美好的留恋。
事实上,物的书写与身体、伦理、历史书写及生命意识具有亲缘性,甚至具有某种同质性。张爱玲细化两幅相对照的场景,将生命的悲伤与庸常、绝望与希望刻画出来,是其有意为之,她希望在故事之外“再多给他们一点别的”[16],使读者感知更深刻。在《花凋》中即为悲剧之外的启示,川嫦身体的日渐凋零、丑化,正与小说开头天使雕塑的美丽及小说结尾皮鞋的“坚固”形成对比,正如《倾城之恋》中的镜子是“现实不再起作用的世界:欲望和苍凉的昏蒙世界,这里的欲望即苍凉”[17],天使雕塑、鞋子与镜子、窗户具有相似的所指,对于死亡来说,这些“不再起作用”,至多昭示着欲望的苍凉。也正如“这花花世界充满了各种愉快的东西——橱窗里的东西,大菜单上的,时装本上的,最艺术化的房间……她不存在, 这些也就不存在。”[18]项圈、无线电可以说从某种程度上展示着川嫦的生存欲望,而药瓶、照片又体现了主体欲望的困囿与易碎,“雕塑”与“皮鞋”等物象还展露出作者对生命意义的深刻拷问。
总之,通过对“物”极富创造性与想象力的刻画,张爱玲在《花凋》中塑造人物形象并呈现其生存环境、展示女性的心灵世界与悲剧命运、营造生命境遇并赋予哲学启示意义,在生活底色中揭示平常人物的悲凉。
注 释
[1]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M].北京:北京十月出版社,2012:26.
[2]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M].北京:北京十月出版社,2012:25.
[3]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M].北京:北京十月出版社,2012:25.
[4]傅修延.文学是“人学”也是“物学”——物叙事与意义世界的形成[J].天津社会科学,2021(05):161-173.
[5](美)苏珊·桑塔格;程巍译.疾病的隐喻[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68.
[6]张爱玲.张爱玲散文[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2001重印):128.
[7]傅修延.文学是“人学”也是“物学”——物叙事与意义世界的形成[J].天津社会科学,2021(05):161-173.
[8]夏志清著;刘绍铭等译.中国现代小说史[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2019重印):413.
[9]张爱玲.张爱玲散文[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2001重印):128-129.
[10]张爱玲.张爱玲散文[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2001重印):126.
[11]赵丽瑾.《花凋》中怪诞、丑陋的身体书写策略[J].兰州交通大学学报,2004(05):102-105.
[12](日)上野千鹤子著;邹韵等译.父权制与资本主义[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32.
[13](法)福柯著;汪民安译.自我技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13.
[14]张爱玲,花调.国家图书馆〔J/OL〕杂志,1944(03):95-96.
[15]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M].北京:北京十月出版社,2012:34-35.
[16]張爱玲.张爱玲散文[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2001重印):85.
[17]李欧梵.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性十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252.
[18]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M].北京:北京十月出版社,2012:33.
(作者单位:长江大学人文与新媒体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