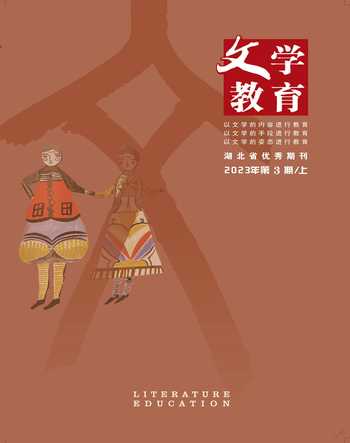李佩甫《生命册》中离乡者生存的多重困境
2023-05-30傅文琬
傅文琬
内容摘要:小说通过描述50年代以来的时代变迁,讲述了在时代浪潮中知识分子在多种外部因素影响下的艰难探索过程。沉重的人情债让吴志鹏无力承担,拼命逃离家乡;城市中的种种诱惑不断扩充着人们的欲望,最终跌进了的无底的深渊;城乡二元对立的叙事结构写出了在城市化进程不断进化的过程中人们在其中产生的精神困境。李佩甫用现实主义的笔触刻画着人们精神状态的异化过程,对当下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困境进行了批判和反思。
关键词:困境 李佩甫 《生命册》 离乡者
乡村多占據着李佩甫创作的主题,作品中或直接描述在乡村生活的人们,或描述在乡村基层组织中的权力关系,或描写从乡村走向城市的这一批人精神世界的挣扎。当然,这与他长期的生活经历是分不开的,他用一个土生土长的平原人的视角,讲述广袤平原大地上的花草树木和风俗人情,进而揭示人们的生存和精神状态。《生命册》就讲述了年轻人逃离家乡,在城市当中生活的经历以及精神世界的迷失与坚守,作为平原三部曲的收山之作,出版之后便斩获多个奖项。这部作品是李佩甫“把几十年对于平原的认识都砸进去”了[1],同时他也强调:“我这部长篇是用第一人称独白的方式来写50年的心灵史,或者50年的记忆。用一个人的内心独白写他50年的心灵史、成长史。”[2]小说以吴志鹏的视角讲述了一个知识分子背负着乡土记忆漂泊的故事,对家乡的逃离和对故乡的回忆,将“老姑父”“梁五方”“虫嫂”“杜秋月”“骆驼”等鲜明的人物形象串联在了一起。
小说以50年代以来的时代变迁为背景,讲述了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差异,以及在时代浪潮中知识分子在多种外部因素影响下的艰难探索过程。李佩甫对于乡村的景物和风土人情采用了大量的描写,乡村与城市相互交织,以树状结构书写位于大平原上无梁村的一草一木,一人一景,构成了他独特的平原城乡叙事。小说以“册”命名,汇编了大小十几个人物,选取不同人物命运的横切面展示不同人物悲惨、苦难的人生命运,作者在叙述众人不同的生存困境的同时也在探索救赎之路,表达了自己的人文关怀。巨大的人情交际网络压的吴志鹏难以喘气,拼命逃离;欲望的不断满足让人们迷失在城市文明的进程中;在城市和乡村的转化过程中,人们面临着精神困境与生存困境的双重挑战。
一.难堪其重的人情之累
家庭是人情往来最初的诞生地,在生存、繁衍的加持下,家族网络越来越庞大,人情的覆盖面也随之扩展,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社会约定俗成的规则。在同一地缘范围上的农村更容易产生人情上的往来,人们在生活、生产以及在交往活动中产生亏欠和偿付的日常性人情较为多见。当个体处于陌生的环境当中需要寻求帮助时,首先会想到自己的亲戚朋友和同乡,在人际关系网络的交汇下产生所谓的熟人社会,通过这种人情往来的交际方式,我们的生活在有熟人的帮忙下似乎更加顺利。在人与人的交往过程中,人情的存在充当着润滑剂的成分,使人与人之间建立一种相互联系的纽带,日常生活也更加充实。邻里、朋友、陌生人之间因为人情展开互助、合作、转借等多种交往方式。人情关系加强了人们之间的沟通和联系,双方在互不损害对方利益的基础下进行互助行为,促进了互助双方之间的情感交流,对维护和谐稳定的社会关系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人情来往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占据着重要席位。费孝通说:“如果双方相互不欠人情,也就无需要往来了。”[3]在经济发展如此迅速的今天,往常通过人情交往来增进彼此之间感情的交往方式逐渐沾染上了利益的气息,纯粹的情感交流方式的模式被打破,到如今发展成为人们精明的计较利益得失的工具。人们谈之“人情”就像是一种枷锁,小说中的主人公“吴志鹏”也因这种人情的枷锁被牢牢套住,让他难承其重。
吴志鹏的母亲在生下他之后就撒手人寰,父亲也因煤矿瓦斯爆炸被埋在了矿井之下,就这样,作为孤儿的吴志鹏由老姑父牵头成为了无梁村人共同的孩子。他喝的奶是老姑父带着他去每家的女人处寻来的;在他每次闯祸之后,也是由老姑父平息众人的怒火的。吴志鹏在无梁村村民的眼中,就是一种“无名税”式的存在,他吃的饭是一家家派的,而后在他上学期间,是每家出麦子或者玉米供养起来的,这种状态持续了二十年。全村人把吴志鹏视为祸害,在推荐上大学时提议老姑父依靠以前的战友给吴志鹏分到一个名额。可以说,无梁村的每个人都对他有着养育之恩,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一种血脉上的联系,也是一种地缘上的联系,“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3]故乡是人们在外最容易与陌生人建立联系的桥梁,俗语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同一个身世出处拉进了彼此之间的距离。吴志鹏从出生起就与无梁村的众人建立了一种亲缘上的联系,“在这些亲缘关系之间必然会产生情感交流或人情交往的日常生活现象”。[4]
在吴志鹏刚踏进城市的土地时,因无法证明自己的身份而无处可去,思来想去终于想到了“七不沾八不连”的同乡吴有才。这也是一种人情关系的动用,“关系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土壤,人们是最离不开关系的”[5],吴志鹏就在寒冷的冬季凭着同乡之间的关系找到了暂得以休憩的容身之所,而他同样也在极其疲惫的状态下与吴有才唠着家乡的体己话。如果说这时候是主人公在享受“关系”带来的便利,这种因人情带给他的束缚则是由一通电话开始的。第一个电话是国胜家女人的,因侄子考大学想让吴志鹏帮忙录取,他跑了十八趟招生办公室,用他在省城靠微笑建立起来的脆弱关系网去打听,最后事情也因这薄得像纸一样的人情无疾而终;第二个电话是保祥家女人因丈夫农用车撞人扣在公安局,让吴志鹏打个电话把他放出来的。而后这种来自无梁村的电话越来越多,难度也越来越大。吴志鹏努力的想把自己这株来自农村的种子移栽进城市,他隐藏着“狼”的野心,在准备许久的蛰伏下一步步走向讲台,依靠自己渊博的学识获得了学生的认可。在原有的人生轨迹下,他会凭借自己的努力成为一个著名的学者,在本校找到自己的人生伴侣,成功的把自己打造成一颗城市的种子。而由于这不断响起的电话,打破了吴志鹏原有的人生轨迹。为了帮乡亲的忙,吴志鹏四处借钱,到后来同事们见他就躲,生怕吴志鹏找他们借钱,这让吴志鹏在同事面前逐渐抬不起头来,对他照顾有加,给他争取讲师资格的老魏也对他失望,一句“农民习气”将吴志鹏打回了原型,而他精心为自己改造成城市人的包装也就此撕开,吴志鹏原本拥有大好前途的生活被电话搅得一团糟,让其心力憔悴。终于在他接起几百个电话之后,他的人情在一次次借钱当中,一次次托关系当中消耗殆尽,让吴志鹏不堪重负。无梁村俨然成了沉重“包袱”,让他产生了割断这种关系的想法。但在吴志鹏漫长的一生中,他始终没有挣脱掉这种人情的束缚,梁五方每次找他时手里都握着一张白条儿,两张帮杜老师跑事的,三张帮刘玉翠打离婚官司的,七张推销春才豆制品的,每一张“见字如面”白条儿的背后,都是吴志鹏背后的三千口无梁村人。
作为无梁村全村的孩子,吴志鹏无法拒绝她们,原因首先在于吴志鹏与老姑父之间毫无血缘的亲情关系,老姑父与吴志鹏的联系是最紧密的。从血缘关系上来讲,老姑父并不是他的亲生父亲,但是在他的成长过程中,老姑父占据了他重要的人生席位,吴志鹏喝的奶水是老姑父抱着他一家一家寻来的,上大学的名额是老姑父动用战友情争取来的。当老姑父张口时,多年的养育之恩使得吴志鹏无法拒绝,以至在后来的岁月中,无数张写着老姑父字迹的“见字如面”的白条束缚了吴志鹏的一生。其次是这是一种地缘上的伦理关系,“一个人生在伦理社会中,其各种伦理关系便由四面八方包围了他,要他负起无尽的义务,至死方休,摆脱不得。”[6]主人公吴志鹏在村里建立的这种伦理关系是错综复杂的,他是无梁村每个人的儿子,这就意味着要承担起更多的义务,他是无梁村的一颗救命稻草,一旦有了困难,村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吴志鹏。当然这也与吴志鹏自身有关,他是一个得懂感恩的人,吴志鹏意识到无梁村人在他的成长过程中赋予了他恩惠,从而在内心深处产生回馈的心理活动,并采取现实行动给予帮助,当他试图做一回“狡猾”的狐狸要摆脱电话时,家乡的回忆让他产生了愧疚之情。在道德和情感的双重作用下,就注定了他无法隔断与无梁村的联系,也无法摆脱这种人情之累。
“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7]人们处在社会的关系网中,必然离不开人情的动用,在吴志鹏上大学时,老姑父带着礼品找到了在部队时的战友老胡将名额争取了过来;厚朴堂药业公司的上市“骆驼”找了很多关系去打通,以及后来生意场上的交际都涉及着人情往来的成分,但与吴志鹏的亲缘关系的人情和老姑父的战友情不同的是,骆驼动用的人情往来涉及到了金钱,是一种纯粹的利益上的往来,这也就意味着它更为脆弱。经济与科技的不断发展,中国传统的“熟人社会”已经逐渐演变为“生人社会”,人情的交际往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人们的感情交流,对社会稳定有着良好的影响;一旦这种人情消耗过度或者异化,就会带来不良影响,例如因人情关系异化导致的腐败现象。[8]
二.难以摆脱的欲望之困
“人类彻头彻尾是欲望和需求的化身,是无数需求的凝集,人类就这样带着这些欲求,没有借助并且在困穷缺乏以及对于一切事物都满怀不安的情形下,在这个世界生存上。”[9]叔本华认为,人的一生不断在欲望和欲望所产生的成就之间不断流转,当现阶段的需求得到满足之后,就会产生倦怠、空虚、无聊、乏味的情绪,此时就需要新的欲求出现来重新调动个体生存的积极性。人类从呱呱坠地开始,在成长的过程中不断产生各种各样的需求,最紧要的首先是一种生存欲望。其次,在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之后,人们将会开始贪恋更多的需求,这些欲望大致可分为物质上的欲望和精神上的欲望,“不论精神的,还是物质的,其最大特性是永远追求满足”[10],有人追求财富,有人追求名利,有人追求爱情,从根本上来讲,都是为了满足欲望。欲望是生命存在的一种形式,适度的欲望会激发人的活力,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但寻求欲望的满足过多,过重,就会产生不良影响,欲望的寻求者会在满足中感受到无穷的痛苦,对社会秩序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人首先要保证自己生命的存在,才能逐步在此基礎上产生更多的需求,所以保证其最基本生存的生活欲望是最紧要的。对于吴志鹏来讲,“钱”是他最重要的欲望,它保证了吴志鹏基本的日常生活需要。他进城后作为一个大学讲师,稳定的工作带给了他稳定的收入来源,那他是什么时候感受到自己的贫穷了呢?第一次是在认识梅村后的第八天,成套的衣服,精致的皮箱,少见的丝绵被,各种各样的在八十年代称的上是奢侈品的物件冲击着一个每个月只拿五十二块钱助教的内心;第二次是找赫主任送礼,烟酒的寒酸;第三次是拿八百块钱去公安局领蔡苇香,此时吴志鹏一个月七十九块钱,他已经借钱借到同事们见到他都躲着走了;第四次是坤生媳妇难产生下的一双患有脑瘫的双胞胎孩子,两万金额的治疗费再一次冲击着他。吴志鹏在一次次人情债中体会到自己的寒酸,感受到了因金钱带来的自卑和窘迫。在金钱的驱使下,吴志鹏辞掉了他的工作,跟随骆驼到北京做了一名“枪手”,同行四人,想要出古典文化的书籍名利双收,但是,在书商的诱骗和金钱的枷锁下,四人从“古典文化”的生产者沦为了“垃圾文化”的生产者,金钱利益的驱使带领他们一步步走向了泥潭。诚然,这笔当“枪手”赚来的钱成为了吴志鹏和骆驼南下炒股的初始资金,在深圳和上海,他们俩靠着当时去蹭课学习的知识,在股市的浪潮里摸爬滚打,仅五年时间,吴志鹏就赚了四百二十八万,骆驼比他赚的还要多。吴志鹏和骆驼对于金钱的需求有其合理化的成分存在,但是人的欲望是永远无法满足的,当一个欲望达成之后,就会有新的欲望出现。就像骆驼和吴志鹏一样,金钱的富裕让他们感受到了高质量的生活品质,他们钻进“钱眼”里了,心底的诉求更加旺盛。骆驼这个人物有着极为聪明的头脑,对金钱有着异常灵敏的嗅觉,他们开起了公司,做起了老板,生意风生水起。“人是一种欲望的存在”[11],当欲望开始膨胀,人心也就开始迷失,吴志鹏感受到了骆驼的变化,在他的身上时不时会冒出“领袖意识”,他们收购工厂,造假包装上市。此时对于金钱合理化的欲求开始变形,产生了畸形的欲望诉求,骆驼在金钱的诱惑下逐渐迷失自我,成为了金钱的奴隶,与吴志鹏渐行渐远。这是一种因为金钱产生的利欲,“利欲惯性在生命力盲目的驱使下,会朝着非理性控制的方面发展,只要唯利心切,便会愈‘发展愈迅速,致为利欲膨胀。在膨胀的状态下不可自拔,最后乃至无视规则,引来‘车毁人亡。”[11]这样就可以解释骆驼后期发生的一些变化以及他跳楼自杀造成悲剧结局的原因。
小说中对于人物在情感上的需求也不容忽视。首先是主人公吴志鹏,梅村是他心中一个极其特殊的存在,用吴志鹏的话来讲,梅村是唯一让他心痛,他唯一爱过的女人,是他心中白月光。梅村带给了吴志鹏母亲一般的温暖,主人公的成长过程中母亲的人物形象是缺失的,成年后亟待寻求一种情感上的慰藉,可能正是梅村像母亲一样的怀抱,在吴志鹏的心里印下了无法磨灭的记忆。以至于在多年后,他没有放弃寻找梅村的下落,带着承诺和九十九朵阿西比亚玫瑰。反观梅村,梅村有着悲惨的童年经历,母亲的改嫁经历以及很坏的继父给她留下了很大的阴影,但是她对于爱情依旧存在着理想主义色彩,就像日记中记载的那样,“我本期望着找一个我爱的人,一个靠在他的肩膀上,能说一说知心话的人……”[5]梅村要找到一个情感契合的人来弥补童年阴影。她在一次一次的寻找中并没有达成心理上的情感慰藉,吴志鹏依靠着自己的才学吸引着梅村,悲惨的童年经历也让她产生了同情心理,梅村对吴志鹏的爱情也在不知归期的等待中消磨掉了。而后,一个诗人——苦水,他徒步黄河的志向,写给梅村的一百首诗征服了梅村,但当她发现这些诗是他抄袭来的,梅村的幻想瞬间就被打破了。离婚后的梅村觉得追了她四年的徐延军是爱她的,第二次的婚姻也仅仅维持了两年,徐延军每天像审犯人一样审问着梅村,她觉得这也不是自己想要的爱情。她又嫁给了一个画家,画家可以发现她身上的美,但她不知道的是画家是对美有一种欲望,但这种欲望并不针对梅村一个人。梅村一生都在追寻,追寻一份纯粹的爱情,但她始终没有找到,最终变成了一个充满怨气的女人,而这怨气就是梅村对生活的不满和发泄。
情感的欲求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演变成性欲。弗洛伊德认为性是一种本能,是一种每个人生来就有的能力,在这种本能的驱使下,人类进行一系列的活动。性本能说是弗洛伊德主义的支柱和基石。[12]小说中有许多关于性的描写,但大多数呈现出来的是一种畸形、病态的状态,最典型的莫过于春才。在性本能的驱使下,性意识在十八岁的春才身上逐渐觉醒,“对现代社会来说,最特殊的倒不是性被指定必须存在于阴暗之中,而是人们在把他作为隐秘的同时,没完没了的去谈论它。”[13]正是在村民的调笑嬉戏中,春才对于“性”有了初步的认识,最初的春才只是“红红脸而已”,后来就直接蹲下了。由于缺乏正确的引导,他将这种本能进行了压抑,从而选择了“偷窥”这种不正当的方式来疏解这种欲望,一方面在众人的谈笑中不断产生好奇心理,一方面又对自己的行为感到不耻,最终在这种折磨下选择了自我阉割的结束方式。
在利欲、情感需求、性欲的诱惑下,他们在满足欲望的过程中逐渐了迷失了自我,成为了欲望的奴隶,困于欲望牢笼。“执行意志,满足欲望(自食色以至道德的名誉,都是欲望),是个人生存的根本理由,始终不变的。”[14]欲望在人们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在一定的刺激下,可以激发创造活力,但是需要“超我”的约束,在道德的范围内严厉的审视来自“本我”的各种欲望。当下社会欲望高度活跃,人们在欲望的冲击下不断追寻着满足,精神意志遭受着侵蚀,个人欲望的释放,并不是为所欲为的,它需要理智的调节和控制,才能成为人类生存发展的不竭动力。
三.进退两难的精神之苦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耕社会,华夏人民生于土地长于土地,因此在文学的叙事传统上,自然离不开乡土叙事。在乡土叙事的背后是作家们在现代进程的诱惑中,灵魂上无处依托以及找不到精神家园的痛苦唤起了内心深处对于故乡的怀念,暗含着浓浓的乡愁。上个世纪20年代,鲁迅的作品《故乡》唤起了现代作家对故乡的回忆,以农民疾苦作为主要内容,创作了很多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的文学作品。随着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城市的范围圈逐渐扩大。乡村和城市作为人类生存的空间,“在当代文明中代表着相互对立的两极”[15]。两个空间彼此交融又产生着摩擦,两者之间的冲突逐渐进入大众视野。城市相比于乡村来说,拥有着更多的机遇和挑战,这种情况也就造成了农村人口的流失。城市的繁荣吸引着无数人的向往,希冀能在时代浪潮的机遇中大展拳脚。作家们也注意到了这种现象,创作了许多关于城乡的作品,这种二元对立的结构作为一个独特角度走进了文学视野。李佩甫的创作中也突出了这种二元对立的结构,文本中写出了在城市化进程不断进化的过程中人们在其中产生的精神困境。
在小说当中,愚昧落后的传统文化造成的一种群体上的精神压抑让人无法忽略。长久的精神压抑必然会产生情绪上的集中爆发,梁五方就是一个典型的受害者。当然传统文化有其积极的一面的存在,九爷与梁五方之间是一种师徒间的传承关系,多种民间技艺在传承的接力下得以延续。凭借著这种技艺上的传承,梁五方找到了生活的立足之本。他身怀绝技,凭着自己的本领在方圆几十里打响了自己的名声,但因此被视为“越师”,师傅九爷将其逐出师门,让梁五方自立门户。梁五方年轻气盛,依靠着自己的本领愣是在水塘之上建起了自己的房子。这座房子没有依靠任何人帮忙,可以说全凭梁五方自己的努力将自己的日子过得风声水起,这自然让村里人产生了嫉妒心理,觉得他太“各色”了,引起了众人的不快。而众人的爆发随着“运动”的到来集中式的喷发。心理学上有一个名词——“黑羊效应”,特指一群好人欺负一个好人的情况。陈俊钦在《黑羊效应》中将其分为三种角色:无助的黑羊,持刀的屠夫和冷漠的白羊。[16]梁五方是“黑羊”,他凭借自己的本领却引来村里众人的妒嫉,群众便是“持刀的屠夫”,“二十四条”罪状给了众人一个发泄口,一窝蜂地冲上去将梁五方淹没,人们或打或拧,或踢或捶,肆无忌惮地发泄着怒火,这些人群当中,大多数与梁五方并没有什么仇恨,甚至并没有什么交集,但是在庸常又平凡的日常生活中,积攒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怨气,长期精神上的压抑让他们无处发泄。梁五方作为一个发泄口的契机恰巧出现,让无梁村的人们“疯狂”的殴打他,“疯狂于单个人是某种稀奇事,但于群体、党派、民众和时代则是常规”[17]。吴志鹏和蔡国寅等人作为旁观者的白羊,对众人的殴打并没有及时采取相应措施,甚至产生了快意。在特定的坏境下,人们的怨恨和恶意是可以传染的,在个体独立存在时,是可以保持正常的价值判断和明辨是非的能力的,一旦放入群体之中,从众心理会驱使他加入群体行动,短暂的丧失行为对错的辨析。而梁五方也在这次群体事件爆发之后变成了一个无赖式的“上访者”,与当初充满活力的奋斗者形象截然不同。
吴志鹏是一个精神上的漂泊者形象,无梁村沉重的人情负担给他的精神上带来了沉重的苦难,于是他“逃离”家乡,辗转游走在各个城市之间,企图摆脱自己“农村”人的身份,在城市中寻找精神的栖息地。“灯”的意象在文本中多次出现,在寒冷的雪夜,暖黄色的灯光一方面温暖着吴志鹏漂泊着的心,一方面又在提醒着他农村人的身份。为了让自己看起来像个城市人,吴志鹏不断修正着自己,学习城里人走路,买一些仿名牌的衣服,开始大量的阅读积累对付城里人的新词,努力缩短乡村人与城里人的差距,让自己这颗“移栽”进城市的种子努力生根发芽。北漂地下室“枪手”的人生经历也给他的精神上造成了一定的折磨。骆驼是吴志鹏人生路上的贵人,一方面来讲,身上具有领袖气质的骆驼带着吴志鹏一起走上了人生的巅峰时刻;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在物欲横流的城市之中精神异化者的形象存在,在关键时刻给吴志鹏竖起了警示牌。城市中散落着的各种欲望吸引着无数从乡下进城打拼的年轻人,金钱、权力、地位给他们带来了精神上的满足,而物极必反,欲望的无底洞逐渐将他们的精神扭曲,在不断追求的过程中迷失自己,就如骆驼一样,他的精神困境有一部分时他的身体所带来的,精神上的扭曲让他沉沦在纸醉金迷的生活中,最后造成了悲剧的结局。吴志鹏在城市中不断游走,寻找着精神的家园,多年之后,他拥有了金钱和地位,像极了一个土生土长的城里人,但在人生的进程中,无梁村的各种画面勾起了他藏在内心深处的回忆。城市中的生存法则让他在精神上产生了困惑,而他拼命想要逃离的家乡却在他精神即将扭曲的关键时刻将他拉回。骆驼的死让他明白自己精神上的根始终都是自己的故乡,此时他要将自己的精神回归,等他再次踏进无梁村时,多年的变迁让他产生了一种疏离感,精神上呈现无处可归的局面。吴志鹏与无梁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地缘和情感的双重作用下,注定了他无法割断与无梁村之间的纽带,而当他意识到故乡始终是他精神的栖息地时,故乡早已物是人非。就这样,逃离不得,回归无门,吴志鹏就此陷入了逃离与回归的两难境地。
长篇小说《生命册》描绘了广袤的平原大地,展现了中原的人情风貌,章节开头以植物喻人,暗指人物悲惨的生活和悲剧的命运。在语言的表述上,大量独属于中原的方言词展现出了浓厚的平原气息;平实细腻的心理描写,形象又生动的表达了人物复杂的心理活动。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李佩甫塑造了很多丰满立体的人物形象,“老姑父”、杜秋月、梁五方、“骆驼”……每个人物都有鲜明的特色,但他们身上多少都有悲剧成分的存在,通过这些人物形象悲剧命运的书写,表达了作者对于人性的审视和生命的思考。独特的叙事结构让故事更加立体,在城市与乡村的交叉叙述中展现了人情带来的沉重负担,充斥着欲望的城市给人造成的生存困境以及城乡文明的冲突给人造成的精神上的异化。
精神漂泊是现代人生存的普遍现象,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经济水平的提升丰富着人们的物质世界,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而人们的精神世界却相对匮乏。李佩甫从人情、欲望和精神等多重困境书写现代人在精神上的痛苦,一方面批判“骆驼”一类人的堕落和沉沦,另一方面通过叙述吳志鹏的人生轨迹表达了自己对普通人的关怀和救赎。李佩甫坦言这是一部自省书,他将自己的生活背景融入到了创作中,用自己独特的乡土叙事坚守着对乡土精神的追寻。在当代社会发展如此迅速的今天,现代化的变革在相当程度上便利着我们的生活,也在一定程度上腐蚀着我们的精神状态。李佩甫用现实主义的笔触刻画着人们精神状态的异化过程,对当下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困境进行批判和反思,警醒世人不要忘记自己的根,时常审视内心,打破束缚自己的重重枷锁,进行自我救赎,摆脱精神上的两难境地。作品对于生存困境的描写和人们精神状态的反思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1]张亚丽.《生命册》:中原的故事就是中国的故事[N].中国青年报,2015-10-23(11)
[2]王波.李佩甫:贫穷才是万恶之源[N].中国青年报,2012-4-17(10)
[3]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中华书局,2013
[4]杨威.中国日常生活世界的人情化特质及其现代转换[J].求是学刊,2000(03):29-34
[5]李佩甫.生命册[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6]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185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35
[8]何旭明.论人情关系与腐败现象[J].社会科学,2000(11):19-23
[9](德)叔本华.叔本华说欲望与幸福[M].高适,译.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55
[10]程文超等.欲望的重新叙述:20世纪中国的文学叙事与文艺精神[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3
[11]赵诣.意识学:生命欲望意识文化与教育——自然主义生命观[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8:42、22
[12]宋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62
[13]弗洛伊德.性学三论[M].浙江:浙江文艺出版社,2015
[14]陈独秀.人生真义[N].新青年,1918:4卷2号
[15](美)帕克:城市社会学,宋俊岭译[M].华夏出版社,1987:275
[16]陈俊钦.黑羊效应[M].北京:团结出版社,2016
[17]尼采.善恶的彼岸[M].赵千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122
(作者单位:天水师范学院文学与文化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