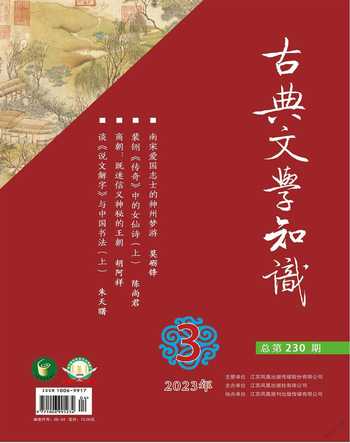《逍遥游》3
2023-05-10王景琳

庄子说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其自视也亦若此矣。而宋荣子犹然笑之。且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斯已矣。彼其于世,未数数然也。虽然,犹有未树也。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
今译
那些智力可胜任一方之官,行为可顺从一乡之情,品德可符合一君的要求,才能可赢得一国信任的人,他们自己看待自己也是如此。对这样的人,宋荣子是嗤笑的。像宋荣子这样的人,即便全世界的人都赞颂他,他也不会因此而更加努力,即便全世界的人都非议他,他也不会因此而更加沮丧。宋荣子能认清自我与外在世界的分际,知道荣辱的界限,这就是他所能做到的。宋荣子这样的人在世上已经是寥寥可数了。即便如此,他也还有未曾达到的境界。列子能够乘风而行,轻巧到了极致,他能出行十五日后才返回。在那些追求乘风而行的人当中,列子这样的人也十分少见。然而,列子虽然能够免于步行,他仍然是有所依赖、有所凭借的。
说庄子
从“之二虫又何知”之“知”、行路之人聚粮之“知”、“小知大知”之“知”到人类社会中各级官员之“知”,我们不难看出庄子说鲲鹏,说蜩、学鸠与斥鷃,说大树小草、说朝菌蟪蛄,都不过是他使用的一种“障眼法”,是为说人所做的铺垫。人,才是庄子论说的真正核心。古往今来那些执着于鲲鹏志在千里,蜩、学鸠与斥鷃目光短浅的人,实在都是被庄子迷住了双眼,没有注意到说“人”才是《逍遥游》的根本。
《逍遥游》的关键词当然是“游”。至此,庄子其实也一直都在写“游”:鲲在北冥游,鹏在九万里高空游,野马尘埃在天地之间游,蜩、学鸠与斥鷃在檀树、榆树、草丛之间游,行路的人在路上游,官员们在各自的位置上游,宋荣子可以心游,而列子则御风而游等等,无论他们怎么游,一句“犹有所待者也”,就把这样的“游”统统否定了。在庄子看来,这样的“游”虽说也是“游”,但离“逍遥”还差得很远呢。
相比较而言,稍稍能入庄子法眼的,应该是宋荣子的“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有多少人能不为世人的是非毁誉所动,始终保持自己特立独行的人格呢!用凡夫俗子的标准来衡量,宋荣子应该已经算是“游”中的极品了。但庄子仍然说他还不够,说他还没有获得逍遥游的任意与自由。为什么呢?很可能宋荣子的问题就出在他那一笑上。这一笑暴露了宋荣子免不了还是以一己之标准对人、对世界做出是非荣辱的判断,而这个判断恰恰说明,不但一切有所凭借的人的形体之“游”不是逍遥游,就是人已经可以心游,但依然为外物所动,同样算不上是逍遥游。
那怎样的“游”才是庄子所向往追求的逍遥游呢?这就要看你是否“犹有所待”了。这就是说,凡是有限制、有条件的“游”,即便像列子那样具有了超人的能力,可以达到随意潇洒、乘风而行的地步,也仍然不是逍遥游。
庄子说
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今译
倘若可以顺从天地的本性,因循自然的变化,游于无穷的境域,这样的人还需要依赖什么呢!因此说,至人能够忘却一己,神人能够忘却功业,圣人能够忘却名声。
说庄子
经过对鲲鹏、蜩与学鸠、宋荣子、列子等一系列不逍遥形象的反复渲染、层层铺垫,现在庄子终于要从正面为“逍遥游”做一个界说了。这一段虽只是短短几十个字,却高度概括了“逍遥游”的精髓、灵魂。
什么是“逍遥游”?在庄子看来,首先便是随心所欲、不受任何束缚地“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简而言之,就是顺应天地自然,不执着于任何外在之物,仅仅在自己的时空领域获得一种特立独行的任意与自由。这样的“游”并不虚幻,也不是“形游”,而是一种超然物外的心游,一种顺应自然的精神活动,是一种心灵的世界。
那么,如何才能进入、享受这样一种“无穷”的心灵世界呢?“彼且恶乎待哉”为我们开辟了走进“逍遥游”的途径。郭象《庄子注》依据这一句把“逍遥游”的精髓概括为“无待”,是深得庄子之心的,可以说是抓住了“逍遥游”的灵魂。什么是“无待”?无待就是不依靠、不凭借任何外在的东西,不把希望寄托在任何外物身上,不让“心”受到世间任何东西的束缚与局限,这才是逍遥游。相反,就是“有待”,就不是逍遥游。用“无待”的标杆来衡量,不但那些才智品行可胜任一方甚至一国的人与学鸠、斥鷃之辈没有什么不同,即便像宋荣子、列子这样超凡脱俗的人也都没有摆脱“有待”的窠臼,仍然算不上是“逍遥游”。
在现实世界,怎样才算是“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了呢?具体来说,就是六个字:“无己”“无功”“无名”。无己,就是丧失自我,忘掉自我。假如人没有了一己之念,这个世界还会作为人的对立物而存在吗?显然不会。那样的话,人自然也就可以“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辩”了。一旦人连自己都忘却了,那功业、名望自然也就都被忘掉了。
如此,便出现了一个问题,既然至人、神人、圣人的精神境界都进入了“无待”,也都是可以“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的逍遥游者,庄子为什么要分別用了三个不同的名称呢?
对此,古往今来的庄学家们存在着这样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这三种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差别,完全一样。这种看法一直占据主流地位。远者如郭象《庄子注》、成玄英《庄子疏》,近者如陈鼓应的《庄子今注今译》都如是说。另一种认为三种人虽都是逍遥游者,但彼此间存在层次的高低,三者中,至人的品位最高,神人次之,圣人再次之。如罗勉道《南华真经循本》,还有北京大学中文系所编《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都持这个看法。
这两种看法貌似都有道理,但也都存在着难以解通的问题。就前者来说,既然至人、神人、圣人完全相同,那为什么要有三种不同的称谓?而且这三个称谓又为什么配上了三个不同的标签:“无己”“无功”“无名”?就后者来说,其看法也难以自圆其说。庄子分明说这三种人都“无待”,他们的共同特征是“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从来没有说过他们之间有高低之分。
要想搞清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是顺着《庄子》内篇继续往下读。这时,我们不难发现,庄子所说的至人、神人、圣人指的是现实社会中三种身份不同的人。在《逍遥游》中,庄子举尧的例子来说明什么是“圣人无名”。尧是一国之君主,做的是君主之事,名如日月。他有名却不以名为名,可见庄子认为君主应该“无名”。在解释“神人无功”的时候,庄子说的是藐姑射之山神人的故事。庄子说神人管的是保障五谷丰登、让老百姓有饭吃,在现实生活中,这是臣子的职责。而神人有功却不以功为功。可见庄子认为做臣子的应该“无功”。而说到“至人无己”时,庄子特别讲了南郭子綦的“吾丧我”。这个“我”,也就是“至人无己”的“己”。丧了“我”就是“无己”。一个人没有了偏见,没有了一己之念,这就是“无己”。而南郭子綦的身份是普通人。可见庄子认为普通百姓应该“无己”(见《齐物论》)。根据这三“无”的具体内容,结合庄子每每涉及至人、神人、圣人的论述,这三种人应该分别代表了庄子理想社会中的君(圣人)、臣(神人)、民(至人),寄寓着对他“逍遥游”理想世界的向往。
“逍遥游”看上去、听上去都很飘逸潇洒,有谁不想进入“逍遥”的境界“游”上一把呢?可是就连庄子也知道,这不过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幻想而已。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庄子要在这一段的开头特别冠上了“若夫”一词吧!
庄子说
尧让天下于许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犹尸之,吾自视缺然。请致天下。”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今译
尧要将天下让位于许由,他说:“日月已经出来了,火炬还不熄灭,想要和日月比光,岂不是太难了吗?及时雨已经降下,却还要浇灌田地,对于滋润禾苗来说,岂不是徒劳无功?一旦先生在位,天下一定会实现大治,而我至今仍占据着这个位子,自己都觉得能力有限,请允许我把天下让给你。”
许由说:“你治理天下,天下既然已经大治,我还要来代替你,我难道是为了名吗?实为主,名不过是实的附属品,我难道要做附属品吗?鹪鹩在深林中筑巢,所需不过是一根树枝;偃鼠去河中饮水,只不过喝饱肚子而已。算了吧,我的君主,你还是请回吧,天下对我没有用,我也不需要天下。纵然厨师不烹饪,主祭之人也不会超越自己的职责去替厨师烹饪的。”
说庄子
这一段紧紧围绕着“圣人无名”展开,阐释了什么是“圣人无名”。
庄子用古代圣王尧让天下的典故来阐述“圣人无名”,一定不是随意为之的。“圣人无名”的“名”指的是君主使天下大治之后所获得的“名”。庄子的意思是说假如君主能把天下治理得四海晏然,百姓安康,并且最终忘记自己所拥有的君主之名,这就称得上是“圣人无名”。那么,此刻的尧是否已经成了“圣人无名”的君主呢?显然还没有。尽管就尧的个人愿望来说,他是想要放弃君主之“名”的,但骨子里却仍未忘了名,心中还有名。如果此时的尧已经“无名”,也就是忘了“名”,他就不至于在乎这个君主之“名”,更没有必要去找许由让“名”了。但尧与所有恋栈君主的不同之处在于,尧已经感受到“名”的拖累,只是他还没有找到如何实现“无名”的途径。我们还要等到他后来上藐姑射之山,见过“四子”之后,才真正成为一位“无名”的圣人君主。
这一段中特别值得注意的人物是许由,应该说他也是庄子本人的化身。位高权重的君主之位,对谁不是一个极大的诱惑?然而对于追求个体生命价值的许由来说,却不屑一顾:“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 。吾将为宾乎?”名是外,是宾;实是内,是主。君主之“名”只是人生的拖累,而不是生命的本质,也不是个体生命所需要的东西。
许由的寥寥数语,凝结着庄子对现实人生的深刻领悟,也直接道出了庄子对待一切虚妄之名的根本态度。森林虽深广繁茂,但鹪鹩所赖以生存的,不过是无数大树中的一根小小枝杈,它绝不貪图占据整个森林甚至是其中的一棵树。江河湖泊千千万万,偃鼠抵达水边不过是喝几口水解渴而已,它从不曾奢望去拥有整个江河湖泊。在庄子看来,尽管鹪鹩、偃鼠以及前文提及的蜩、学鸠、斥鷃等小虫鸟都还远远算不上是“无待”,但人们却不妨像他们那样安于命运的平淡无奇,甘于逼仄的生存空间,不谋非分之位,不贪图外在的一切,这样也就足以远离忧患了。也正因为如此,即便尧不愿意继续有君主之名,行君主之实,许由也不会越俎代庖。他要远离这个拖累,像蜩、学鸠、鹪鹩与偃鼠那样,在有待、不逍遥的现实世界寻得一个可以自得其乐、平淡超俗却无性命之忧的人生。
王景琳 曾任教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现为加拿大政府外语学院汉语言文化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