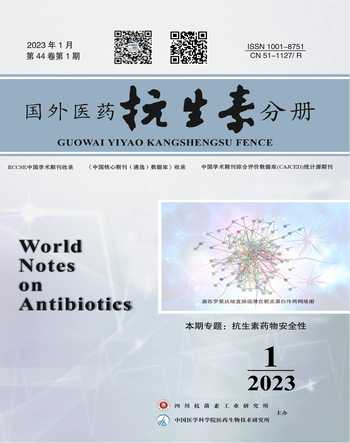抗生素风险管理体系构建策略
2023-04-29贾征张双庆
贾征 张双庆
摘要:抗生素在给人们带来临床价值的同时也带来风险:耐药菌株的不断出现,神经毒性、肾衰竭、心脏疾病、哮喘等各种不良反应发生。我们可以采取措施来控制抗生素使用风险,建立抗生素使用的量化指标进行定量控制,通过处方系统对抗生素的使用进行监控,依靠药师来监督医生的处方行为,另外还可以对患者进行抗生素使用的教育,使其对潜在的风险有所认识。
关键词:抗生素;风险评估;风险控制;处方系统;患者教育;指标管理
中图分类号:R97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751(2023)01-0045-05
Strategie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Risk Management System of Antibiotics
Jia Zheng1, Zhang Shuang-qing2
(1 Tangshan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Tangshan 063004;
2 National Institute for Nutrition and Health, Chinese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Beijing 100050)
Abstract: The widespread use of antibiotics brings both clinical value and risks, including the continuous emergence of drug-resistant bacteria, neurotoxicity, renal failure, heart disease, and asthma.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control the risk of antibiotics, as follows, (1) quantitative indicators are established for the quantitative control of the use of antibiotics, (2) the prescription system monitors the use of antibiotics, (3) pharmacist supervises doctors conduction, and (4) patients are educated on the potential risk of antibiotics.
Key words: antibiotics; risk assessment; risk management; prescription system; patient education; index management
药品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是药三分毒,使用不当不治病反致病,因此用药过程需要监管、保证其安全性,我国正逐步由药品上市后的使用监管进入药品全生命周期的风险管理阶段。风险是指不良后果发生的可能性,可以用某一特定危险情况发生的概率和后果的乘积来表示[1]。药品风险管理不同于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不良反应监测主要是事后反馈,风险管理则是事前预防、事中监测、事后补救的综合管理,其在发现、报告、评价等环节基础上多了一个控制环节[2]。任何一个药品在临床研究阶段,由于病例数的限制,不能穷尽所有可能的不良反应,因此上市以后的风险管理对于药品的安全使用同样重要。药品的风险包括主观风险和客观风险,主观风险主要由使用不当所造成,比如给药剂量过大、剂型不合理、超范围用药以及不对症治疗等。客观风险包括药物不良反应,药品使用个体差异性,药品监测期内的风险等[3]。抗生素自20世纪40年代广泛应用以来,成为治疗常见细菌感染的有力手段,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的健康水平,大大延长了人们的寿命。随着结核、螺旋体、立克次体、痢疾、军团菌、鼠疫等疾病有了相对有效的治疗方法,感染性疾病不再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主要疾病。抗生素大量临床应用的同时其潜在的风险也在不断积聚,我国住院患者的抗生素使用率为79%,这一数字明显高于英国的22%和其他各国平均水平的30%[4]。我国对感染性疾病患者进行细菌学检查的比例不超过10%,超时、超量、不对症、不规范使用抗生素屡见不鲜,抗生素滥用引起的耐药菌不断增长,抗感染药不良反应报告数量占2021年总体报告数量的28.1%。随着抗生素品种和使用量不断增多,抗生素的疗效不升反降,抗生素的生命周期也在不断缩短,近年来几乎没有新抗生素上市[5]。如果不能有效地遏制抗生素滥用,预估到2050年,每年将有1 000万人的生命处于危险境地,抗生素的风险管理不仅是医学问题,也是经济社会问题。
1 抗生素使用风险分类
人们一般情况下在动态评估抗生素使用风险收益比的基础上进行抉择,主观风险相对比较容易控制,而客观风险很难完全去除,只能尽可能减低,因此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后者,客观风险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1 不断产生耐药性风险
人们使用抗生素通常有一些不好的习惯,这些情况包括:病毒感染使用抗生素治疗;社区获得性感染使用广谱抗生素;没有根据细菌培养结果及时调整到窄谱抗生素,这些都可能导致耐药菌株的不断出现。据统计,临床上至少一半的抗生素使用是没有必要的[6]。抗生素不合理应用导致的耐药性是一项紧迫的全球公共卫生威胁,2019年全球至少造成127万人死亡。在全球范围内,抗生素耐药性对公众健康造成重大威胁,如果不采取措施控制耐药菌株的传播,到2050年估计每年将造成1 000万人死亡。抗生素和其他药物的不同之处在于抗生素的效果会随着使用时间的延长而效果减弱,存在时间递减效应[7],而其耐药性风险却随着使用时间不断积累。据统计,在基本医疗中使用抗生素,在治疗完成的12个月后,呼吸道和尿路耐药细菌耐药性风险增加了2倍,和使用抗生素显示出高度的相关性[8]。
在一项针对20个工业化国家的研究中,Albrich等[9]发现了门诊抗生素总消费量与青霉素不敏感性肺炎链球菌感染之间的关系,大环内酯类消费量与大环内酯类耐药性肺炎链球菌和化脓性链球菌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在特定区域研究中,Bergman等[10]检查了芬兰的18个地区,发现大环内酯类的使用量与次年对红霉素耐药的化脓性链球菌分离物的比例之间存在相关性,在医院一级,Fridkin等[11]证明了万古霉素和第三代头孢菌素类药物使用量与成人重症加强护理病房(ICU)中耐万古霉素肠球菌患病率之间存在关联,在社区,Macdougall等[12]发现门诊使用氟喹诺酮类药物与附近医院大肠埃希菌耐药性之间存在关联。目前,威胁最强的耐药细菌是革兰阳性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这种耐多药病原菌已成为医院内的主要感染,尤其是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不可避免地导致其他多重抗生素耐药性变体,最近,MRSA已经转移到医院外,成为一种主要的社区获得性病原菌,具有很强的毒力和传播特征。抗生素耐药性增加的同时肾毒性也在不断积蓄,一项统计显示,347种药物引起的肾衰竭中有166个是和抗生素的使用有关[13],在抗生素联合应用的时候,肾衰竭的风险会显著提升[14]。
1.2 神经毒性风险
头孢菌素类药物相关神经毒性的临床表现包括迟发性癫痫发作、脑病、肌阵挛、躯干—扑翼样震颤、癫痫发作、非惊厥性癫痫持续状态和昏迷[15]。青霉素被认为对γ-氨基丁酸(GABA)传递具有抑制作用,因为它们的β-内酰胺环结构与GABA神经递质具有相似的结构特征[16]。β-内酰胺环裂解灭活,随后癫痫电位丧失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噻唑烷环和侧链长度可能对致痫电位有影响。此外,大鼠研究已经证明,青霉素可以定量减少苯二氮卓类受体,从而降低抑制作用和改变神经元兴奋性[17]。研究还报告了继发于复方磺胺甲恶唑给药的短暂性精神病病例,患者出现急性谵妄,伴有激越、视觉和听觉幻觉,一旦停用致病药物,精神病/谵妄缓慢消退[18],Patterson等[19]也描述了某些免疫能力强的患者中在服用复方磺胺甲恶唑后发生短暂性震颤的病例。
1.3 增加心梗风险
一些常用的抗生素有引起危及生命的疾病风险,例如某些大环内脂类引起心律失常,甚至猝死,特别是通过延长QT间期表现出来。这些药物的安全使用要求医疗机构人员整合大量的科学和临床数据,以评估患者的风险因素,并从许多可用的治疗方案中进行最优选择。
2 抗生素风险管理策略
2.1 不断进行抗生素使用风险预防、风险评估
风险预防是指事先采取措施,阻止风险的发生,比如头孢菌素类抗生素使用前做皮试,喹诺酮类抗生素禁用于18岁以下儿童。风险预防具有安全可靠、成本低廉、防患于未然的特点,虽然其并不能完全避免损失,但可以减少风险发生的频次和损失规模。抗生素风险预防要逐渐改变过去事后行政监管为主的方式,不仅要重视上市后的不良反应监测,还要特别重视上市前的审批,将风险管理贯穿于抗生素的整个产品生命周期。风险预防要逐步改变过去以医疗机构为主的模式,让制药企业成为风险管理的实施主体,加强自查自纠能力,发挥“协同共治”作用[20]。风险预防要特别关注说明书中没有的不良反应,以及已经在说明书中提到,但发生频率显著提高的聚集性不良反应。要将抗生素的风险管理提升到药物警戒水平,不仅能够发现识别风险,而且能够控制风险,通过建立一个系统评估抗生素的安全性使抗生素的风险管理标准化,实现患者用药“收益最大化、风险最小化”的目标[21]。风险预防要重点关注引起风险的因素和影响程度,如患者的生理特征、基础疾病类型、合并用药、药物的溶媒、储存条件、使用方式等,还要关注抗生素在特殊人群中使用安全性、例如肾功能不全、肝功能不全等人群中的使用。人们一般把风险分成可忽略风险和不可忽略风险,可忽略风险通常无须采取措施,不可忽略风险需要采取措施使收益超过风险或达到可以接受的程度,这就需要人们时刻动态评估抗生素的风险收益比,当风险大于收益时,可以通过修改说明书,完善不良反应、禁忌证、适应证、药物相互作用等信息来降低使用风险。根据不同风险水平高低可以将抗生素分级使用,一线抗生素在使用上无过多限制,二线抗生素只有在一线抗生素无效后使用,在治疗高死亡率的疾病比如败血症或者脓毒血症,只要证明治疗产生的效果大于风险时,就可以接受高风险的相对严重一些的不良反应。药品不良反应报告是进行风险评估的重要依据,由于制药企业担心过多报告不良反应会影响自身产品销售,过去对此一般比较消极,我国80%以上的不良反应报告来自医疗机构,而在美国90%以上的药品不良反应报告来自企业,企业主导的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和风险管理体系具有高度灵活性和持续稳定性,可以发现问题后第一时间采取措施[22]。2019年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强调企业是风险管理的主体,产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为了对企业报告形成约束机制,可以尝试将企业不良反应监测制度用法律强制执行,如果消极报告不良反应,药品造成伤害则加重赔偿患者。
2.2 对抗生素使用数据进行分析管理和处方管理
可以建立抗生素用药管理系统对每个医疗单位以及医生使用抗生素的情况进行统计,根据不同的疾病建立抗生素使用的基准水平,将个体和单位的抗生素使用和基准水平进行比较,发现使用异常的数据。同时每个单位建立抗生素使用负责人制度,对所管辖的组织内的整个抗生素使用水平进行总体把握,对抗生素的使用者提供必要的教育,目的并不是单一限制抗生素的使用,而是根据疾病的种类去合理地使用抗生素,包括使用的剂量、种类、疗程等。可以尝试建立标准化抗生素给药比率(SAAR),按照医院的设施科室人员以及就诊情况建立抗生素使用的预测值,将实际使用的情况和预测值进行比较,从而对抗生素的使用进行监管。美国有大约200多家医院向疾控中心提供抗生素的使用数据,通过SAAR系统来评估使用的合理性。医生开具治疗指南以外的抗生素时,需要说明理由,并且在系统中进行注释,该系统还可以进行临床决策支持,实现安全和适当地使用抗生素,当医疗保健从业人员开出对特定患者构成严重心脏不良事件相关风险的抗生素时,该系统会生成电子警报。通过将药物的已知风险信息与患者的具体特征相结合,该系统可以帮助患者进行个性化治疗并改善健康结果。临床决策支持系统重要的是患者的用药数据,电子病历的广泛应用使得创建用于临床决策支持系统成为可能,有助于确保药物的安全使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利用大数据进行抗生素处方监管方面也进行了探索,他们从大学卫生系统内五家医院的电子健康记录软件中提取患者数据,这些数据涉及人口统计学,预先存在的医疗条件,感染的严重程度,来源和源头控制措施,微生物种类数据,抗生素治疗数据和临床结果,在获得数据的同时注意保护患者的隐私,使用自动提取过程可以有效地获得抗生素处方监管和处方点评所需的大约95%的数据。在英国基于用药数据的抗生素管理政策已经发挥有益的作用,减少了头孢菌素类和氟喹诺酮类抗生素的使用同时也减少了艰难羧酸杆菌感染的发生。目标教育及外展计划是通过对医务人员和患者进行关于药品风险的特殊教育来增加这些人群对药品风险的了解,以达到抗生素安全使用的目的。可以给医务人员发相关的指导信件,针对医务人员开展抗生素使用的培训和继续教育,发布药品不良反应公告,改变药品不科学的标签和说明书,通过建立患者疾病与用药管理系统,对某些患者购药采取限制措施,对患者进行如何用药相关知识的教育使其了解风险管理内容,签署用药知情同意书 、进行药物流行病学研究 ,对产品风险和特征化风险因素进行量化,对药品适应证进行限制、降低药品的使用剂量等。
2.3 发挥院内专业人士的作用
对于抗生素风险的认识判断可以汇集各个方面的专家进行有效沟通交流汇总,类似头脑风暴法,整合不同学科的专业人士进行风险识别和分析,各种不同的观点不能被压制,确保风险能够被识别,经过充分讨论的风险识别和应对方案才能够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比如医院内在药事管理委员会的牵头下,组织各个科室主任,护理部门负责人,药房主任等对抗生素的安全性进行充分讨论,对风险水平高的抗生素品种的风险等级用数字定量或定性描述,将抗生素的使用风险分为需要应对的和不需要应对两大类,要特别关注发生频率低但结果比较严重的不良反应,对于轻微的不良反应可以选择忽略,从而集中科室及院内的力量去解决重点突出问题。也可以将过去曾经在使用抗生素过程中暴露出的风险点编制成检查表,医务人员在用药过程中关注检查表中的风险项进行关注警戒,如果高风险点出现按照标准的处置措施进行操作。在抗生素风险管理方面要特别发挥执业药师的作用,药师是抗生素管理计划的重要力量,在美国创伤治疗中心,大约五分之一的药师参与抗生素处方管理[23]。药师相对于医生对药物的代谢动力学参数更加专业,在临床血药浓度监测,准确控制用药剂量,同时在联合用药方面有技术优势,可以协同医生为患者选择抗生素品种,降低抗生素耐药率[24]。药剂师对药物的不良反应更加地关注,而且对医生的不合理处方行为进行了很好的制约。加强药师和患者之间关于合理使用抗生素以及滥用风险等内容的沟通,充分利用社区医院网络分布广,医护人员亲和力强的优势,加强社区抗生素滥用风险的宣传教育。对家庭中不同群体用药过程中风险传递的特点进行深入研究,加强老人、儿童等用药群体的风险提示和监测级别,定期发布社区抗生素使用风险监测报告。
2.4 建立抗生素使用指标和优化管理
抗生素合理使用可以利用指标进行精确量化管理,最常用的指标是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定义日剂量(DDD),通常表示为每100 000人(门诊使用)和每1 000患者日(住院)的DDD。这一指标可以在医疗机构或国家之间(或医疗机构内部不同时期或在不同部门之间)进行标准化比较,并且很容易获得使用数据,为抗生素的标准化利用提供了基础。另外一个衡量抗生素使用量的指标是每种服用抗生素的治疗天数(DOT)(例如3种不同的抗生素服用3 d,每次等于9个DOT),另外一个指标是治疗长度(LOT),也称为抗菌素暴露时间,这是患者接受抗生素的天数,而与不同抗生素的数量无关(例如,3种不同的抗生素,每次服用3 d,每组等于3个治疗长度)[25]。LOT对治疗持续时间给出了更准确的数值,但LOT和DOT都没有反应给药的剂量,并且两者都需要个体水平的数据。与DDD一样,DOT和LOT可以表示为密度,即每1 000个患者日[26]的DOT(或LOT),通过这些指标可以对抗生素的使用进行量化管理。在一项针对400名全科医生和429名传染病专家的调查中,抗生素耐药性在社区获得性肺炎治疗抗生素选择的七个决定因素中排名最低[27],医生选择药品首先考虑的是疗效,面对短期和长期影响,医生更倾向于短期影响。跟踪调查发现限定抗生素的使用或者排除某些抗生素的使用在很多情况下不会降低抗生素的使用成本,相反会大概率造成用药成本的上升,这有些出乎人们的预料。在20世纪进行的一项试验,对12 997名患者的护理成本进行了研究,护理成本的增加和严格限制抗生素处方是正相关的[28],这项研究表明,我们如果仅仅从经济的角度限制抗生素处方,可能会导致治疗成本的增加。因此,对于抗生素带来的风险因素,我们在制定政策时不应该从整体上限制抗生素的使用,而是应该限制抗生素在某些人群中的应用,缩短抗生素的用药周期,尽可能用窄谱针对性强的品种,同时对于病毒感染严格抗生素的使用,从这些渠道来优化抗生素的使用,而不是简单地一刀切。另外也包括利用生物技术手段研发推广预防耐药性微生物引起的原发性或继发性感染的疫苗,预防耐药微生物的最佳方法是首先防止患者感染,疫苗可以成为减轻细菌耐药性总体负担的关键工具。还可以通过抗生素的医保支付比例的调整来控制抗生素使用量,瑞典医政部门曾经将四环素从医保目录中删除,并把其他各类抗生素的报销比例从75%降到50%,这项改革使四环素在临床上的使用量降低了42%,其他抗生素的使用也明显减少,这表明抗生素类药物的报销比例和抗生素的使用量有一定的负相关性,比如日本患者在使用抗生素时除了医保个人部分支付外,还要额外支付一定费用,患者就会主动地去搜集信息,判断使用抗生素是否有必要[29],总之建立医生、药师、企业本身、患者共同关心、营造抗生素安全使用的氛围是必要的。
2.5 企业建立风险管理基金
企业储备一定基金弥补未来可能的风险损失,比如支付产品召回的费用,产品更换标识、说明书等费用。监管部门制定对于企业自身产品严重不良反应造成患者身体损害进行赔偿的制度,赔付的科目包括医疗费、医疗补贴、残疾生活补助费、残疾儿童养育费等,调动企业对自身产品风险管理的积极性。
3 总结
降低或减低抗生素使用风险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既需要规范医务人员的处方,又需要提高患者对于风险的认识,利用科技手段例如大数据等进行处方的实时跟踪以及预警,同时需要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不良反应监测体系,以及通过调整医保报销比例和建立患者伤害赔付制度来从微观使用和宏观政策制定层面来降低抗生素的使用风险,发挥抗生素风险管理的“协同共治”效应。
参 考 文 献
金辉, 宋金波, 曲毅, 等. 我国药品风险管理现状的认识和思考[J]. 中国药物警戒, 2010, 7(4): 229-231.
陆柯茹, 胡明, 蒋学华. 药品风险管理中的风险沟通方法及思考[J]. 中国药房, 2010, 21 (17 ): 1545-1549.
宁艳阳, 杨悦.美国药品风险管理对我国的启示[J]. 中国新药杂志, 2010, 19(23): 2120-2123
肖永红. 我国临床抗菌药物合理应用现状与思考[J]. 中国执业药师, 2011, 8(4): 4-9
Anderson T. Countries mull over incentives for developing antibiotics[J]. Lancet, 2016, 387(10031): 1894-1895.
Holmes A H, Moore L S, Sundsfjord A, et al. Understanding the mechanisms and drivers of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J]. Lancet, 2016, 387(10014): 176-187.
Korpela K, de Vos W M. Antibiotic use in childhood alters the gut microbiota and predisposes to overweight[J]. Microb Cell, 2016, 3(7): 296-298.
Costelloe C, Metcalfe C, Lovering A, et al. Effect of antibiotic prescribing in primary care on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in individual patients: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BMJ, 2010, 340: c2096.
Albrich W C, Monnet D L, Harbarth S. Antibiotic selection pressure and resistance in Streptococcus pneumoniae and Streptococcus pyogenes[J]. Emerg Infect Dis, 2004, 10(3): 514-517.
Bergman M, Huikko S, Pihlajam?ki M, et al. Effect of macrolide consumption on erythromycin resistance in Streptococcus pyogenes in Finland in 1997-2001[J]. Clin Infect Dis, 2004, 38(9): 1251-1256.
Fridkin S K, Edwards J R, Courval J M, et al. The effect of vancomycin and third-generation cephalosporins on prevalence of vancomycin-resistant enterococci in 126 U.S. adult intensive care units[J]. Ann Intern Med, 2001, 135(3): 175-183.
Mac Dougall C, Powell J P, Johnson C K, et al. Hospital and community fluoroquinolone use and resistance in Staphylococcus aureus and Escherichia coli in 17 US hospitals[J]. Clin Infect Dis, 2005, 41(4): 435-440.
Che M L, Yan Y C, Zhang Y, et al. Analysis of drug-induced acute renal failure in Shanghai[J]. Zhonghua Yi Xue Za Zhi, 2009, 89(11): 744-749.
Reis A M, Cassiani S H. Adverse drug events in an intensive care unit of a university hospital[J]. Eur J Clin Pharmacol, 2011, 67(6): 625-632.
Grill MF, Maganti R. Cephalosporin-induced neurotoxicity: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potential pathogenic mechanisms, and the role of electroencephalographic monitoring[J]. Ann Pharmacother, 2008, 42(12): 1843-1850.
Schliamser S E, Cars O, Norrby S R. Neurotoxicity of beta-lactam antibiotics: predisposing factors and pathogenesis[J]. J Antimicrob Chemother, 1991, 27(4): 405-425.
Gutnick MJ, Prince DA. Penicillinase and the convulsant action of penicillin[J]. Neurology, 1971, 21(7): 759-764.
Saidinejad M, Ewald M B, Shannon M W. Transient psychosis in an immune-competent patient after oral trimethoprim-sulfamethoxazole administration[J]. Pediatrics, 2005, 115(6): e739-741.
Patterson R G, Couchenour R L. Trimethoprim-sulfamethoxazole-induced tremor in an immunocompetent patients[J]. Pharmacotherapy, 1999, 19(12): 1456-1458.
王雷, 邵蓉. 欧盟上市许可人制度下药品安全相关责任主体法律责任分析及其启示[J]. 中国卫生产业, 2015, 12(33): 7-10.
于丽萍. 在药品安全监管领域引入风险管理意识[J]. 首都医药, 2010, 17(20): 11.
马保岭.谈风险管理在药品监管中的应用[J]. 齐鲁药事, 2010, 29(12): 756-757.
Hamblin S, Rumbaugh K, Miller R. Prevention of adverse drug events and cost savings associated with PharmD interventions in an academic level I trauma center: an evidence-based approach[J]. J Trauma Acute Care Surg, 2012, 73(6): 1484-1490.
DiazGranados C A. Prospective audit for antimicrobial stewardship in intensive care: impact on resistance and clinical outcomes[J]. Am J Infect Control, 2012, 40(6): 526-529.
Polk R E, Hohmann S F, Medvedev S, et al. Benchmarking risk-adjusted adult antibacterial drug use in 70 US academic medical center hospitals[J]. Clin Infect Dis, 2011, 53(11): 1100-1110.
Harbarth S, Viot M, Beeler I, et al. Variation in antimicrobial utilization for febrile neutropenia in cancer patients[J]. Infection, 2000, 28(6): 375-378.
Metlay J P, Shea J A, Crossette L B. Tensions in antibiotic prescribing: pitting social concerns against the interests of individual patients[J]. J Gen Intern Med, 2002, 17(2): 87-94.
Horn S D.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drug formularies[J]. Am J Health Syst Pharm, 1996, 53(18): 2204-2206.
贾国舒, 梁毅. 日本药品上市后风险管理计划研究及对我国的启示[J]. 中国药房, 2021, 32(19): 2305-2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