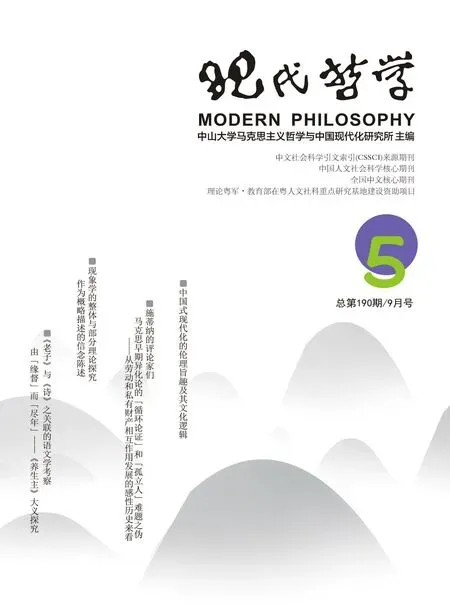破出存在的责任
--列维纳斯的责任伦理思想探析
2023-03-31王玉静
王玉静
一、问题之源起:破出存在的责任?
列维纳斯以其毕生的心血逃离存在的同一和暴力,这从他早期著作《从存在到存在者》中可窥得端倪,如他在这本书的前言提到:“引领一个存在者趋向善的过程……是一个摆脱存在以及描述它的范畴的过程,是一种出越。”(1)[法]列维纳斯:《从存在到存在者》,吴蕙仪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前言第1页。到《总体与无限》时,这种逃离更加显明。他认为将本体论置于伦理学之前,就是将一种“知”的关系置于伦理的关系之前。存在在存在者之前,是存在对存在者的宰制,是一种对他者的同一化。在列维纳斯看来,哲学中的第一关系是伦理关系,而不是事前预设的非人格的存在。如果说他在《总体与无限》中还用的是本体论的语言来试图越出存在,那么在晚期的重要著作《他者的人文主义》(Humanismedel’autrehomme)和《另外于是,或在超过是其所是之处》(Autrementqu’êtreouau-delàdel’essence)(下文简称《另外于是》)中,他用的则是伦理的语言,抽丝剥茧地为超越存在进行论证。
如何超越存在?列维纳斯认为,要“以破出存在的方式来超越存在”,而这破出存在的形式就是“对他人的责任”。(2)[法]列维纳斯:《论来到观念的上帝》,王恒,王士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24、27页。在思想成熟的晚期,他不止一次提到“破出存在就是责任”(3)[法]列维纳斯:《论来到观念的上帝》,第24-30页;[法]列维纳斯:《伦理与无限:与菲利普·尼莫的对话》,王士盛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61页。这一说法。同时,他认为破出存在就是超越存在,就是伦理:“超出存在,善则是卓越、高尚--伦理不是存在的一个构成环节,伦理异于且好于存在,是超出存在之可能性本身。”(4)[法]列维纳斯:《论来到观念的上帝》,第115页。可以说,列维纳斯是在这种“伦理”的范畴内谈论责任:伦理的形式就是责任。可见,“责任”这一概念是梳理列维纳斯晚期对破出存在进行证成的核心。那么,如何在这种超出存在、好于存在的语境中言说责任?列维纳斯认为,责任“并非出自于原则之普遍性的虔敬,亦非出自一种道德的明见性”(5)[法]列维纳斯:《论来到观念的上帝》,第29页。,由此,我们既不能用本体论的语言去言说责任,也不能在一种道德原则中讨论责任。
那么,如何言说对他人的责任?在列维纳斯看来,对他人的责任不只是主体(性)的基础性、首要性和根本性结构(6)[法]列维纳斯:《伦理与无限:与菲利普·尼莫的对话》,第56页。,还是人性的基础(因为人性就是主体性),是人破出存在的缘由,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所以,列维纳斯谈及的责任,不是如传统伦理学所说的要为自己的行为而承担的“责任”,而是在他自己构建的语言体系中言说责任,责任即是对他者的应承。责任不是要承担的,而是被动地“降于”我的。具体来说,列维纳斯在《另外于是》一书中将对他者的责任等同于“说”“善”“切近”“感受性”和“替代”。由此,引出本文要探讨的问题:我们尝试在责任和“说”“善”“切近”“感受性”及“替代”的关系中,考察列维纳斯的责任伦理思想,以期从一个较为全面的视角还原“责任”这一概念在其思想中的统领性地位。
二、“说”和“所说”:责任的言说结构
既然责任是一种应答关系:此一者对另一者(7)“此一者”即“同者”,“另一者”即“他者”。下文择取这两个词的后者译法。之应承(8)伍晓明在《另外于是》一书中将“responsabilité”一词译为“应承”,而非“责任”,是取列维纳斯对此阐释时,强调责任之“应”(répondre):我应(réponds)于另一者。本文仍然选取接受度较高的“责任”一词,一是方便在一种整合的思想语境中对其讨论,二是笔者尝试讨论的“责任伦理”已经是约定俗成的,被普遍认可的概念。。那么,实现责任这一应答关系的首要形式便是言说。列维纳斯首先就是从一种言说结构来分析责任,因为“语言关系的本质因素是呼唤,是呼告”(9)[法]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朱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4页。。他认为说(dire)就是责任:“那起源的或先于起源的说,那前言之言,结起了一张应承之密网。”(10)[法]列维纳斯:《另外于是,或超过是其所是之处》,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1页。柯林·戴维斯(Colin Davis)也提到:说就是我和他者相遇之处,是我向他者的暴露。(11)See Colin Davis, Levinas:An Introduction,Cambridge:Polity Press,1996,p. 76.具体而言,说就是为他者的责任,是“此一者而为另一者”(12)[法]列维纳斯:《另外于是,或超过是其所是之处》,第20页。。
列维纳斯在一种非意向性的,抑或说颠倒意向性的意义上言“说”。在他看来,无论是“是其所是”(essence),还是“是之去是”(l’esse de l’être)(13)本文在选取部分核心概念时,遵从伍晓明在《另外于是》中的译法,同时将两种译法都附上。如l’être译为“是”(存在);essence译为“是其所是”(本质);l’esse de l’être译为“是之去是”(存在之存在),ontologie译为“是之为是论”(本体论)等。参见《另外于是》译序。,都是为己的;而“说”通过接近他者,为了他者,指示的是“无私”或“无是”。这“无私”或“无是”是一种“极端的沉重”,其将“是之去是”里朝外地翻了过来,所有这些“指示着这一先于起源的语言,指示着此一者对另一者之应承,指示着此一者对另一者之替代”(14)[法]列维纳斯:《另外于是,或超过是其所是之处》,第22页。。
既然“说”的状态是“先于起源”“无端”“无起源”,那么“说”如何显现?列维纳斯认为,“说”要隶属于所说,隶属于是之为是论/本体论,才能显现,这也是“显现所要求之代价”。(15)同上,第23页。如是,“说”是否就消失在“所说”之中?
在回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从构词上区别“说”(dire)和“所说”(dit):dire是dit的动词原形,而dit是dire的过去分词的名词化,意思是“已经被说出之事”。可见,“说”指涉的是一种完全开放的状态,因为其没有“所说”的内容,所以我们甚至无法言“说”,“说”是一种无法言之的超越。而“所说”是已经说出之事、是意向性的指示、是已经被强制规定的历史,是是之为是论/本体论的诞生之处,所以指涉的是一种内在的同一。总之,“所说”源于“说”,而“说”通过“所说”显现。列维纳斯将两者的关系勾勒为一种“主体-对象”(16)[法]列维纳斯:《另外于是,或超过是其所是之处》,第122页。关系。柯林·戴维斯指出,列维纳斯通过分析“说”和“所说”,将“语言问题和他的伦理关切联系起来”。(17)Colin Davis,Levinas:An Introdction,p. 76.而这伦理关切恰恰是他晚期思想的核心,也是他破出存在的路径。
从“说”和“所说”的关系,可以窥见责任如何被遮蔽:“而在所言中,在词语的遮盖下,信息在交换,祝愿在传播,责任心在逃逸”。(18)[法]勒维纳斯:《上帝·死亡和时间》,余中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97年,第236页。这里的“所言”即“所说”,同下文。“说”必然要凝练成为“所说”,所以我们向来关注后者,而遗忘说本身之面向他者。在“说”变成“所说”的过程中,在不断被话题化的过程中,切近他者的责任被遮蔽。于是,“说”就消失在“所说”之中。因此,问题的关键也是列维纳斯《另外于是》整本书的核心:要超越是/存在,超越是其所是/本质,这里的超越毋宁说是一种回归、一种还原(19)这里的“还原”尽管是一个现象学的术语,但列维纳斯并没有在现象学范畴内使用它,它指的是“先于本源的、先于现象的,在自我的构成和意识诞生之前”。(Colin Davis,Levinas:An Introdction,p.77.),即从“所说”到“说”的还原。通过还原才能真正切近他者,才能实现责任。
为什么要将“所说”还原为“说”呢?因为“所说”这种同一化的、被固定的名词性系统,关注的是这个世界的实体,是是/存在之秩序,体现是之为是/存在之为存在的努力,代表的是是/存在的暴力:“任何的所言都不能与言说的真诚性相比,任何的所言都不能与先于真的真实性相符。”(20)[法]勒维纳斯:《上帝·死亡和时间》,第236-237页。这里的言说同“说”,同下文。因此,“所说”是没有公正的,因为是/存在的本质为了存在而不顾及他人的;而“说”作为对他者的责任则是公正的开始,“因为说或应承要求公正,才有那关于所说和关于是的问题”(21)[法]列维纳斯:《另外于是,或超过是其所是之处》,第120页。。为了实现公正,就要将“所说”还原为“说”。
如何还原?是否能真正的还原?列维纳斯首先肯定了这种还原的必要性,并给出关键性的提示,即作为对他人之责任的说“乃是其所是之打断”,“乃以好的暴力强制规定下来的某种无私/无是”;而对是其所是者的打断是还原的关键,“对是其所是的伦理性打断才是那供给还原以能量者”。(22)同上,第115、117页。
那么,如何打断?打断之后如何继续?从上文分析可知,所说是是之为是论/本体论意义上的是其所是/本质,而“说”是“无端”“无源”,是伦理意义上“无私”“无是”。诚然,列维纳斯想通过这种言说结构,将是其所是/本质还原为伦理上“无私”和“无是”的“此一者为另一者”的责任。这种还原是“回到尚未及于是之处”,同时“绝不以任何方式表示着一种是之为是论之被另一种所纠正”(23)同上,第118页。,因为“纠正”还是在是之为是论/本体论之中,只有打断,才能将所说从被凝固的,被同一的是之为是论/本体论中抛出,回到“那尚未及于是之处或那超过是之处”。但列维纳斯明确指出,“那尚未及于是之处或那超过是之处并非某个在尚未及于或超过是之处的是其所是者”,即我们要超越这存在,不是用另一好的存在替代这个存在,而是要完全地破出存在,要“还原到表示,还原到包含在应承之中的此一者而为另一者,亦即那人性之处或非处,人性之处与非处,人性之乌托邦,还原到那字面意义上的不安或此种不安之不同时”。(24)同上,第118、119页。既然“说”是“无端”“无源”,甚至我们都无法言说,那么我们就不能再用是之为是论/本体论的语言去思考这还原,不仅要还原到一种可以言说的“说”,而且要颠覆“所说”所关注的是之为是。
有学者注意到这一还原在方法上的不可行:因为“说”是无端、无源,所以“所说”不可能完全被还原,每次还原必定会有剩余。(25)See Robert D Walsh,“Language and Responsibility in the Ethical Philosophy of Emmanuel Levinas”,Hermeneutics and the Tradition: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Catholic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 Vol 62,ed. by Daniel O. Dahlstrom,Washington:The American Catholic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1988,pp. 95-105.对此,孙向晨敏锐地指出:“莱维纳斯就是要揭示那些在语言的存在论方面所发现不了的东西,对他来说‘言说’的内容没有什么好注意的,但‘言说’之谦卑的态度却包涵了太多可以挖掘的秘密。”(26)孙向晨:《面对他者:莱维纳斯哲学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第204页。显然,这种还原不是一蹴而就,而是不断地“打断”,是“无尽的批判”和“怀疑主义”的“螺旋运动”。从“所说”到“说”的还原,并不是其内容的还原,而是言说形式的还原,因为“说”甚至并没有内容,而是一种完全的给予。在被固化为名词的“所说”之中,对他者的责任被遮蔽,只有不断地还原才能回到责任即“说”。
三、善:责任的伦理意涵
在《总体与无限》的结尾,列维纳斯提到:“我们以我们的方式遇到了柏拉图关于善超逾存在的思想。”(27)[法]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第284页。这里,“我们的方式”指的是一种既不是以神学语言,也不是以存在论语言的方式超越。但列维纳斯在《总体与无限》中尚且使用存在论的语言言说善或他者,他真正从超越的角度或者说在破出存在的范畴谈论善是在《另外于是》中。德里达说:“以我们的方式,也就是说伦理学出越并不朝向善的中立性投射,而是朝向他人。”(28)[法]德里达:《书写与差异》,张宁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41页。《总体与无限》中的“朝向他人”,到了《另外于是》就是对他人的应承/责任。在《另外于是》中,列维纳斯是在一种去私和颠倒意向性的角度谈论责任,这种为他性的责任就是善。具体来说,善是对我的呼召:“一种与善的关系,它把我传讯到对他人的责任心上来。”(29)[法]勒维纳斯:《上帝·死亡和时间》,第216页。可以说,与自我那种为了其是/存在做出的努力相反,责任不是为己的,而是此一者而为另一者,而这种为他的责任是自我的变节,是一种去私,并具有伦理意涵--善。
同时,这种呼召是一种绝对的被动:“责任心的这种与自由相比的先行性意味着善的善良:善应该在我还不能选择它之前挑选我;善必须首先选上我。”(30)同上,第215页。与自律相比,列维纳斯更强调一种他律:作为善的责任,不是人自主地选择,善先选择我意味着我对善的被动地接受,并且这种被动是绝对的且时间上先于一切。“在那尚未及于意识之处,此被动性或此应承或此痛苦存在于善对此一者的此种先于起源的支配控制之中,此种支配控制比任何现在、任何开始都更加古老。”(31)[法]列维纳斯:《另外于是,或超过是其所是之处》,第146页。列维纳斯强调善对人的选择,而不是人主动地选择善。这意味着责任是人内在的本质:“我的存在意味着不能推卸责任,仿佛整个创造的大厦都在我的肩上。”(32)E. Levinas,Humanisme de l’autre homme,Paris :Fata Morgana,1972,p. 54.
列维纳斯为什么要强调善在人对其选择前就选择了人?因为只有在这种绝对的被动性中,主体对他者的责任才是第一位的,而主体的自我意识或主体为是/存在的努力是其次的。这种绝对的被动意味着意向性的颠倒。列维纳斯指出:“被动性是善的位置--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非处--它是存在的规则之例外。”(33)Ibid.,p. 86.显然,将善置于一种绝对的被动时,才能真正实现对是/存在的超出。善呼召人对他者负责,在人选择它之前就选择了人。这种完全被动的责任,更能体现责任是人之为人的本质。
那么,我们如何具体地谈论善?在责任的言说结构中,“说”必定要在“所说”中得以显现,“所说”既出卖善又在我们面前传达善。(34)参见[法]列维纳斯:《另外于是,或超过是其所是之处》,第327页。具体来说,列维纳斯在切近中找到善:“在其不安之中,在其对自身的清空之中,在其不同时之中,切近不是比所有的安歇、比所有被抓住了的片刻所具有的充实性都更好吗?”(35)[法]列维纳斯:《另外于是,或超过是其所是之处》,第224页。这里的“好”(bien)就是善,“不安”是他者时刻萦于我怀,“对自身的清空”是回到己,“不同时”是和他者的不对称,所有这些都指向“他人具有价值”。(36)[法]列维纳斯:《论来到观念的上帝》,第234页。这番论证恰恰是对“善就是对他者责任”的回应。善就是责任意味着,善的一切衡量标准悬系于对他者负责。
另一方面,他者不是以强者,而是以贫穷的和软弱的状态在我面前呈现:“另一者性带着贫困和软弱所具有的全部负担落在我身上。”(37)[法]列维纳斯:《另外于是,或超过是其所是之处》,第58页。这种“另一者性”的贫穷和软弱,恰恰源于犹太教的上帝观。显然,列维纳斯对善的阐释路数与他的犹太身份以及二战经历有关:“而其安歇之中亦只有一个不安或不眠,那就是自另一者之悲惨而来的阴影、不安或不眠。”(38)同上,第224页。我们发现,列维纳斯理解的善并不是如康德理解的善的意志,也不是海德格尔的存在内的善,更不是要勾勒一个超越的神,列维纳斯是为了阐释为他者的责任而对善这个概念赋予这超越存在的意义。可以说,善因将他者置于首位,为他者负责而有意义,于是,为他者的善就激发出主体的正义。甚至可以说,因为善源自对他者的责任,所以善就是正义。韩潮指出,列维纳斯“是以犹太思想与现代哲学相结合的‘无限性’概念去解释柏拉图的‘善’”,甚至认为“列维纳斯的工作是以犹太的‘正义’取代了希腊的‘善’”。(39)韩潮:《列维纳斯与海德格尔论柏拉图“善高于存在”》,高宣扬主编:《法兰西思想评论》第3卷,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40-141页。那么,善呼召为他者的责任是否有具体的形式呢?这就是切近和感受性。
四、切近和感受性:责任的具体形式
从上文的讨论可知,列维纳斯强调的是责任中的他律:善/无端呼召我对他者负责。这种对他者的负责/应承就是切近,它作为“同者而为另一者”,是责任的具体形式。然而,它并不是物理上的接近他者,而是对他者的“扰乱”。一方面,这种接近是时间上的不同时:“切近--从我到另一者--是在两个时间之中的,并因此而是一种超越。”(40)[法]列维纳斯《另外于是,或超过是其所是之处》,第204页。主体和他者不在同一时间之中,没有共同的现在,所以切近作为与他者的关系,是“处于所有的知之外的非无差异/有动于衷”(41)同上,第233页。。另一方面,这种“知之外”的绝对的差异是他者萦于我怀的关键,造成了切近对总体的打破:“切近是一个被诸项之间的差异所打破的全体,但在这一情况之中,差异乃是非无差异/有动于衷,而打破则是[另一者]萦[我之]怀。”(42)同上,第201页。可见,切近不是单方面的向他者的暴露,其扰乱的核心在于打破。
我们知道,列维纳斯是在一种逆于意向性的、非是之为是论/本体论的语境中谈论责任和切近。可以说,逃离存在的同一是他论述的前提。由此,他才一直强调这“不同时”及“差异”。正因这种“不同时”及“差异”,对主体来说,他者的脸、这种绝对的他异性,就是一种在切近中的颤栗,“是相对于认识而言全然另外的颤栗--人的颤栗(frémissement)”。(43)同上,第211页。
除了主体和他者的这种“不同时”和“差异”,造成颤栗的原因还在于同者/主体的感受性:为他者之责任或切近其实就是“让自己剥皮露肉之说,是切肤并触及神经末梢之感受性”。(44)同上,第52页。列维纳斯甚至认为,主体性就是“易受伤害性”、就是“感受性”。(45)同上,第142页。如果人是没有肉身的唯灵的生命,对外界的任何刺激都不会有感觉,他何以能感受到他者的脸并有回应呢?所以,人首先是作为肉身的存在才有感觉,才能享受和被伤害。无论是主体对他者的颤栗,还是切近中的扰乱,根本原因都在于主体的感受性和易受伤害性,更确切地说,是主体的身体性和物质性。
我们先讨论身体性和物质性,再返回主体的感受性。列维纳斯强调物质性或身体的重要,这在他的早期思想中就已显明。王嘉军提到:“物质性不是一个绝对消极的概念,正是由于其限定性,才使得主体遭遇外部和他者,并从这种遭遇中获得拯救得以可能。”(46)[法]列维纳斯:《时间与他者》,王嘉军译,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20年,“译者导读”第xvi页。如果没有这身体性,我们便无从超越,这身体性是我们保持自身同一的前提,是我们和他人的界限,也是我们得以超越自身的原因。如果说列维纳斯在早期还是从身体的界限性出发,考虑我和他者的关系,那么他在《另外于是》中赋予身体性更多的是被动性,甚至认为被动性表达的就是身体性。(47)参见[法]列维纳斯:《另外于是,或超过是其所是之处》,第132页。
这种身体性“作为[可以感受]痛/苦的可能性;作为那就其本身而言即是易于遭受病痛的感受性;作为那毫无遮盖的、给出自身的、在自己的皮肤之中忍痛受苦的己;作为那待在自己的皮肤之内待得极不舒服的己,因为它并不为了自身而有此皮肤;作为易受伤害性”(48)同上,第132页。。身体性就是主体的感受性,且这种感受并不是让自己享受,而是一种被动的、需要忍受的“易受伤害性”。可以说,从主体的享受到主体在痛苦中的折磨是列维纳斯对“感受性”这一观念的重要转变。“感受性扩展为主体的被动性和易受伤害性,这在主体内部打开了朝向他人的通道。”(49)钱捷、张荔君:《感受性在列维纳斯思想中的转变及与他人或超越性的关系》,《现代哲学》2020年第5期,第98页。感受性这种向他人的敞开为切近提供了可能。只有对他人的直接感官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在对他人的接触中,主体才能真正承受他者面容的颤栗以及随之带来的痛苦。主体在这痛苦的扭绞中让与自己,“食人以食,衣人以衣,居人以屋”,在“自身之被撕离于自身”中破出存在。(50)[法]列维纳斯:《另外于是,或超过是其所是之处》,第189、185页。
列维纳斯一再强调,西方哲学由是之为是论/本体论演变出来的精神性是一种意识或知的同一性乃至暴力,在这种的同一性之中,主体在存在论中找不到自己,由此引发了焦虑和苦恼。而重返身体性,在感受性、易受伤害性和切近中,承担对他者的责任才是人性之根本。作为为他者的切近,不是要和他者融合,也不是抹杀他者的他异性,更不是将主体压抑在他者之中。(51)同上,第208页。那么,在这切近中,主体和这具有绝对他异性的他者如何共处?列维纳斯认为“这一接近最终会将自身显示为替代”(52)同上,第227页。。
五、替代:责任的最终目的
替代指涉对他者的替代,那么是谁在替代他者?是传统哲学中的主体,还是己?主体又和主体性有何区别?可见,缕清“己”“主体”和“主体性”这几个概念是理解列维纳斯“替代”的关键。
首先,我们要区分主体和主体性。在应于他人的责任之中,主体是“是其所是”,那么主体性就是为他者、是人性,主体必须要“去位”(dé-position)或“失处”(dé-situation),而主体性并不在这种主体的去位之中被替代,而是回归一种独一无二的人性。列维纳斯认为,主体性是为他、是人性:“必须在作为接近之说中去显示主体之去位或失处,而此主体同时却又依然保持为不可被换下的独一无二者,而此即主体之主体性!”(53)同上,第125页。主体之去位或失处,就是主体性显现,就是人性之回归!而这主体去位或失处之后,谁为他者负责?
列维纳斯为了逃离存在论中处于绝对主动地位的主体,用的是逆于意向性的“己”这一概念。责任主体不是“主体”,而是去位的“己”。“己”就是处于完全被动地位的、被指控的,处于宾格的小写的“我”(moi)。“回到自己就是把自己清空到连‘某一者’这样一个近乎纯形式的同一性都没有的地步”(54)同上,第223页。。这种清空自己同时也是“在……之前”(coram),在这里即是在他者之前,为他者负责。所以,回到己和为他者负责是同时的、同步的:回到己就是清空自己,彻底地面对他者;而彻底地对他者负责,就是回到己。“己”恰恰回应了列维纳斯提到的从“主体性”出发的替代。
然而,无论是主体的去位,还是处于绝对宾格的“己”,都是在为他者的责任中的绝对的被动,即“对于诸另一者之应承绝不可能表示着利他的意志,或‘自然仁慈’的本能或爱”(55)[法]列维纳斯:《另外于是,或超过是其所是之处》,第265页。。对他者的责任始终处于对他者震创的萦怀。那么,这种绝对的被动是否意味着“己”之完全没有自由?答案是否定的。列维纳斯认为,对他者的责任虽然是最被动的被动,却“并非表示着对一非我之屈从,却表示着一种敞开,在此之中是之是其所是在[己之为]灵[所]感中被超越了”(56)同上,第274页。。一方面,我因对他者的萦怀处于绝对的被动;另一方面,我因为他者之灵所激发,而呈现一种敞开的状态,像呼吸一样。那么,“己之被动性又如何变成了一种“[己]对于己之把持”呢?”(57)同上,第268页。列维纳斯指出,从这种从绝对的被动变为主动的关键就是替代。
具体来说,这种敞开的状态就是替代,替代就是对他者的责任:“这样的替代和打断发生于[我之]肩起负担之时,此负担紧压在我的身上,没有任何躲开的可能。”(58)同上,第48页。显然,这里的“负担”(charge)就是责任。同时,这里的“替代”不是一种客体地或实体地占据他人的位置,而是从主体性出发的替代,“是作为主体所具有的主体性本身的替代”(59)同上,第48页。。替代就是主体性、就是人性。替代和意向性相逆,是对是/存在的超越,“通过以自身替代他人,主体在其是之中拆解是其所是”(60)同上,第47页。。
结合上节对感受性的分析可知,主体面对他者首先是在一种有接触的,感受性的切近中。所以,替代作为“己”之从绝对的被动到拥有自己的主动的反转,也必须以“恻隐之心的感性为先验条件,必须在与他人直接的面对面中感而后发”,“所以这一替代,尽管极端被动却并非奴役,相反仍有自由在”。(61)朱刚:《替代:勒维纳斯为何以及如何走出存在?》,《哲学研究》2011年第11期,第91-92页。显然,替代发生于为他者的责任之中,与责任并不完全等同。那么,如何看待两者的关系?列维纳斯在《论来到观念的上帝》中,详细解释了责任如何过渡到替代。他认为,西方传统所认为的被动性是一种接受性,即承担责任;然而,在接受中,在迎接中,主体也有构想这被动的感觉。主体从一种完全的被动,转向了主动交出自身,这种列维纳斯言之的“新一层的被动性”(62)[法]列维纳斯:《论来到观念的上帝》,第146页。就是替代。毋宁说,替代是责任最终的形式,是将被动的责任变为主动的形式。因为己在这替代之中“赦免”自己,己在替代中,即“在被动之尽头,己本身逃出了被动或逃出了关系中之诸项所经受的必然限制”,己逃出这绝对的被动的关系而得到自由,“通过对诸另一者的替代,己本身逃出了关系”。(63)[法]列维纳斯:《另外于是,或超过是其所是之处》,第273页。这里的关系意指己完全束缚在他者之中的关系。同时,替代也是被动地应于他者和主动地交出自身的合而为一,这合而为一的极端表述就是“己”之“受难”,“在此呼吸--为他人做出一切牺牲的可能性--之中,主动与被动混而为一”(64)同上,第274页。。
可以说,替代依赖于己为他者负责,也是责任的最终的形式。无论是为他者负责中完全的被动,还是替代中交出自身的主动,关键词都是“为了他者”(pour-l’autre)。列维纳斯不断强调,此一者为另一者中的“为”:“我之为另一者[所做出]的应承就是这一关系中之为。”(65)同上,第237页。中文习惯讲“对”某人的责任,其指涉一种客观的对象性。而列维纳斯强调的“为”不是一种对象化或主题化的参照,他欲意在“说”的层面,而不是“所说”的层面谈论这个“为”(66)[法]列维纳斯:《上帝·死亡和时间》,第187页。。
对于这个“为”,列维纳斯在《上帝·死亡和时间》中有细致的解释:“这个为是人接近他的下一来者的方式,是与他人建立一种不再在一人范围之内的关系的方式。这是一种临近的关系,在其中起作用的是一人对另一人的责任心。”(67)[法]列维纳斯:《上帝·死亡和时间》,第187页。这个“为”他者是在一种伦理意义上的被动关系,彰显的是一种不对等的关系,因为在“为他者”之中,主体所有的一切都为他者建构,“主体就这样成了失去地位的主体”,主体只有在为他中才能重新构建关系,构建自己,否则“我将永远是一个点,一个固定不变的点”。(68)同上,第189页。这个“为”是“一种完全无偿的为,一种与关心/自私断绝了关系的为:一种处于所有先己建立起来的系统之外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为”。(69)[法]列维纳斯:《另外于是,或超过是其所是之处》,第232-233页。但对列维纳斯来说,这还不够。他提到,责任不仅是为了(pour)他者,也是由于(par)他者:“为另一者(或意义)竟一路走到了由于另一者,一路走到了去忍受肉中之刺所引起的烧灼之感,但却又完全无谓。”(70)同上,第130-131页。如果说“为”还是一种伦理上的被动,那么“由于”则更加彻底,是一种先于这被动关系的被动,是被动的被动、根本的被动;换言之,因由他者,主体重新塑造自身。列维纳斯把主体置于绝境:没有他者就没有主体,他者是主体的第一动因。这也是我倒转为己的原因:“我是由于诸另一者而‘在自身之内’的。”(71)同上,第266页。
如果说“为”还有一丝意向性的残留,那么“由于”则完全是一种去私。这就是替代的核心。我们也可以将列维纳斯的上面那句话反过来说:正是因为“由于”另一者/他者,才有“为”另一者/他者:因“由于”他者而倒转自己,清空自己,才能真正“为”他者,才能获得自由。运思至此,我们发现,列维纳斯的“替代”表面上是要通过去位、去私以及逃离帝国主义而“为”他者负责,甚至牺牲,实际上是从一种破出存在论的路径重塑主体和主体性。
六、结 语
在列维纳斯看来,破出存在并不是另一种存在,而是要完全摒除是之为是论/本体论的思维模式。他在以《另外于是》为代表的晚期思想中,用了一套和本体论以及现象学区别的语言--伦理的语言。通过诸如“说”“所说”“切近”“感受性”“替代”等表达伦理的词,他构建出自己责任观。
本文正是对上述概念的逐一辨析,勾勒出列维纳斯的责任伦理思想之概貌。首先,从责任的言说结构--“所说”和“说”之间的关系分析,我们要不停地打断被固化的、被名词化、实体化的“所说”,跳跃出来,回到呼唤他者、为他者负责的“说”。“说”就是提醒我们时刻记得“为他者”的初心。其次,从伦理意涵看,列维纳斯无意于构建一个绝对的、理念的善的概念,而是在超越的角度谈论善。善通过呼召主体向他者负责,而意指一种绝对被动的责任,一种主体在其中没有任何选择权的责任。显然,列维纳斯用善这一概念,为的是给为他者的责任悬设一个具有绝对高度的伦理意涵。再次,为他者的责任具体展现在切近中,在感受性中。切近,作为扰乱,和对总体的打破,并不仅仅意味着向他者暴露,还有他者萦于我怀。最后,替代是为他责任的最终目的,也使为他责任从绝对的被动束缚中挣脱出来,得到自由的路径。可以说,替代回归到人本真的伦理状态:一种完全为他负责的状态。
王恒曾指出:“出离海德格尔的存在,出离胡塞尔的意向性,便成就了列维纳斯的现象学。”(72)王恒:《时间性:自身与他者--从胡塞尔、海德格尔到列维纳斯》,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19页。同样,列维纳斯的责任伦理思想也是对“出离存在”和“出离意向性”的回应,同时,为他者的责任悬系于他者的价值在我之上、之前。这种近似于受难的为他责任诠释了列维纳斯想用希伯来挣脱希腊思想的努力:一种破出存在,逆于意向性的,为他者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