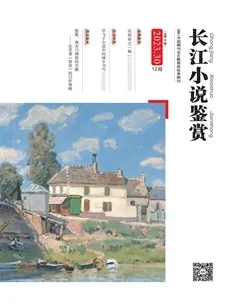“疯癫”与“文明”:《所罗门之歌》中的权力阐释
2023-03-28黄佳宝
[摘 要] 《所罗门之歌》这部小说呈现了美国黑人从废除奴隶制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近百年的窘迫生存环境,再现阶层贫富、男女两性与种族歧视压迫的真实冲突,并提出在物欲横流、急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如何解决精神匮乏、文化失根的社会问题。借助米歇尔·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能够分析这部小说中复杂的权力关系,小说中所提到的家庭之间、黑人种族的上级阶层与下层阶级以及黑白种族之间的话语权力结构表明,当时的社会是优势群体通过规训、惩罚弱势群体,而拥有“文明”的话语权;弱势群体有的“失声”,有的因此造成精神异化进行“疯癫”反抗,也有的走向独立、寻找自我从而获得精神自由。
[关键词] 福柯 话语权力关系 规训 疯癫 文化寻根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2881(2023)30-0069-05
一、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
话语所进行的场景是人与人在交流与互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因而话语具有社会性。说话人与受话人需要在具体的社会语境中展开沟通,同特定社会的文化制度、思想情感和生活方式紧密联系。米歇尔·福柯在话语权力理论中提到,话语主要指在特定社会文化条件下,为了一定目的而说出或写出的论证性话语,是伴随着说和写的过程所进行的一系列社会文化操作活动,是一系列事件,并且强调其是一系列政治事件,通过这些政治事件,话语承载着政权并由政权反过来控制着话语本身。
福柯对于权力的研究早已超过了学界普遍认为的宏观权力范围,如国家、法律这些中心化的存在,他的研究出彩之处就在于对微观权力的研究,他将观察焦点对准精神病院、监狱、修道院等一些社会边缘、阶层底端中的权力关系。并且,他将疯癫的研究范围归为考古学领域,虽然疯癫本身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被人文科学史研究,属于历史语境和历史整体结构,但是福柯却认为疯癫早已被医学和现代社会文化分离出来,逐渐被排除于历史整体之外。因此,他认为疯癫是理性疯狂压迫疯癫的必然结果,其实质是一种“理性疯癫”。
随后,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表明,疯癫与文明的对立和分裂并不是天然存在的。早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二者并不是处于一种二元对立的状态,他在书中提到了“疯癫体验”,认为这是被各种意象笼罩的,是人类的原始堕落、上帝的意志、兽性及其各种变形以及知识中的一切神奇秘密,甚至可以直接体现在该时期的文学文本中,人们借助疯癫表达直觉性领悟并因此进行文学创作,能从文本阐释出疯癫是具有启示性的中心意象。随着时代演变,“文明”社会中产生了禁闭所、精神病院,人们逐渐把疯癫看成一种破坏力量和威胁因素,需要用禁闭来对付它。现代的文明世界要将疯癫与非理性排斥出局,而这个文明的局只是理性权力的建构,“文明”的社会群体与被驱逐的“疯癫”群体争夺话语权力。因此,只有将对有害理性的疯癫因素排除,才能逐渐巩固理性的地位,“文明”世界通过区分、压制疯癫,由此构建了独特的理性话语权,并因此拥有从文化上规范人类文明行为的权力,逐步建立理性社会的秩序。
作为“文明”社会的时代产物,“疯癫”与非理性一直被压抑、囚禁,二者是理性与非理性碰撞的鲜明体现,这一点在托尼·莫里森的《所罗门之歌》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作为一位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对于现代社会中所体现的阶级剥削、种族歧视与性别压迫表现出高度的道德责任感,探索建立属于自己的民族独立尊严和文化传统,更致力于追求多元文化,排斥文化及“文明”社会整体的等级制度。
二、阶层剥削中的话语权力
“阶级制度是现代社会最常见的分层类型,主要以经济地位为基础。但黑人族群中的阶级性往往被种族與性别话语所遮蔽,处于边缘地位而被忽视。”[1]《所罗门之歌》中所涉及的阶层权力结构也不例外,下面将剖析隐藏在小说中的阶层权力压迫。
福柯所说的权力理论除了有人们对其的习惯性理解,还包括了特殊意义。权力首先是一门政治技术,用来对权力主体进行支配,排除所谓阶级或个人的某项权力,还有各种力量关系的结合;权力通过各种力量在运作时展现多样性和丰富性,并且通过这些力的关系在彼此间找到支持,最后建构成一条锁链或一个系统整体,它们也可以彼此孤立;无论如何,这些力的关系使得权力可以产生效用,它们可以体现在国家机器中、法律形成过程以及各种社会霸权中[2]。在黑人群体中,麦肯·戴德是一位靠压榨底层黑人而发家致富的商人,他的父亲被白人强占了农庄并射杀,随后他迎娶了福斯特医生的女儿露丝,并借着这位黑人医生的资源投资各种产业,通过权力的各种连接由此形成话语权力系统,发家致富后提升自己的“地位”——成为黑人群体中的上层阶级,在底层黑人劳动者中展现他的阶层优越性,也在家庭关系中拥有绝对的话语权。
福柯认为,权力关系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实质性体现。人的本能就是对权力的渴望,权力既掌控着阶级与个人,又被其所行使。麦肯成为黑人群体中的优势话语者,靠着对金钱的追逐,通过话语来实现对权力的分配。小说中另一个人物派拉特为人正直、明辨是非,在麦肯杀人后想携金逃跑这件事上与麦肯产生分歧,两人因此分别。麦肯在追求利益的道路上逐渐形成物质主义和极端的利己主义,成为人格异化的黑人资产阶级典型,成为“黑皮肤、白面具”的人。他冷血残酷,带着两位孩童的贝恩施太太付不起四美元的房租,麦肯执意要将其赶出门,并指着她的两个孙子说,“要是你想不出什么办法给我交租钱的话,反正他们是得到街上去的”[3];房客波特对生活无望时在顶楼喝醉酒想要开枪自杀,他赶过来并不是为了劝说解救对方,而是称他为黑鬼并命令他将钞票撒下来,再开枪自杀。多年以后,当他与妹妹派拉特再次相遇时,他已完全无法接受妹妹的一切,命令她不要再踏入自己的家,因为他害怕城里人发现这位事业上精明强干、富有的黑人竟然会有一个穿着破烂、卖私酒的妹妹。全家人会在每周日下午乘车出游,莉娜称他特意带着孩子们去冰窖,在与那些汗流浃背的黑人工人谈话时,时不时看着“哈德森”牌小汽车和穿着光鲜亮丽的孩子们,目的就是让下层工人和那些光着脚、光着膀子的脏孩子羡慕他,以此来满足自己扭曲的虚荣心。
由此可知,在被白人种族压迫的黑人族群中,仍然存在着上级阶层与底层劳动者的区别,麦肯通过一环扣一环的权力结构形成中心权力系统,拥有“优势话语权”。但作为处在社会活动关系中的个体也会受到社会整体的影响,在社会生活中,麦肯的家庭成员关系也形成了一定的权力中心,还有极为尖锐的种族歧视与话语权问题,这两个方面也是《所罗门之歌》中论述的重点,作者莫里森倾注了大量的笔墨,通过对不同类型“疯癫”的展示,描写了他们在对抗占有“文明”话语权的优势群体时所体现的精神异化,作家不仅对这类精神状态进行了解构,还通过正面人物的行为来对当代社会进行积极引导,展现了深厚的文学内涵与文化底蕴。
三、家庭、性别压迫中的话语权力
当压迫性的社会结构延伸到家庭结构,家庭的小群体也分为占有话语权的优势群体和被规训的劣质群体。《所罗门之歌》的前半部分描写了麦肯·戴德二世一家人的现状。麦肯的父亲为保护农场而被白人射杀,父亲的死亡导致家庭缺失,加上成长环境中也深受种族歧视的困扰与影响,麦肯逐渐“疯癫”,他被白人优势群体同化,有着白人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之后,麦肯形成了“疯癫”的家庭观念,他自私、冷漠,只会用暴力解决家庭矛盾冲突,甚至当“疯癫”思维发展到顶峰的时候,他只想解决出问题的露丝以及露丝的父亲——一位让麦肯发家的黑人医生,而不是解决问题本身。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中提到,权力以符号学为工具,把“精神”当作可以铭写的物体表面,通过控制思想来征服肉体。由此可知,家庭成为麦肯挥霍权力、发表“文明”言说的空间。他疏离、辱骂与自己相依为命的妹妹派拉特,发现妻子怀孕时,他想方设法让妻子流产,如灌蓖麻油、让她坐到刚倒出滚水的热锅上、用肥皂水灌进她的肠道、用毛线针插她、用拳头猛捣她的肚子;他还随意践踏三个孩子的自尊心,日常生活中对孩子们也没有任何的交流和关怀。在麦肯的身上,完全感觉不到正常人的温暖,只带有“疯癫”的冷血与极端。这个拥有话语权的男人极端自负,始终觉得自身优越于所有家人,从来都是凌驾整个家庭之上。
莎拉·米尔斯在《话语》中指出,话语并不是存在于真空中,而是始终处于跟别的话语和社会力量的矛盾斗争中。富考多罗茜·史密斯也认为话语是社会各种权力或力量斗争的结果。在传统的家庭结构中,女性群体的话语权已经被男性话语权所覆盖,在这种男权主导的社会家庭中,女性的心理和生活被压抑也会产生“疯癫”思想,由此做出相应的行为,是对麦肯优势话语权的应激反抗。
社会和家庭对女性造成压抑,女性就算接受了教育还是只能为男性服务,永远处于被动地位,没有选择权力而成为男权社会的牺牲品。大女儿科林西安丝,虽然上过大学,但是她所受的教育也只是教会了她如何成为贤妻良母,为家庭做贡献。在相亲过程中,她所见过的相亲对象的理想妻子是能操持家务、善于经营的女人,这些相亲的男人并不愿意接受身边有一个比自己受教育程度高的女性。随后,科林西安丝在就业问题和择偶方面也作出异于平常的“疯癫”举动,她开始对父权进行挑战。就业处处碰壁后开始给一位女作家做起了“知识分子”使女,又和租自己父亲房子的铁路车场临时工波特在一起,这两个“疯癫”之举实属与她的身份不符。可见,专横霸道、父权至上的家庭小社会为女性所设计的教育模式让处在其中的女性价值观早已扭曲,她们只会用别样的“疯癫”行为逃出家庭,去寻找自我认为舒适的地方。
与“疯癫”的科林西安丝不同,派拉特对权威的哥哥麦肯进行反抗,使女性力量得以凸显。莫里森试图用这类人物的精神救赎功能来承担一项重任,告诉女性群体应当学会自我成长,才能逐渐摆脱和摧毁男性话语群体。正如派拉特的名字所指,pilate(pilot)有领航之意,她肩负着精神救赎的重大使命,指引当代人从物欲横流的世界回归到原始自然和谐的社会。派拉特的装扮、名字、生活方式都能显示出最原始的自然狀态,她充满自信、追求自由,即便生活俭朴也过着诗意的生活;她慷慨真诚、热心无私地帮助着露丝和奶娃,是促使奶娃心灵历程发生转变的关键人物。作为非洲黑人传统文化和民族价值观念的代表者和体现者,她坚守本心,耳朵上仍然佩戴着象征民族传统的饰品,在奶娃的成长历程中引导奶娃打开了家族历史的大门。这是莫里森用新的女性观念和价值塑造的人物,表明只有挣脱精神枷锁、追求精神自由才是女性自救的最佳出路。
四、种族歧视中的话语权力
福柯在《性史》(第一卷)中提到,话语不会一直屈从于权力或反对它,也不会沉默,我们必须意识到话语的复杂性和不稳定性。话语既可以是权力的一种手段和效果,也可以是一个障碍、一个绊脚石、一个反抗点和一个对立策略。《所罗门之歌》以麦肯·戴德家族为代表的美国黑人男性的成长历程为背景,当时的西方社会以白人文化为主流,而黑人作为低级的物种处于失声状态。当占有大多数的群体拥有话语权,他们自然而然被赋予规训一切的权力,包括外在行为举止和内在思想意识,这时候他们称自己为“文明”。而黑人因为肤色的不同,他们被白人歧视、残害,这一群体的一切所作所为即被定义为“疯癫”。
传统的非洲文化将命名看作是一个民族的基本权力。《所罗门之歌》中所涉及的名称问题不仅超越了表面简单的象征、讽刺意义,还具有更深层次的特殊内涵,名称蕴含着深意,不只局限于人名,还包括人名的绰号、地名,正是这些名称问题能反映出种族矛盾以及白人优势群体在这种话语权势对抗中所起到的主导、“规训”作用。小说中提到,黑人聚集地没有医生,直到后来有了唯一一位黑人医生,所居住的街道才叫作“医生街”,但在此时,白人又发挥优势群体的话语权,城市立法机关以确定恰当名称和保持城市界标的名义张贴布告,称该街道为“干线大道”,而非“医生街”。街道北端的医院被城南居民称为“非慈善医院”,因为该医院从来不接待黑人,就连黑人医生史密斯先生在其整个职业生涯中,也从未被获准有任何的住院特权。又如麦肯·戴德家族的姓氏由来,白人登记员因为醉酒把“已故(Dead)”错填到了姓氏一栏内,如此荒诞的行为却要成为这一家族世世代代相传的姓氏。名称问题是非洲人非常重视的情结,也是非洲传统文化中较为重要的一环。由此看出,莫里森作为黑人作家,她想要通过姓氏与地名的来源,传递出对于种族歧视的不满,并表达出作家内心深处对非洲文化底蕴的追求。
如果说名称问题只是个例,白人随意残害黑人,让黑人们保持缄默,已经让黑人种族受到实质性伤害。受到这种白人优势群体所建立的“文明”社会规训的长期压抑,黑人群体最终也爆发了可预见性的结局——他们遭遇精神创伤和身份错乱,开始变得“疯癫”。主人公奶娃的好朋友吉他,就是这一类“疯癫”群体的代表,他逐步成为激进分子并加入同样带有激进主义情绪的“七日”组织,进一步导致种族之间的不合理交往。在黑人被白人杀害时,优势群体的法律和法庭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七日”组织就会在同一个时间段以类似的方法来报复白人,让他们横尸街头,做黑人群体中的“罗宾汉”。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杀人是错误的,吉他回答奶娃的困惑时说到,“没有无辜的白人,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是潜在的谋杀黑鬼的罪犯,即使不是一个实际的杀人犯”。吉他坚持着黑人民族文化和意识,明确指出数字、平衡、比例,还有地皮和土地才是他们的行动宗旨。黑人群体在反抗压迫时早已丧失理智和人性,他们的行为是“疯癫”地随意杀害。白人对于黑人的种族歧视让黑人群体置换成对白人固有观念的歧视,“疯癫”使得一种新的歧视又产生了,如果任由其发展,黑白两个种族的问题源源不断,永远不会得到实质性的解决。
如果将“七日”组织的行动看成是维护本民族血脉传统,那与之相对应的即是主人公奶娃的“寻根飞翔之旅”。与激进的血肉残杀不同,奶娃在意识到自己已被白人价值观同化后,毅然决定离开家门、寻找金子,最后寻找到自己本民族的血脉渊源和历史文化。他开始自我探索,在丹维尔这片故土上了解黑人民族的传统文化,从而激发自己的民族使命感,在小说最后,他和姑姑派拉特一起埋葬祖先的骸骨。南方之旅让奶娃寻到了“根”——黑人民族的姓氏与民族文化,回归了在当初被白人“文明”群体所颠覆的价值观,找回错位的本性,完成了自我身份的认同与建构。当奶娃唱歌给即将“飞走”的派拉特时,表明他已彻底领悟,也得到了精神重生和自由。
关于如何应对占有“文明”话语权的白人群体的规训,作者描述了两种方式,一种是“疯癫”的“七日”组织的激烈反抗,另一種是主人公奶娃的追寻本心之路。作者莫里森从奶娃的成长历程来交代自己的愿望——黑人同胞应该回到自己的文化和历史中去挖掘深厚的底蕴,这也是作者赋予黑人同胞的一种精神力量,在异质文化冲突中,应该让自我真正成长,摆脱白人优势群体构建的“文明”价值观以及该价值观所带来的精神枷锁,独立思想、自由精神才能完成自我构建。
五、解放与追寻被噤声历史
赫尔德呼吁重建德国文学的民族特色和民族精神,认为德国文学的民族性只能从自己的民族传统文化遗产中发展出来,重视民间诗歌、歌谣和神话对于文学民族性重建的意义。莫里森在这部作品中也深刻体现了这一点,作品中所提到的名称姓氏传统、派拉特经常唱的歌谣和飞翔的民间神话传说都具有非洲传统民族文化特色,作者通过温柔细腻的文笔来展现民族风貌,唱出一首动听的“非洲文化之歌”,从而帮助黑人重建精神家园。
文本作为形式和意识形态的统一体,也是特定言说者、解释者的话语行为。莫里森想通过《所罗门之歌》引导广大的黑人群体来认清当时存在的社会等级制度,要努力抵抗这一种不合理的“文明”话语权,抛开白人优势群体所塑造的固定认知方式,呼唤被压迫的“疯癫”群体去超越意识形态的制约和规训,揭示被优势阶层遮蔽的生存真相,打破种族歧视,暴露白人话语群体所弘扬的理想社会的虚假性与欺骗性。同时,作为本民族的守护者,黑人弱势群体有责任传承并发展非洲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价值,以维护本民族的独特性和尊严。《所罗门之歌》通过描述黑白种族冲突,解放与恢复了被优势群体的意识形态所噤声的历史,对此类历史实质进行了想象性重建,使黑人种族、女性群体、种族中的下层阶级的历史生活展现出更丰富的面貌。
作者通过细腻描绘主人公奶娃“飞行”的成长历程,深入剖析派拉特的人文形象,旨在引导读者在纷繁复杂的现实中寻找存在的真谛。面对秩序与现实的冲突,我们应当超越世俗的束缚,坚守本心,追寻真实的自我。
参考文献
[1] 刘彬.解读《所罗门之歌》中黑人属下的多重声音与身份策略[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10(4).
[2] 米歇尔·福柯.性经验史[M].余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3] 托尼·莫里森.所罗门之歌[M].胡允,许桓,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3.
(责任编辑 罗 芳)
作者简介:黄佳宝,天水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