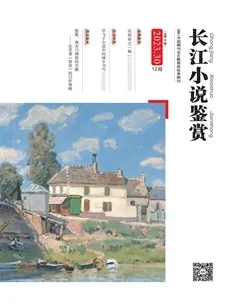《夜雨秋灯录》对《聊斋志异》女性形象塑造的继承与新变
2023-03-28杨睆
[摘 要] 《夜雨秋灯录》及《续录》在《聊斋志异》一众仿书中脱颖而出,被称为唐人小说之流亚、《聊斋志异》之嫡传。与蒲松龄相比,宣鼎在女性形象的塑造上发生明显改变,这种变化主要表现为从以狐鬼为主体的形象向现实生活中女性形象转变,以及从以主观视角来描述转向以旁观者的视角来审视现实中的女性光辉。在这一转变的背后,反映出了作者更为复杂的创作心态和女性观。笔者将以此为出发点,结合时代背景深入剖析女性形象的继承与变化。
[关键词] 《夜雨秋灯录》 《聊斋志异》 女性形象继承与新变
[中图分类号] I2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2881(2023)30-0007-04
一、《夜录》与《聊斋》的渊源
《聊斋志异》是文言传奇小说的巨擘,在后世出现了许多仿作,并形成一种文学现象。“作为《聊斋》之后的余波,《聊斋》仿书仍然是清代文言小说界的一个重要群落,最终以其连贯而趋同的艺术风格而成为一个重要的小说流派,成为清代文言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1]这些作品通常沿袭《聊斋》常用的狐鬼花妖题材,在塑造人物形象、讽刺黑暗现实、反映民生疾苦等方面十分突出。
对《聊斋志异》诸多仿作的界定,目前学界观点较为统一。在时间上一般认为自清乾隆中叶始,受《聊斋》影响,文言小说创作出现繁盛局面。在形式上因思想的分野形成两个派别:聊斋派和阅微派。前者多是对《聊斋》的直接模仿,注重故事的外在表现,重绮丽之思少质朴之言,如《谐铎》《夜雨秋灯录》《夜谈随录》《子不语》等;后者不满足于单纯叙述故事,着力在抒发议论、劝善惩戒之处下功夫,如《阅微草堂笔记》《右台仙馆笔记》《耳邮》等。经笔者统计,综合两种派别之后,《聊斋志异》的仿作书目多达三十种,分别在清乾隆和光绪年间出现两次创作热潮。在一众仿书之中,晚清时期安徽天长人宣鼎所著的《夜雨秋灯录》及《续录》尤为引人注目。蔡尔康的题序赞此书“书奇事则可愕可惊,志畸行则如泣如诉,论世故则若嘲若讽,摹艳情则不即不离。是盖合说部之众长,而作写怀之别调”[2]。从中可以窥见《夜雨秋灯录》艺术造诣之高。
在女性形象的塑造方面,宣鼎在继承《聊斋志异》的基础上做了许多新的尝试。他关注生活在各个角落、拥有不同身份的女性,在作品中寄托了自己对社会环境的看法,对丑恶现实进行揭露、对女性之美进行塑造等。因此,比较两部作品对女性形象的刻画,可以窥见时代的变迁、作家个性的差异与文言小说的新发展。
二、同工之妙
《夜雨秋灯录》能在《聊斋志异》一众仿作中脱颖而出,与其深刻体悟《聊斋》精神是分不开的。在女性形象的塑造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夜雨秋灯录》对《聊斋志异》的继承。
1.具有道德和人情之美的女性形象
《聊斋志异》通过对一系列超现实女性的描摹,表现了作者对理想女性的期待和对美好人性的向往。在小说中,这些女子虽非人间的正常女性,但在接受了人类的恩惠之后,她们展现出了知恩图报的美好品质,不仅成为书生的红颜知己,更在关键时刻挽救了书生的性命。这些女子身上所表现出的美好情操,正是人类所赞赏的。
《聊斋志异》中的狐女娇娜,是孔生的红颜知己。蒲松龄说:“不羡慕孔生有貌美娇妻,却倾慕他得到一位红颜知己。”[3]娇娜第一次出场就帮孔生解除病痛,等他痊愈后便悄然离去。两人再次相见已经过了数年,这次张生为救娇娜几乎殒命,娇娜得知后又再次救活孔生。娇娜虽是狐女,却更像是温柔体贴的女人。另有狐女小翠,因王太常对其母亲在雷电中无意的庇护之情前来报恩,嫁给王太常的痴儿元丰。小翠不嫌弃丈夫智力低下,不仅仔细照顾他,还辛勤操持家务,独自一人撑起了整个家庭,这是许多女子都做不到的。
宣鼎的《夜雨秋灯录》也是如此,作者在超现实的世界中描绘了知恩图报的女性形象。《邬生艳遇》中的狐女小素因邬生吟诗而至,双方感情直线升温,不料遭到小素父亲强行拆散。邬生因此大病不起,小素得知后赠药使邬生痊愈。另有虎女珊珊,为报救父之恩嫁给焦生,不仅持家有方还帮助丈夫走上了仕途,却因受到小妾谗言无奈退回山林。焦生遇难时珊珊不惜化身虎形来解救他,不计前嫌带其问道求仙,实现长生。尽管珊珊多次遭到误解,仍不改初心屡次帮助对方。作者将人和虎的行为进行对比,表达对现实的批判和对理想女性人物的期待。
2.巾帼不让须眉的奇女子形象
自古以来,男性与女性在社会地位上存在显著差异,男性通常占据主导地位,而女性则被限制在家庭空间中,缺乏独立的人格和价值。
但在蒲松龄和宣鼎笔下,却一反传统男尊女卑的思想,塑造出了一类巾帼不让须眉的奇女子形象。她们与男子有同样的才华,甚至更胜一筹。《聊斋志异》中的《颜氏》,讲述了女主人公颜氏因丈夫屡试不第,气愤之下自己去参加考试,一朝高中在官场上大显身手,最后还成了御史的故事;《夜雨秋灯录》中《耍字谜》一篇,讲述女子刘士璜,从小便不甘于自己的女性身份,之后她女扮男装进入仕途,成为一方县令造福百姓,但被证实女子身份后她却难逃世俗规约,前后落差之大,令人唏嘘。这两篇作品皆是女子女扮男装去参加科举,考取功名后造福一方的故事,体现出作者不被儒家思想束缚,对女子才能与魄力的赞美。可一旦真相被拆穿,她们又只能重回闺阁,也体现出现实生活中女性生存空间的狭窄。
另有一类女性身上充满了侠义精神,她们比男性更勇敢,更有决断。如《聊斋志异》中的《商三官》,身为男儿的兄长懦弱无能,身为女子的商三官却为父亲报了仇。蒲松龄说:“家有女豫让而不知,则兄之为丈夫者可知矣。然三官之为人,即萧萧易水,亦将羞而不流!”[3]蒲松齡把商三官比作春秋时的侠客豫让,又说即便荆轲在她面前也要羞愧,可见作者对她壮举的高度赞赏。
侠士、义气多是形容男性的词语,《聊斋志异》却塑造了闺中侠女的形象,这是难能可贵的。《夜雨秋灯录》中也有这类描写,最具代表性的是《闺侠》一篇,讲述两位女性在乱世中扶危济困、互相救赎的故事。富家女凤卿在一次外出路上遇到贫女湘莲,两人萍水相逢,凤卿却慷慨解囊救湘莲一家于危困。危机解除后湘莲一家生活日渐富裕,这时又遇到了落难的凤卿,湘莲当即分出一半家产赠给凤卿,两家自此成为至交。两位女子身上体现出良善赤诚、慷慨助人的侠义精神。
三、异曲之音:女性类型与意图之异
鲁迅先生评价《夜雨秋灯录》:“狐鬼渐稀,而烟花粉黛之事盛矣”[4]。之所以有这样的观点,其实是因不同版本的偏差造成的。申报馆本《夜雨秋灯录》发行后,赝本大行其道,在之后的《清代笔记丛刊》本和《笔记小说大观》本中,也隐藏着托名而作的赝本,由于这些作品质量参差不齐,且多为狭邪之作,难免引起误会。然而“狐鬼渐稀”也是事实,《夜雨秋灯录》中的女性更多为人间女子,在刻画女性形象方面,《夜雨秋灯录》及《续录》在继承《聊斋志异》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
1.《聊斋》女性:狐鬼仙的非人类女性与男性幻想的满足
谈鬼说狐,以梦幻寓真实,是《聊斋志异》的一个显著特点。“《聊斋志异》往往以非现实性的女性人物作为主题与价值观的载体,或者用来提供奇幻的意绪和色彩。”[5]由此,在许多描写爱情故事的篇章中,女性形象的塑造尤为突出。
作者有意将人的特质加在非人类的角色上,以达到艺术性的融合,最突出的一点便是打通现实与异界。《婴宁》《翩翩》《公孙九娘》在刻画异域空间时,从人类进入异界空间展开叙述,随后借人物之口表明,生活在这里的女性为狐女、仙女、鬼女的身份,再用人间的礼节、座位的排列等方法,暗示在异域世界也存有等级秩序、群体意识、家族荣辱之类的观念,从中可以窥见人类世界的影子。故事中的人物可以在不同空间穿梭,无形中破除了人与异界的隔阂,让他们的交流具有真实性,也让读者感觉更真实。
与此同时,蒲松龄又不断暗示故事的虚幻特征。例如《仙人岛》《翩翩》中描绘的仙界风光、仙女演奏的风采,是在人间不可能见到的。《画壁》中朱生遇到的少女,是由他的心境产生的梦境。“梦境作为一个超现实的空间,给了作者以相当的自由去摆脱现实世界时空的局限,因而可以‘时间倒错叙事,在特定的虚幻空间内构思离奇魔幻的事件。”[6]然而,无论梦境多么令人向往,总有清醒的时刻。在蒲松龄笔下,道士或和尚一挥、一敲、一喊就能唤醒梦中人,梦醒时分幻境随即破灭。作者用简单的动作暗示在异域发生的一切都是虚无缥缈的,转瞬就会消失,具有浓郁的梦幻色彩。《连城》展示的鬼蜮空间,虽然为连城和乔生最终相守创造了机会,然而,当现实中的矛盾无法得到解决时,人们往往寄希望于超现实的力量来缓解冲突。这种做法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暂时缓和矛盾,但同时也向读者传递了一种虚假的意识。原本存在的矛盾被华丽的幻想所替代,而读者所感受到的满足感,也仅仅是幻想。
2.《夜录》女性:广泛真实妇女群像图与现实女性魅力的发掘
宣鼎在创作《夜雨秋灯录》及《续录》时,更加关注作品的真实性。作者往往将虚幻世界作为引子,让人物在入梦与出梦之间,从第三视角对其进行审视然后获得体悟,并起到反映现实的作用。
上至贵妇、下到普通女性,宣鼎都有所关注。这些女性虽然身份各异、社会地位悬殊,但在她们身上都闪耀出人性的光辉。这些女性可以分为两大类:现实世界的女性和异域世界的女性。前者如《银雁》中至纯至孝的银雁,是没落富户家的小姐;《龙梭三娘》中豪侠义气的龙梭三娘,是蒙古的逃难女子;《雪里红》中有勇有谋的薛一娘,最初是一名妓女;《卓二娘》中头脑清醒的卓二娘,是出身平民的寡妇;《沉香街》中面甜心恶的素娇,是贪财薄情的妓女。后者如《东邻墓》中的女鬼多络霞有情有义;《迦陵配》中的仙女巧巧足智多谋;《珊珊》中的虎女珊珊替父报恩等。此外,那些担任次要角色的女性人物,她们或心地善良或个性暴戾,对于表现不同的人性也起到了关键作用。《盈盈》中的少女张盈盈不顾世俗眼光,大胆追求婚姻自由,最终和心上人刘钟顺利成婚;《谷惠儿》中的谷惠儿,用比武招亲的方式挑选夫君,在找到中意的男子后主动放水,二人终成眷属;《秦二官》中女艺人阿良的性格更加复杂,她主动追求爱情而不得,最终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最震撼人心的要数《麻疯女邱丽玉》中的邱丽玉不愿将自己的病传染给无辜之人,自己默默忍受多年,由于真诚感动天地病情得以病愈。这种凛然大义已经超越了一般的情爱,在她身上体现的是一种博大无私的爱。
从《聊斋志异》到《夜雨秋灯录》,宣鼎立足于旁观者的角度,将人物本身的自由活动呈现出来。在宣鼎笔下,女性形象更加立体饱满,同时也暗示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
四、《夜录》与《聊斋》女性形象差异的原因
文人的创作离不开时代背景。蒲松龄和宣鼎处于两种社会境况下,经历不同的人生波折,因而形成的文学作品风格各异。从观照自我意识到映射社会民生,这是文人的自觉,也是时代的选择。
1.命运遭逢之变
蒲松龄生活在清顺治、康熙年间,这一时期的社会环境较为安定。蒲松龄十九岁应童子试,连获淄川县、济南府、山东道三个第一,但天不遂人愿,屡试不第后他接受了功名无望的现实,去私塾教书来养活自己和家人。“坎坷多舛的命运,穷愁无聊的人生使蒲松龄一腔激情无从抒发,在世间难寻知己,只能发出‘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愤慨又无奈的呼喊,借花妖狐魅,‘妄续幽冥之录,抒发愤懑。”[7]受这一孤愤心态的驱动,在他亲手构建的狐鬼花妖的世界中,困扰知识分子的难题得到解决,蒲松龄实现了人生的终极追求。
宣鼎童年时期的生活较为闲适,二十岁时养父母相继离世,随后遭逢战乱荒年,接着入赘外祖家。接连的变故使他的内心严重受挫,由富到穷的经历也让他深有感触。二十七岁时宣鼎选择从军,几经生死回到上海,为了维持生计,三十一岁至四十岁时去山东做了幕僚,生活反而愈加困顿,晚年更是依靠朋友接济才能勉强度日。“宣鼎一生恰好赶上一个空前绝后的封建末世兼乱世,帝国主义对满目疮痍的天朝上国进行着军事、经济、文化等多层次的入侵;太平天国起义带来的震撼和战乱,扰乱了社会各层的生活状况。”[8]
《夜雨秋灯录》及《续录》就展示了这樣一幅晚清社会图景:受到新思潮的冲击,人们思想上的枷锁变得松动,对物欲的追求攀升,道德标准却不断下滑。“‘惊盛世之秋,救衰世之敝的时代主题对宣鼎产生了直接影响,激起了他挽狂澜于既倒的救世苦心,因而他把‘无语不关劝诫作为主要的创作目标,寓抒愤于劝诫中。”[7]由于深感国家到了危亡之时,宣鼎带着个人良知与社会责任感,将封建伦理道德融入小说之中,希望通过文字能够唤醒民众。对蒲松龄和宣鼎来说,苦难似乎如影随形,长期经受压抑为宣鼎仿《聊斋》而作《夜录》提供了契机。但二人又略有不同,前者更多是为了抒发孤愤,后者则趋向承担社会责任的自觉。
2.妇女观念之变
蒲松龄所处的时代,男尊女卑的观念还十分严重,但在《侠女》《商三官》《霍女》等篇章中,他创造性地提出女性可以反抗,并为她们的反抗精神唱了赞歌。与此同时,蒲松龄又认为女性是男性的附庸,对女性提出了诸多要求。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展示的妇女观念是相当矛盾的,这一点从他的描述中可以明显看出。
宣鼎对女性的刻画主要集中在三方面:肯定女性对爱情的大胆追求、体现美好的道德品质、揭示封建社会女性的悲惨命运。在古代社会,女性对于自己的婚姻是没有决定权的,但《盈盈》《谷惠儿》中的女性在追求自由爱情婚姻的路上,经过自己的勇敢抗争,最终得以和心上人修成正果。宣鼎对这类女性的刻画及肯定,实则是对男尊女卑传统的反思与批判。小说在展现女性美好的道德品质时,书中的男性往往表现出懦弱、自私、迂腐的品质特征。如《珊珊》《雪里红》的主人公虽是虎精和妓女,但在危急关头总是她们挺身而出,而她们的丈夫却只知道躲在女子背后寻求庇护,宣鼎从中看到了女性优于男性之处,并将其表现出来。在反映女性的命运握于他人之手时,缠足无疑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夜录》及《续录》中常用“莲钩”来比喻女性脚的秀美,宣鼎生动地再现了这一画面:母亲一边流泪一边为女儿裹脚,并认为世间最惨烈之声是母亲为女儿裹脚时发出的哭泣。由此他提出不必过分缠足、一味追求小脚的主张,这与当时社会审美相反,却十分接近现代人的审美,是难能可贵的。宣鼎对女性的刻画立足现实,因此显得较为客观理智,他的一些女性观在当时来说也具有一定的进步性。
五、结语
从《聊斋志异》到《夜雨秋灯录》,不同时代的作家的创作思想也发生了变化。女子不应被囿于闺阁,而是要像男子一样自由展现自己的才能,这样的生命才是有价值的。蒲松龄笔下的女性多为非现实的狐鬼花妖,她们的美好是作者对人间女性的美丽幻想,是作者在现实世界为自己所构造的幻影。而宣鼎笔下的女性除了少量的狐鬼,更多是现实世界中性格各异的女性人物,这些勇敢反叛封建社会父权、夫权的女性来自作者对男尊女卑传统的反思与批判,是在作者经历了社会动荡,在新旧思潮的交互影响之下创作出来的。通过对两部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的对比研究,我们可以更清楚地揭示《聊斋志异》之后仿聊斋系列小说的发展历程及其演变轨迹。同时,这也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评估此类小说的文学价值。
参考文献
[1] 崔美荣,胡利民.《聊斋志异》仿书发展流变[J].蒲松龄研究,2007(1).
[2] 宣鼎.夜雨秋燈录[M].恒鹤,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3] 蒲松龄.聊斋志异[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
[4]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5] 王昕.选择经典:清代文言小说七十年研究的线索与方法[J].文学遗产,2023(1).
[6] 姜克滨.论《聊斋志异》梦境叙事[J].蒲松龄研究,2020(3).
[7] 吴娜.宣鼎《夜雨秋灯录》及《夜雨秋灯续录》研究[D].芜湖:安徽师范大学,2007.
[8] 胡芳.试论《夜雨秋灯录》的末世风度[J].成功(教育),2007(12).
(责任编辑 罗芳)
作者简介:杨睆,贵州民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