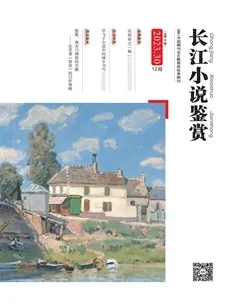探析《呼啸山庄》的悲剧审美意象
2023-03-28左琳
[摘 要] 艺术作品中的悲剧审美意象常常展示了人类的痛苦与矛盾。在艺术哲学中,悲剧被视为一种深刻的表达形式,揭示了人类存在的悲苦与绝望。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是一部经典的文学作品,其中包含了丰富而复杂的悲剧审美意象。本文将探讨《呼啸山庄》中呈现的悲剧审美意象,从现实的制约、情感的扭曲、自由的毁灭以及崇高的意象四个方面进行分析,以展示作品深邃的悲剧性。
[关键词] 《呼啸山庄》 悲剧 自由 崇高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2881(2023)30-0052-04
《呼啸山庄》是英国著名小说家艾米莉·勃朗特在她短暂而辉煌的生命中,精心构筑的一部时代巨作。小说中,构成冲突的要素相互交織,展现了爱与恨、理想与现实、人性与文明之间的矛盾。为了实现复仇目的,希斯克利夫对他人施以报复,还伤害了无辜的人,而凯瑟琳一生都在与痛苦作斗争,他们经历的无法真正获得爱却被无尽仇恨所困扰的遭遇,使得故事具有无限的悲剧色彩,给读者带来强烈的悲剧审美意象。作品采用了冷静而凝重的叙事风格,然而其中存在着狂暴能量,随时有可能爆发。主人公的妥协与反抗,凸显了人类天生具备的自由追求以及超越精神,这种精神持续冲击着人性与社会现实对立关系所形成的桎梏。作者特别强调了情感的扭曲和自由的毁灭,表达了人类本身所蕴含的悲剧审美意象。
一、现实的制约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悲剧性的冲突应当被界定为特殊形式的。在悲剧中,主人公无法实现的要求或理想体现了发展的必然性和历史的合理性。然而,正是由于当时这种必然性和合理性无法满足,才体现了悲剧。当正当的要求与实现的可能性形成对立时,即使这些要求是合理的,它们也会面临被粉碎和摧毁的命运。这种情况展示了历史力量的作用。历史的发展不仅受到理念和理想的影响,还受到现实环境和力量的制约。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悲剧性冲突的分析,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中的矛盾和冲突[1]。
悲剧常以无法调和的社会矛盾为其主题。根据作家所处的现实社会,艾米莉创造了两座山庄,一座名为“画眉”,另一座被称为“呼啸”,两个名字从表面上看似乎超然物外,实际上象征着当时社会中的两个统治阶级,画眉山庄代表着传统贵族文化和符合社会主流观念的理性秩序,外表看起来安宁祥和,实际上却腐朽守旧,压抑了个体天性,使人变得柔弱和萎靡。小说背景设定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这是一个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时代。工业革命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但也加剧了社会贫富差距,使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尽管中产阶级和贵族阶级共同统治英国,但部分中产阶级开始承认社会下层的权利,对民主理念有了更广泛的理解。因此,画眉山庄代表的贵族阶层与呼啸山庄代表的中产阶级在对待社会下层的态度上有所不同。画眉山庄代表的贵族阶层对希斯克利夫的态度与辛德雷相似,只是表现得温和一些。然而,贵族阶层对底层人民的轻视观念已经根深蒂固。
希斯克利夫幼时无家可归在街头流浪,被老恩肖先生收养回来后,其他人不仅冷漠对待他,还时常虐待他,等到老恩肖去世后,希斯克利夫的处境更加艰难,成了一个边缘性人物。凯瑟琳在年幼时对自然和自由充满向往,同时也渴望过上文明的生活。这个人物形象表现出了两面性:与希斯克利夫在一起时展现真实的本性,不受礼节束缚,享受自由和快乐;与林惇一家在一起时则主动扮演大家闺秀的角色,将自由隐藏在温柔端庄的外表之下。然而,随着凯瑟琳逐渐成长,她与希斯克利夫开始疏离。希斯克利夫保持纯真的自然本性,而受到环境影响的凯瑟琳更加复杂,她向往世俗的权势和地位。凯瑟琳周围的人,包括哥哥辛德雷和管家耐莉,代表着世俗规范的制约力量,他们强烈反对凯瑟琳和希斯克利夫的自由本性,试图阻止两人在一起。面对强大的社会规范,以及物质利益和权势地位的考虑,凯瑟琳选择嫁给埃德加·林顿,抑制了自己的自由本性,并融入象征文明和规范的林顿家庭。
希斯克利夫在自尊挫败与爱情背叛的双重打击下愤然离开,同时他也领悟到,在那个充满物欲的时代,他的理想爱情无法击败世俗权力和物质带来的满足感。这一情境揭示了在现实社会制度的限制和阶级对立所带来的制约下,个体的自我追求与社会之间的冲突。在这种历史性矛盾面前,个人往往只能做出悲剧性选择。悲剧的产生与社会历史的发展密切相关。社会历史环境对个体和群体的实践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而这些实践活动又反过来塑造了社会历史的进程,悲剧就是人们在这一进程中所遭遇的痛苦和挫折的产物。
二、情感的扭曲
在《呼啸山庄》这部小说中,情感的扭曲成为悲剧审美意象的重要元素。希斯克利夫与凯瑟琳之间的爱情充满了痛苦和矛盾,他们的感情既强烈又病态,既相互吸引又相互伤害。他们的爱情超越了传统的浪漫观念,在各种矛盾中变得扭曲且充满痛苦。希斯克利夫对凯瑟琳的爱几乎成为一种病态的迷恋,而凯瑟琳也陷入对希斯克利夫的情感中无法自拔。这种情感的扭曲不仅颠覆了传统爱情观念,同时也深刻揭示了人类情感的复杂性。凯瑟琳与林顿的结合是所有情节中最为重要的转折点,她的决定直接引起了希斯克利夫的离开和三年后的复仇行动。正如文中所说:“什么时候你一成了林顿太太,他马上就失去了朋友、爱情和所有一切!”[2]
希斯克利夫和凯瑟琳之间的爱情展现了一种极端的仇恨与激情并存的复杂关系。在凯瑟琳临死前的最后一次会面中,他们以紧密的拥抱和热烈的亲吻彼此表达爱意,同时也用痛骂和诅咒来展示相互之间的仇恨。凯瑟琳去世后,希斯克利夫完全转变成为一个不顾一切只追求复仇的暴君。他毫无顾忌地追随内心的欲望,摆脱了日常道德、伦理和习俗等的限制。他通过阴谋诡计设法将呼啸山庄和画眉山庄都纳入自己名下,还诱使凯瑟琳的哥哥辛德雷沉溺于酗酒和赌博,这不仅加剧了他的堕落,更推动了其死亡的进程。他还将复仇的火焰燃烧到下一代的身上,把哈顿当作仆人看待,不让他接受教化,随意训斥他,就连对凯瑟琳的女儿也没有心慈手软,欺骗她与小林顿结婚,甚至囚禁她。之后,他更加疯狂,为了见到凯瑟琳的鬼魂,故意折磨自己绝食而死。这种状态体现了酒神精神的本质,即人类内心情感力与文明所带来的束缚之间的斗争。作者将希斯克利夫的人性扭曲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无所顾忌,不屑于道德伦理的约束,甚至连累无辜的孩子,在经历悲剧命运的同时,又亲自制造了类似的悲剧。希斯克利夫不断放大内心的怒火,无节制的感性欲望占据了他的全部思想,这种扭曲狂暴的恨意可以看作一种异化的情感,而这也正是悲剧审美意象的由来。
三、自由的毁灭
悲剧以深沉的苦难,彰显了人类在追求未来自由过程中的伟大奋斗。自由的本质在于生命个体在抗争中所展现的痛苦坚持,这种坚持源于内心深处的激情。在小说中,主人公采取了极端的行动,表现出强烈的自我激情。在这种激情的支配下,个体生命展现出追寻自由的尊严和价值。主人公之间的矛盾冲突、相互纠缠的爱恨以及接近自杀的疯狂行为都是基于对自由的渴望,对自我存在的追寻。
艾米莉塑造的凯瑟琳是一个人格分裂的人物形象,表达了她渴望逃离文明束缚回归自然、追求浪漫主义激情和自由主义精神的愿望。凯瑟琳认为嫁给希斯克利夫会降低自己的地位,而林顿则有足够的能力让她成为地位最显赫的女性。虽然她对希斯克利夫的爱一直存在,但在现实状况下,林顿却是她更好的结婚选择对象。她天真地认为自己可以让希斯克利夫和林顿化敌为友,甚至想借用林顿的力量去帮助希斯克利夫,以摆脱辛德雷的控制。然而,她的内心也深知这些想法是难以实现的,只是一种自我安慰的方式,这使她经历了痛苦的挣扎。凯瑟琳在社会现实制约下爱而不得,在将死之际说出:“最讓我讨厌的东西,归根到底,就是这个破烂不堪的牢笼。我已经腻烦,腻烦给关在这里。我心急火燎地想逃到那个灿烂辉煌的世界里去,永远在那儿,不是泪眼模糊地看着它,不是透过这颗疼痛的心宅的壁垒渴望它,而是真正与它同在,身临其境。”[2]这种矛盾反映了现实社会中个人自由与社会限制之间的复杂关系,探讨了自由意志与社会规范之间的冲突。凯瑟琳在将死之际发出悲鸣,她的命运在这种矛盾之下以失败告终,展现出自由毁灭的悲剧性,另一方面她的死亡又代表了永远脱离社会规范、不受制约的超脱存在。
希斯克利夫妄想与凯瑟琳彻底脱离物质世界,永远保持精神上的绝对自由,他代表着那些处于边缘处境的人们渴望反抗中心权威的心声。这种心声表达了对真正自由和解放的渴望,但也暗示了他们的困境和无法实现理想的现实。小说中的悲剧结构映射了人类深层悲剧模式,成为一面映照人性的镜子。主人公的反抗不仅是对外在世界的反抗,更是对自我意识的挑战和超越。他们希望消除种种束缚、摆脱物质世界,追求精神上的自由,但常常在这种追求中失去自我和方向,最终落得悲惨结局。希斯克利夫在经历了凯瑟琳死亡后,转变成一个暴君,在这个过程中,他已然失去了本心。
小说通过主人公的命运和行为,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表达了人类对真正的自由和解放的渴望。作品中,主人公不断地挑战传统观念和社会规范,是对现代社会和人类生存状态的一种批判,也反映出了人类内在的冲突和自我意识的追求。
小说中的主要角色并非造成悲剧的源头,但他们勇于承担悲剧带来的后果,同时展现出深刻的自我审视和自我批判,给读者带来强烈的震撼。在希斯克利夫和凯瑟琳的爱恨纠葛中,作者展示出了震撼人心的悲剧性的破坏力。他们以一种崭新而激烈的形式迸发出内在的力量,直接表达了对束缚和桎梏的抗争。这种原生态的怒吼不仅是一种情感的宣泄,更寄托了个体追求自由、探索生命意义的渴望。在这个破碎而混乱的过程中,他们所呈现出的悲剧美感,凸显了人类内心深处的复杂情感。
四、崇高意象的体现
悲剧作品必定包含了崇高元素,只有那些能够引发我们内心崇高感的作品才能被视为真正的悲剧,而不是虚假的悲剧。悲剧所展示的是自由受到阻碍并最终失败的情节,而正是在这种痛苦中,崇高的美得以创造和展现。车尔尼雪夫斯认为,“悲剧是崇高的最高、最深刻的一种”[3]。古罗马文论家朗吉努斯提到崇高时说:“亲爱的朋友,有一点你一定要了解,正如真正伟大的东西在生活中绝对不会受到鄙视,崇高也一样。”[4]崇高是一种与个体主观感受和心理特征紧密相关的状态,它是在面对非凡、超越、庄严等事物时所产生的一种特殊情感体验,同时也涉及对生命和死亡的思考以及对人类存在的根本问题的探索。这种体验能够引发我们内心深处的震撼和思考,使我们追求更高尚和深远的境界。康德曾指出,崇高常常通过一定的形式或物质载体来展现,诸如险峻的山崖、电闪雷鸣的云层、狂怒的飓风、飞湍的瀑布和熊熊的大火等。在《呼啸山庄》中,环境描写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塑造人物性格和命运具有重要影响。作者注重运用阴郁、恐怖等元素来激发读者的恐惧感,这与康德有关“恐惧的崇高”的论述契合,面对阴森、诡异、黑暗和恐怖等事物时所引发的恐惧常常具有崇高的性质。小说中不仅构建了一个神秘的荒原,还刻画了一个可怖的呼啸山庄,这座庄园充满了颓废、血腥和死亡的氛围。这种环境描写不仅增添了小说的恐怖氛围,也深刻影响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和行为表现。通过将人物置于如此恶劣的环境之中,作者巧妙地展现了他们的坚韧、矛盾和卓尔不群的个性特征,使读者对他们的命运更加关注。
伯克指出,“崇高来源于心灵所能感知到的最强烈情感”[5]。崇高常常产生于爱情与仇恨冲突的巨大张力,《呼啸山庄》展现了异常复杂且情感激烈的爱情复仇故事,希斯克利夫对人们毫不留情地进行打击,对凯瑟琳也实施疯狂报复,这是他内心真实情感的反映。希斯克利夫之所以拥有这种念头,源于他内心深处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引发了强烈的情感。他实施了残酷的复仇计划,导致一些无辜者相继死去。这一连串的死亡并没有使读者质疑,反而让读者产生了置身其中的真实感。这种情感体验影响了读者的精神世界,达到了美学上的崇高。
在《呼啸山庄》中,希斯克利夫和凯瑟琳之间的爱恨纠葛将彼此置于相互折磨的状态中,这展现了他们对自由和自我探索的渴望。然而,在现实社会中,他们的意愿与命运发生了艰难的抗衡。尽管这场斗争注定以失败告终,然而正是通过忍受如此巨大的痛苦,崇高得以诞生。在悲剧背景下,个体的生命力量更加鲜明地展现出来,呈现出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状态。
悲剧是真理与情感之间的高度契合。艾米莉在《呼啸山庄》中以其非凡的想象力虚构了一个故事,让读者得到悲剧的体验。《呼啸山庄》通过现实的限制、情感的扭曲、自由的毁灭以及崇高的体现展示了丰富的悲剧审美意象。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和情节构建了一个充满悲愤和绝望的世界,分析其中蕴涵的悲剧审美意象,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人性的复杂和悲剧在作品中的表现形式。《呼啸山庄》作为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具有经久不衰的生命力,能持续地引发人们对于悲剧存在的思考,为我们提供了艺术体验的机会。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0卷 普及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 艾米丽·勃朗特.呼啸山庄[M].张玲,张扬,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3] 车尔尼雪夫斯基.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A]//西方美学史资料汇编(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4] 朗基努斯.美学三论:论崇高[M].马文婷,宫雪,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
[5] 伯克.崇高与美——伯克美学论文选[M].李善庆,译.上海:三联书店,1990.
[6] 杨亚萍.论《呼啸山庄》的悲剧意识[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11.
[7] 奚霞.自然与文明的冲突[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1.
[8] 薛丽.《呼啸山庄》的悲剧根源解析[J].文学界(理论版),2012(11).
(责任编辑 罗 芳)
作者简介:左琳,天水师范学院文学与文化传播学院,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