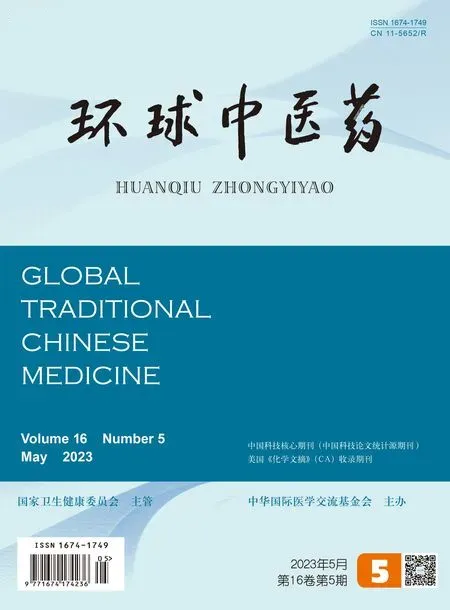浅析傅青主与张锡纯诊疗倒经之异同
2023-03-17陈银婷杨燕贤
陈银婷 杨燕贤
倒经,亦称为“逆经”“经行吐衄”,指每逢经行前后,或正值经期,出现周期性的吐血或衄血者。症状为每次月经前1~2日,或正值经期,亦可在经净时,出现吐血或衄血,多伴月经量少,甚则无月经,并且连续2个月经周期以上[1]。现代医学认为本病与“子宫内膜异位症”及“代偿性月经”密切相关。西医多采用期待疗法、激素疗法、止血疗法、手术疗法等治疗手段,但其有疗程长、副作用大、易复发等缺点[2]。中医药治疗倒经具有一定优势,通过辨证施治,调达脏腑经络,可达到吐衄血止、月经规律的奇效,且不易复发。
“经行吐衄”一词最早出现于清代《医宗金鉴》。清代诸多医家对此病各有独特的论述,其中傅青主及张锡纯两位医家的见解最具有代表性。傅青主,为明末清初著名医学家,尤精于妇科,其所著《傅青主女科》对近代中医妇产科学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张锡纯为清代中西医汇通派代表人物之一,他对妇产科病的诊治有独特见解,《医学衷中参西录》记载的许多治疗妇产科疾病的方剂至今仍在临床上广泛运用。本文从两位医家对本病的病因病机、治疗治则及用药异同进行比较及总结,有利于拓展临床诊疗思路,进一步指导临床工作。
1 病因病机的不同
1.1傅青主认为肾精不足为本,肝郁气逆为标
傅青主提出倒经病机为“少阴之火急如奔马,得肝火直冲而上,其势最捷,反经而为血,亦至便也,正不必肝不藏血,始成吐血之症”[3]。肝肾乃母子之关系,母病及子,故“肝郁而肾不无缱绻之谊”[3]。他从肝郁气逆,肾精血虚两方面阐释上逆之机。“夫经水出诸肾”[3],肾为经水根本来源,肾水足则经血充足,亦能涵养肝木,气机条达,月经可按时而下,故肾精不足为本。肝体阴而用阳,肝木失肾水涵养,木郁火生易气机上逆,肾精血不足易生虚火,肾火借肝气顺势上冲,血随火气升至口鼻出而生吐衄,血不下行而经量少或闭经,故肝郁为标。傅青主认为“反复颠倒,未免太伤肾气”[3],反复吐衄,肝肾火旺,肾精血亏虚更甚。除外,他还指明“肝木不舒,必下克脾土”[3],肝风火旺,更乘脾土,脾失运化,后天不济先天,加重肾精血虚损之势。因此傅青主强调肾虚为本,肝郁为标,同时顾护脾胃,正谓“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既要明察病机之根本,也应已病防变,顺肝补肾兼健脾,且健脾可加强补肾之力,以达气顺血止衄除之效。
此外傅青主还强调倒经应该与内科吐血相互鉴别。他认为经行吐血是因为脏腑功能失调而致血随气逆,内科吐血则与诸经内伤有关。傅青主虽未对倒经进行辨证分型,却指明应辨清病因再用药,但若病机均为气逆所致出血,亦需顺气降逆而止血。
1.2张锡纯强调冲气上逆则生吐衄
张锡纯定义冲脉“在女子与血室实为受胎之处”[4],主宰女性生殖功能,故首推从冲脉论治倒经,以冲气上逆为主要病机。经脉证合参后他对倒经有以下辨证:
1.2.1 胃虚不降,肾失固摄,冲气上逆 冲脉与阳明胃及少阴肾关系密切,“其脉上隶阳明,下连少阴”[4],故张锡纯从胃肾阐述冲气上逆的病机,一方面,冲脉隶属阳明,阳明乃多气多血之经,阳明胃经不仅生化气血为月经提供物质基础,同时“胃气息息下行为顺”[4],胃气下降方可镇摄冲气,使气血循经而行,故“阳明胃虚,其气化不能下行以镇安冲气”[4]则易生倒经;另一方面,少阴与冲脉相连,若少阴肾固摄失司,“其气化不能闭藏以收摄冲气,则冲气易于上干”[4]。所以两者皆可致冲气上逆,一则血随气升,则发为经行吐衄,二则冲气不下行,血液运行失常,易生瘀滞,“下行之路有所壅塞”[4],最终形成虚实夹杂之象。
1.2.2 胸中大气下陷,胃气不摄冲气 张锡纯在原文按语部分补充医案:“曾治一室女,倒经半年不愈,其脉象微弱。投以此汤,服药后甚觉气短。再诊其脉,微弱益甚。自言素有短气之病,今则益加重耳。”[4]他通过审脉察症后推断胸中的大气下陷引起气机逆乱亦可致倒经。“胸中大气”的概念由张锡纯首次提出,并明确解释胸中大气就是胸中宗气[5]。胸中大气司呼吸,为诸气纲领,能通过气化以主持全身之气机,故当其下陷时,“纲领不振,诸气之条贯多紊乱”[4]。其所致气短表现为“呼吸之外气与内气不相接续者”[4],他还点明应与气郁不舒,或气逆而喘,或寒饮结胸等病因所致气短相互鉴别。胸中大气亦是“周身血脉之纲领”[4],当大气下陷时,无力鼓动气血运行,故可见脉象微弱。而对于本病张锡纯将胃气视为胸中大气与冲脉联系的重要环节。“大气常充满于胸中,自能运转胃气使之下陷,镇摄冲气使之不上冲”[4],胸中大气可通过调达胃气的运转从而促使冲脉之气运行有常。因此当大气下陷时,胃气不下行,冲气不得镇摄而上逆,则生倒经。
2 脉象详略之异
在疾病诊疗过程中,傅青主从证略脉,而张锡纯脉证兼具。因傅青主为明末清初医家,西学刚传入国内,尚未对中学造成明显影响,《傅青主女科》中对倒经的论治多传承于《内经》等中医经典,且成书年代是中医理论体系较为成熟时间,故傅青主略脉象重病证,行文简洁易懂,追求实用性,不仅为其他医家参阅,也可供百姓所用。而张锡纯生活于清末民初时期,并受时代思潮影响形成了中西医汇通的学术思想,他主张以中医经典理论为主,再辅以西医理论佐证中医。张锡纯阐述中医理论多征引《内经》《伤寒杂病论》等典籍,受张仲景影响对脉象较为重视,且当时中医受到西医的冲击和质疑,西医高等教育事业首先发展,张锡纯有意培养中医人才,因此原文论述倒经诊疗部分不仅理法方药兼具,且验案丰富,脉证详备,写作具有教材风格,有利于初学者学习及讨论。
3 治法方药的不同
3.1傅青主重视肝肾脾,寓顺于补
傅青主着眼于肝肾,兼顾脾胃,寓顺于补,“必须于补肾之中,用顺气之法,方用顺经汤”[3]。傅青主认为顺气之法内涵有二,一为补益肝肾以顺气,方中用熟地黄甘温入肾经以补精养血,白芍酸寒入肝以柔肝补血,两者合用,酸甘化阴,大补肝肾之血;再予当归与白芍相配,养肝血而解肝郁,牡丹皮清肝泻火以助降逆之功,以上诸药合用可达“肝不逆而肾气自顺”[3]之效。二为和血以顺气,黑芥穗引血归经,使离经之血重回脉中,血归自气顺,故原文指出:“于补肾调经之中,而引用引血归经之品,是和血之法,是寓顺气之法也。”[3]方中还加用茯苓、沙参补益脾气,既可防肝木过度制约脾土,又能补后天之气助先天之气。全方用药性平和,寓顺于补,调和气血,使经血下行为顺而吐衄自除。傅青主虽未描述具体煎服法,却略有提及用药疗程,“一剂而血止,二剂而经顺,十剂不再发”[3]。由此可推出,顺经汤药简力专,一到两剂药即可见效,但不应“血止”“经顺”立即停药,恐其有复发之势,需用足十剂药,也从侧面佐证肾虚为本之病机,故用药时间较长。
3.2张锡纯主张调冲降气,辨证用药
张锡纯主张调理冲脉来治疗倒经,又指明应辨证用药,“致病之因既不同,用药者岂可胶柱鼓瑟哉”[4]。
对于胃肾两虚所致冲气上逆的倒经,张锡纯受陈修园的经验启发,选用“麦门冬汤”化裁,该方为《金匮要略》中治疗“火逆上气,咽喉不利”之验方,原方甘寒清润,润肺益胃,张超等[6]基于三阴三阳开阖枢理论分析麦门冬汤有“降阳明、开太阴”之效,故方中麦冬与半夏的用量比例为7∶1,重麦冬凉润肺以开太阴且制半夏之燥,轻半夏降阳明胃气逆以又可防滋腻之碍。张锡纯经辨证论治后,拟方“加味麦门冬汤”,方中半夏“禀秋金收降之性,故力能下达,为降胃安冲之主药”[4],因此半夏为君药;干寸冬、野台参、大枣大补中气、生津益胃,通过补益阳明胃气以摄冲,同时滋阴以防半夏燥性伤阴之弊;半夏与干寸冬改为比例为3∶5,亦是为了加强半夏降逆的功效;又添山药补益肾气以敛冲;更以芍药、丹参、桃仁开其下行之路,使冲中之血能归故道而吐衄自止。张锡纯用药,既重视降逆药物的调冲作用, 同时也注重补益药物恢复肾胃两脏之职[7]。张锡纯认为经方含义深远,并非为一病一证而设,经辨证加减后,可达良效,可见他推崇经方又不拘泥经方。
倒经另一证为胸中大气下陷,胃气运转失常,冲气失摄而上逆。张锡纯以补气升陷为法,拟方升陷汤,方中以黄芪为君药,《医学衷中参西录》写道“其补气之功最优,故推为补药之长”[4]“又善升气”[4]。他还运用西学之理阐明黄芪的药性,“人之呼吸,亦须臾不能离氧气”[4],而胸中大气通过肺之呼吸与外界清气相通,黄芪“其质轻松,中含氧气,与胸中大气有同气相求之妙用”[4],故重用之。还需加用柴胡与升麻引经恢复大气的升提,“柴胡为少阳之药,能引大气之陷者自左上升。升麻为阳明之药,能引大气之陷者自右上升”[4]。方中加用知母,看似与全方补气升陷之意无关,实则目的为知母凉润可制黄芪之燥,使全方药性平和,得以久服无弊;桔梗为药中之舟楫,能载诸药之力上达胸中。
4 用药原则之同
4.1调经为治本,止血为治标
两位医家治法虽然不同,但都认可调经为治本,止血为治标是倒经的治疗原则。两位医家治疗倒经的方剂皆选用药性纯和之品,多为补气养血、活血调经之药,无一味止血药。《傅青主女科》原文曾指出服用顺经汤一剂已是血止,但仍继续服用至十剂,可见“血止”不是停药指征,“经顺”才是达到治疗效果。张锡纯选用《金匮》麦门冬汤化裁而治倒经,虽无明确道出治疗原则,但从其组方用药可看出调经才是治疗目的。在升陷汤的医案中只提及停药的时机为“短气愈”,并无涉及经前吐衄血止,由此看出张锡纯亦觉止血为治标,短气愈、经水按时而下才为治本。
4.2引血归经,气血调和
关于气血关系的理论最早起源于《内经》。《灵枢·五音五味》载道:“今妇人之生,有余于气,不足于血,以其数脱血也”[8],阐述女子以血为本的生理及气有余血不足的病理特点。傅青主和张锡纯都认为倒经病机以气机上逆为主,但在治疗中加用活血药可达到引血归经,调和气血的奇效。
傅青主寓顺气于和血,《傅青主女科》言:“夫肝之性最急,宜顺不宜逆。顺则气安,逆则气动。血随气为行止,气安则血安,气动则血动。”[3]傅青主就气血关系论治倒经病机,肝为刚脏,以血为体,以气为用,肝血充而血不滞,则肝气顺血自和,月事按时满溢。若肝气上逆,血随气升,从口鼻而出,则为经行吐衄。对此傅青主不仅用白芍柔肝养血、丹皮清肝活血降逆而平肝顺气,还加入黑芥穗引血归经。黑芥穗即荆芥穗炭,荆芥最早以“假苏”出现在《神农本草经》,有“破结聚气,下瘀血”之功效。而“荆芥”一名始载于《吴普本草》,此后被各朝代所沿用。北宋以前荆芥多以全草入药,自《本草图经》提出荆芥穗入药效果好后,明清亦延续了以荆芥穗为入药部位,荆芥穗是荆芥植株最顶端的部位,升发之性更强,故其取代全草成为主要的用药部位。傅青主多将荆芥穗制成炭用,《本草备要》:“治血炒黑用,以黑胜红也”,荆芥穗炮制成炭,可入血分,他认为:“荆芥穗炭能引血归经”[3],“通经络, 则血有归还之乐。”[3]李姝池等[9]对引血归经的含义解释为既可使离经之血, 重回脉中,又能预防离经之血日久成瘀。顺经汤中无使用疏肝理气之药,盖疏散之药偏燥,恐更伤肝阴血加重肝逆之症,故选用白芍、丹皮养血活血及荆芥穗引血归经达到气血调和,经血来潮之效。
张锡纯亦重视引血归经、气血并调,虽在原文中未明确指出,但在加味麦门冬汤中,张锡纯在镇逆安冲,补肾益胃的基础上,又增加活血通经药,此乃因“特是经脉所上行者,固多因冲气之上干,实亦下行之路,有所壅塞。观其每至下行之期,而后上行可知也。故又加芍药、丹参、桃仁以开其下行之路,使至期下行,毫无滞碍”[4]。冲气上逆可致血不循经,一则部分血液随冲气上逆发为吐衄,二则经血下行无力,易停滞成瘀,故有下行之道壅塞的趋势,需加芍药、丹参、桃仁活血调经,通畅脉道,令离经之血重回故道,亦有引血归经之意。《神农本草经》记载芍药具有“除血痹”“利小便”之效,故芍药具有活血之功及通利下行之势,原文中未说明选用白芍或是赤芍,但张锡纯在药物篇中曾言,“至于化瘀血,赤者较优”,故选用赤芍化瘀通经。又言赤芍“与桃仁、红花同用,则消瘀血”,但此方选用丹参,是因其认为红花乃“破血之要品”,为瘀血在脏腑者多用,而下行之道壅塞则为经络之瘀,丹参可化“瘀在经络者”及“化瘀血之渣滓”,故弃红花用丹参。张锡纯还在方中特地注明桃仁应带皮尖捣碎,盖“桃仁不去皮尖者,以其皮赤能入血分,尖乃生发之机,又善通气分”[4],既活血又可通气分,与丹参、赤芍合用,亦是引血归经,气血同调之意。
5 傅青主与张锡纯从不同环节调经
傅青主诊疗倒经以调理肝肾脾脏腑为主,张锡纯辨治倒经主要围绕调理冲脉为法,两大理论看似独立,实则相互联系。关于月经来潮生理现象的描述首次出现在《黄帝内经》:“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10]女子月事能按时而下,有赖于肾气充盛,冲任奇经通调。《诸病源候论》将月经失调的病因病机归责于邪气“客于胞内,伤冲脉、任脉”,显示出胞宫与冲任二脉在月经病机的重要性。刘完素首次提出妇人不同生理阶段应分别从肾、肝、脾论治,为以后朝代医家提供了理论依据,如李东垣侧重脾胃调经,张景岳认为肾主生殖与月经密切相关,叶天士提出“女子以肝为先天”等著名学术观点。傅青主多受张景岳影响,重视补益肾之精血,亦注重调理肝脾,创制了温经摄血汤、安老汤、调肝汤等可肝脾肾同治的调经方剂。张锡纯看重冲脉,将冲脉冠于奇经之首,他创制的妇科方剂有17首,其中有7首是调理冲脉,如理冲汤、安冲汤、固冲汤等。故可见两位医家均是继承前人理论基础上,以女子月经生理过程的不同环节作为出发点去论治倒经。傅青主着重于肝脾肾脏功能运转有常,脏腑气血调和,冲任方能通畅,月经方能按时来潮。张锡纯倡导从冲脉论治倒经是通过调补肾胃两脏以保冲气无上逆之虞,既重视了脏腑功能的正常运行,又突出了冲脉奇经在调治月经病的重要性,因此可将张锡纯奇经理论视为傅青主脏腑五行理论基础上的继承及发扬。
6 总结
傅青主对本病的辨治贯穿了脏腑五行生化的思想,而张锡纯则围绕奇经冲脉的生理病理为要点,指出胃虚不降、肾失固摄,及胸中大气下陷均可致冲气上逆。傅青主追求实用性,从证略脉,张锡纯受《伤寒论》影响且有教学目的,脉证具备。对于病机及治法,两位医家观点虽不同,但均以调经治本,止血治标为用药原则,注重引血归经,调和气血。张锡纯调理奇经需以恢复脏腑功能为前提,故其可视为傅青主脏腑五行理论基础上的继承及发扬。
两位医家对倒经的论治有所不同,但均能在临床上取得良效,盖为辨证施治之功。傅青主重视辨病,指出应与内科吐血鉴别,并根据病因用药;张锡纯则注重辨证,明辨病机再加以用药。通过精读两位医家的著作,可学习到不同诊疗思路及临床经验,同时也应病证同辨,完善并运用所学辨证体系,抓住本质,方可药到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