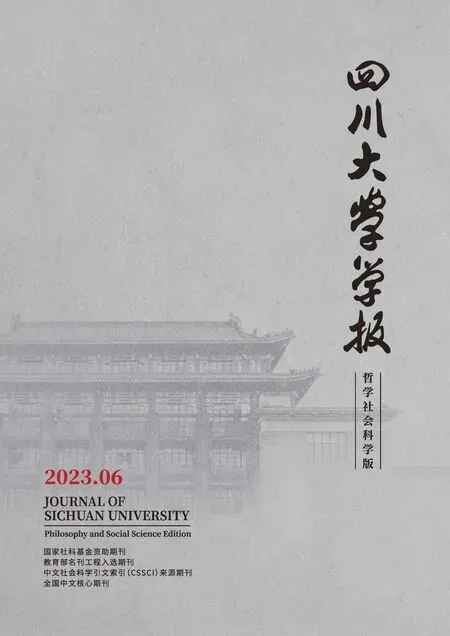三星堆遗址发现年代新考
2023-03-13谌海霞
霍 巍,谌海霞
举世闻名的四川省广汉三星堆遗址,在20世纪以来因一系列重大的考古发现而引起海内外高度的关注。但是,这个著名的考古遗址是何时被发现的,长期以来却一直有不同的说法。按照许宏先生在《三星堆之惑》一书中对此的梳理,“最流行的是1929年和1931年说,此外还有1927年说,一般不为人提及。关于首次发掘的时间,也有1932年、1933年和1934年三种不同的说法”。(1)许宏:《三星堆之惑》,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3页。近年来许杰先生也曾在其研究论文中提到三星堆遗址最早发现的年代问题,(2)许杰:《四川广汉月亮湾出土玉石器探析》,《四川文物》2006年第5期。引发了学术界的困惑与热烈讨论。本文根据四川大学博物馆(前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收藏的档案资料,结合既往的学术研究史,对这一问题展开进一步的讨论。
一、几种不同说法的根据和可能的信息来源
(一)1929年说
在各种说法当中,最为流行和最具权威性的说法,似为1929年说。1979年《四川大学学报》和《文物》杂志几乎同时刊登了由冯汉骥、童恩正先生署名的《记广汉出土的玉石器》一文,其中写道:
四川省广汉县所出玉石器,迄今已经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了。1929年,该地中兴乡(现名中兴公社)的农民燕某曾在宅旁沟渠底部发现玉石器一坑,当即引起了人们的注意。1933年冬,前华西博物馆葛维汉等人曾在此进行发掘。解放以后,四川的各考古机构亦先后在其地作过数次调查,证明这里是一范围很广的古代遗址。……关于1929年发现玉石器的实况,据传当燕家挖掘堰沟将文物暴露出来以后,随即将其掩盖,待夜深始将其搬运回家,其数目不下三、四百件,其中有玉圭、玉璋、玉琮、玉斧、“石璧”等。(3)冯汉骥、童恩正:《记广汉出土的玉石器》,《四川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文物》1979年第2期。
由于冯汉骥先生和童恩正先生都是西南考古的著名学者,他们在文中所提出的1929年发现广汉中兴村月亮湾遗址(后来统称为广汉三星堆遗址)的这一时间点,自然很少有人置疑,影响面最广,持续也最久远,多年来似成定说。
据童恩正先生1976年10月25日给编辑同志的信中说:“这篇稿子是我根据冯汉骥老师16年前记下的部分材料写成的,写成以后,冯老师即重病入院,无法再审阅修改,所以如有错误之处,当由我个人负责。”(4)童恩正:《记广汉出土玉石器》手稿,档号P12595,四川大学博物馆藏。由此可见,1929年的提法是童恩正先生根据冯汉骥先生1960年的材料写成的。至于冯汉骥先生的这个说法是基于何种信息来源,在其文中没有具体透露。但冯、童二人当年曾带领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师生在广汉三星堆遗址进行过考古调查和试掘,据作者自述:“解放前后,笔者曾数次向燕家当时在场的人询问,但由于事隔已久,而且时值深夜,人多手杂,已不能道其详了。”(5)冯汉骥:《记广汉出土的玉石器》,《冯汉骥考古学论文集》,第11页。由此可知,关于三星堆月亮湾玉石器坑发现于1929年的说法,有可能系冯氏向燕家人询问而来,只是由于“人多手杂”,甚至人多口也杂,多人转述之后,已经难道其详。
(二)1931年说
1931年说似最早见于华西协合大学副馆长林名均先生在1942年发表的《广汉古代遗物之发现及其发掘》一文。(6)林名均:《广汉古代遗物之发现及其发掘》,《说文月刊》(渝版)第3卷第7期,1942年,第93-100页。60年代初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撰写的调查简报、试掘报告都采用这一说法。(7)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组:《广汉中兴公社古遗址调查简报》,《文物》1961年第11期;四川省博物馆、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组:《广汉中兴公社试掘简报》未刊稿,档号P8476,四川大学博物馆藏。此说也被三星堆遗址在1986年新发现两个祭祀坑时的发掘报告所采用:“1931年,遗址北部的真武村农民燕道诚在其宅旁掏沟车水溉田时,挖出玉石器300余件,不久流散于世。……在月亮湾、真武宫一带,自1931年以来,屡有零散或集中的玉石器出土。”(8)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星堆祭祀坑》,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9、15页。
首创1931年说的林名均先生在其1942年的文章中描述相关经过如下:
民国二十年春,因溪底淤塞,溉田不便,燕氏乃将水车干,施以淘浚,忽于溪底发现璧形石圈数十,大小不等,叠置如笋,横卧泥中(此系事后随戴谦和先生赴遗址考察之摄影员晋君闻诸燕师爷之子转告于我者,据云燕氏以事关风水,记忆甚确,与葛氏报告中所言之排列方法不同)。疑其下藏有金珠宝物,乃待至深夜,始率众匆匆前往掘取,除获完整之石璧若干外,复拾得古代圭、璧、琮、玉圈、石珠各若干。然颇不知重视,夸示乡邻,馈赠戚友,璧及玉圈数十,遂致分散无遗,圭琮石珠等物,亦大部散落损毁,至不能集中加以研究,诚可惜也。时英人董宜笃牧师(Rev. V. H. Donnithore)正布道于该县城内,闻知其事,以此有关历史文化之古物,不可任其散佚,乃告于驻军旅长陶宗伯氏,复函邀华西大学博物馆戴谦和教授(Prof. Daniel. S. Dye)同往视察。(9)林名均:《广汉古代遗物之发现及其发掘》,《说文月刊》(渝版)第3卷第7期,1942年,第93-94页。
民国二十年即1931年,从文章中可知,其信息来源并非本人调查所获,而是由“随戴谦和先生赴遗址考察之摄影员晋君闻诸燕师爷之子转告于我者”。因此许杰先生指出:“林氏本人在当年并未介入此事,但参与了1934年的发掘清理(时任华西协大博物馆副馆长)。所述应来自晋氏的转告和葛文的介绍。但细究他的文字可知1931年说是不可能成立的。”许杰还对此进一步推测道:“假定燕家挖出玉石器是在1931年春,而董氏听说此事是在该年初春,那末两者相距时间必定很短,因为挖出器物是在董氏获悉之前。董氏和林氏都提到燕家把器物分赠各家,林氏特别指出‘夸示乡邻,馈赠戚友,璧及玉圈数十,遂致分散无遗,圭琮石珠等物,亦大部散落损毁,至不能集中加以研究,诚可惜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应该不可能达到分散无遗或大部散落损毁的状态。因此可以推断,很可能林氏误读了董宜笃的原话,将两事混为一谈,结果把月亮湾玉石器发现的年代误定为1931年。”(10)许杰:《四川广汉月亮湾出土玉石器探析》,《四川文物》2006年第5期。
1934年,时任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馆长的葛维汉先生(David C. Graham)对燕家发现玉石器的沟底以及周围地区进行了清理发掘,发掘报告在当年发表。报告首先转述董宜笃亲言其所了解的月亮湾发现的经过:
那是在1931年初春,我第一次听流言说是离此地不远曾挖出若干石牙璋和石璧。听说是一位农夫在挖一水洞时碰上若干件这些器物,并一直在把它们送给妇女、苦力和各种人……于是我与陶上校(现为将军)说,敦促他查询此事并尽力保存这些器物……他答应去查询,如有可能,并会带其中若干石器给我看。几天后,他又来访,带来五件石器,就是现在在博物馆的那五件……我获准短期保存它们,次日我搭乘公共汽车赴成都把它们交给戴谦和保管……之后于六月,我们去太平场对器物出土遗址进行考察、照相。团队由陶上校、他的六名警卫兵、戴先生、我本人和大学博物馆摄影师晋先生组成。(11)David C. Graham,“A Preliminary Report of the Hanchow Excavation,” 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vol.6 (1933-1934),pp.114-131. 该杂志即《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该文有中译本收录于李绍明、周蜀蓉选编:《葛维汉民族学考古学论著》,成都:巴蜀书社,2004年,第176-198页。此处译文参见许杰:《四川广汉月亮湾出土玉石器探析》,《四川文物》2006年第5期。
许杰先生认为:“这段文字很可能是1931年说的源头,因为粗读董氏原文第一句话,很容易理解为董氏获悉此事与燕家挖出器物时间相隔不久。但董氏所言其实只是明确指出他听说此事是在1931年初春,并没有器物是在之前不久挖出的意思。”(12)许杰:《四川广汉月亮湾出土玉石器探析》,《四川文物》2006年第5期。许杰先生将上述文字理解为1931说的源头有一定道理。从葛维汉文中讲到的情况来看,在1931年6月,董宜笃和当地驻军的“陶上校”,以及戴谦和、时任华西协合大学的摄影师“晋先生”一行去广汉太平场对遗址进行了实地考察,这里所说的太平场,也就是其他文字中出现的广汉中兴场,即今天三星堆遗址核心区域内的月亮湾玉石器坑所在地点。
综合分析上述两种最为主要的说法,即1929年和1931年,其信息的来源大多为他人转述而来,这当中涉及的华西协合大学林名均、戴谦和、随戴谦和赴遗址考察之摄影员晋君、传教士董宜笃诸人,林名均的信息来源系转自他人之口,并非亲闻燕氏家人所言,所以其可信度最低;而戴谦和、董宜笃、葛维汉以及摄影师晋氏应是亲自到现场拜访过燕氏家人的,他们证言的可信度应当最高。那么,这些当事人又曾遗留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信息呢?
二、关于1927年发现三星堆的有关信息
虽然在既往的著述中,如同许宏所言,1927年发现三星堆遗址的说法一般很少有人提及,但并不等于这个说法毫无依据。首先,让我们来看看戴谦和先生留给我们的信息。
1931年,时任教于华西大学的地质学家戴谦和先生率先发表了对月亮湾出土的玉石器的研究成果。(13)Daniel.S.Dye,“Some Ancient Circles,Squares,Angles and Curves in Earth and in Stone in Szechwan China,” 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vol.4 (1930-1931),pp.97-105.戴氏在文中并没有直接指出发现的年份,但有如下的描述:
1931年,一位进步官员把若干石器带给汉州的董宜笃[许注:汉州即广汉,董氏为一传教士],后者又把它们带给笔者。之后我们三人一起去发现地点访问,对发现器物作了照相、研究和测量。该官员把那些器物呈送给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那是大约四年前,一位进步农夫想放入一架牛拉水车,他在明代水沟下深挖到古代地层,在此发现了大型砂岩石璧,并有石质更为坚硬的凿、斧和牙璋……找到这些器物的农夫是一睿智异常的老绅士,一位旧学的学者。假如他不是如此一位人物,那末这些器物可能永远不会来到任何教育机构。(14)D.S.Dye,“Some Ancient Circles,Squares,Angles and Curves in Earth and in Stone in Szechwan,China,” 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vol.4 (1930-1931),pp.97-105.译文参见许杰:《四川广汉月亮湾出土玉石器探析》,《四川文物》2006年第5期。
许杰据此认为:“戴文发表于1931年,而据文中描述他又是在同年见到月亮湾出土器物并考查出土地点。那末文中指称的‘四年前’必定是1927年,这是笔者所知月亮湾发现诸说中年份最早的。戴文是有关月亮湾发现的第一篇学术文章,与发现的时间最接近,戴氏的说法自然值得重视。”(15)许杰:《四川广汉月亮湾出土玉石器探析》,《四川文物》2006年第5期。笔者赞同许杰1927年的推论,不仅仅是因为戴文是发表的第一篇关于月亮湾发掘的学术文章,论文发表的时间与发现月亮湾遗址的时间相距最近,而且戴氏是亲自采访过燕家人士、并最早获得可信程度最高的信息者其中之一。
那么,另一位极为重要的当事人、时任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馆长,也是1934年广汉月亮湾遗址首次考古发掘的主持者葛维汉又给我们留下了什么重要的信息呢?
经过多年来对四川大学博物馆馆藏旧档案的整理与研究工作,我们从中发现了对于解开三星堆最初考古发掘之谜极为重要的线索——葛维汉当年所记的工作日记《汉州发掘日记》(图1、图2)。葛维汉在日记中首先记载了1931年英国传教士董宜笃闻讯前往广汉月亮湾燕家院子探寻出土情况的相关事宜:
1931年春,中国四川汉州(即今广汉)的英国圣公会传教士董宜笃牧师听闻在太平场附近发现玉璧和玉刀的消息。他随后说服戴谦和教授和第二十八军的陶将军与他一起去现场勘察并拍照,晋先生作为摄影师随行。(16)葛维汉:《汉州发掘日记》,蒋庆华校译,第1页,档号P5551,四川大学博物馆藏。下同,不一一标注。
从上述日记来看,1931年春,董宜笃可能是第一次听闻月亮湾燕家院子发现玉石器的消息,从而亲自前往现场,与他同行的有戴谦和教授、当地驻军旅长陶宗伯以及摄影师晋先生。很清楚,1931年并非是燕家院子首次发现三星堆器物的年代,而是玉石器坑发现之后消息首次被透露到外界并最早见诸记载的年代。
葛维汉还记载了有关遗址发现的极其重要的情况:
发现地点位于一座古老山丘顶部的一条大型灌渠中,该山丘较其周边平原高15至40英尺不等。该处以前亦为平坦的低地,历经2000年由灌渠从灌县带下的泥沙堆积,逐渐变成了约12英尺高的山丘。
据燕道诚的次子所述,他们大约是从1927年开始在灌渠底部发现石器的,其后每年清理渠底的淤泥时陆续都有发现。这些石器起初被当成无用之物送人。董宜笃先生劝说陶将军购买了4把玉刀和1块玉璧,并将其赠给华西大学博物馆。(17)葛维汉:《汉州发掘日记》,第1页。
通过这段日记可知,当时是由燕氏家族中燕道诚的长子向董宜笃、陶宗伯——后来也可能包括葛维汉本人——介绍了当时发现石器的情况,信息来源可靠,可信度也最高。按照燕道诚的长子的说法,他们最初是在“1927年前后在沟渠底部发现石器,其后每年在清理渠底的淤泥时都会发现石器”。如果真实情况如其所述,那么燕家院子出土的玉石器就有可能并非是一次性发现的,而是以1927年为起点,在1931年之前这几年间陆续都有过发现。无论如何,1927年是月亮湾最早发现玉石器的年代,董宜笃、戴谦和以及葛维汉等人也都持此论,因此应当值得肯定。
从葛维汉的日记中,我们还了解到由他组织的对月亮湾遗址进行首次考古工作的若干重要情况。例如,他这样回忆了发掘工作的过程:
1933年秋,葛维汉致函董宜笃先生,希望获得关于博物馆玉器的更多信息。于是,葛维汉逐渐制定了一个计划,欲前往汉州在发现玉器的地点进行发掘。
3月1日,葛维汉前往汉州,为发掘工作做最后的安排。在此之前,业已获得四川省政府的正式批准和四川省教育厅的首肯。他惊奇地发现,就在当天罗县令已经开始在这个非常重要的地方进行挖掘了。但罗县令很快命令他的手下停止了挖掘,并承诺只要葛维汉愿意回来并接管发掘工作,他会耐心等待。
葛维汉先生的妻子当时正病重住院,他不得不先对该遗址采取保护措施使其免遭破坏。当医生保证葛维汉太太已脱离危险后,葛维汉先生将两个孩子留在加拿大学校寄宿,随后于1934年3月5日前往汉州,并于次日(星期二)抵达现场。当天下午就在地面立桩进行了打围。接着测量了每个立桩处的地面高度,然后工作……(18)葛维汉:《汉州发掘日记》,第3-4页。
在日记本的扉页中,葛维汉还总结性地写道:
1934年3月6日至14日,在中国四川汉州附近的太平场,华西协合大学考古艺术和民族学博物馆进行了第四号发掘。受汉州县令罗雨苍的诚挚邀请,博物馆的馆长和副馆长按照科学方法进行了此次发掘。(19)葛维汉:《汉州发掘日记》,“扉页”。
根据葛维汉的工作日记,我们可以将当时整个事件的过程做出一个简要的梳理:
(1)1931年,董宜笃、陶宗伯、戴谦和等人已经获得了关于四川省广汉三星堆遗址(即本文所称的月亮湾遗址)发现玉石器的消息,并赴现场进行了采访,核查了事实。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是通过燕家人的口述得知,1927年,他们在挖掘水渠时已经开始发现坑中的玉石器。
(2)1932年秋,葛维汉受哈佛燕京学社委派来蓉履职,担任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馆长。在整理藏品的过程中,汉州太平场(即广汉三星堆)出土的古物引起了他的注意。他随即与当时在华的英国传教士董宜笃牧师书信联系,问其可否继续代为征集汉州古物,后逐渐发展成为考古发掘计划。(20)葛维汉于1931—1932年先后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进修文化人类学、田野考古学。1932年秋,他以学者身份再次回到中国,担任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馆长,他希望在四川开展考古教学和田野考古工作,三星堆月亮湾遗址的考古发掘成为他所主持的多项考古工作之一。
(3)1933年11月17日,董笃宜牧师致信葛维汉教授,商讨农历新年之前要一起去汉州进行实地考察。(21)《广汉传教士董宜笃给葛维汉的信》,1933年11月17日,档号2010-276,四川大学博物馆藏。从葛氏日记记载可知,他也曾亲临月亮湾玉石器出土地点进行了实地考察。
(4)1934年3月1日,广汉县时任国民政府县长罗雨苍曾“抢先”开始“发掘”,但被葛维汉及时劝阻而停止。3月6日至14日,葛维汉率队进入三星堆月亮湾遗址,采用“科学方法”进行了首次三星堆考古发掘。3月19日,罗雨苍县长代表政府将全部发掘出土器物捐赠给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葛维汉代表学校接受捐赠,并感谢县长和当地人民,承诺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将为华西人民永久保存这些古物而努力。(22)葛维汉:《汉州发掘日记》,第59页。
三、结 论
综合上述分析,本文认为:
(1)举世闻名的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年代,以现存于世的四川大学博物馆旧档案为主要依据和线索,同时综合上述学者的研究工作,可以确定为1927年。既往研究中所提出的1929年、1931年等说法,虽影响甚大、流布甚广,但因缺乏文献依据,多系辗转传闻,基于史实,建议应予修改,今后统一采用三星堆遗址最早发现于1927年之说。
(2)由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前辈学者葛维汉等人开始的三星堆考古科学发掘工作的确切年代,应确定为1934年,距今已将近90年。如本文的结论能够为学术界所认同和接受,则2024年将迎来三星堆考古90周年庆典,这是在西方考古学传入中国之后,在中国西南地区进行的早期科学考古实践之一,并为随后三星堆遗址一系列重大考古的发现取得了宝贵的早期经验,积累了初步的科学研究资料,其首创性意义十分重大。
(3)三星堆考古是几代考古学者不懈努力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在我们纪念三星堆考古近一个世纪以来伟大贡献之时,应当加强三星堆考古若干基本问题和重大问题的深入研究,同时客观、科学地认识前人工作的价值和意义,吸取其经验与教训,站在新时代的高度去擘划三星堆考古与古蜀文明研究的宏伟蓝图。这将为我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探寻中华文明多源一体格局的演进路径,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更为坚实、科学的资料,从而更好地去推进学术研究、社会宣传、文物利用等各方面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