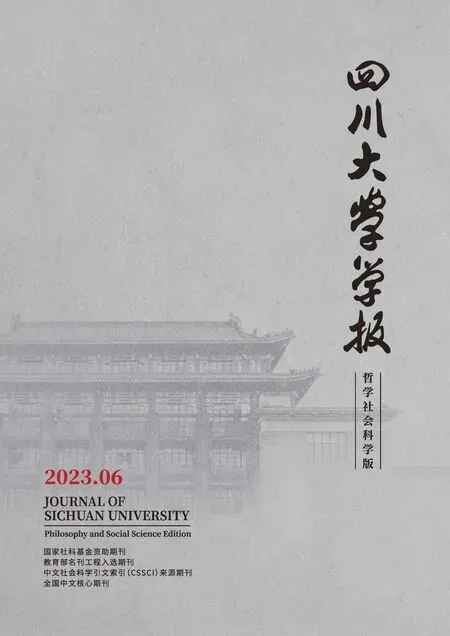慕梵而尊礼:隋唐时期汉传佛教僧众的丧葬制度
2023-12-01王大伟
王大伟
隋唐时期汉传佛教僧众的葬制,形成了水葬、土葬、火葬、露尸葬等基本模式。这些葬式几乎都受到印度佛教的影响,或完全由印度佛教传入。道宣在《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中提到:“中国四葬:水葬投之江流,火葬焚之以火,土葬埋之岸,劳林葬弃之中野,为雕、虎所食。律中多明火林二葬,亦有埋者。《五分》云:尸应埋之。”(1)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三,《大正藏》第40册,台北:新文丰出版社,2000年,第145页中。道宣所言的“中国”指的是印度,并非中华。唐代其他佛教文献在描述印度佛教葬式时,其记载几乎与道宣相同,如道世《法苑珠林》记录:“依如西域葬法有四:一、水漂,二、火焚,三、土埋,四、施林。《五分律》云:‘若火烧时,安在石上,不得草土上,恐伤虫故。’《四分律》云:‘如来、轮王二人悉火葬。’余人通前四葬者多。《五分律》云:‘尸应埋之’(此谓王法不许施身,复恐夏烧杀虫,故令埋之。自外无难,水、林亦得也)。”(2)道世编:《法苑珠林校注》卷九十七,周叔迦、苏晋仁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2788-2789页。从这些材料可看出,隋唐时期僧众能接受的葬式,也是以这几种为基础的,但每种葬式的流行程度有别。道宣《续高僧传》就提到,当时流行的葬法,以土葬和露尸葬为主:“然西域本葬,其流四焉:火葬焚以蒸新,水葬沈于深淀,土葬埋于崖旁,林葬弃之中野。法王轮王,同依火礼。世重常习,余者希行。东夏所传,惟闻林、土。水、火两设,世罕其踪。”(3)道宣:《续高僧传》卷二十九,郭绍林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168页。依道宣的观察,中古时期僧众的葬式,实际是以土葬与露尸葬为主,荼毗火葬与水葬并非主流。由于隋唐时期的石窟瘗葬、土葬(全身塔葬)等葬式保留了较多的文物遗迹与墓志等材料,也可凭借这些材料说明这两类葬式被接受的程度较高。
葬制的核心在于如何处理遗体。土葬是全身入土(塔),这是保留遗体全身的葬制;火葬是遗体被焚化后,骨灰入土(塔);露尸葬是遗体被鸟兽虫蚁等吃尽后,其剩余的骨殖入土(塔)或焚化后入土(塔),这种葬式虽然骨殖最终会被安葬,但葬制核心则是遗体被布施;水葬则是全身沉入水中或漂流,布施给鱼虫等食用。在这个时期,一个僧尼去世后,可能经历多种葬制后才最终被安葬。如最初施行了土葬,后又将其遗骨取出火化,再起塔安葬。或将僧尼遗体先置于尸陀林中施行林葬,之后骨殖再被入塔或火化后入塔。这些葬制虽然多重,但真正能表达僧尼(或其弟子、亲属等)最希望采用的葬制意愿,还是以第一次入葬时的葬制最具参考价值,所以判断一个僧尼采用了何种葬制,应以第一次入葬为准。
日本学者常盘大定早在20世纪初叶就注意到中古僧众的灰身塔,在《支那佛教史迹》中就整理了河南安阳宝山灵泉寺的“历代诸法师灰身塔”,并对一些塔铭录文。(4)常盘大定、关野贞:《支那佛教史迹评解(三)》,东京:佛教史迹研究会,1926年,第205-212页。而关于隋唐时期僧众葬制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的考古学领域就有文章发表,如张乃翥、李文生、杨超杰等从石窟寺遗址的角度对僧众石室瘗窟(穴)等的讨论;(5)张乃翥:《龙门石窟唐代瘗窟的新发现及其文化意义的探讨》,《考古》1991年第2期;李文生、杨超杰:《龙门石窟佛教瘗葬形制的新发现——析龙门石窟之瘗穴》,《文物》1995年第9期。大内文雄对宝山灵泉寺的灰身塔塔铭等内容的整理和研究。(6)大內文雄「寶山靈泉寺石窟塔銘の研究——隋唐時代の寶山靈泉寺」、『東方學報』第69冊、1997年、第287-355頁。关于宝山灵泉寺更早的文物与文献整理成果,可参见河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编的《宝山灵泉寺》(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对相关碑刻的录文。21世纪之后,刘淑芬对中古时期汉传佛教丧葬制度,如露尸葬、石窟瘗葬的研究,无论文献整理还是叙述讨论,都已非常深入;张总对三阶教的葬仪、葬制等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讨论;冉万里《略论唐代僧尼的葬制》一文是对唐代僧尼葬制问题的直接讨论,也描述清楚了此时僧尼葬制的基本形态;其博士论文《中国古代舍利瘗埋制度研究》是从考古学角度对舍利瘗埋的讨论,也兼涉僧尼葬制的研究;高歌根据灵泉寺灰身塔的塔铭题记,分析了中古时期灵泉寺僧众的墓龛形制与丧葬特点;于薇对舍利的瘗埋形式、器物、原则等有考古学的考察,其考察的主要对象是佛舍利等圣物的瘗藏;高继习对舍利地宫的形制有比较深入的研究,为僧尼瘗埋制度的研究提供了诸多借鉴之处;吴桂兵讨论了佛教因素如何影响到世俗葬礼,也对唐代僧人的墓葬特征有整理;郑弌以敦煌材料为据,对敦煌地区的僧人葬制、葬仪等有所研究;杨镜对僧尼如何选择安葬地点等问题,有文献和历史学的研究,是比较有新意的梳理。(7)刘淑芬:《佛教与丧葬》,《中古的佛教与社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张总:《中国三阶教史》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冉万里:《略论唐代僧尼的葬制》;《乾陵文化研究》2005年第1期;冉万里:《中国古代舍利瘗埋制度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年;高歌:《宝山灵泉寺石窟调查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南京大学,2017年;于薇:《圣物制造与中古中国佛教舍利供养》,北京:文物出版社,2018年;高继习:《中国古代舍利地宫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20年;吴桂兵:《中古丧葬礼俗中佛教因素演进的考古学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年;郑弌:《中古敦煌邈真论稿》,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年;杨镜:《隋唐僧尼葬地》,《寻根》2020年第2期。整体而言,关于隋唐时期佛教葬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考古学和敦煌学等领域,这与这两个领域的文献、文物等资源较多,相关学者能更直接接触中古僧人墓葬等有直接关系。
在借鉴上述研究成果基础上,本文对中古时期僧众的葬制进行整理与讨论,试图不仅呈现此时僧人采用的主要丧葬方式,还对印度佛教葬制传入中国后,与中国传统礼制,尤其是与孝道的交涉关系进行一些研究。
一、水 葬
隋唐时期关于水葬的记载并不多,在《续高僧传》中仅能看到隋代释玄景逝后是行水葬法:
释玄景,姓石氏,沧州人。十八被举秀才,至邺都为和王省事,读书一遍,便究文义,……后因卧疾三日,告侍人玄觉曰:“吾欲见弥勒佛,云何乃作夜摩天主。”又云:“宾客极多,事须看视。”有问其故,答云:“凡夫识想,何可检校!向有天众邀迎耳。”尔后异香充户,众共闻之。又曰:“吾欲去矣,当愿生世为善知识。”遂终于所住,即大业二年(606)六月也。自生常立愿沉骸水中,及其没后,遵用前旨,葬于紫陌河深滢之中。三日往观,所沉之处返成沙坟,极高峻,而水分两派。道俗异其雅瑞,传迹于今。(8)道宣:《续高僧传》卷十七,第644-645页。
可以看出,玄景所行的水葬是沉入深水之中。不过故事的后半部分,又转回了中国传统的丧葬叙事模式,玄景投身之处居然可兴起沙坟,且水为之分开。这故事以符合中国社会“入土为安”的丧葬传统为大原则,但梵华嫁接的色彩非常明显。
水葬在中国僧众的葬仪中并非孤例,宋代《景德传灯录》中记载牛头法融的法嗣——唐代智岩禅师也要水葬:“第二世智岩禅师者,曲阿人也,姓华氏。弱冠智勇过人,身长七尺六寸。隋大业中(605—618)为郎将。常以弓挂一滤水囊,随行所至汲用。累从大将征讨,频立战功。唐武德中(618—626),年四十,遂乞出家。入舒州皖公山,从宝月禅师为弟子,……又迁住石头城。于仪凤二年(677)正月十日示灭,颜色不变,屈伸如生。室有异香,经旬不歇,遗言水葬。寿七十有八,腊三十有九。”(9)道原编:《景德传灯录》卷四,尚之煜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22年,第114-115页。不过在更早的《续高僧传》的智严传记中,并未言及他以何种方式安葬,由于《景德传灯录》中关于智岩的逝世年代也被篡改,(10)印顺法师对《景德传灯录》中记载的智岩事迹进行了考辨:“《传灯录》所传智岩的事实,是依《续僧传》的,也说‘唐武德中,年四十’出家;‘年七十八’。如武德年中年四十,那仪凤二年,至少是九十岁以上,怎么还是七十八岁呢?而且,道宣卒于乾封二年(六六七);智岩死了,道宣已为他作传,怎么能活到仪凤二年呢!《传灯录》的改窜,是不足采信的。”印顺法师:《中国禅宗史》,贵阳:贵州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90页。故宋代的记述多少不那么可靠。但即使如此,这也透露出佛教僧众的确曾有过水葬的葬制。
宋代禅师确有施行水葬的,如宋代嘉兴府华亭县的性空妙普就是这样一位有神异色彩的水葬僧人,但其故事已经完全成为禅宗的叙述模式:
汉州人,遗其氏。久依死心获证,乃抵秀水,追船子遗风,结茆青龙之野,吹铁笛以自娱,多赋咏,士夫俊衲得其言,必珍藏,……绍兴庚申(1140)冬,造大盆,冗而塞之,修书寄雪窦持禅师曰:“吾将水葬矣。”壬戌(1142)岁,持至,见其尚存。作偈嘲之曰:“咄哉老性空,刚要餧鱼鳖。去不索性去,只管向人说。”师阅偈笑曰:“待兄来证明耳。”令遍告四众,众集,师为说法要,仍说偈曰:“坐脱立亡,不若水葬,一省柴烧,二免开圹,撒手便行,不妨快畅,谁是知音,船子和尚。高风难继百千年,一曲渔歌少人唱。”遂盘坐盆中,顺潮而下,众皆随至海滨,望欲断目。师取塞,戽水而回,众拥观,水无所入,复乘流而往,唱曰:“船子当年返故乡,没踪迹处妙难量。真风遍寄知音者,铁笛横吹作散场。”其笛声呜咽,顷于苍茫间。见以笛掷空而没,众号,慕图像事之。后三日,于沙上趺坐如生,道俗争往迎归。留五日,闍维,舍利大如菽者莫计。二鹤徘徊空中,火尽始去。众奉舍利灵骨建塔于青龙,寿七十二,腊五十三。(11)正受编:《嘉泰普灯录》卷十,《卐新纂续藏经》第79册,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83年,第351页中下。
性空妙普名义上被施行了水葬,但最终却依然被荼毗火葬,这个故事同样有“入土为安”的味道,与玄景的事迹颇为相似。从目前笔者掌握的材料来看,水葬在中国僧人的葬制中似乎并未受到多大的关注,或者流行度不高,这种葬制也许不符合中国人处理遗体时的伦理观念,因为沉入水中的遗体完全没有留下任何值得纪念或凭吊的“信物”,是后人难以接受的。所以玄景与妙普的故事都被安排了非常圆满的结局:玄景尸身入水后,自起沙坟;妙普更是以禅定的姿态,被他人发现了由海浪冲上岸的遗体,且火化后依然获得舍利无数,这个过程是一个完整的佛教中国化背景下的禅僧安葬故事,也让信众觉得更加“圆满”。
二、土 葬
土葬是传统中国最核心的葬制,在中古时期的僧界,土葬同样占据重要地位,远比火葬和露尸葬重要且使用频率更高。从中古时期僧众的墓志铭等文献中,可以发现僧尼保留全身入土或入塔占非常高的比例;有的僧尼还如俗众一般与子女生活在一起,去世后自然也是按照俗世的葬制安葬。
笔者统计了《隋唐僧尼碑志塔铭辑录》《唐代墓志汇编》与《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中僧人葬制,(12)笔者在最初搜集和查阅关于隋唐僧尼的墓志文献时,尚未获得介永强教授编的《隋唐僧尼碑志塔铭辑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当时根据文本数量的多寡,笔者先整理了周绍良先生主编的《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与《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中僧尼的丧葬样态。整理完唐代部分后不久,《隋唐僧尼碑志塔铭辑录》出版并上市,故隋代僧尼葬制的整理,便依据该文献辑录的文本进行。可以发现土葬在此时僧人的葬制中占据着主流地位,如笔者在这三部文献中,找到66位僧人的葬仪实际是土葬,而这66位僧人的墓志也全部收录在介永强教授汇编的《隋唐僧尼碑志塔铭辑录》中,这部文献“集录隋唐僧人(含居士)碑志塔铭(包括坟幢等)一共三百九十一篇”,(13)介永强:《隋唐僧尼碑志塔铭辑录》之《前言》,第2页。粗略的计算,该文献中收录的僧人,接近17%采用了土葬。
如隋初开皇二年(582)入葬的比丘尼媛柔:“以大隋开皇二年岁次壬寅十月六日遘疾,七日大渐于伽蓝,春秋五十有三,以其月十三日窆于杜陵原。”(14)《魏司空公尚书令冯翊简穆王第二女比丘尼元(媛柔)之墓志》,介永强:《隋唐僧尼碑志塔铭辑录》,第1页。这非常清晰的表述比丘尼媛柔是土葬在杜陵原。另一位隋代比丘尼那提也安葬在杜陵原,“仁寿四年(604)五月廿一日,春秋五十二,(那提)终于真化道场。曰以大业九年(613)岁次癸酉十月辛未朔十五日乙酉归窆于京兆大兴县高平乡之杜原”。(15)《大隋真化道场尼那提墓志之铭》,介永强:《隋唐僧尼碑志塔铭辑录》,第14页。杜陵塬位于今长安县东南,也称“少陵塬”,是汉唐乃至明代以来帝王等贵族的重要墓葬区。那提在去世9年后才“归窆”于杜陵塬,这说明她很有可能经历过改葬。实际上,隋唐时期亡僧经历两次土葬并不少见,如开元年间去世的元珪禅师:“至开元四年(716)岁次景辰秋八月甲辰朔十日癸丑,终于庞坞,春秋七十有三。十三日景辰,权厝于寺北岗之东。至十一年(723)岁次癸亥秋七月,乃营塔于浮屠东岭之左大师味净之所,而庭柏存焉。”(16)《大唐嵩岳闲居寺故大德珪禅师塔记》,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上册,第1273页。再如长安大龙兴寺的崇福法师:“去先天二年(713)五月十八日,泥洹寺房,春秋七十,权瘗于长安城西。以开元九年(721)二月廿四日,迁窆于金城北原。”(17)《大龙兴寺崇福法师塔铭并序》,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续编》,第477页。从“权厝”“权瘗”的描述能看出,这两位僧人都是暂时安葬,几年之后的迁葬才是他们的正式入葬。
从某些墓志能看出,唐代僧尼与其家族保持着非常紧密的关系,所以他们的入葬方式,往往掺杂了梵华两种礼俗的影响。如蒲州(今山西永济市)济度寺法乐、法灯两位比丘尼,他们是姐妹关系,且他们家族姐弟四人都出家入释:
法师讳法乐,俗姓萧氏,兰陵人也。梁武皇帝之五代孙,高祖昭明皇帝,曾祖宣皇帝,祖孝明皇帝,父瑀,梁新安王,隋金紫光禄大夫行内史侍郎,皇朝中书令,尚书左右仆射、特进太子太保、上柱国、宋国公、赠司空……法师则太保之长女也……以咸亨三年(672)九月十九日迁化于蒲州相好之伽蓝,春秋七十有四。权殡于河东,以永隆二年(681)岁次辛巳三月庚午朔廿三日辛卯归窆于雍州明堂县义川乡南原,礼也。(18)《大唐济度寺故比丘尼法乐法师墓志铭并序》,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上册,第676页。
法师讳法灯,俗姓萧氏,兰陵人也。梁武皇帝之五代孙,高祖昭明皇帝,曾祖宣皇帝,祖孝明皇帝,父瑀,梁新安王,隋金紫光禄大夫行内史侍郎,皇朝中书令,尚书左右仆射、特进太子太保、上柱国、宋国公、赠司空……法师即太保第五女也……姊弟四人,同出三界……以总章二年(669)十一月五日迁化于蒲州相好寺,春秋卅有九。权殡于河东县境,以永隆二年岁次辛巳三月庚午朔廿三日辛卯归窆于雍州明堂县义川乡南原,礼也。(19)《大唐济度寺故比丘尼法灯法师墓志铭并序》,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上册,第677页。
法乐与法灯两位比丘尼,年龄相差25岁,是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萧瑀的长女与五女,其家世显赫,且萧瑀自己就是非常虔诚的佛教徒。(20)如《旧唐书》卷六十三《列传第十三·萧瑀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7册,第2398页)提到他:“好释氏,常修梵行,每与沙门难及苦空,必诣微旨。”作为妹妹的法灯虽然早逝,但两位比丘尼都在永隆二年迁葬到雍州明堂县义川乡南原,其中法乐已入葬9年,法灯则入葬12年,那么第二次迁葬很可能是迁入了家族墓地。从此类迁葬的事件能看出,家族或家庭对僧人的葬制影响比较大,有的僧人虽出家,但由于有子嗣,所以他的葬制混杂了梵华两种方式,如净觉禅师就是在家中去世:“禅师本姓李,名隶崇敬寺,自称曰净觉,号之曰方便慈,众称之曰大慈。……天宝五载(746)十月廿九日,化灭于静恭里第,今终于第不于僧房者,盖在俗有子曰收,致其忧也,临终曰涂蒭,礼也。……顷葬于万年县洪固乡毕原之东南,至七载(748)十一月甲申,建塔于此原之腹,县改咸宁而改葬焉,其葬具顺僧事而从遗命也。”(21)《唐故大慈禅师墓志铭》,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下册,第1625页。“静恭”指的是唐代长安的“靖恭坊”“乃朱雀门街之东第四街街东自北向南之第七坊”。杨鸿年:《隋唐两京坊里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343页。净觉的葬仪完全借鉴了梵华两种模式,且他因为有子,还是在家中去世,但在改葬过程中,他的家人又遵其遗嘱,为其建塔安葬。与净觉相似的还如长安昭成寺的比丘尼三乘:“大唐元和元年(806)三月十四日,长安昭成寺尼大德三乘行归寂于义宁里之私第,春秋七十九,戒腊一十九……有二子……晚岁割余杭之爱,由是顿悟空寂,宴息禅林。自贞元四年(788)隶名于此寺……以元和二年(807)二月八日敬奉灵舆,归窆于城南高阳原,礼也。”(22)《昭成寺尼大德三乘墓志铭》,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下册,第1955页。三乘是晚年出家,所以她的生活必然与世俗家庭保持着联系,其安葬的礼仪,很可能也是以俗礼为主。有的僧人在逝世后,则选择安葬在祖茔,如凤光寺的常俊禅师:“和上讳常俊,俗姓张氏,清河人也。……丱岁出家,年龄七十,僧夏卌。奄自会昌三年(843)五月十五日示疾殁世,一起月廿六日还柩于常州无锡县太平乡卞村东一里官何西八十步张宗祖墓中,卜其宅兆庚首而安厝之,礼也。有门人文则、元通、伯昌,族兄秀、姪令容等,恳痛哀催,涕泪交结。”(23)《唐故凤光寺俊禅和上之墓志铭并序》,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下册,第2211页。常俊驻锡的凤光寺位于无锡,唐武德年间建,(24)“寿圣禅院在州城内仓桥下,即古凤光寺,唐武德中建”。《[至正]无锡志》,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宋元方志丛刊》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2250页。从其去世后的葬礼能看出,他不仅被安葬在家族墓地,而且参与葬仪的还有族兄、侄等人。常俊的葬仪很有可能也是兼顾了梵华两种礼俗的土葬模式。
在《续高僧传》等僧传文献中,也不乏土葬的记载,如南朝齐文宣王时代的释真玉:“布萨之后,便卧疾于邺城北王家。神气无昧,声相如常。动京大德,并就问疾。午后忽见烟云相糺,从东而来,异香缠绕,充塞庭宇,空中出声,有如赞呗之响,清亮宛然。当尔之时,足渐向冷,口犹诵念,少时而卒。卒后十日,香气乃绝。大众哀仰,如临双树。王氏昆季俱制缞绖,与诸门人收其尸而葬焉。”(25)道宣:《续高僧传》卷六,第212-213页。唐初逝世的释道庆:“以武德九年(626)八月终于寺房,春秋六十一,即以其月二十三日窆于扶塘之山津也。穿圹之日,锹锸才施,感白鹤一群自天而下,遥曳翻翔,摧藏哀唳。”(26)道宣:《续高僧传》卷十二,第426页。“(慧頵)至其年(贞观十一年,637)七月二十六日,卒于所住,春秋七十有四。葬于高阳原之西,凿穴处之。后又迁南山丰德寺东岩,斲石为龛就铭表德”。(27)道宣:《续高僧传》卷十四,第486页。“(释僧辩)以贞观十六年(642)六月十三日卒于弘福寺,春秋七十有五。于时炎曦赫盛,停尸二旬。而相等生存,形色不变。迄于葬日,亦不腐朽。于时亢旱积久,埃尘涱天,明当将送,夜降微雨,故得幢盖引列,俱得升济。七众导从,不疲形苦。殡于郊西龙首之原,凿土为龛,处之于内,门通行路,道俗同观。至今四年,鲜明如在”。(28)道宣:《续高僧传》卷十五,第518页。以上这些僧人应都属于土葬,而且有比较明显的依从俗家葬制的特点。另外,中古僧传中土葬的僧尼远不止上述几位,有很多虽未明言土葬,但从措辞来看,土葬的可能性也较大。这也就难怪道宣在论述葬制时,强调“东夏所传惟闻林土”了。
三、露尸葬
露尸葬即林葬、寒林葬,是露骸于野,遗体被鸟兽虫蚁啃噬后,再收骨起塔或瘗藏于石室。中古时期,这种葬制被僧众接受,并逐渐成为僧尼入葬方式的主流。关于隋唐时期露尸葬的研究,学界著述颇丰,尤其是张总、刘淑芬等在林葬及石室瘗窟方面的研究,已非常详尽,无必要过多重复。下面仅就笔者的一点发现做一些论述。
从墓志的情况来看,露尸葬的数量并不多,其倡导者之一,正是三阶教的创始人信行禅师。《故大信行禅师塔铭碑》描述:“春秋五十有五,以开皇十四年(594)正月四日卒于真寂寺。即以其月七日送柩于雍州终南山鵄鸣埠尸陀林所,捨身血肉,求无上道。……于是法师净名、禅师僧邕徒众等三百余人。……遂依林葬之法,敬收舍利,起塔于尸陀林下。”(29)介永强编:《隋唐僧尼碑志塔铭集录》,第5页。信行的弟子采用林葬者很多,“禅师俗姓周,道讳灵琛。初以弱冠出家,既味大品经论,后遇禅师信行,更学当机佛法。……年七十有五,岁在玄枵三月六日,于慈润寺所,结跏端俨,泯然迁化……依经葬林,血肉施生……肌膏才尽,阇维镂塔”。(30)《慈润寺故大灵琛禅师灰身塔铭文》,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册,第17页。灵琛的墓塔于唐贞观三年(629)四月十五日造成,其骨灰也很有可能在这个时间入塔。三阶教史上一位重要人物——净域寺法藏也是以林葬后骨殖入塔的方式,安葬在信行塔旁:“禅师讳法藏,缘氏诸葛,苏州吴县人。……粤以开元二年(714)十二月十九日舍生于寺,报龄七十有八……即以其年十二月廿□日施身于终南山楩梓谷尸陀林。由是积以香薪,然诸花叠,收其舍利,建窣堵波于禅师塔右。”(31)《大唐净域寺故大德法藏禅师塔铭并序》,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册,第1178-1179页。法藏受到武则天的赏识,曾检校洛阳大福先寺无尽藏、长安化度寺无尽藏,并奉请为长安荐福寺大德,是一位在武后时期有一定政治地位的僧人。贞观十三年(639)去世的光天寺禅师僧顺,“韩州涉县人,俗姓张氏,七岁出家……春秋八十有五,以贞观十三年二月十八日卒于光天寺……廿二日送柩于尸陀林所,弟子等谨依林葬之法,收取舍利,建塔与名山,仍刊石图形,传之于历代”。(32)《光天寺故大比丘尼僧顺禅师散身塔》,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册,第50页。僧顺同样崇奉三阶教,以林葬的方式舍身,符合她的信仰样态。僧顺的墓塔位于岚峰山塔林(宝山灵泉寺石窟)中,“岚峰山第47号唐贞观十四年(640)《光天寺故大比丘尼僧顺禅师散身塔》,塔为单层,上罗相轮,塔身两侧镌有标题和年代,正面龛中则雕刻着僧顺的相,其头部有残缺,身着袈裟,坐于三足凭几后,两侧有弟子侍立”。(33)张总:《中国三阶教史》,第369页。僧顺的墓塔属于塔龛,并非真正的起塔,这也正是中古时期瘗龛的标准样态。
禅僧中亦有此类者,明州观宗禅师是牛头慧忠的法嗣,属牛头宗一脉,(34)《景德传灯录》中收录牛头慧忠门下三十六人,明州观宗在其中,但无传。观宗的葬制是先藏于瘗穴,这是一种类似半遗身的葬法,时隔六年后才建层龛安葬。“元和四年(809)八月十五夜跏趺化灭,享龄七十九,僧腊卌九。以其年十月一日权闭于太白峰南,先意也……抵元和乙未(十年,815)岁建层龛迩于多宝佛塔,依像法也”。(35)《大唐故太白禅师塔铭并序》,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下册,第1972页。“权闭”就是对其露尸的空间进行一定程度的封闭,所以其尸身未必会被鸟兽等吃掉,有可能是自然腐败后再起塔安葬。(36)刘淑芬认为:“从僧传或塔铭中,可知石室瘗窟是林葬暴尸林野的一种调和的形式。有些佛教的僧人或俗家居士遗言林葬暴尸,但是其弟子或家人不忍心遵从遗命,遂将其林葬的遗愿做了一点修正,改将其遗体瘗藏在石室或石窟之中。”刘淑芬:《中古佛教与社会》,第259页。
与墓志对露尸葬的记载并不丰富相比,僧传文献关于死后采取林葬的僧人的描述则比较多,如隋代释智琳,“及将大渐,诫诸弟子:‘尸陀林者,常所愿言,吾谢世后,无违此志。’沙门智铿等谨遵遗言,以其(大业九年,613)月十一日迁于育王之山。时属流金,林多鸷兽。始乎仲夏,暨是抄秋。肤体俨然,曾无损异。道俗嗟赏,叹未曾有。又以其年闰九月八日,于招隐东山式构方坟,言遵卜兆,全身舍利,即窆山龛”。(37)道宣:《续高僧传》卷十,第349页。信行的弟子释本济,“以大业十一年(615)九月十二日卒于所住之慈门寺,春秋五十有四。弟子道训、道树,式奉尸陀,追建白塔于终南山下,立铭表德”。(38)道宣:《续高僧传》卷十八,第686页。隋代释通幽,“遂诫弟子曰:‘吾变常之后,幸以残身遗诸禽兽,傥蒙少福,冀灭余殃。’忽以大业元年(605)正月十五日,端坐卒于延兴寺房,春秋五十有七。弟子等从其先志,林葬于终南之山至相前峰,火燎余骸,立塔存矣”。(39)道宣:《续高僧传》卷二十二,第837页。隋代释法纯,“卒于净住寺,春秋八十有五,即仁寿三年(603)五月十二日也。葬于白鹿原南,凿龛处之,外开门穴,以施飞走。后更往观,身肉皆尽,而骸骨不乱”。(40)道宣:《续高僧传》卷十八,第677页。唐初去世的吉藏法师,也是采用的林葬:“斋时将及,奄然而化,春秋七十有五,即武德六年(623)五月也。遗命露骸,而色逾鲜白。有勅慰赙,令于南山觅石龛安置。东宫以下诸王公等,并致书慰问,并赠钱帛。今上初为秦王,偏所崇礼……时属炎热,坐于绳床,尸不催臭,加趺不散。弟子慧远,树续风声,收其余骨,凿石瘗于北岩,就有碑德。”(41)道宣:《续高僧传》卷十一,第394-395页。唐代释慧胄:“春秋六十有九,即贞观初年(627)也。乃露骸收葬,为起方坟,就而铭之。”(42)道宣:《续高僧传》卷三十,第1224页。僧传中此类记载颇多,前人已揭,笔者不再重复。与僧传中的记载相似,河南安阳宝山灵泉寺有210座墓龛,其中有80座的题记铭文可辨识,可发现他们普遍采用的是林葬。(43)高歌:《宝山灵泉寺石窟调查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南京大学,2017年,第151-158页。隋唐时期僧尼采用林葬符合当时僧众的丧葬习惯,也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虽然有关僧尼林葬的墓志铭收录不多,但这与墓志文献的流传和出土等有直接关系,也与入葬者是否有人为其筹划撰写刊刻墓志铭有直接关系。从僧传的记载看,露尸葬其实已成为隋唐时期僧众的主流葬制之一。不过,由于明显与中华传统葬制有抵牾,伴随着佛教的中国化及传播势头渐衰,该葬制逐渐退出了僧众的常用葬制。
四、火 葬
由于世尊采用了火葬,所以这种葬制也成了佛教最认可和最标准的丧葬方式。隋唐时期僧人采用火葬的数量亦不在少数,其基本样态是火葬后骨殖(舍利)入塔。另外,隋唐时期的火葬还可视为一种“终极葬制”,也就是亡僧在经历过土葬或露尸葬后,有可能被迁葬或弟子收其骨殖后重葬,往往采用先火化其骨后再入塔安葬的方式。所以,某些亡僧的葬制是复合式的,这也是有别于俗人葬仪的特殊之处。
从墓志铭看,关于火葬的记载并不多,笔者仅找到3篇,如贞观十五年(641)去世的慧静法师:“师寝疾弥留,渐衰不愈。春秋六十有九,以大唐贞观十五年四月廿三日卒于寺所。弟子法演,早蒙训诱,幸得立身,陟岵衔恩,展申诚孝,阇维碎骨,迁奉灵灰,凿镂山楹,图形起塔,铭诸景行。”(44)《唐故慧静法师灵塔之铭》,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册,第56页。弟子们将慧静的骨灰置于瘗龛之中,并在外刊刻塔形及慧静形象,与前文所述僧顺之瘗龛塔形同类,这也是隋唐之际僧尼葬制的一个突出特色。贞观十七年(643)去世的俗姓崔的法师:“春秋七十有八,大唐贞观十七年八月四日迁神于先天寺所。弟子等哀慧日之潜晖,痛慈灯之永灭,乃依经上葬,收其舍利。粤以贞观十八年(644)岁次甲辰十一月十五日于此名山镌高崖而起塔,写神仪于龛内,录行德于庙侧。”(45)《唐故崔法师墓志铭》(自拟),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册,第75页。崔法师的葬制与慧静几乎相同,也是弟子将其遗体火葬后,藏入瘗龛之中,并在崖壁上刻塔图形,好似入塔安葬一般。咸通十一年(870),幽州甘泉院的晓方禅师逝世,“咸通十一年三月十日,迁神于此山,报龄七十二,僧夏五十八……肇建灵龛于院西南盘龙山首焉。以明年 月 日奉迁神座于是山”。(46)《唐故甘泉院禅大师灵塔记》,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下册,第2452页。晓方是婺州五洩山灵默禅师的法嗣,由于其无法语传世,故并未收录传记。从这篇塔记的描述能看出,晓方逝世后是先火化,然后再建瘗龛于盘龙山,其与慧静、崔法师等的葬制也是相同的。
从隋唐时期僧众葬制的使用频率看,火葬也并不能算主流的葬制,也正如前文所引道宣的评述“东夏所传,惟闻林、土。水、火两设,世罕其踪”。不过,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就是如果发生迁葬或改葬,往往会将僧尼的遗骨火化后起塔安葬,所以火葬在此类丧葬活动中,有点“终极之葬”的味道。如禅宗三祖僧璨,其在隋末去世后被道信安葬在居所,天宝年间又被开棺阇维,再将舍利起塔安葬:“门人有道信者,大师异其神意,传付之道,如可公之于大师焉。告之曰:‘有人借问,勿道于我处得法。’从此便托疾山阿,向晦宴息。忽大呼城市曰:‘我于皖山设斋,汝等当施我斋食。’于是邑咸集,乃于斋场树下,立而终焉。异香满空,七日不散。道信奔自双峰,领徒数百,葬大师于所居之处。时人始知道信得法于大师。而时隋末崩离,不遑起塔。洎皇唐天宝五载(746),有赵郡李常,土林精爽,朝端问望,自河南少尹左迁同安郡别驾,怆经行之丘墟,慨茔垄之芜没,兴言改举,遐迩一辞。于是启坟开棺,积薪发火,灰烬之内,其光耿然,胫骨牙齿,全为舍利,坚润玉色,铿铛金振,细圆成珠,五彩相射者,不可胜数。”(47)《僧璨大师碑》,介永强编:《隋唐僧尼碑志塔铭集录》,第16页。开元十九年(731)七月十九日去世的香山禅师义琬,是嵩山慧安禅师的法嗣,他在去世前,曾对弟子们有一番嘱托,涉及他逝世后丧葬样态的问题:
师未泥洹,先则玄记:吾灭度后,卅年内,有大功臣置寺,度遗法居士为僧,卅五年后焚身,留吾果园,待其时也。果廿八年有文武朝纲□国老忠义司徒,尚书左仆射、朔方大使、相国郭公上额于居士,拜首受僧,奏塔梵宫,牓乾元寺。法孙明演授禅父托,葬祖黄金,述德于中书令汾阳郡王郭公彻天,请号焚葬,借威仪所由捡挍。大历三年二月,汾阳表曰:义琬禅行素高,爲智海舟航,是释门龙象,心超觉路,远近归依,身殁道存,实资褒异,伏望允其所请,光彼法流。其月十八日义琬宜赐谥号大演禅师,余依。择吉辰八月十九日荼毗入塔,今卌载,无记不从大禅翁也。(48)《唐故张禅师墓志铭并序》,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下册,第1765页。
如果抛开义琬逝后丧葬活动的神异过程,单从其葬制来说,他实际经历了先土葬后火葬入塔的过程。唐代窥基法师的葬制,是先全身入塔陪葬于玄奘法师塔侧,后墓塔颓圮,故重新修塔安葬,但第二次安葬时,会将全身焚化,荼毗入塔:
法师以皇唐永淳元年(682)仲冬壬寅日,卒于慈恩寺翻译院,有生五十一岁也。后十日,陪葬于樊川玄奘法师塔,亦起塔焉,塔有院。大(太)和(828)二年二月五日异时,门人安国寺三教大德赐紫法师美林,见先师旧塔摧圮,遂唱其首,率东西街僧之右者。奏发旧塔,起新塔。功未半而疾作,会其徒千人,尽出常所服玩,洎向来箕敛金帛,命高足僧令捡,俾卒其事。明年七月十三日,令捡奉行师言,启其故塔,得全躯,依西国法,焚而瘗之。其上起塔焉。(49)《大慈恩寺大法师基公塔铭并序》,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下册,第2187页。
窥基法师的安葬过程与义琬几乎相同,也是先全身土(塔)葬,后迁葬,故又火化后入塔。《续高僧传》也记有此类现象,如上文提及的隋代释智舜的尸身被山民偷走,藏匿三年后才告知他人并火化后起塔:“(智舜)卒于元氏县屈岭禅坊,时年七十有二,即仁寿四年(604)正月二十日也。初,葬于终所山侧,后房子县界嶂洪山民素重舜道。夜偷尸柩瘗于岩中,及往追觅,皆藏其所。三年之后开示焚之,起白塔于崖上。”(50)道宣:《续高僧传》卷十七,第646-647页。唐初释道哲去世后,入葬又迁葬,也是火化后入塔:“(道哲)奄然卒于故房,春秋七十二矣,即贞观九年(635)正月也,葬于京之西郊。故人慕仰声范,遂发冢迎柩,还归周至,行道设斋,以从火葬。收其余烬,为起砖塔于城西二里端正树侧龙岸乡中,列植杨柏,行往揖拜。”(51)道宣:《续高僧传》卷二十,第740页。这些僧众的葬礼,都牵涉到改葬或迁葬,其葬制或华或梵,虽然可以葬多次,但又不显得违和,且也符合僧人的宗教身份。多种葬制都可采用的丧葬模式,是两种文明作用下,汉传佛教葬制的特殊之处,同样是佛教中国化在佛教社会生活史细节问题上的显现。
五、隋唐僧尼墓志铭中的弟子孝行
汉传佛教与中华孝道之间无论从理念还是传统,似乎并不违和,虽然佛教一直强调出世的修行,但弟子们在师长去世后,展哀的方式一直有非常明显的中华俗世孝道色彩。广兴(Guang Xing)认为,中国佛教徒以开放的态度,从印度佛教中获得资源,对孝道进行理性的疏解,也接受中国哲学与文化的深刻影响,以此来回应社会对孝道问题的批评;同时也会驳斥一些认为他们并非中华的指责。(52)Guang Xing,Filial Piety in Chinese Buddhism,New York:Peter Lang Publishing,2022,p.306.“孝”是儒家与佛教礼制之争的重要工具,乃至于《孝经》在中古时期被宗教化,“如果认为这样的孝的德行,与佛的教导相对抗,也就是必须在宗教的水平上而特别有意识地加以彰显,那么通篇全都当然地高扬孝的主题,诵读又很便利,而且早自汉代以来就被相信有‘祛邪’之力的《孝经》就变得被赋予了也与佛典类似的位置。亦即《孝经》就变得被特别赋予了宗教性的位置”。(53)吉川忠夫:《六朝精神史研究》,王启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33页。关于佛教与孝道的关系,亦可参考吉川忠夫「孝と佛教」、麥古邦夫主編 『中國中世社會と宗教』、東京:道氣社、2002年、第1-18頁。所以,“孝道”不仅属于文化和民俗层面的概念,同时也代表社会秩序的构建,“以孝治天下”已成为中国历代帝王统治的共识,“在泛孝主义影响下,孝乃成为传统中国人在家庭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及宗教生活中最核心的伦理基础。根据此一事实,我们不仅可说传统中国是以农立国,而且可说是以孝立国”。(54)叶光辉、杨国枢:《中国人的孝道:心理学的分析》,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8年,第3页。在中国,孝行是渗透社会各个层面的理念,具有重要的指向性意义。中古时期的汉传佛教几乎完整接受了中国的孝道理念。从墓志铭的描述,几乎看不到孝道与佛教之间存在龃龉,相反,许多僧尼的墓志铭不仅记载僧人的家世履历,同时也在表达弟子们的孝行孝心,甚至对孝行的描述成为墓志铭的核心内容。

还有僧尼的葬仪实际是由亲属直接操办的。如东都洛阳安国寺的女尼圆净,于兴元元年十二月十四日去世,兴元二年(兴元二年当为贞元初年)正月十日安葬在龙门天竺寺西南原。为她置办葬礼的弟子,也是她的亲人,“弟子契虚,上座姊之子也。幼稚而孤,顿其训育,继姨母之高躅,为□之律德。哀罔极而难,哭晨昏而不绝。弟子明粲,上座之从妹也;弟子澄照等,痛陵谷之不常”。(57)《有唐东都安国寺故上座韦和上墓志铭并序》,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下册,第1837页。这篇墓志铭比较有趣之处在于,一方面强调圆净的弟子中,有两位是她的亲人,同时又明确他们是佛教信仰样态下的亲属关系。从这篇墓志铭的行文以及圆净的安葬过程可看出,僧尼的土葬样态,其实是佛教葬制外衣下,传统社会葬制的复制。孝子与弟子一样不可缺少,如果弟子能天然地构成孝子关系(或处于五服之内),那么这样的葬制一定是墓志铭中值得特别书写的内容。比较巧的是,同样是东都洛阳安国寺,还有一位姓皇甫的比丘尼——澄空,她在贞元九年(793)去世,弟子中起孝子作用的是她的侄女,“侄女子沙弥契源,教育恩深,执丧孺慕,暨戒依缁侣,殒叩呼天”。(58)《唐东都安国寺故临坛大德塔下铭并序》,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下册,第1873页。文本中描述的契源,是完美的孝子,执丧奉哀,都符合传统世俗社会的要求。两位比丘尼有着相似的丧葬过程,其亲自养育的子侄,在葬礼中的身份是多重的,是弟子与亲人的混合,而且这种关系更加深了两者的紧密感,即使并非丧者所生的亲人,也会给人以如其子女一般的感觉。
有的僧尼曾有过婚育,并在私宅中去世,实际是寄名的僧尼。如元和元年(806)三月十四日去世的长安昭成寺尼三乘,“归寂于义宁里之私第,春秋七十九,戒腊一十九”,三乘婚配昭陵令赠通州刺史李昕,生育两个儿子,在贞元四年隶名昭成寺为尼,元和二年二月八日入葬。(59)《昭成寺尼大德三乘墓志铭》,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下册,第1955页。三乘是居家修行的比丘尼,与寺院也只是“隶名”关系,她的葬仪也是按俗家的样式进行的。中古时期的僧尼居家修行是被社会认可的,在敦煌地区很普遍:“依据一些迹象推测,敦煌僧尼或住寺或住寺外可能都是自由的,僧团和官府似乎并不干涉。”(60)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94页。汉地也存在此类现象,“师俗姓庞,名六儿,法号空寂。右千牛将军同本之第六女也。生长贵门,栖□禅寂。年十五,自割发披法服,将军不能遏。年五十二,以开元六年六月终于家。以开元廿七年八月廿四日葬于奉天县秦川下原,祔先君之茔侧也”。(61)《大唐故空寂师墓志铭》,周绍良等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第569页。空寂可能也是居家修行的比丘尼,似乎并未婚育,她的一生可能都在家族的顾护下走完,其葬仪也是按俗世样态举行的。那些有子嗣的居家僧尼的葬仪尤其突出子侄的孝思,这种葬制其实已与俗世没有差别。道端良秀曾对这种佛教信仰者有过评价:“虔诚地信仰佛教,但作为家族制度的一员,在儒教的孝的制约下,又将孝作为最高指示来遵奉——在家佛教徒就存在于这样的生活中。换言之,在家佛教徒指的就是生活在儒教的礼的世界中,一面遵循礼,一面又像佛教徒般生活。中国的在家佛教,指的就是人们的这种生活。当然,对在家佛教徒而言,正式成为佛教徒也需要受持三皈五戒,所以就又出现一个问题,即必须谋求五戒和儒教五常的结合。”(62)道端良秀『唐代佛教史の研究』、京都:法藏館、1957年、第318頁。从中古时期僧众葬制的使用频率来看,土葬是调和华梵之间文化矛盾的比较好的手段;从墓志铭等文献描述来看,似乎当时的信众也并不觉得违和,佛教的信仰与儒家的五常在此时已经有了很好的融合。
隋唐时期(或整个中古时期)的僧尼葬制是多元的,似乎也只有这个时代才有如此多种类的丧葬模式,而它们又无一例外地被建构在佛教义理的基础上,并努力寻求中华礼制的认同。正如隋唐这个自信、多元、开放甚至恣意的时代一样,佛教僧尼的丧葬表现出个人、家族、教团等多方面的诉求,又带有鲜明的逝者的主观色彩。他们所考虑的是如何践行自己对佛教信仰的理解,但落实到具体的葬制,又不得不兼顾礼制的要求。在浩浩荡荡的佛教中国化进程中,隋唐是佛教从多姿多彩走向一枝独秀的最关键的时期,对此时僧众葬制的研究,能深刻感触到更加圆融的文明互动的过程。开放与包容,建构出绚烂的隋唐佛教文化,为后世留下诸多令人惊叹的遗迹与成果,某些文化现象从那时的寻常之物,到今天的不复得见,这虽然是佛教中国化过程中文明拣择的结果,同时也是一个宗教乃至其制度逐渐走向固定与封闭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