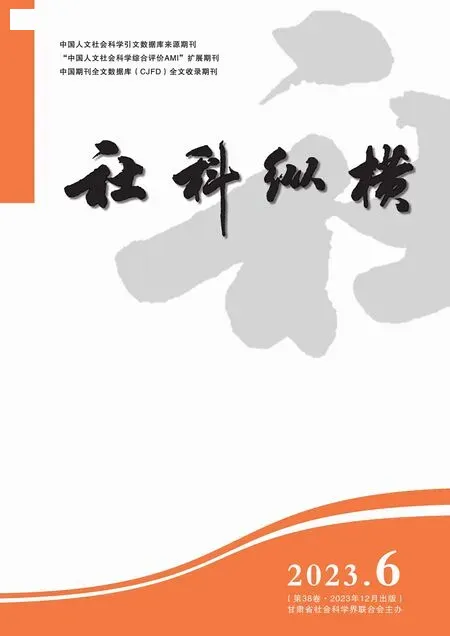董仲舒大一统论基本内涵的三重维度分析
2023-03-13崔锁江
崔锁江
(衡水学院董仲舒与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河北 衡水 053099)
《春秋》的隐公元年经首出““元年春王正月”六个字。《公羊传》解释道:“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大一统是《公羊传》的首要概念。何休以正始说明大一统的原始义,但董仲舒对大一统极有发挥,成为一个涵盖天地、古今、王道、君主、臣官、民人,包容形上形下、时间空间、华夷之辨等丰富内容的巨型理论体系。余治平先生认为《春秋》的“王正月”、《公羊传》的“大一统”与何休解诂包含着“时间、礼制、法度、王政、教化、宗教信仰、天地宇宙、自然万物、存在论、宇宙论、本体论、君道、臣道、治民之道、哲学、政治学、道德学、伦理学、天人关系论等内容,浑然一体,可以释放出无比开阔的解释空间,纵横之捭阖,上下、左右之交叉,而经得起多层面、多角度的意义挖掘”[1]。这说明大一统论具有理论的多维丰富性。与此同时,很多学者注重把握大一统论的精髓。很多历史学者则把大一统作为描述中国古代国家形态的重要概念,甚至以之流变为“大统一”的现代义。
一、大一统论基本内涵的研究综述
何休解大一统得出“正始”的结论,这可以看作是大一统的原始义。现代学者则先后分析出王道说、二维说、三维说、四维说等说法。
(一)“正始”说
何休以“正始”作为大一统的原始义,提出“政莫大于正始”的观点。何休的“正始”说源自董仲舒的“五正”说。董仲舒说:“是故《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内之治,五者俱正而化大行。”[2]174何休说:“《春秋》以元之气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内之治……故先言正月而后言即位,政不由王出则不得为政,故先言王而后言正月也,王者不承天以制号令则无法,故先言春而后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则不能成其化,故先言元而后言春。五者同日并见、相须成体,乃天人之大本、万物之所系,不可不察也。”[3]除了其中的“元之气”容易引起后世学者异议之外,何休提出“天之端”“王之政”“诸侯即位”“境内之治”等“五正始”的推扩过程。“始”存在《公羊传》的“君之始年”“春为岁之始”。“元”“始”“统”在《白虎通义》与何休《解诂》当中用来互释。至此,“正始”被看作是“大一统”原始义。对于“始”而言,就要“变一为元”;对于“正”而言就要“一统”。“正”是“使之正”,“始”是“正之始”。“正”“始”二字本身就意味着“天—王—君”的“大一统”逻辑进路。
(二)“王道”说
谢遐龄先生提出:“大一统,意思是重视、强调王政之开端。”[4]他举出孔颖达的观点,说明何休“五始”有不通之处。他认为:“《春秋》为尊王而作,欲以王法正天下,以天道正王道。此其主旨也。”这说明“五始”并不是平衡的,而是要围绕“天道”“王道”展开,其中的“正天下”则意味着“政治大一统”的一般意义。谢遐龄先生认为“君权是既定事实,无须在论证君权天授上费辞”,因此,他在注重“王道”核心的同时也注重教化、义利之辨、德主刑辅、兴学养士等有关思想大一统的内容。
(三)以思想统一为重点的二维说
周桂钿先生认为“大一统包括思想统一和政治统一两个方面”,其根据则是何休的“政教之始”的说法。他认为:“统一思想就成了大一统的关键”,“董仲舒所谓大一统主要是统一思想”,“大一统的主要思想是统一,统一就是要服从,人民服从皇帝,皇帝服从上天,上天就是儒家思想。实质上就是用儒家思想来统一天下”[5]。以“思想大一统”为重点符合董仲舒对策的背景与目的。
(四)三维说
胡骄键先生把董仲舒大一统观归纳为形上(体元居正)、时间(三统之变)、空间(奄有四海)三重维度[6]。李英华把“奉天”“法古”“爱民”作为“大一统”的三位一体结构[7],以“爱民”抵消“屈民伸君”所导致的君主专制主义倾向。
(五)四维说
王传林先生认为大一统包含政治、意识形态、文化、民族等多维向度。他认为:“董仲舒提出的‘大一统’所追寻的不只是政治、地理与文化层面上的‘一统’,而是更强调追寻天下人心的‘一统’。”他还认为:“董子从《春秋》中绎出的‘大一统’思想的内涵是多维的,既有基于《春秋》大义对儒家王道政治的理想化期许,又有对秦时以李斯与秦始皇为首的抑儒与焚书之历史行为的反动与校正,其中亦有对《尚书》与《诗经》所蕴‘大一统’精神的回应与开新。”他认为:“董子建议的‘大一统’并不能简单地用‘思想一统’‘政治一统’或者‘只有儒家才讲大一统’来笼统论之,董子的建议是多维度与多层次的,既有地理意义上的国家一统、政治意义上的权力一统,又有文化意义上的礼乐一统,以及政治哲学与伦理观念上的思想一统。”这就提到了多维度、多层次。他划分为“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大一统’”就强调政治大一统与意识形态大一统之间的“合”[8]。他又提到“文化与民族的‘大一统’”这就有文化大一统与民族大一统之间的“合”。这就把董仲舒的大一统划分为政治、意识形态、文化、民族四个层次,其中“意识形态”与“文化”还有一定的区分。
黄铭认为“大一统”是天道规范在政治上的体现。由此可见天道维度的优先性。他认为表面上看《春秋》经文仅仅是时间的记录,而公羊学则抓住了“王”这个核心观念,这就指向了王道维度。他认为《公羊传》的大一统是要“建立起一个以周天子为中的有秩序的政治体系”,这就指向了政治维度。他在确立了“奉周正朔”这个原始义之后,以“天道”正“王月”、屈伸之义、大一统与通三统、独尊儒术等四个内容分析董仲舒大一统论[9]。他注意到董仲舒通过“元年春”把“天”引入到公羊学之中,注意到“王”处于“元年春”与“正月”之间,引用董仲舒“上奉天施而下正人”说明“王道”的重要性。他分析“屈伸之义”得出“大一统”是为了“规范君王的行为”的结论,他以“独尊儒术”概括《对策》的主题,得出儒学主导意识形态的结论,而非钳制思想自由,进而认为“圣人的学说对于‘大一统’来说是必要性”。由此可见,正始原始义与天道、王道、政治三重维度都得到了阐释。
(六)“大统一”流变说
晁天义先生首先把“大一统”划分为本义与引申义。他从“大”“一”“统”三个辞说明本义,“大”代表“推崇”;“一”是相对于“三统”而言的“正统”;“统”则一年起始时间,是“统绪”,而不是“统治”。他认为:“及至晚近以来,‘大一统’本义逐渐被人们忽视,在很多场合下被理解为‘大统一’,即‘大规模的统一’或‘大范围的统一’。”[10]他认为这是“对概念本义的一种创造性发展,然而由于容易导致对经典的误解,因此引起不少人的警惕”,并提到李景明、宫云维、蒋庆的观点加以说明。
二、董仲舒大一统三重维度的确立
董仲舒直接涉及“大一统”的文本主要在《天人三策》《三代改制文》之中。其中涉及“变一为元”“王正月”“五始”“天地古今六艺”四个内容。
(一)“王正月”解
董仲舒说:“《春秋》曰‘王正月’,《传》曰:‘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以谓之王正月?曰: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继人,通以己受之于天也。王者受命而王,制此月以应变,故作科以奉天地,故谓之王正月也。”[2]223董仲舒解“王正月”引出“正始”“正统”“三统之变”等众多理论问题。董仲舒的意思是“王”(开国之君)要“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进而说明自己的“明易姓,非继人”与“受之于天”。这相当于建立“正统”。但是,董仲舒没有用“正统”这一概念,而是用“明易姓”“受之于天”的说法。
董仲舒提出的“一统于天下”相当于以王道正天下,而君主则要效法“王道”,进而引申为尊孔、崇儒,形成以儒学思想引领政治的局面。何休称之为“一王之法”。“一统”即是“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继人,通以己受之于天也”。与“王正月”最重要的关联是“改正朔”,即设立以哪一个月为正月,这就是正黑统、正白统、正赤统。由此,“王正月”作为一统,必然包含“正统”之义,必然导致“通三统”的问题出现。
“王正月”指向的史实是周文王“斗建子”“正赤统”。董仲舒说的“王者受命而王”“作科以奉天地”就包含着王道服从天道的含义。后世人君更效法王道,王道代表着一种政治理想主义,进而意味着思想必须统一于儒学。这就贯穿了宇宙、思想、政治,三者各自也处于一统之中。王者是“受命而王”,那么作为诸侯更要奉周正朔、政令,才能实现“公即位”。黄铭以“桓无王”为例说明书写“王正月”的重要性。其意指鲁桓公没有得到周天子的受命。何休把“王正月”分为“先言正月而后言即位”“先言王而后言正月”两个步骤,进而说明“王正月”辞法。这就出现“王”“正月”“即位”三个层面,也说明王道理想政治与君主现实政治之间的差别。
(二)“变一为元”解
《春秋》的隐公元年经首出“元年春王正月”六个字。《公羊传》解释道:“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到这里并没有结束,《公羊传》接着针对“公何以不言即位”展开论述,“公即位”是“元年”背后的历史事件,而不可忽。
董仲舒说:“臣谨案《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11]2188董仲舒针对“元年”,去“年”取“元”,提出了“变一为元”。变一为元的背后隐藏着“天道”,其中“春”就是天道的文本落实,天道指向了宇宙大一统,“王道”指向了思想大一统,而“公即位”则指向了政治大一统。
(三)“五正”解
董仲舒说:“臣谨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然则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11]2187
董仲舒去“月”取“正”,就有了“五正”(五者俱正)的说法。由“正”生出“正统”“正始”等概念。
1.“王次春”意味着以天正王,以天道正王道。“王”则引申为“王道”,“公即位”则意味着现实的君主政治。笔者认为必须认真区分“王”与“君”两个概念,不得混淆,“以天正王”其实质则是要求以天正君,君主是所要“正”的重点对象。对于“王”而言,王者奉天法古,直接达到了“天人合一”,“王之所为”就是“君主”要归于“正”。这个“正”有两个来源,分别是天道、王道,这就形成了“奉天法古”的说法,形成后世君主与天道、王道的关系。需要注意的是“君”与“王”并不是直接等同,后世君主不能直接等于“王”。在《春秋》《公羊传》的语境中,“王”是周文王,“王”意味着古代圣王。董仲舒的“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的“王道”只能是上古圣王之道,这被董仲舒称之为“法古”“复古”。这里的君主、天道、王道构成了一种复杂关系。
2.“正次王”意味着以王正天下,是要儒家要以“王道”正君心,进而使人君能够正朝廷、百官、万民、四方、境内之治理。董仲舒说:“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11]2188其中的“人君正心”就是大一统的向上维度,即“体元居正”,即是要“奉天法古”,而“正朝廷、正百官、正万民”则属于“正竟内之治”,是低层次的政治大一统。
(四)“天地古今六艺”解
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11]2197
1. 天地之常经
董仲舒把“大一统”推动“天地之常经”的地位,把经学运用到天地、万物、自然领域,形成“宇宙大一统”论。而这中间的关键就是“变一为元”,实现从单纯政治哲学向自然哲学的飞跃,把“大一统”树立为绝对真理。
2. 古今之通宜
董仲舒再把宇宙大一统论运用到公羊学的解释系统,进而以阴阳、五行、灾异谴告说明《公羊传》所隐晦的微言大义。董仲舒实现了天人感应论与春秋公羊学的叠加与融合,把“大一统”树立为历史结论,把春秋公羊学设立为绝对的学术权威,形成有关“政治大一统”的治国方略,也就是董仲舒所言的“六艺之科孔子之术”。
3. 六艺之科孔子之术
董仲舒把大一统看作是绝对真理与历史结论之后,就要求君主尊崇儒学——“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进而能够在思想大一统的帮助下实现“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的政治大一统秩序。按照“五始”解,这是宇宙大一统,经思想大一统向政治大一统秩序的秩序推扩,其中包含着针对“今师异道,人异论”,给出“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的“思想大一统”文化政策。
三、董仲舒大一统的天道维度
董仲舒思想利用天、道、阴阳、五行、中和等哲学概念建构了一套“天的哲学”,并以“天人合一”为显著标志,从而在天道维度上形成“宇宙大一统论”的思想建构。
(一)天道不变
董仲舒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损益也。”[11]2195大一统论最重要的是确立天的权威性。董仲舒以“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恒常性肯定了儒家的天道论是绝对真理。
(二)天道贵始
董仲舒说:“臣谨案《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11]2188类似的说法还出现在《玉英》篇,董仲舒说:“谓一元者,大始也。……惟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也,……《春秋》变一谓之元。元,犹原也,其义以随天地终始也。……故人虽生天气,及奉天气者,不得与天元、本天元命而共违其所为也。故春正月者,承天地之所为也。”[2]69“正始”同时也必须“贵始”,“一者万物之所从始”就是把“一元”作为万物开始,进而可以“大始”“正本”。“变一为元”“正始”“贵始”就形成了从天道向人世的推扩动能。这非常类似于“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的易学宇宙观,其中的“春正月者,承天地之所为”“随天地终始”“不得与天元本、天元命而共违其所为”更说明无论是圣王、君主,还是庶民都必须“尊天行道”。
(三)天授君权
大一统强调了君权天授与受命于天的思想,二者是同一事情的两种不同的说法。董仲舒在《为人者天》《顺命》《深察名号》中对“受命”有三次解释。董仲舒用“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2]400来说明大一统的政治秩序源于上天的层层受命。这里的“一国”是指臣民,而君则泛指一切君主。董仲舒说的“人于天也,以道受命;其于人,以言受命”[2]559,区分了“以道受命”与“以言受命”两种方式,其中君主以下的臣民是以言受命,君主则以道受命。这就要求君主行天道,但即使普通人也可以“以道受命”,因此,董仲舒的天授君权并不反对天赋人权。
(四)天立三纲
董仲舒的受命论涉及三纲问题,董仲舒的“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基义》)被认为是基于阴阳论,但同样离不开受命论。受命论具有两个优势。
1. 神圣性。董仲舒说:“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虽谓受命于天亦可。”[2]559这就把天子-天、诸侯-天子、子-父、臣妾-君、妻-夫归结为单向的受命关系。这里的受命关系更具有“其尊皆天”的神圣性。
2. 相对性。董仲舒说:“天子不能奉天之命,则废而称公……妻不奉夫之命,则绝,夫不言及是也。”[2]559顺命就是顺天命,相对于传统三纲说的呆板,董仲舒的受命说并不是顽固的,天子、君、臣、夫、子、夫、妻如果不能行义务,都会被废黜。
(五)尊天祭天
董仲舒说:“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故号为天子者,宜视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号为诸侯者,宜谨视所候奉之天子也。”[2]368这样董仲舒把名号作为天意,进而要求天子、诸侯、大夫、士、民按照名号“守事从上”“各有分”,形成一个尊天体系。董仲舒甚至强化“天子祭天”的职责义务,提出:“天若不予是家,是家者安得立为天子?立为天子者,天予是家……故《春秋》凡讥郊,未尝讥君德不成于郊也。”[2]552董仲舒甚至强调“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2]541,“天子不可不祭天也,无异人之不可以不食父”[2]544。大一统要求以天正王,必然要求天子祭天,才能“屈君伸天”。祭祀成为大一统的必然要求。
总之,“尊天”被看作是大一统论的重要一环。董仲舒提出大一统,重点不在于维护政治大一统,而在于以天人感应、灾异谴告的“天道权威”来平衡、制约君主的政治权威,同时树立儒家的精神权威。
(六)天人感应
天子尊天、祭天、不得僭天的最后依据就是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灾异谴告等神秘性说法。董仲舒在《天人三策》就以此劝谏汉武帝。董仲舒说:“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11]2186灾异必然使得天道与人世之间处于“大一统”的系统之中,而不是“天变不足畏”的“天人相分”,董仲舒以“人副天数”说明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真实性。天人合一与“大一统”诚然是两套话语体系,但是按照“同类相动”原则,天地万物都处于一体之中,二程就以“万物一体”说明“天人并无二,不必言合”。由此可见,天人合一可以被解释为宇宙大一统。
(七)天有十端
董仲舒对天的解释最终形成了“十端”思想。董仲舒说:“天、地、阴、阳、木、火、土、金、水,九,与人而十者,天之数毕也。故数者至十而止,书者以十为终,皆取之此。圣人何其贵者?起于天,至于人而毕。”[2]646十端论包含了阴阳五行的内容,阴阳五行被看作是朴素唯物主义,构成了宇宙大一统论的基础。阴阳五行论论被用来阐释三纲、孝道,而五行论甚至导向五德终始,与通三统一起用来阐释正统性,建构政治大一统。
(八)万物之本
周易早就已经有“天地人”三才之道,董仲舒的十端论也概括了“天地人”三端,这就使得董仲舒的天论出现了狭义与广义、形下与形上的区别。此外,董仲舒还大量论述天地人三本系统,说:“何谓本?曰: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礼,不可一无也。”[2]193董仲舒甚至认为三者所产生的“孝悌”“衣食”“礼乐”如果“皆亡”,那么会导致“民如麋鹿,各从其欲,家自为俗。父不能使子,君不能使臣,虽有城郭,名曰虚邑”的社会大解体。宋儒就把孝悌等规范伦理直接看作是天理。
四、董仲舒大一统的政治维度
董仲舒大一统的政治维度包括法正统、通三统、以君为元、君为国主、尊君卑臣、屈伸之义等六个内容,用来处理君主与王道、今朝与前朝、君主与国家、君主与人民、君主与百官以及君、天、民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法正统
正统源自“受命于天”,落实为“王正月”“改正朔”。董仲舒说:“故汤受命而王,应天变夏作殷号,时正白统……文王受命而王,应天变殷作周号,时正赤统……故《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2]226-227笔者认为“时正黑(白、赤)统”意味着下文的“统三正”“正统正,其余皆正”。笔者进而认为董仲舒已经有了“正统”概念。董仲舒说:“三统之变,近夷遐方无有,生煞者独中国。而三代改正,必以三统天下。曰:三统、五端,化四方之本也……法天奉本,执端要以统天下,朝诸侯也……所以明乎天统之义也。其谓统三正者,曰:正者,正也,统致其气,万物皆应而正;统正,其余皆正。凡岁之要,在正月也。法正之道,正本而末应,正内而外应,动作举错,靡不变化随从,可谓法正也。”[2]237董仲舒对君主提出法天奉本的要求,这相当于“奉天法古”。天、本、古都意味着儒家的先王之道。君主能够法天奉本就具有了正当性、合法性。笔者借用董仲舒的“法本”之说,把“法天奉本”与“正统”结合起来,仿照“大一统”“通三统”的结构,以“法正统”标识此说。
(二)通三统
“圣王”获得统治权之后,需要“改制作科”来增强自己的正统合法性,其中包括: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作国号,迁宫邑,易官名,名相官、存二王后、爵三等、制礼作乐以奉天等诸多内容。正朔即“正月一日”。改正朔就是区别于前朝,根据建子、建丑、建寅依次更替“正月”,并分别对应黑统、白统、赤统。这种处理改朝换代的“儒术”就被称之为“通三统”。通三统是了强调本朝的正统性。董仲舒说:“文王受命而王,应天变殷作周号,时正赤统。亲殷故夏,绌虞谓之帝舜,以轩辕为黄帝,推神农以为九皇。”[2]227其根本世界观则是“天命转移”,通过承认与减杀前朝的正统性,进而使得自己获得正统性,从而维持“正统”的唯一性,即“一统性”。一统说明政权的唯一性,正统说明政权的正当性,通三统说明政权的历史继承性,三者最终趋向于建构政治合法性、合理性。
(三)以君为元
董仲舒说:“有非力之所能致而自至者,西狩获麟,受命之符是也。然后托乎《春秋》正不正之间,而明改制之义。一统乎天子。”[2]559“西狩获麟”被认为是孔子的“受命之符”,这就在“王鲁”的基础上增加“以《春秋》当新王”之说。“新王”即新的王道,但即使新王之道,也要求“一统乎天子”,这说明“君主”具有“一统天下”的权力。儒家显然肯定了君主现实政治,甚至以君为元。董仲舒说:“君人者,国之元,发言动作,万物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端也。”[2]193君为国本突出了“君”在大一统政治秩序中的重要地位,进而成为政治体制最终的决定性力量。
(四)君为国主
董仲舒说:“是故天执其道为万物主,君执其常为一国主。天不可以不刚,主不可以不坚。天不刚则列星乱其行,主不坚则邪臣乱其官”,“一国之君,其犹一体之心也。”[2]629-634董仲舒明确提出“君执其常为一国主”,这就肯定了“君主”制度,进而对“天”与“君”进行了比附,但主要是要求君主效法天道,乃至于要做到“隐居深宫”“至贵无与敌”“任群臣无所亲”“亲圣近贤”“布恩施惠”“无为致太平”。这就以君主为政治大一统的核心。
(五)尊君卑臣
儒家在现实政治中特别儒者要恪守君臣之间的尊卑关系,即“大义名分”,君臣关系甚至被称作“春秋大义”。董仲舒说:“是故《春秋》君不名恶,臣不名善,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臣之义比于地,故为人臣者,视地之事天也。”[2]415尊君卑臣、君尊臣卑是对阳尊阴卑的一种比附,尊君卑臣在《公羊传》中反映为“大夫不敌君”。
(六)屈伸之义
董仲舒说:“《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曰:缘民臣之心,一日不可无君;一日不可无君,而犹三年称子者,为君心之未当立也。此非以人随君耶?孝子之心,三年不当。三年不当而逾年即位者,与天数俱终始也。此非以君随天邪?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2]30这里的“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后被总结为“屈伸之义”,从而梳理天-君-民的关系。屈伸之义的核心是“君”,“屈伸之义”主要从孝道开始演绎,进而上升到普遍意义。“屈君而伸天”是指“逾年即位者,与天数俱终始也”。“屈民而伸君”是“一日不可无君”,是民众要以“君”为正。民间的婚嫁如果遇到国丧,要停止下来并要与新君一起守孝。屈民伸君已经成为秦汉大一统王朝的现实政治。
(七)华夷之辨
何休的三科九旨被徐彦概括为:“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又云: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二科六旨也。又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3]5从三科九旨与大一统的关系来看,三科九旨都在大一统的论域范围。其中的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属于“通三统”,而“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则是“三世异辞”,实现了尊君与“贬退”的平衡,实现了讥刺与避讳的平衡,可以看作是王道与尊君的二重维度。“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是董仲舒大一统论最为含蓄深远的引申义。首先,从正始维度而言,正万民、正四方必然涉及“华夏”“夷狄”的划分。其次,从王道维度而言,华夷之辨属于“王者无外”的一个组成部分。最后,从尊君、中和维度而言,夷狄属于君主政治、天地人大系统需要面对的内容。董仲舒本身也对夏夷关系进行了精彩的论述,把弑君、阴谋诡计、见利忘义看作是夷狄之行,甚至因为“晋伐鲜虞”“伐同姓”“不救鲁”而把晋国看作是“夷狄之行”。董仲舒甚至在分析泌之战的时候提出了“夷夏互变”的思想。董仲舒时代就进行着一场汉匈战争,随着匈奴的归附,汉朝成为一个农耕-游牧二元并存的王朝,这成为中国古代历史的常态。由夏夷一体、华夷之辨就会生成“国家统一”的趋势,晁天义甚至认为“大一统”流变为“大统一”,统一也就成为“大一统”最具有现代意义的维度。
五、董仲舒大一统论的王道维度
董仲舒把“王道”看作是社会、政治、历史的根本纲领,毕竟天道需要圣王解释,而君主政治需要按照儒家对王道的阐释进行实践。“王道”本身作为政治理想模型区别于君主现实政治,所以不应被归纳为政治大一统,而应归纳为思想大一统。
(一)王道贵始
王道是人道的根本正途。董仲舒说:“《春秋》何贵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道,王道也。王者,人之始也。王正则元气和顺、风雨时、景星见、黄龙下。王不正则上变天,贼气并见。”[2]103这里就勉励君主践行王道,把王道看作是根本,进而以王道为正为始,就可以获得“元气和顺、风雨时、景星见、黄龙下”的和谐景象,其中的原理则是“王道通三”。
(二)王道通三
王道统摄天地人三大系统。董仲舒说:“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是故王者唯天之施,施其时而成之,法其命而循之诸人,法其数而以起事,治其道而以出法,治其志而归之于仁。”[2]421这里依然以“王道”为核心论述大一统体系,进而贯通天地人,但这里的“王”不能直接理解为“君”,而是后世君主所要效法的“圣王”,因此,这里依然有“法古”之义。“通三”则意味着大一统是一个横贯天地人的宇宙系统。
(三)王修三本
董仲舒说:“是故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举矣。”[11]2194在君作为国家主权象征与“权源”的情况下,董仲舒提出了“修三本”的主张,即君主要谨承天意、明教化民、正法度别上下之序。
第一,其中的“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显然就是奉天的另外一种说法。董仲舒说:“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者也。”[2]381大一统论要围绕天、王的关系就是要王承天意,而天意的落实则是“成民之性”。
第二,其中的“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有“教以爱,使以忠”的爱民倾向。董仲舒说:“五帝三王之治天下,不敢有君民之心。什一而税。教以爱,使以忠,敬长老,亲亲而尊尊,不夺民时,使民不过岁三日。”[2]103这要求君主在经济上爱民,同时教以忠爱。与之相反,董仲舒分析了“不爱民之渐乃至于死亡,故言楚灵王晋厉公生弒于位,不仁之所致也”[2]186的后果。董仲舒说:“昔者晋灵公杀膳宰以淑饮食,弹大夫以娱其意,非不厚自爱也,然而不得为淑人者,不爱人也。质于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谓仁?仁者,爱人之名也。”[2]316李英华就把爱民作为大一统的重要维度之一,与奉天法古相并列。
第三,其中的“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有要求君主防欲修德之意。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也使用“修德”“修饬”“修身”“养其心”“养其德”“以义正我”“自省”“慎微”“贵志”等说法。董仲舒说:“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何谓也?夫五事者,人之所受命于天也,而王者所修而治民也。”[2]523周桂钿先生认为:“治国最根本最需要的在于道德,道德主要应该在于修身。德治应该有内外之分,对内当政者应该提高道德水平,以身作则。”[12]这说明“德主刑辅”需要“修德”作为基础。
(四)奉天法古
董仲舒说:“《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是故虽有巧手,弗循规矩,不能正方圆。虽有察耳,不吹六律,不能定五音。虽有知心,不览先王,不能平天下。然则先王之遗道,亦天下之规矩六律已。故圣者法天,贤者法圣,此其大数也。”[2]16这里明确地说了“圣者法天,贤者法圣”,圣就是“先王”。“圣人”“先贤”意味着儒家掌握了“其法”“其理”“其道”,成为天道的代言人。君主面对“天”“圣”“贤”的时候就加以尊崇、模仿。“天”代表天道、圣代表孔子、贤代表儒家,君主显然要面对天道、圣人、儒家三位一体的神圣联盟。
(五)推明孔氏
“法古”泛指一切古代圣王,但也可以确指圣人孔子。董仲舒说:“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天端,正王公之位,万物民之所欲,下明得失,起贤才,以待后圣。”[2]183这都说明了圣人的重要性。圣人隐约地出现在了“大一统秩序”之中。圣人可以探天端、正王公之位、明得失、起贤才、待后圣。这样就成为人君所要效法的对象。满足了“法古”之义。
孔子受命,进而成为至圣。董仲舒说:“有非力之所能致而自至者,西狩获麟,受命之符是也。”[2]180“西狩获麟”被认为是孔子的“受命之符”,而《春秋》因为记载孔子绝笔于西狩获麟,而被提升了在经典中的地位,甚至被看作是孔子应天作新王之意。
董仲舒说:“故天子命无常。唯命是德庆。故《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王鲁,尚黑,绌夏,亲周,故宋。”[2]229“新王”即新的王道,《春秋》新王、孔子受命,但由于其来非时,所以孔子只能作“素王”。孔子与《春秋》成为新王道的象征与载体,因此,后世学者要语王道,英雄要开新朝,都必须推明孔氏、尊孔崇儒。
六、结语
综上所述,“大一统”是一个包含三个维度,指向宇宙、政治、思想的复杂的理论体系。《吕氏春秋》《道德经》《周易》都已经蕴含了宇宙大一统的思想倾向。秦始皇统一中国与汉承秦制开创了政治大一统,当汉武帝、董仲舒对策之时,中国社会迫切需要建立起“思想大一统”。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与《春秋繁露》及时而又圆满地完成了这个使命,但就其理论落脚点而言,董仲舒《天人三策》表彰“六艺之科孔子之术”,涵盖“思想统一”“意识形态”“学术安排”多种层次,汉武帝时代的“立五经博士”“兴太学”“选儒为官”“以儒为臣”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建设作用。
董仲舒反对“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这种“学术不统一”状态。董仲舒的“上无以持一统”“下不知所守”描绘了一个“道术将为天下裂”的状态。董仲舒通过“思想融合”把其他思想流派纳入儒学之中,改造儒学,进而又要求“勿使并进”,走向“思想统一”,形成了一个理论闭环,“思想融合”与“思想统一”二者完美体现在董仲舒一人身上。
焦春鑫、杨玉仁认为:“汉武帝时期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意见,使中国古代的封建统治思想得到了初步的定型进而影响了后世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从构建‘大共同体本位’的角度出发,董仲舒所主张的儒家思想尤其是‘大一统’思想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3]董仲舒的说法促使汉武帝作出有利于儒学发展的学术安排、学术规范与学术统一,进而以学术安排引领意识形态。学术安排属于体制内的安排,而意识形态则属于社会层面。董仲舒并没有要求在社会层面消除诸子百家,而是要求在学术上“弃黄老、任孔子”,这又涉及有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聚讼。班固在《汉书·董仲舒传》中的话是:“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班固在《汉书·武帝纪》的最后“赞曰”里提到“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这就使“罢黜百家”得以出现于世。20 世纪初,易白沙在《新青年》撰写《孔子平议》使用了“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说法,为新文化运动树立了标靶。黄星星就把这场思想运动梳理为三个阶段,强调了“改革开放以后,诸多学者就董仲舒对策本事,汉武帝学术政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概念出处等展开论辩和诠释,让部分问题得到进一步澄清”[14],从而使得董仲舒大一统论回到儒学主导、思想融合的正确轨道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