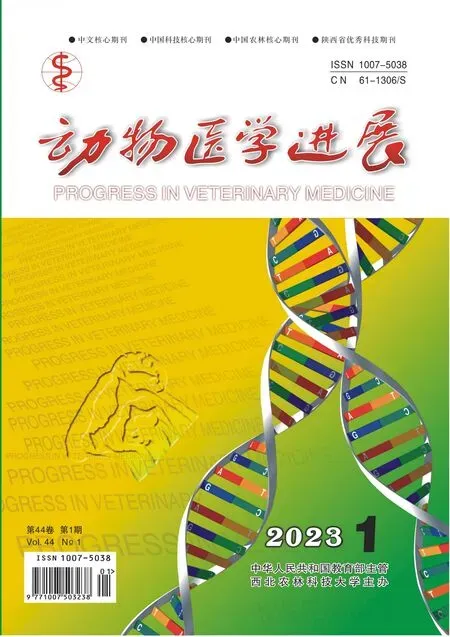伴侣动物源细菌质粒介导的黏菌素耐药机制研究进展
2023-03-10唐欣悦周煜博张玉珠郑慧华黄荣磊杜崇涛谢光洪
唐欣悦,周煜博,张玉珠,郑慧华,黄荣磊,于 超,杜崇涛,谢光洪
(吉林大学动物医学学院,吉林长春 130062)
抗菌药物是治疗伴侣动物感染性细菌性疾病的重要工具,例如犬和猫伤口感染、呼吸系统感染和泌尿道感染等都是临床中常见的需用抗菌药物治疗的疾病,为了控制这些细菌性疾病或并发症,不合理或频繁用药易导致细菌产生耐药性甚至多重耐药性。一旦抗菌药物效力丧失,将会严重影响动物的健康和福利[1]。
黏菌素是治疗多重耐药(multidrug-resistance,MDR)革兰氏阴性细菌,尤其是碳青霉烯类耐药肠杆菌科引起感染的最后手段。目前,耐黏菌素革兰氏阴性菌已在犬、猫和人类分离的肠杆菌科中出现,且不同于已经发现的多黏菌素耐药机制,质粒介导的新型移动黏菌素抗性(mobile colistin resistance,mcr)基因可以随着质粒的接合转移在不同细菌中水平传播,多种细菌及动物宿主均能携带mcr基因[2]。
随着现代社会中伴侣动物的大量增加,它们的社会角色也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养宠人士将宠物视为“朋友”或“家庭成员”,对宠物情感陪伴的需求加大。与抗生素耐药性和伴侣动物的耐药性转移风险相关的一个独特方面是它们与人类的密切接触,这增加了宠物与人之间细菌传递的可能性,为耐药细菌的种间传播创造了机会,伴侣动物中有耐药性细菌的出现成为了一个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3]。本文介绍了当前黏菌素的使用情况,耐药和传播机制及耐药菌在伴侣动物与人之间的流行情况等,这对伴侣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1 黏菌素使用情况
多黏菌素是一类非核糖体合成的阳离子、环肽类抗生素,在已知的5种亚型A、B、C、D、E中,广泛用于动物生产实践的为多黏菌素E和多黏菌素B[4]。其中多黏菌素B的抗菌活性最强,最初被发现是由革兰氏阳性菌多黏菌芽孢杆菌产生的。多黏菌素E又叫做黏菌素,分子质量1 750 u,由一个环七肽组成,其N端有一个脂肪酸尾酰化的三肽链N端脂肪酰基片段的疏水性是固有毒性的主要原因,并对黏菌素的抗菌活性产生重大影响[5]。市面上有两种不同形式的黏菌素,即口服和局部使用的硫酸黏菌素和用于肠外及气雾剂治疗的甲基磺酸黏杆菌素(colistin methanesulfonate,CMS),两种形式均可吸入。黏菌素(通常用作硫酸盐)是一种聚阳离子,而黏菌酯(用作钠盐)是一种生理pH下的聚阴离子。黏菌素能作为饲料添加剂来促进动物生长或治疗由肠杆菌科细菌引起的疾病[6]。
黏菌素潜在的肾毒性和神经毒性阻碍了其广泛引入常规临床治疗,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耐多药革兰氏阴性菌(尤其是铜绿假单胞菌、鲍曼不动杆菌和肺炎克雷伯氏菌)的流行以及新型抗生素的缺乏,人们重新对黏菌素产生了兴趣[7]。当使用b-内酰胺、氨基糖苷或喹诺酮类药物无效时,多黏菌素,尤其是黏菌素,因为它具有快速杀灭细菌、窄谱活性以及相关的耐药性发展缓慢等优点,仍然是治疗耐多药革兰氏阴性超级病菌感染的最后手段。但随着黏菌素在临床的大量使用,已经发现了对黏菌素和碳青霉烯类抗生素同时耐药的细菌[8]。
2 黏菌素潜在耐药机制
2.1 黏菌素传统耐药机制
目前所报道的关于黏菌素的固有耐药性,主要与通过多种途径进行的脂多糖修饰有关。最常见的为外膜孔蛋白的特异性修饰和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LPS)整体负电荷的减少,其次是外排泵系统的过度表达和胶囊多糖的形成。
革兰氏阴性菌对黏菌素的耐药性最常见的原因是由于PhoPQ和PmrAB(两种双组分调节系统)的变化引起的脂多糖重塑,导致与细菌外膜的结合减少,从而导致阴离子脂质A,停止或减少与不同机制的初始交互[9]。pmr位点是一个自动调节的双组分信号转导系统,除了一个传感器激酶和响应调节器外,还包括一个乙醇胺转移酶。乙醇胺转移酶通过在LPS的脂质A组分中添加乙醇胺部分,有助于提高黏菌素的耐药性,从而减少细菌膜的负电荷,减少带正电荷的黏菌素的结合[10]。在许多革兰氏阴性细菌中,获得性多黏菌素耐药性通常是通过添加4-氨基-4-脱氧-l-阿拉伯糖和或磷酸乙醇胺(phosphoethanolamine,PetN)来替代脂质A来介导的。这种作用需要由pmrC介导的ugd和pbg位点和乙醇胺的产物,因此这些修饰去除负电荷,降低了LPS的亲和力,从而增加了对黏菌素的抗性[11]。
激活外排泵或外排泵调节剂如敏感抗菌肽(sensitivity to antimicrobial peptides,Sap)蛋白、BrlR、KpnEF或AcrAB-TolC复合物会导致对黏菌素的耐药性增加。Sap蛋白由sapABCDF操纵子编码的5个蛋白质组成,在肠道沙门氏菌血清型鼠伤寒杆菌中,已经证明Sap蛋白对一些青霉肽和鱼精蛋白的耐药性是必要的,但它们对防御素无效。然而,该操纵子似乎在多黏菌素耐药性中发挥了作用,因为其突变导致奇异疟原虫突变体对多黏菌素B的易感性增加[12]。在鲍曼不动杆菌中,18个假定的外排转运体被氯化钠的生理水平上调,并导致对多黏菌素的耐受性增加,包括一种名为CarO的孔蛋白[13]。使用外排泵抑制剂,特别是羰基氰化物3-氯苯肼(carbonyl cyanide 3-chlorophenylhydrazone,CCCP),表明外排泵确实对肺炎克雷伯氏菌、铜绿假单胞菌、鲍曼不动菌和嗜麦芽窄营养单胞菌的黏菌素耐药有影响,进一步支持外排泵系统参与黏菌素耐药[14]。
胶囊在对黏菌素的抗性中也发挥了作用。在空肠弯曲菌中,低脂糖中修饰细胞表面结构的镍碳糖唾液酸的截断增加了对多黏菌素B的敏感性。同时,还观察到胶囊中单层的肺炎克雷伯氏菌会比多层的菌株对黏菌素的耐药性弱一些。此外,肺炎链球菌、肺炎克雷伯氏菌或铜绿假单胞菌对未封装的肺炎克雷伯氏菌、大肠埃希氏菌或铜绿假单胞菌的胶囊表达导致对多黏菌素B的耐药性增加[15]。最后,一些调控胶囊形成的调控因子,如Cpx(结合菌毛表达)和Rcs(胶囊合成调控因子),似乎通过激活Cpx的外排泵KpnEF或调节PhoPQTCS参与黏菌素耐药[16]。
2.2 质粒介导的黏菌素新型耐药机制
各种细菌对黏菌素具有内在的抗性,而获得性抗性是由于染色体突变或质粒上基因的获得而产生的耐药性。2016年我国学者在一株大肠埃希菌(SHP45)中首次发现了质粒介导的黏菌素耐药基因mcr-1[17],继而世界上40多个国家发现了这种携带耐药性质粒的菌株传播,随后陆陆续续在肠杆菌科细菌中发现其他新型耐药基因。目前,全球共发现有10种质粒介导的黏菌素耐药基因,分别命名为mcr-1 、mcr-2、mcr-3、mcr-4、mcr-5、mcr-6、mcr-7、mcr-8、mcr-9和mcr-10。
mcr-1基因全长为1 626 bp,G+C含量49%,位于Incl2型质粒上。通过预测,其编码的产物mcr-1蛋白与类芽孢杆菌编码的PetN转移酶的同源性达63%,mcr-1可以将PetN添加至LPS 的脂质A部分,使LPS的负电荷减少,从而减弱黏菌素与细菌的结合作用,导致细菌对黏菌素耐药[18]。mcr-1耐药基因主要存在大肠埃希菌中,但最近携带mcr-1耐药基因的肺炎克雷伯氏菌也出现暴发的趋势。目前在Incl2、IncHI1、IncHl2、IncX4、IncFI、IncFII、IncK和IncP等多种肠杆菌质粒中都检测出mcr-1基因。mcr-2基因全长为1 617 bp,位于lncX4型质粒上,与mcr-1的核苷酸序列一致性为76.8%。其上、下游基因环境也与mcr-l相似,mcr-2上游有移动元件IS1595超家族,下游有297 bp 的开放阅读框(open reading frames,ORFs),编码磷脂酸磷酸酶(phosphatidate phosphatase,PAP)膜结合脂质磷酸酶,携带mcr-2的 pKP37-BE质粒不携带其他耐药基因。mcr-3基因全长1 626 bp,与mcr-1和mcr-2的核苷酸同源性较低,仅有45.0%和47.0%。该基因位于IncHI2类型的质粒pWJ 1上。mcr-3上游含有截短的产气单胞菌特有的转座子元件TnAs[19]。通过结构域的互换以及序列分析证实,mcr-1和mcr-2同属同一个基因家族,而且mcr-2的跨膜区域比mcr-1的跨膜结构域更有助于细菌对多黏菌素耐药。进化分析显示mcr-1、mcr-2可能来源于Paenibacillus基因组上的磷酸乙醇转移酶[20]。相关研究报道,mcr-3可能也来源于Aeromonas基因组上的磷酸乙醇胺转移酶,因为携带mcr-3基因质粒的相关转座元件与Aeromonas基因组上的磷酸乙醇胺转移酶的区域有高度的同源性,这表明质粒介导的多黏菌素耐药基因起源的多样性[21]。
mcr-4基因全长为1 626 bp,位于ColE10型质粒pmcr上,含有移动元件IS5,其编码的蛋白mcr-4 的氨基酸序列与mcr-1、mcr-2和mcr-3的同源性分别为34.0%、35.0%和49.0%[22]。从结构方面上讲,mcr-4的空间结构与研究较为清楚的mcr-1结构相似,它们都有N端的跨膜结构域和C端的催化结构域以及两个结构域的连接区域。从进化方面讲,mcr-4和mcr-1在进化树上面形成了不同的进化分支,mcr-4与mcr-1的结构域互换试验也证明二者不能发生互换[23]。但是与磷酸乙醇胺脂质A转移酶(phosphoethanolamine-lipid A transferase,EptA)不同,mcr-1和mcr-4可以赋予敏感菌株大肠埃希氏菌耐多耐菌素的水平达到16 μg/mL,这表明,虽然mcr-1和mcr-4进化和结构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是具有相似的功能性。根据流式细胞结果和激光共聚焦显微结果表明,mcr-4蛋白可以减少多黏菌素对宿主菌大肠埃希氏菌产生的活性氧化物(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化学拯救试验表明,铁螯合剂、半胱氨酸可以减少芬顿反应产生的自由基[24]。
mcr-5基因全长为1 644 bp,是Tn3家族转座子的一部分,位于多拷贝ColE型质粒上。mcr-5基因编码的EptA与mcr-1、mcr-2、mcr-3、mcr-4的同源性分别为36.1%、35.3%、34.7%和33.7%[25]。mcr-6基因最初被认为是来自莫拉氏菌属的mcr-2的变种mcr-2.2,后更名为mcr-6.1,该基因全长1 617 bp,与最初发现的来自大肠埃希氏菌的mcr-2相比,有65个氨基酸不一致,同源性为87.9%,与来自莫拉氏菌属的另一个变种mcr-2.1编码的蛋白mcr-2.1相比,有66个氨基酸不一致,氨基酸同源性为87.8%。由mcr-6.1(mcr-2.2)编码的EptA 与mcr-1和mcr-2的同源性为62%~64%[26]。mcr-7基因全长1 620 bp,定位于Incl2型质粒(pSC20141012) 上,该质粒上还同时携带有blaCTX-M-55耐药基因。在mcr-7侧翼序列中,没有发现移动原件,mcr-7.1编码的蛋白含有539个氨基酸,被注释为EptA[27]。mcr-7与之前发现的mcr-1、mcr-2、mcr-3、mcr-4、mcr-5、mcr-6相比,其氨基酸同源性分别为35%、34%、70%、45%、36%和 33%[27]。mcr-8基因全长为1 698 bp,位于IncFII类型的质粒上,该序列与mcr-3对应区域的核苷酸序列同源性为50.23%,该基因编码的氨基酸序列与mcr-1.mcr-2、mcr-3、mcr-4、mcr-5、mcr-6和mcr-7的同源性分别为31.1%、30.3%、40.0%、37.9%、33.59%、30.49%和37.5%[28]。
据统计,mcr-1.1的患病率下降,相比之下,在2017年-2021年收集的许多分离株中均观察到mcr-9.1和mcr-10.1的出现[29]。mcr-9的氨基酸序列从2010年华盛顿州一名人类患者分离的MDR肠炎沙门氏菌血清型鼠伤寒(Serovartyphimurium)菌株中检测到,与mcr-3的氨基酸同源性达到64.5%。9个mcr同源物(mcr-1至9)表明mcr-9、mcr-3、mcr-4和mcr-7在结构水平上具有高度的相似性[30]。mcr-10在中国临床肠杆菌090065中提取的非结合IncFIA(HI1)质粒中被发现,它与mcr-9的核苷酸同源性为79.69%,并且黏菌素最小抑菌浓度(minimum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MIC)增加了4倍(从1 mg/L~4 mg/L)。通过对基因库的筛选,在四大洲国家的各种肠杆菌科物种中发现了mcr-10,这表明该基因已广泛传播[31]。mcr-10显示了79.04%至83.67%的氨基酸同一性和高度保守的预测蛋白质结构,具有不同Buttiauxella物种的染色体编码的mcr样磷酸乙醇胺转移酶(此处指定为mcr-B)。因此,mcr-10、mcr-9和mcr-B蛋白可能起源于一个共同的祖先。基因库中最早匹配mcr-10的是1株弗氏柠檬酸杆菌临床菌株的质粒pOZ172,该菌株于1998年在中国广州发现,这表明数十年来,mcr-10一直由肠杆菌科的质粒动员[32]。
3 黏菌素耐药菌流行现状
动物的粪便一方面残留有抗菌药物或其活性代谢产物,同时也含有丰富的耐药菌或耐药基因。目前,mcr-1已在6大洲,30多个国家被发现,这表明mcr-1已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流行。在我国,已有25个省(自治区)分离到了携带有mcr-1的细菌。2016年,Liu Y Y等[17]在中国动物、食品和患者的大肠埃希氏菌分离株中全球范围内首次发现了一个可转移质粒介导的黏菌素耐药基因mcr-1。此外,在患者的肺炎克雷伯氏菌中发现了mcr-1,水平基因转移代表了黏菌素耐药性的一种范式转变,在此之前,它只被发现是由染色体突变介导的,从而通过垂直传播来实现。此后陆续报道出质粒介导的新型黏菌素耐药基因,近年来,在尼日利亚[33]、韩国[34]、英国[35]等国家的犬、猫和人分离株中都得到mcr阳性菌株且为MDR。2020年,Moon D C等[34]在韩国首次从伴侣动物粪便和尿液样本中回收的大肠埃希氏菌分离株中存在移动黏菌素耐药基因mcr-1,且携带mcr-1的质粒与来自韩国患者的质粒密切相关。研究显示,在299个家庭(犬及其主人)的直肠拭子中检测到携带mcr-1和blaCTX-M的患病率分别为2.7%和5.3%,同时发现犬和它们的主人之间mcr-1的携带存在显著关联,并分离出相同的mcr-1阳性大肠埃希氏菌(mcr-1-positveEscherichiacoli,mcrPEC)或blactx-m阳性大肠埃希氏菌(bla CTX-M-positiveE.coli,CTX-MPEC)菌株,耐药细菌所表现出的共定植潜力,正可能是耐药基因传播的风险。而前3个月抗生素的使用与犬的blaCTX-M携带有关,只观察到1只犬和主人携带相同的CTX-MPEC。虽然在一个家族中流行相同的菌株非常罕见,但世界范围内拥有足够数量的犬,这种威胁在宠物和人类中应当受到重视[36]。自从质粒介导的耐药基因mcr-1被发现后,陆续有mcr-2~mcr-10基因被报道,2019年在罗根冈肠杆菌临床菌株的IncFIA质粒上发现与mcr-9的核苷酸同源性最高为79.69%的新型质粒携带的黏菌素耐药基因mcr-10[31]。这些耐药基因的突变率很高,并且可在菌株间传播,引起大范围的流行。
4 展望
耐药细菌不断出现在环境中,同伴动物和几种耐多药生物体在伴侣动物和人类之间共存。然而,这些细菌在动物和人类之间传递、转移的方向仍然难以确定,在伴侣动物中使用抗菌药物意味着选择、隐藏和传播抗菌药物耐药性的可能性,这对公众健康构成潜在风险。
随着对先进治疗的需求不断增加,加上耐多药细菌的传播,未来在兽医学中可能需要新的抗菌剂来解决耐药细菌和耐药基因向人类传播的有关问题。微生物危害可能直接或间接对人类健康造成不利影响,对人类健康的直接危害定义为从动物传播给人类并导致人类疾病(人兽共患病)的抗药性细菌,间接危害是可能从伴侣动物传播给动物的抗性基因对公众健康的影响。而动物源性抗生素耐药性向人类的传播是复杂的,需要进一步研究。